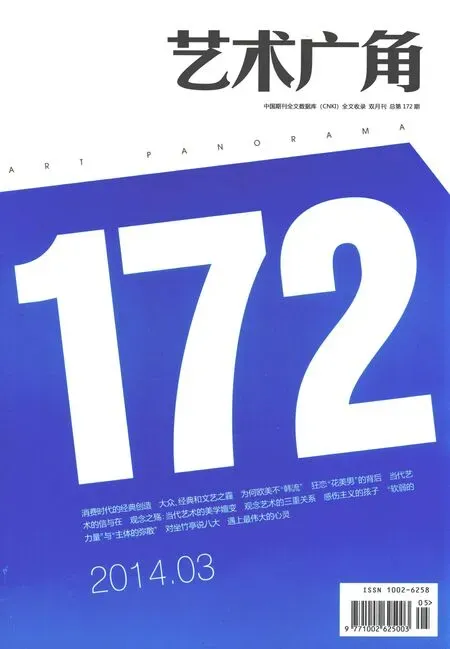遇上最伟大的心灵
2014-03-12李浩
李 浩
一
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经典小说,经典小说又应具有怎样的品质?经典,字典上给出的定义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作品。典范性,就是要求这部小说是某一艺术方式、叙事类型的集大成者,有代表性,有高度,并且达至基本的完美;而权威性,则强调的是它有广泛的认同,有让人信服、敬重的艺术力量。
有时,所谓的权威性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所以,作家博尔赫斯关于经典有过这样的定义,他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长期以来”“世世代代”,它强调的是检验经典的时间长度。我们不少的学者、作家在什么是经典上与博尔赫斯所持的是同一种态度,用作家马原的话来说,我们更应当读的是“死人的书”,是那些已经做古的、和当下的时间有一定距离的、经过岁月淘洗沉淀之后留下来的小说文本——它们会更让我们受益。在对经典的定义中,博尔赫斯强调的标准是读者的阅读,他说读者应对经典作品有一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我认为这点非常值得重视,值得强调。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被命名为“浅阅读”和“读图”的时代。这份获益,也许不是门前车马喧,不是粮食、金钱、房屋和美人,但它对你认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是有益的,对你获得对生活的艺术感觉是有益的,对你的心灵安妥是有益的,对你提高文学悟性、敏锐艺术感觉、提高鉴赏能力,进而成长为一个作家是有益的。我们为什么要长期以来、世世代代抱着“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来阅读这些经典?当然是它的典范性和权威性。
在对时间跨度的强调中我们可能会生出某种忐忑的疑问:时间长度是对经典权威性检验的最终标准么?而那些被后世认为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它刚刚问世的年岁中,难道就不应当获得广泛阅读和“权威性”的敬重?如果我们不从阅读者这样的外部考虑,而专注于小说文本本身,那,经典是不是应当从它出生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具备着经典品质?那,经典品质又应具有一种怎样的标准,可以让我们在这些作品一出现的时候就从中嗅到它所弥漫着的“经典气息”,而不错过它和漠视它?
意塔洛·卡尔维诺在那篇著名的《为什么读经典》的文章里,提出了关于经典的十四条定义,像“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等等,在这里,我不准备枚举这十四条定义,而是选择其中我认为较为重要的、也更能确立标准的几条。他说,“一部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为什么在重读的时候依然会有“初读”的感觉?因为,伟大的作品永远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每次的重读,都会有新的启发,新的发现,新的风景。那,为什么说初读的时候也好像是在重温?因为经典性,因为经典性的标准,因为,一部经典的作品,具备某种“前人经验的综合性”,因为它在任何一个时代似乎都具有现实针对性,是对我们人性某些缺点的深度指认。对此,卡尔维诺有过阐释,“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如何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会听到如此的评价:某某某这个人,就是一个猛张飞。某某某这个人,小诸葛。某某某,活脱脱是一个林妹妹。张飞,诸葛亮,林黛玉,这些经典文学中创造的形象成为一种性格标识,一方面说明着文学形象的魅力,也恰是印证经典的恒久:它早早就是“旧的”,它又从来都是新的。在我们“经典小说研究”一课中,我们会凭借经典小说的这些应有标准从浩渺的文学作品中将它们选择出来。
在第九条,卡尔维诺又如此定义:“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这一点也同样重要,我想我们不止一次地听人谈及《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变形记》《老人与海》《安娜·卡列妮娜》《呼啸山庄》,我们对其中的一些故事也极为熟悉,单单是故事上已经不构成对我们的阅读吸引,但当我们实际去读它们,真的去阅读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你会在其中发现贮藏在其中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这些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恰就贮藏在你已经熟悉的故事中,从那些道听途说中已经获得的所谓经验中。之所以我们强调这一条,是对同学们的提醒:对于经典作品,我们仅有道听途说的间接经验是不够的,仅依仗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你需要耐下心来,用那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认真阅读,从中领略。
在确认了经典的基本标准、确认了我们小说研究的选择标准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得到回答,那就是,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要对经典小说进行研究?我想,一是为我们的审美确定标尺,让我们能更好地领略文学的内在魅力;二是我们借助这些经典作品,可以更好地认知世界,认知人生和我们自己,经典可以让我们和我们的思考变得深邃;三是经典的典范性会给我们的当下写作、当下阅读构成影响,形成启发。斯特劳斯说:“今人已无法与古人直接交谈,因而不能通过聆听循循善诱的言说,来接受其教诲和点拨;同时人们也不知道,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是否还能产生他所说的‘最伟大的心灵’,即使能产生,又有几人能幸运地与之在课堂或现实中相遇。好在‘最伟大的心灵’的言说是向今人敞开的,人们可以也只能与那些心灵在其智慧的结晶——‘伟大的书’中相遇”。我们将阅读那些伟大的书,实现大的心灵相遇。
二
研读经典,不是小说史论。北大吴晓冬教授曾说过,“传统的小说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小说内容的研究,如主题、时代背景、人物类型等,着重点在于小说写了什么,并且进一步追问小说的社会文化根源,但很少关注小说中的这一切是怎么被小说家写出来的。”——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当然重要,应当足够重视,但我试想从另外的角度来完成,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分析留给传统小说研究很少关注的那一点,即:小说中的这一切是怎么被小说家写出来的。我认为,这一点可能对我们学习写作、理解写作、剖析写作更有益,更有收效。从文本的内部出发,追问小说中的一切是如何被小说家写出来的,进而继续追问如果把同样的主题、内容交给我们来处理我们应怎么办,可以怎么办,这是重点——我承认,这具有相当的难度,而且较少同质的资料、成果可以借鉴。然而我愿意在难度中、在探索中行进,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应有之意。
在这里,我想有几点需要强调。
一是,“经典小说研究”应从文本内部出发,专注于小说的生成和生成技巧,专注于细节和细节表达,专注于对经典小说“经典性”的解剖,专注于思想和内容互融的点,通过“案例剖析”探寻“小说中的这一切是怎么被小说家写出来的”。
从文本内部出发对小说进行解剖,这一想法受到了电影教学的启发,受到了徐贵祥主任“文学创作案例教学”的启发。在鲁院上学期间,一位从事电影文学创作的同学告诉我,他说,一个电影导演如何看电影?一,他要先按正常速度看一遍这部电影,这时他基本和我们普通观众一样,了解故事,跟着电影叙事的节奏走,让自己尽可能地融入。但在此之后,他需要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地去看,看什么?他会在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观看中放置不同的关注,譬如第二遍他看剪辑,那故事叙述就要忽略掉,灯光忽略掉,人物命运等一切都忽略掉,只看它是如何剪的,处理的方式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而它没用到,为什么。第三次,他就专注于灯光,看这部电影中光是如何用的,光源位置和达到的效果。第四次,他可能会只关心音乐……是的,这一过程尤其是后面的过程显得有些枯燥,甚至多少是种折磨——但这一训练必不可少,而且完全会事半功倍。如此训练三十部电影四十部电影之后,那位导演再看电影,基本可以在最初的观看中把所有的要素、要关注的都一次完成,而不必再第二遍第三遍第N遍地反复看了。他的这一说法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突然想到,这一方法完全可用在小说的鉴赏解读上。事实上,许多作家就是如此做的,一直这样做,只是可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而已。上次徐贵祥主任“案例教学”的第一课讲的是莫言的短篇小说《倒立》,我很看重那种众人一起的参与感,很看重大家各抒己见的争论,有些问题,看法,很可能在那种争论中得以明晰、确认、渗透和修正,很可能让我们从“他人的角度”中发现自己忽略的却也相对重要的东西。在那里,我向同学们提出过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一、写同学聚会,我们往往会把笔墨集中于聚会现场的喧哗、大家今昔的比较上,它容易引发感慨也颇具意味,而莫言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却点到为止,使用着简笔,和他泥沙俱下、恣肆汹涌的固有风格都有些不相称,为什么?这个不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二、有同学提出这个“倒立”形式感太强,有些溢出生活逻辑,尽管对此我小有保留,但我们是否可以设置一个相似的、又不那么强烈的细节,同时让它的力量感不但不会减弱还会有所增强?三、如果我们也写一篇同学聚会的文字,在莫言的《倒立》之后,我们可以如何去做,既有风生水起的故事,又有丰富细微的描述,同时又与已有的小说有显著区别?……由此,我想,在这一课,在经典小说研究这一课中,我们不仅要准备耳朵更要准备下问题,并致力思考属于自己的解决方法。小说讲述了什么、是如何讲述的、它的效果又是如何达到的、它的新颖性又在哪儿等基本问题是首先要解答的,在此之后,我们似乎还可以追问:这个具有典范性的作品它的典范性在哪儿,我们在自己的写作中如何学习和借鉴?同类的题材、同类的内容,如果交给我们来做,我们将会如何完成,和这篇经典的小说相比,有哪些是可能的长处而哪些又是我们的不及?我能否将这篇经典文本的方法技巧运用到我的写作中,而完全变成是我的、我个人的?
二是,作家角度。我们的经典小说研究本质上是一个写作者对文学文本的看法、解读,在这里我们也许更强调经验和技艺的成分。我想它或许与经典的、惯常的学院批评、专业批评构成某种互补。
传统学院研究注重理论、阐释和知识,这是它的侧重点,而具体针对性、关注文学创作问题则是我们这一经典小说研究的侧重。强调鉴赏力和审美,强调艺术感觉的培养,是我们所更为关注的,而这,恰是一般传统学院研究所忽略的。1977年,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中曾强调,“文学包含许多科学知识”,“因为一切学科都出现在文学的纪念碑中”,“但是由于本身这种真正百科全书式的特别,文学使这些知识产生了变化,它既未专注于某一知识,又未使其偶像化;它赋予知识以间接的地位,而这种间接性正是文学的珍贵的所在”——这种珍贵的“间接性”也正是我们这一课所要着力探寻的。罗兰·巴尔特接着说,“科学(或者说我们的传统学院研究)是概念性的,生命却是精微的,对我们来说文学的重要性正在于调整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我很认可这种说法。我也愿在我们这一课中,探寻和解析小说、小说家是如何调整的,我们还可以如何进一步调整、完善,或者开创。
学者蒂博代把作家批评称为“大师的批评”或者“作坊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应当是恰应的。站在作家的角度,经典小说研究确有“作坊批评”的意味——它是来自文学最深处的,是由内及外的。这种研究方式,更多的,可能是出于作家对作品的辩护和对自我文学观的捍卫,对文学创作规律、知识、智慧的捍卫。蒂博代以雨果《论莎士比亚》为例,认为作家雨果在评论另一位作家莎士比亚的时候,是以一种“体验其创造”的方式来进行批评的:“他体验这种创造如同神秘主义者体验上帝,一个哲学家体验存在一样。”我愿意体验经典小说的创造,体验它让我们两块肩胛骨之间骨骼震颤的那种艺术美妙。
我不否认也难以否认,站在写作者的角度的小说研究有其偏颇之处,有它显见的弱点。第一点就是它缺乏体系感,缺乏一种“史脉”的连贯性。作家的小说研究往往是随意的,偶发的,或者有现实针对的,而缺少理论自觉。在以往的作家批评中,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纯粹是出自于对圣伯夫的保守主义的不满而做出的,列夫·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更多的是出于对自我文学趣味的坚持和捍卫,福楼拜在与乔治·桑的通信中谈论自己的创作主张完全是借与这位纯粹的浪漫主义作家的辩论来阐述自己的现实主义主张,博尔赫斯、昆德拉、库切、王安忆、马原等人的批评和随笔中也无法见到“建立理论体系”的诉求和自觉——尽管在大量的、有针对性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家的背后还是有一个体系存在的,可它却是隐藏的、不确定的,甚至有着相互的否定。第二点,作家的文学批评主观性较强,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带有某种个人化的艺术偏见。列夫·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中当然有显见的艺术偏见,甚至带有隐秘的、故意贬抑的情绪;福楼拜对现实主义的维护中不自觉地对其他方式方法进行着贬低;雨果的《论莎士比亚》,“作为艺术家,他对艺术做出了解释;作为天才,他对天才做出了天才的解释;作为有偏见的人,他的解释也带有偏见。”(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
作为作家、写作者,我觉得我们应当尊重其中的偏见,这种偏见,恰也是文学魅力的部分。当然我也希望我们能合理地纠正某些偏见,达到李健吾先生所说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
三是,我们面对经典小说,鉴赏是重要的,剖析是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那些经典小说看成是“活体”,它的新颖、创见和典范是可以作用于我们的写作的,它有一条脉络延绵到我们当下写作中。我们在捍卫经典小说权威性的同时,也一定要思考:这篇小说如果交给我来写,我会写成什么样子?这句话,这个词,如果交给我来写,我会写成什么样子?这个段落、这个细节我不是很喜欢,那好,如果交给我来写,我会将它写成什么样子?在此之后,也许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要是我利用其中某些核心元素,而写一篇完全不同的小说,并且艺术魅力不减,甚至有更多的丰富,那我应当如何去做?我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工作期间,曾参与过一个栏目的编辑工作,那个栏目叫“文本典藏”——就是请著名作家、批评家自己选择一篇自己喜欢的短篇进行点评,并学习古典文人的作法,批眉批。我从那些作家的眉批中获得了许多的启发和教益,也让我意识到我和他们在关注点上的不同,让我意识到我作为一个作家需要自我修正的某些问题,让我意识到我和他和他们之间哪些不同可以固化变成我写作上的个人标识。我希望我们同学在这一课中能够养成一个作眉批的习惯,它会让你终生受益。
三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经典作品?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才是恰当的?我们如何在这些经典作品的学习中补益我们自己的创作,丰富和确立自己的审美?我想到两个成语,它们都出现在河北邯郸,一个是“胡服骑射”,一个是“邯郸学步”。这两个成语不需要再做解释,它们联在一起,就是我们面对经典应有的学习态度:“胡服骑射”,是拿来主义的,我们要敞开自己,学习他者的长处,不断修正自己,以适应变化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文学的需要;“邯郸学步”,则是要我们在拿来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什么是自己的、本质的,它是根,是固有,所有的拿来都必须作用于你自己的、本质的固有,在对经典的学习中要始终记得什么才是自己的,必须坚持的,和他者区别的。否则,他人的没有学好,自己的也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