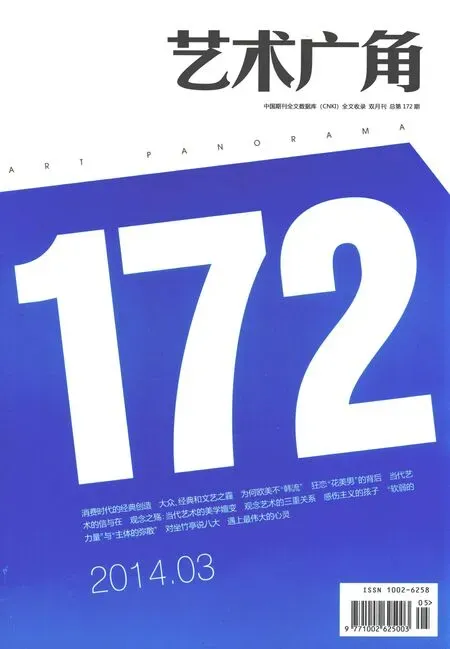“软弱的力量”与“主体的弥散”
——从崔健《无能的力量》到《给你一点颜色》
2014-03-12王翔
王翔
“软弱的力量”与“主体的弥散”
——从崔健《无能的力量》到《给你一点颜色》
王翔
摇滚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一个退潮期。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世界”的追求被“发展主义”取代。从60年代就开始累积起来的“反抗”“叛逆”这些支持着摇滚的能量,在青年中迅速衰退。摇滚失去了统摄青年的力量,渐渐成为流行音乐的一个类型。在大势之下,崔健没有做出面向流行音乐的转型。流行音乐强调旋律,强调让人过耳不忘、优美、好听,以求更大的受众。而90年代的崔健反而弱化了旋律,让节奏占了主角。节奏对旋律的破坏,本身就是摇滚的动力[1]。“节奏与节拍是摇滚的核心。摇滚经常被描绘为非洲节奏怒吼穿过欧洲式和声,激活了欧洲的节拍,直到它失去自我”[2]。律动感,模糊的咬字,一种喉咙和胸腔的共振,发出的铿锵有力的、阳刚的声音,形成了崔健的风格:在爵士的律动感里的说唱。这种演唱的风格营造出来的感觉是,崔健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思想”冲破了旋律,形成了一种颗粒感极强的“说唱”。崔健的咬字很模糊,这和90年代强调“字正腔圆”的流行音乐是不同的[3]。崔健有很多话想说,但听众不一定能听清他的话,听见的是一个律动的、阳刚的声音,被包裹在鼓点、吉他和其他配器中。
在音乐上,90年代的崔健与流行音乐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他的旋律比起他80年代的音乐来还要更弱。崔健这么解释他在音乐上的选择,“我为什么喜欢hip -hop、freestyle,因为它们是底层的。但现在有一个矛盾,就是在中国没有底层文化,这东西是我说的矛盾。中国没有成气候的底层文化,在美国有,我太喜欢这种音乐了,造成我故意用这种音乐代表底层,实际上不是。可是,说到中国的底层文化,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强的底层文化,说简单点就是外地人在北京。当时我想,谁要真正把这东西唱出来,你才意识到你的两只脚是站在大地上的”[4]。在音乐上,崔健选择了“底层”,而不是随着中产阶级一起崛起的流行音乐。“底层”的内涵在这里相当模糊,但它指向了一种音乐上的安身立命。与底层站在一起,与弱者、劳动者站在一起,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部分。崔健的底层意识,以及外化出来的音乐风格,在这里不能仅仅被看做是对美国音乐的模仿,也应该被看做是“红旗下的蛋”的自我认识辐射到音乐上的变形。以“底层意识”为动力,崔健的说唱显出了“阳刚”的一面。一个男性的、肉体的、正直的、威权的、模糊的声音,在90年代软绵绵的流行音乐中,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在歌词上,90年代中后期的崔健却越来越柔软。在《红旗下的蛋》中他唱道:“我没有力气,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反对你。我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我背后骂着你。我们看谁能够,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在《宽容》中则是透露出一种无奈中的不甘心,坚强、死磕的力量在慢慢流失;到了1998年,他唱出了《无能的力量》,把内心“软弱”的一面端上了台面。
在《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里,崔健展现了他的概括力,他唱了《春节》《九十年代》《时代的晚上》《混子》,延续了他与时代对话的一面。然而他也第一次,在对时代的把握中流露出了大量软弱的情绪,这又与他阳刚、男性的说唱形成了一种张力。“软弱”“无能”“安慰”“忧伤”“沉默”“恐惧”“失落”“压抑”“腐朽”“神秘”,这样的词汇贯穿了整张专辑。这些“软弱”的情绪并不是作为被克服的对象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自我呈现、一种描述,好像一些紧绷着的东西松开了,被坚强的外壳封闭住的内在的柔软、不确定、“弱”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在崔健的前两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里,坚强的、紧张的、理想主义的主体与毛泽东时代的对话不可分割,也就是说,他批判、反思的对象实际上也就是他眷恋的对象。在80年代的现代化转型中,崔健唱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与“长征”都要克服物质主义。“新长征”的意象,在与毛泽东时代的纠缠中获得了力量:在对历史的反抗和眷恋中,自身也获得了历史性。而在《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中,变化发生了,这个与毛泽东时代无法分割的主体,意识到了“改变”的不可能,理想主义在这里丧失了力量。到了《无能的力量》,崔健唱道,“我一事无成,但不清闲自在。我白日做的梦,是想改变这时代。我现在还无能,你还要再等待”。崔健80年代唱出的“出走者”[5]没有这样的无能感,这说明崔健在90年代中后期意识到了新的问题。“改变”的不可能不在于没有“改变者”,也不在于“对手”的强大,而在于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抗”。不同理想的分歧、张力,共享着理想主义的质地:双方都把自己献祭给了比自身更高的东西。借用伯林的话来说就是,“不是你杀死我,就是我杀死你,也许来场决斗,最好的是我们不分胜负,双双战死。最可怕的是相互妥协,那等于是说我们双方都背叛了自己内心的理想”[6]。崔健意识到的问题,正是理想主义的失落。不再有真正的对手,也不再有真正的斗争,从理想的层面来说,也不再有改变。崔健在《混子》中唱道:“瞧你丫那德行,怎么变成了这样儿了。前几年你穷的时候你还挺有理想的。如今刚过了几天儿,你刚挣了几个钱儿。我看你比世界变得快多了,要么是漏馅儿了。”“你挺会开玩笑的,你挺会招人喜欢。你过去的理想如今已变成工具了。”“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念念报纸吧。你说理想间的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别让生活恐惧,就别那么固执。因为固执久了世道变了你也看不见了。你说别胡思乱想了,快多学点儿知识。因为知识多钱多就把理想买到了。”崔健在这首歌中反复唱到“理想”,前四次是对理想的悼念;从“穷的时候你还挺有理想的”到“理想间的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第五次是对理想的重新塑造;“知识多钱多你就把理想买到了”,崔健敏感到了一个新时代,理想不再是被争取到的,而是被“买”到的。真诚、反抗、献身突然之间都成了可笑的词汇。物质与世俗主义迅速地抬头。崔健敏感到了一种新的压迫方式。知识多、钱多、理想也多,反之,就一无所有。在80年代,理想意味着一种自我肯定,一种个人的乌托邦,个体可以借此与威权、市场保持距离。而在这种新的压迫方式中,理想从穷人和笨人身上被剥离了出去,也就是说,“知识”[7]和“钱”少的人,追求“理想”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压抑中,理想无法建立,找不到自我肯定的方式,也找不到自我认识的语言,“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就像这手中的音乐”(《九十年代》)。主体的精神状态变成了“混”,而且是要微笑着,迎合这个时代表面的轻盈,以求混得下去,“无所谓的,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微笑。你说这就是时髦,你说这就是潇洒,你说这就是当今流行青春的微笑”。“混子”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人:被剥夺了理想的可怜人。而当他们混下去了以后,又成为了巩固这种新的压迫方式的基础。当“混子”混上去以后,知识多,钱多,“把理想买到了”以后,到手的还是理想吗?
在这样一种新的压迫方式中,崔健感到了“无能”。他在音乐上保持激进,不讨好流行音乐市场,而在歌词中唱出了“软弱”。我感到,崔健在这里,呈现了一种面对这种新的压迫方式的方法,就是袒露自身的“软弱”。90年代初,苏联崩溃,东欧剧变,中国市场经济深入改革,社会主义阵营散掉了,世界向着单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向前进。用分析性语言来说,可以把这种新的压迫方式,看做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合谋的市场经济改革。然而,这样的分析所难以深入的是,在这其中,整个大众的“感觉结构”发生了怎样的翻转。理想变成了逐利的工具,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混得好就意味着一切。这种“感觉结构”进入了个体内部,很难有人可以外在于这样的感觉,再以“启蒙主义”的姿态去批判他人。同时,也很难有人可以从这种新的压迫方式中超脱出来,建立起一种新的理想:所有人都被压住了,并且要被迫学会这种新的压迫方式允许他们运用的语言,那是一种调侃又虚无的语言。“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让我感到一种亲切和无奈。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软绵绵酸溜溜却实实在在”(《缓冲》)[8]。在这其中,主体与他所批判的对象黏在了一起,腻在了一起。基督教里说,只要叫出了魔鬼的名字,就可以降服它。而在这里,旧的语言无法指认新的魔鬼,而新的语言无法建立起来,形塑起新的理想主义的主体。在《时代的晚上》中,崔健唱道:“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爱较劲。不过是积压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这是一个准确的表达,“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在这样的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意识、让人破碎掉的压迫中,“本能的反应”被崔健释放了出来,那就是“软弱”。
在这里,首先要看到的是,这样的“软弱”“无能”“失落”等等情感,是在理想主义失效后的语境里产生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负能量,在理想主义的光辉中,是被遮蔽的。而当“感觉结构”发生翻转,理想主义的失落才让这些负能量裸露了出来。就这点而言,“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暴力在它失落后显现了出来。“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这样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这样他才能制造万物”[9]。“启蒙主义”强调的“理性”排斥了“非理性”,理想主义把人的精神从身体里抽离了出来,“软弱”“失落”“恐惧”这些情感要么被置之不理,要么被当作前进路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就这点而言,90年代的市场机制释放出了一些被80年代的“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压抑住的情感。
在这张专辑里,这些“软弱”、负面的情感能够被打开,是借着“爱情”这个载体。也就是说,它们是在爱情这个空间里被打开的。新的压迫方式关上了反抗、政治的可能性,同时推动商业机制,塑造欲望,塑造爱情。在这种柔软的高压锅里,反抗、自由、平等的诉求被封闭,创造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被封闭,积累出来的能量,随着被形塑出来的“爱情”这个通道释放了出去。因此崔健会唱道,“突然一个能够震撼我的声音严厉地问着我,你是否有那么一点儿勇气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不知不觉地下意识地说了一声‘我爱你’,顿时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一起轻轻地飞起”(《另一个空间》)。这段歌词非常有意思,“突然”“震撼”“严厉”“勇气”“真正”这些有重量的词汇积累起来,推动出了“自由”,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给软绵绵的生活带来一个猛然的惊醒,“自由呢”?被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力推动出来的追问戛然而止,就像是细菌离开了身体,在空气里无法存活。在空白中,“不知不觉地”“下意识地”,我说了一声“我爱你”。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诉求,“自由”和“爱情”就这样忽然被连接在了一起,积累在自由诉求里的能量被转化进了“我爱你”里面。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在这种新的压迫方式形成的高压锅里,这种转化即使被迫完成,主体也会陷入不真实的梦幻感里,“顿时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一起轻轻地飞起”。
90年代,情歌开始泛滥。我爱你,你不爱我。我走了,但不能忘记你。我失去了你,但你还在我心里。我回来了,你还在吗?情歌在流行音乐里变化出无数的样子,并且挤走了别的题材。直观看,在流行音乐上,中国人90年代最大的诉求就是爱情。歌唱爱情也就是在歌唱软弱和失落。这是新的压迫方式反映在流行文化上的一个症候。在表面的柔软甜蜜下,个体是孤独的、被压抑的,找不到出口的能量在窜动。“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请摸着我的手吧,我孤独的姑娘。检查一下我的心理的病是否和你的一样”(《时代的晚上》)。“忍受”成为了爱情的潜在语境,一种相濡以沫的、同病相怜的感情在这里产生了。“你的小手冰凉,像你的眼神一样。我感到你身上也有力量却没有使出的地方,请摸着我的手吧,我坚强的姑娘。也许你比我更敏感更有话要讲”(《时代的晚上》)。这里需要细致地分析一下:在新的压迫方式形塑的“感觉结构”中,理想主义式的反抗不再可能,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背后,大量被压抑的能量积累起来,而“爱情”被塑造成释放被压抑的能量的通道,随着这个出口,大量负面的感情,“软弱”“失落”“伤感”等等被释放出来。在这个机制里,流行音乐里的爱情和崔健的爱情被生产出来的方式没有不同。而崔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软弱中含有一种“承担”,一种没有形状的、在空虚中涌动的力量。这是“红旗下的蛋”延续到90年代后期的精神状态。不是更坚强,而是更软弱。不是向外,而是向内。但这内在的软弱不是对外在刚强的放弃,而是刚强的、对于理想的斗争被封闭住之后,让“软弱”成为一种相互慰藉的力量,把孤独的自我与孤独的姑娘联系起来,而这不是被资本和市场所催生出来的联系——一种纸花般的爱情,而是穿透商品化爱情的一种灵魂深处的联系。“请摸着我的手吧,我温柔的姑娘。是不是我越软弱越像你的情人儿。请摸着我的手吧我美丽的姑娘。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鼓点、笛子和一种类似烟花的声音在这里同时出来,形成了一种又滑稽又欢乐的氛围。这是“软弱”在崔健这里产生的力量。“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彼此默默地分担着一种弱的、共同的感情,而当足够多的“弱”被联系在一起,弱会不会转变成强?当这样的弱被社会充分地意识到后,从弱中会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想象?
2005年,与上一张专辑的出版相隔七年,崔健出版了《给你一点颜色》,这也是崔健在新世纪的第一张专辑。在这个时期,互联网迫使整个音乐产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这个调整的核心是利益的分配,传统唱片公司在这场利益争夺中处于劣势[10],反映到在唱片时代固定下来的音乐类型上,这些类型间的壁垒也开始被打破。互联网时代拉平了音乐类型之间的界限。摇滚在90年代后期失去了文化上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时代更不再是一种精英文化。在这种状况里,崔健做出的调整是,尝试了更多的音乐类型。这张专辑包括了流行、摇滚、电子和hip-hot等音乐种类,可谓相当庞杂。同时,他从80年代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的、一个革命后代的主体性在这里也开始崩溃。在他前四张专辑里,他所唱的“我”基本上是同一个主体的不断变化,从《一无所有》中的“我”,到《一块红布》中的“我”,再到《无能的力量》中的“我”,这个“我”在时代的脉动中挣扎,维持自身的连续性,也维持着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而在这一张专辑中,“我”变成了民工、网虫、写手、歌厅老板,等等。崔健试图进入不同的主体内部,代替他们说话。
主体的弥散成为崔健这个时期的症候。崔健的创作方式,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崔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创作工具,由乐队变成了乐队加电脑。“当崔健拿起了机器,传统的音乐概念消失了,涌来的是音色、音响组织,是创造。也许说拿起机器并不形象,崔健拿起的是鼠标,是旋钮,是推拉操纵杆。这是21世纪音乐领域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的地带,是音乐正在延伸生长的地带。从此崔健离开了乐队,改与机器为伍;离开了歌曲格式,改与新的音乐结构一起生长。这是一个音色的世界,是声音音响组合的艺术。它的基本手法不再是传统的作曲、演奏,不再是旋律、节奏、和声,而是采集、调变、变形、组合”[11]。乐队发出来的声音背后,是人的身体,是人在弹奏,人在舞台上挥洒汗水。人在录音棚里对着机器弹奏,声音被录制下来,再通过机器到达听众的耳边。在20世纪的音乐发展中,机械复制揳入了音乐的生产和流通里。“在世界历史上,机械复制首次把艺术作品从对仪式的寄生性依赖中解放出来。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被复制的艺术作品变成了为可复制性而设计出来的艺术作品”[12]。音乐的历史也是技术发展的历史。乐队的存在,表明了技术没有完全淘汰人的身体。身体在呼吸、呐喊和抗争。而在新世纪,当技术进步到把电脑纳入音乐的生产中时,身体的能量被进一步削弱了,乐手不再需要背起吉他费力地弹唱,只需要坐在电脑前,调试出自己喜欢的声音,身体静止了,能活动的部分只有眼睛和手指。机械复制在新世纪更深地进入了音乐的生产。“如果80、90年代的rap、hip-hop是一种抢麦克风争取发言权的形式、众声喧哗,是肉身的抗争,那么2000年以后的电音则有去论述、去人化的倾向。人的声音越来越少,肉身几乎完全被抽离”[13]。
崔健的创作方式被机械复制更深地控制住之后,反映到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带着集体主义的烙印,要以一己之力为时代代言的主体不见了,呈现出来的是不同个体的声音。崔健第一次为不同的个体写歌,并试图代替他们发言。在这里,一个必须被提出的事实是:崔健唱出的不同个体,来源于他自身的想象,而不是这些个体从自身状况出发发出的声音。也就是说,崔健唱出的民工,并不是民工自身的声音;他唱出的写手,也不是写手自身的声音。在涉及到不同个体的歌唱背后,并没有不同的个体在发声;相反,这里呈现出来的,是崔健的主体破碎之后,在破碎中想象不同的个体,并试图从这破碎的想象中,把自身的镜像再度拼贴起来。
面对快速变化的现实,崔健调动的是以往的经验,可以说,他紧紧拥抱住一个逝去的整体性,以此来对应现实。在唱到农民工时,他用了一个革命时期的话语,“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泽东在国共内战时期的一个战略,在城市被国名党占据的局面下,以占据农村的方式,发动人民战争,包围城市,来取得政权。而农民进城打工,是在90年代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以城市为中心、吸收农村的劳动力的局面。从现象上看,这更像是一种对农村的内部殖民。其引发的新的问题,是在一个与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状况里发生的,一个明显的症候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由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平等,引发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这种症候发生在人的主体内部,表现出来就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彼此在情感和生活上的隔膜和对立。在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的时候,崔健用一种革命时期的话语,来复制和加强这种对立,他在《农村包围城市》中唱道:“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我们农村,你们到哪儿吃东西呀。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又能怎么着吧。”在对城里人的描述上,崔健又进一步把城里人描述成读书人,“你们有什么呀,瞧给你们惯得。这个不行,还有那个不行,有什么呀。不就是多读过几年书吗,那些没读过书的人就不是人吗?”在反问之后还有质疑,“你们读书人最爱变了。好话坏话都让你们说了”。而“有良心和有知识是两回事儿。没有良心有知识又有啥用啊。你们敢说你们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吗,写的每个字儿都是用了心的吗?”在看似尖锐的质疑背后,是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对立,以及由此提炼出来的,“良心”与“知识”的对立。由此不难看出,这背后有毛泽东时代对工农的美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以及这背后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命题的复制。“这种对于城乡冲突的想象方式,若究其根源,是与崔健与‘革命文艺’传统的关系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知识与良心的二项对立中找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说的影子,假农民工之口说出的对读书人的怀疑和质问背后其实是崔健自己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立场的自省和警惕”[14]。在复制革命的话语和记忆,来呈现自我和主体内部的挣扎时,崔健表现了他与历史同在的深刻,而当他以此为工具,要批判当下和代言他者时,革命话语体现出来的,是无法把握当下的复杂状况,和对当下不平等的强化。
在《小城故事》系列中,崔健虚构了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唱歌的姑娘,为了得到她,就先到外地去打拼赚钱,“要想解决它,我只能先出去”。崔健在80年代唱出的“出走”的命题在这里再次出现了,不同的是,这次“出走”不再像80年代那样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和对前路的迷惘感。这里的“出走”目的和出路都很明确,“用不了多久,我就要牛B地回去”。出来一圈之后,小伙子的心也变了,“太多的欲望,不敢多想。太多的姑娘,让我的心发痒。”在北京的崔健,虚构了一个小城故事,他抓住了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一个人口流动的问题,小城市的人要到大城市去,经济次发达地区的人要到发达地区去,这后面的主要动力,是赚钱。但是这些人仅仅是经济动物吗?在这个由经济发展所带动的人口流动中,怎么去理解这些流动人口的主体状态?怎么去呈现他们真实的心情?怎么去表达他们的爱,以及在流动中产生的情感的复杂变化?这都是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大脉络下出现的新的状况。这些状况无法用政治经济来分析,文学、音乐成为触及这些状况的媒介。而崔健在抓住这个人口流动问题的同时,仅仅从外部出发,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为了爱情出门赚钱的故事。在80年代被理解成一种辽阔的、充满未知,因而出走也意味着一种希望的整个外部世界;在这里被理解成了整个资本的内部世界,出去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风光地回来。这里不再有诗意的、幽微的空间。在赚钱的路上经历了一番之后,小伙子小有成就了,开始抒情,“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找不到自己。身体得到了自由,灵魂还是在监狱”。为了赚钱出走的主体到最后忽然有了一种迷惘和分裂感,这突如其来的一笔,是崔健的主体在这里现身了,那个他80年代唱出来的“出走者”,到了新世纪“还是找不到自己”。他把这种感受揳入了他试图把握的“小城故事”里,而小城里出来的打工者,到这里完全被崔健自己的形象覆盖了。“身体得到了自由”,谁的身体?怎样的自由?在新世纪沿海的工厂里,是被固定在流水生产线上的劳工。把这句歌词上接到崔健在80、90年代所唱的“自由”的主题,就完全有了意义。自由是崔健出走的内在动力,在自由不能被明确界定的语境里,它也具有了一种生气和希望。在90年代初,逃离象征着禁锢的医院,“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到了新世纪,自由被落实在了身体上,“灵魂还是在监狱”。那个贯穿了崔健80、90年代的出走者,在这里,以一种碎片的方式回来了。
在整张专辑里,最能体现崔健的,是他在《蓝色骨头》中唱到的写手,这个写手从小就不受束缚,不爱学习,“我说人活着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出来工作,也选择了相对自由的写作,“一开始我就是想用笔来发发牢骚,可是谁知道这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俗话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写手是90年代末随着网络扩大了文学市场而出现的一个群体。新世纪的开头,写手的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能在网络文学市场上生存下来的人,需要迎合这个市场的轻盈,需要与90年代形成的市场机制形成互动,捕捉到新的压迫方式里形成的感觉。面对这个新的群体,崔健调动了他在80和90年代初的经验,与威权政治的对话,“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只有扭曲一下我自己抬头看看上面,原来是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崔健跳过了90年代形成的市场机制,也跳过了写手们生存的真实状况,他甚至丧失了“无能的力量”所流露的与市场机制纠缠的张力。在新世纪,市场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内化进人的主体,生产出写手这样的文字工人的时候,崔健的视点反而后移到了他的起点上,从威权体制里出走,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蓝蓝的天空”意味着什么?“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看起来却像是忍受,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这样的歌词出现在90年代初是让人期待的,因为它抓住了改革的欲望,“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而在新世纪,经济发展成为了大国崛起的动力,而改革所形成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并且在继续加重,“无限的感觉”无法对应于现实,从而成为了崔健个人的回声。
在这张专辑里,崔健的主体弥散在不同个体身上。这是一些被市场机制生产出来的个体。崔健看见了他们,却无法感受他们。他试图在他们身上,重新找到自己。拉开改革的图景,可以看到,改革的脉络,也意味着革命的失落。而出现在“革命—改革”转折点上的崔健,却无法放弃革命的情结和记忆。脱去革命的肉身,走上改革的路,但无法放弃革命的气质和灵魂,从而不断对改革产生批判,在批判中深化自身与革命和改革两种机制的纠缠,这是崔健建构主体的方式。在改革的脉络里,这也是崔健不断体验失落的时期。“如果爱恋的对象本身已经失落,主体却未能放下那份依恋,而对于对象的爱恋转而屈身于自恋认同之中,那么便会启动一项机制,主体将对替代的对象产生恨意”[15]。崔健批判改革背后,有着填补空虚的煎熬;而进入新世纪,批判所需要的理解,却是他所缺失的。在新的音乐语言进入到他的主体,使他坐在电脑前面时,看到了新世纪模糊的图像,闪烁在其中的打工者、小老板等等,他来不及进入这些主体,就转而拥抱一个逝去的自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是我不明白》)。他走了太久了,改革进展得太深了,他的能量在新世纪即将耗尽。这也许是中国摇滚的开创者所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借着这些新的个体,他要回去了,要拼凑出自己,那是他刚刚上路的样子,反抗威权,心怀理想,“无限的感觉”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注释:
[1]Boy Dylon的现场,变换节奏,编曲,重新演绎,往往会让听众听不出他在演唱他的成名曲。而Michael Jackson的现场则强调要原汁原味,效果要和唱片里的一个样子。这是摇滚和流行音乐对现场的不同态度。
[2]露芙帕黛:《摇滚神话学》,台北:商周文化事业出版社,2011年第3版,第17页。
[3]在流行音乐界,直到新世纪,周杰伦出现时,模糊的咬字才被广泛接受。
[4]崔健、周国平:《自由风格》,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页。在这里,需要看到的一个脉络是,说唱在90年代的美国,随着摇滚的衰落,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主流。
[5]崔健80年代的摇滚乐里唱出了一个“出走者”的形象。这个“出走者”离开了家,没有目的地,只有向前的意志,伴随着内心的纠结。这个坚定又痛苦的“出走者”在80年代打动了很多年轻人,这个出走者是没有方向感的,正因为没有方向感,他才需要不停地走下去。把“自由”的诉求放进来,也可以看到,崔健强烈地渴望自由,但他并不知道自由是什么。
[6]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7]这里必须追问,“知识”是被怎样建构的?
[8]在这种氛围中,产生了一些俗话,如“你一认真就输了”。
[9]阿道尔诺·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6页。
[10]曹可臻:《浮沉:中国唱片业三十年》,《全球商业》,2013年第4期。
[11]李皖:《五年顺流而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12]汉娜·阿伦特编:《启迪》,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40页。
[13]王明辉:《变动中的集体听觉》,《人间思想》,2012年第2期。
[14]孙伊:《摇滚中国》,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15]刘人鹏、郑圣勋、宋玉雯编:《忧郁的文化政治》,台北:蜃楼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146页。
王 翔:现为上海大学文学博士。出版小说《夜雪》和诗文集《飞翔的梦》《灯还亮着》《寂静之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