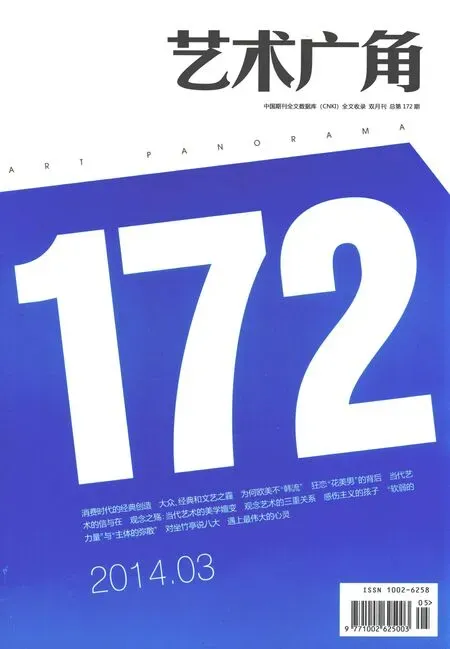感伤主义的孩子
——周云蓬的宽度和限度
2014-03-12刘大先
刘大先
感伤主义的孩子
——周云蓬的宽度和限度
刘大先
1994年,大学毕业、不愿意接受社会福利的盲人周云蓬开始了自己的流浪歌手生涯。这个节点性的时间,正是中国城市民谣兴起的时候。从中国当代音乐谱系来看,城市民谣的兴起是摇滚乐剩余力量流散的结果。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极盛而衰的中国摇滚,本来是在文化匮乏中渴求信仰与思想,进而以西方摇滚形式在既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中撕裂而出。然而,一方面,90年代本土政治与经济发生转型,进入所谓后革命时期,让摇滚的反叛性内涵消弭于无效;另一方面,全球性的资本与信息,带来更为多元主义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应和着城市化的进程,校园民谣转而向都市民谣发展,这是民族与民间的音乐传统反哺于现代西来流行音乐形式,两者相结合的产儿。最主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也给周云蓬这样的歌手带来生存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歌、文和人。
周云蓬一开始是以流浪歌手身份出现的,而此后这变成了他的形象,因为这个形象本身充满了可以满足都市文艺爱好者有关异域、远方、江湖的种种想象——他们自己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做到的事情可以通过心向往之的方式在这样的形象中找到落脚点,所以这种形象本身就具有了消费的价值。而他又是以盲人身份出现,更因集体记忆的积淀而为这种形象增添了传奇性的色彩。
盲人为乐官,是古典中国的传统,《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其中的演奏人员有“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而《周颂》中诗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可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瞽者被认为不受目迷五色之惑,而更方便以精神沟通天地人神。春秋晋国的盲臣师旷更是在擅琴鼓瑟之余大治晋国,《左传》记载楚国进攻晋国时,师旷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在演奏北方音乐和南方音乐的对比中,听到“南风不竞,多死声”,因而楚必无功而返。音乐在这里就具有了神奇的预示功能,其根底里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所以后来就会出现《毛诗序》中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观风采乐,因而就成为君主了解民众俗情的重要途径。“古人将歌谣称为风,也许不仅是因为歌谣像风一样风靡大地,感人至深,更是因为歌谣也像风一样,有一定的季节性,随四时光景的转换而流转。歌为生命的心声,生命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风格,因此,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歌声,歌发四季,四季如歌。”(刘宗迪《古典的草根》)民谣中包含着民间的智慧和民众的心声,直至今日也依然被认为是不悖的真理。
从西方来看,也有类似的文化原型。古希腊的史诗据说就是盲人荷马的杰作,15、16世纪弹着琉特琴的游吟诗人也是欧洲文化中的常见形象。“这些大地上的游吟者,游走在村落间,歌唱在人群里,身份更接近于说书艺人。他们不专事于写诗,节律性的长短句只是方便吟唱的必需。他们也不专事于记叙历史,说历史、传信息、谈论时事变故,是说书娱人混饭的本钱。民谣艺人们着眼于生活,以叙事为主体,把唱歌当说话,包容了生活的全部内容。……游吟者不只是游吟者,还是民间诗人、酒徒、信息传播者、讽喻现实的小丑、助兴人、诗诵家、史诗杂匠;由于传布广远,全凭口耳相传,有时同一首歌流传的版本多达一百多种。”(李皖《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游吟者的后代在今天就演化成周云蓬这样的民谣歌手,他们是口头文学在当代的遗留物,一项卑微、似乎在大众传媒兴起中已经奄奄一息,却终究因应时变、默默前行的文化遗产。
周云蓬在一篇名为《民谣是什么》的短文中对自己心目中的民谣做了一个诗意的描绘:它是单车上的纯真恋情,是千辛万苦寻找失踪儿子的父亲偶尔一次的回到自我,是漫无目的的疲惫旅途中的一次迷失……
是你骑自行车,在梦里。
你老百姓今天真高兴,蹬呀蹬,
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拄了一根盲杖。
实际上,你根本没看过自行车,你走路还得人领着呢。
你也没坐过飞机,在梦里,飞机上有个售票员,在座位间走来走去,她让大家买票。
你也没亲近过女人,
在梦里,她是早上刚出锅的煮鸡蛋,
你吹着气,小心地一片一片拨开,
先是指甲盖大的炽热软润,
然后逐渐扩大,
越来越烫手,
越来越不敢拨。
这种诗意化的描述往往遮盖了民谣和民谣歌手背后的艰辛旅程,当然,也可以视作是一种生活审美化,在歌谣中超拔世俗烦冗生存状态的努力。周云蓬对此心知肚明,事实上他自觉地把自己与小河、万晓利、野孩子、赵牧阳等人的音乐称为“新民谣”。在《江湖夜雨十年灯——关于新民谣的孩提时代》中,他回顾2005年小河在798策划的一场民谣音乐会,第一次冠名为新民谣,以区别于当年的校园民谣。2006年,张晓舟在深圳体育馆组织“重返大地——2006中国民谣音乐周”。2007年,“迷笛”音乐节设立民谣舞台,人气和主舞台不相上下。同年,万晓利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奖”,打破了港台艺人对此项奖的垄断。这一系列事件在很多民谣歌手和听众那里也许不过是无数文娱事件在新世纪的经济繁荣中获得生存空间扩展的证明,而周云蓬则把其中美学自觉的诉求点化了出来。
经过大约十年的北京与异地游唱生涯,周云蓬已经小有名气。他连同“新民谣”对校园民谣的替代性登场,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宏大叙事式的对抗性政治幻觉的完结,新经济模式下被侮辱与损害者的表达欲求,文化多元主义状态的兴起……还有不可忽视的是,“它得力于互联网的自由传播,人们对于宣泄自己心理诉求的渴望,以及平易近人的现场音乐的回归,仿佛多年前的天桥撂地,梨园捧角儿。”技术带来的变革,既是新语境中音乐方式的内部转型,同时也是亘古不变的“歌永言,律和声”的当代变体,甚至连接受方式从本质上说也继承了先辈的传统。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中,周云蓬清晰地剖析了新民谣与高晓松等人的校园民谣的区别:新民谣带有强烈的草根性与社会现实感,因为“我们更多是在城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环境中挣扎的人。”对校园民谣,周云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是不变的三拍子,好像校园民谣就是青春气息这点东西。其实它没有反映出真正的校园。”其实,早期大陆校园民谣的歌手比如老狼也时常是周云蓬联袂演出的伙伴,他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一种长久底层生活赋予的底气——无疑,至少从经历上来说,他接触的社会广度和思考的深度已经大大越过了校园和青春的体裁,夹杂了民谣传统的积淀、摇滚乐的残余、通俗流行乐的营养,因而不免气盛言宜。
在一首叫做《不是诗》的诗里,周云蓬给自己勾勒了一幅肖像:
我在中国的最底层
在人最多的地方
喝最便宜的啤酒
诅咒塔尖上的人
和虚伪的光
我的情人是个丑姑娘
她只上过小学
我是个快四十岁的中国男人背负所有免费的公厕
所有不卫生的熟食摊
所有痛苦的公共汽车
所有麻木的黑白电视
所有口蜜腹剑的主持人
十三亿潮湿的躯体
就算我是最下面的一块砖
即使如此
就算这样
这是多年流浪生涯淤积的意象和情绪,同时在极端意义上也构成了新民谣歌手的心理群像。丰富的经历造就了源自个体经验的诗歌,体现的是弥漫在底层空间的普遍性情感,对于命运的逆来顺受和敞开怀抱矛盾性地交织在一起,对于集体性公共话语虚伪的愤懑最终溶解在不屈服的姿态之中。有时候这种个体经验会导向更为宏阔的社会层面,它显然是间接经验的转化,比如《中国食物链》:
一个香港佬
在深圳包了个年轻女人
女人抽空爱上了一个来自山东打工的小伙子
小伙子把得来的港币寄给留在家乡的姑娘
姑娘把一部分钱分给整天喝酒的弟弟
弟弟在盘子里夹起一块排骨
丢给跟他相依为命的短腿狗
狗叼着骨头舍不得吃
把它埋在树下
一只蚂蚁爬上骨头
发愁
盘算着
要叫多少蚂蚁来
才能把这块大骨头搬走
极简主义的词句将社会层级结构触目惊心的利益与关系网络呈现出来,以至于形成了类似民族寓言式的漫画场景。零度情感的抽象抒情,在客观主义中把态度和判断留给了受众。但是这种抒情固然可以引发同情共感,却不可避免要走向感伤主义。在各地的巡演中,周云蓬屡次倡导痖弦作词,李泰祥谱曲,齐豫原唱的《四匹马》:“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金马看看去/那是昔日。 谁在远方哭泣呀/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灰马看看去/那是明日。 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白马看看去/那是恋。 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黑马看看去/那是死。”昔日、明日、恋与死,唯独缺乏的是“今日”和当下的生活,他在为失去的黄金岁月(如果有的话)而哭泣,为不可知的未来而忧虑,为爱高歌,为死痛心疾首,但是找不到今天的出路。就像崔健那张具有象征意义的专辑《无能的力量》这一名字所暗示的,这种尴尬局面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歌者的普遍经验。歌者的无能为力不仅在于主体力量的卑微和弱小,更在于整个社会语境再也不能把集体性的共鸣转化成有效的政治能量。像那首最为著名的《中国孩子》,周云蓬只能把社会新闻作为集锦一般直白地唱出来,“不作中国人的孩子”,也仅此而已。因为无法摆脱既定的命运,社会差距造成的失落感,与自然生理的缺陷,让他特别敏锐与感伤。他从自己身体的局限和经验的龃龉中,感受到整个社会的痛感,由身体的残疾引申到世界的残疾,那些黑窑工、失踪的人、失业者、丧失现实和精神上双重家园的游民……就是他的同路人,他同他们齐步而行,一路嗟叹呻吟,终究不知所终。这是种并无独特之处的多愁善感,是我们时代无权无势者真切的现实与内心。
周云蓬面对的是整体性消解后的破碎时空,他所钟爱的诗人海子,止步于九十年代的门槛。“诗人之死”具有的象征意味在海子之死中达到极致,诗歌作为立法者的地位让位给了更加繁复的社会过程,与诗学社会的终结并生的是经济学社会的诞生。在这种转型里,“诗人何为?”用周云蓬的话说,他们只能“坐在路边小声自语/这世界不好/不幸福。”这已经是近乎撒娇的做派,却连撒娇的对象都找不到了。回忆圆明园的盲流生活时,周云蓬不无尖刻地反思了原先不切实际的理念:“那时大家谈得最多的艺术家是凡·高,因为通过传记知道他很穷,而我们也很穷,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等同于凡·高,但贫困不等于伟大的艺术,很多艺术家陶醉于自己的悲剧命运中,他们事实上爱的不是艺术,而是贫困,爱上了虚妄中的悲剧英雄。”而“我只有埋头于生活里,专注地走一步看一步。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话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从艺术的虚幻回归现实的生活,好在还有音乐,摇滚的政治激情和诗歌的超验想象结合起来,让民谣歌手得以安身立命:“生活是清醒的水,歌声是如梦的酒。生活是直觉的自由,歌声是幻觉的蜃楼。这些有着世界上最壮丽的伤口的人,在幻觉的导向下,让伤口流成了一首澎湃的歌。”《新疆西游记》中,周云蓬写道:“音乐应该是那种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恐惧的最好的钥匙”,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其结果是在周云蓬的吟唱中,尽管有批判,但是批判的对象是个无名的实体存在,一种抽象总体,就像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让批评者无从入手,甚至批判本身也会被纳入到它的逻辑结构之中。周云蓬在这里显示了他的狡黠,就像他的朋友说的,他很少会对人对事做出个人化的评论,这可能是混江湖的基本生存智慧。排除这种诛心之论,周云蓬的身体体验会影响到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方式。他的心意中理想的民谣应该避免“民间”与“官方”或者类似结构上的二元对立,无疑是从另一面体现了他内在的欲求:以个人幸福、个体反思、美学趣味去疏离社会化叙事。
《声音与愤怒》的作者张铁志认为,大陆有必要出现愤怒、抗议型歌手。周云蓬在这一点与他发生了分歧,他反而认为此类音乐越少越好:“我更主张大陆出现小花小草类似卡奇社、苏打绿这种。像大陆这种土壤,就别老出现很大气、很公众型的歌了。我们的根源在于缺少个人主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民社会的土壤,而不是又出现一个伟人、英雄。”他提出要警惕社会议论式的歌曲,这种歌固然因为扣着热点与焦点话题与情绪,容易获得热烈的反应,但公众的心态比较复杂,很多时候不过是借歌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躲在安全的文本帷幕之后发泄浮皮潦草的情绪。所以,当愤怒成为一种常态和姿态,就容易陷入到被外在事物左右的陷阱,很容易丧失自我。“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所以也警惕自己不能进入一种公众的惯性中。音乐的本身就是音乐,其他像公众性、教育性、道德性,都是附带品。像诗歌本身就是诗歌,它可以承载道德,也可以不承载,但第一性是诗性的。音乐也是这样,不能把它沦为一种工具……我们现在贬低小清新,你可以不喜欢,但应该尊重他们。他们培养了一个大批个体的土壤,有这个土壤,将来我们才可能唱我们自己的歌。”自我的反思和包容的心态,表明了他的自觉和自知。
到这里周云蓬的音乐理念已经清晰地凸显出来:“人生如果不是作为审美对象,它便毫无意义。”“歌就是一个副产品,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你要知道那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都是阴差阳错,一种情绪,沤着,排泄不掉。”歌永远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这其中并没有值得自豪的资本或殉道式的悲壮。这并不是新鲜的观念,然而周云蓬很巧妙地将其表述出来,表述本身的修辞性赋予了陈旧思想以华丽的外衣。陈旧并非必然意味着过时,因为民间的时间给予生活以无限性,从而让其具有了命运的形而上意义。周云蓬对于文字的精炼把握,让他从众多民谣歌手中脱颖而出,如果通读、聆听他的所有作品,就会发现他是个一流的诗人,仅《不会说话的爱情》就足以超越大多数所谓的诗人;他也是个二流的评论者,因为他虽然有关怀,却囿于身体和学识的局限,只能停留在普通民众的见解,而不具备真正知识分子的洞察;他更是三流的歌手,虽然他以此身份为名,但乐器、演唱和应对听众的技巧只能说差强人意。从《牛羊下山》《清炒苦瓜》里的曲目可以看到,周云蓬的总体风格是淳朴天然,他往往采用横云断峰、戛然尖新的意象呈现法,突出细节,又不同于口语诗,与其他叙事性较强的民谣相比,他更注重抽象的抒情。但是艺术或技巧上的粗糙并无关大局,内心体验的丰富才更重要。
从周云蓬的写作和歌唱乃至“在路上”式的生活方式中,可以看到许多与上世纪60年代全球性“反文化”的互文性。就像“垮掉一代”的那一拨毁于疯狂的天才,“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也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运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罢了。”早先的“无因的反抗”或者激进的诉求已经消弭于无迹。他的自我想象资源源于日常主义的经验,也终于此。这个置身事外的形象证明周云蓬像他同时代的无数文艺青年一样,其思想来源因为被大众媒体泛滥地放大而变得肤浅和扭曲。但是也无法证明下面的表述全然虚伪:“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分为三种境界,即:伦理的,审美的和信仰的。我但愿能置身于审美的光明中。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上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这正如庄子所喜的:无用者大用。于我而言达不到一定的速度,是无法克服重力的,飞翔仅当那时才成为可能。我的爱尚且不够,因此病苦还不够深邃。”这里分明回响着塞林格笔下那个麦田的守望者的声音。
这种选择其实是城市民谣的宿命,因为乡土之根已经断绝,而周云蓬这样在衰落的工业区长大的孩子从来就无法吟唱出美妙的田园牧歌。“无用之用”是从坚硬壁垒中凿空混沌,抒泄郁结,以文化上的象征价值获得世俗社会中残存的骄傲。他的受众显然不是农民或者农民工,而是城市小资、文艺青年,因而事实上缺乏广阔的传播场域。
敏感、细致、细腻、明心见性式的审美追求,让周云蓬具有极强的感受力。同时,也注定他逃脱不了题材狭窄、格局仄小的窘境——外在的不可为使得他不得不向内转,只是诉说自己的故事。作为个人最真实的理想状况是求得一个“希腊小庙”式的乌托邦,那个《青春疗养院》中的大理,就像童话《小王子》里的国王、银行家、点灯人……每个人守住的一个星球,回忆过去,自言自语,半梦半醒。在评论“野孩子”乐队主唱张佺《伏热》时,他写道:“一次古老民歌精神的灵魂附体,用石头花儿作比喻,首先要放下争奇斗艳的心,孩子和大师才有的思路。民歌几千年,就是个保守的赋比兴,信手拈来,又无比恰当。像陕北民歌中的‘山坡坡’,‘泪蛋蛋’,一切外物都成了亲娘老子婆姨孩子。”这种保守主义式的思路不独是他个人的倾向,也是新民谣总体的取向。周云蓬歌曲中难得欢快跳脱的《两只山羊》就是典型的西北农民的调调,不过大多数时候他的演唱都可以寻到循规蹈矩的蛛丝马迹:他的声线本来宽厚高亢,但是演唱中总是压抑着,克制、低回、忧伤,从来没有越轨的嚎叫和歌哭。
然而,话又说回来,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周云蓬幼年生活过的铁西区和成年后游历过的每个角落都是一块完整的大陆,他在说自己的故事,也是在说一个群体的故事。“道路死在我身后,离开河床谁更自由……我不要清醒的水,我只要晕眩的酒”。没错,真是“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我想,这可能与他的肉体缺陷有着直接的关联。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且热情拥抱它:“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蜕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能够窥破命运的残酷,还能够坦然面对甚至升华,周云蓬至少是个充满勇气和智慧的人,难能可贵的还具有黑色幽默的特质,像《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中设想的无数可能性,手把手教导如何与厄运相处。而如果世界突然瞎了该怎么办呢?周云蓬会回到自己的内心。
回到内心往往意味着最深刻的洞察和最苍白的退缩。“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盲人影院。周围是空荡荡的无边无际的座椅,屏幕在前方,那不过是一片模糊的光。我们在黑暗中误读生活,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只有想象它真实如流萤,在我们的现实和梦境里盘旋闪烁。一个现实的人,也就是一个抱着自己冰冷的骨头走在雪地里的人,而想象是我们的裘皮大衣,是雪橇、篝火、是再也无法看到的屏幕上的春花秋月,最后,等着死神,这个领票员,到我们身旁,小心提醒说,电影散场了。他打着手电筒带我们走出黑暗。”生命的领票员其实就是自己。有时候,这种逃遁带有庄周式的机智,在日常中能直达自我满足、醍醐灌顶的顿悟。《那些租来的房子》记述他的租房之旅,而结尾就像一个蕴积力道的太极高手,笔锋一转,“还有一个租来的房子,是本人的身体。俗话说,眼为心灵之窗。我这个房子,窗户坏了,采光不好。找房东理论,我胆子小不敢。那只好在里面,多装上几盏灯增强照明。其实,总是亮堂堂的,也不好,起码扰人清梦。坐在自己黑暗的心里,聆听世界,写下这些文字。字词不再是象形的图画,而是一个个音节,叮叮咚咚的,宛如夜雨敲窗,房东就是命运,谁敢总向他抱怨?有地方住就不错了,能活着就挺好了。等我离开这间房子,死亡来临时,那将是又一次崭新的旅行。哪儿都会有房东,哪儿都会有空房出租,流浪者不必担心,生命也不必担心死亡。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之无穷。”他的宽广之处在于能从一己身体出发对更广大的社群有理解的同情,而其限度也正在于无法走出骨子里的感伤,虽然时不时他会用调侃来进行化解——这种调侃也带有无助的凄凉感。
我最初是因为听到《九月》才开始接触到周云蓬,一个行游四方的高大盲人吟唱忧伤的歌曲,正足以满足柏拉图所谓人们非理性中的感伤癖和哀怜癖。在脆弱的夜晚,悠长缓慢的吟唱带有迷幻式的沉溺感。不过,我清楚,在冰冷的工具理性主宰着的功利社会中,滥情主义会成为它吊诡的另一面,因为个体在这样情感已经沦为商品的社会中无力自拔,只能寻找一个虚幻而脆弱的情感投射物。尹丽川曾经写过一段炫丽的文字介绍周云蓬和他的伙伴们:“他们不是精英,不是杰出青年,不是劳动模范,不是政客,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文化人,不是频频奔赴威尼斯的艺术家;他们是民间艺人,是城市和村庄的流浪者,靠手艺吃饭,为自己创作,为普通人献艺。他们跟艺术潮流之古典、前卫没什么关系,跟包装、商业也没什么关系。他们自得其乐,自食其苦。他们不想改变这世界,更不想为世界所改变。”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处处充满荒诞,评价对象时中肯的言辞,一不留神就可能变成反讽。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从事文学、影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