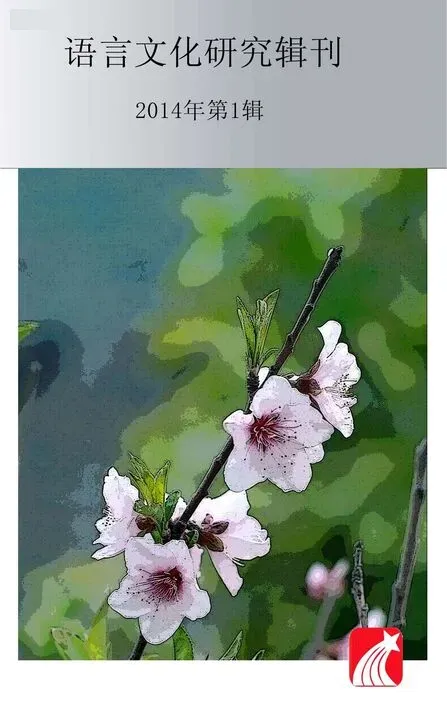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民间传统口头文学*
——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
2014-03-10李长中
李长中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阜阳 236037)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民间传统口头文学*
——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
李长中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阜阳 236037)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拥有丰富发达的民间口头传统,全面而深刻影响到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言说方式、审美建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蕴。不过,学界关于民间口头传统与作家文学创作关系问题的探讨尚存在诸多问题,对于民间口头传统如何影响到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深层机制是什么、有哪些规律可以总结等问题,仍缺乏富有深度和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成果。本文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对二者关联性问题加以研究。
民间口头传统 作家文学 人口较少民族
一 引言
目前,在我国的 2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几乎每个民族都拥有较为发达的民间口头传统,形成了人口较少民族相对发达的口语文化,“包含在当地人的思想、历史、道德、审美等一切意识形态里面,也伴随着当地人的一切物质生活,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审美属性,民间文学延续了当地人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到当地人的一切生活”①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长期生活在民间口头传统文化土壤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审美意识浸润着民间口头传统的滋养,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日益进逼,人口较少民族
因其 “人口较少”而导致文化根基相对脆弱,文化存续能力相对薄弱,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作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的文化寻根和民族忧患意识日益凸显,由此更加自觉地以回归民间口头传统,作为建构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基本依靠,甚至把写作当作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叙事中普遍洋溢着的身份意识、民族意识、现实焦虑和面向未来的诸多犹疑,无疑在验证着阿来谈及的问题。就此而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民间口头传统的挖掘或阐释,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使然,并在审美表征层面彰显民间口头传统的潜在规约。
二 民间口头传统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审美意识
“口头文学是指民间文学中纯粹口头讲述、吟诵的口传文学或口头创作。口头文学与口头语言密切相关,是口语语言的艺术。从形式上看。这类口头文学就有散说 (叙事)体和韵说 (抒情、叙事或抒情叙事相间)体。从体裁上看,散说体有神话、传说、故事、笑话等;韵说体有古歌、山歌、情歌、生活歌、长诗、儿歌等;散韵相间体则有谜语、谚语等。”①黄晓娟:《口传文学的精神生态与审美语境》,《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民间口头传统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际传承的活的传统,集中表现了民族情感力量的最大深度和生命智慧的最后高度,柯尔克孜族的伟大史诗 《玛纳斯》被称为我国 “三大史诗”之一,对柯尔克孜族的审美心理、文化建构、历史传承起到根本性作用;赫哲族民间文学中的伊玛堪、特仑固等大多是叙述古代氏族社会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征战与联盟、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民族兴衰、维护民族尊严和疆域完整的英雄故事,也有一些讲述萨满求神、渔猎生活及风土人情等,是一部再现赫哲族英雄人物、历史变迁与民俗风情的大型古典交响诗。鄂伦春族口头文学摩苏昆是反映民族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 “百科全书”,讲述民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有重大影响的英雄人物、远古时代民族迁徙的经过、萨满的神奇故事、风俗习惯等;②徐昌翰等:《鄂伦春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仫佬族的民间口头文学,如 《婆王神话》、《垦王山》、《潘曼故事》等,“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刻而活灵活现,远远超过当时遗留下来的文字史料……描述出仫佬多侧面的生活场景、多色彩的生活画卷”③龙殿宝等:《仫佬族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民间口头传统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民族性的集中体现,形塑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鲜明的族群意识和集体记忆,积淀着民族群体的文化根脉、哲学意识、审美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正如向云驹所说:“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色和
文化根基,规定并长久地影响着民族文化的风格、特征、面貌。例如各民族无不具有的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歌谣、史诗等,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口头文学的美学特征在语法、词汇、音韵、发声、修辞、比喻、想象的独在与吟诵、说唱、唱诵、讲述、复沓、重叠、诗意、叙事、抒情的独特的套路、结构和体系。”①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学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就是从搜集、整理、改编民间文学转向书面文学的,一些民族作家甚至终身以民间文学的题材、体裁为创作对象,民间文学蕴含的价值取向、实用功能、艺术思维方式等,全面影响着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语言、结构、审美风格、话语模式等,特别对于书面文学相对匮乏且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民族来说,民间口头传统对作家审美观念的影响更加明显。
珞巴族作家亚依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生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从小吸吮着极其丰富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化的乳汁成长,从小耳听惯了博嘎尔 (珞巴)闻名的传说 ‘加英’。”②亚依:《我的故事》,《民族文学》2013年第1期。锡伯族作家郭基南曾说,他祖母名叫阿法罕芝,非常贤慧能干,能阅读锡伯文书籍,又善于讲故事。郭基南四五岁时,祖母每天晚上都将其抱在怀中,绘声绘色地为他讲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有时还讲述汉族古典小说的片断。她还经常带着孙子到街坊邻居家去,参加锡伯族乡亲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 家庭 “念说会”(锡伯语叫 “朱伦呼兰毕”),欣赏娓娓动听的文学作品朗读。遇到民间婚庆喜筵,祖母还带他去听 “沙林舞春”(婚礼歌)等锡伯族习俗歌谣。这些丰厚而渗透在人口较少民族生活中的口头传统,为郭基南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创作基础。
毛南族作家谭亚洲是个知名的民间歌手,善于即兴对歌,常常通宵不败。他从小便受到家庭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的民歌唱本,接触了很多的民间歌手。毛南族喜对歌的民风使其有许多的 “出征”的机会,为其日后收集整理民歌及从事诗歌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诗歌无论主题、题材及其韵味都可见民歌的影响。在阿昌族作家孙宝廷、罗汉等人的作品中,读者能体验到典型的民间口头传统韵味。在裕固族文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描写女性出场时,不像汉族作家那样先把女性俏丽清秀的面容描绘一番,对女性外貌的描摹大多都省略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她们歌声的描绘,也就是说,作家以天籁般的美妙歌声来定性她们的美丽,这是民族文化在书面文学中的典型表现,如苏柯静想的 《白骆驼》先出场的就是心上人美妙的歌声:“如草原上的暖风一般扑面而来”。《雪莲》中雪莲的出场:“我”早晨刚起床,“一阵动听的歌声传入耳中”,这歌声甚至让 “我禁不住拍起手掌来”。铁穆尔的 《魔笛》中的主人公胡热坐在河边吹笛子,“听见河对岸传来一声嘹亮的歌声,他忙起身看时,那个姑娘背着羊皮袋
正欢快地从山路上走向河边”。姑娘美妙的歌声让胡热感觉 “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①参见钟敬文 《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绝大多数景颇族作者均通过搜集整理自己民族的口头文学作品步入文坛,且成绩较突出的作者几乎都同时兼事本民族口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景颇族历史上没有文字,也没有完全成型的哲学、自然科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伦理、宗教、民俗、艺术等观念形态尚未彻底分化独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古老的口头文化传统成了他们民族全部精神文化的基本形式。根据1986年德宏州抽样调查,在景颇族中小学生中间,有22.43%的人受本民族的神话古歌传说故事的影响最大,甚至超过了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其他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的人数比例更是高得多。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生成并崛起的景颇族文学,自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口头传统 “移位”到文学创作之中,渗透着口头记忆的烙印,这在景颇族作家岳丁、岳坚、玛波、石锐、晨宏等人的作品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丰富而多彩的口头传统,形塑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决定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风貌、艺术特征或文学性的表现形态。②目前,在民族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者,还是主流文学研究者,往往以 “落后”、“粗浅”、“文学意味淡漠”等观点,忽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制约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文学性是文学自身的属性,任何一种文学都要有其文学性的存在才能决定这种文学的存在。问题在于,我们要以一种平等、对话的研究立场,才能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加以研究,而不能预设某种观点或立场去套用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自身。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裹挟,人口较少民族因人口规模小、文化根基相对脆弱、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单一等原因,很难经受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冲击,面临民族文化解体的风险,“知识和传统对于部落本身是最大的悲剧,常常并未消亡,但其文化的精髓丧失了,留下的往往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既是自身过去的影子,又是身在已开发世界中的我们的影子”③[苏]尤金·林登:《失去部落,失去知识》,《民族译丛》1993年第5期。。人口较少民族普遍存在 “流散”的现代性体验,“在伤痕累累的云彩下漂泊,在季节伸开的手掌上流浪”(锡伯族诗人傅查新昌 《解决》)。这种 “流散”既是物理家园的沦落,更是失去文化根基后的精神 “流散”。普米族诗人曹翔把这种体验概括为经典化的 “过客”意象。出于对外来强势文化或自觉或自发式的消解,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和守望,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试图从民族文化记忆中,寻求建构自我身份的话语资源。在多元文化引发的 “流散”体验越来越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民族意识之时,向民间口头传统寻求叙事资源并以此作为建构自我身份的必要在场,同样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叙事的基本走向,并影响到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表征。也就是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民间口头传统的一再回望,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民
族的集体记忆,为一个民族的延续建立起精神图腾。
三 民间口头传统中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审美表征
达斡尔族作家李陀在 《致乌热尔图》的信中说:鄂温克 “虽然有十分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传统,却由于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因此一直未能产生以文字语言为表现手段的 ‘正规’的文学。这使你拿起笔来进行写作时一定感到极其困难。你出身于一个根本没有小说传统的民族”①乌热尔图:《沉默的播种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 253页。。即使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大多具有汉文化教育背景,受汉族文学和世界各国文学的文学观念、创作思潮、艺术技巧等的影响,但长期浸染的民间口头传统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 “百科全书”,在 “深层结构”上影响到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审美观念的文学表征。譬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多年里,怒族从未出现过一篇算得上文学创作的作品,更没产生一个称得上是作家的人。只有到了接受新型的学校教育,方才产生一批优秀的怒族知识分子,其中有志于开创怒族文化和文学新纪元的杰出者在搜集与整理传统文学的过程中,有了较为丰厚的思想积累及艺术积累,怒族当代文学这株幼苗,方始破土发芽。②攸延春:《怒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怒族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状况,在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民间口头传统浸润及制约之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题材选取、意象设置、语言运用、叙事风格等方面,均与民间口头传统存在或隐或显的关联。总体而论,主要表现为 “民间故事母题”的现代重述、“口语化”的讲述方式和 “对话体”的叙述风格等审美特征。
“民间故事母题”的现代重述,是民间口头传统影响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典型表征。中国学界通常以美国学者汤普森在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对母题的论述为参照,汤普森认为:“一个母题是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绝大多数母题分为3类。其一是故事中的角色——众神,或非凡的动物,或巫婆、妖魔、神仙之类的精灵,要么甚至是传统的人物角色,如像受人怜爱的最年幼的孩子,或残忍的后母。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 魔术器物,不寻常的习俗,奇特的信仰,如此等等。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 它们囊括了绝大多数母题。”③〔美〕史蒂斯·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99页。鄂温克族作家杜梅的 《木垛上的童话》,以双层文本结构的“互文性”安排,巧妙穿插 “小雪兔找神奇蘑菇”这一民间故事讲述和小主人公妞妞、山普和小恩勒有关 “追求理想”的讨论,妞妞、山普和小恩勒每次在木垛边嬉戏、玩
耍时,妞妞都要讲一段 “小雪兔找神奇蘑菇”的故事,然后引起山普和小恩勒有关打猎和自己理想的争论。妞妞、山普和小恩勒等对理想的追求本身就是 “小雪兔找神奇蘑菇”这一民间故事母题的现代重释。阿昌族作家曹先强的 《远山童话》的故事情节,明显脱胎于流行于中国各民族中的民间故事—— “照镜子”这一母题。仫佬族作家鬼子 “在进入文坛以来,一直没有亮出自己的身份,在他持续不断的小说创作中,也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所属民族的特色,他对自身的仫佬族身份是持回避态度的”①黄晓娟:《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第二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 《会议手册》,2005年12月。。鬼子也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品与自己的出身无关,不承认自己是 “少数民族作家”。他曾说:“有人说,我的创作与我那民族本身的一些渊源有关,但我却丝毫没有这样的痕迹。”②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针对有人说他的创作与其所属的民族有渊源时,鬼子明确反对:“我却丝毫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丝痕迹。”针对鬼子的这些言谈,学界却不加深入论证地就直接以 “鬼子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创作进行着完善自身文化身份建构的复杂工程,他对仫佬族文化、文学与汉民族文化、文学均采取既外在又内在,既依附又背离的双栖性策略。在与多种文化展开对话与交流中,作出取舍,为己所用,这是文化身份重构与定位的重要手段,也是鬼子艺术创作的特殊方式”③黄晓娟:《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的建构与交融—— 以作家鬼子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 3期。作为预设性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以鬼子的作品为例,探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口头传统的关系,也许更具示范性意义。
笔者把鬼子的作品加以抽象化处理后,发现他的作品几乎都存在 “缺失——寻找——失败”这一故事母题,如:
(1)《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寒露的母亲因经济拮据而偷拿了掉在地上的一块脏肉,而导致父亲离家,寒露及其母亲开始外出寻父,最后家破人亡。
(2)《被雨淋湿的河》,晓雷因不愿像父亲一样从事小学教学,而外出打工,终因不遵守当前社会中的违背正常秩序的所谓规则而死亡。
(3)《瓦城上空的麦田》,李四六十寿诞时,想让几个在瓦城的孩子为自己祝寿,但几个孩子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忘记了父亲的生日,李四不得不进城寻找几个孩子 “讨个说法”,最后惨死在车轮下。
(4)《一根水做的绳子》,无论是阿香,还是李貌,都是情感缺失,二人的偶然接触也被损坏,导致阿香不离不弃地寻找李貌,最终二人双双死亡。
其他如 《大年夜》、《农村弟弟》、《苏通之死》等,都能抽象出上述的故事母题。这一母题恰是民间口头传统故事的基本母题,也是几乎所有民族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生产技能相对缺乏、生存环境相对恶劣、人自身精神状态相对不自由
的状态下,对外在世界的一种观照模式或体验方式。譬如,神话、史诗、传说、故事等,几乎都在表述着因自身缺失而不断寻找克服缺失的方式方法这一共有母题,如仫佬族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如 《得芬和钢年》、《凤凰山和鬼龙潭》、《望郎石》、《稼》、《鸳鸯石》等,都是源于对各种 “缺失”母题的不同建构。鬼子出生、成长于民间文学发达的仫佬山乡,他的文学创作与本民族口头传统自然或隐或显地存在关联。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般的民间口头故事都是以喜剧性结尾,“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是其基本结构模式。为什么在鬼子的系列作品中,所谓的 “缺失——寻找”这一故事母题却走向了 “失败”这一悲剧性结尾呢?这就需要对仫佬族的历史和现实境况加以综合性考察。
与鬼子矢口否认自己的创作与民族出身无关相反,达斡尔族作家萨娜明确强调自己创作的民间资源问题,她曾说自己在创作上吸纳了不少民族文化的因素,在 《白雪的故乡》中更是把东北 “三少民族文学”的创作情况作了总结:“三少民族创作的资源来源于民间神话,部落和家族传说,以及英雄的故事。”(《白雪的故乡》)正是自觉借鉴和吸收民间口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技巧,在萨娜的有关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才普遍存在着民间故事 “二男一女”的故事原型,如:
(1)《阿西卡》中的索伦、天秋和阿西卡。
(2)《有关萨满的纪实与传说》中的阿勒楚丹、木格迪和斯罕尔玛。
(3)《野地》中的托博坎、沃登和古珠讷。
(4)《额尔古纳河的夏季》中的白津、亚森和北奇。
萨娜的 《幻觉的河流》、《哈勒峡谷》、《鞭仇》等小说,都可视为 “二男一女”母题的变体。而这一故事母题恰是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特别是莫日根的故事的基本结构模式。达斡尔族莫日根的故事情节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理想追求和审美取向,加之口头文学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使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有着相对稳定的结构方式。作为自觉且善于借鉴或吸收民间故事传统的萨娜,她的作品中的 “二男一女”式的文本结构,蕴含无限的故事拓展空间,这一类型作品的叙述者加以肯定的男性主人公都是出身贫苦、吃苦耐劳、坚强勇猛、敢于担当的人物,如 《阿西卡》中的索伦、《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中的阿勒楚丹、《野地》中的托博坎、《额尔古河的夏季》中的亚森等;另一方男性则是贪婪、自私、懦弱的人物。同时,其中的 “二男”模式也可扩展成 “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开放与保守”、“卑鄙与高贵”、“勇敢与懦弱”、“承担与逃避”等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其中的女性角色也并不一定是作品的主体,但她是一种检验民族精神的标杆,只有在这一标杆面前,男人代表的精神气度、道德水准、价值取向等才得以凸显。
如果说,“民间故事母题”的现代重释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对口头传统的隐性
吸纳和改造的话,“口语化”的讲述方式则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对民间口头传统利用的外在表现。口头传统具有鲜明的口述性、交流性、互动性、集体性、传承性等基本特性,“听众出场参与呼应故事的作用,主讲人和听众共同参与讲故事,这是一种起与应轮流呼应的说唱形式”①参见 Elizabeth Ann Beaulieu,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2003,p.253。。正是源于口语文化的熏陶,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体现出明显的 “口语化”特点。达斡尔族作家苏华的 《金屋、银屋,不及老屋》中有这样一段:“不过达斡尔姑娘似乎不大可能起这么一个哈萨克味儿十足的名字呀,那么,人家为之动容的就不会是达斡尔姑娘啦!”在这里,“呀”、“啦”等语气叹词无不体现口述文学的典型特征。再如,乌热尔图的 《老人与鹿》开头说:“有个老人和孩子,走在树林里。”这正是民间口传文学常见的开头方式。裕固族作家达隆东智的 《猎豹》也体现了这一点:“从此,在包拉尔山的群山之中再也没有遇见雪豹的踪迹……好多年过去了,巴吉还经常回到草原上……”这正是民间故事中 “从前……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典型句型。裕固族作家苏柯静想在 《白房子黑帐篷》中也沿用了民间口传文学的讲述方式:“这是一个到处都能望到绿色的盛夏,满坡的山丹花如点点珍珠,争奇斗艳。谁都知道,祁连山深处的阿尔可草原又遇上了好年景。”故事讲述的“口语化”还体现在 “程式”的运用层面。所谓 “程式”,帕里认为,是 “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洛德在此基础上又补充说,程式是适应表演的急迫性而创造的,最稳定的程式是诗中表现最常见意义的程式。②〔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6页。这一点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中有着极为突出的表征。在 《玛鲁呀,玛鲁》这篇不到4000字的小说中,“努杰他走了,他走了努杰。他是不想走的,我知道。他从来没想到走,一点儿也没想到,可他还是走了”这种 “程式”化重复就连续出现重复了四次之多,叙述者在转述努杰的姐姐巴格达的话时一再重复 “她说”这一人物行为。“她说,七年前,努杰就在那个地方,真的打过一头鹿。她说,就在她去驮肉的地方,她说,努杰也许那天做了一个梦,她说,他想起过去的事了。她说,他就把这个梦当成真的了,她说,他真的这样干了。”“我”在面对 “玛鲁”神灵的表白和祷告中,追述了姐弟三人之间的故事,通过叙述者反复的忏悔或反省,达到与死者、与神灵的握手言和。因为在没有文字的口头传统中,吟诵者或演唱者很难掌握大量的口传故事,他的重复是为了拖延故事的讲述时间,更好地思考如何组织下一步的故事情节,这就必须反复使用某些片语。这些片语的作用,不是为了重复,而是为了构造诗行。换言之,它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具有固定含义 (往往还具有特定的韵律格式)的现成表达式。同
时,这些程式还有 “传统性指涉”的意味。也就是说,读者要思考,这些程式的 “言外之意”是什么。所以,重复是故事讲述者不可或缺的成分;二是从形式上更符合讲故事的絮叨状态,同时,也是在不断的话语重复中,引发人们对努杰出走的思考:提醒读者理解这种近乎原始的口传故事的表达方式对于一个以 “听觉文化”为特征的民族的意义,思考这些言说中留存着的民族记忆,民族经验,以及这些民族记忆和经验的当代语境。这一点在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 《寻找维拉》①这是萨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笔者的小说 《寻找维拉》中的部分,系未刊稿。中也有所体现。话语重复蕴含着多重阐释的空间:“那些重复使用的词语,因为反复的使用而开始失去其精确性,这些重复的词语是一种驱动力量,它使得故事中所赋予的面对神灵的祷告得以实现。”②〔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92页。
随着以逻辑思维或理性思维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现代性”文化,对人口较少民族日甚一日的冲击,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的传统思维方式、言说方式或书写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现代转型,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现代性特征,但长期在 “神山圣水”中形成的 “诗性智慧”仍作为一种潜在结构,影响着当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对话体”叙述方式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征。口头传统的创作过程必须有听众的直接介入,有现场听众的反应和互动,听众的情绪和对表演的反应等都会作用于讲述者的表演,从而影响到叙事的长度、细节修饰的繁简程度、语言的夸张程度等,甚至会影响到故事的结构。听众的构成成分,也自然会影响到故事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对口头传统来说,“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③〔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114页。。口头传统在讲述者与听众间的交流和互动,使口头传统具有典型的 “对话体”的美学特征。作为从口头传统中汲取叙事资源的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也呈现出一种 “对话体”的美学风格,如凯伯德所说,“受口述传统的影响,古老传说和民间故事往往采用对话形式”。
为何受口述传统影响就表现为 “对话体”的叙述方式呢?美国学者沃尔特·翁对此作了分析,“在口语文化里,语词受语音约束,这就决定了人们的表达方式,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过程……那么,‘口语文化如何且为何能够以有组织的方式构建知识’呢?”。他认为:“一个参与会话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人口语文化里,长时间的思考和与他人的交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④〔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26页。在乌热尔图的 《胎》中,叙述者一直在以第三人称叙事,突然间就转换为 “我—你”的对话体叙述,在 《雪》、《清晨升起一堆火》、《玛鲁呀,玛鲁》、《你让我顺水漂流》、《在哪儿签上我的名》、《萨满,我们的萨
满》等,也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进而转换为 “我—你”间的对话关系。在独龙族作家罗荣芬、裕固族作家铁穆尔、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景颇族作家玛波、阿昌族作家孙宝廷、毛南族作家谭自安等人的作品中,也都洋溢着这种 “对话体”美学风格。
四 民间口头传统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建构方式
书面文学是作家在独立状态下的个体写作,创作者不断构思、打磨和修改作品的结构和情节,民间口头传统则因缺少文字这一记忆工具而不得不依靠某些固定模式为叙事动力,如重复、不停的插入、闪回等,来延续不停的口头表演。因此,口头传统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模式——重复的程式、类似的母题、类同的故事型式,就导致民间口头讲述不遵守线性叙事逻辑。
据皮博蒂研究,线性情节与口头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兼容的,诗人在描述英雄盾牌时可能会沉迷于细节而忘乎所以,完全忘记叙事的轨道。同时,由于口头传统是一种现场表演性的民间集体性说唱行为,说唱者不可能脱离听众而单独说唱,离开听众对说唱者来说就犹如鱼离开水,听众与说唱者共同承担起说唱行为,听众的参与与加入说唱是民间口头传统的基本特征。正如有学者所说:“听众出场参与呼应故事的作用,主讲人和听众共同参与讲故事,这是一种起与应轮流呼应的说唱形式。”①Elizabeth Ann Beaulieu ed.,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2003.p.253.尽管 “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终结了古典神话,然而,神话思维却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之中,转换为一种现代意义的神话方式,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②颜祥林:《现代神话与文艺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部落丰富的口头传统尽管丧失了其原生语境,但口头传统的创作思维却被当前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所汲取和承袭,直白本真的生活场景的展示、略显夸张的笔法、口语化的言说方式等,无不是源自山林峡谷、森林荒漠的壮阔之美和深厚的民俗文化,它们对当代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造就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特有的文学气质和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特别是口头传统中的对话体叙述方式更是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结构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并使之呈现出空间并置的结构状态。
乌热尔图的 《在哪儿签上我的名》的故事说的是鄂温克族猎人腾阿道,在诺克托要求下到多勒尼猎场打猎,结果在森林中误射了装扮成熊的人。故事就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者 “我”(即腾阿道)的口吻来讲述的。作为讲述者的 “我”始终是与潜在对话者(即警察)的在场为叙事动力,文本也正是以二者对话完成的。所以 《在哪儿签上我的
名》不时中断叙事顺序和干预叙事进程而呈现空间并置状态,如 “我”正在讲述故事时,突然说:“你说这样讲不对,我不该在这里……这是我说漏嘴了,你不在意吧”,“为啥要停一会儿?我才提起一个话头……是你让我喝口水?可我一点都不渴。”在这种对话中间叙述者 “我”讲述了诺克托的故事,讲述了多勒尼猎场的故事,讲述了叙述者对当前猎人的生活遭遇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叙述者和诺克托面对事件的不同态度等,从而使鄂温克民族的民族性格、言说习惯,甚至思维方式都得到呈现。这种讲故事的程式化形式,在乌热尔图后期的几部作品中都很容易发现。特别是多元文化的日益冲击,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不得不以 “故事叠加式的讲述体模式”、“多重叙述者空间并置”及 “视角越界”等方式,建构空间化的结构模式来呈现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这样既能揭示出民族 “隐藏的文化身份”、“隐蔽的历史”以避免被他者所误读,又能够建构出 “想象的共同体”。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更是从民间口头传统中汲取各种叙事方式,如重复、隐喻等来建构空间结构的书写文本。
在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 《金色牧场》中,第一个故事层是叙述者 “我”在讲述“我”的经历和故事的 “母体叙述”,这个 “母体叙述”实际上是为下一个故事层提供人物讲述及其相关背景的依据,是故事展开的 “序幕”;第二层面的叙述中心是 “母亲”,她向叙述者 “我”讲述达斡尔族的民族传统、历史迁徙和家族起源。在 “母亲”不断回忆民族的历史和有关祖先的记忆中,年轻的叙述者 “我”真实触摸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中汲取了在当下现实语境中生存下去的力量和勇气。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在 《山林的回声》、《鄂伦春人与自然之约》等作品中,也是以这种叙述方式来讲述故事的。在裕固族作家玛尔简的 《阿扎和白马》中,叙述者 “我”只起了一个开头的作用,随即以 “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建构出文本的故事叠加式的叙述模式。达隆东智的 《遥远的巴斯墩》以叙述者 “我”不停地寻访裕固族的历史和人物,听取有关裕固族的回忆和历史传说、故事等,再现了 “尧乎尔”的迁徙历史、风土人情等作为作品的第一个层面,叙述者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追求叙述的真实性;在第二个故事层,叙述者 “我”就让人物华洛老人等长者以当事人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 “尧乎尔”的过往兴衰、荣辱变迁,以强化自我身份的归属意识,并蕴含对自我文化的独特性追求,抵制他者文化侵扰的可能。
五 结语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与他们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存在互动性关系。要使存续能力较为脆弱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能够在多元文化混杂语境下得到健康良性发展,就应该使其文化发展有一个缓冲、过渡的过程。原本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发展缓慢、甚
至是静态存在的,而现代化的发展是剧烈的、全方位的,如果不加以保护,这种冲突和碰撞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所以不能按照普适性的发展规划来要求人口较少民族,应给予其调整、适应的时间和条件,慢慢培育、逐渐巩固,才能强化其自身文化的造血功能,犹如刚载上的树苗不能施加营养过于丰富的肥料。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人口较少民族都被纳入快速的资源开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之中,导致本来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出现环境污染,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而人们对新的生产生活环境又无法适应的现象,加速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消解的风险,所以在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一再出现对现代性的不满或犹疑。譬如,在 《萨满,我们的萨满》中,乌热尔图以萨满的预言揭示了鄂温克族资源开发后的现实困境, “不久的那一天,林子里的树断了根,风吹干了它的枝,太阳晒黄了它的叶……不久的那一天,鸟儿要离开林子,像秋天的松果甩开枯枝……”《哪儿签上我的名》借猎人腾阿道之口,指出现代性发展带给狩猎民族的创伤,“整天你耳根里听到的也是轰轰轰打雷似的机械声,还要咔咔嚓嚓大树被锯倒的怪动静”。鄂温克族狩猎所依靠的森林被大量砍伐,直接危及鄂温克族传统生产方式的继承,驯鹿因吃不到苔藓而濒临死亡,鄂温克族传统的风葬也因难以找到像样的树而导致萨满卡道布老爹甘愿死在猎人的枪口之下。在达斡尔族作家萨娜,布朗族作家石香兰、陶玉明,阿昌族作家孙宇飞、罗汉、曹明强、孙宝廷,普米族作家何顺明、殷海涛、尹善龙、汤格萨甲博、和文平,德昂族作家杨忠德,怒族作家彭兆清、李金荣,基诺族作家张志华、张云,独龙族作家阿柏、罗荣芬等人的文本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对 “过急”现代性的忧思。就此而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民间口头传统的现代性改造,并不是止于文学形式的简单选择和叙事资源的再转化,其实也蕴含着以空间化式的地方性言说方式来对抗现代性发展之意,并试图以空间化形式倡导一种适于本土现实的多元现代性。换言之,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渴望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进入现代化,而不应强行纳入线性发展的心态,其文学创作以空间化结构来抵制线性的、进化论式的现代化,空间化的并置恰好表达他们所渴望的空间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文学的空间结构与人口较少民族在现代性话语中的焦虑和阵痛是一种互渗性勾连。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当代人口较少民族尚无法在现实或政治层面实施某些对抗性策略,就不得不在话语或文本层面实行一种仪式性、想象性的质疑或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文本的空间并不是单纯容纳文学素材的一种文学手段,而是与种族、阶级、性别等交相融合的一种意识形态之网,是表达文化或身份差异且以此差异书写转化一种寻求自我言说方式的手段,罗伯特·史达姆将其称为 “再现的重负”,即以一种新的表意系统来对抗自身话语权日益丧失的现实,以建构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文学是某种社会现实本相之表征,本相是人类
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特别是社会阶级区分。由表征与本相的关系——社会现实本相产生表征,而表征又强化社会现实本相——他说明社会本相之再生产机制,也就是一种社会价值或制度如何延续。①参见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By Richard Nice,London:Routledge&Keg Paul,1984,p.231。社会本相指的是人类生存资源的分享、分配与竞争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及在此体系中的相关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换言之,任何一种文学叙述都是权力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的表征形式。因此,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民间口头资源的审美重述,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的当下焦虑,存在着一种极为鲜明的视域融合和逻辑谱系,“通过叙述性言说来研究民族不仅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其语言和修辞上,它的目的还在于改变概念性的对象本身。如果有问题的文本性 ‘封闭’对民族文化的 ‘整体性’提出质疑的话,那么其积极价值便在于展现那种广泛的播撒,通过这一过程来建构与民族生活相关联的意义和象征场”②Homi Bhabha,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0,p.2-3.。
Memory,Tribal Identity and Traditional Oral Folk Literature: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s a Case
Li Changz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Fuyang Normal College,Anhui Province,Fuyang 236037
Chinese minorities keep time-long oral folk tradition,which has been and is still influencing discourse and diction,aesthetic construction,values,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Though much literature has been published on this theme,many issues are still understudied,such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oral folk tradition and literary writing,i.e.how oral folk tradition affects literary writing,what mechanism is deeply behind,what laws can be summed up,just to name a few.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furthe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v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oral folk tradition and literary writing,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s a case.
oral folk literature tradition;writer&literature;nationalities with less population
李长中 (1972—),男,河南永城人,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后,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联系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236037)。Email:changzhe_li@126.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项目编号:13FZW03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