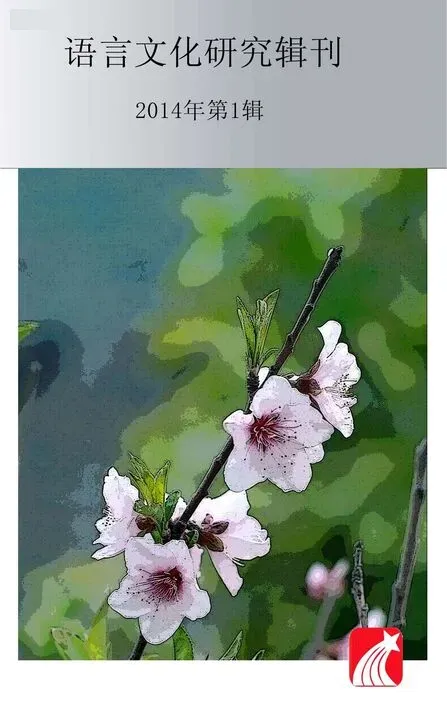诗歌之美,贵在中和
——解读瑞恰慈对诗歌的语义美学分析
2014-03-10谢瑾
谢 瑾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9)
诗歌之美,贵在中和
——解读瑞恰慈对诗歌的语义美学分析
谢 瑾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9)
“中和诗论”是瑞恰慈语义美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对诗歌经验与价值从语义学及美学的双重维度作出的探析。本文从形式结构、阅读经验、复义意涵、冲动平衡等层面,以语义美学视角解读与提炼瑞恰慈的诗论观,指出瑞恰慈 “中和诗论”的核心是高扬诗歌的中和之美,可概括为诗歌的形式融合之美、音韵谐和之美、意义杂合之美及情感调和之美。瑞恰慈对诗歌的语义美学分析是语言学与美学视域融合的产物,既突出了诗歌的语言形式之美,也彰显了诗意经验的美学价值,更高扬了诗歌平衡人类情感的生存美学功用。
诗歌之美 瑞恰慈 中和诗论
一 引言
语义美学是语言学与美学融合汇通后产生的交叉学科,也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美学领域的集中体现。语义美学先驱瑞恰慈一方面关注哲学及美学中存在的语言问题,另一方面则对文学艺术中的语言美加以探析。瑞恰慈认为,诗歌是一种典型的诗意语言,具有创造与生成的诗意本性,是语言情感用法之极致,也是语言之美高度而集中的体现。因此,瑞恰慈对诗歌这一语言美的典型体现样式进行了详细的语义美学分析,指出诗歌之美在于 “中和”。瑞恰慈的 “中和诗论”既是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与美学视角对诗歌之美的别样解读,也与中国美学 “以和为美”的思想之高度契合,体现出中西思想的交汇与融通。本文从形式、音韵、意义及情感四个方面,解读瑞恰慈的 “中和诗论”,指
出诗歌具有形式融合之美、音韵谐和之美、意义杂合之美及情感调和之美。诗歌的“中和之美”使其成为语言之美、经验之美、存在之美的聚集与融合。
二 形式融合之美
诗歌的中和之美体现为诗歌的形式融合之美,即诗歌具有言说与文本合而为一的独特形式。①I.A.Richards,Science and Poetry,London:Kegan Paul,1926,p.22.就起源而言,诗歌通过行吟诗人的唱诵口口相传,本质上是一种艺术的言说模式,还是诗人聆听神谕之后说出的真理,呼唤着人们用耳聆听、用心谛听。诗人的创作是对词句的声音与形式的充分调动。言说具有时间性,是语言符号的延续与流动;文本具有空间性,是语言成分的交叠与聚集。作为言说和文本两种语言形态得以并存同现的场所,诗歌是语言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汇聚,是语言形式融合之美的极致体现。
作为一种文学文本,诗歌通过分行、分节、押韵等外观形式,构成其独特的形式结构,使之与其他文学类型在形式上具有本质区别。诗歌中的对仗、排比、韵脚等独特的形式特征,让诗歌语言更为工整精致,能产生极富张力的审美效果,让读者在阅读诗歌的瞬间就能感受视觉形象的刺激,从而在心理上对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加以观赏和定位,即用诗的眼光去看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形式与意义的密切合作是诗的风格的主要秘诀”②I.A.Richards,Practical Criticism.Edinburgh:The Edinburgh Press,1930,p.233.。
语言的形式美是物质存在的形态美,通常诉诸视觉与听觉,故而直观可感。亚里士多德在 《伦理学》中探讨了审美经验的六个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审美经验源自视觉和听觉感受到的和谐。③W.Tatarkiewicz,A History of Six Ideas:An Essay in Aesthetics,London:Springer,1980,p.314.瑞恰慈也指出:“在几乎所有的诗中,字句的声音和感觉 (这往往被称为诗的形式,以便与诗的内容区别开来)首先起作用,这一事实微妙地影响了我们对诗歌中字句含义的理解。”④I.A.Richards,Science and Poetry,London:Kegan Paul,1926,p.23.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之所以能在人们的情感经验中产生综感,是因为人们不仅对事物进行感知,而且调动了理解、情感、想象等多种心理功能,形成一种综合的审美愉悦。
形式美的直接来源是诗歌的形式结构,但并非只有诗歌的语言形式特征才能激发其形式美。在瑞恰慈看来,诗人能通过语词的独特排列方式使感觉经验连贯、有序、自由。⑤I.A.Richards,“Poetry and Beliefs”,in K.M.Newton,20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A Reader,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p.40.当诗歌的文字符号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发生情感冲动的微妙波动。当文字的形象映
入 “心眼”之内,文字代表的事物的形象就会浮现出来,这些形象继而触发经验因子与发生情感反应,进而发展为情感态度。瑞恰慈高度认可言说中话语声音在倾听者那里产生的心理作用,因为文字的声音落到 “心耳”之中,能激发起丰富的感受与想象。①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London:HBJ Book,1946,pp.1112.因此,真正的诗意语言是形式与意义的协调一致,是听觉与视觉感受的相互激发,是言说与文本的合而为一。作为言说与文本的同现状态,诗歌充分地体现出形式的融合之美。
三 音韵谐和之美
无论是作为声调语言典型的汉语,还是作为重音语言代表的英语,都具有强烈的音韵之美。诗歌正是语言内在音乐性的充分体现,是音韵谐和之美的集中体现。
诗歌之所以常被视为文字的音乐,是因为诗歌的创作过程正是围绕着节奏和音律展开的,且诗歌的唱段和格式化的吟诵方式,也是诗意语言与日常语言相分离的重要特征。诗歌的阅读经验同样离不开语言音乐性带来的审美愉悦。吟咏是对诗歌的反复琢磨,是理解与欣赏诗歌的必要步骤;读诵使得纸上僵死的文字在声音中获得生气,是体味诗歌意境的绝佳途径;朗诵则由眼、口、耳、脑等诸多器官共同参与,是一种复杂的、多向的思维活动,也是感受诗歌审美真意的不二法门。通过诵读,诗歌变得有声有色、有形有神。作为文本与言说的双重特质得以合而为一,诗歌语言丰富的乐感与美感在多个感官的介入所产生的联觉中被充分激活。
语言的语音纷繁不一,能激发不同的心理反应。因此,不同的音素能引发不同的听觉效果,有的清脆悦耳,有的尖利刺耳;有的柔和温婉,有的苍劲阳刚;有的戏谑轻佻,有的庄重肃穆。在诗歌中,效果各异的音素为诗人艺术地驾驭,从而形成声音的和谐共振。此外,诗歌还富有抑扬顿挫、长短强弱的节奏与律动。诗歌运用语言的节奏与声律表现情感,而声律之韵能使诗歌的情感表达更加精炼生动。无论是汉语诗歌中的双声、叠韵、平仄律,还是英语诗歌中的头韵、尾韵、轻重律,都是语言音韵谐和之美最为极致的体现。《文心雕龙》中有 “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②《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黄叔琳、李详等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1页。的观点,国外学界也有语言存在音乐语法 (musical grammar)一说,认为语言的音乐性是语言内在的本性。人的乐感与生俱来,因此人类对语言的音韵美有着认知共性。语言内在的音乐性驱使人们在言说时,倾向于选择富有节奏感与韵律美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更好地展示语言的音乐之美,并通过语言交流与他人共享语言音乐性带来的审美愉悦。③Ray Jackendoff,“A Comparison of Rhythmic Structures in Music and Language”,in Paul Kiparsky and Gilbert Youmans(eds.),Phonetics and Phonology(Vol.1):Rhythm and Meter,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89,p.17.
诗歌通过语言文字将情感节律化,而这种审美情感的节律化来自诗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冲动。诗歌的节奏与韵律和人的生理及心理节奏相契合后,形成心物之间相契相应的同构关系,让人身心愉快,得到美的享受。诗歌声调的抑扬顿挫,节奏的轻重缓急,韵律的充盈悦耳,都会使人产生愉悦的审美感受。音韵与节奏形成的形式张力还能唤起情感,给心灵带来震撼。因此,诗歌中的音韵与节奏是遣词达意的工具,更是平衡协调情感的手段。诗歌还是动态的艺术样式,表现出生命自身的运动变化,体现出一种合规律性的情感运动方式,是一种节律化的语言文字结构形态。通过感受诗歌的音韵谐和之美,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诗人欲传达的情感,进而通过想象活动产生联觉,最终体悟到生命的张弛与律动。
四 意义杂合之美
通常认为词语的意义是常在久居、固定不变的,瑞恰慈却将意义比作一株不断生长的植物,而不断变化自身意义的能力正是诗歌的本性与使命。尽管语言哲学家视清除语言歧义为思想澄明缜密的先决条件,传统修辞学与语言学研究也强调语言表述的明晰准确,瑞恰慈则高度肯定语义的模糊性,认为复义现象一方面普遍存在、无法回避,另一方面还是必要的交流手段,能产生独特的审美价值。瑞恰慈指出:“旧的修辞学认为,模糊是语言里的一种错误,希望对其进行限制与根除;新的修辞学则认为,模糊是语言力量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大多数重要话语的必不可少的表达方式,在诗歌语言与宗教语言中尤其如此。”①I.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p.40.语言的确定性使语言得以成为指涉与交流的途径,语言的模糊性则使语言表述具有弹性与拓展性。语言的模糊性与确定性正如硬币之两面,共同构成语言的本性。如果说科学语言高扬语言的确定性,诗歌语言则凭借多重语义的杂合,衍生出无穷无尽的意蕴之美。
诗歌语言的模糊性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模糊,绝不等于含糊。如果说含糊是对语言缺乏驾驭能力的后果,体现为语言表述的混乱无序,美学意义上的模糊则是具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者特意而为之的产物,旨在通过语言的朦胧疏放孕育出意境之美。正如康德所言:“模糊概念要比明晰概念更富有表现力……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②参见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正是由于诗歌语言的朦胧性,虚与实得以相生,意与境得以交融。这种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的审美意境,召唤着读者与作者进行对话,与文本展开交流,并在这种动态的交互往来之中发掘文本的意义与价值。
与瑞恰慈对诗歌复义的论述相映成趣的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 “诗无达诂”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页。这一观点。一方面,“诗无达诂”的原因在于诗歌的意涵往往隐而不露、秘而不宣,甚至 “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②语出白居易 《与元九书》。;另一方面,“诗无达诂”也体现出文学批评与赏鉴中的审美差异性与阐释多样性。任何一种对诗文的阐释在揭示出某些意义的同时,又会对其本质产生某种程度的遮蔽。因此,不必勉力追求对意义明晰的、唯一的阐释。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吾诗中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③钱钟书:《也是集》,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语言意涵的多重性与阐释的多元性充分拓展了语言的意义空间,也使诗歌这一语言美的极致体现成为可能。语义的模糊性为语言赋予了不断变化自身意义的能力,而意义的冲突、叠加、交织等复义现象,则拓展了诗歌的想象空间,丰富了诗歌的阐释维度,赋予诗歌以意义的杂合之美。
五 情感调和之美
瑞恰慈认为,一切美都具有将异质因素融合交构的能力,真正的美源自中和与综合。受柯勒律治和赫列斯特的启发,瑞恰慈视诗歌为言说与文本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具有净化心灵、升华情感的功能,能使冲动在对立、冲突、矛盾中趋向平衡、达至和谐。瑞恰慈的 “美在综感”这一观点体现出矛盾中求统一的辩证观,也是其 “中和诗论”的核心观点。
柏拉图认为,诗歌使人产生激情,需将诗歌逐出理想国。瑞恰慈却认为,诗歌可拯救现代社会中精神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类。在瑞恰慈看来,诗是多种复杂的冲动达至平衡的文本结构,是自身圆满的世界。诗歌之所以是伟大的艺术,在于能让读者进入一种沉思冥想的境界,在产生并组织自己的多种情感冲动的过程中体悟真、感受美、趋向善。现代社会中道德伦理的约束力日益衰颓,现代人的情感紊乱无序,欲望膨胀失控。因此,“需要一种根据调和而不是依据着分离企图压制的新秩序”④I.A.Richards,Science and Poetry,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Ltd.,1926,p.35.,使人性达至和谐,这正是 “中和诗论”所推崇的审美理想,即通过诗歌来拯救人类,推进文明。那么,这一审美理想何以可能、又如何达成?瑞恰慈从美在于综感的观点出发,指出诗歌具有疗治功能,能使人在混乱喧嚣、充满欲望与压抑的现代生活中寻得心灵的和宁与平静。诗歌在激发情感的同时,使人们克服了混乱无序的冲动,重返心灵的平和与情感的
平衡。①J.Paul.Russo,I.A.Richards:His Life and Work,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1989,pp.151-152.
诗歌之所以能使多种对立冲突的情绪实现平衡,首先是因为诗歌是语言传情达意功能的最高表现,诗歌的阅读体验能激发复杂多样的情感,使读者获得丰富的审美感受。真正优秀的诗作网罗了复杂的视觉形象、听觉形象、主观感受和心理印象,集多种互相矛盾却又相互浑融的情感于一体,从而形成一个丰富均衡、错落有序的整体。若诗歌无法使各种复杂的情绪和冲动达至均衡与和谐之状态,那么即便该诗有着生动的语言、精巧的意象,其审美价值仍会大打折扣。如果说科学语言的 “真”在于其陈述与客观事实形成对应关系,那么诗意语言的 “真”就在于诗意语言之“美”。在陈述诗性时,我们应关注的不是陈述是否真实准确,而是这种陈述体现的情感态度是否具备可接受性,也就是说语言的此种叙述是否能产生适当的心理效果,体现出存在者之间或存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态度。诗歌的诗性陈述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无需真实,只需为诗意语言的言说者与倾听者共同认可。正因如此,瑞恰慈才高度地肯定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对诗人来说,合乎情理的不可能要胜于不合情理的可能。”②Aristotle.The Poetics,Coradella Collegiate Bookshelf Editions,p.50.
诗歌还能通过调和多种复杂的情感,使人获得心灵的宁静,这是因为诗乃人之性情,诗人具有对人类共同经验加以组织和整合的异常能力。“通常相互干扰而且是冲突的、独立的、相斥的那些冲动,在他 (诗人)的心里相济为用而进入一种稳定的平稳状态。”③[英]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精神被瑞恰慈视为一个冲动系统,各种复杂的冲动在精神之中纵横交错、相互冲突、彼此束缚。由于诗人具有组织各种经验的能力,这些错综复杂的冲动在诗人身上能体现为冲动的调和,形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对普通人来说,要想体验此种平衡协调的状态,须以对艺术的感受与经验为途径。诗歌源自心灵的平衡与协调,又具有使人们获得心灵和谐的功用。在诗歌的审美体验中,心智能最轻松、最少干扰地达到自身的有机统一。④I.A.Richards,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Routledge,1924,p.102.
无独有偶,儒家思想也视心灵之和为礼乐之源头,“乐由中出,故治心”⑤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99页。。同样,文学艺术也通过诉诸人类共有的情感、冲动及体验来发挥作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正如 《诗·大序》中这段话所描述的,诗歌以表现情感为其主旨,而且是表现情感最直接的文学艺术样式。
诗歌的内在结构与诗人的情感活动具有同形同构的关系,正所谓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①《乐记·乐本篇》,杨天宇 《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因此,情感之调和能和宁心灵,而心灵之和是自然宇宙之和的映射与拓展。
六 结语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丰富的审美因素。诗歌是语言美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的精神之花。瑞恰慈从语义美学的角度,探析诗歌之美,对诗歌作为诗意想象驰骋空间的美学价值作出细致而充分的分析,彰显诗歌平衡人类情感的生存美学功用,高扬诗歌对心灵的疗治作用。瑞恰慈的 “中和诗论”也契合 “以和为美”这一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无论是 《中庸》强调个体内在情感之平衡协调的 “中和”论,还是 《周易》从宇宙论高度强调生命即美的 “大和”论,都充分承认 “和”是以差异性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诗歌通过对多种异质要素进行调和与综合而产生的 “中和之美”,正是瑞恰慈通过对诗歌的语义美学分析得出的核心观点。
诗歌之美,贵在中和。通过对瑞恰慈 “中和诗论”的解读与提炼,笔者认为诗歌的中和之美不仅在于诗歌的形式,也体现在诗歌的意韵、意涵乃至意境之中。诗歌的形式美在于诗歌是言说与文本两种语言形态的完美结合,诗歌的意韵美则是诗歌的音律节奏带来的审美愉悦,诗歌的意涵美集中体现为诗歌中复义现象对阐释空间的无限拓展,诗歌的境界美则在于诗歌的审美空间能让人进入心灵和宁的审美境界,能使复杂的情感冲动达至平衡和谐。诗歌既是语言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得以统一的文本世界,也是意义不断动态生成的情境空间,还包蕴并传递着复杂微妙的审美体验与存在经验。因此,诗歌的中和之美不仅是语言之美的极致体现,也是经验之美与存在之美的汇集。
The Harmony of Synaesthesis:I.A.Richards'Semasiological Aesthetic Views on Poetry
Xie J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Poetic harmony and synaesthesis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I.A.Richards'
poetic beauty;I.A.Richards;poetic harmony and synaesthesis
谢瑾 (1977—),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美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美学、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外文化比较等。联系地址: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430079)。Email:iamxiejin@yahoo.com。
semasiological aesthetics,which involv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beauty and values of poetic experience from both semasiological and aesthetic angles.Richards'views on the beauty of poetry will be explored from various aspects,namely,the formal construction of poetry,the reading experience of poetry,ambiguity in poetry,and reconciliation of impulses during the poetic experience.Poetic beauty as the harmony of synaesthesis will be outlined grounded on key points of Richards'aesthetic works,which involves the integrated form,the harmonious sound,the enigmatic sense and the synaesthetic experience.With his inter-disciplinary effort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fascinating nature of poetry,Richards has successfully highlighted the formal beauty of poetry,the aesthetic value of poetic experience,and the therapeutic function of poetry through coenesthe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