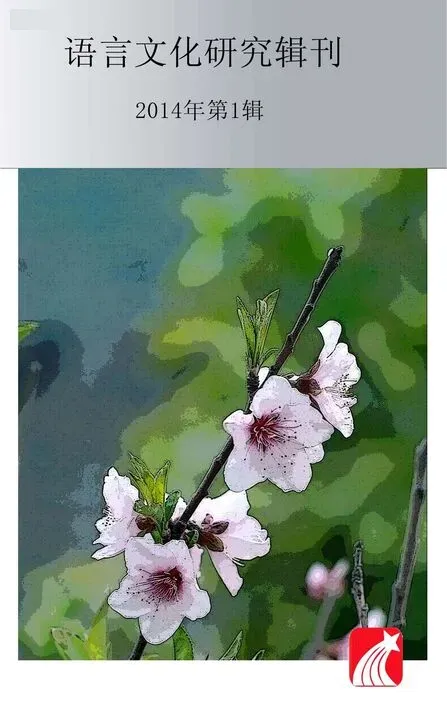《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发刊词
2014-03-10陈国华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发刊词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的创刊是一件好事。在中国,很多学术期刊都以 《××大学学报》或 《××学院学报》冠名。如果该学报的主办单位是专科或职业学校,如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外语学院、农学院、林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以校名命名该校的期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该期刊只刊登相关学科领域的文章,从校名就可知道刊物的学科属性。可如果该期刊的主办单位不是体育大学、外语大学、农业大学、林业大学、政法大学等单科 “大学”,而是university意义上的大学,即全科或综合性大学,那么 《××大学学报》就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学报,因为读者不知道该 “学报”的 “学”是哪一种 “学”。即使给它分出一个 “社会科学版”,也无济于事,因为社会科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多个学科。相比之下,《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在创意上有两个优点:(1)名字取得好,好就好在其学科定位十分明确、专业,让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份探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学术刊物,而且是语言学与文化研 究的跨学科 (cross-disciplinary)和学科间 (interdisciplinary)期刊;(2)包容性强,强就强在语言学和文化研究都各有很多分支领域,二者的结合可以辟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不仅语言学研究者可以来投稿,而且文字学、文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甚至烹饪学等等,凡可被文化研究这把大伞罩住的研究者,都可以为之贡献稿件,只要内容与语言有关。而这些领域又有哪个能说自己与语言无关?
语言和语言学是什么,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共识,这里无须赘言。文化是什么,哪些研究属于文化研究,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似乎没有达成一致。
人们常把 “文化”视为 culture的对应词,其实这两个词并不完全对应。英文culture借自法文,源于拉丁文cultūra,即谓词 colěre“种地、种植、培植”的过去分词阴
性形式;在cultūra前面加上agri-“田地”,就成了agricultūra“田地耕种”,即法文和英文的 agriculture“农业”。可见,英语国家人的说 culture,最初指的是植物的种植或栽培。后来culture不仅用来喻指牡蛎、珍珠、桑蚕、蜜蜂之类动物的养殖,而且用于细菌、细胞、组织的培养,同时还喻指对人的思想、品味、举止等的培养、教育、熏陶,以及由此获得的素养或修养。自19世纪中叶,culture又喻指 “思想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或类型,也喻指某一民族在其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习俗、艺术成就等”①参见 J.A.E.Simpson&S.C.Weiner,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nd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culture词条下第 5项。,这一义项的所指也就是今天文化研究的对象。在英语国家的人看来,culture“文化”的对立面是nature“自然”,明白了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区分自然遗产 (natural heritage)和文化遗产 (cultural heritage),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人观念中的 “文化”,与英语国家的人观念中的 culture颇为不同。“文化”一词由 “文”和 “化”二字组合而成。文在甲骨文里写作,在金文里写作,②参见徐中舒主编 《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文”字条。显然指刺画在人身上的花纹、装饰或图形,即 “纹身”。由于人身上本来没有这些图形,一旦出现,肯定是人为的,可以说该字的写法较好地表示了 “纹理、图形”这一意义。华夏文字发展到了篆文阶段,由于或字本身形状的独特性,省去其中代表图纹的笔画,也不影响其表意功能,于是这个字就写成了,与今天的 “文”没有任何实质区别。人身上的图纹是先民对自然界中花纹、纹理、形象的模拟或抽象,而象形正是文字最初创制的主要方法,“文”自然便有了 “文字”的意思;文字按照文法有条理地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文章,于是 “文”自然又有了 “文章”的意思。自然界里花纹、纹理、形象无处不有,天体的排列及其运行模式被称为 “天文”,山川地貌的形态被称为 “地文”(文和理是近义词,所以 “地文”又称 “地理”),江河湖海等水体的形状、变化和走势被称为 “水文”,人类的语言文字、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礼乐制度等被称为 “人文”。在华夏文化圈的人看来,“文”的对立面是 “武”,所以有 “文王”、“文帝”,“武王”、“武帝”之称和 “能文能武”、“文攻武卫”的说法。
“文”与culture词源和意义上的不同,加之 “化”字带来的语义,导致了 “文化”与culture在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上的不同。“化”字甲骨文写作,金文写作,篆文写作,③参见徐中舒主编 《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化”字条。通过一正一反两个人形,表示 “教人行走”,即许慎所谓 “教行”,或“转变”。④参见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化”字条。“文”和 “化”合在一起,意思就是 “文治教化”,⑤参见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文化”条下第1项。如 “圣人之治天下也,
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 《说苑·指武》)。“文德”意义上的“文化”,用今天的热门词来说就是soft power“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语言与软实力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其次,“文化”还用来指 “运用文字的能力及具有的书本知识”①参见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文化”条下第2项。,如 “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一意义上的 “文化”大致相当于英文的 literacy“读写能力”,读写能力的教学即语文教学,而语文教学又是教育学的重要内容,语言与教育的关系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广义上的 “文化”指 “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②参见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文化”条下第3项。。譬如,“他不相信汉朝对待匈奴的诚意,看不起长安文化”(曹禺 《王昭君》第二幕)。这个意义上的 “文化”无所不包,凡人类创造的事物,只要能与动物创造的事物区别开来,都属于文化。这样一种文化观为语言与文化研究打开了通往各个学科领域的大门。“文化”还是考古学术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③参见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文化”条下第4项。。这其实是从共时的视角来看待前一个意义上的 “文化”。不用说,某一特定时期的语言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题目,既可通过对史前文化的研究来推断史前语言的特征,又可通过对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探讨和发掘文化的演变。
通过以上对culture和文化的来源和语义演变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词殊途同归,最后在culture的最后一个义项和文化的后两个义项上达到了基本对应。
国外对语言与文化和思想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始于普鲁士语言学家、教育学家洪堡特,他通过对爪哇岛上卡维语的研究,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概念。④参见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β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38/1997年版。在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博厄斯通过对北美印第安语言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说;⑤参见 Franz Boas,Introduction to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11/1966。他的学生萨丕尔和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对北美印第安语言展开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语言相对性原则,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人的思维定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说的语言。⑥参见 Edward Sapir,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29/2002;Benjamin Lee Whorf,“Science and Linguistics”,in J.B.Carroll(ed.),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6。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 (Trobriand Is-
landers)的语言,特别是其园艺和魔法语言,进行了文化解读,认为语言对说话人的思维习惯、态度和行为有直接作用。①参见Bronis aw Malinnowski et al,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London:Routledge,1935。柏林、凯对基本颜色词的研究把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新高潮。②参见 Brent Berlin and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近年来,雷考夫和约翰逊通过对隐喻和典型范畴的研究,提出具体化 (embodiment)假说,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开始于对自己身体的认知,然后以隐喻的形式,借助熟悉范畴认知陌生范畴,借助空间范畴认知时间范畴,借助具体范畴认知抽象范畴,他们的研究奠定了认知语言学的基础。③参见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George Lakoff,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9。
在中国,最早对汉语及其方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罗常培,④有关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民国时期也有,如张世禄在 《语言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30年版)、《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中反复强调文化在词义变化中的作用,伍铁平先生于八十年代的词义论文中,多次借用张氏有关文化与词义关系的素材。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部系统探讨语言与文化这一主题的专门著作就是罗常培的 《语言与文化》了。——编者注他通过对字源或词源、借字、姓氏、亲属称谓的研究,探讨了古代文化的遗迹、中外文化的接触、民族的来源和迁徙、古代的宗教信仰和婚姻制度。⑤参见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游汝杰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后,出现了相当一批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专著,⑥参见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有的像罗常培那样,侧重发掘词语的文化、历史、民族与社会内涵;⑦参见曲彦斌 《中国民俗语言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黄涛 《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有的侧重说明词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解释其意义和用法;⑧参见陈建民 《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游汝杰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戴昭铭 《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 1996年版;林宝卿 《汉语与中国文化》,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佐文、郑朝红 《语言与文化》,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有的兼具前两类的特点。⑨参见杨琳 《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 (增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在外语界,有的研究重点考证中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史,⑩有的着重描述当代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⑪参见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年版;顾嘉祖等《语言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有的介绍英语词语的掌故,⑫参见于忠喜 《英语词语掌故辞典》,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我本人则自2000年到2013年一直在 《英语学习》杂志主持每月一期的专栏 “词语故事”,开始是零散而随机地,后来又有计划而系统地,考证英汉两种语言
一些常用词的来源,对比其语义的异同和用法的演变,考察其所反映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特征,发掘讲英语的人和讲汉语的人在不同语言的制约下,在认知特征和思维方式上的异同。
上述各领域仍大有文章可做。祝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办成全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