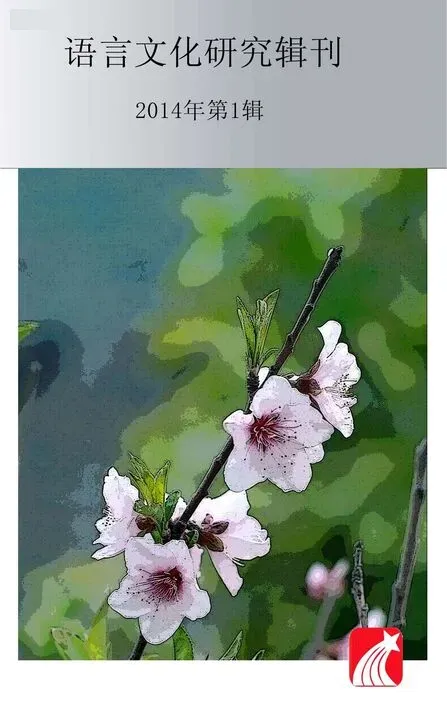语言文化研究访谈录
2014-03-10华白
陈 国 华白 晓 煌
([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2]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语言文化研究访谈录
陈 国 华[1]白 晓 煌[2]
([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2]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白晓煌:您当年在许国璋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和博士,肯定收获不少教益。您能谈谈这些收获对您的影响吗?
陈国华:说到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学术视野或学术追求,这是决定性的。我一直喜欢做研究,1980年就开始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学报上发文章,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最早的。但那时学术视野很狭窄,写的东西貌似实用,却都很肤浅,没有什么理论。1982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做了许老的学生,跟他学语言学名著、文献目录学,还跟周珏良、刘世沐、周漠智等其他老师学莎士比亚、英语史、音系学,跟英国来的外教米克·肖特 (Mick Short)学话语分析、文体学,还有一个月听韩礼德讲授他的系统功能语法,学术视野就开阔了,学术追求的境界也提高了。另一方面是治学方法,许老强调治学要严谨。譬如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对莎士比亚四部福斯塔夫剧的社会语言学研究”(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Shakespeare's Four Falstaff Plays),许老要我先做文献综述,第一步是做一个加注的文献目录 (annotated bibliography)。我一开始也不得要领,花了半年多把国内能找到的中外文文献全都收集起来,然后通读一遍,为每一文献的内容做了总结,拿给许老看。许老说:“对一个没有读过这些文献的人来说,你这个很有用,能让人知道这些文献都讲了什么。但是你只是把每篇文献的扼要内容放在一起。看不出来文献的哪些内容跟你的研究题目直接相关,对莎士比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有什么成果,存在什么问题。”我根据他的教诲把文献目录重新做了一遍,这对我之后的研究帮助很大。1990年我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学时,一个同时在那里访学的日本莎士比亚学者看了我这份目录,问能不能提供给他,我给了他,后来他写文章用到里面的信息,还向我表示感谢。
白晓煌:后来您去英国剑桥大学求学,受到了欧洲学术文化的熏陶,这跟您在国内接触到的学术研究有什么不同?中英学术规范存在怎样的差异?面对这些差异,我们今天该如何开展语言文化研究?
陈国华:中英的学术差异有多大,要看你在国内是在哪个学术领域里做学问,是在跟谁做学问。我是1990年1月由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去英国访学的,出国前,在许老指导下,我已经写好了博士论文的前三章,而且是用当时最流行、最好的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 Wordperfect写的,储存在 5寸的软盘 (floppy disk)里,带到英国。我先去了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和贝德福德新学院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导师名叫凯蒂·威尔斯 (Kate Wales),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文体学家。她看到我的论文是用打印机 (printer)印出来的,不是用当时仍广泛使用的打字机 (typewriter)打出来的,十分惊讶,因为当时就连英国学生也不是人人都会用电脑,而且我的论文,不论是语言还是内容,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全靠许老的前瞻性。当时中国的电脑基本都是台式的 286,一台差不多3万块钱,那是很大一笔钱。但许老向学校申请经费,给语言所买了一台,还让我们去学DOS操作语言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在电脑的使用上,我们北外语言所许老的学生跟国外几乎是同步的。许老上大学时有钱钟书先生做老师,后来到牛津大学读书,导师名叫Quiller-Couch,在英国文学界很有名。经过这些名师的指导,他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和英美国家同行不相上下,我看他跟来北外的外国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侃侃而谈,说起某人、某书、某篇文章,彼此都知道。跟许老这样的导师学习,我的学术视野、受到的学术训练和熏陶,跟英美国家的学生相比,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换一个学校,导师和学术环境都不同,接触不到学术前沿,跟外国同行在一起,别人一问三不知,那就不一样了。因此,对我来说,到英国之后,没有感觉有什么culture shock,只是觉得那里的学习条件太好了,大学的图书馆太方便了。
白晓煌:您认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语言文化具有怎样的作用?研究语言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
陈国华:意义太大了,在中国尤其如此,这方面我想多说一些。语言的作用,特别是文字的作用,非常大。在中国,文字的作用比语言的作用更明显。要是没有汉字,就不会有被全国人民认同的汉语,各地方的人们说的话,要么仍然是原先不同的语言,要么原先的同一种语言早就分化成不同语言了,我们中国也早就分裂成和欧洲一样的许多个小国家了。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也就是标准的北方官话,和南方的吴语、赣语、粤语、闽南语、闽北语还有客家话,彼此差别很大,比印欧语系罗曼语支、斯拉夫语支或日耳曼语支相邻语言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比如罗马尼亚语和保加利亚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德语和荷兰语,说这些语言的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
人,彼此大体可以听得懂,因为他们说的话原本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这些方言区后来成为民族国家,为了彰显自己的民族性,就有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而且采用的全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主要表示语音,不同方言用不同拼写方式甚至不同字母表示出来,就成为难以读懂的语言了。假如中国没有汉字,各地方言也采用拼音文字来书写,写出来的东西恐怕不比外文容易懂。在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汉民族身份认同方面,汉字和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所起的作用比历朝历代英雄豪杰统一中国所用武力的作用大得多。武力解决不了的事情,靠文化认同,早晚能和平解决,这就是民族和解、民族融合的力量。因为说起久分必合,大家首先想到的理由就是同文同种。
然而我们曾经误以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语言,阻碍了民众的教育和国家的进步,所以不但不珍惜和保护这份宝贵遗产,反而用行政手段对汉字进行大规模简化,对它造成了严重伤害。这种伤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削弱了汉字的沟通功能。语言和文字是人们沟通的媒介,沟通要用同一种语言或文字,否则无法沟通,只能靠翻译。汉字简化后,未简化字和简化字之间形成了相当程度的隔阂,对古与今、大陆与港台之间的文字沟通造成了很大障碍。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汉字有表音和表意的双重功能,这本来是汉字特有的优点,对汉字的简化没有增强它的表音功能,却破坏了它的构造理据,削弱了它的表意功能。虽然历史上一直有一些简化字,但那是人们学会了正体字以后,为了书写快捷而采用的变异写法,这些异体字的存在无伤正体字的大雅。但是以行政手段大规模地造一批简化字,并把这些字体连同传统的异体字当作 “规范汉字”来推行,让孩子们只学这些或多或少丧失了构造理据的字体,结果是书写变容易了,识读却变难了。在汉字只能手写的时候,书写的简化便利了当时已经认识了正体字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是利大于弊;对于启蒙阶段的儿童来说,用书写的易换取识读的难,可以说利弊相当。如今在电子设备上汉字的拼音输入比手写容易得多也快得多,书写简化所带来的利大打折扣,汉字识读教学的难日益凸显,这时回过头来再看当初汉字的简化,可以说是弊大于利,因为它虽然便利了当时一两代人,却加重了后代的学习负担。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未简化字无法完全禁止或取消的情况下,一个人不识一定数量的未简化字,就不能算是完全学会了中文。且不说仅认识简化字的大陆年轻人到了香港和台湾就成了半文盲,就是在大陆这边,不仅古迹和文物上以及描写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以前历史的影视作品里出现的全是未简化字,各种书法作品以及领导人在各地的题词大多是未简化字,商店的手写招牌上也有不少未简化字,然而学校里却不教这些未简化字。如今有人呼吁 “救救汉语”,其实真正应该抢救的不是汉语,而是未简化的汉字。呼吁 “救救汉语”的人声称:“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好中国话以及不会用中国话的现象普遍存在。”除了有语言障碍的人外,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我一个也没有遇到过,而不识未简化字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倒遇见了不少。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这样高学历的
人却仍是半文盲,难道不可悲吗?谁能说这种情况是小学开设英语课造成的?
前几天教育部语信司委托我们中心把 《〈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情况简介》和 《通用规范汉字表说明》译成英文,译稿的审订工作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上网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英文版,这才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网站有三种版本,一是中文简体字版,二是中文繁体字版,三是英文版。再看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里面第四条明文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第九条规定 “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可是这两条规定中央政府自己就没有遵守,可见它实际上也认识到未简化字即使在大陆也有其存在的必要,不能取消。我的看法是,即使今后实现了全国统一,未简化字恐怕也无法取消,相反很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东山再起。
再看外语和文化的关系。呼吁 “救救汉语”的人主张取消小学的英语课,甚至要求取缔社会上的英语培训班,列举的理由中有一条是 “娃娃学英语不合国情”。什么是国情?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早已进入中国,这就是国情。在过去,大量英文词是披着汉字的外衣溜进汉语的,例如坦克、声呐、沙发、麦克风;如今这种情况依然很常见,例如酷、粉丝、三文鱼、脱口秀;同时许多英文单词和缩写已经直接堂而皇之地进入汉语,例如 bye-bye、CT、OK、DNA;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一样,早已成为中文书写系统的有益补充,就连机动车车牌上都是汉字+英文字母 +阿拉伯数字。汉语和汉字并没有因为这些外来成分的加入而污染或败坏了,而是表达力更强了。既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英文词和字母来到中国后就不走了,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让孩子们认识、理解它们行吗?
反对小学开设英语课的人还有一条理由,就是 “很多学科其实根本无须外语”。我几年前就写过文章,论证英语不同于法语、德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这样的外语,它早已成为国际通用语,成为国际商务、体育、学术交流的语言,我们不能拿它当一般的外语。我国学科目录上列出的所有一级和二级学科,没有一个能说自己无须英语。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学科的人可以说自己在做研究、写论文时无须参考英文文献,保证外国人没有做过类似或相关研究。那种认为外文文献的问题 “通过翻译完全可以解决”的想法,只说明说这种话的人完全不了解国外学术出版的现状和我国翻译界的现状。
白晓煌:就语言文化研究而言,外语教师应该如何选择语言文化研究的范围与对象,是以英语语言文化为主,还是以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为主?您能谈谈您的观点么?
陈国华:中外对比容易出成果。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化,要到民族区域去调查,对我们外语教师来说不是很现实,除非我们教的是蒙古语、朝鲜语这样既是民族语又是外语的语言。对大学英语和其他外语专业的教师来讲,中外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可以从多方
面进行,有许多课题可以做。不进行对比研究,显示不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异同。
白晓煌:就目前而言,面对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我们应该如何确立语言文化研究的选题?
陈国华:首先学术视野要广阔,视野如果狭窄,就看不到有什么可研究的。视野打开了,很多东西都值得研究,而且现有各领域的研究都有可改进之处,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举个简单的例子,语言与文字方面可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的教学方法、未简化字与简化字的关系、形位 (morpheme)和字的关系、字和词的关系、汉语字典里条首字的排序原则,等等。懂外语的人,可从汉外或外汉比较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
为了拓展学术视野,每个人不妨培养一点自己的学术情趣。在国外,有自己学术兴趣的人相当普遍,他们拿学术当作自己的业余爱好。做一件事,不求金钱或物质回报,只要有所发现,对社会、对他人有益,自己感觉良好就行。比如我参加英国语文学会理事会的例会,会后都有嘉宾做公开讲座,讲座结束后,大家可以自掏腰包跟嘉宾一起吃晚饭。有一次吃饭时,一位老爷子坐在我旁边,互相介绍,发现他是纽贝里市 (Newberry)的市长,他说只要有时间他就一定来听讲座。我很奇怪,一位市长怎么会对语言研究感兴趣?他说他上大学时就对语言感兴趣,可是没能从事语言研究,因为他得考虑找工作的难易问题、薪金待遇的高低问题等,因此他选择了其他行业。后来他女儿嫁给了日本人,他的外孙迟迟不会说话,让他很担心,他由此对儿童语言产生了兴趣,想找机会跟专家交流。在西方,拿学术研究当爱好的情况很多,而且有这个传统。譬如,19世纪编写 《牛津英语词典》时,不是光靠主编和几个编辑在一起编,而是把编写原则和体例发布出来,鼓励各行各业的人都来阅读文献,收集并贡献例证。①这种编撰方法今日称为 “众源方式”(crowd-sourcing)。编写 《牛津英语词典》时,例证几乎全靠各地读者手抄卡片,邮寄给编者,编辑筛选和编辑后,进入词条。网络时代的 “众源方式”则采用互联网的方式进行,维基百科的编写就是采用 “众源方式”的范例,所有词条均由大众按照既定的编写规则自行完成,既方便又快捷,但信息真实度的鉴别由发包方来完成,这与昔日辞书编撰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有关 《牛津英语词典》编撰中的“众源方式”研究,参见秦晓惠 《众源方式在 〈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体现和应用:从古典到当代》,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年。——编者注做这件事没有任何报酬,但很多人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一个非专业人士做得能让专业人士刮目相看,又读了书,长了见识,这是一种乐趣。所以,每个人最好有一种学术爱好。
搞外国语言研究的,可以做一些和中国语言研究、文字学、文学、翻译、词典学等相关的研究。一说起词典学,大家就觉得乏味无聊,其实要是做好了,是很有意思的。譬如,我在 《英语学习》上主持的 “词语故事”专栏,这一期讲脖子和throat的故事,要是把这些东西编入字典,字典的内容就丰富多了,也有意思多了。又如中国文化走出
去这一块,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中国的饮食文化,现在出了一套菜名的标准英文译名,这还远远不够。各种烹饪方法用英语怎么说,各种食材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各个菜系的内容等,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术爱好,研究之后都可以写出文章;反过来,外国的饮食文化,包括葡萄酒文化、奶酪文化等,以及相关术语的汉译,也值得研究和介绍。此外,中医、武术、气功等,都有很多可发掘、研究的地方。
最后,研究者一定养成乐于与人交流的习惯,要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如讲座、报告会、研讨会等,因为在交流中可以通过思想碰撞擦出学术火花。切忌一个人闷着头在家里孤苦伶仃地做学问。
白晓煌:做人文社科研究,想要创新不容易。就您而言,做语言文化研究,如何才能在内容、方法上有所创新呢?
陈国华:创新其实也不难,首先要能发现研究空缺,其次是要有一个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或思路。外语界的优势是对国外的新理论比较敏感,知道得比较早。过去知道了一种新理论或新领域,赶紧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发表出来,这种文章当然没有什么创新。还有知道了新理论或新领域后,赶紧利用汉语数据照猫画虎做一些研究,这种跟风式的研究有一些创新,但创新性一般不大。后果就是对语言本体研究的忽视。对外国语言本体的研究现在是薄弱环节,研究者苦于发现不了问题,发现问题后,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熟读语言学各家各派的经典之作,学习各家观察问题的视角、解决问题的思路、建立理论的方法,对比其优缺点,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发现问题,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白晓煌:您招考博士生有哪些要求?您是怎样培养博士生科研能力的?
陈国华:我招收博士生首先看考试成绩,考试是最低门槛。考试后两个人分数差不多,那主要看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好的、多的优先于科研成果差的、少的。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的,我会劝他们先不报考。当然应届硕士毕业生的硕士论文也算一种成果。以前我只看考试成绩,结果发现有的学生考试不错,语言能力也不错,但没有做学术研究的任何背景,这就比较麻烦。那就只能先跟着大家上一年课,基本入门了,再考虑自身的研究兴趣和选题方向的问题。
白晓煌: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是独立的英语教学机构,负责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英语教学工作,同时还开设英语语言文化辅修课程和后续课程。为了能在搞好教学的同时,提高本部教师的科研能力,我们依托大学英语教研部青年教师发展协会,创立学术性刊物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暂定每年刊发一册,内容涵盖语言学、翻译、文化、文学与比较文学、教育与教学等领域。作为一位同时兼顾翻译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外语教育研究的语言学家,您能否谈一谈您对创建这本刊物的看法?
陈国华:要做,就把档次定得高一些,短期内可能本校的人发的不多,但是要借这
个机会帮他们提高。比如,北外有一位小语种的教师跟我们外研中心的老师一起做语言政策研究。他之前一直没发表过什么东西,但有学术潜力,只是一直没有人给予点拨。一起做研究时,大家一起讨论,慢慢他也就入门了。后来,文章发到了一个非外语的顶级期刊上,他自己也很高兴。这中间的关键就在于他参与课题组做研究,写的文章是课题组其他成员一起帮他修改的,前后修改了好几稿,最后终成正果。一旦出了高层次的文章,以后做科研、写文章就容易了。有高层次的文章,辑刊的档次也就随之提高了。
白晓煌:刚才您谈了对辑刊的看法。为了这本刊物的长远发展,您能否对办刊方向提几点建议?
陈国华:有两条建议:一要有远大的目标,严格按照 CSSCI来源期刊的标准来做,对校内作者的稿件可以通过审读和提出修改建议加以扶持,但不能降格录用,只要执行高标准,坚持下去,就有希望成为CSSCI来源期刊;二要定好办刊原则,制订严密的编辑体例和稿件审读和编辑的操作流程。学术声誉就是品牌,就是生命。
陈国华 (1954—),男,山东招远人,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英汉对比与翻译、双语词典学等。联系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100089)。Email:prof-chenguohua@163.com。
白晓煌 (1974—),女,北京人,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生,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副主任。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教学管理等。联系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 (100048)。Email:baxih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