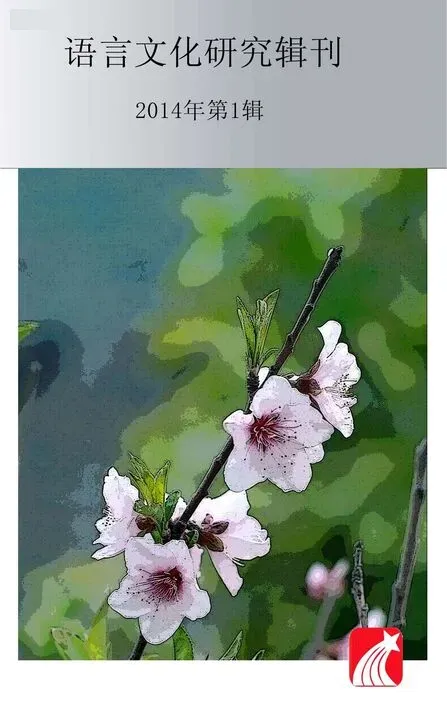关于语言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访谈
2014-03-10清邱
刘 润 清邱 耀 德
([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2]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关于语言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访谈
刘 润 清[1]邱 耀 德[2]
([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2]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邱耀德:您当年追随许国璋、王佐良等中国一代语言文化研究大家,在语言文化研究方面肯定有不少特别的收获。您能谈谈这些收获对您的影响吗?
刘润清:许国璋、王佐良都是造诣深厚的大家,许国璋是国内语言学派的代表,王佐良是英国文学的代表,两个人的汉语文化 (中国文化)造诣也都很深厚,是当时中西合璧的典型人物,对我们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又是深刻的。他们在教英语的同时,传授的是思想,而这思想就是文化和哲学。许国璋旨在通过语言追求哲学新知。曾记得我从英国回来,许先生来我家,发现我带回来两本Karl Popper的书,高兴地对我说:“你有进步啊!你能买这两本书带回来,说明你开始对哲学有认识了。Karl Popper是近代英国的大哲学家。他最著名的创新就是证伪,咱们院①许国璋教授引文中的 “咱们院”指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编者注的哲学多年来都是证实 (verification),或叫归纳、演绎。”比如,我第一天早晨八点在门口见到你,第二天同一时间和地点又见到你,第三天又见到你,第 N天还见到你。结论是每天八点邱老师来,结果是第N+1天你没来,一次就把这个归纳出来的结论推翻了。证伪方法有一定道理。你天天早晨八点都来,这个观察是对的,咱们就先认为它是对的,是真理,直到某一天被推翻。如果一直不被推翻,那它就总是真理。其实,这个理论有点极端,但真算的上是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
许国璋、王佐良两位先生让我们写东西时,主要侧重于 “有思想”、 “有哲学”、“有人文见识”。许老特别反对学生只会几句英语,除了 “How are you?” “I'm fine today.”这几句话再也没有好说的了,那就是 “思想贫乏”。通过英文教书,我们要教
人ideas;他们一直强调ideas,没有 ideas,你就不算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觉得,从他们那里受到的影响,不是我说几句英语就怎么样,而是有底蕴的教育,有底蕴的铺垫。他们的境界太高,不允许你玩那些小儿科的事。
邱耀德:后来,您又追随 Lancaster大学的国际知名教授利奇 (Geoffrey N.Leech)和肖特 (Mick Short),将语用学与 《红楼梦》这一中国文化现象研究相结合。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和收获?国外教授与许国璋和王佐良二老的语言文化研究观点是否有所不同?
刘润清: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一共在英国呆了差不多两年,第一次呆了一年半,第二次不到半年。我觉得受英国文化影响还是蛮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对英文、语言学,包括英国小说有所了解。换句话说,我跟当地人的交流比较深刻、细腻,就是很subtle culture那种,能用英语开玩笑,甚至开很深的玩笑,这时就已经进入了文化层面,两种文化就彼此交融了。有时候,我拿着一杯咖啡或是啤酒,过来一个人我就说:“Hey!Have a cup of coffee”或者 “Have a glass of beer”,对方就说:“Oh,thank you.I didn't expect you would offer”,而我则说:“Oh,I'm sorry.I didn't expect you would accept it”,结果是两人哈哈大笑,气氛马上就非常和谐了。第一句是 humor,而回敬的也是 humor。两个人都很开心,这样谈起话来就容易深刻,没有隔阂。这需要两条:你的英语足够好,够用;你对英语文化有足够了解。
利奇和肖特两位多次来过中国。我去英国前,肖特来中国教过一年书,我听过他的课,成了好朋友。这两位教授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平易近人;国际知名,却没有架子。他们的长处在于对英语和英国文化的了解,中国老师的长处在于对我们的国学的了解。能有机会受到两种文化的大师的指点,是我的幸运!利奇和肖特对中国人都很友好,对留学生特别热情。我在留学生中年岁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留学生有什么事情,他们一般都找我说。如 “有个中国学生有problem”,他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他们无非就是想家,或是想老婆了,我去找他们谈谈好了。我去英国时,主要学的是语用学。记得我去的时候,就把英汉版本的 《红楼梦》都带去了,所以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就把硕士改成了 M.Phil,相当于国内的副博士,叫 Master of Philosophy,哲学硕士,比博士低一格,比硕士高一格,但要做一篇大论文。在第一稿中分析了一部分 《红楼梦》的时候,肖特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了,他说这个题目值得写、但我写得不深,只是把 《红楼梦》从头到尾翻阅了多少遍,才能抽出对语用学分析有价值的对话,最后落实到四大段经典对话:一段是最正式的言语行为、一段是陌生人之间对话、一段是王熙凤跟姑娘们吃螃蟹时开玩笑 (banter)、一段是探春抵制抄家时说的反语 (irony)。这四段都很典型,很有代表性。肖特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他严格、诚恳,给人思想上的启迪,引人进入学术境界。Ronald Carter是我的校外评审 (external examiner),利奇
是我的校内答辩委员 (internal examiner),他说:“我看了,咱们也不用正式地进行问答环节了,去喝咖啡,聊聊天就行了。我真不知道可以用我的 ‘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分析 《红楼梦》。”其实,我也是现学现用,况且我对 《红楼梦》也没有专业水平的研究,不过是涉猎而已。但是,二者碰撞出的火花叫人激动。
回国后,我讲 《红楼梦》分析,汉语部来了四个研究生,他们高兴地说:“我们从来没想过 《红楼梦》可以这样分析。”贾政在元春回门省亲的时候说:“臣草芥寒门……”我说:“臣是第三人称,英文是 ‘Your Subject’,翻译成第三人称,意在指‘我没有资格用我,更没有资格称自己是父亲,已经降到臣民,没有资格说我怎么样’。可是,他是爸爸,就这一个 ‘臣’字,就放弃了爸爸的地位和权利,甘当臣民,只有责任了。”其实,前后是有呼应的,如 “忠于厥旨”中的 “厥”是什么意思,是‘他的’的意思,翻译成英文是 “loyal to his duty”中的his。可见,曹雪芹用的名词性代词和所有格代词都是统一的,自始至终没有用 “我”。后来又用了 “幸及政夫妇”将自己称作 “政”。我查了 《红楼梦》,没有一个人敢叫他 “政”,都是叫他 “政老先生”、“政翁”、“政大人”等,他母亲都得说 “叫你二爷去”,也不能说叫 “贾政”来。可他到元春面前,却只能称 “幸及政夫妇”。你看看,礼貌到什么份上!这也是里奇的“礼貌原则”涵盖不了的,应该加一条 “尊崇次则”才行。汉语学界从来没有这么分析过。①参见刘润清 《论大学英语教学》第五章 “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编者注
实际上,英汉一对照很多文化的东西就凸现出来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关于 Losses and Gains of Politeness in Translation的文章,探讨翻译中常常遇到的问题。譬如, “贱内”怎么翻译?总不能翻译成 “cheap wife”吧?“犬子”也不能翻译成 “my dog son”吧?类似的表达翻译到英文中就都变味了。杨宪益译的 《红楼梦》的英文已经够好的了,但有些文化的东西根本翻译不过去,翻过去了就不是英文了。文化的东西怎么办?文化的差异怎么翻?外语要好到什么份上,才能翻译出文化差异呢?
我曾在某一篇文章中说,什么叫 translation?翻译学术著作和经典小说的译者,必须是语言和文化都达到了与作者相当的程度,才有资格谈翻译,才能打破原著译著两张皮的现状。举个例子说,《红楼梦》译者杨宪益身边有三四十个国学专家朋友,遇到问题就打电话咨询,比如说:“邱老师,这个菜谱有什么讲究么?这个药单有什么讲究么?”。有关中医药方,后来经一位老中医证明,曹雪芹没有瞎写,都是有根有据的。菜单怎么样?节日怎么过?这些都是国学。要是没有这些文化专家作后盾,谁都翻译不到那个水平。语言要好,文化要懂,知识面要广,才能翻译好。如果我们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翻译成汉语,你要是不懂哲学,英文再好
也翻不了。现实中,语言跟文化根本就不可能分开。举个例子说,许渊冲翻译毛主席的诗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将 “不爱红装爱武装”翻译成 “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desire so strong.They do not powder their face but face the powder.”,我看到这句译文,真是拍案叫绝,实在佩服他。所以说,语言跟文化不修养到顶峰,翻译不出这样的句子。
邱耀德:就目前而言,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文化的多元性和语言的多样性。您认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语言文化具有怎样的作用?研究语言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
刘润清: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文化非常重要。总体来说,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 (identity),就是说民族的认同感都在语言文化之中。你说你是中国人,是因为你有中国文化,说中国的语言。同样,一个国家侵略了这个国家,要灭这个民族,第一要务就是灭它的语言。当年,东北三省不是被教授日语么?你忘掉了你的语言,就忘掉了你的文化,也就忘掉了你的身份,这样你就不知道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一个民族团结力量和认同感的基础。换言之,如果你没有这个语言,如何继承这个文化?怎么继承这个身份?
语言和文化还是软实力。语言文化包含很多优良的民族传统,有很多风俗习惯,是用于教育下一代的,是用以传承民族精神的。说文化是软实力,是因为让其他民族了解你的文化,才能相互友好,相互信任,相互来往,求团结,求和平。如果对外宣传说,人家有,你也有,你的那些不新鲜,只有具备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人家才会买你的帐。现在中国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讲汉语的总人数绝对大于讲英语的总人数,说汉语者遍及全世界,全球华人华侨总数达3000万,光加拿大的华人据说就超过76万,美国更多,有 200—300万。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使用英语的国家,接收了大量中国移民。这股文化力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论走到哪里,都有懂中国文化的人,都有会说中国话的人,这种优势是自己语言无法自保的小民族无法比拟的。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学汉语、教汉语,其目的在于欢迎中国人来旅游、来投资、办工厂,等等。可见,要想接受中国投资,吸引中国游客,你服务要好,最好有汉语的服务,否则没戏。譬如,泰国不大,可是会说几句汉语的人不少,就是为了招揽中国旅游者。简而言之,我们不能小看语言文化这个软实力,它是我们民族标志性的东西。
邱耀德:就语言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外语出身的教师应如何选择语言文化研究的范围与对象,是以所学语言的文化为对象,还是以借鉴所学语言文化的视角,研究母语场域内的语言文化现象?
刘润清:总的来说,不要认为我们学了英语,就主要教授西方文化,这一观点是不
全面的。作为一位老师,我有责任让学生既了解西方文化,又了解中国文化。就学生而言,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得也并不多,中国的节日、历史、语言文字、语法、文化史、哲学、服饰等都知之甚少,可能近代史还懂得多一点,古代史就差一些。外语教师的义务就是既要教西方文化,又不忘中国文化,要有一种比较意识,其典型的就是 “They do this in the west while we do this here in China”。一个中国人见到外国人,理想的情况是两者能在文化上有所交融 (meet half way culturally),而不是我去适应你的文化,也不是让你适应我的文化,我懂你的文化,你懂我的文化,咱们彼此交融,这就是相互了解。如果说 “Everything foreign is good”(外国什么都好),这样不好,而说 “Everything Chinese is good”(中国的什么都好),这样也不好。可见,只有懂了第二门语言、第二种文化,并加以比较,人才能欣赏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是普适性的真理。
一个普通英国老太太,从来没有出过英伦三岛,连中国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会了解中国文化呢?她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好像世界上其他人都像她一样生活。我觉得,我是学了英语之后,才更欣赏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说懂一门第二语言,了解第二种文化,你才能有欣赏自己文化的能力,也更有批判能力,也就是 We become more appreciative and more critical about Chinese culture。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不是盲目崇拜外国,也不是说中国文化什么都好,这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文化能创造出这么多好的东西,才能存在这么多年;但也有坏的东西,陋习也不少,比如请客、喝酒、劝酒、不喝醉不罢休、吃饭大声嚷嚷、随地吐痰、到处刻 “某某到此一游”等,这些都是陋习,让外国人笑话咱们。
怎么研究文化呢?一种是研究认同感。现在学英语的人不少,学了英语之后是不是就会对英语文化有一种认同?另一种是这种对外国文化的认同会不会影响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也就是看看他学了英国文化,反观汉语文化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还有一种是怎样用英语传授汉语文化,你可以与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主任史宝辉谈谈,他最近出版了两本汉语文化读本。我问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说要用国学内容把大英教材改掉,因为现在的大英教材没内容,一会生物,一会电学,最后什么也落实不了。所以,他要教学生中国文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学生不懂中国文化;即使懂中国文化,又很难用英语表达出来。第四种是结合课堂的行动研究 (action research)。当前的现状是:很多老师几年都没做研究了,逼着他们看那么多理论书籍不现实,时间太漫长,也来不及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行为研究就是发现课堂上存在的问题,然后读一点参考书籍,解决这个问题,将这个过程写下来,它也有方法论,也有一定的理论,有一定的见解,其本质上就是逼着老师反思为何会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等。
邱耀德:您认为,做语言文化研究,研究者应该如何确立选题?确立什么样的选题比较适合期刊论文写作、科研项目申请和攻读博士学位?
刘润清:虽然你的杂志叫 “语言文化研究”,但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稿子都跟语言文化相关。有的稿件可以专门搞语言研究,如语言教学、二语习得等;也可以专门研究文化。你要同时研究语言与文化,就可以从二语习得角度,考察第二语言对自己的语言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可是,你们的投稿须知上面列出了20项内容,如文学、翻译、教育学、语言学、史学,等等。要让教师打开思路,无须死扣语言学或语言教学,或是文化,因为文化涵盖许多东西。我认为,只研究文化,尤其是关注中西文化差异,也要深入下去。从我 1989年跟邓炎昌写 《语言与文化》①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编者注,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基本还停留在举例阶段,这是不应该的。研究文化,要与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相结合。文化研究也好,社会学研究也好,都要有所提升,提升什么呢?就是社会影响力和制约力,特别是语言使用上的制约力,这是语言对文化的一种反观、反思。譬如,汉语中说:“你英语真好啊!”回答是 “哪里哪里”,而在英语中就不能这么说,只能说:“Thank you”,至多再说: “I was very lucky to have good teachers”或 “I was in Britain for a while”,这是一种礼貌。这种文化所产生的制约力很厉害,除了句子,篇章、言语行为等与英国人不一样,这种研究已有不少成果。
在杂志上投一篇稿,跟攻读博士不是一回事。攻读博士的选题要大一点,深刻一点;写一篇期刊论文,题目要小点。一篇博士论文要 cover很多层面,要有足够的篇幅,要有雄厚的理论基础,还要采取多少个科研步骤才能有所发现,最后的解释还要返回到理论层面,才能有理论高度;期刊文章或申请一个项目,要看题目的大小,但有一条很重要:要有项目申请的前期成果。我曾帮忙复试几个博士考生,他们教了几年书,有好几篇论文发表在不错的期刊上,这些人才有资格复试,才能考上博士。申请科研项目也一样,如果没有前期成果,论述内容不免前言不搭后语,评审人一看就知道你不了解这个课题。如果你已经就这个课题发表了几篇文章,现在遗留了一两个问题,要把它研究透,最后出版一本专著,评审者就会同意把钱给你。其实,我觉得老师们要有一个职业规划,一个长期规划,一步一步地按计划进行比较好。
邱耀德:做人文社会研究,想要创新不容易。就您而言,做语言文化研究,如何才能在内容、方法上面有所创新呢?
刘润清: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但我对语言学有自己的一点小感发、小体会,有时冒出点小火花。比方说,我看懂了一个立论 (theoretical point),我很高兴,但不能光看懂了,我还要用汉语的例子支持它或反证它,比如用 《红楼梦》和曹禺 《雷雨》里的很多例子分析礼貌原则,这就是贡献。此外,用汉语分析国外理论,很容易看到缺点,易于提出批评。因此,你问我提一个什么语法系统,如陈国华想
要提出一个新的汉语语法系统,这个我做不到,也怕人家语法学界不接受,但我用反例证明现存的理论的不足,然后修订、修改这一理论,这是可以做的。比方说,利奇的礼貌原则中的得体原则、赞誉原则等,我就提出在 《红楼梦》描写的那个时代,只用赞誉原则是概括不了的,要是表示尊重权威、尊重上司,必须贬低自己,使劲抬高对方才显得得体。如上文所示,贾政自己谦称为 “政”,对自己的孩子称 “臣”,说这光是礼貌不够。再如 “儿臣不敢”、“罪臣不敢”等说法,不光是礼貌;还有自贬、自毁之意。人与人的关系像跷跷板:贬低自己就抬高对方;抬高自己就压低对方。《红楼梦》中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礼貌,应该是崇尊 (deference)了。利奇听我这么说,也没反驳。在那个世界里 (清朝末年),在那个文化中,只是礼貌原则行不通。后来利奇也修改了他的理论。另有一篇文章 《礼貌:东西方文化的界线》(Politeness: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①参见Geoffrey Leech,Politeness: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2005,Issue 6;Geoffrey Leech,Politeness: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2007,Issue 2。—— 编者注,其中东方文化所指不光是汉语,还有日语、韩语等。这说明,利奇他们也在学习外国文化,不然也是会说错话的。总之,我提不出来什么新理论,但可以对某一理论提出一点批评,有自己的一点看法,有自己的诠释,有自己的素材。仅此而已。
邱耀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是独立的英语教学机构,负责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北京市 “京疆学院”部分培训学员的英语教学工作,同时还开设英语语言文化辅修课程和后续课程。为了能在教学的同时,提高本部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我们依托于大学英语教研部青年教师发展协会,创立学术性刊物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每年刊发一册,内涵涵盖语言学、翻译、文化、文学与比较文学、教育与教学等领域。您能否谈一谈您对这本刊物的看法?
刘润清:这两件事是互相促进的。青年学者互相交流能够促进思考、写作和投稿。要交流就要有所准备,你读了一本书,别人可能没读,互相交流心得,你说一本,我说一本,说上三本书,在场的人都受益,这是一种刺激。你能看这本书,我也能看,或者是语言学的,或者是文学的,或者是关于翻译的。如果能谈谈感想就更好了,这样就已经开始构思了,是稿子的雏形了。写成后,你请大家帮忙提提意见,这个布局行不行,观点能否站得住,有无遗漏之处。有个研究小组,讨论读的书,讨论大家的稿子,打开思路,集思广益,肯定人人受益,对不太懂研究方法的人来说,受益会更大。
邱耀德:刚才您谈了对辑刊的看法。为了刊物的长远发展,您能否对办刊方向提几点建议?
刘润清:首先,严把质量关,一定是要有审稿资格的人来把关。一个期刊的生命在于稿件的质量;质量无法保证,根本无法进入核心期刊方阵。懂行的人一看第一期、第
二期,就发现这个辑刊有好稿子,这个办刊人有眼光,就会开始留心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
其次,无论是谁,不要搞小腐败。比方说,邱老师任主编,要是有人寄给你稿子同时寄给你几千块钱,这稿子就登出来,这期刊能办好么?主编或者编辑不要走后门,要设立一个制度,跟作者说稿子质量一定要好。英文摘要得过关,只要稿件质量好,不愁没篇幅。只要稿子好,符合学术规范,就不至于毁坏期刊的名誉。与此同时,也要跟审稿人说,即使稿件不过关,也要提出具体的意见,这是对作者的尊重。如果作者无法修改到那个水平,那也是与人为善,不伤大雅。坚持退稿时注明改进意见,也是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
再次,学术规范也很重要。那么多稿件,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或是规范不一致,那就乱套了,毫无科学范式可言。规范制订好了,一篇篇稿件规规矩矩,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懂行的人在管理事情。
最后,就是政治敏感度。千万不能出政治问题,涉及政治的句子都要认真审阅。这个事主编要负全责。
刘润清 (1939—),男,河北武强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副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境内外语应用分委会主任。研究方向:语言学流派、理论语言学、语言测试、语用学等。联系地址:北京市西 三环北路 2号北京 外国语大学中国外 语教育研究中心(100089)。Email:liurunqing@bfsu.edu.cn。
邱耀德 (1954—),男,湖南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学院教育学硕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主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系硕士生导师,中国剑桥少儿英语口语考试首席培训官。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外语教学心理、儿童学习心理等。联系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100048),Email:qyd602@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