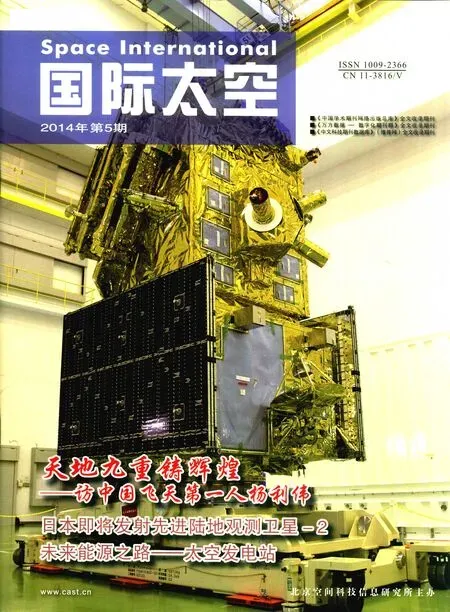新航天基本法—日本产业振兴的源动力
2014-03-07王存恩
新航天基本法—日本产业振兴的源动力

王存恩:研究员,教授,日本航天政策、产业化、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资深研究专家。
2014年,恰逢日本航天60年。在这60年里,日本航天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颁布新航天基本法(以下简称新航天法)。接着,日本航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发体制做了重大调整,开发重点发生了转移;提出了加速航天产业振兴和驱动国家产业振兴的总体目标。新航天法正成为驱动日本产业振兴的源动力。
日本航天起步于1954年,当时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国家顾及不到航天,没有资金投入,以糸川英夫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几位科学家自筹资金,用极其简陋的设备,研制并成功地发射了探空火箭,揭开了日本航天开发的序幕。
日本政府真正关心并领导航天开发可追溯到1969年。同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名为“航天开发仅限于和平利用”的航天基本法,同时确定了科学技术厅和文部省分别负责应用技术和科学卫星及其运载工具的研发。
从1954年到2008年5月颁布新航天法,日本航天开发取得了显著成绩:抢先中国70天发射了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大隅”,使其成为继苏、美、法之后世界上第4个用本国火箭发射自己研制卫星的国家。日本凭借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先进的机械制造、半导体加工、光学仪器生产,在推进机光电一体化进程中,不断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新工艺,不断提高其设计和开发水平,使之成为拥有“领先于国际水平的各类高复杂度的航天硬件和组件的国家”。其研制的许多航天产品,如固体放大器、大型镜面天线、合成孔径雷达、微波辐射计、微波放电式离子发动机、64bit星载计算机等在国际航天市场上颇受青睐。国际权威调查机构—富创(Futron)公司的调查结果认为:“按人均航天能力计算,日本拥有世界上最能干、最优秀的航天劳动力”;“用较少的航天劳动力就能实现生产力最优化,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优势”。美、欧,以及日美、日欧等联合研制的航天器大都采用了日本开发的器件,或由日本提供核心有效载荷仪器。Futron公司还指出:“日本已成为为国际航天市场提供高复杂性的航天硬件和组件的主要国家之一。”
50多年来,日本完成了奠定基础(1954-1970年)、培养独立自主技术(1970-1980年)、确立基础技术(1980-1999年)和奠定产业化基础(1999-2010年)4个阶段的任务,正步入“参与国际竞争”新阶段。2009年,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国的科学技术能力》认为:日本的航天竞争力指数(SCI)在美、俄、欧洲之后,排在第4位。当时Futron公司的调查结果也与之基本相同。
但必须指出,在新航天法颁布前相当长时间内,日本不仅在政治上追随于美国,在航天领域也过分地依赖美国。在美国“抵消贸易逆差必须订购美国卫星”的强大压力下,日本耗费大量外汇购买了美国30多颗通信卫星,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日本这一技术的发展,也推迟了其航天产业化进程。由于日本由两个省厅长期分管航天,所以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统筹规划,以及片面强调研发,忽视应用,也影响了日本航天的全方位发展,推迟了产业化进程。日本右翼势力在否认其侵略历史的同时,以“朝鲜导弹威胁”等为借口,发展军事航天。自民党宇宙开发委员会委员长小野晋也甚至曾鼓吹“日本要与美国的航天开发战略相呼应,不仅要拥有高性能的侦察卫星,还要有监视弹道导弹的早期预警卫星”,这道出了日本极右势力处心积虑发展军事航天和背弃航天开发“仅限于和平利用”承诺的内心世界。基于此,2008年5月,日本国会批准并颁布了新航天法,日本的航天开发政策开始发生以下重大变化:
1)成立以内阁总理大臣任宇宙开发战略本部部长,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航天的领导;
2)由“以研发为主导”转变为“以应用需求为主导”,提出了“加快航天产业化”和通过振兴航天产业带动国家“产业振兴”的口号;
3)从首部航天法中删除了“航天开发仅限于和平利用”,即“非军事”之承诺,目的是为航天军事应用铺平道路。
如Futron公司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新航天法为日本航天活动带来新生机”,“标志着日本航天计划将发生重大的实质性变革,为持续提高其航天竞争力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日本产业振兴的源动力”,“从此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航天活动用于国防目的,标志着日本军事航天政策的战略转变,也将对其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2009年6月,日本公布了新世纪的首部“航天基本计划”并预言:“到21世纪中叶,航天将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子、汽车和计算机产业一样,成为引领国际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新兴产业”;提出要“通过执行航天基本计划,提高航天开发能力和应用水平,增强航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009年刚从自民党手中接管政权的民主党也多次强调:“航天产业是确保日本获得再生的‘前沿产业’”,要“通过执行航天基本计划提高航天开发能力和应用水平,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重振国家经济,并在亚太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不过,此间中国航天开发能力迅速提升,发射次数增多,执行任务能力增强。2010年起,中国航天竞争力指数超过日本。Futron公司2010年公布的调查排序也发生了变化:中国排到了第4位,日本则降至第5位。
不过,正如Futron公司在其调查报告中强调的那样:日本是“近几年唯一一个在各项竞争力指数都全面增加的国家”,日本“航天工业改革已经并将继续渗透到政府和各工业领域”,“政府、人力资本和工业三大方面的竞争力都在提高”。的确,日本的航天开发与应用,以及产业化和拓展国际市场能力都取得了某些突破性的进展:2011年5月,三菱电机公司用DS-2000卫星平台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联合研制的通信卫星中新-2(ST-2)交付并成功发射;与土耳其国营通信卫星公司签订了用DS-2000卫星平台研制的2颗通信卫星—土耳其卫星-4A、4B[(Turksat-4A、4B),土耳其卫星-4A于2014年2月成功发射并交付];日本电气公司与越南签订了用“具备新系统结构的先进观测卫星”(ASNARO)卫星平台研制2颗小型遥感卫星;三菱重工业公司已用H-2A火箭发射了韩国多用途卫星-3(KOMPSAT-3)。为保持这种良好势头,提升航天产业化和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即便是在大地震、诱发海啸、导致核泄漏以及民众支持率降至最低点的危难时刻,民主党野田内阁依然竭尽全力去完善航天政策,调整开发体制,其中包括:
1)修改了“内阁设置法”,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航天的决策和指挥权;
2)修改了“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设置法”,删除了“航天开发仅限于和平利用”,目的是使“和平利用”从日本的法典中彻底销声匿迹;
3)撤消了隶属于文部科学省的宇宙开发委员会,成立了隶属于内阁府的宇宙开发政策委员会;
4)成立隶属于内阁府的国家航天战略司令部—宇宙战略室,既负责制定与航天有关的基本政策,也负责对与航天开发和应用有关事物的综合调整等。
2012年,自民党重掌政权,但仍继续执行已颁布的新航天法,制定各项航天政策和确定开发体制。为标榜自民党的功绩,安倍甚至否定民众和舆论界公认的应以“2011年为日本航天产业化元年”,而把2013年定为“日本航天产业化元年”,提出“提升航天开发能力和应用水平,尽快振兴航天产业”,鼓励企业“提高设计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知名度,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为推进这一目标的落实,2013年1月,安倍内阁又重新公布了新航天基本计划,明确了以下几点:
1)一个基本目标—“加速推进航天产业化”;
2)两项基本方针—“扩大应用”和“确保自主性”;
3)三大重点项目—“安全保障和防灾”、“振兴产业”和“航天科学等新领域”;
4)四项基础设施—“定位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和“空间运输系统”;
5)五项基本措施—①夯实产业基础。“官民协力,面向国外推出一揽子服务式空间基础设施”和“加快研发与推进应用”的新策略。②开展情报收集和调查分析。强化航天政策委员会和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功能。③推进航天外交。“脚踏实地地推进多国间合作”、“强化双边合作”。④明确安全保障政策。灵活、有效地应用航天成果,实现“掌握情报”、“情报共享”和“统一指挥、管理”。⑤认真考虑环境问题。“开展国际对话”、“执行太空态势感知体系”和“开发清除空间碎片技术”。
日本正从国家层面开始重视并全力支持航天开发,推进应用和产业化,以加快产业振兴。自2013财年起,日本扭转了开发经费连续4年递减的局面,航天开发预算较2012财年增加了17.7%,而2014年又较2013财年初(尚不包括可能追加部分)增加了13.9%。
而在预算中,日本航天防卫经费增加比率最高:2013和2014财年分别较2012财年增加144.7%和110.23%。这尚不包括追加部分,以及与民营企业签订合同支持开发和完善X频段专用国防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系统、以内阁其他渠道支持早期预警卫星及其核心部件(双频段红外遥感器)等的费用。
到2014年2月底,日本共发射航天器(含货运飞船)194个。其中,国家投资研制120个,商业卫星40颗,民间机构开发的卫星34颗;为国外研制并交付卫星3颗,尚有3颗在研卫星的合同;为国外发射了1颗卫星,尚握有3颗卫星的发射合同(加拿大卫星通信公司1颗,越南2颗)。
日本航天开发政策还强调:在确保为国民提供通信广播、气象、地球观测、环境变化、防灾救灾等航天产品的同时,积极落实、全力发展以科学技术发展、安全保障和振兴产业为中心的最优先级、优先级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
1)最优先级(5年内):完成自主研发的“准天顶卫星”(QZS)系统(4星体制),满足防卫、反恐用的快速响应小型侦察卫星系统,先进的“具备新系统结构的先进观测卫星”系统,智能化、商业发射用的H-2A火箭和以“艾普斯龙”(Epsilon)为基础发展的低成本、机动能力强的固体火箭。
2)优先级(6~10年):完善“准天顶卫星”系统(7星体制),构建自主防空网络用的早期预警卫星,配备机械手,清除轨道碎片用的环保卫星,双项多用途通信卫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H-3火箭,以及低成本的太空发射系统。
3)长远发展规划(10~50年):构建起太阳光发电卫星系统,研发平流层卫星、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系统和海上发射系统。
此外,日本还计划加强通过发射民用器件性能验证卫星等来推进先进的民用技术在航天领域的应用,把技术成熟的航天专利技术拓展到民用领域,缩短先进的民用技术在航天领域应用的时间,大幅度地提高航天产业的效益,推进/支持航天发展。
新航天法颁布近6年,日本航天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航天产业化进程加快,加快了航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提高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成为日本产业振兴的源动力。2012年,日本航天产业的销售额突破7兆日元。日本的航天/防卫/安全保障专家、日本航空宇宙工业会前技术部长、东京财团研究员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宇宙经济技术委员会委员坂本规博预测:执行航天产业振兴政策,到2020年日本航天产业的销售额将翻番,达14兆~15兆日元。

日本“艾普斯龙”火箭飞行示意图
不过要指出,日本在推进航天产业化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程中,依然存在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日本航天开发投入已超过“航天开发投入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0.05%”的底线,是否会得到国会(国民)认可?即便如此,其实际投入与计划需求尚存在巨大差距,尽管三菱重工业、三菱电机、日本电气等民营企业在不断加大航天投入,短时间内仍很难解决两者间的矛盾;虽然日本采取并将继续支持民用器件在航天领域应用,但依然无法彻底解决因缺乏劳动力,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过高,资源匮乏,绝大多数原材料要靠进口,致使航天产品,特别是火箭和整星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同类产品市场报价,导致缺乏市场竞争力。
不过,新航天法的颁布,开发体制的调整,开发重点的转移,已成为驱动日本产业振兴的源动力,为日本航天活动带来新生机。随着政府支持卫星、火箭等航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经济产业省等正大幅度加大在技术方面占绝对优势且利于产业化项目的投入,以促进“艾普斯龙”火箭、“具备新系统结构的先进观测卫星”平台进入国际市场,以及支持发射民用器件验证卫星等推进民用器件在航天领域应用并进入国际市场、加大对超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小型化研发的投资力度、支持太阳能发电等。这对推进日本航天产业化和解决上述困难,加快航天开发、应用和产业化,加速产业振兴会产生一定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内阁把发展低成本的“艾普斯龙”火箭、H-2A火箭的智能化和低成本,发展运载能力更强的H-3火箭作为最优先和优先级发展项目。这对振兴其航天产业,增强航天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无好处。但与其否认侵略历史,不断与邻国制造矛盾与冲突,以及完善以情报搜集卫星为核心的情报搜集系统、X频段防卫通信卫星系统、加速早期预警卫星研发、拟尽快启动防卫快速响应系统等联系起来,不得不使人们怀疑其是否另有目的,需爱好和平的人们关注。
陆征/本文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