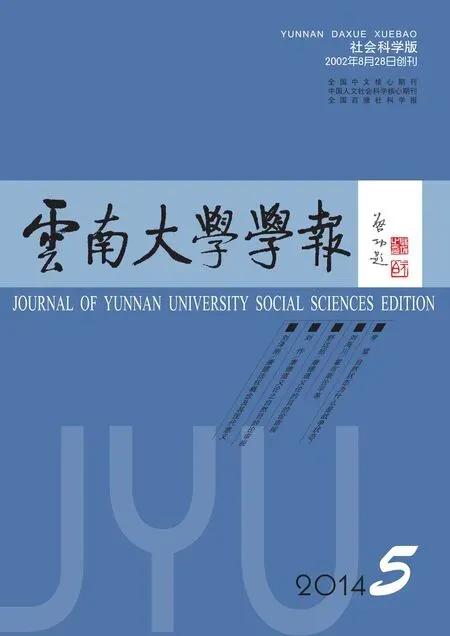康德法权概念及其现代意义
2014-03-06刘泽刚
刘泽刚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法律是什么?这被称作“法律概念问题”。法哲学史可被看作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各种回答汇集而成的知识领域。法律概念问题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一种规范,即法律是什么?或者说,法律与道德、伦理相比有何独特性?二是法官面对案件时应当适用何种法律?无疑,前者才是实践哲学关注的论题。《道德形而上学》第一部分“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就是康德关于法律概念问题的阐述。由于德语“Recht”一词兼具“法律”和“权利”之义,对康德而言,“法律概念问题”即“法权概念问题”。
康德指出:“法权是什么?”(Was ist Recht?)这是一个令法学家尴尬的问题,正如“真理是什么?”(Was ist Wahrheit?)令逻辑学家尴尬一样。他进一步声称,经验法学家是无力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一种纯然经验性的法权论是(就像斐德鲁斯的寓言中那个木制的头颅一样)一颗可能很美、只可惜没有脑子的头颅。”[1](P238)法律概念问题只能交由哲学来解决。遗憾的是,康德的自信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和理解。相反,关于康德法权概念的种种误解阻碍了对其法权思想乃至道德哲学的正确理解。
一、关于康德法权概念的异议
康德法权论在法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显赫。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历来存在的各种对它的批判。叔本华认为康德法权论根本不值一驳:“《法学》是康德最晚期的著作之一,并且是如此无力的一本著作,以致我虽然完全否定它,却认为对它进行辩驳是多余的;因为它,好像不是这个伟人的著作,倒像是一个凡夫俗子的作品似的,是必然会由于它自己的衰竭而无疾而终的。”[2](P717)当代学者赫费(Otfried Höffe)指出: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法权论被视为哲学含量较低,而且缺乏其他康德著作那样的广度、明晰性和尖锐性。[3](P190)
的确,即便以宽容的眼光审视,《道德形而上学》的文本和论述上的瑕疵仍有很多。这可能与印刷排版错误有关,*《道德形而上学》英译本对部分段落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德文本中也有一些调整。关于这些调整的情况可参见格雷格对《道德形而上学》文本的译者注:Mary J. Gregor: Translator’s note on the text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 I.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 Greg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55-357.但成书仓促且作者没机会进行修正也是重要原因。然而瑕不掩瑜,这部著作总体而言仍然是构思严密且逻辑清晰的。对法权论的误解多源于对康德实践哲学的结构和特征把握不准。而这导致了对康德的法权概念的种种误读。
第一种是以康德的其他道德哲学著作中展现出来的立场为出发点,对法权论形而上学进行道德哲学的解析。近几十年来,这一阐释路径占据了主流。包括罗尔斯、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倾向于以《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为依据解读康德的法权论。相反,集中反映康德法律和政治思想的《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却长期遭到忽视。在1991年玛丽·格雷格(Mary Gregor)出版《道德形而上学》译本前,英美学者必须忍受没有可信译本带来的不便。尽管不少学者也能直接参照德文版本,但康德文本的难解特性无疑产生了实际的阻碍。而这似可解释为何杰弗里·墨菲(Jeffrie Murphy)1970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康德:权利哲学》一书的观点几乎完全来自其对《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书的解读。[4]这种“回溯式”的探究尽管也有不少创见,但大多过于强调法权概念“纯粹”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经验运用的一面。
第二种可称为“融合式”解读。近些年来,法学界不少学者从“为我所用”的角度将康德法权哲学与具体部门法论题结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此类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研究者出于自身专业的需要,满足于对康德哲学采取断章取义、为我所需式的片段解读;二是哲学界对康德法权思想的共识较少,也抑制了法律学者从法哲学角度的深入研读。在这种情形下,私法学者注重康德私法的论述;公法学者主研康德公法学说;刑法学者关注康德刑罚理论;国际法学者侧重康德国际法权观点。这类“盲人摸象”式的研究只是把康德法权思想作为一种初级资源,并未对其合理性进行全面、深入的提炼,有时甚至对康德出于时代局限性的个别论述作一番揶揄后草草了事,严重伤害了康德法权论应有的权威。究其根本,这类研究更多地注重了康德法权概念经验运用的一面,而没有正视其纯粹的一面。
对法权概念的片面理解导致了康德法权哲学形象的分裂。在研究者笔下,他既是实证派,又是自然法派;既是革命者,又是保守者;既是义务论者,又是后果论者。有学者甚至判定:康德根本就没有严格的、一以贯之的法哲学,而仅有一些关于法律的片段见解。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曾感叹“康德的伦理学已经成为它的批评者的囚徒”。[5](P1)康德的法权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充分尊重康德哲学的体系结构,才能准确认识其法权概念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彰显康德法权哲学应有的价值。
二、康德法权概念的体系意义
(一)静态结构的意义
在“法权论导论”第二节“什么是法权?”中,康德对法权概念做了如下说明:“法权是一个人的任性能够在其下按照一个普遍的自由法则与另一方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条件的总和”。[1](P238)这个法权概念包含以下特点:1.法权只涉及人格间外在的实践关系;2.法权仅关涉任性(Willkür)间的关系;3.法权只考虑任性交互关系的形式。
但这绝非法权概念的“定义”(Definition),至多算是对法权概念的阐明(Exposition)。康德对“定义”的要求很高:“定义,正如这个术语自己所给出的那样,本来只是要表示这样的意思,即将一物的详尽的概念在其界限内本源地描述出来。按照这样一种要求,一个经验性的概念是根本不能定义的,而只能说明。”[6](P562)在明确指出经验性的概念不能定义之后。康德以一种较柔和的语气说明其实即便是先天被给予的概念也是不能定义的。有趣的是,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特别提到了“法权”(Recht)概念是不可定义的:“严格说来,甚至也没有任何先天被给予的概念是可以被定义的,如实体、原因、法权、公平等等。”[6](P563)康德认为,定义应当是将一个对象的详尽概念在其界限内本源地描述出来。其中,“详尽性”是指对象特征的清晰性和充分性;“界限”是指对象特征的精密性,即这些特征不应超出属于该详尽概念的东西;“本源地”是指这种界限规定不是从任何东西那里派生出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对一个对象的某种解释不能居于对该对象的一切判断的最高位置。
康德认为,只有数学才是具有定义的。因为数学所思考的对象可先天地在直观中加以描述,而这个对象所包含的正好与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完全相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学对象是构造出来的,因此对其概念描述才可能是详尽、精密、本源的。不通过定义,数学中就不可能有任何概念。而哲学的对象则并非如此,哲学概念最大的特征就是其“被给予”的特性,对给予的概念只能通过对其分解的方式来完成。而这就注定了哲学概念的不完备性。从根本上说,哲学的定义只能是对给予概念的解释和阐明。哲学不能像数学一样从定义开始。哲学必须容忍一些不太完备的、具有缺点的对概念的阐释。如果非要让哲学从精确定义开始,那么哲学就根本没法开始。康德也并没有对法权概念进行过定义,而只是对其进行“说明”或“阐明”。实际上,任何对法权的哲学思考都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都是对已经给予的法权概念的一种分解和抽取。法权的哲学阐释根本无法一次性地把握住法权的整全性,而只能基于某种特定立场和出发点对法权进行解释。也正因为如此,任何法哲学的首要工作都是对法的概念进行阐释,否则便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几种理想链模型.在高分子链的各种模型[1]中,最简单的理想模型就是自由结合链.所谓自由结合链,就是把链中最基本的结合单元化学键看成是相互自由连接的.这些键在相互连接时,没有键角限制、化学键没有体积,键在空间的取向完全自由、没有位垒及其他任何阻碍其链接的额外限制.每个键在与前一个键连接时,在空间的取向完全是随机的.这样,由n个键长为l的键所组成的链就是自由结合链,其均方末端距很容易用矢量和的平方平均或用无规飞行的统计分布函数进行平均而得到:
对康德而言,法权概念的阐明更具有显著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康德是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提出其法权概念的。在康德的知识分类谱系中,形而上学属于哲学知识,哲学知识属于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来自原理(ex principiis)的知识,与之相对的历史知识(或经验知识)则是来自事实(ex datis)的知识。在康德看来,理性知识必定是先天的。但有两种先天的知识,依据与概念的关系不同,分别为:从概念而来的哲学知识;从概念的构造而来的数学知识。所谓构造概念,就是在先天的而非经验的直观中将概念提供出来,或者说,在直观中提供出与其概念相一致的对象来。由此,概念就成为康德形而上学知识的重要根据。因为如果概念属于形而上学,例如实体的概念,那么,仅仅从分析这些概念产生的判断也必然属于形而上学,例如,“实体是仅仅作为主体实存的东西”等等。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明确指出:概念而非分析判断,才是形而上学特有的。而且康德还将先天概念称为“构成形而上学的材料和建筑工具”。当然,在康德看来,即便把所有先天概念都收集在一起,并对它们进行分析,也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只与先天综合命题打交道。而这些先天综合命题也是从概念中产生的。[7](P274)
早在1768年,康德就宣称自己正在进行名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系统著作的写作。有证据表明,在早期使用“道德形而上学”这一术语时,康德仅仅是指道德必须被奠基于概念的分析之上,而非直接诉诸情感。[8](P3)那时的康德主张:“只有先验的概念才有真正的普遍性而且是规则的本源(principium)。德行只能依概念去判断,也就是先验地判断。依图像或经验所作的经验性判断,不能为我们提供法则,只能提供实例,但后者的判断必须凭借先验概念……一切道德的基础是概念”。[9](P240)虽说这些论述并非专门针对法权问题而发,但由此可得知康德法权概念也应当是其法权论形而上学知识的来源和基础。法权概念的品质直接影响其法权论形而上学的质量。因此,必须重视康德对其法权概念的阐释。
(二)动态建构的意义
在康德的规划中,哲学应当包含批判哲学及未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体系中只有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两个部分。康德本人并没有计划去构建脱离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哲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正因为如此,康德几乎不使用“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这个概念。《道德形而上学》第一部分“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既不是“法权形而上学”也不是“法哲学”,而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康德通过法权概念阐明建构起来的法权论形而上学就是其关于法权问题的哲学思想的集中表达。
怎样才算从哲学层次把法权概念弄清楚了呢?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并没有对此作详细阐述。幸运的是,康德在《逻辑学讲义》中曾指出:“包含在德行概念中的特征有:1)自由的概念,2)执着于规律(义务)的概念,3)克制好恶(假如这好恶违反德行规律)的概念。”[10](P26)在康德看来,只有将德行(Tugend)中的这些成分条分缕析,才能使其成为明晰的概念。这些论述的价值是很明显的。作为广义“道德”(Sitten)概念的两个方面,“法权”与“德行”应当分享一些共同的特性。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从道理上讲,法权概念也应该包括自由概念、法则(义务)概念和动机概念。如果不能将这些特征从法权概念中分解出来加以明晰化,那么关于法权就只有模糊的看法,甚至也不能从理性上区分“法权”与“德行”。这样一来,“法权论”就只能是没有坚实依据的臆断。很明显,康德是不会容忍这种状况的。他曾尖刻地批评经验法学家的局限性,并许诺要超越他们。于是,他运用独特的形而上学方式,以逐步阐明法权概念各个要素的方式构建其法权学说,最终产物就是“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
从文本上看,康德的法权论形而上学的确是以“法则”、“自由”、“义务”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康德通过提出“法权普遍原则”、论证“外在自由”的特性廓清了法权与德行的主要区别,又以法权义务为线索,构建起法权论形而上学的主体构架。相比而言,对法权的“动机”问题谈得较少,只是结合法则、自由和义务进行了简要说明。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已经非常详细地论证了动机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康德看来,严格的法权概念本身可以不考虑动机。
必须承认:康德对法权阐释的几个方面的论证都引起了很大争议。如关于法权普遍原则,康德似乎缺失了一个演绎。对此,学界分成了很多派别:有的学者认为康德是因为觉得该演绎过于显明,所以有意省略之;有的认为康德有无须提供这个演绎的理由;有的则认为康德根本就无法做出这样一个演绎,并进而否定康德法权论形而上学构想的合法性。[11]又如,康德对法权的“外在自由”的论述也显得高深莫测。学者们对外在自由与道德自由、先验自由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以研究康德自由理论著称的阿利森(Allison)也对法权论的自由问题退避三舍。在其《康德的自由理论》一书中,阿利森虽明确指出“外在自由”是康德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中心概念,却对其“暂且不予考虑”。在法权义务的问题上,康德的处理同样令人迷惑。康德在“德行论”中曾明确分析了14种伦理义务,其中每一种义务都明确或隐含地以某种绝对命令的公式为基础。反观“法权论”,则大相径庭。康德虽然对一些法权,如对父母的法权和家长的法权,也做了义务和责任方面的说明,但大多数法权的义务基础却并不明显。换句话说,康德似乎并没有过多地呈现这些法权义务的道德基础。
这些问题并不能以否定康德法权概念的方式加以解决;相反,只有在承认康德法权概念合理性的前提下,才能“内在地”理解这些问题,并对其进行同情性地分析与解释。否则就只能不顾康德的内在理路,“外在地”批判后草草了事。这样做尽管快意,却失去了理解大师思想精髓的机会。关于这一点,阿多诺(T.W. Adorno)在其解读康德道德哲学的著作《道德哲学的问题》中曾说:“如果说我能够给你们提供阅读康德的方法,那就是你们要对连续的、所谓正式的总体意图与无数的修改(康德试图用这些修改使他所遇到的辩证关系生效)加以区分,并且予以正确的理解,这样,你们就可能从整体上理解康德”。[12](P146)的确,面对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康德哲学,我们必须更加虚心与耐心。惟有如此,方能窥其堂奥,得其珍宝。
(三)体系限定的意义
对康德来说,法权本身就是道德的一部分,而非与道德无涉。只有从道德哲学的立场出发,才能把握康德法权概念的精髓。但康德还提出过一个“严格法权”(Das strikte Recht)的概念。不少学者认为,康德试图以此厘清法权与道德之区别。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就是康德对法权的实证主义界定。这些看法误解了康德。严格法权概念也是法权论限定的范围内的一个道德性的法权概念。
康德认为:“严格的法权,即不掺杂任何伦理性因素的法权,就是除了外在的规定根据之外不要求任性的其他任何规定根据的法权”。为了进一步做出说明,康德给出了一个著名的例证:“如果说,一个债权人有一种法权要求债务人偿还其债务,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债务人记住,是理性本身责成他这样做,而是一种强迫每个人这样做的强制,完全能够与每个人,因而也能够与他自己根据一个普遍的外在法则的自由共存;因此,法权和强制的权限是同一个意思。”[1](P232)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援引上述文字并做出如下评价:“康德的解答充斥着严格法的精神,因而也充斥着法律成熟期的精神,而成熟期的法律与严格法之间存在着许多密切的关系……在康德的理论中,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13](P143)这其实是一种误读!以上文本探讨的是“法权”(Recht)与“伦理”(Ethik)的关系,而非“法权”与“道德”(Sitte)的关系。
如果了解康德所处时代的道德哲学与自然法学对“道德”一词的独特用法,术语方面的疑惑或可得到很大缓解。据比尔德(B. Sharon Byrd)与赫努希卡(Joachim Hruschka)考证,康德对“道德”一词的用法很可能来自17世纪伟大的自然法学家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的“物理实体”(entia physica)与“道德实体”(entia moralia)的著名区分。在普芬道夫的区分中,“道德”仅意味着非物理的或非自然的。[14](P4)这样一来,至少从话语背景上看,康德仅将形而上学规划为两个部分,乃至将法权论形而上学划入道德形而上学的做法就不奇怪了。另外,这一背景还告诉我们不能从当代狭义的“道德”术语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涵盖了所有严格的实践领域。
既然同属道德实践领域,法权和伦理就都是因自由而可能的。自由与自然有不同的法则。自由的法则就是道德的法则。对人类这种任性受到感性影响,从而不是自行去遵守法则的不完善的理性存在者而言,道德法则只能采取命令的形式,而且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命令式。为了使外在自由共存,人们就必须承认法权的效力,这是无条件的。尽管法权与伦理有不同的动机,但二者都有立法,都是强制性的,而不是邀请性的。法权法则仅仅要求外部的合法性,所以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执行;伦理法则还涉及对道德主体内心目的的道德要求,而目的的设定是不可能由外部强加的,只能由主体自行设定,所以不能通过强制执行。使一种行为成为义务,同时使这种义务成为动机的立法是伦理学的。而在法则中不包括后者,因而也准许另外一个与义务本身的理念不同的动机的立法,是法权的。
法权的“严格性”仅仅是就其与伦理的区分而言,说到底是外在自由(强制)与内在自由(强制)的区分。法权与伦理的关系不是外在对立的,而是关联互补的。严格法权与“法律实证主义”大异其趣。后者强调法律对道德的独立性,试图将法律构建为规范自足的体系。遗憾的是,许多学者都忽视了康德对法权概念的明确的道德形而上学限定,而误以为或想当然地认为康德讨论的是一般的法权概念的定义;还对“法权论形而上学”的性质、任务产生进一步的误解,并严重误读康德法权论文本中的论证与观点。
三、康德法权概念的现代意义
拉斯穆森(David M Rasmusen)认为,在哈贝马斯之前,德国文化产生过两种关于法律的理论话语,分别是以黑格尔与韦伯为代表。而哈贝马斯则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开创了第三种话语模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对黑格尔与韦伯都进行了超越。就对前者的超越而言,哈贝马斯“既不将法律的发展与生产性政治经济捆绑在一起,也不将其与国家的理性独立性捆绑在一起”。就对后者的超越而言,哈贝马斯“从规范的有效性向度弥补法律赤裸裸强制性的缺陷”。[15](P4)
拉斯穆森所谓的哈贝马斯的两重超越其实并没有超越康德法权概念的旨趣,反而恰恰对应于康德法权概念限定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康德对法权概念有着严格的实践哲学限定,以防其与实用、审慎等关注混同;另一方面,康德的法权概念是对外在自由强制权限理性追问的产物,此种意义上的法权正是实证法律与政治制度的规范根据。
哈贝马斯真正超越康德的地方并不在其思维的高度,而在于其广度。这尤其体现在他广泛借鉴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多种成果,并使之与哲学思维方式相契合。重视多学科的交叉运用,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特征相关。这种复杂性首先是由现代社会急剧的功能分化与系统分割造成的。经济、政治、法律日益成为功能相对独立的系统,每一系统内都有独特的编码与沟通方式,各系统间又存在着复杂的耦合与关联。人类社会,乃至法律系统都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形下,对法律与政治的阐释很难以单一学科来完成。
即便不考虑法律在功能方面的膨胀和扩张带来的复杂性因素,规范层面的复杂性似已难以应付。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律规范之为有效的,还因为它不仅能够用道德的理由来辩护,而且也能够用实用的伦理-政治的理由来辩护,必要的话,它们也必须代表公平的妥协的结果。在辩护法律规范的时候,必须运用全部范围的实践理性。”[16](P192)哈贝马斯的实践,与康德严格限定的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其中包含了更多审慎、实用层面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严格限定的实践法权概念又有何价值呢?
或许有必要回顾康德的如下揶揄:“一种纯然经验性的法权论是(就像斐德鲁斯的寓言中那个木制的头颅一样)一颗可能很美、只可惜没有脑子的头颅。”[1](P238)时过境迁,如今的法学犹如一个有很多脑子,但却六神无主的木偶。这就是法学中的所谓“当代多元主义(contemporary pluralism)”。实际上,多元主义法学的基础正是法律概念的多元。也就是说,不同的法学研究路径依据的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例如,法律经济分析依据的是法律的经济概念;而法社会学则依据的是不同类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法语言学依据的是语言学视角中的法律概念,等等。对这些法律概念,不能一概否定。它们对反思当代法律都是有价值的。但对这些概念也不应该等量齐观。外在自由的法权概念仍应具有根本意义。在康德看来,法律的第一特性是其实践性,而实践正是因为自由的理念而可能的。所以康德的法权概念的核心是自由,而非法律可能具有的功能(如秩序、福利、效率等)。
康德的法权论以外在自由的永久协调一致为鹄的。这是其所有规范性分析的核心。其他特性都必须围绕这一本质加以认识,而不能喧宾夺主。这一点对当代法学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只要一种法学思考是实践取向的,也就是以促成某种目的的实现为取向的,那么就必然不能绕开康德意义上的法权概念。当然,现在也有许多法学理论并不直接以实践为取向。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理论取向的法学研究忘记了自己的局限,反而僭越于实践取向之上,或否认实践特性的至上性,就会造成极大的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混乱。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波斯纳(Posner)*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拉丁文学荣誉学位),1962年以哈佛大学法学院第一名荣誉毕业。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威廉·布伦南的法律助手。1969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81年,里根总统任命波斯纳为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在学术上,波斯纳涉猎广泛、勤于笔耕,著述丰富且影响巨大。其作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位居美国法学界引用率前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我国大陆法学家朱苏力先生长期译介,波斯纳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非常深广,是年轻学子追捧的法学学术明星。的法律经济分析。
波斯纳在法学中涉猎颇广,除了法律经济学外,还包括法律与文学、法政治学等。其著述丰富,且影响巨大。波斯纳的高产与博学正是法律当代多元主义的典型象征。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不仅影响深远,且新见、异见频出。在众多令人惊异的观点中,其关于1954年“布朗诉教育局”(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的评价所引发的争议较多。布朗案是美国民权史上里程碑式的判决。它宣布此前在美国长期实行的“隔离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违宪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有色人种争取法律平等的民权运动的进展。在布朗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给出废除教育种族隔离制度的日程,只是宣布该制度应该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予以废除。原因在于:第一,这绝非司法权消极中立特性所允许;第二,对立法和行政权来说,这一问题涉及面很广,很难给出具体方案。于是,各地对布朗案判决的执行情况差异很大。而且有不少南方白人家庭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颁布后,宁可举家搬迁至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区(这种现象被称作“白人逃亡”[white flight]),或干脆付费送子女就读高价的白人私立学校。
针对此种情形,波斯纳从经济学的偏好概念出发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评价。在他看来,“种族歧视”本身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偏好。部分白人家庭面对判决后可能发生的黑白同校,主动花钱搬迁或让子女就读私立学校,这反映了种族歧视这种偏好的经济特性。而在波斯纳看来,这正提示着另一种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利用白人对种族歧视、黑白隔离的偏好的重视,让他们为黑人社区公立学校教育条件的改善“埋单”。具体而言,波斯纳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本可不判决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是要求南方各州政府对黑人教育追加更大的投资,并以此作为维持种族隔离学校的条件。这样一来,平均收入更高的白人就会为教育领域的隔离政策付出更多的代价。而这将会使白人无理由的“嗜好性歧视”转换为“有效率的歧视”。在波斯纳看来,这远比最高法院的判决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波斯纳甚至还当真算起了这笔经济账:“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社区中有200名黑人和800名白人,黑人的平均收入为5000美元,而白人的平均收入为1万美元,假设消除种族隔离教育能使黑人平均增长2000美元的货币和非货币收入(不计变化了的教育条件及更佳就业的滞后),这样,黑人居民就可以从消除种族歧视的过程中取得40万美元的收益。但如果该社区中的白人愿意平均每人支付1000美元而避免学校的黑白人学生混合,那么他们就是愿意为改善黑人的教育支付80万美元,并以此作为继续进行学校种族隔离的代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即白人在这方面的所有支出都应成为黑人的收益。如果真是这样,这种白人的开支会使黑人的收入比取消种族隔离时的收入高出40万美元。”[17](P858)
波斯纳的观点自然招致不少非议。如有学者坦言:“波斯纳一直强调法律只应追求‘有效率’、‘有用’,认为这才是惟一的幸福之源,认为这样做(促成社会财富总量最大化)对社会带来‘最好的结果’(best results)。而又由于财富是较可以估算的,所以可以估算其经济上的后果来决定法律应该如何规定,这让法学显得‘科学’了。但是……其最初的大前提并没有被证立,即为什么‘社会利益’或‘社会财富总量最大化’为什么是一个价值、能带给人们什么幸福?”[18](P456)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波斯纳的分析并无不妥,反而是非常有创意和有实效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波斯纳的反对者都是一些百无一用、头脑僵化的道德说教者。
然而,若从实践取向的法权概念出发,我们就不得不对波斯纳方案的实践价值提出质疑。如果人类平等的尊严不能得到保护就侈谈效率问题,固然可能非常有启发性,很能显示作者的聪明才智,但却不符合实践的原则。毕竟波斯纳的构想如果能够符合法权,如果其构想背后的准则能够成为法则,那么我们将会构筑出一种怎样的外在自由和谐共存的法律制度呢?这首先会取消作为平等的生而具有的法权。在这一分析中黑人看似取得了好处,但其人格中人性却成为某种外在功利目标的单纯手段。这直接违反了康德法权论中提出的“人性的法权”和“生而具有的自由法权”。如果我们能构想并接受以波斯纳分析中暗含的准则为基础的法律制度,那我们甚至也有权设想和讨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经济效率问题。说到底,波斯纳的分析只是在纯粹理论的兴趣上来说才有意义,从实践立场看则乏善可陈。如果把这种出于纯粹理论兴趣,或出于技术和实用立场的论述当作严格的实践命题,会严重干扰人们对法律的实践探讨。这一点从一些学者对波斯纳进行反驳时的混乱立场也能看出端倪。在上文所引述的反对波斯纳的言论中,我们不难读出这种盲目与混淆。实际上,反驳者只需指出波斯纳的分析不属于严格的实践意义的分析即可,更不应该进一步将严格实践意义上的法律与福利、幸福混为一谈。而这一洞见恰恰是两百多年前的康德法权概念早已揭示了的。
我们不能以法律的复杂性为托词容忍法律观念的混乱。对今天的人类社会来说,以外在自由长久稳固共存为标准的法权概念仍具有首要的价值。关于法的思考,如果不想沦为纯粹的理论游戏,就必须关注与外在自由相关的实践性,并以此为思考的背景,否则就容易滋生许多冗余甚至无聊、无益的理论分析。康德的法权思想在当下仍焕发着勃勃生机。今人到底能从中获得多少启示,取决于我们阅读与阐释的真诚、耐心与决心。
参考文献:
[1]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M]. 张荣,李秋零译. 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石冲白译.杨一之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奥特弗里德·赫费. 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M]. 郑伊倩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Katrin Flikschuh. On Kant′s Rechtslehr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1,1997.
[5]芭芭拉·赫尔曼. 道德判断的实践[M]. 陈虎平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6]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C].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Allen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Timmons, Mark, (ed.)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erpretative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黄添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康德. 逻辑学讲义[M]. 许景行译.杨一之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Gerhard 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17:1 , 2009.
[12]阿多诺. 道德哲学的问题[M]. 谢地坤,王彤译.谢地坤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罗斯科·庞德. 法律与道德. 陈林林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4]B. Sharon Byrd and Joachim Hruschka.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Comment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戴维·M.拉斯穆森. 有效之法如何可能——评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高鸿钧译. 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C].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16]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 童世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7]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M]. 蒋兆康译.林毅夫校.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18]林立. 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