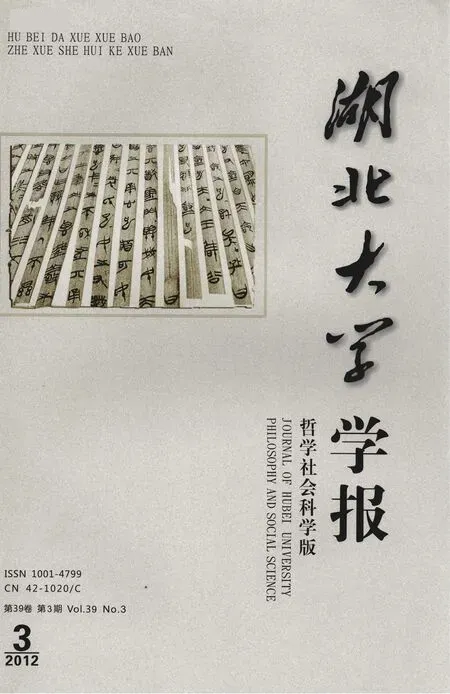从法权概念到法权逻辑——中国法权研究评析与展望
2012-04-10段凡
段 凡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从法权概念到法权逻辑
——中国法权研究评析与展望
段 凡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法权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混乱的名词和概念,较少上升为一个上位概念的法权。在英文文献中,还没有一个与汉语法权完全对应的单词。是一个既不完全相同于权力,更不完全等同于权利的概念。不从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和辩证关系中理解法权,则无法建立一种法权逻辑。法权逻辑是指对法权关系进行重新安排的一种思维、理念,并循着这种思维和理念,对中国的法理论、法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厘定和建构的过程。对于法权来说,一种新的法权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维度,其一是公权的建设和规范,其二是私权的维护和保障。这两个方面的维度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法权逻辑。法权逻辑的重新确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较大意义。
权力;权利;法权概念;法权逻辑
一、汉语法权在中国的起源
法权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混乱的名词和概念。说它熟悉,因为它曾经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更谈不上被客观公正地对待。说它混乱,是因为论者要么是从法律权利,或者是从法律权威,来对法律关系的内容进行说明,而较少上升为一个概念的法权,以致于法权成为一个边界不怎么明晰的概念。这可能和汉语法权概念在我国的一段历史有关,汉语法权产生的历史命运,是由于一些原本可以不出现的“事故”造成的。它们的发生既具有历史偶然性,同时也具有历史必然性。具体来说:
第一,法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近代史时期。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开埠通商,强行设置租界。为了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也为了保护本国公民“利益”,列强利用武力强行同清政府签订了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赋予外国领事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此外,还在租界之内设置会审公廨。会审公廨其实是一个法庭,它是领事裁判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领事裁判权为‘甲国领事在他国得裁判甲国人民’,而治外法权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则是‘在国外的某国人民因外交互惠等原因不受他国司法管辖,仍受本国裁判’。清末民初因翻译等原因,致两个名词常被拿来诠释外国人在华享有的种种司法特权,终成惯例”[1]1。治外法权里面的法权,其实是指一种公权力,即司法权。
所以,法权名词在中国之最早闪现,是基于一种外来的暴力。从其最初的内涵来理解,彼时的法权是指一种公权力。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法权的掠夺,其实也是获取在华的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是指,本来不该获得和享有公权力的列强,却在中国境内获得和享有了公权力。以致于现在有学者谈及法权,仍然以这种相同或近似的意思来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
第二,建国后,法权一词曾是一个“流行”但也被误读过的概念。说它流行,是因为在我国早期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法权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汇。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早出现“法权”字样的,是在马克思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这段翻译文字的原文是这样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21~23在这里,马克思将“法权”和资产阶级相联系,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意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后来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他“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发挥了马克思上述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是一种残余的阶级关系”[3]。
而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1958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工农兵学商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4]447~450既然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已是指日可待,那么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则到了应该破除的时候。紧接着,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转载了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既然将法权和资产阶级联系,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之一,便是超越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进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只是细究法权的来历,却发现马克思主义著作原本中被译为“法权”的词汇,“实际上都是德语和俄语的‘法’(Recht/npabo)一词。由于一词多义的缘故,在原著中不同上下文所使用的这一词汇分别表达了‘法’和‘权利’两种不同的含义,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微妙的,因此给翻译马列原著的译者造成了一定的翻译困难。译者在一些地方苦于搞不清到底是译为‘法’还是译为‘权利’更切合原文之意,便将这两种含义合二为一,生造了一个‘法权’的概念,在吃不准如何翻译的地方便以‘法权’一词代替”[5]。
根据陈忠诚先生的解释:“被译为‘法权’之处的原文,实际上都是德语和俄语的‘法’(Recht/npabo)一词。由于一词多义的缘故,在原著中不同上下文所使用的这一词汇分别表达‘法’和‘权利’两种不同的含义,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微妙的,因此给翻译马列原著的译者造成了一定的翻译困难。译者在一些地方苦于搞不清到底是译为‘法’还是译为‘权利’更切合原文之意,便将这两种含义合二为一,生造了一个‘法权’的概念,在吃不准如何翻译的地方便以‘法权’一词代替。……终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通知,废止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名,总算是拨云见日,‘法权’终于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翻译失误,真理战胜了谬误。”[5]
二、法权概念在中国研究的现状
国内以法权作为论文关键词的文章并不太多,具有代表性的论作中,对法权的理解或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多将法权界定为权利或法律权利。例如,高远戎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研究了我们国家曾经发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因、过程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其将法权界定为权利;龚廷泰和眭鸿明从民法制度的视角来看待习惯中业已存在的一些权利,以期对中国民法典的编撰提供一些见识,在理论上将权利同人的价值和尊严进行互通,认为法权是主体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直接权利要求,存在于主体的相互交往活动之中,它是国家法定权利构造的基础;许章润认为法权即自由,其实在法学和政治学上,权利和自由应该联系在一起,自由是权利的内涵之一。从权力的向度来思考,它是不可能和自由进行定义转换的;第二,将法权界定为法律的权威。例如,林乾曾撰文从“法与天下共”论传统中国法权与君权的关系,但该文除了标题带有法权一词之外,内容中几乎不见法权一词出现。其实该论作主要论述君权和法律之间的一种关系,由此可以确定该文法权一词的含义是指“法律的权威”;第三,将法权定义为法律主权和法律关系。典型的是,一行从法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乃至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没有给法权一个明确的定义,倒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引用法权,以致出现了不同层面的含义。有时将法权解读为国家法上的法律主权,提出法权(国家)的实现,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有时将法权限定为法律关系,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构成了多层法权关系;第四,将法权界定为法律本身。诸如,郭道晖曾撰文解释法权关系为什么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以此回答孙国华教授和管仁林博士的质疑。他将法权指为介于主观法(实然法)和经济基础之间的那部分应该表现出来的应然法律;第五,将法权界定为公权力。比如,李启成曾对调查法权委员会进行个案研究,来考察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他从近代史那段丧权辱国的时期出发进行考察。认为治外法权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法律现象,治外法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公权力;第六,将法权界定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例如,储昭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启示与教训进行了再认识,研究法权的逻辑基础与实质。认为法权的抽象性,体现是其内涵的抽象性和空泛性,它本质上只是一种形式的法则。在这种形式法中,如此抽象的权利就其效应而言,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或许可、一种价值上的单纯应然,还达不到真正现实的普遍性。
对于汉语法权的英文翻译而言,相同的法权一词在不同的中文文献之中,却被译成了,“Legal Right”、“Legal Rights”或者“Rights”,即译为“法律权利”或译为“权利”。而较早的关于法权的概念,是“治外法权”,其英文翻译为“Extraterritoriality”。正是因为这样,在英文文献之中,还没有一个与汉语法权完全对应的单词,来与它进行语言转换。
法权在中国被赋予了权力的内涵后,法权的英文翻译便开始出现了分化,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争议。例如,郭富青将其译为“Legal Power and Right”,童之伟就直接用汉语拼音音译为“Faquan”,黄建武译为“legal force”,“force”的英文原义就有力量和暴力的成分,而“power”的英文含义就包括权力,说明作者已经将权力和法权进行了关联。
可见,由于法权概念在中国的特殊起源原因,其是一个在用法上较为混乱的概念。是一个既不完全相同于权力,更不完全等同于权利的概念。
三、从法权概念到法权逻辑:中国法权概念研究前瞻
随着理论研究的进行,有学者开始从权力和权利统一的角度来界定法权。如果仅仅是单向度地对法权进行定义,而不从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和辩证关系中理解法权,则无法建立一种法权逻辑。从权力和权利统一的角度来开展法权的研究,于是法权概念在中国逐渐出现了演化,开始了一种法权逻辑的思维。法权逻辑是指对法权关系进行重新安排的一种思维、理念,并循着这种思维和理念,对中国的法理论、法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厘定和建构的过程。
首先提倡“法权整体说”的是童之伟,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并一定程度上占据通说地位的“权利本位说”①“权利本位说”以当时任教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张文显教授、郑成良教授的解释最具有原创性和代表性。进行了批判。在2000年的时候,即开始了以法权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构想,提出法权是法定权利和法定权力两者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者中之任何一种。这一观点使其同此前出现过的,仅作为法定权利简称的法权有明显的区别。2001年,童之伟在回答刘旺洪教授提问的时候,提出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所谓法权中心就是权利与权力的统一体,或权利权力统一体本位。意味着法定整体利益(即人民利益的全部法定部分,是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体,一般简称整体利益)中心,也可以说是整体利益本位。法权中心强调的是全部合法财产中心,即各种主体的财产或各种所有制下的财产的平等保护。2002年,他在对刘旺洪、范忠信两教授的商榷意见作进一步回应时,对法权中心说进行了补充,即法权中心中的权利是公民等社会个体的各种法律权利,范围十分广泛。而法权中心中的权力,包括依宪法、法律应由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掌握和运用的全部权力,主张寻求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可见,童之伟将法权理解为权利与权力的统一体,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阐释法权结构内部的运作规律,秉持的是一种法权整体说。
在童之伟的法权整体说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也开始承认并循着这一思路开展对法权的研究。例如,赵平萍以法权结构论,作为一个权利与权力互动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法权结构的概念和法权结构论的模式构造,所谓法权结构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权利与权力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郭富青也指出法权有两种形态,一是权利,二是权力。前者是私法的基本范畴,后者属于公法的基本范畴。现实中,法权形态的异化,导致权力权利化以及权利权力化,形成了权利与权利功能的二律背反的状况。防止权力与权力异化的途径,是明确权利与权力的边界,建立法权关系的制约机制。林纯青以环境权为视角分析,认为运用法权理论来看环境权的属性,环境权应当是一个复合的法权概念,是环境法律权利与环境法律权力的统一体。
以上关于法权的观点和论说,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法理学的研究范式。从权力和权利的角度,而并非是从传统的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法理学的一种框架性建构,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方法,来对社会关系当中的法现象进行剖析和解释。但是“由于缺乏对‘法本位’的解释,缺乏对……‘权利’、‘权力’、……等基本概念的联系和区别的解释,缺乏对这些判断所依据的理论框架的描述,所以,让人感到这些提法自身缺乏逻辑周延性和相互协调性。可以说,童之伟对‘权利本位说’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对自己提出的‘人民权利本位说’或‘社会权利本位说’的论证却是非常薄弱的”[6]。虽然法权整体说一定程度上对权力和权利,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脉络厘清和框架建构,有助于一种法权逻辑的建立。但仅就二者并无重新解释、不厘清权力和权利的区别与联系的条件下,在实施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是不足以建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的。
综上,以上这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法权问题的理论研究。但在关于法权概念的统一界定、法权内部关系的研究、法权外部关系的阐释,以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性研究视角方面尚存缺憾,缺乏整体性的逻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他们的法权说存在一些不足。
四、余论:法权逻辑的阐释
如上所述,正因为他们的法权说存在不足,便对继续进行法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空间。法权包含了法定权力和法定权利,法权的厘清实际上是要建构一个新的逻辑——法权逻辑。从权力行使主体和权力行使目的的角度而言,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就属性而言,权利一般属于自然人、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如法人、各种社会组织)所有,相对于国家的公权力而言,属于私权利”[7]25~26。私权利可简称为私权。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语境下,法定权力和法定权利必然有了新的解读。对于法权来说,一种新的法权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维度,其一是公权的建设和规范,其二是私权的维护和保障。这两个方面的维度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法权逻辑。
现有的法权关系已经造就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既有逻辑,它成为了当下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对它的重新建构,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主观需要和客观存在的统一。就法权逻辑而言,它是通过对公权和私权之间关系的重新梳理和辩证认识,进而建构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并在理念和制度上对它们重新进行相应地安排,以期实现社会的和谐。当前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之间关系的倾倒或不平衡——法权失衡。而“当下社会语境中的权利供需矛盾——法权失衡——而这将或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8]。因此,法权逻辑的重新确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较大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权利的本质、起源、属性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进行抽象和解读,从而将权力和权利抽象为一个整体性的法权(公权与私权),是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科学发展观思维之下的法权逻辑(公权与私权的平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整体理论的一个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研究的拓展,也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范式。
[1]杨湘钧.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高远戎.“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J].中共党史研究,2006,(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5]陈忠诚,邵爱红.“法权”还是“权利”之争——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5)[J].法学,1999,(6).
[6]张恒山.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7]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8]段凡,李媛.基本权利:科学发展观的法学核心价值——兼论“科学发展观”应该载入宪法[J].前沿,2009,(7).
D920.0
A
1001-4799(2012)03-0070-04
2011-12-02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资助项目:2012 Q 061
段凡(1977-),男,湖北咸宁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