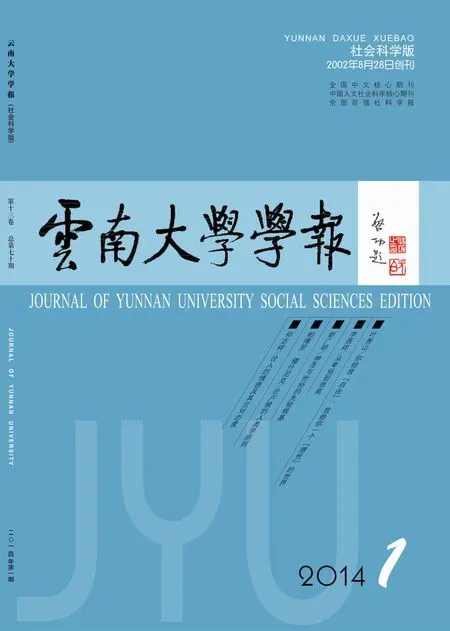论卢梭的人类学原则*
2014-03-06帕博罗穆什尼克文泉译
[美]帕博罗·穆什尼克文, 林 泉译
[1.Emerson College,Boston 02116;2.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92]
心理学起点
(I)躲藏在面具后面即为在枷锁中生存。(II)在枷锁中生存即为背叛一个人最深处的本质。(III)只有已经背叛自我的人才能够背叛他人。(IV)互相背叛和欺骗体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①我用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Victor Gourevitch对卢梭的两卷本的翻译:第一卷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和第二卷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引文首先是着眼于这一版本,其次是借助法文版《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ditions Gallimard, 1964),其中First Discourse和Second Discourse分别用FD和SD表示,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为E,Social Contract为SC,Emile为EM,Lettre à C. de Beaumont为LB。
这四条陈述结合了两种不同层面的解释,传达出卢梭对个人特征的洞见以及对文明的诊断。或许有人会将它们称为心理学的(陈述I-II)和社会学的(陈述III-IV)维度。这些术语是为了指出两种相反的方法论出发点。心理学的维度是指围绕个人的精神过程来解释社会行为的角度;社会学的维度是指将社会行为看作某种既有的,并据之解释精神过程的角度。因为在“两论”中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因果的,如果不能明确这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也就领会不了卢梭的人类学核心。②“第一论”(FD)的问题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道德的净化”,“第二论”(SD)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否被自然法授权”。
这一关系是存疑的。尽管陈述(III)已将这两种解释层面明确连接起来,但背叛的起因是来自于个人内部还是外部尚不明确。即,它最终能否被简化为内部过程或外部输入。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卢梭的人类学图景是否站得住脚,而他的人类学格言是“人们(men)是坏的,人(man)是好的”。*参见SD (I, 197; III, 202)的注释IV和LB, Oeuvres complètes, IV,935-6.“坏的”和“好的”的意思是由接下来的部分确定的。通过借用“人们”和“人”的区分,我想暗示——与卢梭时代的用法相反——一种无性别区分的语言。我坚持用卢梭的术语,是因为对那些术语的不同提法会使我使用不便。
任何已有的解释都会遭遇内在的困难。如果把社会学维度看得比心理学维度具有优先性,就会陷入这样一个预测谬论,就是人的背叛的起因维度必须不是在自然状态中存在的,而根据卢梭,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是相互孤立的。那么,我们就倾向于要去除自然状态,似乎它只是“生动的卷头插画”,而且会把卢梭的政治哲学从他的人类学假设的有效性中排除出去。*这是沃恩(Vaughan)的观点。参见C. E. Vaughan, Studies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5), pp.28-9.人们在天性上是而且一直是社会性的;对卢梭而言,想象一种非社会的状态是无意义的。
这种解释遇到的麻烦是,它不仅歪曲了卢梭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更要紧的是歪曲了他的精神。将自然状态作为卢梭狂热的想象所虚构的产物,既损坏了它的批判性功能,也破坏了它的规范性功能,即,为当代社会的堕落提供评估标准以及为建构一个健全的政治秩序提供一个范式这两种功能。倘若剥夺了卢梭的人类学的道德基础,也就丧失了其全部观点。人们是社会性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仅仅因为他们变成了如此这般,并且在形成社会性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本质。
然而,另一个相反的选择看起来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如果心理学的维度具有优先性,那么概念上的困难是如何说明从一种和谐的自我关系转为一种分裂的、自我疏离的自我关系,后来的关系反过来又导致与他人关系的扭曲。换言之,必须遭遇坏的起源的悖论。既然卢梭把人定义为在自然上是好的,自然状态也预设了社会关系的缺席,那么,人决不会将自己牵扯到坏的社会关系中,如果他尚未在某种程度上变坏的话,这一点似乎是明确的。弱势(身体的或道德的)不能够解释社会的起源,因为弱势是制度的产物。
坏的起源的悖论越出了任何其他起源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于被发起之物必须以它自身为先决条件和起因。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坏不仅以它自身为先决条件,而且与人在自然上是好的假定原则相矛盾。两个选择都呈现了它们自身。卢梭必须摒弃人自然地好的假定,并收入相反的人类学出发点(即,人自然地坏),或者他一定要保留好的假定的话,就要有所修正。两种方式都是存疑的。第一种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需要卢梭牺牲他的基本信条来换取一致性。第二种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将他置入否认霍布斯人类学假定的同时又接受霍布斯的心理图景的真理的困境中。*参见R. Derathé, Jean-Jacques Rousseau et la science politique de son temps (Paris: Vrin, 1995), pp. 139-40.这意味着在引入人的内在变异的同时,仍保留自然地好作为一个本质特征。请允许我称之为坏的困境,即,在自然状态中预先存在着破坏性的精神结构,这与它假定的和谐相矛盾。这种结构暗示了这样一种反馈机制,一旦被激发,就无可避免地加剧。
总之,针对将背叛的源头是置入人的内部还是置入人们之中这一问题所给出的任何解释都有了令人烦恼的附带效果。如果接受社会学维度,自然状态就成了陈词滥调;如果倾向于心理学层面,人自然地好就会受到质疑。
这里有几条论据来论证心理学维度的优先性。(1)不同于社会学角度将社会看作是既有的,心理学起点要找寻可能性的条件。(2)因为对卢梭而言,社会是欺骗与敌对的场所,所以,对它是如何从优先的心理特质中产生的这一问题的提出,就使得个人为他目前的不幸负全部责任。(3)这种责任的实现使他要修正这样一种情况。另外,(4)正是在文明的系谱学中潜藏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指导方针,就如倒影一样。
也就是说,心理学维度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性支撑了卢梭对文明的批判并且指向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产生的条件。但这一观点的理论必要性尚需受到其解决上文所提出的困难的能力的检验,即,如何理解人的自然孤独和自然地好。因为这两个问题都将自然的概念作为公分母,我首先分析卢梭对这一概念的运用。
作为理想的自然
如果依照字面上理解卢梭关于自然状态和社会关系的二分修辞,就会丧失对导致目前人类的不幸和进一步改善的希望的复杂问题的洞见。如果“人们是坏的,(而)人自然是好的”,那么一旦丧失了原初的好,人们就注定停留在持续堕落的道路上。如果情况如此,卢梭就不会写下《有关波兰政府或科西嘉宪法方案的思考》。尽管文本中提出的政治程序是不可信的,但这不代表它们是不可能的。*我对Shklar的卢梭属于传统乌托邦的观点提出质疑。参见J. Shklar, 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in Rousseau’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第1和第4章。即便《社会契约论》算是如此,但卢梭意在使他以前的作品成为政治理论在具体时空中的应用。
人改善的希望是有的,因为人自然地好是无可消除的,它不会因人一旦社会化就简单消失,但它会被淤堵起来,成为焦虑的源头。希望和焦虑是对人的自然地好的记忆所产生的心理学效果。如果自然人是有关过去的一幅模糊的图画,那么他的形象既不会使我们禁欲,也不会让我们在颤抖中期待。如果存在人的自然,那它必然作为一种理想而被有效保存,即:作为一种异常错综复杂地存在于是中的应当。
让我来陈述一下我所理解的这种理想是怎样的。这种“应当”等同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这种意志不受他人意志的支配或决定。“自然”将人受自我支配的意思界定为满足自我需求。如果这些需求属于人的自然,那么他就能够自我满足,或者说如果其他人的意志尚未成为一个人满足的起因,因而一个人的自我能够不受他人的兴致的影响。*一种相似的图景,参见N. J. H. Dent, Rousseau (Oxford: Blackwell, 1988), pp. 38 and 53. ibid., p. 14 ff.自然的意志未必是唯我论的,对与其他人类的联系无动于衷,而是根据一种明晰的自我关系,能够像与自身发生关系一样,与其他人产生当下的和不被扭曲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不排除社会联结,但它无疑被在竞争社会中存在的习以为常的交换损坏了。
自然包括多种情形,比如原始人在草地上狩猎,文明人纯粹出于怜悯做出的行为,夫妻恩爱或友谊的实例,以及公意作为自我服从实现的政治生活。原始人为了杀死一只鹿的荣耀而竞争,文明人为了获得感激而帮助其他人,以及将公意作为特殊利益的伪装是非自然的。
虽然还有其他例子,但这些就足以使我的观点清晰了。对“自然”和“非自然”的界定并不适用于人类情形的本质属性——孤独、社会或政治生活。毋宁是,自然的准则存在于人的意志与其本身的关系中,它同时也设定了与他者(人类和物质环境)的关系。如果需求的可变因素和满足手段之间是平衡的,那么人的意志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纵使一个人的行为牵连到其他人的意志,这种牵连并不是个人意志的原因,而是其产生的场合。“非自然”是指我忽视自己的意志,需求和满足手段之间的平衡被破坏,而且其他人的意志不仅在补足我的虚弱,还指挥我的意志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场合变成了原因,人的意志也是以他人为中心的。
让我来概述一下这些概念。借助情形,我是指行为的环境;场合指一个人的意志与其他人发生的关系;原因指外部刺激(要么是其他人的欲望,要么是单纯的感觉)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意志指易受内在或外在决定影响的欲望和行为能力。如果在一个场合中,意志能够自由行动,即,表现内在决定,那么,我说它就有行动的根据。在另一方面,原因指行为产生于外部决定的情况。卢梭自己并没有系统地使用这些概念。我要说明的是,必须拟出这些概念,把它们重建成他运用作为理想的自然的必要框架。
一些情形会不利于自然。例如,如果我在社会生活中的福祉依赖我的名誉,我必须将他人的观点融为我行动的原因,在如此行动的时候,我就在遵守情形规则的行为中背叛了我的自我。然而,即使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情形也并不决定我的行动;否则,我就不会为此负责了。作为理想的自然的功效依赖于它是独立于环境的。一些情形是非自然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哪种情形构成充分条件。这一事实抓住了自然的规范权力,不用去考虑行为的情形性如何。虽然自然指的是情形可以鼓励或阻碍的事物,但它超出了单纯的环境。内在感受的语言是情形可以转述,但却始终不能详尽表达的。
既然如此,如果自然在社会环境下是一种有效的理想,那么,将它的逻辑功能和历史的先在合并起来就过于简单了。因此,对产生这一理想的逻辑条件的分析,在理解卢梭的立场的时候就有了方法论上的优先性,因为这些约束条件遍布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系谱论述中。我把这一分析称为结构性的,以此来区分起源性的分析——这一种是卢梭在两论中就提出的。这一区分为解决前文指出的困难扫清了道路。因为坏的难题和人的自然孤独源于将本属于结构的决定应用于历史。
理想的逻辑
在当下语境中,借助逻辑,我指的是对概念的意涵的分析;概念指卢梭人类学思想的主要范畴。当这些意涵在纯粹概念的层面上被检验的时候,即不考虑它们源头的联系,逻辑的任务就是要明确卢梭的假设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网。这里,结构是指单由概念的逻辑呈现出的人类学整体图画。*我头脑中的广义的逻辑,指对概念的意涵的分析是某些类型的人类行为的要素。因为那些行为是概念决定的经验的/历史的关联,逻辑的第二种意义必须在后期被加以论述。
尽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张,但从结构上讲,对自然的规范使用带来了人在本质上是朝向他者开放的这样一幅图画。个人的自我意志的独特性来自于它与他者意志的不同,而且不受他者意志的决定。正是在反对外人的视野下,自我的意志才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自然的理想过去是用一种否定式定义来表达:“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是不受其他人的意志支配和决定的意志”。*卢梭也同样用了否定的方式,在SD的第一部分,他将自然人定义为与文明人相对立。参见I, 157; III, 159-60.这并不是偶然的。他者的意志永远都是呈现的,而且永远都是被压制为我的意志的原因。它可以伴随我的行动成为情形的一部分,但它不能够决定我的行为。场合为行动提供的是根据,而不是原因。*我在这里所提的原因与依据的区别是指,原因消除了一种不同行为的可能性,而依据指明了在行为的场合之中的内在动机。这一动机为另一行为类型留下了空间。我说“行为类型”而不说“行为”,因为在情形之中,一个人的意志所拥有的关系永远不能够被充分说明。即使在某一情形之中的行为看起来很相似,但它们的类型可以不同。这有赖于一个人的意志是外在决定的,还是对内部决定的回应。自然或非自然是根据行为被决定的方式所形成的情形——通过依据或是通过原因。
人虽然本质上朝外部开放,但如果他的行为保持是自然的,这种行为就一定来自内部。意志若要成为自然的,就必须逆转人之所造所呈现的秩序。*对“所造”的运用,见SD, Preface, I, 124-5; III, 123.这一概念取代了卢梭的术语“人类构建”,我引入这一新的概念来避免由哲学传统对“构建”一词的运用所产生的混淆。虽然他的感觉和意志自发地朝向外界,但如果这种方向对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话,我们一定说它是非自然而不是自然。因此,可以说,在人的情形中存在自然的非自然:其他意志的场合也是感知最初作为行为的原因所呈现的,它将行为归到环境中。
人之所造与内在决定之间的紧张关系,解释了为何在卢梭那里自我认识是最必要的,尽管也是最困难的。
由自然所提供的器官注定专为我们的保存之用,我们仅利用它们接受外来印象,我们仅设法向外部表达,生存在我们自身之外;过分忙于增加我们的感觉的功能和扩展我们生存的外部领域,我们难得利用将我们拉回到我们的真实维度并将不属于它的万物与我们分离开来的内部感觉。但如果我们希望认识自我,就必须利用这种感觉;唯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够评判自身。*引自Buffon的Histoire Naturelle,卢梭在前言中借助这一点来解释获得自我认识的困难。参见SD, 注释II; I, 189-90; III, 195-6.
在自然的非自然之中存在的张力的根源,是由卢梭的省略造成的,他用自然这一个概念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是描述性的,指出了人的感觉的外部倾向和意志的自发的方向;另一种是规定性的,指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的理想。两者都是“自然的”,但一个要陈述事物是怎样的,而另一个要说明若要认识一个人自己的基本特征的话,事物必须如何。为了避免误解,请允许我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指称它们:人之所造和人之自然。前者涉及描述性的一面,抓住了人的那些可变的特征。后者指我所说的作为理想的自然,即,规范标准以及可以照它衡量变化的永久视野。人之自然代表人的本质,因为它是人身上最大的价值;人之所造代表外观,因为它是附属于人的。*在卢梭的人类学模型中,本质和外观的概念意在抓住人之自然和人之所造的共时规范关系。这一关系并不限定一种目的论关系。相反,如果外观被历时地来看待,它就更是反目的的。因为人之所造的方向的历史流行性意味着对作为理想的自然的颠覆。正是这种反目的使得卢梭能够使用人之自然作为文明病理学的诊断标准。
即使在卢梭的起源论述中,人之自然的概念也被赋予了逻辑的、本体论的、伦理的和历史的优先性。根据结构的观点,它不是自发的概念,而毋宁是取决于人之所造的概念。两个概念互有逻辑,一旦假定一个,也就理所当然地引入了另一个。
不可否认的是,“第一论”和“第二论”的论证都假定了一个历史模型,而且卢梭是从起源的角度构思了这样的模型。但是,它的发展是在由结构决定的,属于纯粹的概念逻辑。若要从历史中找寻这样的规则,就会发现一种“情况的偶然串联”(SD, I, 139; III, 140)。然而,如果分析逻辑上的决定关系,就会看到事物不可能曾是其他样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卢梭呈现了自我转变的一种人类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下,人之自然的逻辑必然会被人之所造的逻辑所取代。
让我来描述概念的演变是如何使人与自己的本质相矛盾的。一个人自己的意志与其他人结合起来构成行为场合,因为人所具有的根本开放性迫使他去解释环境,个人的意志必定会逐渐改变它的自我特性。他对其他人意志的构建,消极地转变成他自己意志的部分决定因素,而其他人意志的本质虽然显露出来却不是在他们的行动中被阐明的。由于排斥他们的意志力,他按照否定的方式将它们合并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必须抑制它们作为行为的原因。人在不自觉中构建其他人在他眼中的身份的方式,还原了他在其他人眼中的身份的定义。其他意志的场合逐渐扩散到自我意志的指令中,而且过了某一点后,就成为自我行为的原因。自此,人的意志就成了与他相异的,他的自我也变成自我疏离的。*参见Dent, op. cit., p. 22.
就卢梭呈现了自我转变的人类学模型而言,自我疏离的过程必定会涉及时间。在这方面,对不平等起源和道德堕落的历史描述是一种方法论的需求。然而,在卢梭的自然概念隐藏了人之所造和人之自然的概念性的对立情况下,历史发展的法则也固有了在结构上的优先性。
考查“第二论”的布局就会发现它联结了起源和结构两方面。前言抱怨了关于自我认识的困难,第二部分通过痛惜人在文明社会中的状况做了总结。通过抱怨和痛惜就认识了按照损害个人幸福的方式构建所带来的不幸。我们之所造“仅仅设法向外延伸”,我们的自然仅仅从内在寻找满足。对遮蔽和扭曲了通向个人的自我因素的描述与卢梭比较文明的和野蛮的所做描述所用术语完全一致:第一种生活在自身之外(hors de lui),第二个生存在自身之内(en lui-même)(SD, I, 187; III, 193)。
不平等的历史就是原则逆转的历史,即由于人之所造的方向颠覆了人之自然的目的,它也是对导致人生活在自身之外的过程的叙述。“第二论”中的文本循环的特殊形式表达了逻辑对其内容的决定意义。野蛮人和布尔乔亚经过几个世纪被区分开来,这些世纪使得人种变老而且似乎使人永远保持孩童状态(SD,157;160)。这两种人是结构分层的历史化身,这种结构分层既不存在于历史之中,也不在历史之外,却构成了历史的可能性的条件。
坏的难题源于卢梭将作为理想的自然置于一种绝对起始的地位,它是在人类头脑中同时原初呈现出的一种与人的自然地好的原则相矛盾的破坏性结构,原初地同时成为规范性准则和历史事件。也就是说,人之自然的概念在结构上依赖于人之所造,也体现所有进步都是一种背离的起点。暂时展开的逻辑关系就好像按顺序一样取代了自然这一概念中包含的先天结合在一起的矛盾意义。起源的程序使我们带着希望找寻——从结构上来说——隐藏起来的运动之源。
我承认:自然人不能够将自己牵扯进入坏的社会关系中,如果不是已经坏了的话。但如果我们不是在演变过程中,而是在何以使它在可能的事物中寻找坏的起源,这种悖论就消失了。即,具有对立需求的人类学模型,这些需求体现了具有同等结构地位的方向。结果,坏就是它自己的起因和先决条件,因为它完成了与人之自然共同出现的另一个原初方面:人之所造。
“自然的”与“非自然的”社会性
关于人的自然孤独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在针对社会学维度是否能够接纳方法论的逻辑优先性的讨论中,我们被引向了为了解释社会影响——人的内在背叛——的可能必须假定社会存在的恶性循环。因为如果“人是好的,而社会腐化了他”(LB, IV, 935-6),并且“只有已经背叛自我的人才能够背叛他人”(陈述III),那么,这种背叛的源头一定是来自社会秩序。但不能声称这种秩序存在于自然状态中,因为自然状态中的人被说成是相互孤立地生活。*这种困难类似于在通过契约形成的政治秩序周围出现的困难。正如沃恩(Vaughan)所推论的,将契约作为政治义务起源的基础,就是将一种需用政治义务来使之有效的机制作为基础。一条契约即是一种不可能在政府设立的秩序之外构成的交易;因此,不能用它来解释那种没有这一制度社会契约就不存在的制度(参见C. E. Vaugh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Contrac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iv)。换言之,政治制度的问题形式类似于坏的源头的问题。两者都有同样的概念困难:某种现象可能的条件(社会的存在和为了构建政治秩序而遵守承诺)为了想要解释的东西(人的自我背叛和契约的有效性)发生作用。我的观点是,卢梭从在他的人类学模型中的心理学预设中存在的困难中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在这里我还无法充分证明。人之自然解释了前政治义务的起源,而它与人之所造之间的关系解释了自然孤独的意义,并为构建从文明到一种良好秩序的社会通途提供了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接受(1)自然之物是在社会背景下的一种理想运作,以及(2)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定义不排除他人的存在,那么,对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二分法就明显不与社会的和反社会的之间的差异相重叠了。第一个命题可作为对个人在文明中遭遇的心理不幸的解释,第二个则是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的理想的暗示。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关于人的自然孤独的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他人的意志是作为自我认同的否定视野,和我的意志被共同假设的。但从起源的角度来看,卢梭能够将结论(社会)界定为人的内在背叛的原因。因为他没有打算要原本地解释社会纽带的起因,而只是要解释导致人的不幸的根本纽带的起因。既然有关社会的起因的推理只有在社会纽带之内才得以发生,卢梭的洞见包含了这样的意识,人的概念也使得社会的概念成为必然,而且当代社会完全与人的概念相矛盾。如果人们现在将自身分裂了,而人自身依然有幸福的潜能,那么由他所遭遇的悲惨而构成的系谱即是对人如何偶然破坏了自己的本质的叙述。
我认为,这种系谱之所以可能,在于卢梭假定的人的“自然”的概念与自身相矛盾。因此,如果把人的孤独作为一种绝对起点的话,那它必定可被视为对人之自然必然拥有的心理学框架的隐喻。卢梭的个人此时此刻的幸福的概念投射到遥远的过去。*参见EM, Bk II, p. 81 ff。关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主义角度,参见J. Staro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Transparency and Obstruc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hap. 3, p. 33 ff.将方法论的优先性给予社会维度的错误并不在于对人类社会性的预设(对此,卢梭是不会争论的),但却在于忽视了由这个隐喻所传达的真理:我们当下的社会性是非自然的,它使我们必然不幸。孤独绝不作为一种历史真实而存在,它总是作为一种道德的必要条件。
我似乎自相矛盾了。因为如果在结构上解决人的自然的问题(即将人之自然与人之所造的对立决定合并起来)被当作系谱发展的内部法则引入,道德的责任就消失了。人目前的自我疏离也会是先验条件在概念中运作的结果。历史只能认可逻辑先行到达的命题。
这一推理的宿命论的语调是卢梭对引发两论的问题的理解的结果,这些问题似乎是因果性的,尽管想把它们看成是历史性的。他通过认识不平等的事实和霍布斯的真实开始探究问题,提出了能够解释这一形势如何形成的基本概念。对他的概念的意义在理论上的抽象分析与起源解释获得了相同结论,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这种调和不应被称为宿命论,而毋宁是一致性。事实是:卢梭成功回答了第戎学院所提问题与他自己的道德意图相冲突。按因果关系解释某物,即使它看起来是非自然的,亦会将我们对它的存在的必然性的理解调和起来。理性和感受在这里有不同的要求,能相信的却不具有说服力。*关于卢梭对“令人相信的”和“具有说服力的”的区分,参见Letter of J.J. Rousseau to M. de Voltaire, I, 235 ff.; IV, 1062 ff.
我认为,在卢梭的自我转变的人类学模型中所蕴含的延迟概念提供了介于理论上的一致性和道德上的批判性之间的折中立场。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许可了逻辑条件和人对目前的不幸所担负的责任之间的游戏。人之自然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反社会的,但却包含了社会性的延迟,恰恰是因为它与人之所造有概念上的关联。自然的和社会的交叉起来,因而后者的实际效应依赖于前者的演变。这一演变带来了人之自然的终结,与自身相矛盾。卢梭把人之自然作为历史开端的逻辑必然。人表现的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对自己不幸负有责任的代理人,而这一不幸在结构的矛盾中表现的却是隐而不露的。正是必然的模棱两可性和延迟的效应使得卢梭能够将社会性作为一种道德的真实,排除了历史的真实。
对理想运用的方法论问题
对自然的概念的逻辑分析为解释坏的难题和人的自然孤独提供了一种解释方式。然而,这些成果似乎弄巧成拙,因为它们排除了卢梭的人类学最显著的特征,即,对历史的使用,对将时间作为先决条件的过程所涉及现象的解释。
我有什么权利采取一种与卢梭在两论中的叙述策略相矛盾的姿态?倘若它们的新颖之处在于系谱性,那我就夺去了卢梭最喜爱的武器。如德拉泰(Derathé)所论述的,所有其他的自然法理论家都犯了同样的方法论错误:他们忽视了可完善性的概念以及社会生活对人的自然所能带来的深刻变革。*Derathé, op. cit., p. 132.那么,我也可以被指责为向卢梭强加了其他哲学家对人所强加的同样错误。
我只找到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回应这一指责。我所呈现的结构定位正是卢梭自己为回答不平等的起源和道德堕落的问题所被迫采用的。将“自然的”作为一种诊断仪器使他别无选择。因为卢梭将关于人的知识与关于不平等的源头的知识联系起来,但获得前者的可能性与后者的发展成反比(SD, I, 124; III, 122)。文明的进程破坏了人的自我关系,以至于无法认识其原初状况。如果不能立刻认识到这点,对“自然的”研究就不单纯是一场“获得精确概念之必需的”(SD, I, 135; III, 123)难解的梦,而是一种绝对的幻觉。一个人的自我必须能够同时被置于自我背叛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处。系谱学的叙述策略是后来出现的,它是使读者拒斥这一过程的最有效的修辞工具。
这种起源方法通过加入常新的决定合成式地发展,以片刻的分析为先决条件。*参见卢梭的早期作品(1745), Idea of the Method in the Composition of a Book, I, 301; II, 1244.只有夺去从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他自己的/普遍的自我,卢梭才能到达假设的起源。然而,这种起源方法的前进过程在进行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使它得以可能的回归的或分析的时刻。
让我来重新表述方法论的问题。卢梭貌似有理的系谱学源自于潜在的概念框架,具有分析特征,这是我在结构方法中提出的。但这一框架的存在依然处于假定的层次上:它必须在卢梭在起源论述所做的说明的基础上重建。理想的逻辑是对所做说明的陈述。而这一陈述表明必须有一过渡元素——更深的逻辑感,由此,概念的条件才能在卢梭告诉我们的故事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机制,用以将暗含的一套逻辑关系转换成卢梭描述不平等和道德堕落所用的语言。机制是指广义的逻辑,借助机制,对结构的纯粹概念上的决定构成了人类行动的类型,即,卢梭将之描述为历史现象的行为类型。
我认为,能调解历史和结构的不同需求的最好方式是在广义的逻辑意义上构造一种准先验的(quasitranscendental)方式。*我对“先验的”使用,参见I.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 57/B81 (trans. N. Kemp Smi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5).卢梭观察到不平等的事实,追问其可能性的条件。这一过程可被界定为先验的,因为它涉及的通常不是一种事实的不平等,而是带有演绎性的人类学条件。但它又不是完全先验的,因为它不是停留在这些条件之内,而是将它们呈现为一种归纳性的历史决定论,这就为我们遭遇他第一部分作品带来了困难。如果“自然的”在卢梭的起源论述中依然是作为一种理想运作,那这种准先验的特征就是必然的。当转为历史的时候,它呈现的就是结构的形式:这正是卢梭的道德人类学必须采用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因此,让我们先撇开所有事实不谈(卢梭这里提到的是基督教的人和世界的起源,也是哲学界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因为它们对问题不会有影响。对这一主题的追溯探究,不应被当成历史的真实,而应只是假设的和条件性的推理;与其展示真正的起源,不如说明事物的自然。(SD, I, 132;III,132-3)
简言之,对自然的陈述丢弃了历史的真实,获得了理论上的必然性。卢梭思想的先验性方面与我称之为结构的路径相重叠。这是在狭义的逻辑下进行的分析。它非先验的部分与卢梭的系谱学的策略相一致,把逻辑条件表现得好像是先验的和归纳的。广义的逻辑阐释了逻辑框架如何构成卢梭在起源论述中描述的行为类型。卢梭的道德控诉要能够站得住脚,必须具备这种可转化性。下面我会说明理论的一致性和道德的义务性需求是如何在广义的逻辑基础上共存的。*尽管通常这种声称适用于卢梭的人类学作品,但本文仅挑出第二论,因为我发现其中包含了卢梭对准先验过程的最系统的论述。
我 感
在起源论述中,人的自然状态是通过理智地去除理性和历史向推测出的原始人类结构所增加的全部东西而实现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去除所有的社会印记并不是要显露一块等待外部输入的简单白板,而毋宁是需要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所有的潜能都既依赖外部环境,也根据内在能力被认识。因为潜能之一恰恰是人的责任,卢梭调节白板,使因果决定的欲望和感知不会介入人的责任能力的特殊领域。作为有感知的生物,为外界所引导,人是外界刺激的玩物和环境的被动接受者。人外向的一面是我先前界定的人之所造。如果这些都是合其自然的,人就不会对自身的行为负道德责任了。真正的人类会在自我决定中,在被我称为人之自然的内向的一面中找到表达。
因此,自然人是一块白板,在那里人之所造和人之自然拥有同样原初决定的意义。问题是卢梭须将何种潜能置于首要地位。因为最初的一步会决定他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方向。如果他选择人之所造的方向,作为理想的自然就会丧失诊断力量,因为人作为外部世界的玩物与卢梭的生活“在自身之外”的布尔乔亚的概念相一致。文化操作会继续操纵自然界。因为这条路径非常苍白,所以系谱学不得不将人之自然的结构决定放在一种绝对历史开端的位置。
因此,让我们抛开那些只教会我们从人们使自己已变成的那个样子去看人的所有科学书籍,反思人类灵魂的最初和最简单的运作,我认为我在其中察觉到先于理性的两个原则,其中一个使我们对幸福和自我保存非常感兴趣,另一个激发我们对看到任何有感觉的存在,尤其是与我们自身相似的存在遭遇痛苦或毁灭产生天然的厌恶。我们的心智使这两者协调起来。在我看来,所有自然权利都是源于它们,没有必要再加入社会性。后来,理性在持续的发展中到达了窒息自然的程度,理性就被迫将这些原则在其他基础上重建。
与理性相关的原则在逻辑和道德上具有优先性。逻辑上是因为它们表达了心智的最简单的运作——它们为后来更复杂的运作提供了标准。道德上是因为在纯粹的当下感觉中确立了与自己的需求(幸福)或其他生物的需求(怜悯)相关的总体。在怜悯的情况中,其他人的痛苦是自己关心的依据,因为自己的感觉与其他人的感觉相一致。这种认同是当下的。意识到人之所造会使人之自然更容易被接受。
或许有人反对这种阅读,认为这种意识太具有反思性和理性,在这一阶段不可能出现。对此,我可做四条回答。第一,卢梭的这些先理性的“心智运作”对动物和人而言都是常见的(因为两者都有感觉),它们也只是表现知觉(SD, I, 140-1;III,141-2)。第二,因为人之自然与人之所造决定的方向相反,而且两者在白板上都拥有同等的潜能,一旦卢梭将人之自然作为系谱的先行,他就有资格来把玩两者的对比差异。第三,这一阶段预设的自我意识是反思性的,不是概念性的,而毋宁是对自己的感受的意识,是可以表述为“我知道我有感受”的自我意识的初级形式。最后,正如我思是笛卡尔形而上学建立的原则,我感也是卢梭道德的基石。最基本的直觉似乎是“我感,故我在”。卢梭的直觉产生的结果和笛卡尔的明显不同。笛卡尔的思的怀疑过程使世界倾塌,自我被关在思考的物质的牢笼中,而卢梭的感的感受过程则促进了自我和世界的当下连接。物质的二元论问题就避免了,因为自我被植入了自己的自然中,而不是像笛卡尔那样,自然是自我的他者,纯粹的非思考之物。另外,在卢梭的道德中,我感一定要伴随人的所有行为,但不意味着所有的行为都表达我感,而是最终能归于我感。只有伴随人之自然发生的行为才能充分表达自我的知觉。所有可能的行为都可涉及我感的事实指明了人的责任和与之相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因此,尽管卢梭认为自我保存和怜悯是“灵魂的最简单的运作”,我感的直觉依然是更基本的,因为它使那些运作得以可能。在起源论述中,我感所表达的是人之自然和人之所造在结构上的逻辑关系。这是那些概念的逻辑的准先验的转化。
我不是声称卢梭清晰地论证了观点二和四,而是说对他的思考而言,它们必须表现为接受了本身含有的形式。纵使我们必须认识到卢梭的先理性原则(尤为明显的是在怜悯当中)中的反思,这也不意味着那些原则是理性的,这种反思毋宁是植根于道德感受所表现的更高级的知觉形式。承认这种反思并不破坏我的论证,相反,它带来了另外的证据。它证明了如果卢梭的起源策略是可能的,结构框架就一定是首要的运作背景。
静态和动态原则
我感是人之自然和人之所造同时呈现的一种起源转化,它是在自我保存和怜悯的基础上所发现的一种基本假设。前者不仅指个人的身体耐力,还指个人的幸福。它不只是活下去的生理驱动,而且是为了活得更好。卢梭在这里没有分析“好”的意义,但它无疑可与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联系起来。这种理想即是,自我不是一堆相互冲突的激情,而是一种和谐的欲望体系,欲望的满足反过来会容许与他人的一种节制的关系。因为个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他人并不是满足的理由。自我保存可以确立与自我相关的总体,自我通过怜悯可以扩展为更大的感受总体。为此,对同类的感知比假定的理性更重要。感受到同情不是因为他人是一个拥有权利的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感受的存在。不伤害他意味着认识到我们有外在导向的生物的共同身份。*参见EM, Bk IV, p. 221. 一个人会在而且只有在将他人的弱点反射为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才会产生同情。他人的理论和幸福会变成感受同情的阻碍。
这就是说,卢梭最初的原则同时在个人的水平(幸福)和与他人关系的水平(怜悯)上概括了关系的理想类型。如果这些原则是人的唯一的精神动机,激情就会永远僵滞,道德不平等的可能性就会在它发出第一声哭喊之前被去除。
我设想了人类的两种不平等:其一,我称之为自然的或身体的,因为这是由自然确立的,包括年龄、健康、身体力量和心智或灵魂的质量的差别。另一个或许可称之为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因为它依赖一种习俗,是由人们的同意确立的或至少是许可的。它包括不同的特权,一些人享有对其他人的损害,如更富有、更荣耀或更有权力,甚至是让另一些人服从他们。(SD,I,138;III,131)
与建立在自然道德基础上的对称纽带相反,道德不平等的固有声明是有更多,它以人与人之间敌意的比较为基础。对某些品质(如财富和权力)的断言会否认另一主体的这类品质。一个人的享受导致了另一个人的不幸。道德不平等是作为第二种不平等运作的:(1)一个客观的区别被重申为(2)内在主体的不对称性。也就是,一种客观的优越同样确立了道德的从属性。*正是这种联合使得所有权的概念才易于表述道德不平等。“我的和你的”的理念有一个客观基础来传达主体之间的关系——道德关系。相反,身体的不平等依然处在第一种不平等的范围之内,因为客观的差别不会转化为道德上的。这就容许了将其他个人加为自己行为的依据。即使这预设了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某种不平等,但不会消除对同为有感觉的生物的共同身份的意识。
自然道德运作的格言可以这样表述:“在得到你的好处时,尽可能少地伤害他人”(SD,I,154;III,156)。怜悯不能要求损害个人的幸福而帮助他人,而毋宁是建议在帮助行为中认可个人在情形中的力量来增强幸福。以自我为中心不是无私的,而是将他人整合为行为的依据。相反,道德不平等的格言可以这样表达:“如果对你有好处,就伤害他人。”这不是命令去伤害他人,而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伤害、欺骗、屈服,或形势所可能产生的其他方式。这样就构成了互不信任的前提假定。即使一个人实际上不会伤害其他人,但如果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他就会这么做。信任表示的假定是,如果不会对施与者造成伤害就会援助;而不信任的假定是,如果有好处就会滥伤。
卢梭拒斥两种不平等之间有任何因果联系。否则,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就可以声称比服从的人更明智或强壮了(SD,I,132;III,131-2),因果关系会使社会不公以自然差异为基础变得合法化,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习俗的维度和导致道德不平等的主体的内在转变。尽管不平等乍一看是以“有权力的人的暴力和对弱者的压迫”为基础的,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具有欺骗性的。“再也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更不稳固了;这些关系被称为弱或强,富有或贫困,它们通常是偶然而不是智慧的结果”(SD,I,128;III,127)。社会的建构依赖于一种更不可动摇的基础——人的意识的彻底转变。
这种转变究竟何以可能?怜悯和自我保存的对称关系如何变成了道德不平等的不对称纽带?人的自然功能中的什么元素许可自我疏离?
卢梭引入两种附加的心理学原则回答这些问题:自由和可完善性。它们解释了人的自然的不稳定性。我把这些原则称为动态的,以此区分静态的关联——怜悯和自我保存,它们倾向于保持自我和他人之间的适当平衡关系。对这些静态原则的保持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本能的。本能属于生物学范畴,但静态原则具有道德意涵。它们表达的是人之自然中永久的规范核心。另一方面,动态原则揭示的是人如何偏离了这一核心,他如何在自身之外,总而言之,人之所造的方向如何颠覆了人之自然。它们可以被描述为自然的功能跳入非自然的动力。虽然动态原则可以导致人类的膨胀或贫困,但从结构意义上讲,它们被迫打破了道德范式的平衡,消除了人的当下幸福。
自由指出了这一事实:即使自然沉默,人的意志也会继续发声。“自然命令每种动物、野兽服从。人经历了同样的印记,但却认识到他自己可以自由地默许或反抗”(SD,I,141;III,141-2)。
倘如卢梭似乎建议的自然只是在因果决定的感觉范围内,那么论证的一致性就瓦解了。因为一种感受的道德平等,如怜悯,恰恰依赖于情形不决定行为的事实。如果行为是受外在决定的,内在的道德价值就会消失。因此,如果卢梭的论证依然一致的话,他一定会从自然的概念中发现表里不一的特征:(1)自然必须指定一套可以最终转为机械法则的固定的回应(感觉);(2)自然必须指定内在的感受(即人之自然)。自由被设想为同时否定这两种意义的能力。
卢梭引入自由的原则是为了使人对否定自然负责。因为自然的概念模棱两可,否定在逻辑上就传播了双重意义。人可以否决他的人之自然,背叛他的道德核心,设法满足外界(自我疏离);或者,人也可以否定感觉(人之所造的外部指引),依然忠实于道德核心,设法满足内部(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后者是静态原则得以可能所暗含的条件,自由作为动态原则在逻辑上注定要带来第一种否决,即自我背叛。否则,道德不平等的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人之自然的规范能力在于为场合假定了不可逆的条件,即,为行为提供了依据而非原因。因此,虽然自由在起源论述中被确定为不道德的,因为它成了否决人之自然的原则,但从结构的观点看,它又呈现为本来无辜的,否则静态原则本身就会缺乏道德意义。
第二种动态原则——可完善性——补充论述了人使自然沉默的能力。就像自由是自我背叛的能力,专门用来逆转自我保存的静态原则,可完善性成了塑造世界的力量,专门逆转怜悯的能力,建立更大的感受总体。可完善性是“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环境的帮助下,继而会发展其他人;它存在于我们当中,既在个人内,也在人类中”(SD,I,141;III,142)。
当遭遇到障碍,人在克服困难的时候感受到自己的优势。他进行反思,并整理这些克服困难的方式去做事,从而就使用了工具理性。理性消除了与环境最初的当下关系。人面对事物时的优势很快就会表现为社会关系。支配自然逆转为支配人们。万物都成为可利用的手段。想象被刺激,全部的激情被唤醒,人被迫走得过远,向外伸展。他不再可以在同一情形中逗留,他必须超越。不稳定性成为生活的原则。
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在进入动态原则的漩涡之前,请让我短暂地停留在它们爆发之前的时刻。人的自然状况可以被想象为与他自己的自我相关的确定性,因为工具理性尚未破坏欲望和满足手段之间的当下关系,他所能企及的还只是原始的欲望。他的激情遵守自我保存赋予的极限,会把欲望带到不可预料的方向的知识要受那些激情的简单性的检验。
唯独除了身体需求——这是自然本身的需求,所有其他的需求都是由习惯或我们的欲望造成的。在拥有习惯之前,这些需求都不存在,人也不会欲求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由此,既然野蛮人只欲求他知道的东西,只知道他的能力所能及的或容易获得的东西,没有什么会比他的灵魂更平静,没有什么比他的心智更受限制。(Note XI,SD,I,212;III,214)
人为需求并不比自然需求的需求程度更小。当前者无休止地被理性和社会虚浮交错在一起产生的时候,后者就被限制在身体需求的有限集合中,满足依赖个人内部的力量(饥饿、性欲等)。人为需求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身体需求是自我参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主体根据实际需求来构想它们,欲望的客体也在当下回应那些需求。
自我保存和怜悯的静态原则提供了一种自我关系以及在自然需求的框架内运作的与他人关系的道德范式。这一范式并不与社会纽带相对立,相反,它为以和谐的自我关系为基础的内在主体性关系提供了理想。需求是自然的,因为它们属于趋向人的幸福的系统。“孤独”是卢梭表达其他意志作为个人自我满足的依据而在场的隐喻,即,将它们从原因中排除。
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思并不是——像霍布斯意义上的——一种主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对抗与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并不相容。只有恐惧和虚弱才使人变得残酷,而且这两种激情都不可能具有支配性,因为它们源自普遍依赖,即,与自给自足状态相反的状态(SD,I,151;III,154)。自然力量和通常的依赖性互相排斥,虚弱和不安是“使自己屈从普遍依赖,接受那些没有义务给予他们的人的所给的一切(SD,I,151;III,153)”人的必然结果。借助自由和可完善性,人设法支配一切,成为所有人和物的奴隶。他的奴役性实现了以他人为中心的心理学框架。
社会中的自我和他人
在论证之前,我先纵观前文所述。我感的反身性转化成起源论述,而自然概念框架内的结构张力,静态和动态原则表现出人之自然和人之所造的方向并解释了逆转是如何可能的。它们将演绎的(结构的)限定在经验的(心理的)决定之内。人的结构变化因而就表现为一种矛盾的心理驱动形式。静态原则表现的是卢梭的道德理想,动态原则则是解释理想转移的系谱工具。结构因而就经历了变动,并揭示了内部的决定,好像它是一个历史问题一样。
卢梭的人们在文明社会情形中的图景以普遍依赖和侵犯为特征,这需要根据暗含的结构不和来理解,即:以动态原则的逻辑取代静态原则的逻辑。这里的逻辑是广义上的,即带有推理性的人类学条件并由之构造的行为类型。
可完善性和自由实现了人无视对静态原则的规范需求的固有可能性,开启了通向被卢梭归为文明人行为的角度。可完善性超越了怜悯,导致工具理性的发展。支配自然和消除个人确立感受总体相继发生,作为不幸的无休止的锁链。这些不幸的共同特征是暴力和侵犯。可完善性阻碍人将他人作为有感觉的存在,并把他们作为与自己对抗的主体相区分,即,可任意处置的客体。另一方面,自由压制了自我保存,打破了需求和满足手段之间的平衡,并否定了人之自然的决定作用。自由带来了自我背叛,并导致普遍依赖(以他人为中心)。我感依然运作,但却是以一种被剥夺的形式进行,也就是作为一种对自身麻木的关系,由此产生对他人的敌对关系,但同时又以感知为可能条件。
为丰富对自我疏离过程的描述,卢梭引入了两个概念:自爱(amour de soi)和自负(amour propre),前者被视为植入静态原则中的道德,后者认可受动态原则影响产生的扭曲。
自负和自爱在性质和效果上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激情,决不能将它们混淆。自爱是自然的情感,它使每种动物进行自我保存,在人身上受理性的引导,并受怜悯的修正,产生了人道和美德。自负只是一种相对的情感,是人为的,在社会中产生,使每一个人比其他人储备更多,用人们对彼此做的坏激发人,也是荣誉的真正起源。(SD,I,218;III,219)
自爱将自我保存和怜悯融为一个原则,将卢梭道德理想的核心——幸福体现在个体上,将美德体现在社会交往中。因而,它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和人之自然的需求。自负是将霍布斯的精神框架界定在当代社会中的一种激情,它是动态原则的逻辑缩影,构成了以他人为中心的心理学方向,因此,表现了人之所造的需求。它的特征是宣称自己对其他人的令人厌恶的优越性。这一声称以比较为基础,以至于在排除了平等分享的时候,较多就使较少成为必然。自负意味着支配的意志和对他人的从属关系。它之所以被称为“不自然的”,不是因为它与人之自然的某些特征不一致(即人之所造),而是因为它暗中反抗人自然的或真正好的东西。
这表明卢梭遭遇了两种好:一种是真正的好,另一种是表面的好。为了使比较得以可能,它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依据衡量假定的真实(不真实)。我认为,这一规范存在于人建立总体的能力,最初靠自己和其他人,后来又衍生到环境。
自然人能得到“好处”,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他“将自己视为自己的唯一观察者,宇宙中唯一对他感兴趣的人,也是唯一评价自己的人”(SD,I,218;III,219)。他可以被其他人伤害,但绝不会被冒犯,因为冒犯就意味着一种他没有的意向性解释。自然的激情是唯一评价其他人行为的法官,它们不能给出一种标准来解释那些行为是傲慢的还是顺从的,因为他的前提假设是“一个人在尽可能少地伤害他人的条件下获得好处”。他是自己唯一的符号范式,因为他内在是好的,外在也没有什么坏的。
另一方面,文明人也追求他们的“好处”,但他们的整一概念被所有权概念——也就是独占的模式——扭曲了。不是个人属于整体的一部分,而是个人想要整体属于他自己;不是培养内在,个人有外在激情和获得表面的好处的贪得无厌的乐趣。个人疏离了自我存在的中心,将以他人为中心作为自己符号范式的基础。
必须满足第一需求,然后是奢侈;在美食之后,又是巨额财富,然后是主体,而后是奴隶,他没有片刻的安宁;最奇怪的是,需求越不自然,越不紧迫,激情就越大,更糟的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权力也是如此;所以,经过长期发展,在吞掉大量财富,毁坏很多人之后,我的英雄就会以抹断所有的脖子告终,直到世界上只剩他作为宇宙的唯一主人。简言之,如果这不是人类生活的图景,也一定是道德的图画,至少是每个文明人心中的秘密野心。(SD,I,199;III,203)
静态原则的独裁模式在动态原则中依然运作,但是以一种反常的形式。个人意志的确定性不是由在感受总体中与他人联合的能力得到的,而是由在二元冲突过程中其他主体的服从中获得的。自爱意味着将一个人的自我扩大到包括他人的整体中(怜悯),自负意味着两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其中一种肯定是被贬低的。虽然依然在努力构建总体,但一个以排斥另一个的平等道德地位为基础。
这些失败的总体的自我矛盾的要素是反思(比较)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感受总体表达了联合体产生的当下性。因为总体不属于自己,一个人属于总体不排斥其他人也同样享有这种关系。相比之下,考虑到(1)对这一关系的享有权和(2)作为有感觉的存在的地位的双重放弃,以独占模式为基础的总体只能在否定意义上包括其他人。如果感受总体是真正的总体,需求总体就是二元冲突——虚假的总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感受到其他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占有其他人;我联合为一,在其他人那里我成为集合体。
一种共同的心理学类型可以比较真正的好和表面的好,它的重要性有两个原因。(1)解释了为何从起源的角度讲,静态原则“先于理性”。也就是先于可完善性施加的作为情形原则的分离,但并不先于我感的反身。另外,(2)解释了自然如何作为规范准则来衡量文明中的坏。正是由于人构建感受总体的心理学能力,卢梭才能将通过动态原则的逻辑建立的需求总体描述为非自然的。
自负所追求的好处是自我攻击的,理由有三。(1)在比较中所预期的一个人的自我是不能实现的,即使这个人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其他人的自我在一个人宣称自己的优越性的时候就被否决了,变成一种幻影,不能再支撑任何值得拥有的自我形象。其他人的从属性取消了保证一个人自尊的所有可能性。(2)人为的目标(人造需求)不像身体需求,它们是象征性地被创造出来,因而几乎是无限的。无论一个人多富有、多有权或多受钦佩,在个人之外总是还有更多的财富、权力和赞美。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手段之间的不对称将人置入永久的不安和无情无义之中。文明人在身体和心理上消耗殆尽,他们耗尽所有却享受更少。(3)在设法超越其他人的时候,一个人就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了。这种现象有双重意义。(I)人与自己的适当需求分离了,与自己的中心断裂了,被与其他人的观点相关的许多意见去中心化,取代了自己的当下感受。(II)一个人的存在(本质)和外在彼此混淆。在寻求评估的过程中,真正的和假装的品质都任意展示,因为真正紧要的是他人的观点而不是一个人实际所是。被异化的自我将自身作为一种景观呈现出来。*参见Pierre Burgelin, La philosophie de l’existence de J.-J. Rousseau, Libraire Philosophique (Paris: Vrin, 1973), pp. 251-5.
如果说自然人生活在当下感受中,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相似;那么,文明人就生活在算计出来的观察他人的距离中,这伪装了对他们的看法。对他人的当下认识受怜悯的引导,但却被理性工具破坏。与自我分离使得人对感知冷漠。这就放弃了原本的、以感受和对他人的我感的认识为基础的道德关系的依据。理性使人丢掉了与情感的当下联系,反过来促使他信奉错误的价值、错误的好处和错误的满足手段。理性使人在应该朝内看的时候,反而朝外看。
只有人的意识转变才能解释道德不平等的持久性。暴力不会产生权利。“最强的人从不会强到一直是主人,除非他将暴力转成权利,服从转成义务”(SC II,Bk I,Chap.III,p.354)。这就是说,除非他能将身体的力量转成道德的。支撑强制的是过量的、持续的警戒。这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支配方式,这种方式的外在效果与削弱人的自我中心的效力成反比。富人为管理社会发明了一种双重策略:“向人们灌输其他的格言,并给出不同的制度;自然法有多么反对他,这就有多么对他有利。”(SD,I,172-3;III,177)这种策略的效力依赖一种更基础的转变。因为“人们接受自己被压迫,只是因为他们对盲目的野心着了迷……将掌控支配视为比自由更珍贵,并同意被锁链束缚,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将链条反过来加到其他人身上”(SD,I,183;III,188)。只有以他人为中心的个人才能忍受锁链。为了满足自己的支配欲,人不仅背叛了最深处的自然的理想,也破坏了实现那种欲望的根基,因为为了命令其他人,他必须先服从他们。想让有权的人变得有依赖性和虚弱,变得以他人为中心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式。
如我们所知,卢梭将自然人和文明人的差异用一个区分总结,概括所有:“野蛮人生活在自己之内;社会人生活在自己之外,只能靠他人的意见生活,也就是只能从他人的评价中获得自己的情感动力。” (SD,I,187;III,193)这一首要差异是自我背叛的长期历史进程造成的,将我们引回到结构中的演绎张力中,这一张力使得历史得以可能处在首要位置。因为人之自然和人之所造之间的冲突正是在野蛮人和布尔乔亚的原型以及生活在自身之内和自身之外的范式中表现出来。
在现代生活中,“一切都成为人造的和表演的……永远在问别人我们是什么,甚至不敢问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不过是欺骗性的和无聊的外在”(SD,Ⅰ,187;Ⅲ,193)。对这种平庸化的认识是根据许多存在的模式和存在的确定性的模式判断的,通过投射到过去来批评现在。存在和显现的差异需要健全的认识论结构,卢梭在人之自然中发现了这种结构并将之作为一种理想。在文明人强制自己所戴的面具背后,卢梭看到了人的灵魂的不朽特征,并将他们简要地表达为对自己的可能性的提醒。在大海和风暴摧毁的大量石雕下面,卢梭也看见了神的脸。他看见了格劳克斯,神圣而又残忍的野兽,柏拉图将它描述为“灵魂经过无数的恶后所沦为的状态”(见Republic,X,611 d)。
结 论
这篇文章通过展开心理学原则的基础,阐释了卢梭的人类学。自然是在社会背景下的理想运作的观点引导我去分析自然概念的逻辑含义。通过人之自然和人之所造的相反决定性,构建了让我能同时解决坏的困境和解读人的自然孤独的结构机制。但是,完成这些的代价是抛开了卢梭的起源论述。为了避免这一困难,我将卢梭的程序类型设想成准先验的。因此,纯粹的逻辑约束变成了在历史中发展为一套有经验决定作用的行为类型。这些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心理学原则,静态的和动态的,在起源论述中,它们表现出人之自然和人之所造的结构决定作用。卢梭注意自我背叛一步步转变的过程,因为它意味着人之自然的逆转以及强行将以他人为中心作为有支配性的心理学框架。
文章的核心在于总结一种简单模式,以此呈现作为一种基本对立体系的卢梭的人类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