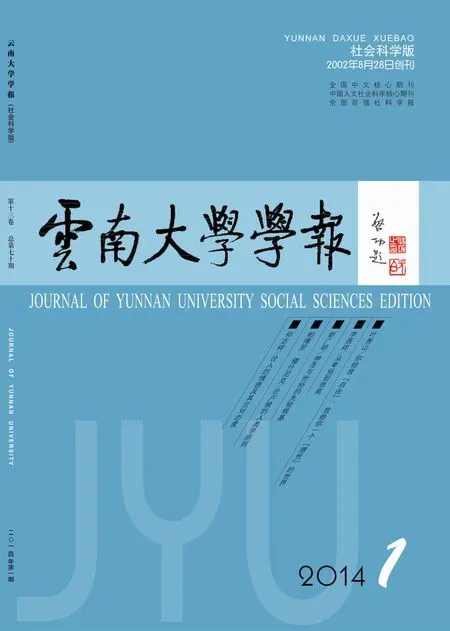《古文孝经孔传》为伪新证*
——以《孔传》与《管子》之关系的揭示为基础
2014-08-23刘增光
刘增光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清代中叶,自日本回传中国的《古文孝经孔传》(下简称《孔传》),甫一面世,其真伪问题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虽然如此,四库馆臣还将其收录于《四库全书》的经部中。[1]从历史上看,在《孔传》尚存的唐代,其真伪便已引发时人关注。以至于在争论《孝经郑(玄)注》①《孝经郑注》的作者是否郑玄,在历史上曾有广泛争议,现经清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和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之疏证,其作者为郑玄已成定谳。[2](P7)皮锡瑞《孝经郑注疏》,见光绪乙未(1895)师伏堂本。和《孔传》何者当置于学官时,由于没有定论,唐明皇不得不亲下御笔,撰成《孝经御注》。从文献目录学的角度看,《古文孝经孔传》并不见载于《汉书·艺文志》,其首见于身份本即可疑的王肃注本《孔子家语后序》,②《孔子家语》,上海:源记书庄,1926年,第118页。今传《孔子家语》源于王肃注本,唐以前无人怀疑其真伪,但宋以后多数学者视为王肃伪作,尤其是书中之《后序》更被作为伪书的关键证据。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儒家者言》一篇文献,与今传《家语》、《说苑》和《礼记》等书在内容上多有相同,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家语》的真伪问题。目前极具说服力的主流观点认为《家语》绝非王肃伪作。但出土文献并无直接与《后序》相关之内容,故《家语后序》之真伪仍悬而未决,这从学界的讨论集中于《家语》正文,而很少触及《后序》亦可见一斑。研究者注意到《后序》前后语气不一,内容亦有相互冲突处。故很多学者认为后序是由前后两段组成,关于前一段,一说以为是出自于对《家语》进行编订的孔安国之手;[3]一说则谨慎地以为是“借孔安国口吻”、“以西汉孔安国口气写的序”。[4](P49)、[5]关于后一段,古人怀疑《家语》之伪者多视为王肃所作,今则有人以为乃孔安国之孙孔衍所作,因其内载有孔衍奏言(参前揭张固也文)。此外,学界又有一种观点认为,后序前后矛盾处甚多,有可能是由三段“拼合而成”。[4](P49)我以为,张固也在文中力主《后序》之前后两段分别出自孔安国与孔衍,此说极难证成,原因有二:一、无法回答为何即使是认为的孔衍序之第二段中亦有前后重复拖沓之处,何况后序本未署名;二、忽视了正史《汉书·艺文志》以及许冲《上说文表》皆仅言及孔安国得孔壁《古文孝经》而已,并无其作《孝经传》之说。故贸然将《家语后序》第二段视为真,这在文献上找不到一丝旁证,孤立无援。而数年来致力于《孔子家语》研究的杨朝明教授在言及《后序》时态度更显模糊,一方面径直称为孔安国后序,似乎是针对整个《后序》而言,另一方面则称张固也所说的孔衍序为“有孔衍奏言的内容”。[6](P119、157)据此,《后序》是真是伪,绝难盖棺论定。至《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
关于《孔传》真伪的问题,学界目前的共识是:《孔传》绝非孔安国(约前156-前74))所作,亦非王肃或刘炫所伪作,伪托孔安国之名者另有其人,此书之成当在魏晋时代。[4](P507)、[7](08)③本文第三部分将揭明,成书于魏晋的《孔传》在宋代增加了“言之不通也”5字,传入日本后,又有人为此5字作注,故今本《孔传》绝非魏晋原本。有研究表明,《孔传》成书尚在王肃之后,其中内容多参酌郑玄、王肃注《孝经》之语,依违其间以敷畅己说,且《孔传》释《孝经》非止训释字义,而重在发挥义理,与六朝义疏体同。[4](P44-46)、[8](P241、247)唐代司马贞奏议亦言“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唐会要》卷七七)荀昶为晋末宋初人,故可推测《孔传》成书当在王肃与荀昶之间的魏晋时代。[4](P44-46)、[8](P241、247)
本文欲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孔传》抄袭《管子》但隐去后者之名的事实,揭示《孔传》在以义疏体形式注解《古文孝经》时,通过吸收《管子》的内容而使其思想带有糅合儒、法之浓厚色彩,甚至体现出法家化的鲜明倾向。若从汉代经学传统观之,经学讲求师法与家法,孔安国为经学名家,且是孔子十一代孙,断不会阴袭《管子》以变乱儒家之说。且孔安国以《尚书》名世,而《孔传》却不见引及《尚书》,反而对《管子》似有特殊之嗜好。总之,《孔传》非孔安国所作当不复可疑。
一、《古文孝经孔传》与《管子》对参
《孔传》所引文献虽十分丰富,其内却未有一处言及《管子》书名或其章名。但是,通过比较《孔传》与《管子》的相关内容,就会发现《孔传》抄袭《管子》甚明,其迹斑斑可考。就管见所及,大陆及港台学界至今未有人留意《孔传》与《管子》的这种密切关联,唯查考日本学人之著述,有宽政元年(1789)片山兼山(1730-1782)所著《古文孝经孔传参疏》(下简称《参疏》),*此书之首《古文孝经参疏序》谓:“先师讲业之余,标其所原,属山祐夫辑之。”故此书的著作权当归于片山兼山。见《古文孝经孔传参疏》,宽政元年己酉刻本,东都:嵩山房梓,1789年,第2页。又,此书凡例谓:“音义从太宰氏之旧。”对照《参疏》与太宰纯所整理之《古文孝经孔传》(知不足斋丛书本),可知两书所本《古文孝经》内容完全一致,《谏诤章》皆有“言之不通也”5字。而据舒大刚先生的研究,此本绝非隋唐之际由中土传入日本,其说甚详。[9]此书对《孔传》作了疏通工作,在《孔传》每一章之下皆“标其所原”,即将《孔传》内容之文献出处标列出来,其中便注意到了《孔传》对《管子》多有取用,共列出《孔传》引《管子》61处。*片山兼山:《古文孝经孔传参疏》,第2页。但此书仍有些许遗憾:一是未能将《孔传》和《管子》的相同处全部列出;二是所列《管子》语有几处略显牵强,只是因为《管子》之语有一两个词与《孔传》相同便被列入,但实则并不相关,这样的讹误共有9处;*如《孝经》言:“立身行道”,《孔传》:“立身者,立身于孝也。”《参疏》引《管子·禁藏》“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一长段内容。而这与《孔传》内容的相关度实则极小。见《参疏》卷上,第7页。三是限于《参疏》的体例,此书仅罗列了两者文本的相似语句,并未揭示出《孔传》袭用《管子》的思想缘由。其因有二:一是作者未能将《孔传》与《管子》的对比工作做到极致,二是《参疏》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地看待《孔传》之前后内容的,故而当其在《管子》中寻找与《孔传》相对应的内容时,是以某关键词或句子在二者中同时出现作为选取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以机械的统计学方法疏通《孔传》之意,故而存在很大的局限。《孔传》内容前后一贯,是一整体的思想文本,质言之,《孔传》的作者既然对《管子》多有关注,故其所引之内容就必然会对作者注解《孝经》之内容发生影响。因此,《孔传》在某些地方虽未出现与《管子》对应的关键词,但其对《孝经》的注释却是本于在此之前与《管子》有联系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地方亦应视为与《管子》的相同处。出于这样的考虑,很有必要对《参疏》另作一番补充完善的工作,下表中将《孔传》所引之《管子》篇章及次数列出:略去《参疏》已列出者;补充《参疏》所未列出者27处及所涉《管子》原文,并以着重号标示《孔传》与《管子》相同处;删去《参疏》所列不当者9处,不作标明,读者对照《参疏》一书即可明了。*亦可参刘增光:《晚明<孝经>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49-74页。
“《孔传》与《管子》对照表”(《管子》与《孔传》文句雷同处以着重号标示):

《古文孝经》《古文孝经孔传》《管子》1开宗明义章第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训天下。自“道者扶持万物”至“别而名之则谓之孝、弟、仁、谊、礼、忠、信也”。《形势》1次,《形势解》1次,《白心》1次。《形势》:“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道之所设,身之化也。”2开宗明义章第一民用和睦,上下亡怨,女知之乎?自“言先王行要道奉理则”至“先王之以孝道化民之若此也”。《形势》1次,《君臣上》1次,《明法解》1次,《形势解》2次。《形势》:“道之所设,身之化也。”《形势解》:“天之常也,治之以理……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和子孙,属亲戚”;“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3开宗明义章第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自“孝道者乃立德之本基也”至“道之美莫精于德也”。《心术上》1次,《形势解》1次。4开宗明义章第一中于事君。自“仕服官政”至“奉法无贰事君之道也”。《明法解》1次。5天子章第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自“谓内爱己亲而外不恶于人也”至“旦暮利之则从事胜任也”。《版法》1次,《版法解》1次。6天子章第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自“内敬其亲而外不慢于人”至“国有纪纲而民知所以终始之也”。《问》1次。 7天子章第二爱敬尽于事亲然后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自“刑法也”至“有其人则通,无其人则塞也”。《君臣上》1次,《权修》1次。8天子章第二《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自“天子有善德,兆民赖其福也”至“由于上之德化也”。《君臣上》1次,《形势解》1次,《版法解》1次。9诸侯章第三居上不骄,高而不危。自“高者必以下为基”至“虽高犹不危也”。《版法》1次,《版法解》1次,《形势解》1次。《版法》:“安高在乎同利。”10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自“法言谓孝弟忠信仁义礼典也”至“先王之所以合于道也”。《形势解》1次。11卿大夫章第四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自“必合典法然后乃言”至“是以不重也”。《形势解》1次。12卿大夫章第四口亡择言,身亡择行。言满天下亡口过,行满天下亡怨恶。自“言所可言”至“此皆灭亡所从生也”。《形势》1次,《形势解》1次。《形势》:“顾忧者可与致道。”“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13士章第五资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自“是故为人父者不明父子之谊以教其子”至“上有禁而民不犯也”。《形势》1次,《形势解》1次。《形势》:“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14士章第五故以孝事君则忠。自“孝者子妇之高行也。”至“其忠必矣”。《形势解》1次。

15庶人章第六因天之时,就地之利。自“天时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蔵也”至“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也”。 《小匡》1次。16孝平章第七孝亡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自“躬行孝道”至“以勉人为高行也”。《形势解》2次。《形势解》:“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17三才章第八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自“曾子闻孝为德本而化所由生”至“乃知孝之为甚大也”。《白心》1次。《白心》:“道者……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 ①18三才章第八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谊也,民之行也。自“经,常也”至“下之事上不虚,孝之致也”。《君臣上》1次。19三才章第八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自“则,法也”至“不用则者危也”。《形势解》1次。20三才章第八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训天下。自“夫覆而无外者,天也”至“则兆民赖其福也”。《版法》1次,《版法解》1次,《白心》1次。《版法》:“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版法解》:“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21三才章第八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自“以其修则且有因也”至“不加严刑而政自治也”。《形势》1次,《形势解》1次。《形势》:“造父之术非驭也。”《形势解》:“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22三才章第八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自“好谓赏也”至“则人君无以自守之也”。《明法解》1次,《形势解》1次,《版法解》1次,《重令》1次。《版法解》:“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畏众,非禄赏无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畏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畏众,禄赏不足以劝民,则人君无以自守也。”23孝治章第九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自“所谓明者,照临群下”至“故曰明”。《明法》1次,《明法解》1次,《版法解》1次。《明法》:“夫国有四亡:……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版法解》:“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24孝治章第九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自“说天子、言先王”至“所以供事其亲”。《版法解》1次。
①《孔传》作者对《管子·白心》涉及“行道”与“得福”关系的这段话颇有戚戚之感,故其传文屡屡引及这段话,如下文第17、20、25、26等4条。此亦表明《孔传》内容的前后一贯性和整体性。

25孝治章第九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自“如此,福应也”至“下之能孝,化于上也”。《白心》1次。《白心》:“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26圣治章第十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自“正君臣上下之谊”至“所以为贵也”。《版法解》1次,《白心》1次。《白心》:“道者……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27圣治章第十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自“人主以孝道化民”至“复何以加之孝乎”。《形势解》1次,《明法解》1次。28父母生绩章第十一父母生之,绩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自“父母之生子”至“有由然也”。《形势解》1次。29孝优劣章第十二不爱其亲……以训则昏,民亡则焉。自“夫德礼不易”至“则民无所取法也。”(附:《左传·僖公七年》记载:“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30孝优劣章第十二虽得志,君子弗从也。自“无润泽于万物”至“不昧食其禄也”。《宙合》1次。《宙合》:“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31孝优劣章第十二言思可道,行思可乐。自“言则思忠”至“行必果也”。《形势》1次,《形势解》1次。《形势》:“顾忧者可与致道。”“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形势解》:“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故曰:顾忧者可与致道。小人……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遇人有信……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32孝优劣章第十二容止客观,进退可度。自“容止,威仪也”至“不越礼法,则可度矣”。《形势》1次,《形势解》1次。《形势》:“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形势解》:“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惰,则臣下轻之。故曰:‘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33孝优劣章第十二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自“以者,以君子言行德谊进退之事也”至“则君道成矣”。《形势》1次,《形势解》1次。《形势》:“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34五刑章第十四要君者亡上,非圣人者亡法,非孝者亡亲:此大乱之道也。自“此无上、无法、无亲也”至“能从法者,良民也”。《正世》1次,《任法》1次。

35广要道章第十五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言礼最其善孝弟之实用也”至“所以政成也”。《版法》1次。36广至德章第十六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自“此又所以申明上章之谊焉”至“人然后成其化也”。《形势》1次,《形势解》1次。37广扬名章第十八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自“能理于家者”至“不肖不敢处官也”。《形势解》1次,《明法解》1次。《形势解》:“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38谏诤章第二十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自“慈爱者,所以接下也”至“所以事上也”《五辅》1次。39谏诤章第二十虽亡道,不失天下。自“无道者”至“人訾食则体瘠也”。《形势》1次,《形势解》1次。《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飺者,多所恶也。谏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体也。主恶谏则不安,人飺食则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体也。’”“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40谏诤章第二十大夫有争臣三人,虽亡道,不失其家。自“三人谓家相、宗老、侧室也”至“故以天下为称”。《形势解》1次。41谏诤章第二十臣不可以不争于君。自“事君之礼,值其有非”至“是谓人主殴国而捐之也”。《小匡》1次,《君臣下》1次,《明法解》1次,《立政九败解》1次。《君臣下》:“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忠臣之行也。”《明法解》:“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惟恶之,则必候主闲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①42事君章第二十一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自“将,行也”至“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也”。《明法解》1次。43事君章第二十一故上下能相亲也。自“道王以先王之行”至“上下之分定也”。《君臣上》1次,《明法解》1次。《明法解》:“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乱主则……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贵。”
①《明法解》这段话虽与《孔传》并无关键词上的相同,但《孔传》言良臣之于奸臣,正与《明法解》一致,故列入。
据此,《孔传》引《管子》之情况为:《形势第二》10次,《权修第三》1次,《版法第七》4次,《五辅第十》1次,《宙合第十一》1次,《重令第十五》1次,《小匡第二十》2次,《问第二十四》1次,《君臣上第三十》5次,《君臣下第三十一》1次,《心术上第三十六》1次,《白心第三十八》5次,《任法第四十五》1次,《明法第四十六》1次,《正世第四十七》1次,《形势解第六十四》25次,《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1次,《版法解第六十六》8次,《明法解第六十七》9次。《孔传》有多达43处内容引用《管子》之文,次数高达80次,涉及《管子》19篇内容。《管子》一书共8组86篇,《孔传》之引用将近其书的四分之一篇章,涉及其中6组,《形势》、《权修》和《版法》属于《管子》的《经言》组,《五辅》、《宙合》和《重令》属于《外言》组,《小匡》和《问》属于《内言》组,《君臣》、《白心》和《心术》属于《短语》组,《任法》、《明法》和《正世》属于《区言》组,《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和《明法解》则属于《管子解》。除《杂篇》和《轻重》2组未引外,其他6组均有涉及,这表明:《孔传》的作者很可能阅读了《管子》各组所包含的所有篇章。再就《孔传》自身来说,《纪孝行章第十三》、《感应章第十七》、《闺门章第十九》和《丧亲章第二十二》四章的传文未袭用《管子》,因为这四章的内容主要是叙述为人子者如何孝亲事亲的具体节目,不直接关乎治理天下的方面,《管子》中亦无相关资源可资取用。其余十八章,《孔传》之作者都或多或少地从《管子》中找到了对应资源。从字数上来说,《孔传》除《序》之外,传文内容为14755字,若将《孔传》未引《管子》的四章之传文除却不计,则为12380字,而《孔传》引及《管子》内容的传文则为6119字,故说《孔传》二分之一的内容都直接与《管子》有关,绝不过分。《孔传》之作者对《管子》内容之熟稔毋庸置疑,其如此大量地引《管子》解析《孝经》着实有些令人意外,二者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当在《管子》中找不到与《孝经》相对应的内容时,《孔传》的作者便引用《左传》中所记载的管子之言作解(表第29条)。这意味着《孔传》的作者颇为“有心”,对管子的言行事迹以及《管子》一书肯定做过深入研究。
二、融合儒、法思想的《孝经》诠释
证明《孔传》内容杂有法家思想,是证明《孔传》非孔安国所做的关键步骤,欲确证这一点,通过考察《孔传》如何吸收《管子》中的法家成分以解析《孝经》便可达成。众所周知,《管子》成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增益和整理的过程,其内容更是将儒、道、法思想熔为一炉,被视为是代表了齐国之法家思想的作品。但此书非管仲自著则已无疑义,《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类,亦颇值得推敲。[10](P23-24)当前学界的共识是,应按《管子》之分组对其进行研究,考察每组篇章的成书时代与思想。据张固也先生的《管子研究》,《管子》的86篇内容主要是春秋末至战国晚期的作品。*张固也之《管子研究》一书在充分吸收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进了对于《管子》的研究,反映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书中认为:大致说来,《经言》组为春秋末至战国早期之作品,《外言》组为战国中期作品,《区言》组为战国中晚期作品,《内言》组的成书时代早于《经言》或与后者相当,《短语》组和《管子解》为战国晚期齐国之法家作品。[11](P57-60)而前文已说明,《孔传》成书于魏晋时代,远远晚于《管子》,故一定是《孔传》引《管子》,而不可能相反。下文通过分析《孔传》所引《管子》各篇的思想内容,将表明:《孔传》对《管子》的引用,具有融合儒法思想的特点,而《孔传》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因此而显得复杂,可概括为融合儒法或儒法相杂。
在《管子》一书中,《管子解》组和《区言》组最能体现齐国之法家思想,尤其是《区言》组篇章与秦晋法家思想有着很大的相似,[11](P307、356)故《孔传》对这两组篇章的引用必须重点分析。考虑到《经言》作为《管子》学派的经典文字,其中诸篇并无明确的思想派别倾向,[11](P68)故而在分析《孔传》的法家思想倾向时,这组文章不予考虑。《内言》组的《小匡》和《问》是讲桓管历史,[11](P76)亦可不论。《外言》组的《五辅》、《宙合》和《重令》,《孔传》均各引1次,比例极小,《五辅》的儒家色彩浓,《宙合》的道家色彩浓,《重令》的法家色彩浓,[11](P142-147)但引《重令》处又见于《版法解》中,故对这一组的分析也略去。我们将聚焦于分析《孔传》对《短语》组2篇、《管子解》3篇和《区言》组3篇的引用上,以呈现《孔传》之法家色彩,条陈于如下。
《短语》组:1.《白心》为“稷下道家黄老学派作品,君人南面术的色彩很浓厚”。《君臣》上下两篇“都是战国晚期儒道法诸家之说杂糅,表面上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以法家思想为实质的作品,简单地称为‘齐法家著作’或过分强调其‘以儒家学说为主导’,都不很妥当”。[11](P45、244)《孔传》对《白心》的引用主要集中于“行道”则致“有福”的论述上——“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而第一次引及正是在对《孝经·开宗明义章》的解释中(表第1条),《老子》多言祸福,故《孔传》此处有以道家之“道”解释《孝经》作为“至德要道”之“孝”的意味。此外,《孔传》第17、20、25、26等4条亦皆涉及到《白心》这段话。2.《孔传》对《君臣上》的引用,在第2、7、8、18、43条,其中前4条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强调君主要立身正德以化导万民。第43条谈到论材量能,这也是儒家所主张的,但其中言及君佚臣劳、严上下之别以防上失威势,则明显倾向于法家。
《区言》组:1.《孔传》解《孝经·五刑章》时引及《任法》内容(表第34条),虽然《孔传》引《任法》仅此1条,但此条正是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典型表达。2.《孔传》对《明法》和《正世》的引用各1次,分别在第23条和第34条,并无明显的法家色彩。
《管子解》组:1.《形势解》中颇多儒家之言。[11](P367)而从《孔传》的引用来看,除了第13、22两条强调君主令行禁止,第33条讲君主对民要恩威兼施外,其余引用《形势解》的22处都具有鲜明的儒家倾向。2.《版法解》亦颇多儒家之言。[11](P367)《孔传》引《版法解》的第22条讲君主以号令使下,以斧钺畏众,以禄赏劝民;第23条讲信赏必罚;第26条强调须明君臣上下之别。其余《孔传》所引5处都绝非法家性质的,而是属于儒家。3.《明法解》的法治观点相当接近韩非子,标志着齐国之法家思想达至巅峰,此篇“用‘法’字百余次,为先秦单篇文献之冠。它极为强调法之重要”,对“势”亦非常重视,其中“用‘势’字多达十七次”,且“《明法解》的术治思想在(《管子》)全书中也最为明显而丰富”。[11](P361-363)正是在对《明法解》的9次引用中,除第2条外,《孔传》其余8次都涉及法家的法、术、势思想。[11](P361-365)涉及“法”的有第4、22、42等3条,涉及“术”的有23、37、41、42等4条,其中第23条谈到君主“有不蔽之术”,《孔传》改为“有不蔽道”,其实质则无变化。第37、41条讲君主操秉循名责实等御臣之术,第42条讲诛赏分明之术。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涉及法家“势”思想的第27条,《孝经》本是说周公为圣人,能躬行孝道而宗祀文王,四海之内诸侯皆向风归化,不远万里前来助祭。但《孔传》的解释则不从行孝立论,而是以法家的权、术、势之说立论:“周公秉人君之权,操必化之道,以治必用之民,处人主之势,以御必服之臣,是以教行而下顺,海内公侯奉其职贡,咸来助祭。圣孝之极也,复何以加之孝乎?”诸侯之服从与助祭是因为周公的权势,而非周公能行孝。这一解释就将儒家尊为至德之圣的周公幻化成了法家思想中善于运势操权的威权君主,其与《孝经》文本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意义分裂。且《孔传》引《明法解》和《版法解》解《孝经·圣治章》“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表第23条),赋予“明王”以信赏必罚、操不蔽之术的“明主”的意涵,这与《孝经》以孝弟礼乐治理天下的“明王”意涵亦有天壤之别。
据此以观,《孔传》对《管子》的引用,涉及道家的成分极微弱,但对《管子》中所包含的儒家和法家思想则关涉甚深。《孔传》对《管子解》组之《明法解》的引用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以法家思想诠释《孝经》的倾向,尤其是对《孝经》中的“明王”的意涵和“周公”形象的转换,法家色彩浓厚,已绝非儒家思想所能范围。这一方面说明,《管子》中虽既有儒家思想,也有法家思想,但《孔传》在引《管子》解《孝经》时,并未因《孝经》为儒家典籍便单纯地取用《管子》中的儒家成分以作解,而是也取用了其中的法家成分;另一方面说明,《孔传》欲糅合《管子》的法家成分以解《孝经》,难免会造成二者之间的意义紧张,尽管《孔传》的作者采用了便于义理发挥的义疏体,亦不能将性质相异的两派思想泯合为一,这也就造成了《孔传》之内容儒法并陈的情况,其对“周公”形象和“明王”意涵的解释显得扞格难通,并非偶然。因此,将《孔传》的内容定位为糅合儒法、儒法相杂,应该说是合理的、可靠的。
三、《孔传》之证伪与学术史意义
据前所述,可推导出证明《孔传》为伪的两个有力的理由是:1.《孔传》的作者能够大范围地引用《管子》,涉及《管子》中的6组篇章。这表明作者所接触和阅读的很可能正是经西汉刘向(约前77-前6)校理过的本子。[11](P49-50)孔安国(前156-前74)虽生活于西汉,但当其殁年刘向仅4岁,孔安国绝不可能读到刘向校理过的《管子》86篇。2.《孔传》之传文糅合儒、法,甚至让人心生驳杂之感。其对《孝经》之“周公”、“明王”意涵的解读,尤显法家化色彩。孔安国作为孔子后人、西汉之经学大师,绝不会如此抄袭《管子》,以法解儒。故《孔传》绝非孔安国所作,当不复可疑。
认识到《孔传》为伪及其与《管子》的密切关系,对于《管子》学的研究有着一定意义。明晓了《管子》被《孔传》大量袭用这一事实,就应将其视为《管子》在魏晋时期流传的重要一环。据笔者所知,学界论及《管子》的历史流传,涉及魏晋时期时对《孔传》不置一辞,[12]忽视了魏晋时期为继春秋战国之后《管子》流传的又一极佳时段。其时恰逢汉代经学衰落,而曹魏时期兴起的名法思潮方兴未艾,儒学独尊之势不再,沦为安邦定国的治术之一,甚至不及刑名法术之地位,《晋书·傅玄传》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即是当时时代精神的概括。而三国纷争之势与春秋战国十分相似,在这种背景下,不乏有识者会想到效法管子以治国,实现统一与富强的双重目的,出现如西晋傅玄上疏晋武帝效仿管子创制法度之事,实为必然。同理,魏晋时期出现以齐国之法家作品《管子》解释儒家典籍的著作,如《孔传》,亦是绝对可能的。
当然,确证《孔传》为伪的最重大的意义仍在于《孝经》学本身。知晓《孔传》乃成书于荀昶之前的魏晋,并非真正的孔安国注,那么,我们就应以新的眼光重审今、古文《孝经》学的纷争,进一步厘清《孝经》学的历史脉络。
历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分者,多谓二者的差别重在其所推崇的制度,今文经学推崇《礼记·王制》,古文经学推崇《周礼》。但《孔传》本就不是在汉代今古文经学相争的背景下产生,那就不能将其视为汉代古文经学的代表。且与郑玄的《孝经》注相比,*据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可知,郑玄综罗今古,屡屡引《周礼》注《孝经》。《孔传》对涉及制度之处亦非常简略,由此可见其并不关注儒家经典中的制度,所重视者为近于法家的治国理论之阐发。就文本内容而言,《孔传》经文绝非汉代时的《孝经》原貌,而传文亦很可能不是魏晋时的《孔传》原貌,此点下文详述。故将《孔传》拉入汉代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中,实为自扰之举。而从《孔传》的产生和流传来说,其成书于魏晋,在东晋时流传已较广泛,至梁武帝时,与《孝经郑注》并立学官。至隋代,刘炫得《孔传》,后闻于朝廷,亦与《孝经郑注》并立学官。及至唐代,刘知几主《孔传》,司马贞主《郑注》,互相攻驳,是此非彼,莫能归一,唐玄宗始作《御注》。[7](P343-347)自此后,宋元明清,争论《孔传》和《郑注》之是非者,代不乏人。由此看来,后世一般所谓的《孝经》今、古文之争,实则是在唐玄宗时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这并未形成一个问题。而唐代时的争论,又主要是因《孔传》亡于五代之乱,唐建国后《孔传》不知从何处复现,故时人颇疑其伪,由此纷争遂生,并愈演愈烈,成为《孝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故而我们在对《孝经》学的历史发展进行叙述时,应将唐以来的今古文《孝经》学之争与汉代时的今古文之争区别对待,而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孔传》是汉代古文经学之代表。否则,便有违历史的真相,亦会造成研究中不必要的混乱。
当然,判定《孔传》为伪,并不等于说《古文孝经》本身为伪。但在这一前提下,仍然需要判定的一点是:汉代的《古文孝经》与日本回传中国的《孔传》本《古文孝经》二者有别。《古文孝经》在汉代的存在毋庸置疑,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今文孝经》出自颜芝、颜贞父子所献,《古文孝经》则与《古文尚书》同出于孔壁。其时,今、古文《孝经》皆有流传,且治《今文孝经》者有数家: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
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13](1719)
据此,汉代时22章的《古文孝经》和18章的《今文孝经》之别除却分章不同,内容文字上的差异是非常微小的,仅有两处不同,这正是日后刘向可以“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以十八章为定”[14](P935)的根据。否则,若二本差异甚大,是无法“以颜本比古文”的。[15]而日传《孔传》本的《古文孝经》却与《汉志》所述有异,其鲜明之处有二:一是其中多出《闺门章》,二是《谏诤章》“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之后多出“言之不通也”5字。《闺门章》为汉代之后有人误将长孙氏注文篡入经文,前人论之甚详,兹不赘述。[7](P360-362)但关于“言之不通也”之问题,尚有未发之覆,兹结合前贤成果,备述于下。
今传《孝经郑氏注》、唐玄宗《孝经御注》、邢昺《孝经注疏》等《今文孝经》本俱无此5字。假若汉代时《古文孝经》已有此5字,《汉书·艺文志》以及校订《孝经》的刘向不可能都未意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差别,而《隋书·经籍志》亦同样未见记载。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宋之王应麟之说可解此疑窦,其《困学纪闻》言:“‘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司马温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说》误以‘言之不通也’五字为经文,古今文皆无,《朱文公集》所载《刊误》亦无之。”[16](P975)舒大刚先生据此详考,指出“言之不通也”5字之篡入经文并非范祖禹之《古文孝经说》所为,而很有可能是南宋之杨简(1141-1225)将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和范祖禹的《古文孝经说》合刊在一起时“弄出的笑话”。他进而以此作为判定日本回传中国的《古文孝经孔传》绝非隋唐之际传入日本的有力根据之一。[17]
但今本日传《孔传》中确实有此5字,又如何解释呢?日传《孔传》本《古文孝经》为江户时代太宰纯以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刘炫之《孝经直解》为底本,“以数本校雠,且旁及他书”而成。*《重刻古文孝经序》,载《古文孝经孔传》,知不足斋本。足利学校所藏之《孝经直解》仅有第1卷和第4卷,其中并无《谏诤章》经文,故无法得知其中是否有“言之不通也”5字。*笔者所见为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而这5字也绝非太宰纯校订时所增入,原因是早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便流传有多种《古文孝经》钞本,包括:三千本(三千院藏建治三年写本)、宝本(高野山宝受院藏镰仓后期钞本)、静乙本(静嘉堂文库藏室町时代钞本)、两足本(建仁寺两足院室町末近世初钞本)、斯直本(斯道文库藏室町末钞本)等多达数十种,此处所列这几种钞本无一例外地均有“言之不通也”5字。*阿部隆一:《古文孝经旧钞本の研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无版次信息,第904-905页。在此,笔者要非常感谢博士后合作导师吴震教授慷慨赠予此书,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其中,以三千本最早,时在公元1277年。除却有此5字的钞本外,日本其余的众多钞本以猿投本(猿投神社藏建久六年写本)最早,时在公元1195年。而杨简的生活时间在南宋后期的1141年至1225年,比照时序可发现:三千本的抄写时间正在杨简之后,而猿投本写就时,杨简尚在世。巧合的是,猿投本并无“言之不通也”5字,三千本中恰有此5字。朱熹(1130-1200)以《古文孝经》为底本作《孝经刊误》,内亦无此5字,猿投本的写就时间正相当于朱熹的晚年,同样无此5字。时间上的对应,足以佐证舒大刚先生的结论,有“言之不通也”的《古文孝经》绝非隋唐之际从中土传入日本,而应是在南宋末或之后。
“言之不通也”5字本为司马光之《指解》注文,而将此书与范祖禹之《说》合刊在一起的本子只是误注为经,并未对此5字加以注释。*见《唐玄宗注、宋司马文正公指解、范淳父先生说》,清纳兰成德辑《通志堂经解》本,康熙十九年刻本,后为四库全书所收录。但上举日传诸钞本《孔传》之《谏诤章》中不但有“言之不通也”5字,且文后还加以注释,这就颇显荒唐。*阿部隆一:《古文孝经旧钞本の研究》,第905、909页。既然日传《孔传》乃是南宋或之后才从中土传入日本,而《孔传》之作是在魏晋时期,后者中理应无此5字,遑论注文,故这段注文当非《孔传》原本所有。这表明,今传《孔传》绝非魏晋时期的《孔传》原本,与隋时刘炫所见《孔传》、唐时司马贞、刘知几所见《孔传》俱不同。否则,司马贞和刘知几当时激烈争论《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之优劣,缘何从不言及“言之不通也”5字,而仅怀疑《闺门章》的真伪。而另一个显明的事实是,“言之不通也”5字在元、明时期屡屡为学者们所注意和道及,甚或有尊崇古文者竭力加以注释,疏通其义,*如吕维祺:《孝经大全》卷十,第428页;朱鸿:《孝经质疑》,载《孝经总类》巳集,第111页;孙本:《孝经释疑》,载《孝经总类》午集,第137页。以上三书均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这一做法正与日传本一样,画蛇添足。故而司马贞和刘知几,以及后来的朱熹未提及“言之不通也”的问题,并非因其不重要,只能是因为当时流传的《古文孝经》中的确无此5字。由此亦可反推,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刘炫的《孝经直解》中当亦无此5字。今传《孔传》反而为此5字作注,恰证明其并非魏晋时期的《孔传》原本。
余论
综上所述,《古文孝经孔传》为魏晋时人托名西汉孔安国之作品,其书以义疏体形式广引《管子》之多篇内容以释《古文孝经》,有着糅合儒、法思想的鲜明特色,其为伪书无复可疑。但《古文孝经孔传》一书命途多舛,且不论其在历史上有着多次亡佚而复现的经历,就其文本而言,首先是其所据《古文孝经》并非汉代出于孔壁的《古文孝经》,而是含有将长孙氏注文误为经文的《闺门章》的《古文孝经》,故绝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孝经》古孔氏一篇”。再则是《孔传》的传文亦同样有被后人增益的遭遇,传文本非孔安国所作,当它远渡东洋,又不知何人在篡入的“言之不通也”5字下加以注释,故可说今本《孔传》之成乃是魏晋时人和日本的某位无名氏共同撰述的结果,而南宋的杨简误注为经,又是其间的关键助缘。因缘际会,竟使今本《古文孝经孔传》之身份从“伪书”变成了“伪中之伪”,其伪更不容置辩。故对于《孝经》学史的梳理,不可忽视的两点是:不可将《孔传》所据之《古文孝经》混同于汉代时的《古文孝经》,亦不可将今本日传《孔传》视为魏晋时期的《孔传》原本。对这两个问题的澄清,当是论证今本日传《孔传》为伪之最重要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顾永新.日本传本《古文考经》回传中国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2).
[2]陈铁凡.孝经郑注校正[M].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
[3]张固也.从《孔子家语》后序看其成书过程[J].鲁东大学学报,2009(5).
[4]陈鸿森.孝经孔传与王肃注考证[A].经学:知识与价值会议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
[5]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2).
[6]杨朝明.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M].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
[7]庄兵.《孝经·周门章》考[A].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五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林秀一.孝经学论集[M].明冶书院,昭和51年.
[9]舒大刚.论日本传《古文孝经》绝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2).
[10]胡家聪.管子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张固也.管子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
[12]耿振东.《管子》研究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13]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舒大刚.论宋代胡《古文孝经》学[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
[16]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7]舒大刚.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