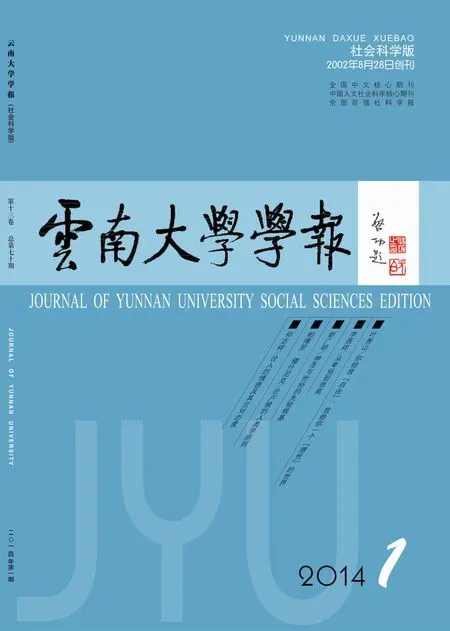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
——兼及对“诗分唐宋”的新考察
2014-03-06谢琰
谢 琰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一、何谓“思维模式”
苏轼之于宋诗,不仅具有代表性,还具有超越性:他“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即便不好宋诗者也会独爱东坡,[1](P321)[2]甚至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认为:“不特在宋无此一家手笔,即置之唐人中,亦无此一家手笔也”。[3](P1396)。相比之下,黄庭坚就只具有代表性,他的诗通常被认作典型的宋调。诗史地位的显著不同,意味着两人诗歌创作的根本差异。而此差异,很容易被归因于两人的天赋、人格等虚泛要素,①王友胜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苏以才气取胜,黄以学问见长,分别代表两种不同创作倾向而又各具风采。”[4](P72)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美学观照。这种缺失,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关:目前学界分析诗歌,无非从内容、形式、风格三个角度入手。内容分析浅显质朴,不能说明宏观审美问题。形式分析易入细碎,风格分析易入飘渺,常常得出各自确凿但又相互抵牾的结论。因此,在解答“苏、黄差异”这样既宏观又微妙的论题时,三种分析法皆有局限。
我以为,要合理研究此论题,必须找到一个既宏观又直观而且深刻的新角度。美国艺术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中指出:“要想达到对某种事件或某种状态的科学性理解,就要发现这些事件和状态的‘力’的式样”,“一件成熟的艺术品会展示出一种高度敏锐的形式感和一种把意象的各种不同成分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构图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5](P257,P359)这个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结论提示我们,诗歌的内容、形式、风格等审美特征背后,隐藏着诗作者存在着思维模式,即:诗人会用某种抽象的形式感去安排诗歌的意义单元,或连贯,或断续,或直露,或隐蔽,或单线,或复调。思维模式可以表现为章法特色,也可表现为修辞习惯,但又不是具体的结构或手法,而是对建立结构、运用手法起到支配作用的那种潜意识。因此,思维模式既可以从简单、坐实的章法分析或修辞分析中抽象出来,又包含着长久的艺术经验、深刻的艺术修养,具有形而上的宏观意义,不妨成为本文分析苏、黄差异的新角度。
颇有意味的是,在历代诗论家看来,思维模式的两大表现即章法特色和修辞习惯,恰恰分别成为苏诗和黄诗的最大优势所在。如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云:“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自此以后,诗人迭起,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煅炼精而情性远,大抵不出于二家。”[6](P220)又《宋诗钞》卷28黄庭坚小序:“宋初诗承唐余,至苏、梅、欧阳,变以大雅,然各极其天才笔力,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庭坚出而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为宋诗家宗祖。”[6](P270)又方东树《昭昧詹言》卷11:“坡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境,非人所测。于篇中又有不测之远境,其一段忽自天外插来,为寻常胸中所无有。不似山谷于句上求远也。”[3](P1469)又据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记载,黄庭坚自己就有此分判:“鲁直谓东坡作诗,未知句法。”[3](P457)以上材料中,苏诗之“波澜”、“终篇远境”、“天外插来”,皆谓章法特色;黄诗之“煅炼”、“句律”、“句上”、“句法”,皆谓修辞习惯。尽管苏诗的修辞手法同样巧夺天工,黄诗的篇章结构亦堪师表天下,但一旦涉及到“苏、黄差异”这样的宏观诗学问题,苏诗的修辞似乎就只服务于章法,黄诗的章法仿佛就隐没于修辞。也就是说,历代诗论家已敏感地认识到:苏、黄的根本差异不是内容的悬隔,也不是风格的优劣,更不是具体形式的高下,而是在抽象的形式感上给读者以不同的体验,亦即整体思维模式的分野;苏诗的思维模式集中体现在章法特色,而黄诗的思维模式集中体现在修辞习惯。那么,本文首先需要追问的就是:在“波澜”、“句律”等相对模糊、感性的诗学概念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思维模式?我们如何将体验转化成理论?而苏、黄差异一旦在思维模式层面上得到很好的理论诠释,苏、黄与唐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会得到重新梳理,最终“诗分唐宋”命题也会得到新的考察。
二、从章法特色看苏诗的思维模式
苏诗成就最高的四大体裁是七古、*本文遵照王力说法,把七言古、杂言古、歌行体统称为七古。[7](P16)七律、五古、七绝。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章法要求,苏诗亦不能例外。本节先依次分析苏诗四大体裁的章法特色,然后从中发现共通之处,从而揭示苏诗的思维模式。
1.七古和七律的“突转”
七古和七律的章法原本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宋诗普遍存在古体入律的“破体”问题,苏轼的很多优秀的七律也具有七古的章法特色,所以合并言之。
苏轼七古最突出的章法特色是“突转”,即:诗歌思路向相反方向突然变化,且符合逻辑或美学的原则。*本文使用“突转”、“发现”等概念,借鉴了戏剧术语。[8](P89、82)在篇幅宽敞、气韵激荡的七古中,“突转”最容易产生奇效。
在苏轼七古中,“突转”多以议论形式出现在诗篇的中段或结尾,符合“正-反-合”的逻辑原则。比如《泗州僧伽塔》的前半段:“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9](P906)其中“耕田”四句,前两句是对“私心”的反思,后两句又是对前两句的反证。又《百步洪二首》其一,本用铺天盖地的“排喻”塑造“险”、“驶”之势,但却被“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二语瞬时解构。[9](P860)又《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之“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9](P1526)把假象想成实境,再从实境翻出“人仙不二”之哲理。至于《中秋见月和子由》之“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明朝人事随日出,怳然一梦瑶台客”、[9](P833)、《登州海市》之“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9](P1313),则跳出去讨论写作本身的“存在与虚无”。可见,苏轼七古在苦乐之间、动静之间、虚实之间甚至文本内外之间频繁地运用“正-反-合”的原则,时而由反趋正,时而由正趋反,甚至由反趋合。可以说,庄子的相对主义在苏轼七古中重新焕发青春,并获得了更为生活化、人情化的演绎。
“突转”的另一种形式是写景。如果说议论式“突转”符合逻辑原则,那么写景式“突转”则遵循美学原则。苏轼七古,本以“豪逸”为主体风格,若突然飘出清丽之句,其惊人的美感往往超过一切势大力沉的铺陈或精雕细琢的修饰。这种风格反差极大但直接拼连的写景,把美学的“烘托”原则用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样堪称“突转”。比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9](P997)《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之“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9](P896)《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之“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9](P1001)《和秦太虚梅花》之“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9](P1137)这些佳句,皆非雕琢、夸饰,只是使用最简单的白描、最平淡的比喻、最自然的对照,就能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其奥秘就在于前后文完全异质的烘托。这就好比在很多心理实验中,一个最先跳出惯性思维的人往往是天才,而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换个相反思路,貌似简单,却包含着巨大的智慧和信心。
要之,苏轼七古俊逸豪丽、飞动奇纵的风格背后,有鲜明的章法特色作为支撑,即“突转”。这不是简单的换个话题、另起一意,也不是技术性的故作奇语、以资调剂,而是在诗歌思路的主干上制造质变,以达到优化章法、挑起全篇的效果。
在古体入律、散文化风气甚嚣尘上的北宋大环境中,苏轼七律也常包含“突转”。比如以下五首佳作:
《寿星院寒碧轩》: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9](P1595)
《登玲珑山》: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9](P463)
《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9](P90)
《宿九仙山》: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余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9](P464)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9](P2218)
第一、二首包含议论式“突转”:前者一直说竹林之“寒瘦”,最后却质问“鹤骨”之“肥”;后者平行铺陈,笔力密集,最后翻出“力尽”之后的人生哲理。第三、四首则包含写景式“突转”:一直虚写人生、虚写古迹,最后突然定格写实,显得极有画面感。此外,第三首和第五首的中段也有“突转”,都是用颔联去反思首联。前者谓:人生之无常,不仅在于客观存在之脆弱,更在于主体意识之偶然与茫然。后者谓:风雨后的夜空,不须明月点缀,而是自具澄明,犹如我那历尽苦难的心灵。后者尤其是苏轼七律的绝唱:到了末联,又把前面的苦乐一并解构,认为一切都是我之精彩人生的一段,无所谓苦乐,“奇绝”就好了。此种“奇绝”之笔,出现在短短八句之内,实在只有天才方可驾驭。要之,尽管七律的篇幅和格律使它无法容纳过多的蓄势,也就无法把“突转”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苏轼还是尽可能地在方寸之内随机应变。
2.五古的“回环”
七古的章法重在奇纵,而五古的章法重在工稳。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一云:“试以五言古论之,韩、白、欧、苏虽各极其至,而才质不同。韩才质本胜欧,但以全集观,则韩太苍莽,欧入录较多而警绝稍逊,然不免步武退之。白虽能自立门户,然视其全集,则体多冗漫,而气亦孱弱矣。至于苏,则才质备美,造诣兼至,故奔放处有收敛,倾倒处有含蓄。盖三子本无造诣,而苏则实有造诣也。”[10](P381)可见,苏轼五古的章法,不同于韩之“苍莽”、白之“冗漫”,而是有“收敛”、“含蓄”之妙法。由此细观其五古,最突出的章法特色是“回环”。
所谓“回环”,即诗歌思路在变化过程中返回到之前某一处,出现相似的境界、事件、物象、观念等。比如《藤州江上夜起对月赠邵道士》的前半篇:“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径寸珠,堕此白玉盘。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9](P2230)开头四句原本一气推进,但苏轼紧跟着用“我心本如此”扣紧第一句“江月照我心”,形成小回环,就没有继续“倾倒”下去。类似笔法还出现在《行琼儋间……戏作此数句》的前半段:“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9](P2108)“此生”回向“我行”,“四顾”回向“四州”。又如《寒食雨二首》其二:“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感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9](P1081)首四句沉痛奔放,愈往后则愈哽咽,最后“也拟”二句乃是双关,既把沉痛写到凄厉,又以“死灰”呼应“破灶烧湿苇”,把溢出的情绪收回到生活情境中。
此外,苏轼的对仗技巧有时也会产生“回环”效果。比如翁方纲《石洲诗话》卷3曰:“《答任师中家汉公》五古长篇,中间句法,于不整齐中幻出整齐。如‘岂比陶渊明’一联,与上‘闲随李丞相’一联,错落作对,此犹在人意想之中。至其下‘苍鹰十斤重’一联,‘我今四十二’一联,与上‘百顷稻’、‘十年储’一联,乃错落遥映,亦似作对,则笔势之豪纵不羁,与其部伍之整闲不乱,相辅而行。苏诗最得属对之妙,而此尤奇特,试寻其上下音节,当知此说非妄也。”[3](P1387)
3.七绝的“发现”
就章法而言,七绝最讲究压缩,即用最狭小的篇幅去展现最显著的起承转合之势。盛唐七绝多为“场景式”,充满戏剧性和抒情性;宋人七绝多为“片段式”,或者纯议论,或者纯描写;而苏轼最优秀的七绝,是“发现式”,即:诗歌思路展现出从不知到知的观察过程或认知过程。它既可以展示对人生场景的发现,也可以展示对思想片段、景物片段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七绝最容易写出悠长的情韵。
比如以下四首名作:
《和孔密州五绝·东栏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二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9](P703)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其一: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攲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9](P1435)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9](P404)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9](P1155)
第一首从美景中发现惆怅,如《御选唐宋诗醇》卷35所评:“浓至之情,偶于所见发露”。[11](P595)第二、三首从画面想到实境,从美景想到美人,仿佛灵光乍现,不辨真幻,“发现”的瞬间更令人惊喜。第四首的“发现”稍显隐晦:冯应榴注引《西溪丛语》:“南山宣律师《感通录》云:‘庐山七岭,共会于东,合而成峰。’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9](P1155)可见,这首名作仿佛全是虚处弄笔,其实仍是从实处“发现”出来,可谓自圆其说、自然高妙,与那些上来就说理、以敏锐取胜的宋代七绝大不相同。
综上所述,苏诗的章法极具特色:七古和七律都以“突转”取胜,五古以“回环”见长,七绝则以“发现”为惯式。由这三个特色可见:苏轼习惯于用最突出、最鲜明的方式去演绎各种体裁的基本章法规律。比如七古章法,原本讲求奇纵,他便用“突转”去强调;五古章法,原本讲求工稳,他便用“回环”去强调;七绝章法,原本讲求压缩,他便用“发现”去增加“场景”的深度,延长“片段”的生命,以使更多的情味被压缩进来;至于七律,原本就有极大的章法张力,在格律和句式上具有工稳的可能性,在句长和篇幅上又不乏奇纵的可能性,他便用“突转”去强调它奇纵的一面。也就是说,尽管苏诗在具体内容、形式、风格上极为驳杂、深奥、丰富,但就抽象的形式感而言,它力求连贯、直露、单线,从而形成随体诘曲的章法特色。此种思维模式,可称之为“历时变异”,即用极为明显的转折、回归、递进等变异方式去强调诗歌语言的历时属性。因此,苏诗往往具备“一唱三叹”的节奏和韵味,能够掩盖细节上的晦涩与驳杂,让读者产生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错觉。
三、从修辞习惯看黄诗的思维模式
苏诗的思维模式,必须在黄庭坚的烛照下才能彻底显示其独特性。
首先,就章法而言,黄诗多规范而少特色。而其最具特色之处,又是变连贯为断续,实是以局部的修辞去替代整体的章法了。比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12云:“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6](P319)又王楙《野客丛书》卷25云:“《步里客谈》云: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鲁直《水仙》诗亦用此体:‘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仆谓鲁直此体甚多,不但《水仙》诗也。如《书酺池寺》诗:‘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趁渔船。’《二虫》诗:‘二虫愚智俱莫测,江边一笑人无识。’”[6](P137)可见,黄诗往往故意“造成诗歌脉络的不连贯性和结构的不完整性”,“激起读者强烈的参与补充的欲望”。[12](P460)于是,“精要之语”、“断句”自身的审美价值凌驾于结构功能之上。
其次,就修辞而言,黄诗极具特色,成就极高,形成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修辞习惯,彰显着一种与苏诗迥然不同的思维模式。翁方纲《黄诗逆笔说》云:
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势将伸而反蓄之。右军之书,势似欹而反正,岂其果欹乎?非欹无以得其正也。逆笔者,戒其滑下也。滑下者,顺势也,故逆笔以制之。长澜抒写中时时有节制焉,则无所用其逆矣。事事言情,处处见提掇焉,则无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陈,事所欲详,其不能自为检摄者,亦势也。定以山谷之书卷典故,非襞绩为工也,比兴寄托,非借境爲饰也,要亦不外乎虛实乘承、阴阳翕辟之义而已矣。[6](P298)
“逆笔”,从字面看易被理解为“历时变异”,但其实是与“时时有节制”、“处处见提掇”相对而言的。因此,黄诗之“虛实乘承、阴阳翕辟”的思维模式,可称作“共时对立”,即用极为隐晦的对立方式去强调诗歌语言的共时属性。尽管黄诗仍然依赖“书卷典故”、“比兴寄托”等修辞旧法,但在对立的原则下,形成了一些新颖而独特的修辞习惯:
一是“夺胎换骨”,即意与语的表里相对。释惠洪《冷斋夜话》卷1云:“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6](P32)这段定义暗含玄机:黄诗的“无一字无来处”,不是单纯的修辞手法,而是在意与语之间不断制造错位:学意则必造新语,学语则另换新意。这就从根本上制造出对立的共时层面,而不是简单的以古代今,以彼代此。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云:“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翠水,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孔稚圭《白苎歌》云:‘山虚钟磐彻。’山谷点化之,云:‘山空响管弦。’卢仝诗云:‘草石是亲情。’山谷点化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当姬妾。’学诗者不可不知此。”[9](P92)这几个“换骨”例子中,黄庭坚不改前人诗意,但选取了新的关键词,如“堆”、“空”、“朋友”、“姬妾”,意谓:我看到的湖面更有波澜,故称“堆”而不称“盘”;我听到的管弦是声大,不是钟声那种悠长,故称“山空”而不称“山虚”;我不是唯草石可亲的寒士,而是以山为友、以草为妾的精神贵族。又杨万里《诚斋诗话》云:“诗家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笔》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笔,用之抄书,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笔是也。《左传》云:‘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而山谷《中秋月》诗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9](P124)这两例属于“夺胎”:《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的前三句都用“猩猩”典故,第四句才出“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13](P149)所以,他写猩猩“爱酒”、“能言”、“著屐”,没把典故本身的讽刺和寓意带入,而只是借其字面强调毛笔材质所出。至于《八月十四日夜刀坑口对月奉寄王子难子闻适用》之“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13](P1147)同样悬置《左传》原意,以“龙蛇”比喻“寒藤老木”,显示月光之澄澈。以上两例,尽管黄诗另换新意,但典故中的趣味与壮美却保留下来,存留于意与语错位的夹缝间。
二是“以物为人”,即人与物的虚实相对。吴沆《环溪诗话》卷中云:“山谷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者,此所以擅一时之名而度越流辈也。然有可有不可。如‘春至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是用主人三请事,如《咏竹》云:‘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残暑已趋装,好风方来归’,‘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谓残暑趋装,好风来归,苦雨解严,诸峰献状,亦无不可。”[9](P163)又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载:“蜀人石翼,黄鲁直黔中时从游最久。尝言见鲁直自矜诗一联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晩年最得意,每举以教人。”[9](P46)吴聿《观林诗话》载:“山谷云:余从半山老人得古诗句法云:‘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9](P107)《王直方诗话》载:“方时敏言:荆公言鸥鸟不惊之类,如何作语则好?故山谷有云:‘人鸥同一波。’”[9](P24)可见,黄庭坚的自矜之句,他人的叹赏之句,往往都采取“以物为人”之法。这不是普通的拟人,而是特殊的影射,力图把士大夫的身份、尊严、趣味、观念贯注在自然形象中,正如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所云:“以草木文章发帝杼机,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虽百世之相后,犹使人跃跃兴起也。”[9](P144)此法亦是黄诗制造“共时对立”的惯式。
三是“避体就用”,即体与用的有无相对。释惠洪《冷斋夜话》卷4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见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9](P34)又方回《瀛奎律髓》卷21评《咏雪奉呈广平公》之“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云:“山谷之奇,有昆体之变,而不袭其组织,其巧者如作谜然,此一联亦雪谜也。”[9](P199)这种如同歇后语、谜语般的修辞习惯,融合用典、比喻为一体,步步回避事件或物象的本体,制造出最晦涩的共时层面。它比李贺的“代字”更抽象,又比欧、苏等人的“禁物体”、“白战体”更凝炼。也就是说,在其他人那里只是局部为之或偶一为之的修辞手法,到黄诗中组合、升华为修辞习惯。
综上所述,黄诗的修辞习惯主要包括“夺胎换骨”、“以物为人”、“避体就用”。可见,黄诗惯用错位、影射、回避等极为隐晦的对立方式去强调诗歌语言的共时属性,显示了“共时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尽管苏诗与黄诗在具体内容、形式、风格上拥有诸多相似特征,共同代表了宋诗成就,但就抽象的形式感而言,苏诗力求连贯、直露、单线,而黄诗讲究断续、隐蔽、复调。在这个意义上,黄诗缺乏“一唱三叹”的节奏和韵味,可亵玩而不可远观。
四、苏、黄与唐诗的关系
苏、黄的根本差异是思维模式的不同:苏诗重在“历时变异”,黄诗重在“共时对立”。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二者诗史地位的不同:苏诗超越宋诗,黄诗只代表宋诗。而二者诗史地位的不同,又将我们引向更多问题的思考:黄诗是典型宋调的代表,意味着“共时对立”也是宋诗的核心思维模式,那么,苏诗之所以超越宋诗,是否意味着他在思维模式上继承了唐诗的精髓呢?毕竟,“非唐即宋”与“唐高于宋”这两条不成文的定理占据了很多诗论家的头脑,而苏诗“一唱三叹”的节奏和韵味,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唐诗。
事实上,苏诗的诸多章法特色皆与唐诗大家消息相通。
首先,苏轼七古的章法最得李白真传。李白七古中充满议论式的“突转”。比如《梁甫吟》之“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山兜屼当安之”[14](P169),从绝望突然转向自信。又《梦游天姥吟留别》之“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14](P705)从“行乐”突然转向空寂,然后又转回“开心颜”。又《把酒问月》之“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14](P941)往返于短暂与永恒之间。又《江上吟》之“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14](P374)冲撞于脆弱与不朽之间。至于写景式“突转”,更是李白七古的拿手好戏。比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之“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14](P663)《行路难三首》其一之“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14](P189)《蜀道难》之“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14](P162)《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之“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14](P861)此外,苏轼《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之“归来诗思转清激,百丈空潭数鲂鲤”[9](P1234)以及《送张嘉州》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9](P1627)更是对李白丽句的直接模仿与搬用。
其次,苏轼五古的章法最受杜甫启迪。《杜诗详注》卷1引范梈论五古章法曰:“五言长篇,法有四要,曰分段、过脉、回照、赞叹。……回照,谓十步一回头以照题目,又五步作一消息语以赞叹之,方不甚迫促。长篇怕杂乱,一意为一段。以上四法,备于《北征》诗。”[15](P79)又据吴可《藏海诗话》记载,苏轼自己说:“作古诗当以老杜《北征》为法。”[3](P291)我们可以把苏轼《过淮》和杜甫《北征》作个对比:
苏轼《过淮》: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度千山赤。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黄州在何许,想像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独喜小儿子,少小事安佚。相从艰难中,肝肺如铁石。便应与晤语,何止寄衰疾。[9](P984)
杜甫《北征》(节选):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瞋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15](P400)
张佩纶《涧于日记》辛卯下卷评曰:“《过淮》诗若写己之肝肺铁石便浅,乃云:‘独喜小儿子,少小事安佚。相从艰难中,肝肺如铁石。’夫以小而安佚之儿子,尚能耐此艰难,何况于我。此缩临《北征》而无其迹者。”[3](P1586)二者都是在写行旅之苦时,斜逸出一段写家人之温馨,但很快又回望行旅,两相比较,愈见其苦。在以叙事见长的五古中,这种不断回环的章法特色是增添表现层次、容纳更多内涵的关键。它使叙事诗不再单纯讲故事,而成为社会史和心灵史的综合反映。
再次,苏轼七绝的章法最接近杜牧。杜牧七绝中,充满着活泼的“发现”过程。比如《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16](P1223)《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16](P545)《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6](P221)《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16](P501)以上七绝,前两句或前三句都故作不知,到后两句甚至最后一句才抛出核心形象或命意。此种先冷后热、先松后紧、先实后虚的章法特色,实为俊爽风格提供了重要支持。而《道山清话》载:“子瞻爱杜牧之《华清宫》诗,自言凡为人写了三四十本矣。”[3](P207)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评苏轼《和孔密州五绝·东栏梨花》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东坡固非窃牧之诗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11](P595)这些记载,都显示了苏轼学习杜牧的自觉与精勤。
要之,“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在唐诗中广泛存在,而苏轼对唐诗的学习,往往选取最具“历时变异”特质的诗人,面对同一诗人则选取最具“历时变异”特质的体裁,面对同一体裁则选取最具“历时变异”特质的作品。比如在所有唐人里,他最亲近李白;在杜、韩之间,他更欣赏杜;在小李杜之间,他更青睐小杜;在李白诗中,他最看重七古;在杜甫诗中,他更关注大处的“回环”,而非小处的“顿挫”。这些都说明他希望把“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发挥到最突出、最明朗的境地,使其诗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的沉重的宋调气息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涤荡。
如果说苏轼继承并发展了以“历时变异”为核心特质的唐诗思维模式,那么黄庭坚则完全抛弃了该模式,转而创立了以“共时对立”为核心特质的宋诗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根本置换,导致了黄诗与唐诗尤其是黄诗与杜诗之间关系的悖谬:一生崇杜、学杜的黄庭坚,却被一些诗学大家指为杜诗的最大叛徒。比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8云:“山谷所得于杜,专取其苦涩惨淡、律脉严峭一种,以易夫向来一切意浮功浅、皮傅无真意者耳;其于巨刃摩天、乾坤摆荡者,实未能也。”[6](P316)又周亮工《书影》卷2引钱谦益语曰:“余尝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6](P249)可见,黄诗学到了杜诗的“苦涩惨淡”、“律脉严峭”、“横空排奡”、“奇句硬语”,而丢掉了杜诗“巨刃摩天”、“乾坤摆荡”、“飞腾余波”的“真脉络”。也就是说,黄诗抛弃了杜诗所具有的“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而把杜诗对于修辞技巧的追求升华到思维模式的高度,最终形成“共时对立”的新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杜甫的“熟精文选理”、“语不惊人死不休”,与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杜甫一方面秉持“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一方面也开创了“共时对立”的思维萌芽,只不过,他把后者压低在具体形式层面,没有干扰其抽象的形式感。
综上所述,从思维模式看,苏诗与唐诗根本融通,黄诗与唐诗根本隔膜。因此,苏、黄的思维差异,昭示着唐诗与宋诗的本质分野。
五、对“诗分唐宋”的新考察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论宋诗曰:“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7](P26)这段话远不如“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诸语有名气,但其精辟性不容小觑:著名的那几句,恰恰只是内容、形式、风格层面的分析,而“一唱三叹”却涉及到了思维模式层面——唐诗的“一唱三叹”,宋诗的“有所歉焉”,不是简单的音律节奏或语法结构方面的差异,而是思维深处的语言运用模式的分野。
众所周知,语言原本具有历时属性和共时属性。在历时线索上,语言可以依次铺陈意义单元;在共时层面上,语言也可以同时叠加意义单元。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由于汉语天生的表意性、精炼性,以及集部传统对于“典故”、“出处”、“含蓄”的重视,其语言的共时属性被显著夸大了:当下诗句可以不连贯、不明白、不复杂,因为背后还有约定俗成的意义网络,可以弥补、增饰、充实。于是,当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高潮之时,便已出现了质变的萌芽——从杜甫开始,诗歌语言的共时属性越来越受重视;而到黄庭坚那里,共时属性超越了历时属性,意味着诗歌思维模式从“历时变异”转变成了“共时对立”。
然而,语言艺术归根到底是时间轴上的符号序列。语言与音乐的关系,要更近于语言与美术的关系。诗歌的历时线索,是首要的阅读体验。唐诗“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能够对历时线索形成根本强调和精彩修饰。此种“一唱三叹”的节奏和韵味,最鲜明地表现在李白身上,在杜牧那里有所压缩,在韩愈、白居易那里有所削弱,而在杜甫那里得到了更复杂、更微妙的展演,以至于产生了某种遮蔽或干扰的可能性,为黄庭坚所捕捉、夸大,最终形成“共时对立”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众多宋诗。而一味强调诗歌的共时层面,既不能像美术那样提供可感的物质空间,又会对符号的时间流造成阻碍,违背了语言艺术的本质属性。
总之,唐诗终究高于宋诗,苏诗终究高于黄诗,根本原因是:“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更符合语言艺术的本质属性。这就好比一首乐曲的灵魂,永远在于优美的旋律,而不是绚丽的和声。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A].唐宋诗论稿[C].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2]曾枣庄,等.苏轼研究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3]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M].滕守尧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6]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8.
[7]王力.诗词格律[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苏轼.苏轼诗集合注[M].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许学夷.诗源辩体[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1]曾枣庄,等.苏诗汇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12]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M].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
[14]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杜甫.杜诗详注[M].仇兆鳌.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杜牧.杜牧集系年校注[M].吴在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17]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