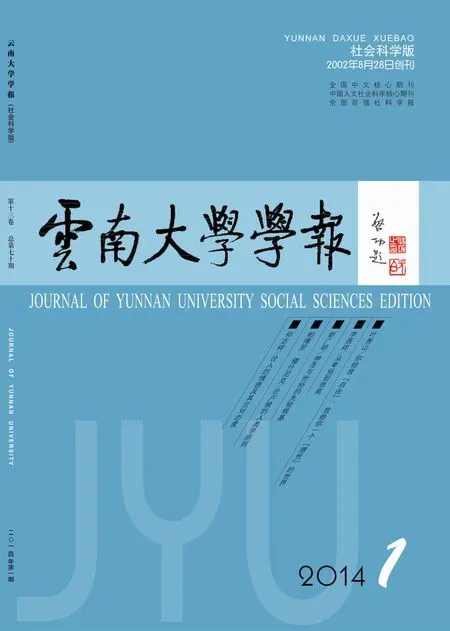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
——对定性研究①的反思
2014-03-06刘林平
刘林平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
《史记·太史公自序》言: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如果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评价,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司马迁提出了个人苦难和其文化成就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的假设(尽管他没有明说),并以某种类似弗洛伊德的“升华”思想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解释。
但是,司马迁的名言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指出其中的不完善之处:
1.不完全归纳。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比如老子、孙武等,根据司马迁本人的《史记》记载,没有听说他们有过特别不幸的遭遇,但其成就至少不在孔子和孙膑之下。当然,在普遍的意义上,所有的归纳都是不完全归纳,归纳都是一定范围内的归纳。②卡尔·波普尔说:“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3](P3)逻辑演绎之所以可能有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它所依赖的前提命题是由不完全归纳得到的。
2.没有考虑反事实问题。*斯坦利·利伯森说:“若结论是根据未发生的事件所做的断言时,哲学家称这种叙述为‘反事实的条件’。”[3](P52)而所谓“反事实条件”是指一种条件陈述,形式是“如果a,那么b”,这种陈述断言,“如果a已经发生了,那么b也会随之发生。”由于在反事实陈述中的“前提”不能满足,那么,对涉及这种主张的“结果”的经验评估就会有某些困难。这种似乎可能的陈述依赖于被引用的令人信服的、可以判别条件陈述的证据支持。[4]比如,屈原即使没有那些遭遇,是不是也还是个伟大的诗人呢?
3.没有控制变量。有过特别遭遇的人,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划分为两类,其一是有文化的,其二是文化(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后一类人取得伟大文化成就的概率很低,即使前一类人也不一定都可以成为哲人、诗人和思想家。所以,我们还要联系个人的教育程度、家庭和社会背景来进行分析,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我们还应该控制更多的变量。
所以,个人苦难和文化成就之间存在的较强的正相关的假设尽管伟大且具有强烈而积极的激励作用,但是否确定,还有待检验。
在上述分析的第二点中,我提到了反事实问题。谢宇在《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中说:
因果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事实问题。就是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你没有做这一件事情,情形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想组与组之间的差别,更要想同一组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差别,因为这是一个反事实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干预得到验证。[5](P40)
作为个体的个人(或群体、组织、民族、国家等),经历了某一件事情,就不能不经历这一件事情,比如,我曾经作为知识青年下过乡,这一段经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就始终存在并抹杀不了;同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或中华民族)就有了这一段不可能不经历的历史。然后,我本人(或我们民族)就会从我(或我们民族)的这一段经历中得出一些或显或隐的带有因果论断的结论,比如说,是上山下乡使我真切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村;又比如说,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等等。
这些结论对吗?可能对。但不确定。因为,我们必须反过来想一想,也就是必须考虑反事实问题,必须进行反事实思维。*反事实思维关注过去可能已经怎样,或现在会成为怎样,有什么不同。这样的思维通常由于人们的目的和愿望受到阻拦的负面事实所激发。反事实思维对情绪、信念和行为产生了各种影响,其中,后悔就是由此产生的最普遍情绪。当我们谈及“如果”或“几乎”,或使用诸如“可能”、“将要”或“应当”等词语,我们可能就已经在表达一个反事实的思考。研究者在两类反事实之间作出了区分:上行反事实指的是对情况如何变得更好的思考,下行反事实表达的情形是情况变得更坏。三种情景最可能引起反事实思考。首先,最常见的引发反事实思考的是负面情绪或出现麻烦的情景。当人们对一个负面的结果感觉糟糕时,他们通常会反思这一结果如何可能被避免。其次,反事实思考最可能发生于“失之交臂”或某事件几乎要发生的情况。因为当某些事情几乎要发生时,它可能会引发对替代性选择的思考。其三,当人们惊讶于某一结果,或当某一不同于人们之前预想的意外结果发生而引发对这一结果发生原因的注意和反思时,人们也会以“如果只……”的形式思考。发展心理学者相信,由于反事实思考与目标密切相连,孩童开始思考行动的可替代选择意味着他们开始对他们自己想要的和渴望的有所觉悟。反事实思考似乎还是跨文化的,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说,想象过去替代性选择的能力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普遍的,不论语言还是教养。反事实思考指出了人们认为什么造成了结果。例如,“如果我没有吃那么多薯片,我现在就不会生病了”这样一个想法暗示了吃太多薯片会导致人生病。当然,这些反事实思考可能是不准确的(流感可能是生病的真正原因),尽管如此,本能性地对反事实的思考具有感知“正确”的特征。许多反事实思考的结论已被研究——例如,对责怪受害人应为他们的不幸负责的偏见——可以根据反事实思考而获得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6]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就真的不能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了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会中断吗?
结论当然是不确定的。但是,我本人已经经历了上山下乡,而中国也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从我们自身的立场已经没有办法验证这个反事实的假设了。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说的是,河流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我们在那一刻踏进了某一条河,我们就不能同时不踏进那一条河。那一条河是否在流,对我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分身乏术,我们在某一刻只能做某一件事情,而一旦我们做了某一件事情,我们就不能不做那一件事情。这就是人生的遗憾,是万事万物的自然,过去了的,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从头再来,而即使是未来,我们也只能像过去那样踏进了某一条河流就不能不踏进那一条河流。
这种人生的遗憾,转变成了一种思维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反事实问题的存在,我们从个体层面就不能得到确切的因果关系。所以,谢宇说:“在个体层面上你根本不可能得到因果关系,因为你无法找到反事实情况下的同一个个体作为对照组。如果你已经读了大学,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如果你不读大学的收入情况会是怎样的。”[5](20)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模拟式启发(The simulation heuristic)”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20世纪的哲学家对反事实问题十分着迷,反事实问题涉及逻辑与自然、起源以及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对反事实的心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学界认为这种思维对人们如何理解过去、预测未来及理解他们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有关键意义。[6]
利普认为,因果理论是以反事实推理为基础的,各种归因理论都可以看成是反事实思维的一个特例,反事实思维可以作为归因推理理论的一种框架。[7]
斯坦利·利伯森也说:“不管喜欢与否,反事实条件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不断地为未曾发生的事件行为做结论。真正的也好,模拟的也好,所有的实验都是基于反事实的条件。这两种实验法都是透过比较来评量某些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因果影响。”[3](P55)
尼尔·弗格森曾经叙述了人类(主要是西方)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决定论思想和反事实思维的发展过程,他说:
宗教历史学家把神的作用看成历史事件根本的(不过未必是唯一的)原因;唯物主义者用类同于或者派生于自然科学术语(例如普遍法则)的解释理解历史;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史学家通过想象将过去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论的)结构。然而,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超越了这一切分歧的共识:这三种思想流派都认为“假如……将会怎样”式问题纯属一派胡言。[8](P6-7)
“假如……将会怎样”是反事实思维的一种典型的提问方式,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这种提问方式的确是有问题的,历史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卡尔认为,历史是一个人们做了些什么的记录,不是人们没有能做到什么的记录。[9]
但是,在历史学家那里,总是有人要不断地提出反事实问题,“假如我们想不调用普遍规律而对过去的因果关系发表看法,就只有使用反事实推论,即便只是为了测试对因果关系的假定。”[8](P100)而在弗格森看来,真正运用反事实思维取得历史领域研究成就的是福格尔,他说:
新经济历史的阐释者对反事实论辩进行了可谓全新的运用。率先以严肃态度冒险进行数量的反事实论辩的是R·W·福格尔,他研究的是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他构建了一个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对铁路在美国工业化中作用不可或缺的传统看法提出挑战。……这种反事实的最终作用是通过在总体上量化铁路对经济的(相当大的)贡献,昭示铁路之所以被建造的原因。[8](P23-24)
福格尔对美国铁路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反事实的,同时是定量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个案不能验证反事实假设,只有多个个案才有可能。所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回到谢宇所讲的:“统计学虽然不完美,但却是社会科学刻画异质性唯一可靠的工具。……在个体水平上,反事实结果是不可能被评估和证明的。……定量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没有定量的方法就没有科学的东西。”[5](P27-28)
单一个案不能解决反事实问题,也就不能得出确定的因果关系,这是定性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难题。
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中国人并不缺乏反事实思维。*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西方心理学界,就土生土长说汉语的人是否能使用反事实思考曾经发生过争论,因为汉语中缺乏一个专门的词表达“如果就”。[6]后悔是平常人常有的一种情绪,后悔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反事实的,后悔者总是会想,我当初要是不这么做或那么做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结局了。鲁迅在《祝福》中所塑造的祥林嫂,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她的孩子被狼吃了以后,祥林嫂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真傻,真的”,所表达的意思是,要是当初她好好照顾孩子,就不会有那样的惨剧发生了。
但是,在理论思维的层面,反事实思维却很少见到。我将《论语》和《老子》重新读了一遍之后,竟然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反事实思维的语句。
我认为,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其一,孔子的思想以伦理说教为重,他告诉人们的是应该怎么样,而不是追究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当然就用不着反事实思维;其二,在老子那里,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他已经先天性地给定了一个抽象的“道”,所以也用不着追究具体事物的因果关系,当然也就用不着反事实思维;其三,中国历来缺乏定量思维,在实际上难以解决反事实问题,当然也就难以发展出那样的理论思维方式了。
我们说单一个案无从解决反事实问题,是因为单一个案无从进行比较。毛泽东也说过,“有比较才能鉴别。”[10](P416)比较是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比较。*迪尔凯姆说:“科学调查只有针对可以比较的事实才能达到目的,而且越是有把握汇集那些能够有效地进行比较的事实,就越有成功的机会。”[11](P7)比较和反事实思维是紧密联系的,“比较法就是一个制造反事实条件叙述的研究法。”[3](P54)定量研究中的模型,就是将理论上确定有关联的变量,装进一个篮子里进行比较,这些变量有不同的分类,类与类比较是否具有差异性,进而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因果关系。
定量研究必然是多个案的,*根据统计学的标准最少要有30个个案,或100个个案。所以它能进行比较。定量研究也必然是反事实的,简单来说,因为它在逻辑上至少要分成两组,一组有某一经历,另一组没有,然后进行比较。比如,一组是大学本科毕业,另一组非大学本科毕业,然后我们才能看大学本科毕业对这两组人的影响。
定性研究的个案数较不确定,当然最少要有一个。*在2006-2007年《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96篇“论文”中,共有实证的定性研究的论文32篇,占所刊“论文”的三分之一,其中只有一篇明确说是比较个案研究(应星,2007),一篇是四个个案的对比研究(王卫平、黄鸿山,2007),还有三篇是多个案研究(金一虹,2006;毛丹、王燕锋,2006;陶传进,2007),其余的27篇都是单一个案研究。但是,由于有反事实问题的存在,单一个案不能评估和证明因果关系,所以,定性研究也必须是比较研究,才能具有某种科学的“合法性”。杰克·古迪说,“比较研究还是我们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中所能够做的可与科学家们的实验相媲美的少数几桩事情之一。”[12](P15)
比较最基本的条件是至少要有两个个案,这两个个案有相似之处,又有相异之处,才能进行比较。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和理查德·列万廷说:“事物是相似的:这使得科学成为可能。事物是不同的:这使得科学变得必要。”[13](P14)相异之处好办,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相异是绝对的,我们可以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因为这个前提条件容易满足。相似或相同之处呢?这个就难办了。我们要比较上大学对两个人的作用,一个上了大学,一个没有,上了大学的人收入高,没有上大学的人收入低,上大学对收入有正向影响,如果简单地做这样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那个没有上大学的人可能智力水平就低很多,相对能力也要差很多,当然收入就要低一些。所以,比较是要在相同或类似的个体中进行,找出同中之异,这就是控制变量的概念。
北京奥运会开得很成功,奥运会的规则公平是前提条件之一,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控制变量,至少要控制性别,也就是说,男子和男子比,女子和女子比。中国男子足球踢得很正常,输了,我们可以接受。巴西女足、很厉害,如果中国男足去踢巴西女足,我以为,赢的概率很高,但是,人们不能接受,因为是男子和女子比。我在看举重比赛时,男子、女子,体重又不同,弄出那么多级别,我猜想,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可能是个统计学家,深懂控制变量的精髓。
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一到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就变得非常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最简化的情况来说,我们比较两个个体(最简单的就是个人)的同中之异,其中的“同”是难以控制的,性别、民族、党派、教育程度等外显的个人特征,较为一目了然;然而,人有很多内在的东西,他的动机、态度、智商、情商等内隐的东西,就较难了解;如果我们再引入时间变量,也就是说,人在时间中是变化的,那当然就更难了;还有,人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环境又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又可以分大环境和小环境,人和环境的关系又不是单向的、静止的,等等。当我们将个体、时间和空间一并考虑,来比较同中之异,这怎么不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呢?
如果要比较的个体不是个人而是组织、民族或国家,我们就还得考虑系统效应,[14]因为组织并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民族和国家就更为复杂。
此外,我们用什么标准来确定“同”和“异”呢?“比较所涉及的问题是‘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性具有不确定性,而差异性又不计其数。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可信标准来确定‘相似性’和‘差异性’呢?”[15](P14)
还有,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很少有单一的原因与结果。“雷根(Ragin)宣称,在史学中使用严格的比较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学或者史学中的因果假设通常是多重原因的组合。严格地考察包含着那些组合的假设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给所有可能的组合提供证据。”[16](P278)
当然,上述的困难并不是定性研究所独有的,定量研究也同样如此。可是,定量研究在不断地发展它的技术,力图克服这些困难,在统计模型中,它会将纳入模型的变量在技术上加以控制。定性研究则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变量的技术手段,所以,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它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洞察力。而在中国,在定性研究中要控制变量的理念都不普及。
据说,在美国,人们为了严格地控制变量进行比较,就找来双胞胎或多胞胎进行研究。双胞胎的优势是明显的,年龄、长相、智商和最初成长的家庭或社会背景都相同或类似,这样的“同”是普通人难以比拟的。但是,双胞胎出生的概率较小,他们是否可以代表普通人群呢?当一大群双胞胎和多胞胎的孪生子女聚集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成立一个类似于女权主义或同性恋的组织而开Party,而是为了社会科学研究,我们中国人要是看到这样的情景,是会大吃一惊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或较为缺乏控制变量的严格比较的概念。
三
思想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马克思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应用了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他的话语似乎提出了一个学科科学化的“合法性标准”:是否运用数学语言来表述。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海登·怀特的著作让我思考:日常生活语言是否可以进行科学表述?
在前面,我提出了反事实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单一个案不能得到因果关系。那么,退一步,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但是,比较必须控制变量,而定性研究的方法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变量的技术手段。那么,在定性研究中,我们对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对于因果关系的认知,凭借什么呢:是我们的直觉?是灵感?还是归纳?抑或逻辑推演?
要说清楚定性研究中的思维过程是很难的,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定性研究的结果是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表述的,*当然,对这一点,有人也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艾维尔泽·塔克尔就说,“史学也不是用日常语言来写作的。”[16](P193)或者换句话说,定性研究的结果不是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的。因此,我必须重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常生活语言可以进行科学表述*迈克尔·马尔凯说:“科学正式、公共的话语,被认为体现了文化中有效知识的集合,故风格上具有非个人性、内容上具有技术性,价值取向上具有中立性,而且总体上给人以非社会的自动产生而非由有血有肉的人类所创造的印象。这种正式语言……在科学家最终获得对文化的优势上是一种关键的修辞资源。”[17](P343)当然,他对科学话语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又说:“科学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在本质上是非反思性的。科学是一种掩盖和否定它自己语言特征的语言形式。科学作为知识的一种,掩盖和否定其创造者的社会以及其内心体验。”[17](P46)吗?
海登·怀特在其伟大的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是特指历史学的,不过,我认为,他的论述也基本适合一切的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作品。
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18](P1)
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将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18](P2-3)
海登·怀特把历史著作的本质理解为“诗性的”、“修辞性的”和“文学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鲁迅也做过类似的理解,他将司马迁的《史记》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在这里提到鲁迅,并不是要用一个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去佐证美国的一个伟大史学家,而是想说明,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似乎不是一种巧合。
海登·怀特之所以做出上述论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现象》一书中分析了黑格尔、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等八位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逐一分析并验证其论断。
海登·怀特的论述逻辑是,历史著作是用日常语言写作的,日常语言是比喻性的,*海登·怀特说:“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关于诗性语言或比喻性语言的分析确定了四种基本的比喻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些比喻允许以不同类别的间接性或比喻性话语来表述客体的特征。”[18](P41-43)他又说:“人们需要隐喻性的表达来描画对于世界的体验当中最为复杂难解的方面。没有隐喻,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简单陈述句中得到表述。并没有非隐喻性的语言这么一种东西。”[19](P29)这种语言有它构成的“句法”、“语法”和“语义学”,历史事件的叙述其实是讲“故事”,“故事”怎么编排,取决于讲述者的理论逻辑和编纂风格。“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他预构了历史领域,并将它设置成施展其特定理论的场所,他正是用这种理论来说明在该领域中‘实际发生了什么’。”[18](P2)这么说来,历史学家就像一个时装设计师,先建构了他的图式(理论模式),然后再照此来剪裁布料(历史),再剪裁好了之后,再来缝补拼凑完成作品(表现历史)。不同的时装设计师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历史学家也一样。这种预先建构的理论模式或理论逻辑之所以是“诗性的”,是因为“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它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18](P40)说白了,大多数历史学家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图式和剪刀去剪裁历史并没有认真反思过,更没有确证“图式”和“剪刀”的可靠性或“科学性”。这使人不得不想起似乎是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管我们是否认同海登·怀特的论断,不容忽视的是,他实现了所谓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用日常语言表述的历史作品是“诗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
海登·怀特的论断可以适用于一切用日常语言表述的定性研究作品。任何用日常生活语言写作的“科学”论文或著作,都是一个“文本”,*默顿说:“社会学企图生动地描述人类丰富的全部画面的传统,造成了社会学论著冗长啰嗦而非言简意赅的状况。这一传统很少是从哲学,实质上是从历史,大部分是从文学那儿继承来的。那些继承这一可观外来遗产的社会学家执著地寻找绚丽惊人的词句,以最完美地表达研究中的社会学现象的特殊性,而不是找出客观的概括性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科学的内核,使其区别于艺术。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用错了地方的艺术技巧取得了公众的称赞,他们常常鼓励社会学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文笔像小说家……而社会学家越迎合这种公众的赞扬,越近于口若悬河……”[20](94)作为文本,它有一套语法、句法和修辞的规则,它的概念不可能是“精确的”,*迪尔凯姆说:“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始终是模棱两可的。”[11](P7)而更可能是“多义”的,由不确定的概念所构成的语句和文本,所叙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是不“准确的”。它的语言中或明或暗地借助于“比喻”,大理论家或思想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修辞风格”,都有自己的“语法”和“句法”。由这样的一套修辞规则所写作出来的文本,是文本的作者所看到的世界或事物,与真实的世界肯定有某种差异。但是,定性研究者只能通过“文本”来表述客观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就是文本。
语言是什么呢?汉斯·凯尔纳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语言不是帮助我们直视事物的望远镜,而更像是拼凑碎片、在不同时间呈现给我们不同事物的万花筒——那是一种总是不断变动的图景,永远也无法将其恰当地变为一个整体,因为你碰一下万花筒,它就又进入新的局面。”[19](P56)
语言不是望远镜,而是万花筒。这个比喻的确形象、生动。万花筒是变动不居的,是色彩鲜艳的,是丰富多彩的。但是,万花筒使我们眩目,使我们充满好奇,它给了我们一个幻象中的世界。
当然,这样的比喻很可能是错误的,汉斯·凯尔纳自己就说,“比喻学研究的是,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是如何生活在错误之中。我们在使用字词时,不是在撒谎,然而我们是在错误之中。我们是在以幻象的形式来谈论真实。……语言的使用必定是错误的。反讽是某种视界的一种纯然理论性的模式和理想化的比喻,那种视界像所有其他的视界一样对我们而言是不可能的。”[19](P74-75)
对语言表述客观事实和真理最极端的否定,在中国文化中,也许来自于佛教中的禅宗。由达摩东渡而传入的禅宗,其基本立场是“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21](P10)禅宗的中国本土化是以六祖慧能为重要代表的。《六祖坛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盘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
慧能是个文盲,不识字,他认为佛理与文字无关,这不奇怪。令我们惊奇的是他的思想,倒不在于他的记忆力有多好,悟性有多高,而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真理是否要用日常语言来表述?
禅宗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怀海(720-814),他用下面的话语表述了禅宗哲理:
灵光独耀,迥脱根尘.
体露真常,不拘文字。
心性无染,本自圆成。
但离妄缘,即如如佛。[21](P133)
“不立文字”的做法很难让人接受,实际上也行不通,你有思想,有主义,或有研究,总得用某种形式来表述,不能老用肢体语言,打哑谜,当然,即使是顿悟,打机锋,当头棒喝,也可以视为是某种另类的“文字”。“不关文字”的说法,的确有其高明之处,这就是说,我们不要被真理的外在形式所束缚。而“不拘文字”的思维最为正常,这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文字表述,也可以不用文字表述,你可以用日常语言表述,也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述。当然,我猜想,怀海大约没有想过要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禅宗哲理,尽管中国古代有些和尚是很厉害的,实际上是当时的科学家。
四
如果说我们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科学研究有很大困难或不可能的话,那么,在汉语里就尤其如此。
汉语的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是从图画发展而来的,它最初适合表达具体的东西,而不适合或很难建构抽象的概念。象形文字适合艺术性的表达,比如书法成为高超的艺术,龙飞凤舞,就说明了这一点。
汉语的最小单位是字,而不是词,词是由字组成的,也就是说,抛开那些单个的字的概念,词所表述的概念,最少由两个字组成,既然有两个字,就比西方语言(英、法、德、意、西等)以词为基本单位的概念,在结构上更具有多义性。而且,“汉语的名词及形容词没有明显的单数与复数、阴性与阳性的区别。……一个词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和动词。这种不确定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产生复合词的必要。汉语的多义性,也是由于这种暧昧性而产生的,并成了一种显著特征。”[22](P241)
因此,林语堂说:“中国文字既属于单音组合,殆无可避免地必须用象形字体。单是这个事实,大大地变更了中国学术的特性和地位。”[23](P201)
适合艺术性表达的语言,必然是诗性的。也由于字组词以及词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所以汉语词汇丰富多彩,如果运用恰当,可以写出非常漂亮的诗词文章。因此,我赞成辜鸿铭的说法,“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24](P106)
但是,诗的语言尽管浪漫,却可能不准确,更可能不适合科学表述。“这种装饰文字所谓骈俪文的格调深具表现精确性缺乏之弊病……故从英文译为中文,其中最感困难者为科学论文。”[23](P77)另外,这种语言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使得我们徒增很多烦恼,经常为了经典中的一个字、一个词而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中村元说:“中国人在对古代经典字句的理解上,相互对峙的见解常常争执不休。”[22](P241)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也算读过不少的著作和论文,其中的大部分争论,我以为,是词义的含糊或多义所引发的,并非是主义之争。如果我们的论文或著作,将关键的概念定义清楚,最好是能操作化,学者们就可以少费很多口舌,少打许多口水仗,而真正去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中国古代难以发展出现代的自然科学,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所使用的文字,这种艺术性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留下了不少的哲学伦理经典,留下了世界上少有的丰富的历史记述,科学作品却较之大大逊色。
如果说日常语言是充满比喻的,那么,在汉语中,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本的特点之一,就是说理的比喻性。
一个典型的文本是《老子》,其中到处都是比喻和类比思维。我们且举几例:
上善若水。(《老子·第八章》)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第三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
中国有不少人的名字叫“若水”,大约就是来自于老子这句“上善若水”的名言。比喻其实是一种矛盾或辩证的思维,*利科说:“隐喻的‘是’既表示‘不是’又表示‘像’。”“我们应该把相似性本身理解为由语义的更新推动的述谓活动之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25](P4、6)当老子说“上善若水”时,显然他并不是要给出善的定义,而是给出了善的一种比拟物,也就是说,善和水是类似的,但并不是水。由这样的一种比喻,我们可以生发出对于善的想象,并把这种想象和自然界中的水联系起来。但是,这并不能严格地定义善,更不可能给出善的操作定义。
文革期间有一首流行歌曲唱道:“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里的逻辑联系令人费解,鱼是离不开水,怎么国之利器就不可以示人呢?它就是一个类比,到底恰当不恰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几乎所有的类比都有这样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我觉得那几句歌词更好一些,但是,由鱼水关系和瓜秧关系推理所得到的结论“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却又搞错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共产党离不开人民,人民是水、是秧,党是鱼、是瓜。
我上面所引老子的第三段话,其逻辑更加混乱,我这里不作分析,只是想说明,类比推理是靠不住的,这么经典的类比都靠不住,何况其他。即使比喻或类比得很恰当,也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有几句名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他的结论我很赞成,但是,我们能从泰山之高、河海之深的由来逻辑地推论出王者之德吗?不一定。我们也可以从泰山之高得出结论:王者要是只将老百姓做垫脚石,一点都不爱护,又怎么会有德呢?
中国古代文本的另一个特点,是过分追求对仗和工整。“中国学者……极为重视形式的齐合性。”[22](P293)我们读古代的诗,尤其是七律,甚为佩服其用字的功夫,中间的四句必须是工整的对仗。古人做诗讲究推敲,一个字一个字地去用心,对出了不少绝对。这种对诗文的要求,转化成一种思维方式,也就用一种工整的要求去剪裁、整理事物,比如阴阳五行的观念,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两分(阴阳)的、五分(五行)的。其实,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事物的分布是随机的,既有两分的,如男女、雌雄;也有多分的,如中国有56个民族,人的年龄则可以从1岁到100岁(甚至更大),等等。但是,中国的传统思维好像缺乏多分的概念,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没有连续变量。毛泽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他特别坚持两分法,实际上是坚持中国古代的阴阳二分的概念,我认为,之所以这样坚持,原因之一就是追求工整和对偶。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这个说法比两分法更恰当。但是,他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这就是追求工整的五分法,和实际事物是有差距的。“在自然现实中‘对称过程’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罕见的例子’。”[15](P62)
对于这种追求思维形式的完整及其表述的工整,鲁迅先生有所认知,他说: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沈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26](P191)
世界本不完美,非要显得完美,就只能说是“病”。
这种“病”表现为漂亮的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看起来工整、对仗和完善,实际上离真实的事物及其关系已经非常遥远。这是典型的“以辞害意”,追求的是思维形式的完美和文辞的完美,而不是真实、客观和准确地表现事物及其关系。
五
如果将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由于反事实问题的存在,单一个案不能确定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的困难在于控制变量,而定性研究缺乏控制变量的技术手段,定性研究的结果是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的,但日常语言(尤其是汉语)是诗性的,进行科学表述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
但是,这样的结论可能遇到的诘问是:那么,社会科学还要做定性研究吗?定性研究还有用吗?
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回答,正是因为定性研究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要改进,我们要用比较研究来取代单一个案研究,在比较研究中要有意识地控制变量,既然日常语言难以准确地进行科学表述,那么,就要改进文风,用词要准确定义,不要单纯地追求文章的形式漂亮,等等。
可是,这样的回答是很不够的。因为,我所提出的定性研究的上述问题或缺陷,在目前的思维水准上是难以克服和改进的,或者换句话说,这些问题是“存在论”的,而不是“认识论”的,是根本的思维模式缺陷,而不是思维的技术性缺陷。
进一步说,我之所以指出定性研究的缺陷,主要是为这种研究方法划定其能力边界,知道定性研究之不可为之处。
我认为,定性研究是有根本性缺陷的。*当然,定量研究也有根本性缺陷,由于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主题,留待今后讨论。社会科学在进行实证的定性研究时必须面对这些缺陷。对这些缺陷的克服,也许就是社会科学前进的动力。
当然,定性研究也许还不科学,它也的确有着根本的缺陷,而思维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透视自身的缺陷,世间本无无缺陷的东西,有缺陷自有其缺陷美,对称(完善)的美只是特例,而一切宣称自己是无缺陷的东西最后必然沦为笑柄。
参考文献:
[1]诺曼·卡·邓津、伊冯娜·S·林肯.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3]斯坦利·利柏森.量化的反思:重探社会的逻辑[M].陈孟君译.台北: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996.
[4]David Jary & Julia Jary:Collins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
[5]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Fessel, Florian & Neal J. Roes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ncyclopedia of Social Psychology. SAGE Publications 2007.
[7]Lipe.M·G.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as a framework for attribution theor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1,109(3): 456-471.
[8]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M].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9]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1]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2]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主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C].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4]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M].李少军,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1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M].王昺,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16]艾维尔泽·塔克尔.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M].于晓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8]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9]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C].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0]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M].何凡兴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1][宋]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M].林太,马小鹤译.台北:淑馨出版社,1999.
[2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2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5]保罗·利科.活的隐喻[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6]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