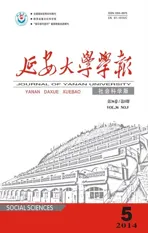《醒世姻缘传》薛素姐形象之女性主义解读
——兼谈明清家族小说中悍妇形象的话语模式
2014-03-06牛景丽阮丽萌
牛景丽,阮丽萌
(1.河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律学院,天津 300401;2.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古代的“悍妇”故事由来已久、流传甚广,至明末清初西周生之《醒世姻缘传》,可谓将“悍妇”的刻画推向极致。从字面含义来看,所谓“悍”,即凶悍、野蛮;而“妇”,《尔雅·释亲》解释为“女子既嫁曰妇,妇之言服,服事于夫也。”《本命》有云:“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妇”者,服从,顺从,与凶悍是根本矛盾的。词义本身的相悖,正说明了“悍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否定、被批判的境遇。在男权社会下,任何关于女性的描述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男权中心色彩。“不言而喻,直到最近为止,文学中的妇女形象都是男人塑造的”[1]。无论是“天使”也好“恶魔”也罢,无非都是出自男性的想象。“悍妇”一词,即属于男性的创造。本文旨在以女性主义之视角重新解读《醒世姻缘传》,分析“悍妇”形象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及文化内涵,反思中国传统女性在男权话语中的生存境遇与人生价值,从而对明清家族小说中的“悍妇”形象的话语模式做出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一、“悍妇”班首——薛素姐对男权中心的反抗
儒家所崇尚和奉行的“三从”“四德”是对传统女性的最具约束力的制度规则,毫无疑问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最直接的体现,女性在这里毫无人身自由、精神独立可言。“在两性权利关系中,女性群体的受虐,已被社会伦理道德合理合法化,权利压抑导致受虐一方只能采取家庭暴力手段。”[2]《醒世姻缘传》中的以薛素姐为代表的众多“悍妇”即是以暴力行动表现出了对于“三从”“四德”的反抗。
1.对于“父权”、“夫权”的反抗
未嫁从父。儒家传统道德要求子女要对父母表示尊敬,绝对不允许忤逆父母,即使家长的决定是错误的也要无条件服从以示孝敬。在素姐出嫁前夕,薛教授曾苦口婆心的对素姐进行了一番关于出嫁之后要宽容处理与丈夫的关系、不能悍妒泼辣的教导(44回),可素姐出嫁后的种种野蛮凶悍的作为俨然是对这番儒家陈腐说教的反叛,丝毫没有把父亲的教诲加以践行。当薛素姐由于狄周媳妇怀疑小玉兰偷鸡而痛打小玉兰时,连薛教授的劝阻也听不进去,甚至还顶嘴薛教授道“嫁出去的女,卖出去的地,不干你事!脱不了一个丫头,你又将的去了!刚才要不是你敦着腚,雌着嘴吃,怎么得少了鸡,起这们祸?”(48回)素姐把自己出嫁后的不幸全部归罪于父亲,骂父亲说:“他爹是老忘八,老烧骨拾的,把个女儿推在火坑里,瞎了眼,寻这们个女婿。”(52回)事实上,素姐的这种表现有些不近人情、难以被世人所理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薛教授是薛素姐婚姻悲剧的直接导演者,素姐婚嫁后对于父亲的态度也正是她满腔怨恨的喷射。
既嫁从夫。儒家传统美德要求既嫁女子顺从尊重自己的丈夫,而《醒世姻缘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让人感到最触目惊心的便是薛素姐等“悍妇”对于本来是“天”的丈夫的花样翻新的虐待和折磨方式。但凡狄希陈有一点不合她心意便大肆惩罚,有时是将丈夫踩在地上用鞭子狠狠抽打一番,有时又“使腚坐住头,从上往下鞭打”,直打得“狄希陈脊梁上黄瓜茄子似的,青红柳绿,好不可怜”,使得“那狄希陈一片叫声爹娘来救人”(48回)。有时候会动用钳子,把狄希陈“拧得那通身上下就是生了无数紫葡萄”(60回)。后来竟发展到拿箭射向狄希陈,险些使其丢了性命。素姐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放眼整个“悍妇”发展史来看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夫权”的反抗还有一点突出体现便是素姐对于所谓“贞节牌坊”的不屑一顾。对于张大张二夫妇由于孝道而获得旌表时,素姐用鄙夷的态度说道“我也做不成那孝妇,我也看不得那牌坊,我就有肉,情知割给狗吃,我也做不成那汤!精扯燥淡!”叶绍钧在《女子人格问题》一文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义。一种是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的人格,叫做‘诱惑主义’。一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不承认他是和己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他的人格,叫做‘势力主义’。”[3]关于第一种“诱惑主义”最为典型的便是名分,而素姐丝毫不在乎自己会被丈夫休妻与否,对于男性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贞洁观念也是嗤之以鼻,其对“夫权”制度的反抗可见一斑。
2.对于“四德”的反抗
“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不过是男权社会为女性设定下的一套规范准则,依郑玄所言其核心便是“贞顺”,对丈夫保持贞洁,对翁姑表示孝顺。及至清末,其内容又被丰富,多了“去妒”“安贫恭俭”“重义”等含义。
对于“妇德”所要求的“贞顺”而言,素姐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可以看作是一种彻底的颠覆。素姐对于孝道的反叛还能体现在她对于公婆的态度上,骂婆婆是“养汉老婆”(52回),当公公娶妾时骂公公“没廉耻老儿无德,鬓毛都白了,干这样老无耻的事。”(76回)更有甚者,由于担心公公娶妾生子会分割家产,竟昼夜算计要阉割了公公,如此野蛮行径把婆婆气成了半身不遂、把公公气得最后一命呜呼。至于“去妒”,对于素姐而言更是比登天还难,素姐所有的剽悍行为刨根究底还是一个“妒”字。“妒”是其之所以剽悍的心理根源,而“悍”则是其“妒”的外在表现。她不允许狄希陈与其他女人有联系,对狄希陈步步紧逼到了变态的地步,由此可见,关于“妇德”的核心要求素姐无一能做到。再来看看“妇言”,最本质的便是要求女性可以说话得体,可是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素姐也算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小姐,自小也受到了父亲的谆谆教诲,但是从其话语流露出的却是污言秽语,她骂丈夫、骂公婆、骂父亲、骂婢女,种种话语可谓是不堪入耳,儒家传统所要求的谨言慎行在她这里可谓消磨殆尽。至于“妇容”,在素姐身上是丝毫看不到有任何庄重,素姐不论在任何场合都敢撒泼耍狠。从书中描述来看,也没有关于素姐劳作的描写。
总而言之,薛素姐与历史上其他作品中的“悍妇”相比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素姐的这种反抗和凶悍是坚持到底的。这样持之以恒的反抗在中国“悍妇”历史上并非经常之事。不过,尽管薛素姐的某些悍妒行为体现为一种叛逆或反抗精神,但有的行为只是一种朦胧的潜意识里本能的反抗,而不是反抗意识明确的斗争。[4]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主要有三:争取恋爱自主权,争取人格独立权,争取社会参与权。[5]而素姐在这三点的争取上的行为显然都是不自觉的,并不是主观意识明确的斗争,所以她并不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
二、“恶魔”自毁——男权制度下薛素姐的宿命
西周生作为一个传统男性,在作品中所恪守的价值观依然是男权伦理道德。因此,作为“悍妇”之班首的薛素姐,不过是男权社会中的为人唾弃的怪物,其结局只有毁灭。
1.“悍妇”——邪恶女性之标签
小说还有另一个名字《恶姻缘》,赋于素姐“恶”的标签。作品在貌似处处凸显女性之强悍与男性之无能的叙述中隐含着作者的感情倾向,那就是对于“悍妇”的批判与嘲讽。
书中第8回谈到了小青梅的价值观,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无论是嫁与人做妻做妾还是为娼为妓都是十分不自在的,处处被拘谨的很,索性不如做了姑子来的自由。这是一段颇具女性解放色彩的言论,表明了女性开始从自身需要角度出发选择自己的命运和道路,在今天看来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但作者却对此表示出了一种鄙夷,甚至为了直接表现出自己的鄙夷而在后文中把出家后的小青梅,即海会姑子写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爱挑拨离间的邪恶女人,写她到处结交宦门妇女好吃懒做的丑习,甚至把她归罪为害死计氏的帮凶之一,还让她因计氏官司受到了种种惩罚,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由于自己的男权思维对这种思想违逆的女性所持有的偏见。对于素姐等众人,作者更是抱有一种看怪物杂耍的心态,在素姐众人逛庙会时用语言描写百般嘲讽,直至让其当众出丑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蔑视。纵览全书,书中出现的女性角色大多都是处于这种被批判的地位,细数起来可能晁奶奶和童奶奶算是作者持褒扬态度的。晁奶奶被塑造成了一个具有菩萨心肠的老妇人,慈悲为怀并宽容大度,不仅照顾穷亲戚,在灾荒年月还救济乡人。不过,无论是“天使”还是“妖魔”,都是男权社会中男子对于女子的想象和定位,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男性需要。一旦女性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体现出了反叛,便会成为他们所认为的“恶魔”。把女性写成“悍妇”,男性在这里主要是充当了两种角色,一种是在文本中大肆宣泄女性“恶德”寻求快感,一种便是作为一种隐含作者充当卫道士以警醒后人。
2.缘于恶,终于毁——男权意志下薛素姐的毁灭之路
从故事情节发展来看,表面上薛素姐对于狄希陈等男性的折磨越发严厉,实际上则是男权社会对于素姐的惩罚越发严苛。
从表象来看,素姐从一开始的不让进房掌掴责骂,到后来动用酷刑直到最后险些一箭射死狄希陈,其剽悍程度似乎是愈演愈厉,暂且不论这是否有夸张成分掺杂其中,读来也是令人咋舌。如果我们变换立场以薛素姐的角度重新来思考,就会发现素姐在这个过程中是节节败退的。从一开始接受家长安排不情愿地嫁给狄希陈,素姐率先面对的就是婚姻不自主的责难。及至成亲之后为了发泄不满而虐待狄希陈,在私愤未曾畅快宣泄时便遭到了众人的责难甚至还一度遭到了相大妗子等人的毒打教训,肉体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争夺外交权的斗争中,自始至终她都没有获得人们的认可,甚至还遭到了一群流氓光棍的侮辱和殴打,素姐丢尽了颜面,受尽了白眼。甚至在最后,素姐为了寻求公道诉之于官府得到的结果,竟是太守的一顿教训以及张榜公示带来的又一番耻辱。显然对于素姐的惩罚已经渐渐的从家门扩展到了社会,从平民发展到了官府。至狄希陈偷娶童寄姐,素姐之前苦心限制狄希陈接近女性的努力宣告破产。童奶奶等人还合计将素姐欺骗,寄姐更是专房有加,到此时的素姐虽然没有屈服,但不可否认的是她已经一无所有了。但作者还是不肯就此放过她,所以最后素姐只能将性命也丢了去,才算是了却了一段恶姻缘。男权社会的步步紧逼葬送了素姐这个如花的生命。
三、“万悍同悲”——男权思想下的“悍妇”群像与话语模式
明清时期社会的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并取得一定发展,伴随着经济的新气象而产生的便是社会思潮的涌动和革新。自宋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渐渐遭到人们的怀疑,取而代之的是以李贽“童心说”、汤显祖“至情论”等为代表的以宣扬人的个性、发掘真情为核心的新思潮。新思潮对以往的学说和思想造成了剧烈冲击。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想从被程朱之学及其他封建思想禁锢的牢笼里渐渐走向了一种较为开放的风气面貌,对于传统女性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如李贽就从自然人性论及“天下万物皆生于两而不生于一”的社会二元论出发,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在《焚书》中他提到“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更为石破天惊的是他主张妇女有恋爱自由和再嫁的权力。李贽的进步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人挟一册以为奇货”,“举国趋之若狂”。这种社会时代背景的大变化为当时“悍妇”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动力源泉。而“男性无视时代的发展,无视自身的变化,顽固地坚持男性传统的家庭权利和地位,这必然造成两性间‘战争’的升级。”[6]
面临着社会上传统思想的松动,男性感受到自己的男权统治地位的逐渐动摇,所以他们不惜以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一些“悍妇”和“恶姻缘”,以起到警醒世人、妄图恢复绝对统治地位的作用。此时期有关“悍妇”形象的作品大量出现,而这些故事有着固定的话语模式。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悍妇”故事中体会到男性作家对于传统秩序井然的儒家道德社会结构的怀念。这是和男性面临着逐渐失势的局面而产生的扭曲心理状态不可分割的。
1.“悍妇”、“懦夫”组合
明清时期以描写“悍妇”“妒妇”故事而闻名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醋葫芦》、《醒世姻缘传》、《疗妒缘》、《连城璧》等,这类小说有着共同点,在人物形象组合上是“悍妇”和“懦夫”的组合,“悍妇”往往凶狠残暴、因妒而悍,对丈夫百般折磨、严厉管制,且大多数悍妇无子嗣却又千方百计阻止丈夫纳妾,对家中之妾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进行惩治,如《醋葫芦》中的都氏“四从三德一例无”,采用焚香限时的方法限制成珪的外出,采用令人叹为观止的“龟头盖印”的方式预防成珪与其他女子有染,设计娶石女为妾,险些打死与丈夫私通的婢女翠苔,对丈夫更是动辄打骂。
2.身处绝境,孤立无援
“悍妇”与“懦夫”之间的力量对比设置,乍看来读者会觉得“悍妇”凭借其剽悍和暴戾明显的在斗争中占据着上风,可仔细分析文本便会发现,由于男性作家自私心理的作怪,“悍妇”的力量实际上远不及男性一方。综观此时期众多或较早描写悍妇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文中会有众多次要人物站在男性主人公一方为其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男性如此,就连女性也大多成为了男权秩序的忠实拥护者。《醒世姻缘传》中,对于薛素姐来说,能够从始至终理解支持她的只有她的生母龙氏,但其身份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实属下贱,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发言权,更无法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对于素姐的帮助只能算是情感上的。与之相对的狄希陈一方力量可谓强大。不仅狄希陈家人坚决维护自己的儿子,就连薛教授一家也是如此。不仅男性如此,就连相大妗子这样的女性也是如此,她们不自觉的充当了男性的帮凶。《醋葫芦》里的男主人公成珪也是拥有着周智夫妇这样的出谋划策的人,他们帮着他偷偷娶妾生子,更有神明暗中帮助,完成其延续香火的梦想。而对于女主人公都氏来说,也只有天神雷闪娘的一番话算是为她做了些许辩白。由此看来,最然众多悍妇作品中的“悍妇”气势逼人、凶神恶煞,但大多都是一人独自撑台,孤立无援,远不及“懦夫”一方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男人的权力并不因女人的反抗而受损,女人的反抗只能一次次的证明权力制度的不可动摇。”[7]
3.“悍”毁身灭
“悍妇”故事的结局安排也有类同之处。伴随着“悍妇”层出不穷而产生的便是方法各异的“疗妒”“惩悍”之术,作者在作品中冥思苦想的为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悍妇”们安排了悲惨的结局以达到自己泄愤的心理。一类结局便是让“悍妇”吃尽苦头后使其改过自新,如《马介甫》中的尹氏,最后沦落街头受尽羞辱,遇到前夫杨万石后悔恨不迭。又如《醋葫芦》中的都氏,在地狱中遭受种种酷刑,最后由于波斯尊者委托地藏菩萨求情才得以还阳,但依然被抽去了背上一条妒筋,至此而不再妒忌泼辣,痛改前非。这显然是作者借神明之力的幻想,企图以报应之说对世间女子产生震慑,重塑男权社会威严。另一类“悍妇”的结局则是以死亡收尾。如《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西湖二集》中《李凤娘酷妒遭天谴》里的李凤娘,个人结局都十分悲惨。李凤娘甚至连棺木都被震碎,尸骨不留。从男权社会中“悍妇”的结局中可以看出,男性作家带有报复性的变态心理,是他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结出的又一朵“恶之花”。
“悍妇”的主要特点是内心极度扭曲、嫉妒心极强,外在行为表现的十分残忍暴戾,大多是家中正妻且无子嗣。明清小说中出现这样大数量的“悍妇”群体,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艺术夸张。男性作家在作品中之所以大肆呈现“悍妇”们的“恶德”、种种恶劣行径,把这些夸张化了的女性刻画成了人见人畏、十恶不赦的“恶魔”,一方面他们想借此来警醒世人,甚至妄图达到教育闺阁女子以净化世风、重新树立男性权威的目的;另一方面便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在口诛笔伐中寻找泄愤的快感。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集[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183.
[2]王伟.独具特色的狐精形象——薛素姐[J].戴宗学刊,2007(12):20.
[3]叶绍钧.女子人格问题[J].新潮,1919(2).
[4]李华.《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叛逆性格的表现[J].剑南文学,2011(2):49.
[5]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95-100.
[6]吴秀华,尹楚彬.论明末清初的妒风及妒妇形象[J].中国文学研究,2002(3):43.
[7]付丽.男权压抑下的悍妇心理——略论《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J].明清小说研究,2003(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