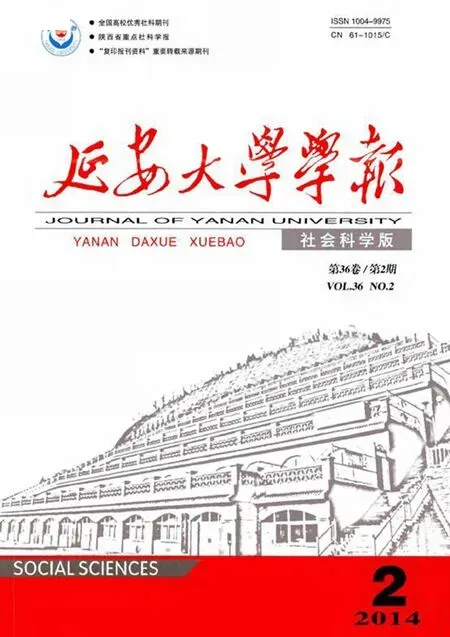清季中朝乙酉勘界谈判探微
2014-03-06李宗勋
倪 屹,李宗勋
(1.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2.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清光绪十一年(农历乙酉年,1885年),中朝两国曾各派代表就土门江边界问题举行勘界谈判,史称乙酉勘界谈判。关于谈判的具体过程,虽然吴禄贞、筱田治策、刘凤荣、张存武、杨昭全、李花子、陈慧等学者的著作①已经作过比较详细的探讨,但由于视角差异,所选文献以及解读方式不尽一致,至今学界仍存在很多认识分歧。笔者试在综合上述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其中的关键环节,以期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勘界谈判的背景
清王朝定鼎中原后,为保护满族的特殊利益,对发祥地鸭绿江、图们江边境长期实行封禁政策。图们江在当时中国文献中亦作土门江,而朝鲜则称为豆江或豆满江。由于封禁区内除极少数满族住户外,不准移民入居,因此当时图们江北岸广阔土地沦为荒野。虽然清廷在布尔哈通河、海兰江等处设立了堡、哨、卡,并建立统巡制,但因国境线守备空虚,朝鲜边民仍不时潜入中国一侧,采参拓垦。同治、光绪年间,朝鲜咸镜北道庆源、庆兴、稳城、钟城、会宁、富宁六镇接连发生水、旱、虫灾,在地方官员的纵容下,流民越界愈益严重,渐有不绝于途之势。与此同时,清廷为防范沙俄蚕食东疆,于光绪七年(1881年)在图们江北岸设帮办吉林边务大臣、珲春副都统、珲春招垦局,开禁实边。是年,珲春招垦局委员候选知府李金镛巡查发现,图们江支流嘎呀河附近朝鲜流民私垦荒地竟高达8 000余垧,且咸镜道刺史擅自“发给执照,分段注册”,“经阅多年”,于是迅速禀报吉林将军铭安及帮办边务大臣吴大澂商讨对策。[1]次年(1882年),铭安、吴大澂上奏清廷,建议“准其领照纳租”,分归珲春、敦化两县管辖。[2]清廷准奏,并命礼部、铭安、吴大澂分别咨告朝鲜国王及朝鲜地方官吏。最初朝鲜政府对于清廷所提政策并未表示任何异议,然而时隔数月,朝鲜国王便咨文光绪帝,以“习俗既殊,风土不并……万一滋事,深为可虑”为由,请求将所有朝鲜越垦流民遣返,交付本国地方官弁归籍办理。[3]清廷答应朝鲜请求,鉴于流民数量过多,一时难以全部遣返,最终协议放宽时间,准其一年内悉数收回,以示体恤。然而,朝鲜垦民大多留恋中土,不愿返回故国。为避免遣返,有些不明真相的垦民遂倡议国内讹传的“土门、豆满两江说”,妄指拓垦土地原为朝鲜领土。
所谓“土门、豆满两江说”,须追溯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当时穆克登虽准确勘定了中朝图们江边界,但朝鲜单方建立界栅时,认为穆克登认定的图们江初源实际并非真正图们江源,而是邻近石乙水和红土山水的松花江支源,于是将木栅终点连接到穆克登认定的图们江次派水源。[4]后来木栅渐朽,朝鲜国内一再夸大臆断的穆克登错认的土门江地理范围,最终遂演成“土门非豆满,豆满非国界”的谬论。而朝鲜之所以一再夸大臆断的穆克登错认的土门江范围,否认豆满江为中朝国界,与18世纪以来朝鲜实学派学者宣传的民族、国土观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当时实学派学者,如申景浚、洪良浩、丁若镛等,为树立朝鲜民族主体意识,摆脱对清朝的从属关系,纷纷研究朝鲜文化和历史地理,以激发国民对所谓古代朝鲜疆域故地的怀念。这些学者大都否认穆克登勘定的图们江边界。其中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以松花江、黑龙江一线确定朝鲜北方边界的走向,而另有些学者则主张以分界江,即海兰江或布尔哈通河来划分中朝边界。虽然这些论断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但在19世纪朝鲜社会确有很多人相信穆克登立碑前或立碑之初,分界江就是分中朝边界之江。
受上述社会思潮影响,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朝鲜越界垦民上诉钟城府使李正东、会宁府使洪南周,强烈要求以其臆断的“土门江”重新勘定中朝东段边界。两位府使在西北经略使鱼允中的授意下,据流民牒状分别照会敦化县知事。其要旨如下:[1]
(一)康熙年间穆克登奉旨查边所定土门江边界,是以钟城越边90里之分界江(按:指图们江支流布尔哈通河或海兰江)而非豆满江为界。朝鲜流民所垦土地介于土门江以南、豆满江以北,并非清朝领土。
(二)穆克登碑文刻有“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字样。碑址以东有当初朝鲜建筑的石堆、土堆,其下土沟两岸对立如门,恰好符合碑文中“土门”的地理形势。
(三)分界江北岸清朝设有卡铺,如果土门江原指豆满江,卡铺只能设在豆满江北岸,不可能设在分界江北岸。往年中朝两国在土门江边境开市,中国商人到朝鲜境内交易,朝鲜所出车马必须输送到分界江,如果中途替输,中国商人肯定要责备未到达替输界限。
光绪十年(1884年)冬,朝鲜年贡使金晚植借朝贡呈文清礼部代奏光绪帝,正式提出勘界动议。礼部认为疆域事关重大,不可凭一纸呈文代为转奏,遂退还呈文,但留下所附地图、穆克登碑文、钟城会宁府使致敦化县知事照会以及朝鲜北兵使上政府文,以备参考。次年(1885年)六月,朝鲜高宗国王又特遣斋咨官李应浚携咨文出使清廷,再次请求光绪帝重新勘界。
在此期间,朝鲜越垦流民不仅数量日益增多,所垦荒地亦越来越广,且有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导致图们江北岸中国居民“人心惶惑”,不得安宁。为妥善解决边务纠纷,根据吉林将军希元的建议,七月,清北洋大臣李鸿章奉命咨文朝鲜国王,表示同意选派委员同朝鲜进行勘界谈判。
二、中朝勘界及其交涉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中朝两国先后在朝鲜会宁和茂山举行界谈。当时中方代表为珲春左翼协领兼边务交涉承办处事务委员德玉、督理吉林朝鲜商务委员秦煐、护理招垦边荒事务委员贾元桂,朝方代表则为安边都护府兵马节制使李重夏。在界谈过程中,双方曾于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同时分勘西豆、红丹、红土山水及穆碑。勘界结果,查得长白山,即朝鲜所谓白头山,山南麓有一石碑,碑面汉文有“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等字样,由此东南去,至鹤项岭,中国统称黄沙岭,朝鲜称此岭北首近长白山处为分水岭,中间为虚项岭,南首为鹤项岭。岭碑西有一沟西南流入鸭绿江,碑东有一沟,朝鲜呼伊嘎力盖,又称杉浦,汉语则称黄花松沟子。此沟绕长白山东麓东北行,沟之东南岸上首有石堆,下首有土堆,共180余个。过大角峰,沟形忽窄,两岸土堆高深数丈,朝鲜称为土门,堆之尽处距碑已90里。自此以下数十里,此沟始见水,再下与沟东之斜乙水并斜乙水东之董维窝棚水合流,入娘娘库,由娘娘库西北行至两江口,入松花江。又石碑微南有两座土山,朝鲜称次乙峰,再南有胭脂峰,再南为小白山,距石碑处40里。小白山东北坡有一沟,沟掌甚宽,顺山坡而下,东北行数十里,沟形渐窄,夏始见水,其南岸为茂峰,北岸为大角峰,分支东去之八峰,至八峰东首之董维窝棚,此沟之水冬夏常流不断,由此东北行十余里,水入平岗烂石塘中不见,又十数里,水复出,与此水西之斜乙水并斜乙水西之伊嘎力盖,合流入娘娘库,下入松花江。又查斜乙水之发源即在八峰之北坡。小白山东北百余里有红土山,中间漫岗起伏,不见峰峦。红土山与长白山东西相望相距120里,红土山东即长山岭之起峰处。由红土山西北行5里平岗上有一圆池,池之两旁各二三里有二水,由漫坡流出,绕过红土山合流,由长山岭南面曲折东南流,经甑山以北过长坡至小红丹地方,约百余里与红丹水合流。小白山东南、黄沙岭偏东有三汲泡,由该泡顺岭西北行,过小白山至石碑130里。其泡西南15里有小岩,朝鲜呼虚项岭,再西南约30里,有一水朝鲜呼以湎水,顺岭坡而下,西南流入鸭绿江。其泡之东顺岭坡而下,东行约30里,有泉涌出,即红丹水发源处。自此而下,南有刀凌河、板桥河、柳洞三水入之,曲折东流经甑山过老人峰约200余里,至小红丹与红土山发源之水合流,又东南行北有红旗河之水入之,至江口地方与西豆水合流,入图们江,即朝鲜豆满江。黄沙岭上、三汲泡东南即蒲潭山,朝鲜呼宝髦山,距石碑约180里,岭西坡有一水,西北流入鸭绿江。西豆水源于东坡,至板桥之下平甫坡之上与源自距石碑四五百里之鹤项岭北坡之西豆水之经流相汇,自蒲潭山至江口地方280余里。自鹤项岭至江口地方400余里。②总之,黄沙岭之小白山以南至鹤项岭一段为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而小白山以北至长白山一段则为鸭绿江、松花江分水岭,穆克登碑址与碑记并不相符。③
此次会勘论辩双方主要围绕四个问题:(一)勘界基础。中方代表认为,中朝土门江边界,向以图们江亦即朝鲜所谓豆满江为界。只能以江求证穆克登碑,不可能以穆克登碑现址求证江流。寻流溯源是确定土门江边界的的唯一途径。而朝鲜勘界使李重夏则认为,清康熙朝穆克登奉旨查边是中朝两国间正式定界、划界,穆克登建立的石碑即确定两国边界基点的定界碑,碑东连接的当初穆克登委托朝鲜建筑的石、土堆就是划分国界的点线标志。勘界即勘碑,只有根据石碑现址及“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的碑记才能确定土门江边界的具体走向。(二)土门江与豆满江是否一江。中国代表认为,土门、图们、豆满都是满语的音译,意同汉语“万”字,载于满语权威辞书《清文鉴》。《钦定皇朝通典边防门》、《钦定皇朝四裔考》等皇帝钦定、颁行天下的文献均明确记载吉林、朝鲜以图们江为界。以常理而论,钦定文献不可能滥行载入,误传后世。之所以出现“土门、豆满两江说”,只是因为吉林幅员辽阔,边地未开,而朝鲜地脊民稠,为解决边民生计,朝鲜官员纵民越界私垦,考虑“收回则无地安插,又恐有不便之处”,遂误信传言,欲将流民所占土地诡辩为朝鲜疆域。朝鲜代表认为,土门、图们字样悬殊,不该混称。用满语音译解释土门、豆满似乎过于牵强。而豆满来自朝鲜方言,与土门江并非一水。土门应指穆克登碑记“东为土门”之土门,即碑东水源之下连有“土壁如门”之意。豆满江源与穆克登碑及碑东石、土堆并不相接。至于土门江究竟指哪条河流,李重夏称钟城府使在给敦化县知事照会中以海兰江为分界之江,是一时笔误。在勘查图们江源和穆克登碑之前,他认为布尔哈通河是真正分界江,但勘界之后,又将穆克登碑东松花江指为土门江。(三)穆克登碑真伪。由于清礼部并没有查到穆克登定界的档案,中国代表认为,穆克登碑不免存在后人伪造的嫌疑。首先,乌喇总管为康熙年间所设官职,当时乌喇衙门既用满文,也用汉字。穆克登作为乌喇总管同朝鲜立碑应当满汉合璧,但如今见到的穆克登碑只有汉字,并无满文。其次,按碑文记载的立碑时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月十五日,立碑年限已将近200年,风雨摧残,文字不可能无一残缺,而如今碑体、碑文却依然保存完好。再次,穆克登碑现址与碑文所记原址并不相符。碑文明确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但石碑现址却并非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而是鸭绿江、松花江分水岭。朝鲜代表认为,清朝开国以后同朝鲜往来文字一直使用汉字,不用满文。现存清太祖皇太极在朝鲜广州三田渡地方竖立的丙子东兴碑,镌刻数千言,全部都是汉字,没有一字满语。况且康熙朝文化方兴,穆克登碑文完全使用汉字自在情理当中。穆克登立碑至今只有170年,金石篆隶尚有秦汉古迹,碑文完好无缺,亦属正常。(四)穆克登碑原址。中国代表认为,如果穆克登碑不是后人伪造,那么石碑发现位置与碑文不符,就只有两种解释:1.穆克登当初错立石碑;2.石碑原本立在鸭绿江、图们江真正分水岭——小白山虚项岭,但后来却被人从小白山虚项岭移到现址长白山南麓鸭绿江、松花江分水岭。朝鲜代表认为,对于当年穆克登是否错立石碑,暂时尚无法作出最终判断,但是石碑现址肯定是初立位置。小白山虚项岭以西虽有鸭绿江源,以东虽有图们江源,但毕竟远隔75里,并不适合建立定界碑。而且,各种图志一直都记载长白山为中朝界山,以小白山定界,该岭距离长白山100余里,长白山主峰将完全排除在朝鲜界外。穆克登碑现址恰恰处于长白山,既邻近天池,又邻近鸭绿江第一水源,穆碑东西沟壑距离只有数步,碑东沿界设堆,而土堆之上“林木丛生,往往有老而拱者”,明是当年旧限。④
由于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中国代表再三筹思,既然山水查明,“若不公同详核绘图会印,终无确据,故先彼此照会”,迨绘图之后,再商如何定界。但双方互致照会,绘图签押后,朝鲜勘界使李重夏却“踌躇莫决,意似深有所畏”,最终“以不敢自下议定,必须归报国王为辞”,中断勘界谈判。[3]
三、乙酉谈判结束后中朝两国的反应
十二月十六日,中国代表德玉、秦煐、贾元桂将前述勘界及谈判情况禀报吉林将军希元。值得注意的是,在禀文中他们并未否认穆克登当年所立石碑是中朝定界碑。但他们认为穆克登勘定的土门江源肯定是发源于小白山三汲泡的红丹水,不可能是石碑现址以东的黄花松沟子。只有以三汲泡红丹水定界,并在小白山分水岭立碑,才能与碑文所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八字吻合,而界址亦“东西绳直,斩然齐整”。[5]
希元详阅图说并参考直隶省藏《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而后致咨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发源于三汲泡的红丹水即舆图之小图们江,而西豆水则为舆图之大图们江。按舆图记载,穆克登立碑定界本以西豆水为界,但考虑西豆水流域朝鲜居民繁众,为“不失朝廷字小之意”起见,可以退让以三汲泡红丹水确定图们江边界。他痛斥朝鲜上年既指海兰江为图们江,而今会勘时,却又以黄花松沟子两岸有土如门附会土门含义,“明明有定之地,竟游移于无定之口”。而所谓“必以碑堆为据”,“岂知碑无定位,可因人为转移”,江则千古不易。况且界碑现址,并不排除朝鲜越垦流民暗自向北迁移的可能。[6]
与此同时,朝鲜勘界使李重夏也向朝鲜高宗国王以及承政院呈送了《乙酉状启》、《别单》和《追后别单》等秘密奏章。虽然出于职责,李重夏在状启中详细解释了自己为“土门、豆满两江说”所作的辩解,但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且稽考咸镜道所存穆克登定界文献后发现土门江与豆满江明明同指一江,所以最后不得不尊重事实,道出问题的真相。他指出:“豆满江之名,自古不一,中国去来公文或称土门江,而未曾有边界讲理,故随所称,不甚分别”。“备边司关文有曰土门江,华音,即豆满江。以此知悉次,推此一句豆江为界又分明”。而穆克登碑现址之所以与碑文不符,是因为“穆克登但以碑东沟道是豆满上源,而立碑而刻之曰:东为土门,故我国于穆克登人去之后数年为役,自碑东设土石堆,东至豆江源。而豆江之源,本不接于此沟,故平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而遂称之以土门江源矣。今则数百年间,木栅尽朽,杂木郁密,旧日标限,彼我之人,皆不能详知,故致有今日之争辩。”⑤
他还向高宗透露,在同清朝委员勘界时他单方面发现了土堆之下残存的木栅,而木栅同样证明土门江与豆满江同指一江,这令他感到非常恐惧:⑥
而今番入山之行,默查形址,则果有旧日标识,尚隐隐于丛林之间,幸不绽露于彼眼,而事甚危悚。其实状里许,不敢不详告。
尽管朝鲜君臣已经准确了解事实真相,但不久,朝鲜议政府仍致咨北洋总署,继续坚持“土门、豆满两江说”,要求以穆克登碑为基点,沿碑东土堆以下“土壁如门”之“土门”——黄花松沟子,连至另一派发源于哈尔巴岭的“土门”——即清朝所谓土门子,朝鲜所谓分界江的布尔哈通河——划分中朝边界。[1]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总理衙门参考朝鲜议政府及吉林将军希元咨文,上奏光绪帝,提出“三辨析、五考证”,建议重新勘查。[1]
光绪帝旋即批准北洋总署的奏议,北洋总署遂咨文通知吉林将军及朝鲜政府。朝鲜政府接到咨文后,态度立即发生显著变化。九月,朝鲜统理通商交涉督办金允植与中国驻朝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就图们江界务进行笔谈,表示完全承认豆满、土门为一江,并以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源作为复勘的基础。[6]关于复勘图们江勘界谈判,亦即丁亥勘界谈判,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
注释:
①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长白从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日]筱田治策的《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1938年),[韩]刘凤荣的《白头山定界碑与间岛问题》(韩国《白山学报》,1972年,第13页),张存武的《清代边务问题探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杨昭全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李花子的《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陈慧的《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②李重夏的《照会誊抄》(韩国《白山学报》第4号附录,1968年,第276-278页),杨昭全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83-285页)。
③《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到”(《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5册,2005年,第1807-1814页),马孟龙的《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④李重夏的《问答记》,写本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奎21041)。另见韩国《白山学报》第4号附录,1968年,第260-274页。
⑤李重夏的《追后别单》,写本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奎21036)。另见韩国《白山学报》第2号附录,1967年,第172页。
⑥李重夏的《追后别单》虽提到他单独发现了残存木栅,但是笔者所见现存各种文献都未提到李重夏真正看到的木栅终点。李花子女士认为木栅终点连接的图们江源为红土山水。参见李花子的《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77-87页。
[1] 郭廷以,李毓澍.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Z].台北: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2.1938,1910-1913,2093,2091-2095.
[2] 王彦威,等.清季外交史料·卷27[Z].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4.6-7.
[3]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A].李澍田.长白从书:初集[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61,82-83.
[4] 倪屹.穆克登碑原址考证[J].北方文物,2012,(2).
[5]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2[A].李毓澍.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4)[Z].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676,677-678,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