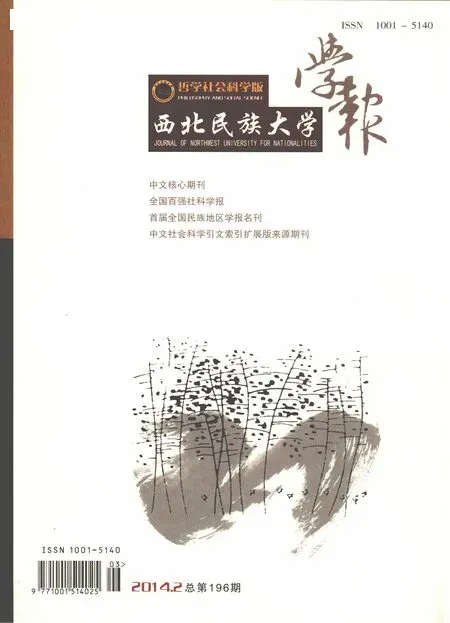文化人类学视野下探讨“活鬼”文化现象——以德格县中扎科乡为例
2014-03-05扎西措
扎西措
(西北民族大学 格萨尔研究院,甘肃 兰州730030)
一、德格县中扎科乡简介
德格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边境,青藏高原东南缘,金沙江(长江)东岸,现今与其他17个兄弟县隶属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东邻甘孜县,南连白玉县,西与西藏江达县隔金沙江相望,北与石渠县接壤,是西进西藏,北入青海的主要交通枢纽。全县幅员面积11955.55平方公里,共辖26个乡(镇),分5个行政片区。德格在历史上对整个藏区影响深远,是古代藏族文化发达的重要地区之一。
中扎科乡位于雅砻江沿岸,由于位于雅砻江中游,故称中扎科(rdza-wr-ma)。它是德格县所辖26个乡镇之一,距离县城300多公里,是离县城最远的乡镇之一,也是德格县最大的农业乡。它与甘孜县相近,当地所操语言和服饰也与甘孜县相近,当地人也有持自己是“霍巴”的说法(甘孜县人具有霍巴后裔的说法,这里的霍巴是指蒙古人)。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方土地有史以来信仰的是苯教,现位于中扎科乡的丁青寺据记载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是康区最古老的苯教寺庙,也是康区苯教寺庙的母寺。“作为藏族地区古老而原始的宗教,苯波教早在隋唐之前便已在德格地区普遍存在。公元7世纪,苯波教在德格地区仍属唯一的宗教。”[1]公元11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宁玛、噶当、噶举、萨迦派也相继传入德格并迅速扩张势力,极大地削弱了苯波教的实力。
纵观康区历史文献,明末清初,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与德格土司组成军事联盟,消灭了独尊苯教的甘孜白利土司武装力量,这位甘孜白利土司曾经在整个康区势力极大,连美名远扬的德格土司对其都是束手无策,时时不得不屈从于白利土司。而白利土司以苯教为独尊,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信仰的都是苯教,据丁青寺的现有历史文献记载,现在德格县管辖的丁青寺从前就是白利土司的家庙,而随着白利土司的衰竭,丁青寺也就归顺于德格土司管辖内,迁到现在的中扎科乡,很多苯教寺庙也相继改成了佛教寺庙。德格土司均奉行不分教派的宗教政策,苯波寺庙也在生存与发展中与藏传教各派相互吸收融合,逐渐演变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派系。现今,德格县共有62座寺庙,其中10座为苯教寺庙。虹化身夏赞扎西坚赞等贤能就诞生在中扎科这方土地。在苯教文化极其浓厚的中扎科乡,也存在极其普遍的“活鬼”文化现象。然而这“活鬼”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苯教信仰地的专属现象,因为在康区其他各个地方都普遍存在这一奇特的“活鬼”文化现象。
二、“活鬼”的面纱
首先,谈谈“鬼”与“活鬼”的区别。翻看汉文字典,对鬼的定义基本上是“迷信的人以为,人死后有灵魂,叫鬼”。现在的藏文字典,对此也是“迷信的产物……”之类的解释。这种字面上的肤浅解释显然并不能代替扎根于人们思想深层的“鬼”的形象。《东噶大辞典》中说:“本教徒一般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他的神灵,也有危害他的鬼。佛教中则说如果一个人是属于非自然死亡就会变成鬼……”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我的释尊观》[2]里谈到:“通常说到恶魔和魔鬼,总觉得是神秘的……但佛法中的‘魔’,则绝不是这样的……从而‘魔’的本性就有了‘夺命者’这样的定义,具有从根本上夺取人们的生命力的作用。”甲骨文中的“鬼”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脑袋形状下一个人字。《西藏的宗教》[3]一书中引用《教法琉璃》记载直古赞普葬仪的情形,提到法师“训尸”时说:“仪式的概念可能是为防止鬼魂回来伤害活人。这类仪式在许多原始部落中普遍存在,甚至今天的喇嘛教仍然在人死了四十九天以后焚象送鬼。”《藏族神灵论》[4]中说:“在藏族苯教文化中,鬼怪通常属赞神之一类,赞神多半是一些游神、厉鬼、妖精……”从上述记载看,苯佛两派对“鬼”的定义虽有细微差异,但对“鬼”的特点有共同的认识:“鬼”,就是人凶死(非自然死亡)后灵魂无处安歇,不升天堂亦不入地狱,游魂于人间,并给人畜的生命带来危害。
“活鬼”(gson-'dre),即藏语意为活着的鬼,他既是活着的人,又有“鬼”的属性。对“活鬼”一词的解释非常少见,在诸多苯佛教的书籍里并没有“活鬼”的介绍和记载,在很多词典里也没有“活鬼”这类词。只在《藏汉辞典》里泛泛提到:“活鬼就是传说中形象和常人相同的男、女鬼。”然而这形象和人相同的男女鬼也赋予了“传说”的环境。这种种迹象表明,“活鬼”在人类生活中并不像“鬼”那么常见,而且本人在对甘肃青海一带的藏族朋友反复追问和调查后发现,甘青一带的藏区并没有“活鬼”这种说法,他们在听到我所叙述的“活鬼”后,各个表示诧异和不了解,即使有,与本文所说的“活鬼”也有着本质性差异,所以更不会有“活鬼”文化现象。可见在藏区,“活鬼”文化现象也只是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活鬼”和“鬼”的共同特点是:作祟于人类,甚至给人畜的生命造成威胁。不同点是:“鬼”是人凶死后灵魂不灭的产物,它面目狰狞,游走于荒山野岭间。而“活鬼”平时和常人无异,只在特定的时间段,它的灵魂离开它的躯体后开始作祟于人类。
就德格县中扎科乡这一地方而言,关于“活鬼”的由来,一为家族世袭制的说法。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为“活鬼”,就要看他的家族传承里有无“活鬼”的血统,如果有,那么他和他的下一代就无可争议的被认为是“活鬼”。二为女人大多是“活鬼”的说法。当地有句俗语:一百个女人里有九十九个是“鬼”,而一百个男人里只有一个是“鬼”。这句俗语明显有些夸大,因为在当地也并不是把所有女人都当成“活鬼”,系个别情况。长得非常漂亮或者非常丑陋的女人被贴上“活鬼”标签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当地人说,长得非常漂亮的人,会用美色诱惑人心,据说这种漂亮的“活鬼”远比长得丑陋的“活鬼”厉害,她会使用心术先勾住人们的魂然后加害于人,而长得丑陋的“活鬼”则直截了当加害于人。“活鬼”的认定权在民众手中,一旦一个人表现出有“活鬼”迹象,在有人亲眼看到并口耳相传后,这个人就会被群众认定为“活鬼”。然而,最稀奇的是,被认定为“活鬼”的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活鬼”。他们平常照样和人们沟通交流,并和常人一样尊奉信仰。只是他们不知道,把他们认定为“活鬼”的群众在暗地里悄悄地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掩盖这种距离不让他们发现。他们保持距离的方法是不与“活鬼”在衣食上有任何接触,且不会与“活鬼”家族有联姻。据说,保持的这种距离要是让“活鬼”发现了,那么他会变本加厉地加害于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表面上,人们是互帮互忙、和谐相处,而暗地里人们尽量与“活鬼”们敬而远之。每当天快黑时,人们就再也不会提起“活鬼”们的名字,并督促自己的小孩也不要提起。若是遇到非提不可的时候就用“那个人”等来代替,因为据说只要提到“活鬼”的名字他便会立马出现在你的面前,并徘徊于家中不肯离去。
再谈“活鬼”的镇服方法。面对“活鬼”,人们一般都持敬而远之、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尽量处处让着他们,让他们满意,甚至有意无意地讨好他,取悦于他,以免自己被害。一旦被“活鬼”害了,就会去找活佛、喇嘛祈福禳灾,以后就更是对他客气相待了。镇服“活鬼”,有一个系统的宗教仪式,这个仪式藏语里叫“mo-'dre-rdzs-mdos”意为女鬼驱器,是用糌粑捏成一个女人的形象,经过念经,使所有鬼气和不干净的东西依附在这个模拟物之后,命人把它带出家门,这时此人要头也不回地把它带到离自家甚远的地方后抛弃,然后头也不回地直奔家里,据说如果此人途中不慎回头了,那么“鬼气”也会随其而来,那么此次的驱鬼也就徒劳了。然而这种驱鬼仪式并不会锣鼓宣扬,因为前面提到,“活鬼”们一旦知道自己被别人当成“活鬼”,会陷入疯狂的境地,以使更加难以制服。万一让“活鬼”知道了,那就只有请修法高深的活佛、喇嘛去制服,活佛、喇嘛制服“活鬼”后,经常对他进行授教、灌顶,使他从此以后“改过自新”、诚心向佛。面对少数特别厉害、极其妖艳或者丑陋的女“活鬼”,活佛、喇嘛也有用直接娶其为妻的镇服方法,因为只有在这些佛的化身的眼皮底下,“活鬼”才不敢作祟、危害于人。
三、“活鬼”作祟的个案调查
据德格县志记载,中扎科乡全乡人口为5 123人,男性为2 522人,女性为2 601人,共有1 130户。据本人实地调查,全乡范围内被认定为“活鬼”的有三户人家,其中他们的作祟等级也有所不同。第一户作祟较为厉害,以他们家的母亲为典型,据说她会时常出现在各个地方,只要有人使她不满,她便立刻实施报复,使令她不满的人得病、受灾、家人受灾甚至死亡。这户人家的其他成员,即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虽然带有“鬼族”血统,但却并不像他们母亲一样做出危害乡邻的事。且她的儿子还在寺院出家为僧,我曾问及这个孩子,众人都表示“他很聪明,学经也刻苦勤奋”。第二户被认定为“活鬼”的这个人是从外地入赘到当地的一名男子,据说他们家也是世代“鬼族”。只是这个“活鬼”,他最大的作祟行动就是经常在半夜里骑着一头红牦牛四处游荡,或在他们家的附近点燃“鬼火”等,相传他并没有做过危害乡邻的事。第三户人家,是由一对父母和两个女儿组成,据说他们也是“世袭制”。他们家的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是全乡里数一数二的美女,然而她却是他们家典型的“活鬼”代表,据说他们家其他人并没有任何作祟现象。这位美女虽不做危害乡邻的事,但据说她经常半夜坐在他们家前面的桥头上,过路的人们经常撞见,让人很害怕。这三个不同的鬼族家庭,人们对他们所持的态度也不同。后面两户人家,人们经常与他们来往,且在衣食上的接触也并没有像第一家那么小心谨慎。而对第一户人家,主要是那家的母亲,人们经常避而不谈,或与她敬而远之,她的作祟故事也比较多。下面是本人对当地关于“活鬼”作崇故事的访问记录。
个案一:拉巴,木匠。他说:“有一次,村里的好多马儿被盗马贼偷走,他们在山上留下了一些可寻的痕迹,于是村里组织所有年轻人连夜追赶。在我们翻山越岭极为疲惫的时候,忽然有人看见‘那个人’(前面提到第一户人家的那位母亲)也一直跟着我们,忽隐忽现。我也频频回头,有一次还真看见了,她背着一个背筐,我没有看见背筐里背了什么,但有人说看见背筐里满是人头。当时大家都挺害怕,其中一个比较大胆的年轻人大声说:‘大姐啊,跟着我们干嘛呀,赶快回去睡觉吧。’于是真的就不见她再跟来了。到了半夜,我们点燃篝火围坐在一起稍作休息,只见一只大蜘蛛在面前空地上旋转(当地有个说法,晚上出来的蜘蛛必定是‘鬼’)。于是有人用碗把它盖住,并沿着碗边洒了厚厚的一层糌粑,再把碗取开时,见那蜘蛛一直试图翻过那个糌粑堆却没成功。后来,大家觉得追不到马贼了,便决定回家。太阳刚刚升起时,我们回到了村里。众人各自散去,到最后剩下家住较远的泽仁和我。我们经过‘那个人’的家门口时,见她正准备收拾牛粪,见到我们,便很热情的招呼我们,还闲聊似的说:‘唉,昨晚一直梦见我被一群白雪皑皑的雪山困住,怎么努力都走不出来。弄得我今天都精疲力尽的。’说完,便摇着头进屋去了。我跟泽仁当时就愣住了,心想昨晚被糌粑围得严严实实的黑蜘蛛,肯定就是她。”
个案二:顿珠,农民。他说:“五六月份都是挖虫草的季节,村里人去山上挖虫草,我眼睛不好挖得不多,所以留下来帮全村人放马,晚上他们回来会给我分一些虫草当是酬劳。有一次,我把马赶到水草比较丰盛的地方,途中因为几匹走在前面的马怎么都不肯回到马队里,于是我用石头把它们赶回来了。当时我确实用石头打着了一匹马,也不知是谁家的。看没什么异样我也没在意。晚上,大家正吃晚饭时,‘那个人’(又是前面那位母亲)怒气冲冲跑过来对我大吼:‘你把我们家的马怎么样了?它现在一瘸一拐的,你赔我们家的马来。’然后便拉开嗓门开始诟骂。我当时也是冲动,觉得委屈就跟她争执起来,后来被人劝开了。当时劝我的人悄悄对我说:‘你不想活了?还敢跟她顶嘴。’我一时气着了说:‘有种她就放马过来!’后来,她也没在提什么,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谁知几天后,我刚满岁的小儿子却突然病重,一到晚上就大哭,弄得乡邻好友都鸡犬不宁。去医院吧,医生说不知道啥病。找喇嘛打卦,卦相为凶兆,喇嘛说:‘怕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我心里顿时就懊悔呀!我请喇嘛做法事,做了法事后,孩子是不哭不闹了,可整天显得病怏怏的,不怎么爱动。几个月后才发现,小孩左脚和左手都瘫了,不能动了。当时去县里、州里各大医院都瞧了,医生说是先天性的,表示没有办法,我大儿子都好好的,小儿子却成了残疾人,我真倒霉(顿珠摇着头,满脸痛苦)。”
个案三:当措,农民。她说:“有一天,村里的扎多家打墙,一大早我就去帮忙。路上经过‘她们家’(还是第一户那家母亲),我看见她在二楼上迎风吹青稞(在风的吹拂下,使青稞粒子和青稞皮分离的一种农活),见我下来,她微笑了一下,也没说话,我也微笑了一下以示回应。再走下去一点,就是那座小小的马尼房,我准备转它三圈再走,可是就在我要转经的时候,‘她’突然迎面走来,还背着个背筐,额上挂着几滴汗珠,见了我气喘吁吁地说:‘扎多家打墙,人好多,我先回来了。’我当时就吓傻了,根本顾不上回答她,她也不等我回答就低着头走了。我在那里缓了好久,才有力气走回家,当天扎多家打墙我也没去,一天都迷迷糊糊的,眼里不断浮现她前几秒还在她们家楼上吹青稞,后几秒又迎面走来的样子。后来请喇嘛灌顶赐福才没有得什么病。”
四、“活鬼”文化现象分析
追溯“活鬼”历史。关于藏族的人类起源,很多藏文史书上都有一个神话记载: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生下六个小猴,这些小猴逐渐演化为藏族先民。这则神话,被佛教徒历史学家大为广用,他们把猕猴说成是大慈佛的化身,所以父系一族都是聪明、胸怀宽广、具有慈悲心的类型,而罗刹女则因是罗刹,故母系一族都是愚昧、妒忌、顽劣、恶业深重的类型。从这类记载中不难看出,虽然佛教教理中再三强调“女性地位和男女平等”思想,但在藏族古老社会中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他们把女性与所有丑陋的一面联系起来,甚至与“鬼”(罗刹)扯上关系,以至于形成在供奉佛堂或举行一些佛事活动时女性不能接触的局面。从这里,我们也就大概可以理解“一百个女人中,九十九个是鬼,一百个男人中,只有一个是鬼”的说法了,从这些描述中也隐约可见“女活鬼”的雏形。另外,在藏族社会中,灵魂、鬼神观念历史悠久,“西藏传入佛教以前,当地固有的宗教是苯教,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驱鬼降神等事为其主要活动”[5]。可见在原始苯教盛行的时候,“鬼”的观念就已深入人心,扎根于社会,苯教巫师就成为了人与鬼神之间的“桥梁”。在藏族的神话、故事、传说、民谣以及史诗中,“鬼”和“男神女鬼”的体现也是数不胜数的。然而,从有限资料来分析,对“活鬼”的记载,不管是原始苯教还是后来的雍仲苯教以及佛教当中都很少见到。很多苯佛教的活佛、喇嘛们也表示并不认同“活鬼”这种说法,认为它是与苯佛教的教理相悖的。可见“活鬼”是在灵魂观念和“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民众观念。活鬼的认定权在民众手中,它是在最基层的民众当中生根、发芽的一种民俗现象。
“活鬼”自身的心理和身体状况。一篇关于“活鬼”文化现象的论文中提到:“经调查发现,被活鬼附体者一般心脏都有问题或者心理素质比较差。常人被活鬼附体后,完全模仿活鬼的语言、表情和行为代表活鬼说话,严重者出现自残,甚至自杀情况。”还说:“在调查中发现,多数被“活鬼”依附上身者是心脏病患者,有些甚至不断被上身。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所谓被活鬼附身实际是程度不同的精神分裂症。”[6]由于本文所调查的地方具有不能让本人知道自己被大众认为是“活鬼“的风俗,故不能把那些认定为“活鬼”的人逐一拉去看病或心理咨询,但是当地的一些说法和事例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与上述论文比较相近的论证。比如,据说一次跳神节上,当跳神的喇嘛带上各路神祇的面具跳出驱鬼、镇鬼的动作时,一位被人们认定为“活鬼”的妇女当场晕倒,鼻流鲜血,全身颤抖,胡言乱语,场面甚是瘆人,后来被活佛制止并对她进行了治疗。活佛的治疗方法除了念经、灌顶外,还有对她进行心理治疗,给她讲法,让她从心里产生对佛法的虔诚顶礼,让她做善事,持善心,从此不再有害人之心。当地一位活佛也表示:“这些被人认为是‘活鬼’的人,其实她本身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况是不佳的。有的人因为生辰八字和五行相克,以致身体阳气甚弱,这种体质很容易被‘不干净’的东西趁虚而入。”前面提到,即使是被认定为“活鬼”的一家人,他们的作祟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表示“鬼”附体因人而异,有的人会时常被“鬼”附体,而有的人则不会或很少被“鬼”附体,因此“活鬼”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
“活鬼”文化现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是从藏族最初的万物有灵、神鬼信仰里逐渐分化出来的。由于活鬼的认定权在最基层的群众手中,且活鬼的存在是苯佛教的教理所不支持的,故谈不上是藏族统治阶级或喇嘛僧人建构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苯佛教认为,人死后灵魂借生前所做的业力投生于神、非天、人三善趣与饿鬼、傍生、地狱三恶趣的六道轮回中。然而,“活鬼”,他首先具有人性,但是由于自身体质等原因和前世所造的孽缘又使其具有了“鬼”性,且依据大部分“活鬼”是女鬼、非常漂亮和丑陋的女人这种说法来看,这是藏族社会中固有的灵魂观、阶级观念、男尊女卑思想的环境中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历史唯物角度来看,中扎科乡是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弱。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规律与某种人格化的超自然存在联系起来,形成了他们自己对自然力量的见解。人畜受到灾难、生命受到威胁、风雨不顺等现象也就归咎为“鬼”和“活鬼”的作祟力量。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由于中扎科乡和很多藏区一样地广人稀,交通极其落后,成天被封闭在大山野岭间,与外界的沟通和交往较少,因此不能引进新的思想和新鲜事物,使其当地人的心理有很强的孤独感。为了不使生活单调乏味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民歌民谣来解闷。而这种“活鬼”现象,只要一经人们相传,便会添油加醋,使其更生动、更刺激以充斥他们单调的生活。本人出生在中扎科乡,小时后经常能听见这种“鬼”故事,对于我来说,这种“活鬼”的故事远比其他的神话、动物故事有趣得多,所以在睡前,父亲或哥哥姐姐便会给我讲这种“活鬼”作祟的故事来哄我睡觉。他们给我讲的故事有些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有些则是他们所谓的亲身经历。不过当时对“活鬼”的忌讳却是事实,父亲从来不允许我们在日落后提起那些人的名字,更不用说与他们有衣食上的接触或成为他们的玩伴,如果那样做,回来后就要受到重罚。现在,村里通了土路,小学也建了,虽还没有通水电,但日子比较宽裕的人家都或发电或买太阳能电视,终于对外面的事物有所耳闻了。至今,似乎“活鬼”们也忙得不亦乐乎起来,因为他们作祟的事列传得也是越来越少。
总之,活鬼文化现象普遍存在于藏东(康区)各个地区,各地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流传方式。它是藏族古老社会文化背景下特定的历史产物,它的存在给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沟通造成了阻碍,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这些“活鬼”的存在成了一些神秘蹊跷事物和超自然力量存在归咎责任和社会矛盾出气的对象。而“活鬼”的女性化和女性的“鬼化”,更是给原本浓厚的男尊女卑思想提供了有力借口,使原本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更没有接近大众的机会。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的生活方式替代了原本自固封闭的生活生产方式。随着人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潮机会的增加,人们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神秘事物不再一如既往地追加在“活鬼”的头上,而是客观对待,冷静分析。这样,“活鬼”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甚至临近瓦解。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勤劳睿智的同胞会用犀利的眼光、独到的见解对一切神秘事物揭开其神奇的面纱,长期桎梏人们生活和心灵的“活鬼”文化疑结也会迎刃而解,而养育我的这方热土会随着时代的步伐,带着自己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立足于世界园林之中绽放她的光彩!
[1]泽尔多杰.雪域康巴文化宝库——德格[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61.
[2]池田大作.我的释尊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79.
[3]霍夫曼.西藏的宗教[M].北京:中国科学院民俗研究所,1965.10.
[4]旦珠昂奔.藏族神灵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5.
[5]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7.1.
[6]胡静.康区“活鬼”文化现象调查与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