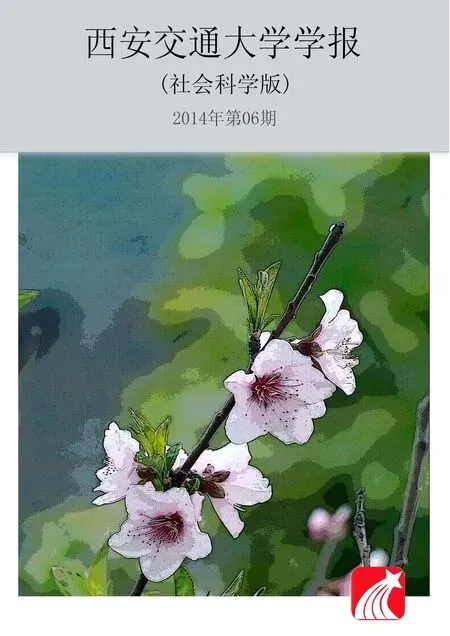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2014-03-04曹桂生
曹桂生,曹 阳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曹桂生,曹 阳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具有本土特征或民族性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在于冲突,还表现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差异性,也有着一些相通的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在于取长补短,在于促进人类文化共同发展。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不会出现一种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是多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并存。
全球化;本土化;多元化;西方文化;民族文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向别国渗透自己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这实质上就是从经济霸权延伸到文化霸权领域,从而达到文化殖民的意图,其目的在于使世界文化同一化或美国化。但是,文化全球化恰恰在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或多元化,而并非同一化,这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根本意义上讲,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世界文化的趋同化和同一化,而是具有本土特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唯有如此,才能使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从而持保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
世界是由多元和多极构成的,因而文化也应该呈现多种形态。文化的单一性和或趋同化不利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只有保持文化的多种性或多元化,才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文化认同与抗拒
文化认同是指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认同(identity),即身份,或者同一性。这也是异趣沟通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个‘认同’是从自我出发的对个人、集体、民族和国家的身份的确认。”[1]
亨廷顿认为,在全球化的21世纪,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最大威胁的力量并不是在经济或政治方面,而是在文化方面。文化将是造成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因素。他还指出,在当今世界,文明和文化冲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激烈,而且这种冲突的趋势一直在不断增长。也就是说,未来世界的冲突仍然是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而并不是来自于经济或意识形态方面。“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1]一种文化或文明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2]这里认为,“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会出现“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也就是说,只有西方文化才具有“世界意义”和“普世价值”。其实,这种观念在西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在审视自我文化的主体性时,常常以一种普适性或中性话语表现出来,仿佛人类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应该与他们求得苟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全球化,就达不到与西方文化对话与沟通的目的。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当今西方所推行的文化“普世性”和世界文化大同的“主体性”,即西方的式的“普世性”和“主体性”。这种文化观念潜在着极大的欺骗性,我们既无法认同,也不能置之不理,必须进行有力地批判和抗拒。坚持自我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抵抗“文化趋同论”和“主体文化死亡论”等解构主义消解性理论给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化本土化或民族化是对全球化语境下产生的同质化、一体化和趋同化的拒抗,坚持民族文化操守或文化认同是异于文化同质化和一体化的一种民族话语向度。所以,文化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本土化。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西方强势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了一系列不平衡政策,他们在不断地为全球化制定游戏规则,这种无休止的扩张被称为“帝国主义”。这种国际间的不公平竞争和倾销政策,严重伤害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世界上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因而有的学者担心,全球化并不能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也不能消除强势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更不可能使弱势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改变自己的身份。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和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是在西方经济强势国家、主要是由美国控制着现代高科技之下的全球化,即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
从表面上看,西方强势国家似乎淡化了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渗透,其实并非如此,“西方中心论”却鲜明地反映出一种霸权和侵略色彩。如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正在向世界各国全面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从影视、书籍到服装、餐饮等,这些无不体现出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扩张。而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积极推行自己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西方现代话语霸权的根本特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大国正在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来达到谋取世界霸权的目的。它既不在于军事和武力,也不在于经济和政治,而在于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本身。
目前,西方国家正在通过政治霸权渗透和推行其文化霸权,因而这也就意味着西方推行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很难实现平等话语。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对外交往和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往往迫使对方接受其不公平的文化条约。如美国电影出口协会首任主席曾宣称:“美国出口的影片在输出国上映时间要占60%以上,如果哪个国家胆敢压缩,我就会提醒该国财长要小心。”[3]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全球化或许会消解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使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坚持文化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们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对认同的向往就越强烈。”[4]这种认同的内容和范围包括对自我民族文化认同和对他者的文化认同或接纳两个方面。两者在平等交往和共存的前提下求得共同发展。如果把文化全球化理解为宰制性的或强权的主宰,这些都不利于和平相处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
有学者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非西方国家无法摆脱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那么,如果非西方国家一味模仿西方国家的文化模式,或否认自我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必然会造成文化趋同现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非西方国家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和能否保持民族文化身份,是关键所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和美国化,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项度的模式,它是由世界不同民族构成的多项度的综合体。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决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竞相效仿的模式。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拒绝全球化,置身于全球化之外,成为一块“飞地”。即是说,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既不可一味地排斥或置之不理,也不能茫然顺从,听之任之,亦步亦趋。甚至失却民族身份和特征。
全球化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强盛,经济落后的国家可能会再度陷入贫困而被边缘化。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它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现象。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能使本国文化保持其固有的地位,不会在世界多极经济和文化碰撞、交流的同时被他国文化同化。
概言之,在跨文化语境的对话中,“一切忽视文化差异的结果,一切抹平少数话语的立场的做法,其最终结果都可能是复制老牌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丧失差异而变成一种平面的模块,那将是人类文化的末日。”[5]
二、文化认同与身份危机
民族文化认同是建立在自我身份确认基础上的,而不是对他者的盲目趋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认同和自我身份的确认遭到了危机,它使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不断地渗透到其他国家。像影视、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卡通片、“麦当劳和迪斯尼以异常诱人的魅力占据了人们的消费领域和想象世界,从而把一种无限扩展的美国消费文化发展到全球范围,它模糊了各民族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因而全球化对我们今后的文化发展战略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6]
不可否认,全球化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尤其是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有学者担心,在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各民族的文化会越来越走向趋同,而造成民族文化的“身份危机”。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果忘却或模糊自我民族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就会堕入“后殖民文化”的陷阱。也就是说,对他者尤其的对强势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如果不建立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就会有丧失的危险,甚至陷入对他者认同的危机之中,而导致在未来的文化对话中失去话语权。
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将会发生碰撞、吸收、排斥、提粹,充满着差异和断裂,拒斥与认同等矛盾。由于一元文化主义和多种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和冲突,尤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不断扩展,它将会导致弱势民族忘却和模糊原有的文化身份,加剧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因此,“一种丧失自我确认的标准与定向、不知所措的分裂与迷茫感正在困扰着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7]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人类自由性创造的价值体现,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无法孤立地存在,它必须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民族文化的交往和对话中来,否则就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中来就没有出路。当然,在介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不坚持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样没有出路。也就是说,“在价值选择上如果故步自封地坚持原有的价值标准是行不通的,但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更是违背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与价值”取向[8]。如今,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9]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土化的产物,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我们应当“着眼于全球化,行动于本土化”。[10]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充满生机的大国文化,具有开放和兼收并蓄的特性,这也就使得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与西方及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往和互动。如今,全球化已经把我们推进激烈的价值冲突之中,“在这种有时会很惨烈的碰撞中,人们一时会模糊或者失去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社会认同,产生新的认同危机。但是全球化带来的观念、物质和感官上的冲击,也会扩大人们的视野,从而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扬弃自己原有的认同。”[11]
因此,我们既要立足于本土,坚持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又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系的组成部分,这也就决定了世界性与民族性本来就是息息相关的。世界上无法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与世界截然隔绝的文化,也不存在世界大同的和失却民族性的文化。在全球化的境遇下,异域文化的因子在不断地影响并渗入本土文化之中,而折射出变形和移位的现象。在我国,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在这里,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积极地参与国际间的交流和对话,又如何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文化认同。换言之,思索文化全球化的审美价值尺度,和在文化全球化的视野中创造和建构中国文化自身的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和必须正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三、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冷战宣告结束,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依照亨廷顿的观点,自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由意识形态和政治之间的冲突转变为文化实体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全球政治主要的危险将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以往那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而,这就需要人们从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视角来审视民族文化和世界政治的关系问题。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文明的冲突模式”将会取代过去的“冷战模式”,世界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文明并非政治实体,而是文化实体,不同文明的差异将会导致价值观念的分歧。在亨廷顿看来,也正是由于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差异才会造成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和冲突。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已经由原来(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升级到难以调节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武力对抗,并带来了恐怖事件的不断发生。这一新的世界矛盾发展趋势的标志,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发端。从此,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种族、宗教之间的差异,即文明和文化认同的差异一直成为民族、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就指出,未来世界冲突和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以宗教和文明为特点的区域性冲突。同时他还指出了导致世界冲突的三大主要文明,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本质性差异。他认为,儒家文明有着巨大的潜力,是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没有认识到其本质。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在于冲突,还表现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不同民族、国家的文明和文化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差异性,也有着一些相通的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在于取长补短,在于促进人类文明和文化共同发展。因此说,如果一味地强调人类文化的同质化而忽视其异质化和只强调冲突而忽视其融合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取的。其实,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和异质互化、冲突和融合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过程。
全球化的过程将意味着一种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和排斥。这也就使得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将会产生一种张力,并不断发生碰撞和冲突。在人类文化史上,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与其它民族文化相互交往和碰撞基础上的。例如,古希腊哲学曾给予基督教文化以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基督教神学曾受惠于古希腊哲学;伊斯兰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启示;在中国思想史上,由于印度佛教文化(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经过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它已远远不同于佛教在印度的内涵。在中国的这片文化沃土上,印度佛教被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本土化的新的佛教宗派和文化内容,它所负载的文化和思想内涵比印度佛教更加丰富。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将会自觉地确认自我的文化身份。我国自古有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传统,我们绝不赞成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强加于他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加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通过对话来达到理解与宽容,也许是实现世界文化走向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希望所在。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
[3] 孙维学.美国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89.
[4]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1.
[5]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66.
[6] 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M]//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7.
[7] 陶东风.全球化、文化认同与后殖民批评[M]//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0.
[8] 叶启绩.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37.
[9]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54.
[10] 罗兰·罗伯逊.西方视角下的全球化[M]//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
[11] 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5.
(责任编辑:司国安)
Multi-culturalCollisionandFusionintheContextofCulturalGlobalization
CAO Guisheng, CAO Yang
(School of Fine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s a kind of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with local features and national charact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does not lie in conflicts but is expressed in the interplay and fus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s well. There is some divergence between cul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s and there are also some communicating aspects. In more circumstances, the interflow and collision between them consist in learning from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set off one′s weakness and propell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human cultures.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 there will not be a single universal culture, but the simultaneous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diversity; western culture; national culture
2014-03-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XJA880005)
曹桂生(1962- ),男,山东单县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阳(1989- ),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G115
A
1008-245X(2014)06-0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