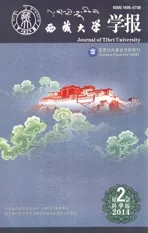犯罪故意的明知内容:社会危害性认识还是违法性认识
2014-03-03薛瑞麟
薛瑞麟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88)
一、明知的内容是狭义的社会危害性认识
依照我国刑法第14条,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1]这里的“明知”是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即意识要素。前不久的通说认为,犯罪故意的意识要素以“两个明知”为条件:一是明知自己行为的实际(自然)性质,即认识到构成事件或犯罪构成的事实,如行为、结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二是明知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即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中,第二个“明知”是对“认识的认识”,属于行为人的价值判断。
目前,这一通说受到质疑和批判,并且火力批判矛头直指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承重结构”——社会危害性。
应当指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虽出自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但它的最早发现者既不是我国,也不是苏联。早在18世纪后半叶,意大利著名学者贝卡利亚就在其成名之作《犯罪与刑罚》中写道:“犯罪的真正尺度是它们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这是既不需要象限仪,也不需要显微镜就能够发现并且是任何中等智力的人都能够理解的显而易见的真理之一。”[2]稍后,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将这一“真理”法律化。该《宣言》第5条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危害社会的行为。”当然,我们也应公正地说,首次明确地将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认识引入刑法典中的是苏联,如1926年《苏俄刑法典》、1960年《苏俄刑法典》。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部分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响起了一片倒社会危害性之声,仿佛落得骂名的社会危害性是破坏法制的“万恶之源”。在俄罗斯,一部分学者断言,为了加强法制,必须把作为“意识形态标记”的危害社会性彻底清除。他们在刑法典草案中建议用“造成损失”取代社会危害性概念,因为刑事立法不仅保护社会利益免受犯罪侵害,而且也保护个人合法利益免受犯罪侵害。这些学者提供的犯罪定义是:“犯罪被认为是刑事法律所禁止的对个人、社会或国家造成损害或者造成损害危险的行为。”[3]不过,上述建议并未被立法者所采纳。如果该建议付诸实行,社会危害性认识也就成了无皮之毛。
不同于俄罗斯,在塞尔维亚、黑山两国,主张犯罪概念去社会危害性化派已取得了胜利。依照其刑法典,犯罪不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而是违法有责的行为。在编纂刑法典的过程中,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兹·斯托扬诺维奇竭力主张清除来自苏维埃刑法中的、威胁法治基础的社会危害性概念。在以法治国原则为依据的刑事立法中不应当有它的安身立足之地。他还语出惊人:“社会主义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所追求的目的与法西斯刑法中的‘健康人民的感受’别无二致。”[4]
在塞尔维亚、黑山,实现犯罪概念去社会危害性化,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渴望加入欧盟,另一方面也同它们接受了西欧的刑法理念有关,因为西欧诸国的立法和理论把犯罪形式概念奉为圭臬,排斥以社会危害性为实质内容的犯罪实质概念。
在我国,主要在刑法教义学层面来讨论社会危害性的去留,很少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一部分学者对社会危害性说“不”,主张“应当把社会危害性这个概念摒弃、排除出去。”[5]因此,对这些学者来说,用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认识是在犯罪故意问题上合乎逻辑的反应,其主要理由是:其一,社会危害性认识依托于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是超规范概念,是社会对有害行为的一种政治上的否定评价。只有在理论刑法学层面探讨立法者基于何种理由将某种行为确定为犯罪才最有意义,而在规范刑法学层面,它并不具有基本的规范质量,更不具有规范性,不能成为判断犯罪成立的直接标准;违法性是刑法对行为违法的一种法律上的否定评价,是对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一种直接的、客观的评价,因而具有客观性。其二,社会危害性是模糊性概念,而违法性是明确性概念。社会危害性是站在社会整体立场上对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出来的结论,是抽象的评价,因而,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的认识水平、出于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同一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违法性依据刑法规范进行判断,标准是明确的,而结论也是唯一的。因此,从概念本身的科学性来看,违法性认识更科学,违法性认识必要说更为可取。[6]有的学者还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来证明,把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成立的条件是错误的,也是不可取的。例如,行为人在随地吐痰时认识到这种行为对社会有害,而事实上该种行为确实有害于社会,但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犯罪的故意。[7]
以上论说事关重大,涉及刑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必要严肃地讨论。
其一,社会危害性是否为“社会对有害行为的一种政治上的否定评价”?
在我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是行为的社会属性,具有原初性。它不以立法者的评价为转移,用李斯特的话讲,“法律只能发现它,而不能创造它。”[8]在法律发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前,社会舆论可能对一些行为(如醉驾、飙车等)已作出了否定评价,即认为它们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公正客观地说,社会上的否定评价还称不上政治上的否定评价,社会也不是政治评价的合格主体。但是,如果立法者接受了社会上的评价,这种评价就会发生质变,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否定评价。因为立法者是当权者,他将某种行为评价为对统治秩序有危害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立法者将行为评价为社会危害行为是以刑法规范为形式的。例如,我国刑法第13条所说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是例证。此时的评价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否定评价,不如说是立法者在自己的决定中体现大众民意的法律评价。因为无论行为具有多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立法者没有以法律形式加以禁止,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就不是犯罪。所谓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不是指“裸”的社会危害性。它以刑法规范为形式、为前提,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并且与刑事违法性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统一关系。”[9]
笔者认为,把社会危害性视为“社会对有害行为的一种政治上的否定评价”,是不确切的。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的特点。
其二,社会危害性真的“不能成为判断犯罪成立的直接标准”?
主张把社会危害性概念从刑法中扫地出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它不具有规范性,不能成为判断犯罪成立的直接标准。社会危害性术语源于刑法社会学或者犯罪学。后者所说的社会危害性的确不具有规范性,但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是否也如此呢?众所周知,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采用“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即刑法既定性又定量。例如,刑法第13条在犯罪的一般概念中除了描述它的基本特征(性质)外,还载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定量因素。刑法分则也是如此,它设有大量的“罪量要件”,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严重后果”等。有的学者认为,“数额较大”等是刑事违法性的标志要件。[10]笔者分析,它们既是刑法违法性的标志要件,也是展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要件,或者确切地说,是集两者于一身的要件。这些罪量要件各有其特点。“数额较大”、“严重后果”是对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限定,具有单一性和客观性的特点;“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则是一种综合性的要件,既可以是对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限定,也可以是对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限定,具有综合性和主客观相统一的特点。
我国刑法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数额较大”等罪量要件是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一种底线式的限定”,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具有定罪功能。通说认为罪量要件具有定罪功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罪量要件是相关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要件具有概括性,立法者并没有揭示其具体的内容。在实践中,它们的定罪功能是借助于司法解释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司法解释的精确定罪或者填补具体的内容而成为可以直接适用的标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第1条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这里,作为诈骗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11]体现的“数额较大”得到精确量化,从而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又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第5条,偷越国(边)境罪中的“情节严重”,是指:①在境外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的;②偷越国(边)境3次以上的;②拉拢、引诱他人一起偷越国(边)境的;④因偷越国(边)境被行政处罚后1年内又偷越国(边)境的……。以上可以看出,彰显偷越国(边)境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节严重”的内容被具体化了,并成为区分该罪与非罪的标准。应当指出,不是“裸”的社会危害性,而是它与相应的刑法规范一并履行定罪的功能。关于社会危害性不能成为判断犯罪成立的标准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至少是片面的。它没有考虑到我国立法的初步定量、司法再精确定量的特点,也有意或无意地把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对立起来。
其三,社会危害性是否为“模糊性概念”?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模糊性与明确性是相对的,对事物的概括取决于观察的视角。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概念,学者们对它的看法不一。一些学者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持狭义理解,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或现实威胁。[12]这种意义的社会危害性是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是一种纯客观的社会危害性,不包括犯罪的主观方面和行为人的自身情况。狭义的社会危害性与李斯特所倡导的实质违法性概念十分相近。在他那里,“实质违法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违法行为是对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集体的重要利益的侵害,有时是对一种法益的破坏或侵害。”[13]
多数学者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持广义的理解,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由行为的主客观诸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是由纯客观的行为自身决定的。[14]显然,后者的观察角度不同于前者,他们把社会危害性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立足于它的结构分析,认为凡影响和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质与量)的因素均属于社会危害性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不限于犯罪构成的诸因素,如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还包括犯罪构成之外的一些因素,如减轻处罚的情节和加重处罚的情节。苏联著名学者A·H·特拉依宁对广义的社会危害性有一个生动形象的说法,即“社会危害性是由犯罪的全部因素的相互融合而溢出的。”[15]这里,A·H·特拉依宁讲的是犯罪的全部因素而不是犯罪构成的全部因素,显然他对社会危害性也是持广义理解的。社会危害性概念是我国刑法理论的“一个根本”,对于行为的犯罪化或去罪化以及刑罚的适用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持广义理解的学者对这一根本性概念的研究却不令人满意,其中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有学者批判社会危害性概念具有模糊性也源于此。
现在的问题是,狭义的社会危害性是否也属于模糊性概念?如前所述,狭义的社会危害性是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实际侵害或现实威胁,它不包括犯罪的主观方面和行为人的自身情况(责任年龄、责任能力等)。因为对行为人的认识来说,无论构成要件事实还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都是外在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危害性的再认识是以排除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处在犯罪之外的行为人的自身情况为条件的。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日本也有所见略同者,只不过他们用的术语是实质违法性或违法性之实质。如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违法性之实质,乃客观的‘法益侵害’,故主观要素之故意,对违法性之有无、程度,完全无影响。”[16]据李海东先生的研究,德国在违法性判断中,具体行为人的特点是不加考虑的。[17]基于此,笔者认为,狭义的社会危害性概念并不模糊,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它是“任何中等智力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一种对社会危害性泛化理解的倾向,“随地吐痰”以及“从楼上向下倒污水”等事例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援引这些例子的学者企图证明,把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是错误的。我以为,错误的一方很可能是援引前述事例的学者们。大家知道,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的成立以行为人的两个“明知”为条件的,即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以及在此基础上明知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随地吐痰罪”和“泼倒污水罪”,因此,随地吐痰等行为不属于构成要件事实,对它们的认识也不是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我们讲的构成要件事实是由刑法规定的,这表明符合构成要件事实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或者“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把符合构成要件事实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悖德行为的有害性混为一谈,是对社会危害性的泛化理解或者曲解。当然,我们也应指出,认识、把握社会危害性的性质、程度及其结构,是我们法学家的任务而不是行为人的义务。对于后者,奉行“外行的平行判断规则”,即只要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危害社会就足矣。后一认识属于价值判断,即行为人根据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常情”所作出的是非善恶的判断。
二、主张违法性认识有超前之虞
在主张以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学者那里,对违法性中的“法”的理解也不尽相同。随着认识的深化和优胜劣汰,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刑事违法性认识说。违法性中的法是指刑法,而违法性认识则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违反刑法规范或者为刑法所不容许的认识。刑事违法性认识说的倡导者是陈兴良教授,他认为“在违法性认识范围内,还是应当采取刑事违法性认识说。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在罪刑法定的构造中,具有明确的界限,应当成为违法性认识的内容。”[18]五年之后,他又深化了前述认识,指出“由于违法性认识是以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为前提的,因此,违法性认识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19]这里,陈兴良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违法性认识是对自己的行为违反具体刑法规范的认识。
其二,一般违法性认识说。违法中的“法”是泛指国家颁布的一些法律法规,如刑法、民法、行政法规等,而违法性认识则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规范或者为法律规范所不允许的认识。在我国,倡导该说的有刘明祥教授等。他认为,“把违法性认识解释为是违反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意识较为合适。”[20]
如何看待前述两种学说?值得研究。我认为,刑事违法性认识说的优点与缺点都比较突出。就优点而言,首先,它在理论上具有自洽性。刑事违法性是我国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犯罪故意是行为人对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在心理上的反映,将刑事违法性认识视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在逻辑上具有融贯性,毫无问题。其次,刑事违法性认识说有助于区分犯罪故意与民事违法行为故意和行政违法行为故意。前述部门法中均载有故意,其共同点是同实施违法行为的责任密切相关。犯罪故意同刑事违法行为相联系,是行为人对它在心理上的反映;民事违法行为故意同民事违法行为相关联,是行为人对它在心理上的反映;行政违法行为故意同行政违法行为休戚相关,是行为人对它在心理上的反映。明确把刑事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内容,就在形式上划清了它与民事违法行为故意、行政违法行为故意的界限。此外,刑事违法性认识说所蕴含的理念也值得称道和认同,即该说“更倾向于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倾向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尤其是限制国家的刑事追诉权”。[21]不能说这只是一些仁爱的词句,恰恰相反,这些词句表达出刑事违法性认识说倡导者对个人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和渴望。
在笔者看来,刑事违法性认识说的最大不足是脱离了我国的现实国情,或者说,它对我国社会显得太超前了。因为无论是立法者、司法工作者,还是社会法律意识,都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刑事违法性认识说的程度。从立法上看,刑事违法性是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主张刑事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的明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辩护。但是,我国刑法第14条明确规定社会危害性认识是犯罪故意的明知内容。立法者的这条规定显然是基于对我国现实国情的慎重考虑而作出的,并表明对刑事违法性认识说的态度。为了使自己的主张不与立法该条规定相抵触,刑事违法性认识说倡导者提出,“应当坚持社会危害性认识与刑事违法性认识相一致的观点。”[22]如果两者真的“相一致”,那恰恰是我们所期待的,但问题在于,刑事违法性认识说倡导者所主张的“刑事违法性认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其属性来说是抽象的,因此,行为人对它的认识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如何“相一致”?
从审判实践的情况看,据笔者的不充分调查,司法工作人员的出发点是,只要行为人在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的基础上明知自己行为危害社会,就认定成立犯罪的故意。形成这种思维定势和操作习惯的主要原因在于刑法第14条规定。此外,对于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判断行为人有无社会危害性认识,比判定行为人有无刑事违法性认识要相对容易些,且不会放纵犯罪。如果坚持刑事违法性认识说,就会使司法工作人员陷入尴尬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行为客观危害严重,但因行为人拒绝承认有违反刑法的具体认识而无法证实,依照刑事违法性认识说,恐怕只能放弃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做社会能答应吗?另一方面,由于司法体制的原因,我国的法院尚不能完全独立,它们常态性地面临着外界的干预和压力,或者被要求在办案时践行“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很可能作出另外的选择: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不问他是否认识到行为违反具体的刑法规范,就推定其具有刑事违法性认识。这样一来,“就使得对法的认识努力瘫痪了”,[23]也难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当然了,上述情况含有假定的成分,但也不是随意的、没有根据的假定。
从现实国情看,我国人口众多,国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法律意识不强。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刑事法律变动频繁,法条急剧增多。更要命的是,刑事违法性认识说要求犯罪故意的成立以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具体的刑法规范为条件。这样的要求显然太高了,不仅犯罪行为人难以企及,就是法律工作者也不可能知悉所有的刑法规范。
总之,我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将刑事违法性认识说付诸实行的现实条件。如果坚持实行,就可能产生南辕北辙的消极后果。
同刑事违法性认识说相比,(一般)违法性认识说把认识对象的范围界定得较为宽泛。违法性认识说的认识对象不限于刑法规范,还包括民法和行政法规范等,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规范,不论违反何种法律规范,均可以成立故意。违法性认识说源于德国,其首创者为宾丁,是他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该理论,行为人只有借助违法性认识进行行为时才成立故意的罪责。易言之,违法性认识是故意成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里,宾丁创造性地提出了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不过,他所说的违法,是指违反成为刑罚法规前提的规范,即根据法律的规定论理上推导出的规范。[24]
二战结束后,“目的行为论”走上了德国刑法理论舞台的中心,成为光彩夺目的主角。与此同时,故意论被进一步边缘化了。在目的行为论中,威尔采尔奉行“适当破坏原则”,通过拆散主观心理事实与价值评价联姻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规范性罪责概念。具体而言,就是把弗兰克的二元罪责概念变为一元,把作为对行为和结果反映的心理事实(故意和过失)以及过失犯罪中的客观注意义务转移到构成要件中,罪责(责任)概念只保留规范性要素,即可非难性。在威尔采尔那里,可非难性的成立因素变成了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应当指出,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从理论上讲,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一对历时性矛盾范畴。可能性是指包含在事物之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25]可能性在具备一定条件下转变为现实。而现实的展开则表现为必然性,它高于可能性。不过,威尔采尔并不要求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而是把它设定为现实的可能性。经过威尔采尔改造更新的罪责理论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强势理论,它认为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条件,在完整的罪责中也不是必需的。[26]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德国刑法典》第17条规定,即“行为人行为时没有认识其违法性,如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则对其行为不负责任。如该错误认识可以避免,则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被罗克辛称为“标志着一种历史性的转变”[27]的第17条规定在对违法性认识说说“不”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跟随”了规范罪责(责任)论,即确认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罪责的成立因素。
至于我国一些学者主张的违法性认识说,涉及一个理解的问题。如果将违法性认识的对象限定为违反法律规范,就会重蹈刑事违法性认说脱离实际的覆辙。因为一个不知刑法规定的人,未必就会知道民法规定或行政法规定。当然,不排除有的人既懂刑法也知晓民法或行政法,但这样的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所占的比例甚小。从实证刑法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数据,是比例的大小。
笔者不认同违法性认识说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它与我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不能兼容。不同于德日,我国在立法上提供了犯罪的一般概念和故意犯罪概念,并且指明它们的特征。从这些规定看,违法性既不是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也不是犯罪故意的明知对象。在笔者看来,它不接地气,也难以与我国的立法和理论相契合。
三、结语
通过对前述诸观点的评析,可以看出,笔者赞同社会危害性认识说,并且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坚持此说仍是必要的、合理的。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认识说的最大软肋在于,对于“大义灭亲”、“为民除害”、“安乐死”等案件,它无法自圆其说,存在着主张与现实的明显矛盾。在“大义灭亲”等案件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审判实践的情况看,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处理规则是:不免责但酌情可以减轻责任。对于法院实行该规则背后的潜台词,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但它至少不应成为否定社会危害性认识说的理由。因为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由于错误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该错误认识并非不可避免,追究其刑事责任,与法、与情、与社会危害性认识说并不相悖。当然了,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我们不妨参照德国的做法,让在刑法上“不可交谈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借鉴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增强法院应对此类案件的适应力,而且也有助于维护行为人的自由和权利。从这一点出发,我不赞成社会危害性认识说与刑事违法性认识说的择一说。因为“两头堵”的择一说虽然在理论上左右逢源,但它的实质是主张双重标准,因而在逻辑上不具有彻底性,同时也可能使行为人与免责或减轻责任失之交臂。
[1][1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201,72.
[2](俄)H·ф·库兹涅佐娃,И·M·佳日科娃.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上卷)[M].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31.
[3](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总则》(草案)[G]//犯罪学家论丛,1993(1).
[4](俄)全俄第四次刑法·刑事执行法·犯罪学国际会议材料汇编[G].莫斯科,2009:779.
[5][6][7]陈忠林.违法性认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239,239.
[8][13](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2,201.
[9]姚渂君.现代刑法思潮下的未遂犯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45.
[10]阮齐林.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45.[11]社会危害性程度是社会危害性的量的指标。
[14]何秉松.刑法教科书(上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46.
[15](俄)国家与法[M].2010(6):70.
[16](日)川端博.刑法总论二十五讲[M].余振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5.
[17]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1.
[18]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9.
[19][21][22]陈忠林.违法性认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39,123.
[20]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44.
[23][26][27](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12,611,611.
[24]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306.
[25]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