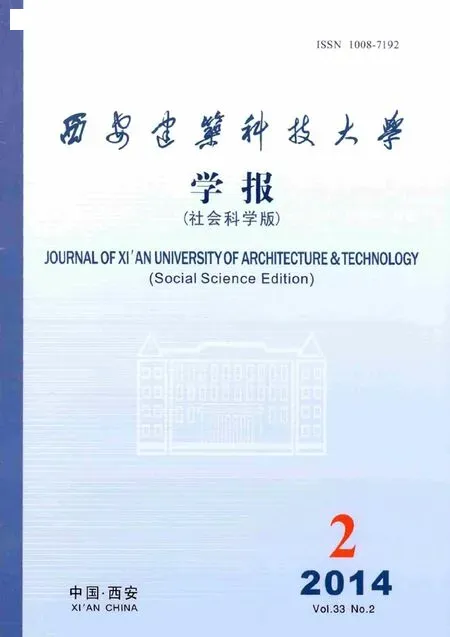德里达“幽灵政治学”伦理形态的出场逻辑
2014-03-03孙全胜
孙全胜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89)
解构主义是过去几十年影响甚大的一种思潮,它的方法不但普遍地融进当代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而且深刻指导了人类实践,尤其对建筑和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解构主义不是一种凝固的理论立场,它的精神勇气和宽容气质,使它具有悲世情怀和救世情节。伦理作为外在规律的内化,其形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在生存的目的达到后,寻求精神家园就变作了更深层次的追求。学会真正地生活,正是“幽灵政治学”的伦理向度。
一、“幽灵政治学”伦理形态出场的逻辑起点:如何学会更好地生活
德里达沿袭了柏拉图“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的观点,在他看来,生活与死亡紧密相连,死亡既是生活的仇敌,也是生活的朋友。“学习生活,应当是学习死亡,为了接受死亡而充分意识到生命的绝对有限性”[1]65。的确如此,人一出生,双腿就朝向死亡之路。我们既无法改变前进的方向,也不能放慢沉重的脚步。死亡从背后紧紧掐住我们的脖子,令我们只能做徒劳的反抗。死亡成就了生活,也成就了哲学。上帝在此处为你关闭一扇门,在别处就会为你开启一扇窗。人生有终点,却无法预知过程。通达生活的真正意义,是幸福中最大的幸福。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 ”探讨“幽灵”的话语与指令,就是为了让人们学会更好地生活。
首先,德里达声称,死亡是通达生存意义的唯一道路。
只要我们活着,就应该向死亡学习,因为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就是矛盾。明知道人生的终点便是死亡的家园,将来,人人都只不过是一座孤坟。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会更好地生活?人生天地之间,命运的魔君故意捉弄我们,让我们戴上死亡的枷锁。假如人生只是如幻的泡影,醒来之时便是死亡来临之时,我们但愿永远不再醒来。可既然活着,就不应该辜负命运的安排,就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学会更好地生活,从希望开始。的确,怎样才能获得生存的真正价值?这既是我们必然会遭遇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省察的问题。接着,德里达就开始了对这句指令的解析与论证,他反问道:“但为什么是最终?”[2]1学会生活,这句“习惯指令”,是前辈传给我们的,既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经过分析。正如德里达自己迷惑的:“我们会懂得怎样去生活吗?”[2]1因为我们是不能依靠自己学会更好地生活的。也就是说,单个的人既无法通过自己弄懂生命的意义,也无法凭借现实来弄懂生活,必须通过“第三者”且必须凭借死亡才能通晓生存的意义。凭借死亡弄懂存在的意义,既无法形成完全的价值,又无法百分之百地实现,但这是灵魂独行的必经之途。因为,只有在面向死亡之时,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才会呈现。永生的代价就是经历死亡。每个人都毫无理由的出生,又必然的死去。在死亡的审视下,人孤独地栖居在寂寞的星球上。
因此,在德里达看来,人生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永恒之死亡,引领我们向上。一切存在都是虚幻的,唯有死亡才是实在的。死亡如同深谷,面对它,人不可能不恐惧和战栗。人在死亡谷地的边缘上行走,难免战战兢兢。死亡把虚无带入人生。死亡的出现,既凸显了生命的意义,又建构起生活的桥梁。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更好。人生如同一座空坟,垒筑它是为了拜托它的纠缠,从哪里远行,到达新的生活。肉体和灵魂没有太多关系,人生只是沧海一粟,死亡才是永恒,死亡的降临使生活的价值突显出来。而且死亡总是迫不及待,很少有人是死于衰老,而绝大多数人都死于提前的“意外”,绝大多数人死前都相当痛苦,因此,死亡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这里,德里达把学会更好地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与死亡的交流中,要求人们重视死亡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德里达声称,学会更好地生活的路径,只能在生与死之间找寻。
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经历和体验死亡,而且单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很有限的,或许终其一生,也弄不懂生活的真正价值。但我们可以通过幽灵的默示来思考日常生活的断裂。“幽灵政治学”就是一个利用幽灵的默示来认识人生的学问。哲学家惟有与幽灵开展对话交流,才能弄懂生活的意义。人生若要获得完全的解脱,预许要走的必由之路便是死亡,“学会生活,如果此事有待于去做,也只能在生与死之间进行”[2]2。而且只有与鬼魂交流才能维护生存的意义。被传统遮蔽的“幽灵”隐身不见,为的是让人们反观自己的心灵,为的是让人们用生命去交换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它意味着重生,意味着精神的胜利,意味着继续另一种生命。被遮蔽的“幽灵”是人类通向永恒的指引者。以往的学者忽视鬼魂的指令,“传统的学者不愿相信鬼魂的存在——也不愿相信可被称做幽灵的虚幻空间的所有一切”[1]13。对待幽灵要充满善意和温情,不仅要很真诚地相信它们,还要对它们的处境充满同情。尽管,“幽灵”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从另一角度,“幽灵”又是存在的,它就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存在于宗教、艺术、文学等当中,它是人的一种意识。幽灵如同具有生命力的人类一样,我们务必学会怎么与其融洽共处,并视需要,或对其妥协,或对其关怀,或施与同情。和幽灵共存,就是与死亡共存,死亡对人充满悲悯,它看到人的可怜、凄惨、痛苦,决定把人带离悲惨的世界,到达一个没有苦难的国度。
最后,德里达表明了“幽灵政治学”的伦理指向:某些“既不在场又无生命”的鬼魂。
德里达锋利的批判和无情的解剖绝不只是“怨”和“恨”,而是爱憎分明。他的思考以个体的发展为立足点,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境况。个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宏大的世界,过去那种以二元的对立统一观点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是人类的狂妄。人类永远无法了解整个宇宙的全部相关内容,只能宽容地看待一切;但只要人类能够继续存在,人类了解自然的水平就会愈来愈高。德里达触动了长期占据人们思想头脑的定见,对已经融入了我们血液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做了不懈的反抗。经过探询和思考,德里达得出结论:我们要学习的鬼魂实际上是“某些既不在场、当下也无生命,某些既不会向我们呈现、也不会在我们的内部或外部呈现的其他东西”[2]2鬼魂始终徘徊于不朽与可朽之间。鬼魂脱离自肉体,其过程无比痛苦,因此,灵魂在走向空洞前会给人们一些提醒。人们期待的那鬼魂其实早已在专制和高压下退场。于是,我们不禁思索,这个已经退场,将来必定继续出场的东西,如今“在哪里?”“明日在哪里?”“向何处去?”[2]3问题被归结为:什么东西会在必将到来的将来出现?而这个东西之所以会在未来必定显形,是因为它曾出场过,它曾经发挥作用。德里达声称,正义独立于人的生命存在之外,是内心道德律的外化。而如今就发生了时空错乱,这个脱节的时刻既不依附任何时空,可幽灵出场需要的就是非时空的时空。幽灵的出场,从来就不选择具体的时空,它惟有轨迹:“‘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哈姆雷特》)”[2]3。正义的责任需要有人承诺,而且,必定有一个灵性的存在,以确保普遍正义的实现。因此,正义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必须遵行的价值法则,是衔接在场者与他者的桥梁。
因此,德里达所谓的某些“既不在场又无生命”的东西就是正义等法则。人们要弄懂存在的意义,就必须接受这些价值法则的指引。异端不是思想的异数,而是思想的常态。为了粉饰自己,掩盖罪孽,推卸过错,而开始的自欺欺人,是人类的懦弱。但比谎言更可怕的是不原谅、不宽恕。因为,能够纠正谎言的不是真诚,而是宽容。宽容是引领人们学会更好地生活的明灯。解构启发我们要有面对真实的勇气,更要有宽容的气度。
当整个时代沉沦于歇斯底里的无序争斗之时,德里达无所畏惧,挺身反击传统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霸权。在这场“正统”与“异端”的比试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个人独立思考的尊严。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不仅打开了思想发展的一扇门,而且为我们学会更好地生活开启了一扇窗。善恶一体,苦乐相随。我们要活着,必须让牵挂、真爱、责任在心中扎根;我们要活着,必须用死亡限制放纵,用死亡平抚心灵。要理解限制的意义,人就必须历经死亡;而获得意义,必须全心全意,必须在时间中慢慢生成,不是靠占有和索取,而是靠真爱和创造,靠灵魂的参与,如同履行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类是愚蠢的,怕死而好斗,珍视生命却不断作恶。无论幸福还是痛苦,最后预示的都是死亡。整个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死亡共舞,可我们丝毫不察。世界被死亡管辖。死亡一直被深深地歪曲着,其实死亡无比宁静安好,它有着永恒而迷人的微笑,它有着宽阔而广博的襟怀。安宁地来到这个世界并穿越死亡的人,就是智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而悠然自得才是最大的不幸。真正的可怕不是死亡,而是麻木。以功用论人生,则人生的意义全失。当然,死亡不是起点,而是历经千辛万苦必定要走的路,它意味着重生,意味着精神的胜利,意味着继续另一种生命。结束并不是停止,死亡也不是终结。死亡是人类通向永恒的指引者,生命是能够穿越虚无之门,到达永生的。弄懂生存的意义必须借助偶像的力量。经过反复思考,德里达表明了要弄懂生活必须参拜的偶像: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因此,德里达对“幽灵”的维护和解说,也就成了“在生死之间如何生活”的思索,而思索的伦理指向就是学会更好地生活。
二、“幽灵政治学”伦理形态出场的逻辑展开:何以持守正义与良知
何以持守正义与良知?是德里达幽灵政治学的伦理向度。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目的是给世人寻找美好生活道路,可革命运动带来的也并非总是希望和价值。于是,走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还是惨淡收场。苏东剧变,一方面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纷纷庆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另一方面是前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些所谓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纷纷改换门庭,真是世态炎凉,墙倒众人推,马克思主义成了和法西斯主义等同的名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黑暗内幕暴露在世人面前,使人们有如梦初醒的感觉。正当此时,一直对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德里达却公然为马克思作了辩白。
也许思考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人不是单靠食物活着的,人具有审思的能力。如何生存,需要我们用心思考。思想是人类的自由之路。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人生,这是自古以来,人们不断提出的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问一位饥饿的人,他要说的是食物。如果我们问一位单身汉,他要说的是爱情。如果我们要问一位临死的人,他要说的是活着。可“人们还是一生下来就不得不承担一些责任”[2]23尽管这些责任就如同像在没有人认罪的时候,由你来承担罪责。哈姆雷特本来是犹豫苦闷、没有行动打算的,但由于父王幽灵的蛊惑,他胸中燃起复仇怒火,采取了决绝行为。混乱的时代会把原本不起眼的人推向历史前台,成为英雄,“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3]33而相应的是,断裂的时代正是良善能够出场的条件。
德里达谈论的是“幽灵”,这与死亡有关。死亡是人的一种仪式,是一种终结,也是一种新记忆的开始。人永远不能逃脱自己的死亡,这不是很诧异的事情吗?可死亡又是什么?死亡之后就真的是一无所有吗?也许,我们可以选择生存还是死亡,也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但是却永远不能摆脱死亡的降临。我们甚至根本就不曾选择要做一个人。面对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除了顺从,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人死之后还会有生命吗?生命为何要回归虚无?这是如此的不公,却毫无办法。沉沦堕落,或许可以使我们暂时忘记人会死这件可怕的事情;但只要努力思索,就会知道这是绝无可能摆脱的命运安排。这个世界只是一局棋,每个人都充当着自己的角色,没法转换自己的宿命。冥冥之中,结局已定,如同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布局,无法改变。只有通过死亡,我们才能确信曾经存活过。德里达是对社会满怀激情的责任意识的。他完全相信自己,不相信传统和现实,没有这份责任意识和大胆无畏,就不可能有后来他公开声明自己的哲学要成为摧毁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武器。生命本是矛盾的存在,死亡不会终结矛盾,而只是让矛盾暂时隐形。死亡会把黑暗角落里的幻影展示出来。幻影不是无所作为的,它会以生前的样貌重返世间,发出指令。幽灵因为自己的罪恶只能处于游荡状态,这既让人们充满恐惧,又让人们怀有希望。既然,死亡不过是我们必须要走的另一条路,那么就任凭现在埋葬过去,因为埋葬不是退却,而是前行;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不是死亡,而是新生。但有时一些东西是无法忘记的,因为它们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渗入我们的血液,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忘了它们,就是忘了我们自己。马克思的“幽灵”既是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又是我们自己,所以是隐形的在场者。
通过揭示现实的异化,德里达号召人们摆脱既定现实,从而超越脱节的时代,认清世界真理。在脱节的时代,德里达决心承担起拯救时代的重任。他要担负的责任就是:在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引导下,提醒人们持守正义。正义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的生存就失去价值,“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165。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彰显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求,检验着正义的完善性,所以,批判精神的出场并不是徒劳无功,而是以不在场者的身份导向生存的真正意义。因此,可以把苏东剧变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涅槃”,马克思主义是带给人世间光明和正义的使者,它背负着人类的一切理想和爱恨情仇,投身于烈焰中自焚,以旧生命的毁灭换取新生。在肉体饱受轮回之苦后,它才能以崭新的面目复活。因此,苏东剧变绝不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眼烟云;也不是“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闹剧。它只是经历了暂时挫折,不是“落了片白茫茫真干净”的惨淡落幕。
马克思的“幽灵”与精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德里达声称,马克思的“幽灵”内蕴着诸多精神,具有精神的特质,“它有着精神的性质,它来自于精神,就好像精神的幽灵般的重影一样追随着精神”[2]123。德里达剥离出了马克思“幽灵”的精神内核:正义精神。这种正义兼具三重色彩,既是“哈姆雷特”要实施的“复仇”的正义,也是马克思号召的“弥赛亚性”的正义,还是德里达倡导的“解构”的正义。
首先,德里达考察了“复仇”的正义。“复仇”的正义虽然常与惩罚相联,但仍能给人学会生活的启示。
复仇是哈姆雷特必须执行的使命,也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但哈姆雷特对复仇是犹豫悲伤的。虽然,母亲的“背叛”的确不应该,使人伤心欲绝,但复仇是否就可以实现正义?他在不断追问:顺从命运的安排还是挣脱复仇的牢笼?有些事情根本不能了解,我们只能认清自己。有很多事情也根本无法预料,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也无法解脱。流泪、自责、痛骂都无济于事。既然无法避免,既然这是命运的安排,就顺从它好了,既然无力改变颓败的世界,只有先改变自己。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就是因为惩罚式的正义代表了血腥与暴力。复仇能够实现暂时的正义,但带来长久的黑暗和失衡。现实的不公义,让哈姆雷特的心情极度槽糕。复仇必须执行。但复仇的意义何在?复仇能毁灭邪恶,却不能带来美好。复仇实质上是一种惩罚,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彰显的是善恶极端对立的理念。复仇式的正义体现的只是强者利益,表征的是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资本扩张的罪孽,本质上也是一种复仇。怀着对未来的恐惧,斯大林批判资本,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势力的帮手。要想获得新生,就必须历经地狱之火的焚烧,就必须历经由死向生的锤炼,倘若经历不了狱火的考验,侥幸得来的新生也只是昙花一见。马克思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5]。共产主义坚持善恶对立的法则,主张“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寒冬般的冷酷”。这显然与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相悖。解构就是要消解僵化的二元等级秩序。弥撒亚要拯救的不是善人,而是罪人。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手段。它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6]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叙事,对人类而言,“它所造成的创伤远远大于精神分析学的打击”[2]95。
其次,德里达阐释了“弥赛亚性”的正义。马克思“幽灵”的弥赛亚精神,将继续发挥作用,号召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围堵。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弥撒亚”,鼓动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国家,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马克思作为一个犹太人,自小受到犹太教的熏陶,后来又随着家族改信基督教,深深崇拜弥撒亚精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号召“显示的是耶稣复活”[2]100。生活不是美丽的幻想,而是空虚无聊的困境。苏联体制营养不良,没有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持久的光彩。马克思主义的暂时离开,我们要懂得放手。因为任何事业要取得成功,务必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对于苏东剧变,我们不必太在意,也不必隐藏什么,它只是历史的必然之路。“没有什么看起来能比位于《马克思的幽灵》核心处的弥赛亚性和幽灵性离乌托邦或乌托邦主义更远的了”[7],马克思思想指向共产主义社会,并内蕴着弥赛亚精神,既能给贫苦大众以精神的抚慰,带给他们希望,又能号召大众追求幸福未来。共产主义即使再践踏公民人权,在最初它也是抱着打破不平等旧世界、使人们更好地生活的崇高目标的,而且它的一些罪过也并不是有意为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作为一个犹太人,自小就受到宗教熏陶,坚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8]。但一连串的打击后,他否定了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但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精神给了他毕生的影响,使他不自觉地学着上帝的样子,要给人类建造地上天国。作为人类最终理想的共产主义,必定是永恒的图腾。马克思,崇尚的是集体主义。而西方自由主义,崇尚的是个人。它强调要尊重每个个体的人。国家的创立,只是契约,是为了维护个体的利益。而争取个体利益,就是争取国家利益。马克思对未来充满激情和职守,他完全相信自己,不相信任何鬼神,没有这份自信和大胆无畏,就不可能有后来他公然宣称无产阶级哲学要成为摧毁旧世界的武器。马克思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义务。可追求人类解放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各种宗教也在追求,只不过,它们的救世主是神,开出的方法是“爱”和“宽恕”,他们要建立是“天国”。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自己才是救世主,他开出的方法是“斗争”,要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最后,德里达申明了“解构”的正义。解构与正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在解构思想之中,“正义”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实现正义是解构的宗旨,德里达高举正义的旗帜,是为了彰显多元的价值。解构是对不可能的肯定,是对宽容和良知的呼唤。正义是无法解构的,因为正义代表着人类永恒的伦理追求。正义是不会退场的亡魂,它不仅使解构行为得以进行,也是解构行为进行的必要条件。“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主义不可解构,它是一切解构的前提,但它不是确定性的基础,也不是cogito(我思)的坚实基础……这是一个准先验的假设”[9]。在高度集约化时代,持守真理和良知不是为了复仇或破坏,而是为了实现那种超立场的正义。解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完全的正义,正义是解构能够顺利进行的源泉和动力。德里达认为,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就会造成对个人合法权利的干涉。作为公平的正义,依然为民众所憧憬着,向往着以此为原则构建出个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但这只是幻想。因此,解构“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10]“解构”的正义建立在“宽恕”的基础上,宽恕并非宽恕可以宽恕者,而是宽恕不可宽恕者。惟有不可宽恕的他者存在,宽恕才可出场。马克思与德里达的立场显然不同,马克思的个人目标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就会是最幸福的人。而德里达显然不想为了成为最幸福的人,而去做一些事。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残害自己的同类都是不正确的,即使打着再正义的旗号。完全正义的构建不只是理论的构想与期冀,更是我们强烈的现实追求。真理往往是朴素的,而善良往往是纯粹的。正义通常很简单,而生活通常很平凡。“解构”是对未来完美“乌托邦”世界的追求,也是试图让被现实遮蔽的正义精神重新出场的努力,还是对不可宽恕的人和事的同情与怜悯。“解构是传统之子,更是传统的‘叛徒'”[11]。在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偃旗息鼓之时,正义的精魂将继续承担点燃人们内心希望的责任。然而,把解构认作就是正义,也会给人形而上的感觉。麦柯·瑞安也明确指出,“千百万人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遭杀身之祸,然而没有谁因为他或她是解构主义者而非得去死”[12]。
三、“幽灵政治学”伦理形态出场的逻辑指向:为何是更好地生活的允诺
伦理形态,即伦理理论形态,是对伦理进行理论形态考察的方法。对伦理形态可以从横向(宏观)和纵向(微观)两个角度考察。伦理形态的微观考察首先应该彰显三个维度的分析: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是怎样的?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人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其次要蕴涵伦理的现实关照: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最后要体现伦理的价值指向:个人如何实现德性的生活?个人如何塑造理想的人格?个人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传统将道德和伦理内外二分,并将道德化为宗教和社会规则,成为生存手段。伦理是社会对人的外在规范,道德是人对社会的内心承诺。道德的产生得益于人有“自由意志”,能够在行为选择中,作出牺牲,以顺应群体需要。因此,道德是个体对群体或他人在行为上作出的牺牲。伦理道德始终是人的事情,但道德不应只超越个体的局限,而应超越人类的局限。伦理形态应当由“个人为群体”向“群体为个人”转变,以“平等、博爱”代替等级的“忠孝节义”。“一切不侵犯他人权益的言行都应该受到保护。”做到互不伤害,就是目前道德的应有之义。因此,维护正义是共同责任,尤其是社会、政治的责任,而达到真、善、美则是个人的权责和追求,正义与良善既互补又异质。善良是品质,正义是良善发挥的条件,而善良又能促进正义实现。
在与马克思“幽灵”的对话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学会生活的启示。马克思用生命讴歌了正义与良善,在共产主义失去在场的意义之后,适宜的是与马克思的“幽灵”一起去追寻生活的意义,一起去唤起对美好生活的记忆。德里达用生命讴歌了正义与良善,我们追随他考察苏东剧变后的社会现实,就是为了理清马克思的真精神。“虽然理论不能产生现实的力量,但理论可以驱动我们采取行动,改变不完美的世界其实”[13]。正义和良知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有时选择了遗忘。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是马克思为全人类幸福而不断斗争的精神,还是德里达一再呼吁的宽恕不可宽恕的?是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满腔热情与自信,还是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犹豫与追问?到底哪种精神才是济世良策?到底哪种价值才是永恒准则?斗争只是一种达到幸福的手段,它与流血、残酷联系在一起。可是,仅仅有斗争是不够的。当我们还把二元对立当做科学真理时,德里达却早已质疑了这种天经地义的观点。其实,复杂的世界,怎么可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就能建构。二元对立自以为对世界的解释很合理,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因此,“无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现在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忽略雅克·德里达的作品”[14]。社会需要正义和多元,个人需要修养和良知。是个人不断“克己复礼”以适应社会,还是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以保障个人权利?解构正如暗夜中的灯塔,可以照出我们生活的路。德里达关于幽灵的思考具有异乎寻常的重量,既是性命攸关的投入,又是空灵的超脱。要弄懂生活的意义,必须建筑要塞,树立偶像,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就是我们认清传统和现实的极好偶像。因为,马克思批判精神代表着正义,可以唤醒我们沉睡的内心,从而建造理想之路。虽然,马克思“幽灵”的“形体”已经烟消云散,但是“幽灵”的灵魂——正义精神却将继续指导人们寻找更好的生活。
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属于黑暗之光,用的是灵魂之眼,看起来冷峻,实际充满着对生命的关爱。虽然,它为我们找到的是一条解决生存困境的“逃路”,而不是出路。但它决不是消极的,更不是痴人说梦,而是积极的思考与探索。它将为我们排遣心灵的孤独,抚平记忆的伤痕,从而获得灵魂的安详和宁静。“也许任何一种不是从危险所在处来的拯救都还是无救”[15]。幽灵政治学凝聚了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观察和思考世界的钥匙。它启示我们要摆脱无知、恐惧、偏执和诽谤,作良心上的反省,要找寻新的规则和道路安抚心灵。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维护,是真正的悲悯。他期望每个人都受到尊敬。它启示我们要打破专制和暴力,自在地思考与生活。它告诉我们,世界本来就是自由的、多元的,人类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本能性的,而异端往往是人类精神生命力的体现。幽灵政治伦理学的一个原则就是包容,让每个个体都能获得生存的尊严。
[1]张宁.解构之旅·中国印记:德里达专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5.
[2](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3.
[4](德)伊曼努尔·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5.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7](法)雅克·德里达.友爱政治学及其他[M].胡继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38.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9-828.
[9]J DERRIDA.“Marx&Sons”[M].Ghostly Demarcation,Verso,1999:253.
[10](法)雅克·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
[11]孙全胜.两歧性与多重性: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场形态[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3-52.
[12]ICHAELRYAN.Marxismand Deconstruction[M].Baltimoreand London.1982:1.
[13]荀泉.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27-32.
[14]JIM POWELL.Derrida for Beginners[M].New York: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1997:89.
[15](德)马丁·海德格尔.系于孤独之途[M].成穷,余虹,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