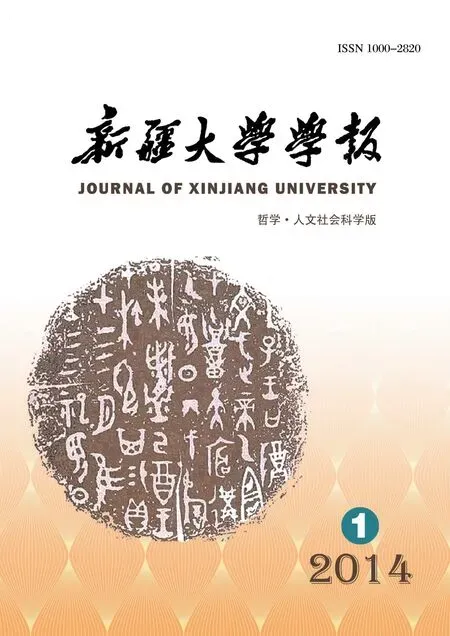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
——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
2014-03-03陈祥军
陈祥军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一、提出问题
自建国以来,国家及地方政府为提高牧业生产及改善牧民生活状况,在牧区原有的社会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与探索。这其中对牧区草原产权制度的调整(即草场承包的实施)力度最大。这是因为,公社化时期的草场公有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自身也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和弊端。同时也是为了打破草原牧区的“大锅饭”,提高牧业生产效率、改变牧民的贫困状态,以及更好地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
但草场承包实施之初在牧区乃至学术界都引起了争论,如当初作为草场承包试点县的新疆富蕴县,基层干部及技术人员就此问题持续争论了近一个月。他们中有人担心草场承包会把多年来积累的牧区管理经验都丢失掉。在学术界,研究牧区的专家学者们大多对此持赞成意见,认为这是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大方向。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照搬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不适宜游牧业生产的特点。尽管如此,但在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背景下,绝大多数人把牧区与农区同质化了,这也成为后来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草场承包实施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激发了牧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牧区社会内外环境的变化逐渐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学术界纷纷展开对“草场承包”的调查与研究,以期对其进行完善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长期研究新疆牧区社会的崔延虎教授认为,草场承包忽视了哈萨克社会家庭“分帐”的文化传统,遵循“生不加死不减”的原则,可能会导致草场的破碎化①此观点摘自崔延虎教授在2008年“中国草原牧区的环境变化与社会经济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内蒙学者敖仁其通过对草原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发现,草场承包其实只是明晰草场使用权的初级形式,当前草原产权仍面临着调整,必须要对其进行创新[1]。在藏区,杜国振从2003年开始对青藏高原玛曲地区的牧民联户和单户经营管理愿意与否进行了调查,有近70%的牧户选择了联户②数据来源:第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中国草原保护专题研讨会”中,兰州大学杜国祯教授的发言记录,2009年7月。。这也恰恰说明游牧社会的基础性特点:草场的不可分割性。
近年来,随着工业资本大量进入牧区,麻国庆从进步与发展的视角剖析,集体经济随着“草畜双承包”完全解体,这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2]。这也恰恰是后来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世界范围内游牧区域的草场私有化和牧场分割到户现状,国外有学者指出:这种行为的后果已经戏剧般的重构了当地的游牧空间和社会生态环境[3]。可见,草原产权(使用权)变动的确在牧区及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应。
基于此,本文将以草原产权的变化过程为重点,以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资料展现出草原产权“质”变后牧区社会的反应,以及对牧业生产及牧民带来的影响,以期发现其不足之处,为今后草原产权制度的调整与创新提供个案基础。
二、草原产权的“质”变:从共有到私有
(一)微调:从部落共有到公社所有
建国前,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牧区根据自然地理环境把草场划分为四季三地或四季六地草场。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季节草场,别的部落不得侵占。一般春、夏、秋三季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游动放牧,而冬季则是以哈萨克社会最为基础的游牧组织“阿吾勒”为单位进行定居放牧。关于当时的草场所有权问题,尼合迈提·朋加尼1952年在阿勒泰牧区的调查中提到,牧区中除冬营地外,其余的草场都属于氏族部落共有①“共有”指在当时草原产权比较模糊的历史背景下,草场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一般是氏族部落所共有。它类似于现在的公有概念。,由于受当时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调查组认为,草场只是形式上归部落共有,实际上却仅供游牧社会统治阶级占有[4]。
但笔者认为,这正是由牧草资源的季节性、不可分割性,即今天所说的“草原连片才有价值”[5]以及游牧经济的单一性特点决定的。在当时的条件下,牧主、部落头目们之所以将部落草场称为共有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防范外部落的侵犯。一旦受到外部落的侵犯,他们可以号召所有部族成员为保护共有草场而进行战斗,即当时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草原产权的完整性或对抗外来侵占草原的各种力量。
建国后,针对当时牧区社会的经济特点,中央决定在牧区采取完全不同与农区民主改革方式。1952年7月,新疆政府确定对牧区采取“不斗不分,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当时政府并没有没收私人、寺庙、氏族部落等占有的草场,而且保护他们对草场的所有权,允许其自由出租,他人不得侵犯。但到1956年,新疆政府又开始对原来的牧区政策进行调整,并指出其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牧民必须走畜牧业合作化的道路,才能进一步发展畜牧业,接着又将全新疆的私人占有、寺庙占有、民族部落占有和国家占有的草场应全部收归牧业社所有②资料来源:新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等编《牧区政策文献汇编》(内部资料),1985年第46页,第69页。。为在短短4年之后要对牧区政策进行重新调整?因为在当时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影响下,牧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于是从1956年开始,畜牧业合作社运动在全疆牧区范围内开始逐步推广。富蕴县于1956年底,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了牧业社,接着又陆续建立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至此,那些过去部落头目及牧主的四季牧场、打草地及部分耕地都必须由公私合营牧场统一使用和调整。同时,牧主们的牲畜及其生产工具都以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归入公私合营牧场,以后逐渐被收归公有。公私合营致使原有氏族部落首领的牲畜(财产)和草场直接被“剥夺”,并且失去了支配本氏族成员的权力,但草场的“共有”性质并没有改变,过去是氏族部落共有,现在是公社集体所有,所以游牧业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自1956年至公社化结束,虽然当地在牧业政策上经历了几次变化,但草场的所有权、使用权及管理权等都归公社所拥有,即最终形成了“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体制,从而否定了草原的可分割性和可转让性,也延续着“草原连片才有价值”的原则。公社化时期之所以没有对草原进行分割,其原因也是遵循了当地草原环境的季节性及游牧业生产的移动性特点,保证了灾年季节内放牧草场的机动可调性,从而避免因草场不足给牧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所以说,从部落共有到公社所有的草原产权调整,并没有给原有的牧业生产方式带来多么大的改变。
(二)质变:从集体所有到个体私有
众所周知,草场承包实施的背景主要是源于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农区实施的承包制在短期内就初见成效,并对提高农业生产及农民积极性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此后,在中央1号(1984年)文件的指导下,牧区提出了一些指导口号,如“深化牧区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牧业生产责任制”、“最大限度的提高牧民生产积极性”等。于是,新疆当时提出了“畜牧业生产责任制”,其从思想和实践中基本是套用农区模式。
不久新疆地方学者杨廷瑞就敏锐地发现,在牧区实施的改革模式、构思及观念完全照搬内地农村,但没人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这主要是绝大部分人都坚信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凡是集体的都是没有效率的,必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认为农业集体化(大锅饭)的低效率是由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而且至今没有被验证。但是,这个先期提出的假说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念,成为一个学界共识”[6]。牧区当时也基于这个假设,首先提出要解决两个“大锅饭”问题,即人吃牲畜的“大锅饭”和牲畜吃草场的“大锅饭”,所以要把牲畜和草场承包给了个人。
这个基于农区经验的假设移植到牧区之初就遭遇了挫折。富蕴县当时被作为新疆牧区草场承包的一个试点县。该县于1984年的5月在16个牧业队实施草畜双承包责任制,按“谁承包、谁使用、谁建设、谁保护”的原则管理草场,最终达到“人草畜,责权利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政府逐渐发现,牧民家庭经营出现了“小而全”的局面,即一户人家马、牛、羊、驼俱全。各种牲畜混杂放牧,草场分成小块后牲畜品种改良、疫病防治以及较大草场建设遇到困难[7]。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这是因为草场承包到户直接改变了草原产权的“共有”性质,尤其是草场的使用权完全转移给了个人,这逐渐改变了传统草原游牧业四个基本要素(人群、草原、牲畜和移动)之间的稳定关系。
首先,草场承包到户把游牧业基本要素之一的“人群”打散了,这就意味着每个牧户要独立承担一个完整复杂的牧业生产。自古以来,草原上之所以有不同层级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组织,就是因为单个牧户不可能应对复杂多变、不稳定的草原环境。历史上哈萨克游牧民都是以“阿吾勒”作为最基础的游牧和生产单位[8]。牲畜和草场分给单个牧户,意味着他们要单独面对过去由集体才能完成的牧业生产过程。可是在草原上,像农业社会那样独门独院的生存是很困难的。当地的草原环境及放牧特点也决定了一家一户不可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游牧生产过程。
其次,草场承包弱化了草原的完整性,放牧空间出现了固定化。传统哈萨克社会,草场从所有制性质上来讲一般是氏族部落所共有。各氏族内部草场基本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各季节牧场处于一个连贯和完整的状态。这种草场利用方式是以“人草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为基础。公社时,草场的共有制性质没有改变,其利用方式也基本没变,且更加统一化和专业化。承包后,草场的使用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变为个体私有,草场使用权和边界都被固定了。单个牧户固定的草场与界线清晰的边界使政府也失去了机动调节牧草资源分配的权力,人草畜的关系处于分离状态。这也是草原产权发生质变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第三,“一户一地”的草场承包束缚了牲畜的“移动”性。移动是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形成人畜与草原之间稳定关系的纽带。所以,固定的产权界限必然会阻碍牲畜的移动。同时,固定的草场与界线清晰的边界也使地方政府失去了机动调节牧草资源分配的权力,人草畜的关系处于分离状态。
即使如此,草场承包确实大大刺激了牧民生产的积极性,牲畜数量也获得了迅速发展,牧民收入更是有了极大提高。但随着牧民收入提高,牲畜数量的增加,如何解决草场承包到户与草原的规模经营和利用成为牧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问题。
三、草原产权“质”变后牧区社会的反应
(一)基层干部的争论与妥协
笔者从参与当年草场承包的县、乡、村干部那里了解到,草场承包使他们在心理上和思想上又经历了一次大考验。在实行草场承包之前,县政府特意邀请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及部分牧民代表,召开了一个讨论会。大家在会上就草场承包有很多疑问和异议,而且争论得很激烈,甚至点着煤油灯讨论到深夜。会上既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因此,此次讨论会持续了近一个月,最终彼此都做出了妥协。
在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还是认真听取了牧民及基层干部的建议,在具体操作层面做了适当变通。因为,分散的四季草场不同于铁板一块的耕地,根本无法做到像农区那样一地一户,所以如何把这些不同等级、相距较远的四季草场分给每户牧民,当时的基层干部们为此研究了好长时间。例如,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如何分草场,因为一旦给每户牧民划分出草场,不是简单的一处草场,而是要划分出“四季草场”。各季草场都有不同的等级、距离有远近、转场也有难易之分。对此,地方政府在听取民意后做了适当变通。在划分牧场,尤其是夏牧场时,考虑了哈萨克传统基层游牧组织的特点,采取了以“组”为单位划分草场,即夏牧场是以2—5户为一组共同拥有一处草场,组内牧民之间一般具有血缘或姻亲关系。
草场承包实施了10年之后,富蕴县政府于1995年7月对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在肯定它的诸项优点时,承认由于缺乏经验,也造成了一些与生产力不太相适应的问题。如牧民既要放牧牲畜,又要管理草场,出现顾此失彼现象。最后,大部分干部认为要改变目前“单家独户”的个体经营模式。有干部甚至提出:“以自愿互利的原则组成以传统游牧基层组织“阿吾勒”的形式从事畜牧业,实行简单的分工负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①资料来源:中共富蕴委办公室,富蕴农牧业研讨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95年第7页。。其实十几年之后,类似的做法在内蒙一些牧区已经在逐渐推行和试验。
从富蕴县当初实行草场承包时出现的争论、怀疑,到10年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一些基层干部逐渐意识到草场承包在促进牧业生产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要对其进行不断完善。近年来,受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牧区也开始进行草场流转的尝试。
(二)牧民的心理历程与实践
当地牧民对草场承包的态度又是怎样呢?牧民大体上经历了怀疑、观望、尝试直到最后接受的心理历程。起初,大部分牧民对草场承包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富蕴县最先在农业队进行试验。县里在农业队建立了一个试验合作组。每个合作组由10户组成,假如这10户人家共有1 000亩地,给他们规定了每年要完成10万斤粮食的任务。如果他们收获了15万斤,多余的5万斤粮食就由他们自己分配。经过在农业队的试验成功后,当初那些持怀疑的农牧民才逐渐相信,同意草场承包的人逐渐增多。
草场承包初期牧民们很高兴,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市场因素对牧区的影响在逐步加大,新疆农牧区普遍出现了消费大于生产的增长局面,市场对牲畜的需求过旺而导致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1988年,新疆农民的总收入比上年增长了6.6%,而牧民收入比上年增长了8.58%[9]。部分牧民的口袋里一下子拥有了很多钱,有很多是过去部落内的贫困牧户。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新疆关于草原和畜牧业的制度设计缺陷逐步显露。同样在其他省的牧区也是如此,吉林白山草原站的丛培义经过研究发现,现行的草原产权制度导致草原使用权主体组织程度低,妨碍了草原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10]。因为,单个牧户对整个牧业生产过程以及规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愈来愈感到力不存心。
2000年后,牧区社会逐渐被纳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单家独户的牧民很难应对复杂万变的市场经济,加之经营管理不善与生产生活成本的日益提高,牧区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渐减缓,在实践中表现为牧民的支出普遍高于收入。当地信用社牧民每年的贷款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牧民初春贷款,秋末还款,这已成为一个不变的规律。牧民戏称自己是“银行流动的雇工”。每个牧业队百分之百的牧民都有贷款,可以说牧民主要依靠信用社的贷款来维持生计。由于受灾害、市场波动及管理不善等影响,很大一部分牧民无法还贷,不得不卖掉牲畜甚至出租草场,依靠给别人放牧为生。这又造成了牧区社会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
四、草原产权质变动对牧业生产及牧民的影响
(一)牧业生产:从统一到分散
游牧业生产中转场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也是最体现游牧业特点的地方。草场承包后,政府由过去事无巨细的统一经营逐渐放手让个体牧户自己去管理,而只保留了统一安排转场的职责。当初政府处于保护草场及公平性考虑,每个乡都统一规定了各自转场的时间。然而这个设计方案在实践中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后来,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地要求牧民服从统一安排的转场时间,并指派各乡、村干部堵截提前转场的牧民,还对违规的牧民处以罚款。部分牧民宁愿被罚款也要提前转场,那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草场承包后,牲畜和草场分给牧户后,原来转场需要的畜力(马、骆驼)和部分机车也都分散在各个牧户手中。在承包的最初几年,要想做到统一转场是无法实现的。过去是公社会组织畜力、机车,分工合作统一搬迁。可如今在缺乏畜力和机车的情况下,牧民搬迁日期前后持续可达一个月。后来随着牧民畜力数量的增加,情况有所改变,但还是无法做到统一搬迁。
富蕴县各个乡规定的转场时间大致相同。吐尔洪乡规定每年9月5日羊群才能从夏牧场下来,11月15日过乌伦古河,来年3月20日离开冬牧场,6月20日到达中山牧场。虽然政府规定了统一的转场时间,实质上牧民还是依据天气情况和草情随时自行调整。如果初春积雪融化速度太快,牧民只有提前从冬牧场搬迁至春季牧场。例如:2006年冬季冬牧场一直没有降雪,牧民只能停留在秋季牧场。2009年9月中旬,牧民马某因为提前转场被乡政府罚款,最后只好交了一只羊。马某家是因为缺少一处过渡草场。原来的那块草场靠近额尔齐斯河,连年的洪水冲刷致使草场缩小了很多,已无法承载现在牲畜。可见,牧民提前转场有各种原因。
总之,草场的使用权私有化后,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极大地刺激了牧民生产的积极性,打破了牧业上的“大锅饭”,也促进了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们也要正视其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足之处。怎样消除个体牧户分散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是今后牧区管理者和学者共同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单从草原管理角度,牧区草原与农业耕地利用方式完全不同,草原大多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它代表的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产力。因此,较之私有的管理方式来说,采用公有的方式进行草原管理更有利于草原资源的发展[11]。
(二)个体牧户:抗风险能力减弱
首先,草场承包政策的设计还存在不足之处,没有考虑到哈萨克社会家庭“分帐”的文化传统。按照哈萨克传统习俗,当儿子成家一年以后,父亲要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家庭,其必要的条件是:一顶毡房,几十只牲畜,以及从大家庭中分出的部分草场。所以,儿子成家后的“分帐”使原有草场面积进一步破碎化,并导致各类牲畜混群放牧和移动范围的又一次缩小。这种状况到了第三代,每户牧民的草场面积已经无法再进行分割。草场的分割致使单个牧户的劳动力在不断减少,意味着抵御风险的力量也在减弱。
土地承包在农区获得极大成功,但牧区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同于农区,所以,如果简单套用农区的成功经验则一定会出现问题。农区在自然条件同质的情况下,分家分田地具有可操作性,而在牧区简单套用农区的这种方法,可能会造成局部地区的生态退化,还有可能加剧牧区的贫富差距。对于那些女儿较多的家庭,其草场的放牧压力相对较小。因为女儿出嫁后,人口减少了,原有的草场不必再进行分割,所以女儿多的牧户,其家庭生活、收入都相对较好。这也是造成当下牧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一个原因。
2010年年初,阿勒泰地区又发生雪灾。富蕴县喀拉布勒根乡的牧民贾某讲:由于积雪非常厚,小牲畜(羊)根本吃不到草。他们家的冬牧场离定居点较近,当政府把牧道打通后,他们就立刻把羊群赶回了定居点,接着又花了1 000元租车拉回冬牧场里的生活用品。对于冬牧场较远的牧户来说,在牧道没有打通之前只有自救。牧道打通后,牧民又面临一个大问题:积雪太厚,羊群根本无法前行,只能租车把羊群运回定居点。由于运费太高,每只羊要收50元,绝大部分牧户无法支付,还是要依靠亲戚朋友的互助为自救手段。
所以在面对严重自然灾害时,草场使用权的个体化使得地方政府无法做到像过去那样采取大范围跨县域的移动避灾。在集体化时期采取的大范围移动实质是一种“主动”避灾,而草场承包后迫使地方政府已转变为“被动”防灾。但对单个的牧户来说,这些自然灾害时常会给他们的牧业生产带来致命打击,有时需要三五年甚至更久才能恢复牧业生产。可见,草场承包给个体牧户后,如何重建一套新的抗击风险的机制是一个亟待完善的问题。
五、结论
针对当前牧区社会内外的新形势,对草原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已成趋势。在2014年中央1号文件中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稳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所以本文认为,对现有牧区存在问题与不足的了解是创新和完善草原产权制度的前提。笔者经过长期调查发现,牧区社会当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是源于农区成功经验的移植。农区与牧区在自然环境、生计方式、知识体系、社会组织、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承包制度在农区、牧区、乃至中国社会都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一源自小农生产组织的经验推广到牧区后,应该进行不断调试以适应牧区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因为,传统的农耕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生态系统里完成循环,其社会组织也是“迷你”型的——基本以家户为单位组织生产。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被称为“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12]。而牧草资源空间分布上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则需要大范围的迁徙移动以适应多变复杂的自然环境。
草场承包在实施过程中对草场资源时空分布的异质性特点有所忽视。原来一个整体的放牧草场被分割成无数个小块承包到户。30多年后,我们发现它虽然实现促进牧业生产和提高牧民收入的目标,但草原生态环境却出现了退化迹象。周立认为,这一外部输入式的产权制度改革,的确在短期内对农牧区生产能力是一种释放,但却导致了市场脱嵌于社会与自然,突出表现为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等“三牧”问题[13]。
因此,笔者认为,首先要对这一“移植”农区经验的草场承包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创新,以适应牧区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草场承包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它开启牧区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只要通过不断创新以完善其设计上的缺陷,才能发挥其对牧区社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