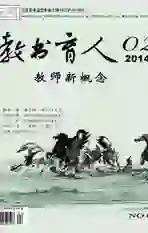教育行者“凌宗伟”的行读人生
2014-02-26邓文圣
邓文圣
翻开河南每周三的《教育时报》“读书会”一版,你会准时神会凌宗伟先生。他的专栏《行读人生》,总是让你抚掌,让你共鸣,让你震撼。
笃信“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全国知名教育学者凌宗伟,2013年2月6日应邀开专栏时,说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因此,深知唯有通过读书与行走方能自我救赎”。
这是凌宗伟行读教育三十余年的真实写照。凌宗伟三十多年如一日,秉持谦诚之心,进取之意,处处时时“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主张,进而改善自己的行走方式,并在行读之中涵养人生应然之气”。
心存“叛逆”站立真我
凌宗伟认同莱特兄弟,他们尽管不善言辞却让人类实现了飞翔的梦想,而鹦鹉会说话却飞不高。他们“学舌”的能力也不可谓不强,但往往风靡了一阵之后,就偃旗息鼓,终化作一团烟云而散。他以为,教育之中,求“真”最为重要,除了说实话,办真事,走正路之外,这个“真”还应指教育者的“本真”,即在教育界乱花迷眼、似是而非的“色相”中,不失掉“自己”。有个人的底线和原则,有独特的教育理解和运用,要学会“做自己的教育”,即使在别人的眼里变成了“叛逆”也不为所动。
工作之初,他被分配到全县最红火的通州石南小学初中班任教。第一个星期日,数学老师说不休息,要补课。他说星期日就是休息的,于是将教室门锁上并带着钥匙回家了。
身为教师,为了闯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来,他“叛逆”地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凡文言文教材都要背诵,做到进教室不带教材、不带教案。上课的时候,也常不按照套路出牌,而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着手,从学生的实际生活诠释知识。那时他最“叛逆”的事情,就是开始在课堂、在教参上找“瑕疵”,慢慢地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下来。在2011年哈尔滨举行的“慢课堂·慢教育”的教研活动上,毫不留情的对“一面五星红旗”的公开课提出了与施教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凌宗伟说他的这种“叛逆”个性的延续,也深深得益于自己的师父江苏省特级教师陈有明的“鼓励”。一次,在南通市“钱梦龙教学艺术研究会年会”上,县里推荐他上一节汇报课。师父告诫他:“学钱梦龙,不在于学其形,而在于学其神,万不能丧失个性,成为钱梦龙的翻版。”师父的告诫虽寥寥数语却让他很是受用。汇报课后,钱梦龙先生用“功底深厚、备课精细”八个字对他的课给予了高度概括和评价。
凌宗伟的“叛逆”个性,在他的一段与记者朱蒙就课堂模式的对话记录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朱蒙:好教师的课堂有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呢?
凌宗伟: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这个“法”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教学环节。我始终认为,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以及即时的课堂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就会很机械、很教条,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与我提倡的“课堂生成”啊、师生互动啊、生本互动啊、生生互动啊,就形成一种冲突,不利于达成我们提倡的“生命化课堂”。
朱蒙:你认为教师如何才能摆脱“模式”的诱惑呢?
凌宗伟:好教师应当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风格”是好教师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高屋建瓴的专业追求。而现在盛行的建构“模式”之风,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微观到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渡,连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是可怕的,这样的教师是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教师。
一堂课、一篇课文带给人的感受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多姿多彩的,它的魅力就在于能给人一个驰骋想象的自由空间。好教师应该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努力让自己的教育教学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这里的“得意”包括三个维度:一是要“得教材之意”,也就是说要吃透教材,准确把握教材的主旨、特点和编写者的意图;二是要“得学生之意”,也就是说要了解学生的需要,适时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使之渐入佳境;三是要“得课堂之意”,即充分认识到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套不变的、机械的程序。而“忘形”是指,一个好教师,一是得忘掉自己的教师之形,把自己与学生放在同一个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学生的合作者、帮助者,要时刻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学生;二是要忘掉教材之形,即不拘泥于教材和教案,也不拘泥于某一种程式,而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方案,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教育教学情况;三是要忘掉课堂之形,努力将课堂视为一个小社会和师生互动合作的舞台。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在与学生的合作、沟通中享受到教育的乐趣。只有这样“得意忘形”才是最大化的成全学生的健康和全面的成长,才能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叱咤风云的豪杰才俊。
身为教师,要紧的是不在乎其技艺如何,不在乎其资历多深,而关键的关键,是他有没有为理想而动,为信念而生?有没有不为世俗而随波逐流,不唯权位而惟命是从?简而言之,他有没有活出一个“真我”来?贝多芬曾经宣言:“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贝多芬却只有一个!”每一个老师都应自豪地说出:“老师有千万个,而‘我只有一个!”
凌宗伟有今天的成就,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老师,“我”只有一个。
不弃“扒皮”成就精彩
熟悉凌宗伟的人都知道他在网上有个绰号教“凌扒皮”,凌宗伟说,自从“凌扒皮”的名声被渐渐传开,他所在的学校引来了教育界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的关注、研究和仿效。大家在对“扒皮现象”的热议中,逐渐接受了他对生命化教育的理解和感受,更多的思想和智慧开始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汇集,也使他更加坚定了“扒皮”的信心。
几十年沉沉浮浮教育人生路,凌宗伟以“扒皮”自谓,一路跋山兼涉水,永远为它忧心萦怀,为它倾注心力。
凌宗伟的老家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的石港镇,这是一个历史积淀颇为深厚的藏龙卧虎之地。当地的戏剧、诗歌、书法等都堪称一绝,幼时的他每天浸泡在宽松、有趣,颇有“儒雅之风”的环境中,再得些淳朴民风、温厚民情的滋养。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就开始在简陋的物质生活和日益充盈的精神世界中,努力“扒皮”,构建属于他自己的“教育学”,以实现自我的价值。
工作后,由于离家较远,加上身挑班主任和一周28节课的教学重担,他索性寄宿在学校,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研读文本、设计教案中。得地利之便,他天天到有经验的教师课堂上去听课“扒皮”。他还给自己立了“凡欲达人者,必先自达之”的规定。“宝剑锋从磨砺出”,七年之后,他在学校里打开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凌宗伟的“扒皮”,可谓是“三箭齐发”。
其一是“扒专家之皮”。他坚持研读最先进的理论知识,渐渐地,他熟悉了陶行知、朱光潜、叶圣陶、夸美纽斯、苏霍姆林斯基等一大批国内外的古今教育专家、学者;刚开始他研究钱梦龙、林炜彤、魏书生,尽可能多地听课、评课、议课,将自己的想法拿出来与人讨论,请人点评。摸索,衍生出他自己的教学形态和教学风格。教育学者肖川说他的课“细处摄神,机趣灵活,旷达潇洒”。
担任南通二甲中学校长期间,孙绍振、张文质、成尚荣、刘铁芳、刘良华、陶继新、许锡良、陈大伟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被他请进校门言传身教。其中,张文质先生先后十多次来校与学校的管理者、师生、家长对话交流,共同探讨文化发展学校的战略和策略、生命化课堂建设的思路、家校协作的途径。2010年7月,学校承办了“全国生命化教育研讨会”,2011年7月,承办“全国首届文化发展学校”高端论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顶尖学者来校切磋。
其二是“扒教师之皮”,就是不断地给教师们催发新的动力,振奋他们的斗志。他在“1+1”教育博客上坚持转贴“每天一个小故事”,从2009年4月22日开始后就从未间断,他做这一系列的初衷仅仅是希望学校师生不被世俗的、繁杂的、平庸的生活所打倒,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想不到后来竟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当贴满600个故事时,福建省永定一中的校党总支副书记廖旺华老师特地写了《故事,润泽我们的心灵!》。
扒教师之皮,让二甲中学真正跻身于“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协会”,建立了“教育行者QQ群”、“心智家园”、“三人行班主任在线”博客圈,创办了《今天第二》校刊……
其三是“自我扒皮”。凌宗伟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虽以“扒皮”自居,但这校长的位置可不好坐。有时为了平衡心理,“自我扒皮”成了他的缓冲剂———大概有点“自虐”的味道———每天早上5点他就开始给自己找事情干:向学校师生露一下脸,给网友们喊起床、“挠痒痒”。大家看他如此“自虐”,以及其他同仁被“扒皮”后安之若素的样子,也就在潜意识中消除了对他这个“扒皮”的担忧,久之还聚拢了不少铁杆粉丝。
2010年11月30日,《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编辑张以瑾,做他的“影子”,蹲守学校两天。听从张以瑾的建议,他开始了《日出日落》系列的写作,就是用简练的笔触写下当天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关于教育的大事小情,到他卸任时已经写成近800篇。
凌宗伟认为,“扒皮”现象就是一种对话创生思想的主张,一种思维碰撞的实践。在教育依然禁锢的今天,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勇敢地面对、思考和改良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有更多的教育人积极地去探索和认真对待、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正是这样的共识者还不够多,作为提供思想、情感和学识渠道促成交流、共享和启迪的“扒皮”,他才有不竭的动力和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面对当下的教育现状,凌宗伟常以此自励:坚持做匍匐于大地上的普通教育人,以一腔悲悯情怀,深切呼唤教育新春天的到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坚持“扒人”与“扒己”,无怨无悔。
特立独行叫响二甲
凌宗伟对于教学研究特立独行,对于学校的管理也不例外。
2008年,他来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做校长。那个时间段,正是“二甲中学要被三余中学兼并”,办成一所“甲鱼中学”的谣言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那些不明真相的乡间百姓在茶余饭后争先预测着二甲中学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以舆论对舆论那是“空对空”的毫末之技,终究治标不治本。如何赢得生存的尊严?凌宗伟认为需由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来决定。于是立足当下,审时度势,提出了“人文关怀、文化立校、效益优先、质量第一”的管理理念和“办有灵气的教育,育有个性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并且大力提倡教师的“个性化”成长。
在当下“小富即安”的社会文化浸染下二甲中学也不例外。如何才能破除这些阻滞学校发展的羁绊呢?正当他在为下一步的发展寻找具体落脚点的时候,区教育局一个关于“创建特色学校”的文件给了他启发。他提出了“理念改变·行为改变”的“行为文化建设”路线,并作为学校“特色创建”的具体抓手。对内为注入新的因素以打破原有的平衡寻求新的发展,对外为让二甲中学在“拆并之谣”的风声中找到一个出路。为此,他展开了一系列指向“理念”的行动。首先,建立博客圈,如包含教职工及省内外专家226人在内的“教育行者”办公群、由学校青年才俊和国内名媒名师55人组成的“今天第二”成长群等,通过网络进行集体大讨论,像对杜郎口现象的反思、对课堂“学教案”的梳理、对刘百川、杜威教育思想的解读。其次,给教师发书,倡导读书,《教育是慢的艺术》、《活着就是幸福》、《民主主义与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地改变众人;还有外出参观取经,国内如沪宁浙,国外如澳洲。通过这些慢慢地扭转改变了领导班子和教师的理念,进而转变了他们的行为。
“行为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他对学校建设大问题的一种求解之道,其实,在很多方面它都包含着一些细小的方面。凌宗伟认为,我们只要沿着困难的方向再往前一点点,或许我们就站在了解决困难的拐角处了。比如,他主张“管理从厕所开始”,用星级宾馆的标准来改造和管理学校厕所,如今二甲中学的厕所已经是学校的一张名片了;办“阳光体育器材超市”,变“堵”为“疏”,满足了学生“随时”的需要,也成为二甲中学的一个醒目亮点。
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如果我们观察动物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会发现有的生活在高处,有的栖息在低处。同样,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也有着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维度的需求。所以,学校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引导他们往更高的层面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各个不同层面教师或学生的需求,让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诗意栖居”的精神归属。
为了掌握教师的“垂直分布”情况,凌宗伟一面潜沉下来调查了解,一面采取主动测试的方法来进行判断。由于他一直重视读写,所以他“探矿”的第一步便是寻找会写文章的“民间高手”。因为担心可能存在走访对象故意“推荐”或“排挤”的情形,也有可能沧海遗珠,他再次选择了博客实施“测试”。每天早上,他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博客圈中查看更新,并判断孰优孰劣———朱建是在“走访”中被多人提到的,邱磊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季勇则更具戏剧性,是在与他的“隔空叫阵”中大显不俗的。在他的引导下,朱建获得了南通市首届教育博客大赛一等奖并成为《班主任之友》杂志的封面人物。邱磊受惠于读杜威活动而在《中国教育报》、《教师月刊》等刊物上写发了不少有质量的读书笔记,成为《教师月刊》杂志的2012年度人物。
倡导写博,但无论他怎么样鼓励和推动,积极回应的永远只有那么几个人,许多教师或是敷衍了事,或是无动于衷。于是,凌宗伟觉得必须为“他们”也寻找到“增长点”。这一次他想起了课堂。他认为,不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写文章,但他们“每一天”都要上课,他采取“尖端人物”自主报名、成立“志愿小组”,邀请大学教师和课程专家来听课诊断的方式吸引教师参与。部分年轻语数外老师得到定点指导,进步尤其迅速。
生物组的周林聪老师是个善于动脑钻研的人,他把二甲地区盛产葡萄和生物教材中“果酒果醋制作”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带领学生开展了葡萄酒酿制的实验,并得到了南通市教研室的认可,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室———传统发酵实验室,还自编了校本教材。
南通市二甲中学出名之后,凌宗伟校长陆陆续续接待过不少省内外的参观者,大家问得最多的是:这里怎么没有星罗棋布的标语?怎么没有统一的课间操?孩子们怎么不用穿校服?其实,凌宗伟的主张就是人不可被某个模子套死,需要尊重其精神独立性。标语不是用来灌输意志的,课间操不是用来打军体拳的,校服也不是用来供人“规范管理”和“迎接检查”的。每个教师、学生本就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教育哪里有亦步亦趋的“精确”拷贝?哪里有包治百病的标语口号?曾经有记者问他:“你理想中的好学校标准是什么?”他说:“就是当学生离开学校,别人一见他的言行举止就赞叹地说‘这一定是某某学校的学生。”
凌宗伟的“特立独行”,实现了江苏省南通二甲中学迅速成为全国的“草根名校”。
如今,凌宗伟担纲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中小学教师培训的工作,他一定会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他的智慧和结晶,会有更多的教师因他而受益,因他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