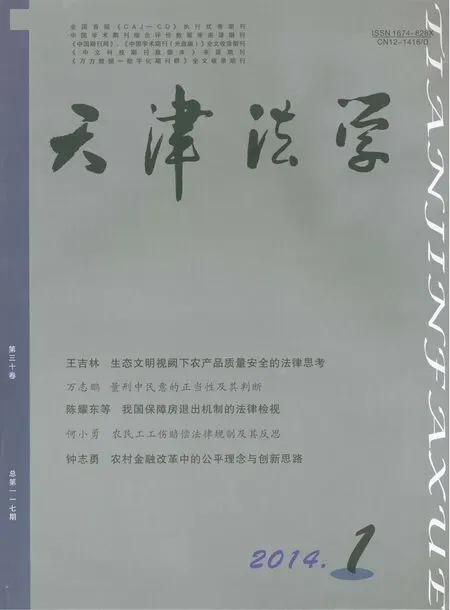对检察机关适用庭前会议程序问题的思考
——以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分析视角
2014-02-12李智许斯文
李智,许斯文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天津300102)
·司法理论与实践·
对检察机关适用庭前会议程序问题的思考
——以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分析视角
李智,许斯文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天津300102)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已近一年,其中,作为一项新制度,第182条第2款规定的刑事庭审庭前会议程序,在司法实践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渐渐体现出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以检察机关的视野为出发点,通过对庭前会议程序适用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庭前会议程序的一些方法,以期能够对庭前会议程序的进一步科学构建及制度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庭前会议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已一年的时间了,其中,作为对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改革,第182条第2款规定的庭前会议程序,在司法实践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渐渐体现出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对于适用该程序的检察机关来说,更是如此。笔者将立足于检察机关,对庭前会议制度实施以来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力求寻找和构建一套更为规范的制度架构,以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环节的职能作用,实现维护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权威三者合一。
一、检察机关适用庭前会议程序的基本问题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79年《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庭前准备程序做出过一些修改,但其具体规定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意义上的变化,仍旧停留在一些基础性、手续性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庭前程序尚属空白。而刑诉法修改中增设的庭前会议程序,是从提高庭审质量、确保诉讼效益的角度进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有益尝试,那么该制度的司法现状如何,制度定位如何,价值体现又如何都是我们首先需要清楚的基本问题。
(一)司法现状
刑事诉讼过程中,庭审法官的自由心证,即对证据的采信和判断很重要。然而,具体司法实践表明,目前,许多问题诸如申请回避,申请通知证人、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非法证据的排除等问题以及控辩双方之间非实质性的争议、争论焦点不明确等问题,均通过正规庭审程序解决,不仅耗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分散了控辩双方及审判人员的主要精力,同时还会造成审判程序的中断,降低了庭审的质量和效率[1]。然而,上述问题的凸显应该归结于我国刑事庭审庭前准备程序的虚无化,特别是庭前会议程序的欠缺和空白。纵观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设置,均普遍注重庭前准备程序的设立与运作,以期明确案件的争点,提高庭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7.1条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规定法庭可以命令举行一次或者多次会议以研究考虑诸如促进公正、迅速审判等类事项;英国设有“答辩及指示听证会”,控辩双方需要将涉及案件中争议问题、影响被告人或证人任何智力或医疗上问题等的答复提交给法官。此次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吸收并借鉴上述先进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以第182条第2款对庭前会议制度进行了设立,就司法现状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庭前会议制度实施一年以来,各地检察机关一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及应用中不断尝试、不断总结。一方面,积极与人民法院进行沟通与协调,探索适用的方式和机制,制定《适用庭前会议程序实施细则》,明确庭前会议程序的适用范围、启动主体、程序内容、效力作用等;另一方面,组织检察系统内部的尝试、观摩与研讨,交换有益的经验并归纳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发现影响庭前会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效用所容易受到的制约因素,特别是制度设置上过于简单导致发挥功能有限,监督功能缺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未予解决等。但值得肯定的是该制度构建是回应和满足当前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尊重刑事诉讼活动基本规律的客观需要。
(二)制度定位
由于我国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刑事诉讼庭前程序一直都是欠缺,直到此次新刑诉法对庭前会议程序的增设,才开始了刑事诉讼庭前程序构建的第一步。刑事诉讼庭前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开庭审判前程序的总称,具体是指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之后到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之前,人民法院进行的各种审判准备所应遵循的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而庭前会议程序,则是指审判组织为了提高庭审效率、确定庭审重点,而于开庭审判前组织有关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程序事项发表意见,以期将有关程序争议解决在庭审之前的一项制度。该制度的设立和构建,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以后的刑事诉讼庭审活动做好充分的准备,以防止和避免正式的庭审被非必要的纷争和问题所干扰,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从而提高庭审的效率和效果。从我国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对庭前会议制度的规定来看,设定了庭前会议召集人员为法庭审判人员,参与各方为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会议内容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由此看来,庭前会议程序是“将纯粹手续性的庭审审查程序改造为程序性的庭前预备程序”,“将附属于审判的程序改造为相对独立的审判前程序”,从而确立了庭前会议程序作为庭前准备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地位[2],因此,对该制度进行的探讨不应超出庭前准备程序这一整体的立法框架和范围,同时,结合各国先进立法及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庭前会议程序的制度设计应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中心。
(三)价值体现
新刑诉法修改对庭前会议程度的增设是首次在法律上对该项制度予以确立和初步构建,虽然仅有1款规定,但是其所体现出来的立法价值和意义却非比寻常,它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为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提供了立法依据。该制度设计的价值体现为:第一:有利于促进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庭前会议程序作为开庭前的审判人员与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之间进行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其有效排除了参与各方单方面接触的一些非理性因素,同时也有效负担了资讯功能,即在信息交流之中保证了控辩双方诉权的平等,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影响诉讼的平衡,保障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公正,同时也节省了庭审时间,追求了诉讼效率的最大化,实现了公正与效率价值统一;第二,有利于刑事程序人权保障与审判品质的实现。将庭审活动中对提出回避、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的准备工作提前到庭前会议程序中予以解决,促进了刑事诉讼程序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特别是非法证据的排除有助于落实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的原则,提供了人权保障,同时有利于使庭审审判人员在正式的庭审活动中有效发挥审判职能,让审判更具实质化,提高审判品质,另外,对公诉权进行制约,进而保障人权;第三,有利于控辩双方明晰争讼焦点,提高控辩的针对性。庭前会议程序不对案件的证据进行实质的审理,但控辩双方可以就案件及证据的争议焦点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从而在实质意义上明确了争讼焦点,也大致了解了双方的攻击与防御策略,以期更好的将精力集中于把握正式庭审时控辩的方向、重点和关键,为庭审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司法实践中,对于很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涉及当事人数量、证据数量较多时,庭前会议程序作为中间程序的必要性就会尤为凸显,提前确定回避、证人名单,排除非法证据,确定案件的重点和争点,将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在该程序中确认,庭审重点针对有异议的证人、证据展开,有效保证庭审的顺利、高效进行。
二、检察机关参与庭前会议程序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庭前会议程序是此次新刑诉法修改在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法治国情所构建的一项新的制度,鉴于此,检察机关对该程序的适用,在理论层面上还没有较为丰富及完善的司法解释予以具体规制,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更没有得以成熟、自如的运用和应对,因此,可以说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笔者将其归纳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庭前会议程序的监督权力问题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特别是法院审判阶段承担着依法履行公诉和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双重职能定位。而且当前,检察机关在积极探索充分发挥自身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亦越来越重视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的作用,以期有效保障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切实维护法治尊严和基本人权。据此看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法院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应该是贯穿整个审判环节始终的,当然也应该包括庭前程序的进行。如基于庭前会议程序而言,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只是规定了检察机关作为参与一方可以参与庭前会议程序的权利,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2012年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第430条、431条、432条虽然对于具体参与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如“公诉人通过参加庭前会议,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争议和不同意见,解决有关程序问题,为参加法庭审理做好准备。”但均没有对检察机关如何行使庭前会议程序的监督权力作出规定,显然,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庭前会议程序的运行,检察机关只是较为被动的处于“舞台上的表演者之一”,而从根本上缺失了其监督者的角色定位,从而使庭前会议程序的运行和适用脱离了有效的规制和制约。因此,对于新刑诉法构建的庭前会议程序,检察机关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必须首先要考量的难题就是如何在依法履行公诉职能的同时,有力承担起自身对该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
(二)庭前会议程序中是否适用证据开示的问题
庭前证据开示,也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刑事法概念,溯源于传统的诉讼模式的当事人主义和重视程序公正的程序本位主义,是与控辩双方对抗式的审判方式相适应的一套重要装置。其有益于探求案情真相,实现司法公正;有益于进一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提高诉讼效率;有益于控辩双方庭前准备,保障控辩平衡;有益于执法部门办案质量的提高[3]。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是带有职权主义模式的色彩,尽管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一些对抗式审判的因素,但也并未建立起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而是规定了一些控辩双方了解案情的途径。此次新刑诉法的修改,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庭前会议制度构建的本身就是对于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借鉴,但实际上,第182条第2款并未作出这样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我国案卷移送主义及律师阅卷权利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控方,其所掌握的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均能通过审查起诉阶段及法院审判阶段的律师完全阅卷权被辩方知晓,而辩方却没有同等的证据开示义务,这种案件证据及信息的沟通方式可谓是“单向的证据开示”,是资讯享有方面的不平衡、诉权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使公诉人在与辩护人双方之间交换各自观点、互通案件信息的庭前博弈[4]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使检察机关自身容易在实际的庭审过程中对于辩方证据无从得知,而落入辩方的证据突袭,以致措手不及。因此,作为相互获取证据和信息的一种程序设置,在庭前会议程序的构建中,是否要引入证据开示,将对控辩双方特别是检控一方能否获得平等的庭审准备条件和机会,以及实质性庭审的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的实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如果适用证据开示,证据开示的方式、地点、控辩双方的权利义务等都是必须予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三)庭前会议程序有无裁决性结论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对庭审审前程序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刑事庭审过程中非常重要并且可以直观评断出审判程序是否具有程序公正性的形式问题,例如:案件管辖、回避、证人或鉴定人或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出庭、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公开审理、延期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等问题均是涉及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备公正性的最基本问题,因此,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开展和裁断往往会对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审前动议程序主要是实质性地解决非法证据的排除,即在陪审团组成之前就已经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过程外,使审判事实的陪审团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而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庭前会议程序,其表述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虽然要求“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但其只是参与各方共同协商所产生的结论,并没有要求作出裁断性的结论。如果庭前会议中,诉讼各方意见不统一,又难以协商一致,应该如何处置,法律并未作出规定,而法官作为会议主持者居间裁判于法无据;如果庭前会议中,诉讼各方意见达成一致,但开庭前任何一方再次产生异议也无法律禁止。以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为例,与美国的审前动议相比较,我国的庭前会议,对涉嫌非法的证据并没有将其排除,而是仅仅听取参与会议各方的意见,这样非法证据就会一直陪伴走完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直到法官作出最终的判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程序的公平和公正。从这个意义来看,我国庭前会议程序的构建尚停留在浅表层阶段,一定程度上无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
三、检察机关完善庭前会议程序的几点思考
下面,笔者将以检察机关的视野为出发点,结合前面提出的庭前会议程序的基本问题,针对检察机关自身作为该程序参与一方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试着对庭前会议程序的进一步科学构建及制度设计进行一些探讨和思考,以期能够对庭审会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和适用有所裨益。
(一)进一步强化监督实权,保障庭前会议程序的公平、公正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仅以第182条第2款一款之规定对庭前会议程序进行了阐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程序的具体运行和适用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设计和规范。而前面笔者已经谈到,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一方是庭前会议程序的参与者,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必须对庭前会议程序的运行实施法律监督,以保障该程序的公平、公正性。具体来讲:第一,对于庭前会议主持形式的监督。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的规定,由“审判人员”召集,那么这里的“审判人员”是否应该是庭审过程中的审判人员,法条并未明确。虽然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尚未设立预审法官,但笔者认为,从维护法官心证的独立性的角度考虑,专门设立审前程序法官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而鉴于现有的审判程序并未有这样的设计,故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赋予检察机关建议权,建议法院在召开庭前会议时由专门、独立的预审法官来召集,例如:在立案庭中设置或选择审前程序法官来对刑事案件的庭前会议程序主动发起;第二,对于庭前会议主持内容的监督。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庭前会议的审查内容限于“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2012年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第431条则具体规定为“案件管辖、回避、出庭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辩护人提供的无罪证据、非法证据排除、不公开审理、延期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庭审方案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应该监督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审查内容不应超出上述程序性问题的范围,更不能涉及任何案件实体问题。
(二)适当引入证据开示,以期获得实质庭审的平等权、主动权
所谓适当引入证据开示,指的是通过在庭前会议上拟对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使用的案件证据一一出示,使控辩双方获得对该证据是否持有异议的分别表示意见的权利。虽然,公诉方对证据开示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存在一些疑虑和担心,但实际上,其亦能为公诉方带来利好因素,如可以了解辩护方的防御策略,并根据与辩护方进行证据沟通的情况,有针对性的重点核实、补充相关自身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为参与庭审指控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不仅提高了公诉的效率和质量,更有利于更好的履行公诉职责,同时也保证了控辩双方尽可能“平等武装”,进而使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那么在庭前会议程序中,证据应该在什么范围内予以开示?根据当前司法实践经验来看,庭审前,由于辩护方基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法院审判阶段的阅卷权往往对检控一方所掌握的证据已经全部知悉,但检控一方却常常对辩护方单方面所掌握的证据无从知晓,因此,使得检控一方在庭审准备上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基于此,笔者认为:凡是与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有关联,同时控辩双方准备在接下来的实质庭审过程中用作证据的材料均应当在庭前会议中予以开示,因此,庭前证据的开示应该是双向的[5],其不仅应当包括检控一方所掌握的证据,也应当包括辩护一方所掌握的证据,不仅应当包括涉及案件定罪事实的证据,也应当包括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据,例如: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的认定等。另外,在证据开示的具体程序上,笔者认为:在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仅应就所出示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表示有无异议的意见,而不能对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经过对证据的出示和表态,控辩双方对证据无异议的,视为达成合意,有异议的,如提出系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庭前会议结束后,由书记员制作《庭前会议证据开示清单》,详细列明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和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情况,并交控辩双方核对。在法庭上对排除的非法证据以及无争议的事实、证据不再作法庭调查。
(三)合理利用各方“意见”,促进庭审公诉准备工作的完善
我国庭前会议程序仅限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不形成裁决性结论,这对于检控机关的公诉工作来讲,无疑会陷入被动的境地。为了更好的履行自身公诉职责,确实实现庭前程序解决私权与公权力的对抗功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不妨进行一些尝试:第一,通过庭前会议,应该掌握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供述或辩解意见。刑事庭审主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因此,被告人作为庭审阶段的核心人物,其对自己有罪或无罪意见的陈述是非常重要的,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只有在掌握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对指控的态度,才能顺利的开展和有针对性的作出调整。对此,新刑诉法并未将被告人的此项权利明确列入庭前会议的制度设计中,但笔者认为,基于庭前程序实现控辩双方证据沟通的角度,检察机关可以提出相关的申请,以弥补该重大缺陷;第二,及时就程序性问题及证据证明力问题进行庭前沟通,以有效对抗当庭申请的重复或突袭。虽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会议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利,但由于我国庭前会议并不形成裁决性结论,故实践中有时参与各方出于种种顾虑并不在庭前会议中提出申请而在庭审当庭提出,从而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和法院的实质庭审均造成了被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非法证据排除作为庭前会议阶段的主要工作,控辩双方将有异议的证据提交庭前会议予以排除,并记录在案,如若参与各方在庭前会议中提出证据系非法取得,检察机关可以在庭审之前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核实而进行证明,如若庭前会议的参与各方未提出相关的申请或者检察机关对提出的申请已经进行有效证明,双方即达成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合意,那么对于在庭审当庭提出申请的情况,检察机关应当进行有效对抗,建议法庭要求申请一方提供足够合理、充分、有效的证明。
总之,新刑诉法对庭前会议程序的引入,是强调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产物,其规范与构建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该程序在理论探讨及实践操作来看,还没有真正得以完善,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检察机关作为庭前会议程序的参与者和监督者来讲,更加亟待积极探索如何解决自身在适用该程序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以期能够更好的履行公诉职责和法律监督职责,从而进一步促进刑事司法程序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的有机统一、积极发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效能,有力促进中国司法文明的发展进步。
[1]童建明,张智辉,王洪祥.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199-200.
[2]陈卫东,杜磊.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适用——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之规定[J].浙江社会科学,2012,(11):31-43.
[3]李健.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建路径[J].河北法学,2012,(8):174-179.
[4]李爱君著.公诉中的博弈——我的公诉战争[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171-179.
[5]沈志先,汤黎明,郑天衣.驾驭庭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5-83.
O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Application of Pretrial Conference Program Problem——IntheNewCriminal ProcedureLawPerspective
LI Zhi,XU Si-wen
(Tianjin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Nankai District,Tianjin 300102,China)
Thenewly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Lawhas been formally implemented sinceJanuary 1,2013, in which,as a newsystem,the pretrial proceedings in criminal court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82 gradually manifest the unique function and value i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judicial practice,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merging at the same time.The authors proposed some methods to further improve pretrial conferenceprogram,by takingthevisionoftheprocuratorial organsasthestartingpoint,throughanalyzingthe applicablejudicial status of pretrial conferenceproceedings,for the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current procuratorial organs,in order toprovid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and systematic design of pretrial conferenceprogram.
theprocuratorial organ;criminal litigation;pretrial procedure;themeetingbeforethecourt
D925.2
A
1674-828X(2014)01-0088-05
(责任编辑:张颖)
2013-07-21
李智,女,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主要从事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许斯文,女,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助理检察员,主要从事刑事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