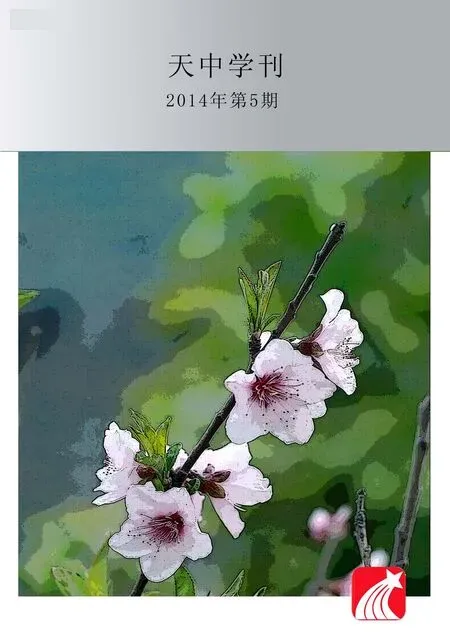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回教困境探析——以回教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2014-02-12单侠
单侠
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回教困境探析——以回教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单侠
(宁夏师范学院 思政部,宁夏 固原 756000)
近代以来,回教的核心教义不举,不但忽视了对外界的宣传,而且教民本身的义学修持水平也很低下,这就大大限制了回教的发展以及回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此外,回教内部派别分立且相互攻讦、非难,使回教的处境雪上加霜。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回教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民国时期;回教;回教教育
中国回教若以地域说,西北最多;以时代论,宋元为盛。在元朝,回族的地位在汉人以上,到了明朝,尚能维持,清朝时却一落千丈。晚清以降,由于自身和现实的原因,回教和佛、道一样,更是江河日下,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正如重川20世纪30年代所感慨的那样“说到教育的颓废,经济的破产以及其他的颓丧残败的事迹,更是不一而足的。总而言之,无论考察到中国伊斯兰教民中的哪一件事结果都是可悲的。”[1]
一、回教教义不举
虽然回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教徒,但由于特殊的环境,回教没有向外宣传自己的思想,致使外界与之隔膜甚至产生误解而丧失了研究兴趣。《新晨》曾发表社论称“外界对回教所知的只是不吃猪头而已”[2]。甚至有些人认为回教是“保守的,是秘密的,是尚武力的”[3]。由此可见,回教虽事实上已普遍存在,但在某种形式上却与国家和民族有着鸿沟。
不仅教外人士,大多数教民也对经文既无深刻的研究,又缺乏真切的了解。他们多数还过着几世纪前的封闭生活,甚至“连自己的宗教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的都有”[4]。尽管他们的信仰是诚恳的,但真正知道伊斯兰真义及价值的,却是极少数,他们大多数只是仅在内心里有着回教观念,盲目地信奉罢了!一般教民简直就是“入了五里雾中,成天在那昏暗的环境中乱冲,于是那阐扬真理的清真寺,也就变为沉寂的破庙。”[5]他们中有专门学识的大概万不得一,稍微懂得一点回教知识的就妄自尊大、自命不凡,假如“问他个究竟,他自己也茫然了”[6]。一些乡老也是“脑筋腐旧,思想愚鲁,除把持寺务监视财政外,别无所能”[7]。教民的精神更觉涣散,对于教义毫无研究,教政方面当然无人过问,以至礼拜寺虽设,而门常关。每日礼拜寺里只有几位掌教礼拜,“乡耄真是绝迹了,就是聚礼日也不过二三十人”[8]。
即便主持教务的阿訇也是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不能发扬回教教义。能以阿文著述或能通外国语言及明了世界回教大势,博通学术,热心教务的阿訇极少,他们大都与世浮沉混沌毕生,即便有个别人能顺应潮流,阐发教理“则一般老旧,耻为野狐,诋妖孽,故川事难言也”[9]。由于一般阿訇学识太浅,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理,以至常常有些神怪荒唐的说法,而不能把真正的教旨阐明出来,不仅教外人难明其妙,就是教中一般的青年,也难免由怀疑而生出冷淡的态度,只晓得回教是不吃猪肉的宗教,而阿訇也仅是以念经谋生的人,至于“真理如何,不复加以重视”[10]。甚至有些老道式的阿訇们,除了红白大事去应酬应酬或礼礼五时之外,有几个会“张开眼睛去看看世界上的变化趋势,有几个人实心实意研究研究古尔阿尼上的记载及各种学术”,他们以为念几句阿文,“去作变相的老道、和尚并且能替别人作作超度灵魂的买卖,能够赚几包经礼吃饭,就可以安度一生”[11]。
在时代和学术进步的同时,回教与其宗教一样墨守旧章,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也是造成回教困境的一个原因。关于此点最典型的莫过于教内分为“念经的”和“念书的”:“念经的”指会阿文而行教门的人,“念书的”是普通读书人。固然也有“经书兼通”的宗教者,然而究竟是少数。这两种人实际上关系回教的盛衰存亡。然而两者之间终究不同,甚至有时候背道而驰。“念书的”有学识,他们多受过欧风美雨的熏陶,惟欧美的学说是求,对于教门不但不去研求,反倒把伊斯兰的教门看成迷信,认为它是文化进步的障碍物,足以阻止人们的向上心。因此,他们对于自己回教的教义茫然无知,也不愿意去了解,以为回教是无聊的,而研究和了解回教更是无聊,甚至认为回教是以武力为主义,以杀伐残暴为精神,因而对其深恶痛绝。有的认为回教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加以蔑视、离弃;有的看到回教的腐败落伍而加以污蔑。所以“念书的”多半轻视宗教,而且念书越多宗教观念愈浅,尤其到了大学时其宗教观念更是微乎其微了。与“念书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念经的”,他们无学识,多半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不知道回教的真义。人们向他问点宗教问题,他有时回答不上来,便拿“使不得这样问”以愚人而自愚。他们一般阿文基础不好,对于回教没有深入研究,以至于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纵然想作高深的研究,但连字典、文法一类的工具书都没有。即使有个别人的阿文基础好,然而也苦于经籍太少(清真寺里又没有图书馆,所有的只限于那几种重要的经典)而无法找到参考文献作深入的研究,造成他们回教知识的浅薄。由于学识所限,他们又不能将自己仅有的回教知识用口头白话向外界表达,而只知“有事出去料理,有油香吃,有经礼接”[12]。“念经的”无学识、好虚荣引起了“念书的”反感,继而让他们看不起回教。反过来说,“念经的”也自然看不起“念书的”,两者互相看不起,导致回教陷于更加危难的境地。
二、回教教育的落后
教民文化程度较低,教中识字者“只占百分之四五,其余无力受教育及无暇受教育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13]。在宁夏不识字的人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回汉感情的不睦,更造成了穆民反对读“汉书”的心理,因而文盲充斥,知识落后[13]。面对这种状况本应大力发展教育,但由于条件所限,受教育的儿童“至多只有全数五分之一”[14]。由此可见,小学教育未能普及且欠完善,所以回民子弟在幼小受过回教教育的,除西北各省外,为数较少,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也不能理解回教真义。而回教女子的教育,能升到中等学校的就寥寥无几。女子教育比回民男子教育更糟糕:“一方面,有一半是受着经济的压迫,使之根本无受教育之机会;另一方面,是历来一般顽固者的舆论,紧紧的缚束着,他们以为回教是绝对禁止女子求学。”[15]
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中说:西北的地方教育尤落伍可笑,各县皆无中学,高等小学已为最高学府[16]。至于中等教育,回民上中学的为数已甚微,而自办之中学,在战前根本没有;战后才有少数中学出现,但是得不到当地政府教育经费之补助,而自己的经济实力又非常薄弱,所以只有“苟延残喘的存在着而已,受高等教育的为数更少,全省大学生也不过四五十名”[17]。
属于中国回教范围以内的学校教育,可分为旧式的和新式的两个阶段,但并不是由旧式的走上新式的,而是两者在并立的状态中。
差不多的清真寺中都有所谓大学,就是特聘的阿訇所教授的学校。这类学校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旧式的学校,这些学校授课在北方各省通常采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讲授方式是复式教学法,就是10个学生之中往往分5个程度,阿訇在同一的时间内要为这5种不同程度的生徒讲授5种不同的课本。并且这种旧式学校的生徒终身只念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不念中国文字。由这种学校造就出来的大阿訇固属不少,但是他们不能操流利的阿语或波语,甚至大多数人都不能写一封阿文或波文书信。因此,受经堂教育的人大都只念阿文而不读中文,以致多数人都不认识汉字,不但阻碍了回教的发展和穆民的进步,而且隔膜了回汉间的感情,一切误会、摩擦也就随之而生。
就课程而言,这类学校主要教一些普通的宗教学,对于其他的学科完全置诸脑后,以致“形成了不能处世的灰色状态”[18]。口称继承圣业,替圣传道的阿訇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守旧,活泼儿童经过他们的教育,也不过“只数落几个阿文字母而已”,至于回教根本教义,依然茫然无知,只不过深知不吃猪肉[13]。学生们除终日食、饮、睡三项外,不知学业为何物,不但不了解社会上的普通常识,而且也不能发挥教理以教化民众。毕业时,他们则“各处而告某月某日,掛幛行礼,以示卒业,而幛文上居然大书替圣传道,品学兼优可以为师,等等颂词”[19]。这样一代代地传流下去,不但不能振兴回教,反倒影响回教前途。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回教有识之士开始兴办新式回教学校。新式学校的滥觞,肇端于王浩然改善教学方法。民国成立以后,回民和社会的接触日益紧密,回教有识之士有感于只念经不念书无法将回教发扬光大,于是群起努力致力于新教育。但当时所有宗教性质的新式学校的组织、课程等都差不多,教师和图书都很缺乏,当时的一名在校生光仁说:“我在学校读书,对于各样的知识一切都没有,平日除功课外,所阅的都是些杂志报纸。”[20]还有一些学生只崇拜新事物和外国传来的东西而无视其是非优劣,“凡一事一物只问其新否,是外国传来否,如是新或是外国传来皆崇拜之,珍视之,并不探其原来是、非、得、失,浮躁之气大作”[21]。以至于一个青年受相当的新式教育之后,便再不会诚心诚意遵守缺乏科学理由的宗教教规,甚至很多读书青年由于对回教有种种错误的认识,而喊出“宗教腐败”“打倒阿訇”“改革宗教”等口号。他们多被一些狡猾的教民所利用,尽管打着发扬回教的旗帜作些运动,表面上看去“似乎很有作为,标着的题目也好像堂堂皇皇,结果不是达到私人的某种目的,便是成就某人的势位官爵”[22]。
总之,旧式的经堂教育由于自身的问题,没能从整体上提高教民的宗教修养。而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新式回教学校的创办,经堂学校更是日益没落。然而,新式学校培养的青年学生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宗教观念更加淡薄。落后的回教教育已不能真正普及回教真义。
三、内部派别分立
虽然中国回教徒以团结精神闻名于世,但回教人数众多又散居各地,加以河山阻隔,“势难团结,为时既久,彼此声息断绝,感情渐渐冷淡,以最有关系之教规,日久生疏以至于尔为尔,我为我。”[23]据统计,全国几万座的清真寺,数以万计的阿訇各据一处,各司其事,成为几万个发号施令的独立政府,“弄得我们这几千万的教徒头晕眼花,也不知哪是我们合法的政府,哪是我们应当绝对服从的合法教长发布之教令”[24]。由此可见,各地礼拜寺均各自独立,这种寺与寺之间毫无联络的气象,使“教胞的感情日疏一日”[25]。
回民组织分崩离析,互相倾轧,个人主义盛行。教民们只是本着“凡是穆民都是兄弟”的精神,简单地强化地位平等,所以不免出现彼此不能相协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教长若是没有足够强的组织能力,教胞又彼此不相服从,势必导致分裂不能团结。而身负宗教工作责任的宗教事业者,更是派别层出,意见分歧,各不相容,各树一方,甚至“变本加厉五花八门的自分小派,非但是失掉了穆民一家的情分,而且是各以己见而行事”[26],致使回教虽没有遇到外界狂风骤雨的摧残,内部反倒因为一时意见的分歧,互相攻讦,互相倾轧。
除了组织的分崩离析外,回教还有新旧之争,旧教之下还有派别,即回教所谓门宦,门宦之下又有小门宦[27]。中国回教新旧派争由来已久,起始于清乾隆年间的陕、甘两省,渐次蔓延于全国。究其原因不过因各教长所遵之教法、经典不同,导致他们在传习回教礼法时难免有所差异。于是,各教派各是其所是,不甘屈服,先是各结党派,断绝往来,继而互相诋毁,亲朋反目。新派视旧派为顽固,旧派视新派为异端。在新旧两派之间,持中立态度的教长和教徒都袖手旁观,仅有极少数热心教民不辞辛劳去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但该教长等便引经据典,剖陈教理,甚至表示“宁可断头流血,为教牺牲,绝不能与异端并立”,往往使调解人瞠目结舌,不敢置辩。在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调停人也只好敷衍了事。即使新旧派争虽于表面上暂归平息,而“骨子里之暗争,仍为与日俱争”[27]。
旧派盛行于甘、青等省,对宗教的形式看得比较重要,较为守旧,对教内教外的屏限特别认真,在经典、礼拜、斋戒、课施、朝觐各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异之点,只是在婚丧及别的事情上混了不少的中国风俗而已[27]。其长处是“慎重将事”,认为教门中一切仪节,都是先辈贤达根据天经推衍出来的,足以垂范于后世。因此,教民只能奉行遵守,不能非议,更不能擅自变更。其短处是“抱残守缺”,恪守先辈遗留的有限典籍,排斥其他的社会学科,墨守旧法不知顺时维新。
新教则比较开明、进步,对不适应环境的细枝末节勇于改革,此派主要盛行于宁夏。其长处是“实事求是”,凡遇宗教问题,都要认真研究,对于学术,不故步自封,而是力求进益。其短处是‘轻举妄动’,凡见到西方各地与我国旧日所行略有不同,不问是非辄便改革,甚至全盘否定,将西方传来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过于趋重形势,忽略精神[13]。
由此可见,中国回教“新派”“旧派”的分歧,并不是根本信仰上有所抵触,而是纠结于一些枝叶浅层的问题,遂生发了不同的观念。所争之点,只不过是日常习惯和礼拜形式上稍有歧异。但“一夫倡之,百愚合之,驯至年长日深,意见滋甚,由立异以疏远,由疏远而断绝往来猜忌横生,至互相仇视,互相攻击”[28]。而两者思想分歧甚至相互攻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回教的发展和振兴。
回教除了遭遇上述困顿外,回民经济的落后、政府政策的缺失和当时社会环境的恶化等都使回教的处境雪上加霜。就经济而言,在中国回民中,除几个极少数家境稍微充裕的“小康之家”外,很少有富拥巨万的大资本家,十之八九都是“朝服夕食的小市民,及专凭两双胳膊挣钱讨生计的小工人,他们的生活简直是痛苦极了,走遍中国的回民住地‘穷回回’是时常能听到的”。[29]就社会环境而言,随着科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和宗教对立便成为一种时尚。受此影响,“非基督教运动”“反宗教运动”“庙产兴学运动”等都曾一度声势浩大,仿佛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使回教遭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和打击。就政府政策而言,虽然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明文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宣称“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真正尊重和平等对待,而只是加以利用,所以在处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事务时往往暴露出偏见与限制。1928年中央命令,登记全国各地寺庙庵观,并估价纳税,“官府将吾教清真寺也误认为寺院之类,所以各地回民,均甚恐慌”[30]。1940年10月,参照《监督寺庙条例》,另行制定《清真寺管理办法》,得到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批准和备案。
总之,近代回教在发展中教义不举,不仅教民义学修持水平低下,而且没有向外界宣传,这就大大限制了回教的发展以及回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尽管回教有识之士认识到回教不重视回教教育和宣传的弱点,并企图有所改变,也兴办过一系列的学校,但限于教职员的文化素质较低,没能取得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效果。内部派别分立使他们相互攻讦、非难,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回教的发展。上述问题使回教处于困境之中。这尽管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总的来说,和伊斯兰世界当时所经历的严重近代化困顿密切相关。面对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回教徒需要具有相当的适应和容纳能力,像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逐步走出封闭状态,投入变革的浪潮。
[1] 重川.本报周岁的一点感想[J].月华,1930(31).
[2] 馨吾.回教不振的根本认识[J].月华,1929(3).
[3] 薛文波.回教两个重大的问题[J].月华,1930(9).
[4]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J].月华,1937(22).
[5] 王国华.回教的一线曙光[J].月华,1929(4).
[6] 静.现代中国回教青年的危机[J].月华,1930(6).
[7] 正钧璞.黑龙江全省穆士林之概况[J].月华,1931(33).
[8] 杨健美.扬州回教概况[J].晨熹,1936(5).
[9] 苏德宣.四川穆民概略[J].月华,1934(11).
[10] 马君图.伊斯兰学友会第一次公开讲演词[J] .月华,1930(8).
[11] 陈智伯.一段心声[J].月华,1930(29).
[12] 翔平.“念经的”与“念书的”[J].月华,1935.
[13] 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14] 罗扬.牛街回民生计谈[J].月华,1930(17).
[15] 戴鹏亮.河北交河泊头镇回民状况[J].禹贡半月刊,1935(4).
[16]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17] 特瓦杜拉.中原回回[J].月华,1947(6).
[18] 马绍良.昆明回教概况[J].月华,1935(25—27).
[19] 文迈台.教法应由大众互相维持[J].月华,1930(19).
[20] 光仁.洛宁县回民概况[J].月华,1930(33).
[21] 袁烈成.中国二十年来之教育观[J].佛化新青年,1923(7).
[22] 天,伶仃.回教青年的出路[J].月华,1930(8).
[23] 王振远.回教在中国所以不能发展之原因及其挽救之方法[J].月华,1930(35).
[24] 作者不详.北平回教同人迎王大会志盛[J].月华,1930(27).
[25] 李荣昌.我对于兴教计划的意见[J].月华,1930(21).
[26] 万里.中国回教在派别上的立场[J].月华,1932,(5).
[27] 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28] 王曾善.长安回城巡礼记[J].月华,1933(1―14).
[29] 庄稼人.中国回民的生计问题[J].月华,1930(15).
[30] 笑飞.威县黄家街小学校的沿革现状[J].月华,1930(10).
〔责任编辑 刘小兵〕
K26
A
1006−5261(2014)05−0099−04
2014-02-24
单侠(1978―)女,山东单县人,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