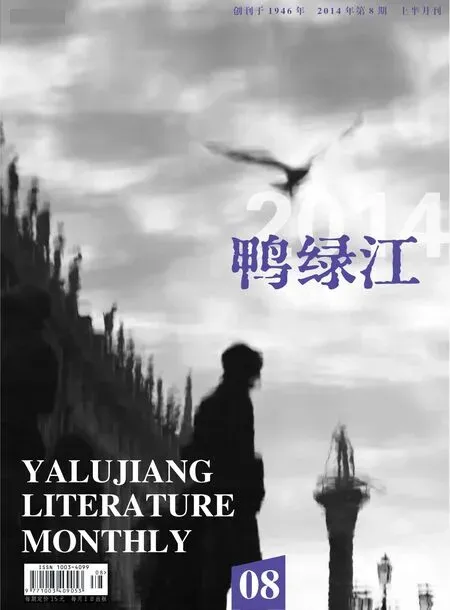我写《故宫的风花雪月》
2014-02-12祝勇
祝 勇
我写《故宫的风花雪月》
WO XIE〈GU GONG DE FENG HUA XUE YUE〉
祝 勇

祝 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纸天堂》等,二十卷《祝勇作品系列》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任总撰稿和导演,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十佳纪录片奖、学院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有一天,欧阳江河对我说,他喜欢《故宫的风花雪月》,因为它既是文学,又有专业特点。接着,他补充说,很像《香水》。
在此记下这句话,并不是要借欧阳江河老兄的话表扬自己,而是觉得他很犀利。因为某些专业性的知识是很难与文学相融的,这几乎是要把一份说明书写成诗歌,但我认为写作本身就是难度的同义词。写作不是工作总结或者思想汇报,只要把意思说清楚就可以。
我至今说不清楚《故宫的风花雪月》究竟是怎样一本书。表面上看,它是一本关于故宫书画藏品的书,这些藏品包括王羲之《兰亭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实际上这些艺术珍品不过是我透视历史的一个“视窗”,从那一扇扇美轮美奂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种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看到个人与时代的纠结,以及复杂的人性。因此,我不只把它当作一部艺术之书,更当作一部历史之书、一部人性之书。
没有一部艺术史会回避这些作品——关于《兰亭序》《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言说早已穷尽了,你还能说什么?我想起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曾经说过,“红学”已经完成了,或者说,它已经终结了。
每个写作者都面对着自己的难度,但这本书的写作又是一种别样的难度。它的困难在于它瞄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最广为人知的艺术作品,有无数的专家站在那里,等着给我的文字挑毛病。我没有挑选一些生僻的藏品,或者生疏的题材去“独辟蹊径”,而是往人堆儿里扎,去写人们最熟悉的艺术品,说明我任性、放纵、胆儿肥,不管不顾,不预估成败。在我眼里,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是一样。他们是人,有幸福和微笑,也经历着平凡、痛苦、失败甚至屈辱,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作品的品格固然高山仰止,但至少人格是平等的,因此,只要以人的思维、情感去面对他们就可以了。这是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基本态度。
写作上的任性和放纵并不等于胡来,艺术的基本标准是必须承认和遵守的。关于上述艺术作品的所有研究资料,只要我能找到的,都尽量搜罗来。不只是专业上的慎重,更是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但难度其实是一层屏蔽,我们常常被它遮蔽掉了,冲破它,有时只是挑破一层窗户纸。那些汗牛充栋的材料绝不会捆住我的手脚,因为我知道所有人的观察都有盲区,在那个盲区,我可以放心地驰骋。
这些艺术史的研究成果固然巨大,但它们几乎全部是把故宫收存的这些艺术品当作研究对象、当作一个历史的“遗址”来进行解析的。在他们眼里,它们都是死物;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活的,它们就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说过的:“我不会完全死去。”它们的神经和细胞仍有着生命迹象,所以才能与我们的生命进行交流——尽管有些艺术品被完成以后,它的作者就在历史的长河隐身。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这样。
张择端的结局,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被历史弄丢了。自从他把《清明上河图》进献给宋徽宗那一刻,就在命运的急流中隐身了,再也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他就像一颗流星,在历史中昙花一现,继而消逝在无边的夜空。在各种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是,汴京被攻下之前,张择端夹杂在人流中奔向长江以南,他和那些“清明上河”的人们一样,即使把自己的命运想了一千遍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流离失所。也有人说,他像宋徽宗一样,被粗糙的绳子捆绑着,连踢带踹、推推搡搡地押到金国,尘土蒙在他的脸上,被鲜血所污的眼睛几乎遮蔽了他的目光,乌灰的脸色消失在一大片不辨男女的面孔中。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品都是由人创造的,但伟大的作品一经产生,创造它的那个人就显得无比渺小、无足轻重了。时代没收了张择端的画笔——所幸,是在他完成《清明上河图》之后。他的命,在那个时代里,如同风中草芥一样一钱不值。
所以,由那些起起伏伏的线条,我看到的是起起伏伏的手,和起起伏伏的命运。我想我的文字也是有线条感的,它是由作品本身的线条、个人命运的线条和历史的线条共同组成的。我自信没有一个人像我写《故宫的风花雪月》那样写过它们和他们,无论我将成功,还是失败。
聚斯金德的《香水》是我最推崇的作品之一。虽然它只是一部小长篇,但它“薄皮大馅”,是一部多层次的、有立体感的作品。首先是它的专业性,也就是说,聚斯金德有着无比精致的香水品位,以至于我时常把他当作他作品里的格雷诺耶,无须目视,凭借天生的超强嗅觉就能分辨世界上的事物,无须仪器化验就能准确地判断一种香水的配成比例。此书中文版译者在出版前言中说:“丰富的专业词汇,遣词造句的巧妙准确,是小说取得成功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让我想起有些中国文学作品,张口就看出业余,比如写医生的,病人送来时,医生只会说:“救人要紧!”同样的场景出现在一部外国作品中,医生脱口而出的绝不会是这些口号式的废话,而是一连串的专业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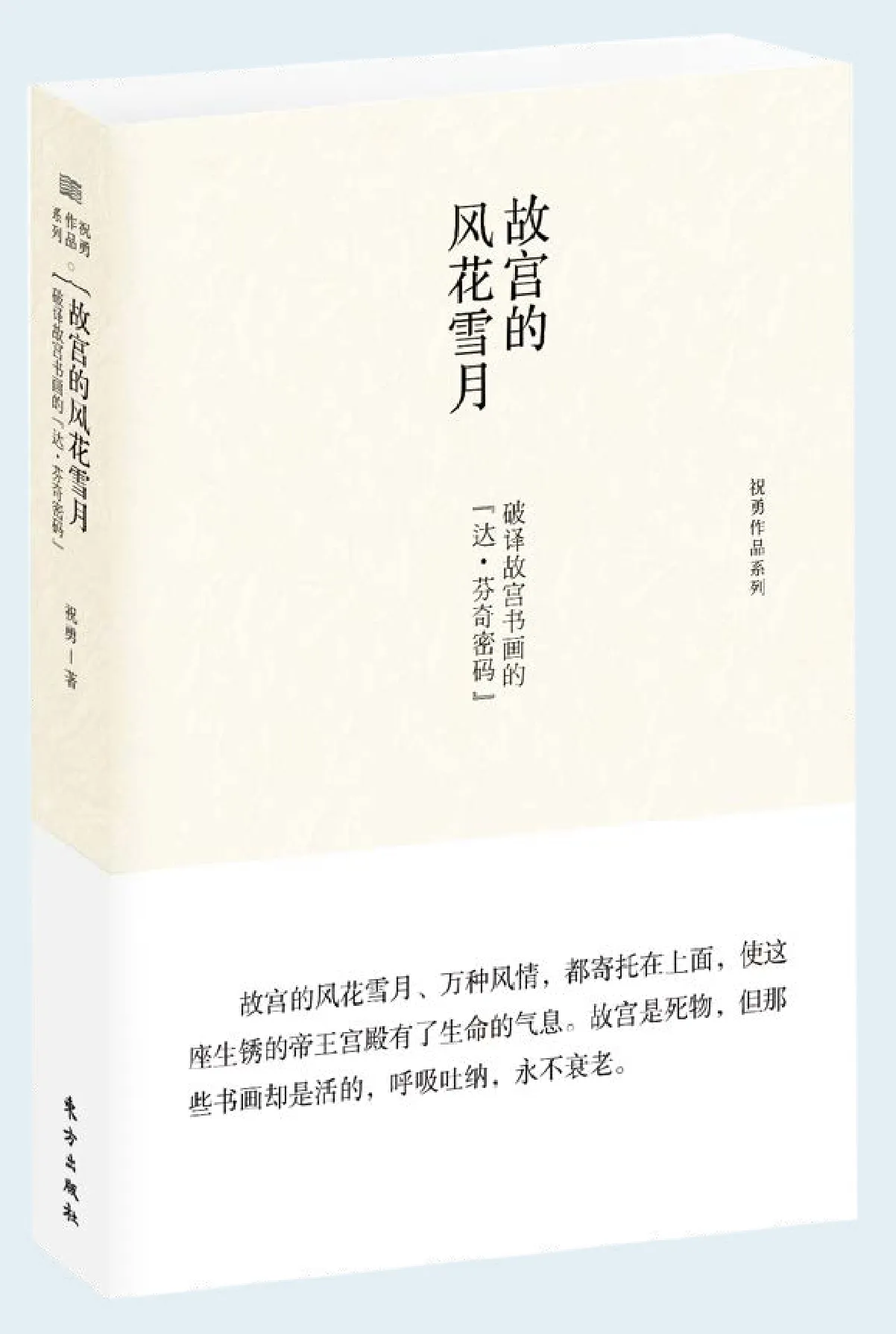
这种专业性,为《香水》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作品的故事性(传奇性)完全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甚至,这种专业性本身,就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它,就没有了整部小说。
当然,《香水》最伟大的地方,是它对于人类命运的某种深刻的隐喻。尽管它写的是历史,但这不是一部封闭性的作品,而是有着无限广大的阐释空间,对它的阐释就可以再写一本书。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当格雷诺耶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像《香水》这样建立在专业性上的作品,中国并非没有,比如麦家的《暗算》。这部作品同样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但它的隐喻性、传奇性,首先是建立在他的专业性上的,尽管那个“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的耳朵”“最小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的耳朵”的瞎子阿炳,多少有点像靠一只鼻子闯世界的格雷诺耶。
文学不是无数种专业学科中的一门,文学与其他学科相比,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交叉关系,甚至笼罩在其他所有学科之上。因为文学并非只是文之学,而是人之学。其他所有学科都是关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或者一个侧面,而文学则是关注这个世界的全部。人的存在,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存在。因此,条条大路通文学,从任何一门学科出发,都可以抵达文学。无论是香水学、密码学,还是历史学、艺术学,甚至工程学、医学,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一拐弯,就可以进入文学,并因文学而殊途同归。
反响:
祝勇不是一个一般的散文家,应该说这个作家在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散文发展中是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早年间进行新散文写作,祝勇可以说是其中最坚决、最彻底、坚持的时间最长的一位。现在看,我觉得我们衡量一个潮流或者一个现象,一个是看他本身的成就;另外一个也是看这个潮流和现象对于文学,对于我们某一方面的创作,确实发生了潜在的持久的影响。这么多年下来,祝勇通过他大量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写作,当年新散文所确立的一些话语方式,在现在已经成为很多散文的通律。一个作家的这种创造和坚持,到最后某种程度上影响文风,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在可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从那么多的散文中,去辨析祝勇的声音,确实值得研究,确实是祝勇的厉害之处。
《故宫的风花雪月》,我觉得第一是很好看,第二也确实有研究的价值。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祝勇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关于我们的文化,关于我们的经典,我们不断地进行现代性,或者世界化的阐释——用“五四”以来的世界性的话语要去重新解释一遍。我们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概念,但我们有时候一说就错。当我说古人想什么的时候,我一说,一定不是古人想的那种,因为我已经用了那么多现代的概念了,我们已经抓不住古人的那个微妙的调子了。我们现在说中国要有文化自信,要去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更需要从传统内部、要用它自身的概念和自身的范畴,去对它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需要恢复对传统的感受力。当我们试图用这套现代话语对传统加以理解,拿笊篱去捞,虽然捞上来一些东西,但是从笊篱眼里流下去的东西更多,甚至,那些才是传统文化的生命、精神、神韵。
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祝勇,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他在这方面做了很艰苦的努力,我之所以说很艰苦的努力是因为这个局面特别难。祝勇是很现代的,祝勇也有一大套的概念,但是我觉得祝勇蹲在故宫里做一个“老学人”还是很不一样的。我最喜欢和最珍视的还是在这本书里透露出来的对于我们文化的经典带着体温的理解,带着温度,有可能做到的是你贴上去的那样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力的恢复和重建,是祝勇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进展。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难度和我们应对这个挑战的勇气和方向。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故宫的风花雪月》是当代散文创作中一部难得的作品。它具有很强的复杂性,真正优秀的作品不可能是单一的,用一个角度完成的。祝勇对散文的边界有很大的拓展,既不是按照我们中学课本上学到的刘白羽的模式,锐气也超过了余秋雨,当然散文流派众多,但无论怎样,像祝勇这批写作者,把散文的文体边界大大地拓展了。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 梁鸿鹰
关于故宫的叙述确实是一个大学问,祝勇是一个文学家,他带着良好的审美天赋进入故宫,以一个作家的角度去面对故宫,没有文物系统人的腔。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强烈好奇心,所以他能够跳出来,用文学的和现代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古代的遗物,把历史话题激活了,写得很漂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 孙 郁
习总书记讲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我觉得讲得最好的一句是“让收藏在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迹里的文字都能活起来”,我觉得祝勇的书产生在习总书记说这个话之前,确实把宫殿里的这些文物、书画,做了个人性的还原,这种还原是非常美的,在当代做这样一个事情特别有价值和意义。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何向阳
散文本身是一种具有极强的现代性的文体,西方的现代哲学越来越非常散文化,比如本雅明、罗兰巴特、福柯,都已经不是那种模式化、结构化,像黑格尔那种庞大的体例,而是打碎体系,从语言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来进入哲理上的书写。
祝勇对故宫的叙述也是现代的,他完成了我想象中的对古典文化的现代性叙述。其中,我最喜欢这里面的《韩熙载,最后的晚餐》,他对四层权力关系的分析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深入,事物本身的深刻性随着谜团一层层解开,达到了非常深的深度,已经超越了散文。只有超越散文,才能写出真正的好散文。否则,散文就仅仅停留在美文或者抒情散文的层面上,而没有思想的高度。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就是我理想中的散文。
——著名作家、《十月》副主编 宁 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