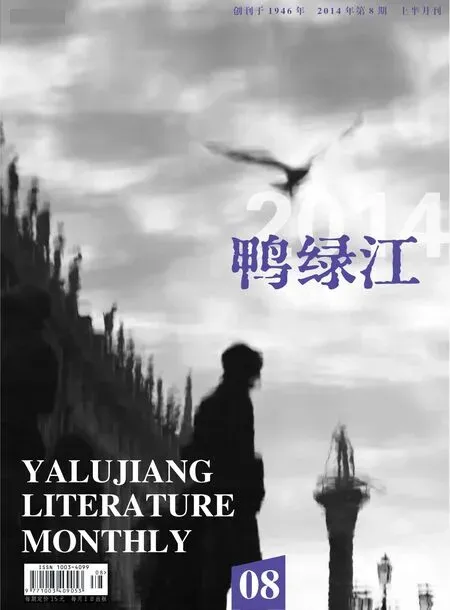抒写苦难,书写光明
——论白朗的文学创作
2014-02-12李春林
李春林
抒写苦难,书写光明
——论白朗的文学创作
SHU XIE KU NAN,SHU XIE GUANG MING
李春林
白朗一生创作丰富,共有短篇小说二十六篇,短篇小说集五部,中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两部;散文二十八篇,散文集四部;报告文学二十篇;诗歌十二篇;短篇传记七篇,长篇传记一部;评论十六篇;其他作品三十二篇。由于资料有限,这个统计是很不精确的,肯定有遗漏,也难免有重复。
白朗的创作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创作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作家本人在其表现东北地区土改的短篇小说集《牛四的故事·前记》中写道:“这个小集子里收集的六篇东西,是一年来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创作方面的一点点表现。按质量来讲,自然这些东西都是极不成熟的半制品;按成绩来讲,更是微不足道的。但稍堪自慰的是: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由于自己开始进入了农村,放下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与农民接触,向农民学习的结果。从而认识了自己,改进了自己,同时呢,也正是改变创作风格的开端,这是与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个人说来,该是一种微小的收获和进步……”所谓创作风格的改变,主要是指由原来的“主情”转变为“主事”;前期抒写苦难,后期书写光明。当然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两者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抒写苦难要以对苦难的述说为前提,书写光明更绝非弃绝对光明的感情,两者是互相渗透的,只不过有主次之分罢了。
前期:抒写苦难
白朗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之一,其前期创作具有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普遍特色——敢于直面美丽乡土的无尽苦难,着力抒写人们的丰富情感世界。
白朗出生于沈阳市一个中医世家,童年的生活快乐而幸福。后来祖父失业,从小康坠入困顿,白朗开始体验到社会的种种苦难,这决定了她的文学创作直面苦难的基调。同时对鲁迅的憧憬和对苏联文学的热爱,为她的文学创作注入了进步的、革命的因子。后来她在哈尔滨直接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活动,这必然使得爱国主义情愫及反抗、战斗精神成为她许多作品的与苦难抒写相纠结的重要内容。
《叛逆的儿子》是白朗最早期的代表作,1933年在《大同报》副刊《夜哨》连载。作品有三条故事线索:主线是地主子弟柏年携父亲小妾银娜离家出走;两条副线一是K村王老伯一家被柏年父亲逼得家破人亡,一是良家女儿银娜被另一地主儿子欺骗落入妓院又被柏年父亲赎回为妾。三条线索相互交织,两条副线使得柏年了解到下层人民的无尽苦难和死亡,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无量罪恶,最终促成了柏年的叛逆之举。值得注意的是,柏年虽与银娜一起出逃,两者却非情色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同情和扶持的“难友”关系(同被柏年父亲压迫欺凌)和“同志”关系(寻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这在柏年出走后给其父的信中有明白的昭示:“我要从充满了奸猾、残忍、欺骗、自私……的家庭里救出我自己,并且和我同样可怜的人——银娜……我们不是逃来要组成一个狗男女式的小家庭,我们是出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要做一个健全的人,要做一个生命、肉体、思想、意志、自由都健全的人。我要创造幸福的世界,造福给全人类,我要打破现代社会一切制度的矛盾,我要毁灭片面的自我或局部的自私自利的人类……”有的研究者仅用作品写的是一个青年携地主父亲小妾出逃的叛逆故事来概括作品,易引起理解的歧义。柏年与银娜的关系绝非《雷雨》中周萍与繁漪式的关系。正因如此,柏年的叛逆不独是对封建家庭的反叛,更是对其所属阶级——人间无量苦难的制造者——的反叛,是有着更为高远的理想的反叛。尽管此时刚刚步入文坛的作家笔力还未免柔弱,但作品的思想意义却不容低估,并且小说的结构安排、故事线索的处理、人物关系的设计也是值得肯定的。

李春林,1942年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已退休),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现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理事。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方意识流文学》《寻找“绿棍”》《鲁迅世界性的探寻》等七部,译著、合著专著、主编与合著教材、工具书等二十部,论文、评论等二百三十余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七十五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三十五篇。
白朗早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尚有中篇小说《四年间》,此作刊于1934年《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带有明显的作家自传质素。主人公黛珈是一位纯洁而清高的女性。自与矢野结婚后,在婆婆的迫使下中辍了学习生活。她有着“要做一个人,要做一个有为的女人”的理想,但由于接连不断地生育和三个孩子的夭折,只能陷于痛苦悲切之中。后来虽然到学校任教,却备受打压排挤,不久即被迫辞职。作品揭示了社会和家庭对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摧残,表现出在那样一个社会,女性很难得到自由和解放,同时也批评了许多社会陋习。作品从女性精神生活的视角控诉了社会的种种苦难。
《狱外记》是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哈尔滨到上海后,于1936年写的长篇小说,共三十二章。到延安后在文艺座谈会前曾改写。在延安的《谷雨》和《解放日报》各发表两章。其余全部手稿均在“抢救运动”中被收缴,再无下落。现在能见到两种文本,一种编在《白朗文集》三至四卷“散文集”,另一种在该文集第六卷“未了篇集”。文集编者未说明两者写作及发表顺序。从文字上看,前者似比后者更有润色;从内容上看,最大的调整在于后者的《与我的敌人握手》章名不见,内容亦由找日本主管司法的官员青柳疏通关节变成找官员的夫人,官员的名字也变成了山田,如此改动显然有益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从作品的人物名字来看,后者多用真名,如金人、金剑啸、萧军、萧红等,前者几乎都改了名字。这更像是创作小说,而非纪实文学。所以,我以为前者是后来修改过的文本。

1949年,白朗(左三)与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主人公原型(中间持花者)等合影
作品男女主人公姓名分别为申勃和刘笠,与罗烽和白朗的笔名“彭勃”和“刘莉”暗合。故事有着浓烈的思乡情结,在“九一八”之夜的松花江畔,男女主人公一起思念着故乡的万泉河:“万泉河的荷花恐怕已经萎谢了吧?莲子是成熟的时候了!”或许是一种心灵感应,就在他们强烈思乡之际,故乡沈阳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从此申勃投入了反日救亡的秘密工作,终于被捕入狱。而此时的“我”(妻子刘笠)恰正陷于一连四个婴儿夭折所带来的苦痛之中,丈夫的入狱给她带来的打击有如雪上加霜,更显沉重。丈夫正在报刊上连载的小说《离散之群》成了不幸的先兆和隐喻。家中被炒,一塌糊涂。对丈夫的忧心和挂念,使得“我”决意去给丈夫送衣服,结果却备受刁难和凌辱。“我”试图打通关节,同样困难重重。噩梦连连,同事讥讽,加重了“我”的精神苦难。她去狱中探望丈夫时监狱里传出的话是“把这里的惨痛宣布到世界去吧!”使她得到了鼓舞。这篇《狱外记》如其题名,主要不是写入狱人的苦难,而是写狱外人的精神苦难。作品有这样的心理描写:“和勃别离时,月儿正像一把明亮的镰刀。夜夜,我望着她那逐渐发胖的脸已经是皮球一样的滚圆了。而我却正和她相反:逐渐消瘦了。我那红润的、丰满的脸,已在开始苍黄、凹陷。到月缺时,我的脸是否能再恢复原形原色呢?”此处既有苦难对她的精神折磨的外在反映,也有着经过苦难磨砺后内在的些许平和。她虽然觉得丈夫的宁死不屈可能会给自己和全家人带来噩运,甚至为此惊恐,但她马上反驳着自己:“然而,勃做错了吗?难道他的行为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吗?”她对狱内的丈夫的肯定,亦是对狱外的自己的肯定。
人生最大的苦难还是死亡,白朗对此有深切的会心。她不单充分地展现了形形色色的死亡,还剔挖了死亡的意义。她前期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的许多篇章正是如此。
首先是对反抗、战斗者的生死观的抒写。
《轮下》写的是哈尔滨居民面临日伪当局野蛮拆迁的苦难及反抗斗争。南岗一带的居民遭遇水患之苦,不得不在空地上搭起小茅草房暂时栖身。然而日伪城管当局以整顿市容之名,野蛮强迫他们拆迁。走投无路的人们在陆雄、宋子胜等人的带领下前往市府请愿无果,最后与前来拆迁的城管官员和军警搏斗,陆雄等七十余人被捕,陆雄的妻子与儿子被碾死在囚车车轮之下:“陆雄嫂顺势一跌,便横卧在囚车的前边,身子和车轮紧紧地贴着。她是那么坦然地搂着小柱倒在那里,好像是睡在温暖的床上。”这同样是一种“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至于那被捕的七十余人,等待他们的也只有死亡:他们已经是武装反抗了,尽管武器十分简陋。诚然,此种被压迫者以死亡向压迫者进行绝望的反抗对于牺牲者本人或许已经没有生物学或曰物质方面的意义,却留下了战斗的火种、复仇的基因,或早或晚终会变成胜利的号角。
此种对于死亡的描写和死亡意义的剔挖,在《一个奇怪的吻》中亦有突出的表现。此作品主要是写一对革命伴侣的人生最后时刻。李华及丈夫在被敌人押解的途中一起跳车,李华不幸摔伤。为了让丈夫及时逃离继续从事战斗,自己不致成为负累,她选择了投河自尽,以自己的死换得丈夫的生——革命的继续。作品不仅写出了李华的革命坚定性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并且抒写了她对生命、生活的挚爱和对丈夫的多情。其实她最初的跳车动机,不独是为了继续战斗,也是由于对生活的热爱。押解她们的车辆途经故乡,引发了她对儿时的回忆:“无数的美丽的蝴蝶盘旋着,活泼的小鱼游着。”故乡之美激发了她强烈的生的欲望,因而才实行了跳车之举。但当自己负伤注定要成为丈夫的拖累,她就决然地选择了死亡:“我死,无论谁都不要为我流眼泪,当我瞑目之前,我看见一个为我爱的人,正向为民族而牺牲的大路上走去,我仿佛也看见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她将个体的死与民族的生的关系理解得非常透彻。她的生死观不单是理性的思考,并且有着丰富的感情因素。
另一篇《生与死》从命题上即已流露出其哲理性意义。本篇主人公安老太太是一位女看守,人称“老伯母”。绰号本身同其职业严重对立,业已告知读者主人公的母性情怀。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哈尔滨后,她被调任特别监房的看守。这使得她与八名女政治犯有了亲密接触。她对这些文质彬彬的女政治犯逐渐有了好感,不相信她们会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她看到她们病了,敢冒风险为她们送衣送被、传递家书,甚至不惜投入自己的工薪。她还破天荒地允许女犯们秘密串门交流。她对女犯们所遭遇的酷刑感同身受。同时,儿子与儿媳所遭遇的欺凌迫害,使得她更迅猛地觉醒,最终寻机设计将八名革命者全部救出。对于“老伯母”本人而言,她所换来的是惨烈酷刑和秘密处决;然而对于八位女革命者而言,则是新生,是革命和反抗的烈焰的更加猛烈。“老伯母”“一根老骨头换八条青春生命”的生命价值观,不仅从生物学的意义上非常划算,更重要的是,此种生与死的辩证法的实现乃是依凭民族大义和复仇正义的,从而进一步昭示了民族大义和复仇正义的永恒性。
《伊瓦鲁河畔》是一篇反对日本侵略者、以抗争精神为主调的作品。此作书写了一个偏僻村落漂筏村的农民自发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战斗的故事。“满洲国”的宣抚使带着一队护兵来到此地宣传“王道乐土”,强迫全体村民更换满洲国的所谓“国旗”。村民们在贾德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他们咒骂,抛掷泥鞋,故意将“王道乐土”读成“王大烟土”,尽情地予以嘲讽。他们发誓要做中国人,捍卫自己的乡土。后来他们遭到了镇压,贾德被捕,由于他依然大骂不止,嘴竟然被戴上了“嚼子”。最后义勇军的骑兵队赶来,救下了贾德,抓住“宣抚使”,祭奠了烈士的英灵。人们随义勇军进入山林,以进行更长久的抵抗。作品直面了故土故民惨遭异族凌虐的现实苦难,更讴歌了民众的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小说尾声尤蕴深意:曾经为敌伪做过事的老村长,在进山的浮桥上与已经参加义勇军的儿子相遇,老人呼唤儿子前来搀扶自己,儿子却大义凛然地说道:“卖国奴!谁是你的儿子?”老人羞惭难当,纵身跳河。儿子对父亲的决绝显示了民族大义可以战胜亲情;老人的跳河昭示出背叛民族者无有生路,只能以自裁的方式自我救赎。死亡使他的人生在最后时分终于闪烁出一朵火花,因而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尽管作品写得令人感觉未免匆忙和浮泛,但所宣示的民族抗争精神仍给人以崇高的审美感受。
白朗1940年春还写有中篇小说《老夫妻》。作品写的是一个落后的富裕农民在民族苦难中的觉醒和蜕变。张老财是一个思想愚昧、爱财如命的人。老伴经常布施穷人,他十分不满;为了能使亲生儿子得福居家守业,居然强迫其学抽鸦片。儿子不从,为了使自己的家产有人继承,居然过继了侄子得禄为子。老伴和得福被迫出走。当日寇即将袭击他所在的中条山石玉村时,我军动员百姓空室清野,进山避难,张老财却舍不得家财,并相信自己的“寿眉”,不肯离去。可是得禄及其妻、子为了逃命,弃他而去。在此孤独难耐之际,张老太太却回来了,但她是受命于在我军工作的儿子来烧毁自家谷库以免被日军缴获的。日寇进驻后,张老财亲眼目睹日寇轮奸了一对母女,之后将其虐杀。这使得他感到非常恐惧。在自卫队赶来袭击住在他家的日寇时,为他们的英勇所感动,并获得了复仇的快意。为了快速彻底地消灭日寇,他举火烧毁了自己的房屋。后来在向我军报信途中重伤不治,死前将自己的钱财全部交给老伴,让其散发给英勇作战的自卫队员,而置忘恩负义的继子于不顾。正是由于亲眼目睹了敌人的疯狂罪行,直面了民族的苦难,才使得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变,认识到了自我的小家和钱财在民族灾难面前的渺小和不堪一击,只有投入民族的复仇和战斗才会获得存在的意义。他对生命与钱财的弃绝,使他完成了从自私自利的农民到一个觉醒的人的精神蜕变。
1939年9月完成的《战地日记》比较独特。作品以日记体记述了从1939年6月18日至同年9月5日她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在华北前线的生活。作品仍流露着母子情、夫妻情、同志情、战友情,特别是抒发了民族战争中的昂扬的战斗情感,但整体看来,作品是以叙事为主,已经呈现出由主情向主实演化的苗头(其实《老夫妻》亦有此种倾向,这篇作品的素材也正是来自这次对前线的访问)。然而《战地日记》尽管写了许多战斗和胜利,却仍未全然离开抒写苦难,个体的与民族的,平民的与士兵的,妇女的与孩童的,访问团自身的(团长的死亡)与访问对象的。“这一切灾难与痛苦全是敌人的赐予”。在作家看来,苦难乃是一种个人成长和民族振兴的磨刀石。值得注意的是,此作写的是国民党军队战区,但其英勇作战、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对于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居然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统辖区毫无二致。这说明正义的民族战争会使所谓旧军队得到空前的洗礼。此作甚有历史价值。
白朗前期创作在艺术表现方面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作家善于驾驭较大的群众场面,如《轮下》中无论是写请愿还是写搏斗,都能群体场景与个体表现兼顾,彰显了陆雄的领袖风范、宋子胜的临危不惧、邹家昌的莽撞粗鲁等不同个性特征。作家有时还采用蒙太奇手法实行场景转换,由议论请愿到实行请愿,由请愿高潮到请愿失败,没有任何中介和过度。关于请愿队伍的脚印相互垒叠的描写,更是绝妙的电影特写。在语言运用方面也颇有特色,有时一语一词即能达到传神之效,如“由无数只眼睛,把气息奄奄的宋子胜送上不花钱的马车走了”。笔致似乎有点儿越轨,但将众人对宋的爱戴与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应该说在越轨的笔致方面,白朗与萧红有着近似的风韵。这些作品中,心理解剖也相当深刻。如《老夫妻》中对张老财的阴暗心理的剔挖就很有层次感,平时的自私自利,战时的胆小恐惧,惜命而又不舍财,尤其是在日寇轮奸顾大娘女儿时,他在刺刀的威逼之下居然帮助按住女人的手。“心像撕裂一样的痛”,但“死的恐怖使他不得不屈服”的复杂心理,表现得尤其深刻。
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浓郁的地方色彩,无论是语言还是具体情节,都满含着关东风情,苍茫旷远的大地,不幸而又不甘不幸的人民的命运交相融会,形成了苍凉、悲壮的美学风格。《伊瓦鲁河畔》的命名与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样,让读者悄然动容的都是作家对故土故民的静静流淌着的浑厚情思。再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白朗前期作品主情色彩浓烈,大多篇章均如此。这自然与她的独特生活道路和命运遭际相关联。本来东北作家群的主要创作都是完成在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之后,是流寓之中的对故乡的哀歌,白朗自不例外。他们有无尽的感情需要抒发,所塑造的人物和所描写的事件,有时甚至成为抒情的载体。这甚至决定了他们的代表作有时具有悼亡诗的素质。
后期:书写光明
1942年白朗创作甚少,除《狱外记》外仅有三篇(一篇短篇小说《诱》,两篇散文《纪念知友萧红》《自勉》)。以后至1945年几乎没有创作,只是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白朗回归故乡,进入东北解放区,才又有了爆发式的文学创作。
在反映土改的未完成的中篇小说《长城脚下》中,两位主人公宋良和孙洪蒙冤,县委赵部长和他们谈话后,他们觉得“不但给他们带来了安慰,更带来了光明和力量”,“使他们在苦闷的窒息中又看见了阳光”。白朗后期作品的重要内容就是书写光明——如实记载新社会的光明。
白朗初到解放区,其成绩主要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牛四的故事》颇有代表性。
《牛四的故事》内容及成就确如作家本人所言,都是反映东北农村土改前后的生活,艺术成就也不平衡。《牛四的故事》与《顾虑》是写党对落后群众(无论是个体的亦或群体的)的改造。在《牛四的故事》中,干部叶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并发动群众改造了懒汉牛四。主写牛四转变过程,侧写叶同志的工作作风,不独牛四的形象较为清晰,叶同志的形象也较鲜明。《顾虑》是写焦家村的农民土改后不积极搞生产。原因何在?起初“我”及其他工作人员均未发现——农民们不肯讲。但经过工作人员同农民一起劳动,终于心贴心了,了解到了实情:原来此村经常受胡子的滋扰,农民无心种田。于是工作人员领导农民开展了挖匪根运动,依靠焦家村群众自己的力量肃清了匪患。群众提高了觉悟,消除了生产的顾虑。
《孙宾和群力屯》描写了原姜恩屯(以当村地主姜恩命名)农会主任孙宾等人带领群众同地主姜恩、姜文飞父子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揭露了某些笑面虎似的地主的伪善面目。客观地反映出农民积极分子在斗争中只有阶级仇恨、缺乏掌握政策的能力,致使坏人钻了空子;褒扬了鲁区长深入细致、循循善诱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敌斗争的谋略。小说最后以将姜恩屯改为群力屯作为结束,肯定、歌颂了土改中群众的作用。《棺》同前篇一样,也是写土改中煮“夹生饭”的故事。四喜屯虽说斗了地主分了地,可是地主的威风并没有被打倒,农民并没有真正翻身,连已经分得的土地都不敢去种。党派工作队来煮“夹生饭”,地主也机关算尽,同翻身群众决一死战。地主马得镖装病装死,其实是在棺材里装满财宝、弹药,自己躲到地窖里顽抗。机智、勇敢的农民终于揭穿真相,将其捉拿归案。小说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民众的力量,同时也昭示出没有党的领导,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也就无所作为。
这部短篇集表明,白朗善于选取土改斗争中的一些特殊事件来对土改斗争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观照。作家自觉地遵照毛主席《讲话》的指导思想,追求语言大众化,但不芜杂化。同时又能依照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地位、个性,语风有所变化。
至于《长城脚下》,则将土改的曲折与复杂展现得更为厚重和深沉。由于左倾路线肆虐,位于长城脚下的冀东马村的土改进行得极为艰辛痛苦,突出表现就是落后势力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反攻倒算。值得肯定的是,作品并未将农村的复杂斗争仅仅局限于土改的当下,而是以主人公回忆的倒叙和插叙方式将笔锋上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各阶层、阶级之间的纠葛与较量,从而使对土改斗争的表现有了纵深感和历史探源的意义。尽管斗争十分残酷,作家仍给我们展现了光明的前景:两位被诬陷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的解决熹微初露,倘若作品得以完篇,理应是光明的结局。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是白朗书写土改生活的主旨。
随着大批城市解放,白朗关注的重点也移向了城市生活。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是白朗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1950年10月10日完成初稿,同年12月15日修改,翌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同年12月再版。1953年5月第二次修改于沈阳,翌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九次印刷,讫198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印刷十五次。
作品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区的工人生活,题材比较鲜见。当时只有草明有较大收获(长篇小说《原动力》《火车头》)。作品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位先进女工的形象,这是与草明创作的不同之处。主人公邵玉梅本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婴,被其养父拾来养大。但由于养母重男轻女和她并非亲生,不独得不到母爱,反而备受折磨和虐待。然而苦难锻炼了她的品格和意志,养成了她坚韧顽强的性格。作品从多个方面展现了她的美好性格基因,她不独有天生的美丽,而且有似乎天生的善心:总是“关心别人更甚于关心自己”。在日本人的纱厂出劳工时,为了使同伴们逃过鬼子的打骂,她经常帮别人干活,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活落下。睡觉时,她专拣又潮又冷的地方,好位置让给别人。她所在的城市解放后,她获得了新生,并且为了谋求真正的独立而到一家军工企业工作。在那里,她体验到了人间的真正的广大温暖,在此种外来热力的激发下,原有性格的美质得到进一步发扬。诸如不怕吃苦、舍己为人、胸怀大度、肯于学习等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必备的阶级素养在她身上迅速形成。作为一位年轻女性,她敢于并乐于从事危险工作,几经受伤而终未悔,尤其是最后一次为护厂险些丢掉双臂。作家为了彰显邵玉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还浓墨重彩地叙写她对其他职工的帮助和培养。她不单在生活方面关心他人,而且启发她们的工作热情和美好理想,思想单纯的小于、情感复杂的傅金苓都在她的帮助下成为共产党员和准共产党员。她的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大哥邵仁也在她的帮助下入了党。尤其令人击节的是,那位曾经百般刁难她、压制她学习技术积极性的组长刘勇,最后在她的英勇事迹感召下,也发生了精神蜕变。
然而作家并未将邵玉梅写成一个天生的英雄,而是着意描写了党将这块璞玉雕琢成美玉的力量。这种力量作家也未写成纯然的说教,而是依靠榜样的力量。在解放初期,党的各级干部朝气蓬勃,浑身闪烁着理想的光芒,有一种无坚不摧的伟力,更有着与广大的底层民众水乳相连的亲情。所以,邵玉梅这个贫苦、清纯、好学、向上的女孩子,很自然地引起他们的关注,并得到了培养和重用。无论是温存娴静、和蔼可亲的分场长章林,还是身残志坚、指挥若定的工厂总支书记黎强,都对她的成长关心备至。“她的天真,她的单纯,章林非常喜欢。她感到,这个平凡的女孩子,有着一个不平凡的个性,她那种内在的英雄主义,正在她的身上滋长着,如果注意启发和教育,是很可造就的。”这也确实成为章林、黎强一干人等对邵玉梅的基本态度和指针。看来,彼时的企业,不单将生产物质产品作为重要任务,更将培养一代具有英雄主义底色的劳动者作为必须殚精竭虑为之的事业。黎强“站在台上,仿佛一块铁,又像一座山,沉着,威严,给人以崇高之感”。这是邵玉梅对黎强的感受。黎强俨然已成为邵玉梅的审美对象。特别是在邵玉梅重伤之际,正是同样身遭重创却肩担重任的黎强,成为她近在咫尺的榜样。
邵玉梅是一位女性作家作品的一号主人公。这一形象理应包蕴着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邵玉梅在旧社会所受压迫并非来自男性,而恰恰来自女性。养母对玉梅的虐待固然有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的深刻影响,长嫂的寻衅亦不乏在老旧中国经常发生的妇姑勃谿的传统旧习,然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却是极度的贫困。因此,玉梅的出走,与娜拉的出走决然不同:不是女性与男性的抗争,而是经济自立与依附他人的抗争,亦包含着求自由与反压制的深层心理欲求。有意思的是,作品还描写了玉梅在发现了章林“女性特有的温存”后,觉得此种温存“在他母亲身上,在她嫂子身上,是连一分也找不到的”。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此时的玉梅那里,近似以是否“温存”来判别。此种觉醒还并非是性的觉醒,只能说是人的觉醒。此作的话题亦并非女性和女权的问题,而是人性和人权的问题。

1962年,罗烽、白朗乔迁到木樨地24号楼,朋友们前来祝贺
倘若说玉梅进入工厂之前其对立面主要是养母和长嫂,那么进入工厂之后则是组长刘勇。此人是个农村知识分子,工作虽然是积极的,但原则性不强,曾被地主拉了一把。他脱离群众,瞧不起没有文化者,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女性。将玉梅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矛盾冲突必然不可避免。而另一个曾与玉梅发生冲突者傅金苓亦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尽管后来两人都在玉梅的感召和帮助下发生了蜕变,但他(她)们毕竟是曾作为玉梅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作品如是设计人物关系显然带有彼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的影响。
总的来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在当时看来确为一部佳作,曾经哺育了众多读者,一再再版就是一个证明。在今天,其审美价值也许不高了,但其认识价值仍然存在。在今天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态下,无论是邵玉梅这样的人物,还是《为了幸福的明天》这样的作品,都是不可复制的。让我们为过往曾有的道德的辉煌和文学的崇高而自慰吧。
《开路的人》也是一篇描写普通工人成长故事的作品。鞍钢工人李凤恩在旧社会备受欺凌与压榨,不独有反抗意识,而且由于被迫干起了小商贩,在一定程度上沾染了些微保守意识。解放后,他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迅速地成长为产业工人的卓越代表,不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且掌握了一流的技术,成为一位优秀的炉前总技师、全国先进生产者。他自己说道:“从工人变成技术人员,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开路的人罢了!”他确实是党将普通工人提升为有着较高文化技术水平的高级劳动者的成功范例和先行者。需要指出的是,此作与《为了幸福的明天》明显不同:在那里,知识分子是作为批判对象、先进人物的对立面而塑造的;而在本篇,知识分子周传典却是工人技术成长道路上的不可或缺的导师,他不单有着高超的技术水准,更有着大公无私、诲人不倦的优秀品性。若说党组织是将普通工人培养为高级劳动者的战略制定者,那么周传典则是执行这一战略的战术制定者和实施者。这表明作家对社会认识有了长足进步。惜哉,篇幅所限,周传典这一形象无法得到更为丰盈的展现。
报告文学《纽带》发表于《鸭绿江》1966年3月号。作品描写的是大连(当时称旅大市)斯大林路食堂及其负责人鲍静芝的光辉事迹。一个普普通通的食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由于其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最底层的人民服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从而成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作品采取宏观叙说与微观描写相结合、面与点相胶结的表现方式,使店与人都能给人以较清新的印象。《“管得宽”小传——金纺老工人张功元二三事》记载了金州纺织厂老工人张功元的先进事迹。他大公无私,爱厂如家,凡事只要不符合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必要出面“管”——无论其是否与自己有关。此种强烈的自觉的主人翁意识,即便在那个光明的年代,亦堪称楷模。十年春节,他完全自愿地替人值班,“他想的不是自家的欢乐,而是工厂的安生,别人的幸福”。他在值班时,还要检修机器,每每累得大汗淋漓,“汗,像洗了澡;心,也像洗了澡——好舒畅啊!”为工厂、为社会做奉献,俨然已经成为他的内心要求,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国境线上的伏击手》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终于在我党我军细致入微的培养和教育下成长为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拉祜族战士扎拉(袁应忠)的阳光形象。白朗在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还书写了模范邮递员罗淑珍(《不平凡的劳动》),全国先进生产者、河北省模范教师郑清明(《锻炼》),全国先进生产者、“超轴”(多带车厢)和“绿街”(大区间不上水、不上油、不停车)运行记录的不断刷新者曹俊杰等各条战线的英模的事迹,表现了他们在光明社会的阳光人生阳光心态,揭示了时代造英雄的真谛。
白朗创作的大量散文作品同样以书写光明和英雄为主调,但与其报告文学作品相比,抒情气息较浓,这或许与散文体裁有关。
白朗说过:“英雄——这是一个多么高贵而美丽的名词啊!”(《心连着心》)作家前期业已塑造了不少英雄或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只不过他们大都带有悲剧色彩。后期,作家更将书写英雄人物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主旨之一,但减弱了悲剧质素,强化了崇高格调和楷模作用。
散文《英雄的时代》书写志愿军的英雄们,既写了黄继光、罗盛教等几位英雄的具体事迹,又对志愿军整个群体热情地讴歌:“他们曾经成班成排地冻死在凯旋的歌声里!当战友们来打扫胜利的战场时,竟发现他们仍然阵容整齐地摆着雄赳赳的战斗英姿。他们没有死啊,英雄们千秋万代都是永生的。”他们为新生的祖国“写下了一大部多么辉煌的史诗”。作品先由自己是一个克制力极强、不爱流泪,而今却每每被志愿军的事迹感动得流泪写起,然后引发出志愿军的伟大与崇高,感情层层递进,最后点出时代与英雄的关系:“英雄创造着时代,时代哺育着英雄。”此作与《为了幸福的明天》可作为姊妹篇来读:不独关于时代与英雄关系的立意相同,且有些地方具有互文性。如《英雄的时代》篇首所写的作家本人的自我克制力量与邵玉梅的自制力(后者的自制力可理解为前者的外射);英雄必须“忘我”,“有我”难成英雄,在志愿军和邵玉梅那里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考虑到《为了幸福的明天》1953年5月(抗美援朝胜利前夕)曾二次修改,我疑心作家将志愿军的优秀品质移植到了邵玉梅身上,因为邵玉梅给人的感觉过于理性,也是理想化了的——她毕竟是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女青年,作品中的她显得过于成熟。《谁不热爱英雄?》记叙和歌颂了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的英雄事迹,文末写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李兰丁同志。”昭示出作家书写此类英雄,乃是为了以他们为榜样,促使更多的英雄出现,庶几方可不愧于这英雄的时代。作家将英雄与生命力相连接,透视出这样的信息:没有英雄的时代,亦是没有生命力的时代,也就无有光明可言。此种思想在今日尤有深意,这也正是白朗这些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
白朗还是一位和平战士,是和平的歌者。在她看来,没有和平,也就没有光明。
她无限热爱新中国,不独因她是中国人民幸福的乐园,而且是“东方和平的灯塔、希望和信号”(《和平,人类的母亲》)。她赞美和平,宣称“和平一定战胜战争,生命一定战胜死亡,和平就是太阳,太阳是永远不会停止发光的”(《对战争的庄严宣判》)。她深信唯有和平才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她曾见证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高兴地写道:“东方西方和平的种子,在和平的阳光哺育中,已经冒出了青春的嫩芽。”(《和平的音讯》)她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和平的阳光下长大”(《保卫我们的孩子》)。而为朝鲜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祖国则沐浴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中。祖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因而更加光明。即便在《向普天下的父母控诉》这样的挞伐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集团对朝鲜儿童的屠戮的檄文中,亦不乏光明的乐音,写出了朝鲜儿童的坚韧、顽强、机智、勇敢、乐观、向上。《我要歌颂她们》则是以对个体有名英雄和全体无名英雄相互胶结的方式书写了战火中的朝鲜妇女,昭示出无论尚有多少苦难,她们终将会有光明的前途。

1952年,白朗受周恩来委托,陪同英国工党领袖、斯大林和平奖金获得者费尔顿夫人访问朝鲜前线,左一为白朗
白朗后期创作的美学风格可谓崇高与昂进。她此期间热衷于表现光明的时代和阳光的人物——英雄和模范,自然会使得作品禀赋崇高的美感;而与此相应,她的叙述基调也大多欢快、明朗,叙述节奏有如进行曲,少了些婉曲,多了些昂进。她的一篇散文命名为《祖国在昂进中》,写的是昂进中的祖国,表达的也正是自己昂进中的心态,读者也感受到了此种昂进的韵律,因之使得那种崇高的美感更为强烈。
遗憾的是,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94年逝世,白朗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再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这是白朗的悲剧,是中国文学的悲剧,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和那个时代的悲剧。
责任编辑 郝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