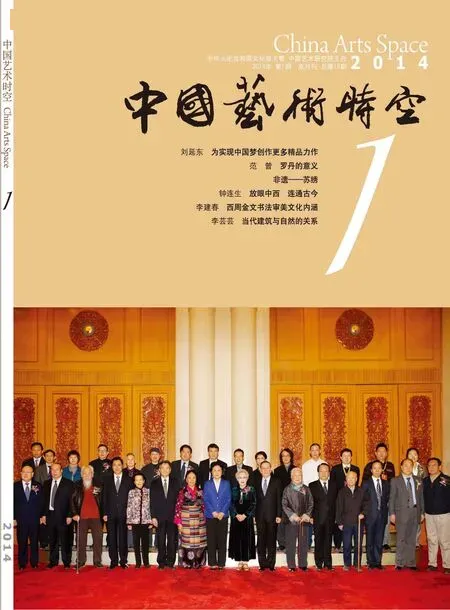我看齐如山与梅兰芳
2014-02-06杨建东
杨建东
我看齐如山与梅兰芳
杨建东

1928年4月15日的《晨报》载文说:“梅兰芳之名,无人不知,而使梅之藉获享盛名,实为高阳齐如山先生,则世能知之者鲜矣。梅所演诸名剧,剧本以及导演,胥由齐氏任之。”对此如何看待?
旧时代文人的“玩”和“趣”
先说说齐如山。要了解齐如山先要了解旧时代的文人,同时要了解旧京的“爷” 文化,旧时代的文人把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的范畴,基本上都称呼为“玩”。他们注意玩的精巧,玩的内行,玩的开心,玩的五花八门。而玩着玩着就玩成了行家里手。像鼎鼎大名的大收藏家张伯驹,本行是盐业银行的董事长,但他酷爱收藏和京剧艺术,结果在金融界倒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玩出来的古玩收藏和精研的京剧余派艺术倒成了他的立身之基了。王世襄先生,后来成了古旧家具的鉴赏专家;朱家溍先生成了京剧昆曲的研究家;吴祖光先生也是从“广和楼的捧角家”玩成了中外驰名的剧作家了!齐如山也是这样一位北京的“爷”。现在我们能找到的关于记述齐如山先生如何帮助梅兰芳先生的记载很少。因为从他的本性来说,在成为专业编剧之前,也仅是出于一种“玩”。如果仅凭文字记载的材料,没亲身接触过这类人,就很难理解到这一类人的文化性格。
在梅兰芳自述《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有段记载说:“我排新戏的步骤,向来先由几位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随时留意把比较有点意义,可以编剧本的材料,收集好了,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大略的写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同商讨……起草打草稿这位朋友,就是齐如山先生。” 这是一种情况,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齐如山为梅兰芳编的第一个剧是独立创作的,因为那时尚未有为名伶编著新戏的人。齐如山先生为梅兰芳写作的第一个剧本是在1915年,剧目是《牢狱鸳鸯》。此剧演出后,大受欢迎。齐先生的一位未记载姓名的朋友这样记述:齐如山兄曾为梅兰芳编《牢狱鸳鸯》一剧,初演于吉祥戏院。姜妙香饰卫如玉,高四宝饰胡知县。戏演到卫如玉含冤入狱,一上堂被胡知县喝令责打。这时台下有位观众一时激动,大喊:“杀人的不是他!”跳上台去,要与胡知县拼命,幸被巡警抱住拉开。可见当时演员演得多么精彩,也可见这出戏在当时观众中影响有多大!
在一个戏子没有任何地位的时代,为什么齐如山先生会走到梅兰芳身边呢?这也是有原因的。有清一代,王公贵胄、朝廷命官,嫖娼宿妓是要受到惩处的,但是狎优,却是没关系的。尤其晚清时期,中上阶层消费者如官僚、文人以至商人等的娱乐场所主要是戏园子和“堂子”。堂子,从嘉庆、道光、同治直到光绪时期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堂子初时叫做“下处”,即伶人的集体宿舍。嘉庆八年《日下看花记》等笔记中,有了伶人以“堂名”作为住处标识的记载。所以,堂子、私坊、下处,各种叫法都是指伶人的住处。
逛堂子也有个说法,叫“打茶围”,从事打茶围行业的伶人叫“相公”。相公从事的是“以歌侑酒”、“以曲伺人”的服务。所以又叫他们“歌郎”。“打茶围”是歌舞表演的配套服务,伶人演完戏之后,也在这里服务,额外再挣一份钱。台上看戏,台下看人,来消费的人们就乐此不疲了。“那时北京相公堂子,收拾雅洁,为士大夫游玩之处。余闲时亦常与二三知友,同游消遣。相公即是幼年学戏的孩子,年纪总在十三四岁,面目清秀,应酬周到。每逛一次,必须摆酒,只费8元,有八碟冷荤,颇可口,能饮者供酒无量,一面饮酒谈天,一面听曲赏花,亦觉别有风味。亦可飞笺,召他处相公来陪侍听唱,相公貌皆娟秀。亦有老板,即是师父。亦有娶妻,妻不陪客。出师后方可自立门户。出师即赎身之意,须缴一笔金钱与师父。”这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十五章的记载。堂子业由于必须要有好歌郎,所以,很多是由名伶兼营。这些场景在清代小说《品花宝鉴》中有详细的描写。据章诒和先生讲:越到后来,堂子业主就越重视歌郎舞台演艺的提高。这样,“堂子”作为科班的职能,就开始上升。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就是堂子业主,开了“景龢堂”。因此看来,北京的堂子除了是娱乐业之外,它还是培养名伶的重要渠道,这个职能差不多和科班相同。从道、咸、同、光四代215个名伶,堂子出身的有139个,占百分之六七十。所以当时出身堂子的名伶,非但不以这种出身为耻,相反能出身在名堂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对于自己的弟子,有的在自己的堂子里培养,有的送到别的堂子。如梅兰芳的伯父是把梅兰芳送到梅的姐夫朱小芬的“云和堂”里习艺的。
齐如山入梅丛撰写剧本
梅兰芳在“云和堂”结识了帮助他一生的一位“钱袋子”,此人名叫冯耿光,字幼伟(亦作幼薇),早年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回国后,在清政府任职。这期间,他通过梅兰芳的叔父梅雨田与梅结识。对此,曹汝霖也有过记载:“我友冯幼伟(耿光),日本士官毕业,服务于军咨府,爱护梅兰芳。时兰芳年方十二三岁,未脱稚气,然态似女子,貌亦姣好,学青衣工夫孟晋。幼伟月入银四百两,以其半助兰芳成名,始终如一。”1908年,14岁的梅兰芳加入了“喜连成”科班,带艺投师,在他19岁这年,上海《申报》有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梅兰芳尚未大红:“第一台特聘天下无双最著名优等艺员著名汪派须生王风卿,第一青衣花旦梅兰芳。……梅艺员貌如子都,声如鹤唳,此二艺员真可谓珠联璧合,世无其倚矣……” 王凤卿挂头牌,包银每月3200元,梅兰芳挂二牌,包银每月1800元。不过对于丹桂第一台的老板许少卿来说,此次演出无疑具有一点赌博的性质,梅兰芳是否能在上海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据《上海文联》沈鸿鑫记述:这次沪上之行,冯耿光陪同,帮助梅兰芳做了许多的宣传。把《时报》、《申报》、《新闻报》记者和文艺界要人统统拜访一遍。这以前,梅兰芳身边的人物大概有冯耿光、吴振修、李释戡等几人。除李释戡善文墨外,其他尽是金融界人士,而李释堪也是日本陆军学校出身。直至齐如山出现,才开始了梅兰芳的新剧排演。
继《牢狱鸳鸯》之后,齐如山又为梅兰芳编剧了《嫦娥奔月》,他记述的为梅兰芳写作《嫦娥奔月》的全过程,在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之前,我以为可为信史。
那是1915年的中秋节,照例是戏曲界必争的票房强档。第一舞台精心准备了应节戏《天香庆节》,这出戏本是宫里的老本子,演出效果极为辉煌热闹。王瑶卿还专门花费了8000两银子从上海置备了新的背景机关、华丽戏服,各种道具应有尽有,演员方面也汇聚了当红的杨小楼、陈德霖、王瑶卿、王凤卿、朱幼芬、王蕙芳、萧长华、姚佩兰、钱金福等十余位名角。这时的梅兰芳正加入俞振庭的班社。俞振庭找到他说:“我们也要排一出新的应节戏才好,否则一定要栽给他们!”……第二天兰芳跑到我家:“您可得救命!”齐先生问为什么?梅先生道出原委。齐先生一口答应,给他编一出神话剧。齐先生想到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戏写好交给梅兰芳,他和这些金融界的朋友看后不是很满意,齐先生建议他拿回去折单本(剧中每个人单人台词唱段叫单本),赶紧发给大家,让他们快些熟练起来,他亲自给大家排练。
当年的《戏剧丛刊》第三期中清逸居士有文写道:“至民国改元,各名伶虽排演新戏,而顾客仍未重视。自齐君如山,与名伶梅畹华(兰芳)编辑新戏,取昆曲之舞戏,移入皮黄,冶文学艺术于一炉,从此各名伶皆效仿之,争排新戏,风气为之一变,为鞠国数十年之创作!”另,据《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记述:“《霸王别姬》是齐如山先生执笔起草的,齐老根据《史记》及明代沈采所著《千金记》传奇铺叙成篇,末场用司马迁《项羽本纪》‘力拔山兮气盖世……’原句,对英雄、美人、名马作了概括的咏叹!而虞姬的出场引子‘明灭蟾光,金风里,鼓角凄凉’……此句是从《千金记·虞探》一折中一支【石榴花】曲子演绎过来的:金风飒飒,角韵动凄凉。时断续,暮云黄,乍明乍灭闪荧光,暮笳声,戍鼓残腔。把这只曲子浓缩成11个字,而不失其原曲本意是颇见才华的!……‘缀玉轩’中的诗人罗瘿公、李释戡等参加了整理剧本工作,而齐如山是欢迎大家修改的。”
从当时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身边的编剧如齐如山、清逸居士、罗瘿公、金仲荪和陈墨香创作剧本的时间先后来看,齐如山的创作时间居首,记载中始做剧于1915年,而也属较早开始做剧的罗瘿公为程砚秋所做的《梨花记》是1922年,清逸居士为尚小云做的《秦良玉》是在1924年,陈墨香为荀慧生做的《辛安驿》是在1926年。从这个排序看,齐老做戏在先,让当时不熟于此道的人去和已经实践写戏的人一起编写剧本的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罗瘿公和清逸居士、陈墨香也都是在齐老的鼓励和激励下开始从事编剧生涯的。
在戏曲圈里,向来讲究的是流派。当时的四大名旦,各领风骚,各人有各人的特色,各人有各人的创作班底,齐专为梅量身定造剧本。但自打齐如山和梅兰芳的合作中断以后,直至到1949年梅兰芳再无新戏出演,他身边虽然还是文人来往不断,但再能为他提升艺术而充当写家的几乎没有了。在新中国建国10年时,梅先生移植演出了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成为了他的绝响。
齐如山安身段舞动霓裳
齐如山不但给梅兰芳编剧,还独立执导这些戏,并给梅“安身段”。这里所谓的“安身段”不是像戏校或科班,先生一招一式的把动作设计好。齐先生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所谓的“技导”。我导演戏曲电影和戏曲MV时,在拍摄时为了适应镜头调度,有时有些动作需要改变,这样的时候,我会上前给演员示范一下,然后演员按照我的提示动作,做出程式化的标准动作来。在戏剧排演中,这也是“安身段”。另外,熟悉昆曲的人士都会知道,在民国初年,河北高阳一带是北方昆曲的祖庭。像与梅兰芳年纪相当的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等就是高阳籍昆曲演员。当时,昆曲在高阳一带还保留着很多班社。齐如山先生正是高阳人士,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唱昆曲的曲友。且其父还是苏州人帝师翁同龢的弟子,自然接触了南方昆曲。昆曲是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出现的,齐如山必受此影响颇深。在文人笔记中曾有学生赶考带着本村好戏者同行的记载,齐先生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说明耳濡目染很重要。像俞振飞先生的昆曲戏不是找老师学的,而是其父粟庐公亲自教授的,京剧艺术则是拜程继先学的。
我们至今仍保留着一句俚语,把到剧场观剧叫做“听戏”。那是因为在老年间京剧中的青衣只重唱工,不重视身段。那时的青衣演员往往是双手放于腹前,在台上演唱大段唱词,形象呆板,称作 “抱肚子”青衣。原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梁燕先生撰文《与梅兰芳同行的岁月》中提到:“齐如山要求梅兰芳在《嫦娥奔月》中的表演突破以往的范式,体现‘唱做并重、歌舞合一’的特点,他重点设计了嫦娥的身段动作。经过认真研究,反复琢磨,齐如山从汉赋、唐诗中描绘舞姿的词句里,从宋代的《德寿宫舞谱》等古籍上找到古代各类舞式的名称,设计出第十场‘采花’中唱【原板】时的‘花镰舞’和第十三场‘思凡’中唱【南梆子】时的‘袖舞’。这两场戏的歌舞表演是此剧的精华所在。在排练过程中,齐如山亲自穿上有水袖的褶子为梅兰芳示范。”
另据齐如山之女齐香的回忆:“他编的一出歌舞剧就是《嫦娥奔月》。除了化妆,要考虑身段。按昆腔剧,几乎每出都有身段。父亲自幼看过很多昆剧,起初他想安身段不致很难,没想到一入手,才知道难度很大,因为昆腔的歌唱音节圆和,皮黄的腔都是硬弯,身段安排有一定难度必须与音乐腔调相呼应。研究了几天,排出两场,只安排了南梆子和原板两种。以后在《天女散花》中,才安上慢板的身段。父亲也穿上有水袖的褶子,和梅兰芳一起排练,梅极端聪颖,理解深刻,演做俱佳。”
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也有齐先生给梅兰芳安身段的记载:“主要还是京剧舞蹈的东西,还有一部分动作是外行设计的。其中齐如山就出了不少点子。姚玉芙曾说过:齐先生琢磨的身段有些是反的。我说:有点反的也不错,显得新颖别致,只有外行才敢这样做,我们都懂身段的正反,也不会出这类的主意。”梅先生接受了齐先生虽看似外行但却别具一格的身段,是他思想上锐意改革的重要标志。
齐如山助梅访美
许姬传《梅兰芳旅美散记》记载:这次美国之行源于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曾观看梅兰芳表演的《嫦娥奔月》,他对梅兰芳的艺术大为赞赏,还特地到梅兰芳家拜访。他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此话被当时在座的交通总长叶恭绰(玉虎)听得,将此话告诉了齐如山,引起了齐如山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便与梅兰芳等人商定,“决议要把这件事情办成”。齐如山为此多方奔走,四处筹款。1929年春天,齐如山求助于李石曾,希望他能玉成此事。于是,由李石曾出面邀请了周作民、钱新之、冯幼伟、王绍贤、吴震修一些银行界人士和司徒雷登等人作为董事,以创办戏剧学校的名义进行资金的筹措。由李石曾、周作民、王绍贤、傅泾波、齐如山几位在北平筹款5万美元,钱新之、冯幼伟、吴震修诸人在上海筹款5万美元。
齐如山为这次访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国剧艺术,特意写了《中国剧之组织》,传记性的《梅兰芳》,特别要提到的是出版了《梅兰芳歌曲谱》,就这个曲谱的成书,我们在齐香先生的回忆文章里可以见到那曾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过程。首先让徐兰沅等人先把梅的唱段记成工尺谱,再由刘天华先生改写成五线谱,再拉给梅先生听,再进行修改,然后梅先生通过与之加工修改后的曲谱再跟胡琴和练,终于固定下来,历时七八个月。而将工尺谱改变为五线谱是为了要将曲谱呈现给美国方面而做的工作。
1929年冬,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曾连发两次电报给齐如山,告知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可暂缓来美。在梅剧团启程前的两天,齐如山才把电报交给冯耿光看,冯耿光问他这电报怎么不早点拿出来?齐老回答:“早拿出来,我怕动摇军心!”后来,冯把电报交给梅看,梅表示,欢送会也开了,船票也买了,报纸也报道了,若改变计划,恐成笑柄,遂毅然决然赴美,结果盛况空前,载誉而归。与司徒雷登的联系应该是出于齐如山的关系,因为他们在中国时已经开始接洽梅兰芳赴美之事。至于后来张彭春的加入是另一回事。
齐如山在台湾期间始终挂念着梅兰芳,他给友人陈纪滢的信中说:“……昨接小女自上海来信,……并云,梅先生已回沪,他在北平对人宣布,齐二爷未回平以前,国剧学会由他负责。即此一语,学会亦有益。大致因从前赴苏演戏关系,共党对他必相当有面子,果如此,则(焦)菊隐、马彦祥诸小丑,当不至再为难也,此亦差堪告慰者。”今岁旧年聚会,席间齐如山先生孙女齐克新和我谈了很多他晚年的情况,她说爷爷齐如山从广播中听到梅先生去世的消息,老泪纵横,她看到祖父连着三天都在房中落泪。并把梅先生赠给他的条幅挂上,以为缅怀。第二年在看戏中,因低头捡拾拐杖而突发心脏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