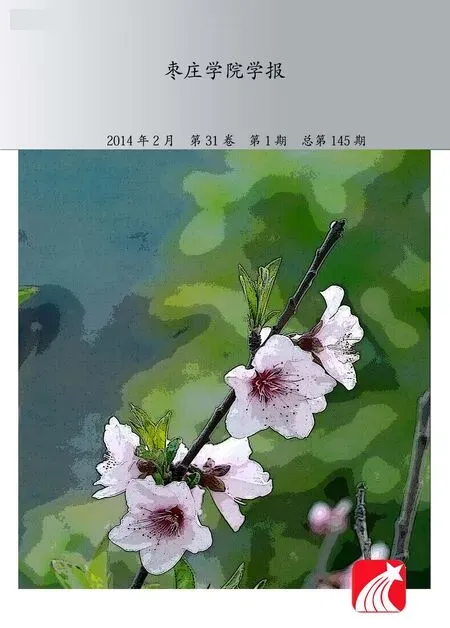飞廉之死考
2014-02-05张志祥李祖敏
张志祥,李祖敏
(1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2黄岛区博物馆,山东 青岛 266400)
一、引言
飞廉,也作蜚廉,是秦族的祖先。关于飞廉之死,有两种记载。《孟子·滕文公下》云:
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史记·秦本纪》云:
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林剑鸣、何光岳、白国红等先生均指出《孟子》与《史记》所记飞廉之事不同,如林剑鸣先生云两者“记载稍异”[1](P18)。何光岳先生云:“《孟子》言‘飞廉戮于海阳’,而此(《史记》)言天赐(飞廉)石棺以葬于霍太山,妄也。”[2](P99)白国红先生云:“有人质疑,飞廉之国在山西境内,与被‘驱于海隅而戮之’的说法相乖舛,因此,将这一材料弃而不取。其实,既然周公能率军长途跋涉去平叛,那么飞廉率本国之师东进与反周之师相会合又有什么奇怪呢。”[3](P101)但其均没有对飞廉之死做进一步研讨论证,都是一笔带过。《孟子》和《史记》中关于飞廉之死的记载截然不同,加之飞廉所在年代的久远,至今已成为谜团。幸而近年整理的清华简中也有飞廉之死的相关记载,我们再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对飞廉之死作一简要考证,推测《史记·秦本纪》所载飞廉之事与史实不合。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予以斧正。
二、结合《系年》证《孟子》的可信性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三章云:(文字依宽式读法,古文字均读作相应的今字)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彔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先,世作周卫。[4](P141)
清华简《系年》云成王杀飞廉于东方,《孟子》云周公杀飞廉于东方。其实不论是成王、抑或周公,可以肯定的是:飞廉在周公摄政时期被杀于东方。《孟子》与清华简《系年》均成书于战国时期,《史记》成书于汉代,按照古史流传的基本常识,前者的可信性是高于后者的。
《史记》之后的书册中也有飞廉之死的相关记载,如:《辽史·卷九九》云:“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七》云:“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全辽文·卷十一》云:“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辽史》和《续资治通鉴》等著作的作者均可以看到《孟子》和《史记》中关于飞廉之死的记载,但是他们选择了《孟子》的说法。他们为什么不采纳《史记》的说法?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孟子》成书年代比《史记》早;二是《孟子》所载比《史记》更加合于逻辑。我们认为这些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会平白无故地采用《孟子》的说法,而舍弃史学巨匠司马迁的说法。按,谯周认为司马迁所记飞廉之事“事盖非实,谯周深所不信”(《史记索隐》)。何光岳先生云:“《孟子》言‘飞廉戮于海阳’,而此(《史记》)言天赐(飞廉)石棺以葬于霍太山,妄也。”[2](P99)白国红先生云:“有人质疑,飞廉之国在山西境内,与被‘驱于海隅而戮之’的说法相乖舛,因此,将这一材料弃而不取。其实,既然周公能率军长途跋涉去平叛,那么飞廉率本国之师东进与反周之师相会合又有什么奇怪呢。”[3](P101)谯周先生认为《史记》所记飞廉之死“事盖非实”, 《辽史》和《续资治通鉴》等著作的作者直接舍去《史记》的说法,何光岳先生认为《史记》所记飞廉之死“妄也”,白国红先生认为飞廉之国在山西境内,与被“驱于海隅而戮之”的说法并不矛盾。以上不难看出古今学者均认为《孟子》所记飞廉之事的可信性高于《秦本纪》。
三、从商周军事实力对比证《孟子》的可信性
飞廉是纣王宠幸的幸臣。如《荀子·儒效》云:“(纣)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荀子·解蔽》云:“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尉缭子·武议》云:“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飞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市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武经总要·后集卷十三》云:“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全梁文·卷五十七》云:“辛受生而飞廉进。”《册府元龟·卷七百十三》云:“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六》引《尸子》云:“飞廉、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太平广记·卷一三五》云:“纣之昏乱,欲杀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于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与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四书章句集注》云:“奄,东方之国,助纣为虐者也。飞廉,纣幸臣也。五十国,皆纣党虐民者也。”《王安石集·卷七十》云:“桀、纣之世,飞廉进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
飞廉是纣王的“知政”宠臣,权倾朝野。武王克商时杀死了纣王和飞廉的儿子恶来,丧君之痛和丧子之痛深深地鞭打着“力角犀兕,勇搏熊虎”的飞廉,飞廉怎肯躲在霍太山偷度余生呢?况且当时小邦周的军事实力并非能够超过商纣王,相反,其时小邦周的军事实力相差纣王甚远。《史记·周本纪》云:“(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一年》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须知纣王伐东夷,军力外出,即使武王发兵时纣王的军队已然回朝,想必亦是受到东夷的损耗。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纣王依然可以集结“七十万人距武王”,无疑说明纣王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周武王。此外,《逸周书·大开武》云:“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逸周书·小开武》云:“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命。”《逸周书·寤儆》云:“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从《逸周书》这些记载来看,周伐商的消息泄露,令武王“忧其深矣”。武王对于小邦周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攻克大殷商,并没有信心,以至于“夙夜忌商”,“今朕寤有商惊予”。以上不难说明周武王时小邦周所具有的军事实力远远达不到压倒商军之势。
所以,飞廉从心底里对周是十分痛恨和蔑视的,痛恨是因为赋予自己极大权力的君王和自己的爱子被周武王所杀,蔑视是因为周人的军事实力并不是特别强大,反周复仇并不是没有可能。据此,从情理上推断,飞廉绝不会在纣王和恶来被杀后一个人默默地躲在霍太山。纣王既然重用飞廉,说明飞廉必有过人的政治本领,否则飞廉早被“暴君”纣王杀了,正所谓伴君如伴虎,自古已然。飞廉在商末也是风云叱咤的人物,作为纣王炙手可热的权臣,有极强的号召力。飞廉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加之东方各国对周也是持仇视态度,至于武王克商后飞廉东逃,联络东方各国反周,东方各国群起反周就更加自然。武王一日克商,而周公三年苦战才打败东方各国,也从侧面印证了小邦周的军事实力并不是特别雄厚,所以飞廉和东方各国打心眼里并不惧怕周,东方各国有勇气也有实力反周。东方各国要团结一致,必需一个德高望重,有极强号召力的人统筹,除了飞廉,还有谁可以担此重任?正如武王去世时,周公毅然摄政一样,因为当时成王的威望根本不足以敷政天下。自古成王败寇,周公伐东胜利时,必是飞廉被杀日。综上,飞廉被周公或成王杀之于东方,才合乎史实或者更加接近史实。
四、结语
结合近年整理的清华简《系年》,从时间顺序上《孟子》和《系年》均早于《史记》,且前二者关于飞廉之死的记载近同。从后人对史料的甄别判定来看,谯周不信《史记》的说法,《辽史》和《续资治通鉴》的作者均采纳了《孟子》所记飞廉之事,何光岳先生认为《史记》所记飞廉之死“妄也”,白国红先生认为飞廉之国在山西境内,与被“驱于海隅而戮之”的说法并不矛盾。说明古今学者亦认同《孟子》所记飞廉之事的合理性。我们再从情理上来看,周武王杀了纣王和恶来,飞廉是纣王的股肱之臣,恶来是飞廉的爱子;此外,其时小邦周的军事实力并不是多么强大,加之东方各国对周亦持敌视态度,飞廉身负国仇家恨,以其声望和号召力联络东方各国,与周公东征军大战三年,最后兵败被杀于东方,这才合乎历史的真实。
[1]林剑鸣.秦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3]何光岳.先秦的来源和迁徙[J].船山学刊,1994,(2).
[4]白国红.飞廉考[J].学术月刊,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