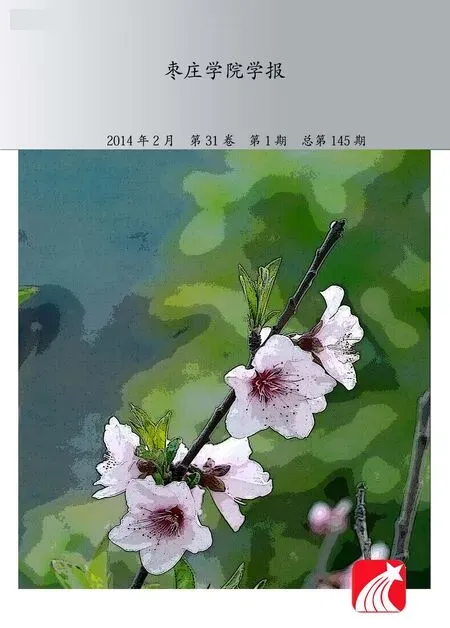开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新思路
——评张伯存、卢衍鹏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
2014-02-05赵立春
赵立春
(临沂卫校,山东 临沂 27600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和变动为文学提供了新的语境,文学也因此发生质的变化,这就要求必须以新的范式和思路来进行研究。在政治方面,政治不再直接干预文学艺术领域,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进行影响,文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价值规律影响了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在社会方面,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加速了社会转型,文学发展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文化方面,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再加上文化全球化、文化产业等文化潮流的推动下,“文化转向”成为影响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和文学发展现状,张伯存教授申请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批准号:08BZW060),于2012年顺利通过鉴定。现在,由张伯存、卢衍鹏合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正式出版,它试图通过“外层解读——内层解读”相结合的学术思路,来客观地探究文学的内在特质和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1](P10)。因此,这就决定了该著作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考察既不是纯粹美学、文学和艺术层面的学术研究,也不是脱离文学本身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层面的泛化研究,而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的方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观念的创新与人文精神的彰显
文学研究首先要确立文学观,《研究》将文学放在“历史化”和“总体性”的理论视野,文学观念的创新为文学研究的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对文学的全面认识,《研究》能够在新的立场和视角上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进行考察,包括资本、市场、传媒、现代化、全球化、消费文化等都成为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文学的价值立场、思维方式等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应对九十年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研究者的重大挑战。《研究》立足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从多角度解释文学创造、现象与社会思潮等复杂关系[2](P7),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工程,也是当前文学研究的难点,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和理论素养才能完成。《研究》通过对诸种文学观念的比较与甄别,寻找出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文学与外在因素的嫁接和融合,涉及到一定时期文学状况的总体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国社会整体面貌的判断。
文学观念的革新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倡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新思维和想象力,甚至是一种“野性思维”。具体而言,《研究》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理论与方法,还尝试运用阿尔都塞式的“症候阅读”方法,找出文本与社会的内在关系,深挖文本的内在结构、意识形态和叙事策略等深层机制。不仅如此,《研究》还注重意识形态的美学效应,以及文学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形成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格局。这种研究不仅是多种方法和视野的累加,而是层层深入的揭示,不同的理论视野各有自己的优势,能够针对文学的不同问题,让不同方法之间产生化学反应,让理论创新在聚焦中得以实现。《研究》告诉人们,文学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之前很多看似是背景性的因素,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成了实体性的内容,这不仅是文学研究内容的扩展,更是研究理念和思路的革新。
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要对人的思想和精神有敏感而准确的把握,《研究》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了专门论述,厘清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状况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为分析和评价文学创造打下了思想基础。发生在二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这是研究该时期文学不能回避的话题,从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和分化。《研究》从回顾“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入手,认为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剧变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震惊”体验,随之而来的是非常深的精神困惑和迷茫,“人文精神讨论”成为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标志[1](P17)。《研究》强调精神问题与文学的关联性,希望为合理的制度提供相应的精神上的根据和支撑,文学就是能够滋养人性、激发想象力、安妥灵魂的精神创造,文学能够促进精神健全社会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站在了人类精神和社会革新的高度来研究文学,这种理论构想其实回归了“文学是人学”的宗旨,文学研究就是要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和思想状况,这种理论高度为《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是一种大境界。
二、总体性的独到眼光与历史辩证的创新方法
文学观念的创新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研究》以“总体性”的独到眼光和历史辩证的创新方法考察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方方面面,尤其重视对意识、欲望、精神等核心问题的开掘,凸显了文学的精神价值和终极关怀的意义。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于研究文学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创造性地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中,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观点。首先,选取典型文本进行总体考察,将文学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能够发现文学的总体性价值。总体性的独到眼光可以发现原来被忽视的文学价值,这些发现是单纯的文学角度所不能实现的。《研究》从社会转型角度考察了王朔现象[1](P118)。其次,抓住生产机制进行整体考察,将文学生产作为社会机制的有机部分,能够发现文学各个因素的内在关系。《研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出发,突出了九十年代文学生产转变的来由,进而也凸显了文学体制的重要性。正是梳理了“总体性”的文学生产机制,《研究》全面概括了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生产主体、运转机制、评价机制等各个环节,内容涵盖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文学生产的“总体性”原则。具体而言,在文化语境上,主要是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文学生产的关联;在生产主体上,主要是写作者的分化和知识分子的选择;在运转机制上,主要是体制改革、品牌生产和出版主导;在评价机制上,主要是传媒策略、娱乐精神和文学导购。最后,深入把握文学与媒介的张力关系,将文学、意识形态和现代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来,强调其中的个人尊严、公正诉求和文学消费。可以说,“总体性”是《研究》的重要特色,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得出了很多新的认识。
历史辩证的创新方法建立在文学观念的创新基础上,同时也是“总体性”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研究》以历史辩证的创新方法分析了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嬗变,包括文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新市民小说、日常生活与新写实小说、私人生活与私人化写作等方面。历史辩证的创新方法能够更为全面、客观地认清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等多个方面,不仅是文学存在的语境,而且是文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与诸因素之间相互渗透、嫁接,能够产生新的文学因素和社会思想和文化形式。在分析文学如何表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研究》以“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为中心,分析了其产生语境、深层原因,通过外在的历史考察和“深描”(Thick Description)[1](P2)的本文分析,总结出文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多重关系。在分析市场经济与新市民小说方面,《研究》以“理论旅行”的视角分析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想象特质,认为这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文学的现代性文化诉求,文学想象建构出审美的文学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与新写实小说的考察中,《研究》指出了日常生活在历代文学的流变与地位,说明新写实小说赋予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日常生活具有意识形态性。在私人生活与私人性写作的考察中,《研究》综合分析了公共生活、文学自律和私人性写作的关系,指出了私人性写作蕴涵了性别政治、欲望症候、文化隐喻和合法性困境。可以看出,历史辩证的创新方法为《研究》提供了全面、多元的理论工具,能够深入挖掘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关联,得出历史的、美学的论断。
三、文学的“文化研究”与文本意识的坚守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被广泛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格局。在专著《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中的男性气质》中,张伯存深入考察了1950年后的文学、杂志、电影、电视等媒介所建构的男性气质,以及与民族、国家、历史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运用的方法和理论也都体现出作者跨学科的学术追求,具有较强的深度和难度。《研究》同样采取了跨学科、“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同样注重文学的文化阐释,更加重视“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因此能够重新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做出独到的阐释。
文学的“文化研究”不仅是方法和视野的扩展,更是理念和思维的革新,《研究》从多层面、多角度对文学进行文化阐释,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现实的指导意义。针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热”,《研究》考察了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张中行的“学者散文”和“小女人散文”等三种典型的样式,以点带面地进行了深入的文化阐释并指出了其文化局限。同样是文学的文化阐释,《研究》从宏阔的文化视野对张承志的《心灵史》进行了解读,首先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切入作家的心灵秘史,然后从历史意识分析中融入心灵形象,最后从信仰精神角度指出其儒家文化之外的异质建构。可见,只要真正以文学为中心,只要真正理解文化,文学的“文化研究”确实能够扩展文学研究的思路和视域。
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文学和文本,文本意识对文学研究而言至关重要,《研究》虽然运用了多种方法,但始终坚持以文本为依据,凸显了强烈的文本意识。无论是对“人文精神讨论”、传媒、市场经济、欲望等分析,还是对王朔现象、新市民小说、新写实小说、私人性写作等文学现象的分析,都以文本和作品为中心,并且能够根据文本的特点寻找合理的研究方法,建立合适的理论框架。具体以欲望的书写为例,《研究》从欲望的多义入手,以作品和文本分析为基础分析情爱叙事的嬗变,考察欲望的异化和悖论[2],从未离开本文和形象的分析,这就让跨学科分析更具感性体验。可见,“文化研究”的文本意识避免了脱离文学本身的危险,能够让文学在复杂、多元的“文化”分析中回归人学和自我。
总之,《研究》从文学观念、研究方法、理论模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以新的理论建构和文本阐释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做出了准确、独到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范式和新的思路,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1]张伯存,卢衍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2]卢衍鹏.论1990年代中国文学中欲望叙事的多义、异化与悖论[J].文艺争鸣,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