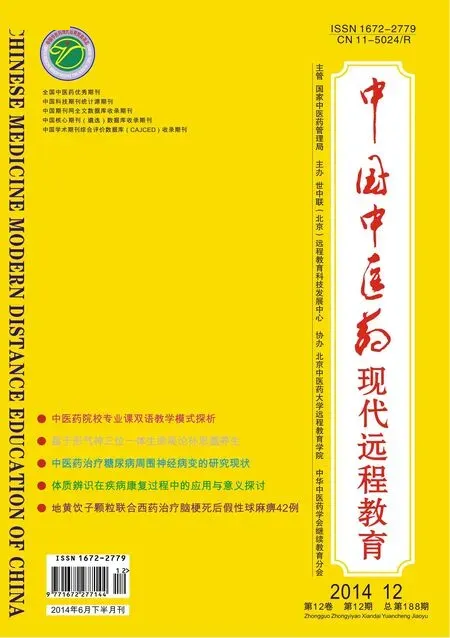疏肝健脾法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研究概况
2014-02-05范剑薇
范剑薇
(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桂林 541001)
疏肝健脾法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研究概况
范剑薇
(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桂林 541001)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疏肝健脾;泄泻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 是指一组包括有排便习惯改变、粪便性状异常、腹痛及腹胀等临床表现的症候群,属胃肠功能性疾病。罗马Ⅲ亚型分类标准将其分为腹泻型(IBS-D)、便秘型(IBS-C)、混合型(IBS-M)及不定型(IBS-U)[1]。临床以腹泻型IBS(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D)较为多见,为公认的中医药治疗的优势病种。目前从肝脾辨证IBS-D己成为比较趋同的认识[2],肝郁脾虚为IBS-D主要的中医学病理机制,可解释50~60%的临床证候。中医药以疏肝健脾法治疗IBS-D突显疗效,现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根据IBS-D的临床表现,当属中医学“泄泻”、“腹痛、“郁证”等范畴。本病除主症大便次数增多、粪质稀烂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症状为腹痛、泻后痛减,并伴有精神紧张焦虑、神疲乏力、腹胀不适等症。其发生主要与饮食不节,素体脾虚、情志失调,外感时邪等因素有关,肝郁脾虚是发病的基本病机[3-4]。肝郁克土可致脾虚,或素体脾胃虚弱,肝木又会反侮,最终都形成肝郁脾虚共存的现象。如《医方考》所云:“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肝责之实,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肝气横逆,克脾犯胃则可见腹痛,脾气虚弱则现泄泻[5]。《知医必辨》言“肝气一动,即乘脾土,作痛作胀,甚者作泻”。《景岳全书》指出:“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必先怒时挟食致伤脾胃,但有所犯即随触而发,此肝脾二脏之病也,盖以肝木克土,脾胃受伤而然”。
路正志[6]认为本病的发生均与情志变化关系密切,过度思虑劳累紧张等可导致脾虚,而精神因素刺激或平素性情抑郁又可导致肝气郁结,肝气横逆则腹痛,脾气虚则泄泻。汪红兵等[7]通过对360例IBS-D患者进行辨证,发现IBS-D的证候分布以肝郁脾虚证为最多,占44.7%。结果也显示情志不畅、精神紧张和饮食不节是IBS-D的诱因。同时也说明了中医“肝郁”与“脾虚”在IBS-D发病中的重要地位。现代医学研究显示[8-9]肝脾不调的病理观点和IBS患者脑肠轴功能紊乱学说之间可能存在密切关联,神经肽Y(neuropeptide Y ,NPY)作为一种脑肠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的肝郁,NPY基因可能是中医和西医对于本病认识共同和客观的物质基础。
2 临床研究
2.1 药物治疗 黄绍刚等[10-11]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对疏肝健脾中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患者进行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结果发现疏肝健脾法治疗IBS-D有效,能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并结合药理研究发现,自拟的疏肝健脾肠激灵方对IBS的作用可能是通过降低内脏高敏感性来改善患者腹痛、腹胀、腹泻等临床症状。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12]认为肝郁脾虚是IBS-D的病机关键,治疗上应抑肝扶脾,标本兼顾。善于使用羌活、防风、升麻、柴胡、独活、葛根之类风药,兼以平肝。冯文林等[13]认为痛泻要方与逍遥散都适用于肝脾不调之腹泻。两方皆有“白术-白芍”药对,二药相使配伍共奏调肝和脾之功效。并认为系统分析“白术-白芍”药对与5-羟色胺信号系统的相关性能够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对于开发新药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新月教授[14]认为本病肝郁脾虚为基本病机,以疏肝健脾为治疗大法,同时兼用风药,调养心神。聂惠民教授[15]认为本病在治疗上应着眼于肝脾,以抑木扶土、疏肝健脾法为基本治法。陶琳等[16]认为中药健脾疏肝法不仅改善IBS-D肝郁脾虚证临床症状,还能持久提高其生活质量,并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疗效更加显著。孙洁[17]自拟健脾疏肝汤(柴胡、枳壳、白芍、白术、茯苓、半夏、陈皮、郁金等)口服并保留灌肠治疗IBS-D疗效满意,可改善患者体质,减少复发。李国霞等[18]自拟调和肝脾方(柴胡、香附、枳壳、白芍、木香、防风、白术、陈皮、茯苓、炮姜、乌梅等)治疗IBS-D疗效满意,认为其机制可能是抑制了某些亢进的体液免疫指标,增强了细胞免疫功能,从而起到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
2.2 针灸治疗 IBS被认为是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一种,针灸治疗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调节肠道运动过强或过弱反应。在改善IBS症状方面有不错的效果。孙建华等[19-21]拟疏肝健脾针法治疗IBS-D,选取天枢、上巨虚、足三里、三阴交、太冲、百会、印堂为主穴。研究结果提示疏肝健脾针可有效降低患者腹痛、腹泻、腹胀等症状的发作程度和频率,明显缓解患者伴随的排便不尽感,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有明显的提高。裴丽霞等[22]运用针灸治疗腹泻型IBS 肝郁脾虚证,取穴:天枢(双)、足三里(双)、上巨虚(双)、 三阴交(双)、太冲(双)、百会、印堂,治疗总有效率达90.0%。通过对该证型的针对性研究肯定了针灸治疗该病证的疗效,同时表明针灸治疗该病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对腹部不适、排便习惯和心神的整体调节上,而不是单一症状的控制。
3 实验研究
3.1 痛泻要方实验研究 IBS-D的基本病机是肝郁脾虚,也是最常见的临床证型,疏肝健脾法在治疗本病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而痛泻要方的临床运用及作用机制研究也成为近年的热点。钱锋、张涛等研究[23-24]认为痛泻要方可能通过调节内脏敏感性阈值而发挥缓解脾虚肝郁型大鼠IBS症状的效应。具体可能通过减少肥大细胞脱颗粒,降低大鼠血清5-HT及血浆SP含量,增加血浆、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含量等。李冬华等[25]研究发现痛泻要方可降低IBS模型大鼠不同脑区核团c-fos 蛋白表达,进而调节肠道功能亢进,说明痛泻要方对IBS大鼠的脑肠轴功能紊乱有调控作用
3.2 自拟方实验研究 张声生等[26-31]自拟疏肝健脾方(党参、白术、八月札、白芍、陈皮、防风等),通过对IBS-D模型大鼠的研究,揭示疏肝健脾方可以改善大鼠的腹泻及内脏的高敏感性,其作用可能是通过调节结肠5-羟色胺(5-HT)及其受体,减弱神经元兴奋性、提高内脏痛阈、消除肠道敏感而达到的;并对大鼠血浆中胆囊收缩(CCK)及生长抑素(SS)有调节作用;同时揭示多巴胺(DA)可引起D-IBS模型大鼠结肠黏膜吸收活动增强,疏肝健脾方能通过发挥与其对大鼠结肠黏膜多巴胺通路相关的Cl-及HCO3-转运的调节作用有关,这一过程主要由结肠黏膜顶膜侧Cl-通道,基底膜侧阴离子交换体及Na+-K+-2C1-共转运体等膜通道蛋白共同介导。从军等[32]以疏肝健脾法自拟肠吉泰,研究发现此方对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肝郁脾虚证模型大鼠具有改善应激状态、调节肠动力、解除内脏高敏感性等治疗作用。推测肠吉泰通过调节大鼠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P物质(SP)mRNA表达及结肠SP mRNA表达,改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肝郁脾虚证模型大鼠对束缚应激反应导致肠动力的紊乱,改善内脏痛觉敏感状态。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医药在治疗IBS-D上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本病病位在肠腑,与肝脾关系最为密切,肝郁气滞,横逆乘脾,脾失健运致肠腑功能失调,故临床上肝郁脾虚型患者颇多,大多采取疏肝健脾治法,有效方剂多用痛泻要方等加减。针灸多选脾经、胃经、肝经穴位以调肝理气、健脾止泻,同时结合现代医学从分子、基因水平进一步揭示其相关机理。但目前中医药研究IBS-D领域仍应注意:⑴IBS-D病情复杂,需发挥中医整体观的特点,在疏肝健脾基础上进行规范的随证加减;⑵ IBS-D患者临床普遍存在多层面情绪障碍,总是表现出对胃肠道过度关注与担心。因此在中医药治疗过程中如果能运用恰当的心理疗法对患者进行必要的认知干预将是非常必要的。
[1]Drossman DA.RomeIII:The Functional Gastrointertinal Disorders [M].3rd Edition.Mclean :M clean Degnon Associates inc.2006:557-593.
[2]黄绍刚.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肝脾辨证体系构建的思路与方法[C].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十二届全国脾胃病学术交流会,2010:479-481.
[3]中华医学会脾胃病分会.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诊疗共识意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7):1062-1065.
[4]李德锋,徐陆周,周晓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病机治则探析[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14(5):104-106.
[5]窦志芳,张俊龙,阎川慧,等.肠易激综合征与肝脾相关性探讨[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1,18(12):91-92.
[6]苏凤哲.论情志与脾胃二——路志正教授学术思想探讨[J].中医临床研究,2010,2(3):1-4.
[7]汪红兵,张声生,李振华,等.360例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主要证候分布与不同因素关系的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0,17(3):18-20.
[8]黄绍刚.肝脾失调在IBS内脏高敏感性发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7):530-532.
[9]房财富,唐洪梅,廖小红,等.肠激安胶囊对IBS-D模型大鼠脑肠轴中NPY mRNA表达及ACTH含量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33(7):948-952.
[10]黄绍刚,张海燕.疏肝健脾法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随机对照试验的Meta分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80-81.
[11]黄绍刚,黎颖婷.中药复方肠激灵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随机对照临床研究[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0(2):152-156.
[12]陆为民,徐丹华,周晓波,等.徐景藩教授论治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经验「J].江苏中医药,2012,44(11):1-3.
[13]冯文林,伍海涛.“白术一白芍”药对与5-HT信号系统相关性的研究思路探讨「J].时珍国医国药,2012,23(4):990-991.
[14]刘果,王新月.王新月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经验[J].中医杂志,2010,(01):23-24.
[15]路广林,张秋霞,郭华.聂惠民教授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经验[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09):637-638.
[16]陶琳,张声生,肖旸,等.健脾疏肝法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2012,31(6):437-439.
[17]孙洁.疏肝健脾汤口服并保留灌肠治疗肠易激综合征[J].陕西中医,2011,32(1):8-9.
[18]李国霞,宁志芬,李经秀,等.调和肝脾法对肠易激综合征免疫学作用机制研究[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1,17(3):317-319.
[19]Sun jianhua,Wu xiaoliang,Xia chen,et al.Clinical Evaluation of Soothing Can and Invigorating Pi Acupuncture Treatrment on Dianhea-predomina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J].Chin J IntegrMed,2011,17(10):780-785.
[20]占道伟,孙建华,徐陆周,等.疏肝健脾针法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穴位机制研究[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4):583-586.
[21]李浩,裴丽霞,周俊灵.针刺与西药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疗效对照观察[J].中国针灸,2012,32(8):679-682.
[22]裴丽霞,孙建华,夏晨,等.针灸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肝郁脾虚证临床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1):27-29.
[23]钱锋,卜平.痛泻要方干预大鼠肠易激综合征肝郁脾虚证的作用及机制[J].苏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30(6):1179-1181,1238.
[24]张涛,潘峰,徐建军.痛泻要方干预脾虚肝郁型大鼠肠易激综合征的实验研究[J].中成药,2011,33(4):687-689.
[25]李冬华,白霞,谢小磊,等.从脑肠互动的角度研究痛泻要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作用机制[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0,16(12):118-121.
[26]张声生,汪正芳,郭前坤,等.疏肝健脾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5-择色胺相关的结肠黏膜上皮分泌功能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12):3092-3095.
[27]汪正芳,郭前坤,张声生.疏肝健脾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血浆及结肠组织5-HT,SP,VIP的影响[J].天津中医药,2012,29(5):459-462.
[28]张声生,郭前坤,汪正芳,等.疏肝健脾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模型大鼠结肠黏膜多巴胺信号通路离子转运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12,20(9):385-389.
[29]汪正芳,郭前坤,张声生,等.疏肝健脾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结肠粘膜5-羟色胺及其受体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2013,32(6):406-409.
[30]张声生,郭前坤,汪正芳,等.疏肝健脾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多巴胺信号通路结肠黏膜吸收功能的影响[J].天津中医药,2013,3(9):546-549.
[31]郭前坤,汪正芳,张声生,等.疏肝健脾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血浆胆囊收缩素及生长抑素含量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2012,31(10):776-779.
[32]丛军,蔡淦,林江,等.肠吉泰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 CRH SPm RNA表达的影响[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3,47(5):81-84.
10.3969/j.issn.1672-2779.2014.12.105
1672-2779(2014)-12-0157-03
杰 本文校对:江 伟
2013-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