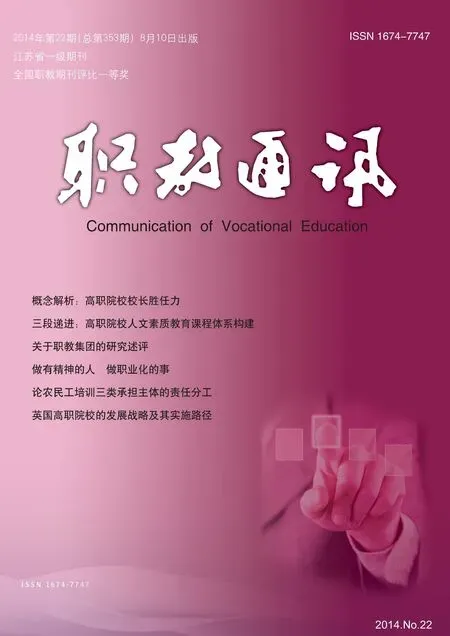对话理查德·德斯贾丁斯教授
——全球化视野中职业教育研究的定位、方法与蓝图
2014-02-05汤霓
汤 霓
理查德·德斯贾丁斯(Richard Desjardins)教授,加拿大出生。经济学硕士,国际比较教育和经济学双料博士。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系。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终身教育体系、经济学、教育与技能政治经济学等方面。对中国的终身学习、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等领域也有着浓厚兴趣。
与理查德·德斯贾丁斯教授的第一次见面经历非常具有戏剧性。在同学的推荐下我顺利地获得了旁听他的课程的机会。虽然我屡屡听旁人说起这位教授是多么的博学,但从未见过真容。怀着一份敬仰之情,第一节课我早早来到教室,静候教授的到来。十几分钟后,一位身材高瘦、面容俊秀、发丝硬朗的帅气“型男”走进了教室,直接坐到了教室后排,我想这应该是和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这时,另一位同学开始起身向他介绍我。而我的目光一直跟随在他身上,完全没听进我同学在说什么,便开始径直向这位“型男”说起我是来听某某教授的课。劈里啪啦说一堆之后,他无奈地打断我,说道:“对,我就是这堂课的教授”。顿时,在场同学哄堂大笑,我窘迫地赶紧掩面。这才知道原来这位年轻的“型男”不是学生,而是教授。
就是这样一位教授,从他身上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多元的气质。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不仅仅只有一种文化背景,甚至不仅仅使用一种语言。得知他去年九月份刚从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来到UCLA任教,我即刻对他多元的工作经历产生了兴趣。而事实确实是,理查德·德斯贾丁斯教授(以下简称理查德)本身丰富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国际化的气质,也为他的教育研究工作提供了的全球化的视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他分享了他关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的定位、方法与蓝图的看法。
一、职业教育研究的定位
笔者:除了英语以外,你还能使用法语、瑞典语和丹麦语,能谈谈你的语言学习经历吗?
理查德:我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母语为法语。7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英语。26岁时开始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国际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住了10年,所以可以说我也是一个瑞典人。我的妻子说瑞典语,她来自芬兰,所以在家我妻子跟孩子们说瑞典语,而我跟孩子们说法语,这确实是多语种的家庭。瑞典语是我的第三语言,和丹麦语很接近,在芬兰也有一部分人说瑞典语。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角度来看,北欧国家,比如瑞典、挪威、丹麦、芬兰,他们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成人教育体系,这是非常有用的。瑞典语可以帮助我了解、阅读和学习整个欧洲发达的成人教育体系,并在那里进行交流。
笔者:语言学习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不是非常重要?
理查德:我觉得这有利于去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视角。世界上不止一种语言,而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欧洲人这方面很厉害,有很多语言,很多文化,地理位置也相近。在欧洲做社会科学研究,非常令人兴奋。因为这就像是一个实验室,有着非常多元的文化和语言可以去比较。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也非常有趣,可以看看不同的统治方式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是如何相互接近的。所以这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好的。
笔者:能否谈谈你为什么要读两个博士学位?
理查德:我具有经济学的背景,本科和硕士都是经济学背景。我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国际比较教育学,我深谙经济学、教育学,特别是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但是,这和经济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开始在社会学、政治学方面扩大了我的专业领域。但是,和经济学家合著与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想要在经济学学术领域去发表文章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所以我决定再拿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样你就可以和更大范围的学术团体、不同研究兴趣的学者们去交流了。不同的学术团体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试图通过对话把他们联系起来,努力将经济和教育相联系。
笔者:你觉得将教育学和经济学相联系起来容易吗?如果从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角度来看,是如何将它们联系起来的?
理查德:不容易,但是我的志向是将三个领域联系起来:比较教育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我希望能基于比较教育学将这三者联系起来,将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应用到比较教育学中去。而我擅长教育和技能的政治经济学,更远的来说是成人教育,更广义来说是终身教育。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成人教育体系,这是关于成人教育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这是试图将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教育学和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联系起来。
笔者: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吗?
理查德:每个领域在过去的10-15年当中都有所成长,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在政治学,技能科学这些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着非常不同的文献,在比较经济学也是如此。我试图做的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将他们引入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研究团体中来,这是我的贡献所在。
笔者:你对你的研究定位或者领域有什么期望吗?
理查德:我的志向是为政策分析提供一种视角,以此来更好地提供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机构,更好地管理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系,在体系本质方面做更好的研究,提高政策决策者们的可行性。研究兴趣在于国际比较视野下职成教体系的教育机构、管理和资金方面。
二、职业教育研究的方法
笔者:你在OECD和在UCLA的工作经历有什么不同吗?
理查德:在我去OECD以前,我是丹麦奥胡斯大学的一名副教授,我在那待了5年,然后去OECD待了三年,现在我又回到了学术界。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和在巴黎OECD的工作,或者是在这里的,都非常相似,三者我都会做相关的研究或项目的管理,但是在学术界我还会上课,而这在OECD是不会做的。
在过去的17年中,我在OECD做的项目都是关于成人技能测量的。从90年代开始,第一个项目叫做国际成人读写能力调查(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简称为IALS)。1997年,在我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后我就开始做这个项目了。当时我作为政府公务员在加拿大统计局工作。从那时我开始和OECD合作,因为那是OECD和加拿大统计局的合作项目。当我去瑞典之后,我在那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已经有第二代了,叫做成人读写能力、生活技能调查(Adult Literacy and Lifeskills Survey,简称为ALL)。而第三代就是最新的国际成人能力测验(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简称为PIAAC),它是差不多20年工作后的结果。
这些项目,IALS, ALL和PIAAC,都是大规模大样本的调查测验项目。超过20个不同国家参与进来,非常庞大的队伍。我被安排进了国际组,来指导不同的国家团队,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一项目。但是我的专长是回过头来进行分析,我需要准备好数据和数据集,来分析不同的有趣的数据,作图并提前将结果发送给政策制定者们,以此做政策分析。所以在PIAA项目中我是主要的报告撰写人,这一报告去年10月出版,这就是我在OECD去年的工作。我准备了所有的PIAAC数据库,所有PIAAC的相关产品,和撰写报告,是和不同的小组成员合作一起完成的。
笔者:你认为当前这种大样本的调查对于职业教育或者成人教育研究非常重要吗?
理查德:是的,我认为一般的社会调查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政策角度来记录经济社会条件以及社会团体的分布。但我不认为这能回答政策决策者们从统计结果中发现的问题。大样本调查不会教你应该怎么做,只是教你看到社会中不同的情况,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或者部分政策导致的不同结果。但是这种调查成本非常高,政策决策者们需要为这种调查买单,他们通常是唯一的支付方。我不认为社会调查,或者社会科学研究能提供答案。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调查是帮助形成问题,提出正确的问题,并提供信息来让人们争论;或者是提供一些可选的观点,来影响决策。政策决策者们非常希望获得答案,我不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能提供解答,这不是社科研究的工作所在。
笔者: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定量和定性研究的?
理查德:两者都非常重要。我不喜欢像许多经济学家那样,用定量研究来看因果关系或者效应。我不相信单一的因果关系,我觉得世界太复杂了,各因素都处在一个互动的、充满活力的环境下。我通常使用定量数据只是用来看统计出来的不同形式或结果,从而来产生问题。而这些数据需要进一步分析处理,比如定性分析,案例研究。所以我相信要混合用不同的方法,两者结合起来。最好是能将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将他们视为研究过程的循环步骤。而我喜欢用定量方法来产生问题,以此开发更好的数据采集项目。
三、职业教育研究的蓝图
笔者:PIAAC目前还没在中国开展,你认为它可以被引进中国吗?
理查德:我们试图这么做。当我还在OECD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官方会议。PIAAC和PISA类似,OECD和中国政府也有协商。中国参与了PISA,但是非常受限,只有上海和香港、台湾地区参与。PIAAC并不是只调查一个省,时间上至少也需要一年。我知道中国政府可能会决定再次参与,但是他们将要考虑这一项目涉及到的农村人口。中国非常大,我不认为中国有许多社会调查。我试图寻找过数据来做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是些行政数据。目前,据我了解,中国也没有劳动力的调查,而这是所有OECD国家的标准调查,比如在欧洲、北美。我不认为社会调查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我不一定准确,但是中国特别大,而这些社会调查成本又非常高。这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政府要考虑到其关联性的时候。
笔者:那你认为中国要引进PIAAC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理查德:其中之一是政治承诺的资源,然后才能去实际操作,因为成本非常高。我不太确定在中国是否有家庭调查的文化,这会是统计专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有没有家庭调查,有什么以往的经验,有没有可行性。考虑到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多样性,先做人口和户口抽样调查是有可能的。所以对于我来说,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在这些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笔者:目前中国在国际教育研究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理查德:非常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是G20的成员国之一,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格局,也想了解更多国家的情况和数据。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被考虑的国家,同样还有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OECD想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数据,将OECD国家和中国进行比较。所以,OECD有很大的兴趣去做这件事,OECD的不同部门也与中国官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试图来看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提供数据,比如在《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glance)中,中国政府就提供了相关数据。而这一做法是为了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尽可能收集中国的数据。
而我是做比较教育的,在做比较教育的时候,拓展到职业教育和成人学习领域,如果能将中国包括进来会非常好。这有助于我理解中国正在开展的东西,包括政策、观念的形成等。到底只是关注公司的企业培训?还是包括了更广泛的学习元素?我认为欧洲所界定的成人教育和学习和中国的定义是不同的,我想中国成人教育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和文化,但是许多欧洲国家成人教育所考虑的范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合适的,比如为了发展国家经济的政策需要。但是中国成人教育更多是从文化、社区的角度来考虑的。我想在欧洲,成人教育这两个方面都会考虑,成人教育一方面是和经济相关,另外,也是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两者相联系的实现,不能将两者分开来。我对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没有太多了解,但是去了解中国是如何接近这一成人教育观念的是非常有趣的。只是关注制造部门或许多新兴服务业部门的成人职业教育机会?还是会涵盖更广的范围,将各种各样学习轨道的路径相连?广义上来说,这是非常整体的终身学习的观念,将经济、社会、文化相联系起来。
笔者: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想要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话,你认为有什么优势吗?
理查德:由于我关注政策借鉴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能有许多相关研究和分析是非常有用的。中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其社会的流动性,不同人的不同路径,以及他们的前景和未来,还有不同路径之间的联接,等等,这都需要很多研究。如果中国做好了,那么在政策学习方面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很多借鉴的,也很有价值。
笔者: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研究在欧洲似乎要更加普遍一些,而在美国却不是,该如何借鉴美国的职业教育呢?
理查德:是的,可能是这样,一般来说”职业教育与培训”在美国要相当薄弱。成人教育是更加广义的概念,职业教育是成人教育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二次教育机会”,“夜校”、“社区学院”、“成人教育机会”等,我想这些研究在美国都非常发达。“二次教育机会”是那些成人返回学校的能力,进入大学或者社区学院。在美国,职业教育在中等技能开发方面并不是很发达,但是在专业继续教育方面非常发达。医生、医学领域都有终身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但是被叫做继续教育,这方面做的很好。而中国职业教育的定义可能会不一样,有的在基础能力范围,或者是面向读写能力水平较低的人群。当然在美国也有这样的项目,但是职业教育的定义或者叫法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