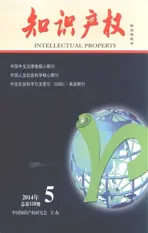晚清著作权立法:权利保护与工具主义的博弈
2014-02-03陈凯
陈 凯
晚清著作权立法:权利保护与工具主义的博弈
陈 凯
晚清著作权立法主要包括1903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著作权互保条款》和1910年出台的《大清著作权律》。这两个法律文件从实质上讲是著作权保护与工具主义博弈的产物:晚清政府为外国著作提供有限保护的主要目的是收回领事裁判权;《大清著作权律》在为国内著作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有控制言论、加强统治的目的。同时,法律移植与本土化关系也是伴随在晚清著作权立法中需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商约谈判 《大清著作权律》 利益 法律移植
1910年12月18日,晚清政府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作为“晚清新政”a“晚清新政”,通常指从1901年慈禧太后颁布变法诏书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晚清政府实行的包括官制改革、修订法律、预备立宪等一系列变革旧体制的政治、法律活动。之一,它的颁布实施对中国著作权立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围绕这部著作权立法的动因,学者的观点见仁见智。例如,有学者指出“迄今为止,没有历史证据证明有自然法上的理由促成了这部法律的形成。相反,许多证据表明,这部法律是一部在紧迫的政治改革压力背景下制定的制定法,其立法动因完全是在于功利主义的因素。”b董 皓 :《 自然权 利的实现还 是功利 主义 的立法 :从历 史角 度看中 国版 权法的 哲学基 础》 ,载刘 春田 主编《 中国著 作权 法律百 年论坛文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1~82页。也有研究成果强调外来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中国近代版权保护制度完全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c周林:《中国版权史研究的几条线索》,载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Ⅷ页。甚至认为“它(《大清著作权律》)绝对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自然生成,而是非理性时期的非自然结果”,d翟志宏:《有关清末著作权的两个问题》,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90页。是“枪口下的法律”。e为凸显“外来因素”对中国近代著作权保护制度产生的影响,李雨峰将近代著作权法称之为“枪口下的法律”。参见: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近代中国版权法的产生》,载《北大法律评论》(2004)第6卷第1辑,第144~166页。也有学者“因循马克思唯物史观之经济决定论,以及恩格斯晚年所阐发的历史合力论或者意志合力论”,认为“外在因素的作用力虽不容否认,赋予其决定性作用力之地位却缺乏理论与事实基础。《大清著作权律》的颁行是多元化社会因素合力推进的结果,尽管诸因素的作用力大小有别,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却应该且只能是内在因素。”f王清:《〈大清著作权律〉的奠基石:晚清版权立法的前期实践》,载刘春田主编:《中国著作权法律百年论坛文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422页。这些观点针锋相对,对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价《著作权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的是,《大清著作权律》虽然制定出来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否具备了制定《著作权律》的条件?在众多的原因中,是内在原因,还是外在因素成为促成晚清政府制定《著作权律》的决定性动力?以及作为制定者的晚清政府又是以何种态度看待《著作权律》?
一、问题的提出:权利的萌生与著作权律的制定
(一)著作权的萌生
著作权,一般而言,是指作为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著作权保护制度,以郑成思和安守廉教授为代表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g相关论述可参见郑成思:《中外印刷出版与版权概念的沿革》,载《版权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3~114页。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梁治平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6~338页及注释#8。本文认为,唐宋至明清曾出现过的特许出版权制度,例如,南宋时一些书籍印有申请官府颁发“不许复版”的榜文或公据的版记,h以南宋光宗时王称所撰《东都事略》一书所载版记为例,该版记为:“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此外,南宋理宗淳佑年间贡士罗樾刻印的《丛桂毛诗集解》一书载有宋朝国子监颁发的禁止翻板公据,南宋嘉熙二年祝穆刊印的《方舆胜览》一书载有禁止翻刻的官府榜文。其重点保护的是刻书者(书坊)的印刷特权,而非作者的著作权。“‘不许复版’特许令状的主要受益者是出版者。而作者权益仅受到间接的保护。从权利主张的内容来看,出版者考虑的多是印书之利,而创作者更为专注的似为文章之誉。……而未涉及作者的财产利益。……在封建中国,作者却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最终成为这种知识财产权利的享有者。”i吴汉东:《关于中国著作权法观念的历史思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3期,第46~47页。
虽然古代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自宋代起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图书市场,但商品经济的停滞和私有观念的阙如构成了古代中国未能创制出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根本原因。除商品经济因素外,传统的儒家文化伦理道德——重义耻利、文章不为稻粮谋——也严重影响着作者著作权保护观念的产生。通过“立言”获得美誉、得到肯定和传诵,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创作动机;“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利善之美德”是古代文人的价值追求。在这样的文化理念下,没有作者会将自己的精神产品与经济价值相联系,更枉论催生出作品财产化、知识商品化的观念。当书商为了垄断出版利益,积极寻求行政庇护,打击“翻版”时,却往往打出维护作品完整和作者声誉的旗号:作者“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嗜利翻版”书籍“窜易首尾,增损音义”,j国子监颁发禁止翻版《丛桂毛诗集解》公据。转引自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从不言明经济利益。作为书商、“翻版”者利益之源的作品,其财产属性和商品价值被有意无意地遮掩起来,而最该受到保护的作者的财产利益被严重忽略了。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较早在中国宣传和倡导西方的著作权思想和著作权保护制度。思想的启蒙使人们的著作权观念开始有所变化,但是,直至晚清制定《著作权律》,这种变化仅局限于知识精英,广大百姓的观念一如既往。
近代著作权保护意识的萌芽和深化,还与传统知识分子向新型职业化文人的转变有很密切的联系。作为“晚清新政”之一,科举制于1905年被废止。以此为界,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路被切断。迫于生计,许多文人转入他途,其中不少人进入到著作界、报界或出版界,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以卖文为生的职业著作家群体。为求生存,他们不得不走出耻于言利的藩蓠,积极主张自己的著作财产权利。以严复为代表的新型职业文人的疾呼呐喊是晚清著作权立法的重要理论酝酿和舆论准备。
然而,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开始形成职业文人至1910年制定出《大清著作权律》,毕竟时间过短,在既有的文化观念和现实条件下,制定著作权法的时机其实并没有成熟,那么晚清政府又为什么要仓促制定《大清著作权律》?其动机何在?
(二)《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
中国著作权立法开端于清末,是晚清变法修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一个突兀孤零的历史事件。近代以降,中国社会与法律制度遭遇“数千年未变之大变局”,晚清王朝面临着外患频生、内乱叠起的困境。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欧美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各种经济、政治特权,更以“中国法制不健全”为由强行干预中国司法,窃取领事裁判权,社会各界视之奇耻大辱。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重拾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以度时艰。1902年5月13日,清政府颁布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k《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九八。1902年9月(光绪28年8月),中英两国在上海续议的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中特别规定:“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l《通商各国条约·英国条约·英国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二款》。在此后与美、日等国修订的商约中,也将类似条款纳入其中。无论列强的允诺出于何意,清政府由此看到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希望。
在续议商约谈判中,以美、日为代表的列强要求清政府增订著作权保护的相关条款,并希望中国加入国际著作权保护公约组织。从1902年到1903年,中美、中日在著作权领域的谈判围绕是否给予外国人著作权保护,以及著作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期限等方面展开。经过近两年的谈判,其间产生过多个草案,最终于1903年获得批准,并互换约本,著作权保护条款生效。m中美、中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关于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基本相同。以中美双方最后签约的版权条款为例,其内容如下:“第十一款 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之利益给予该国之人民。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十年。以注册之日为始,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除以上所指明各书籍、地图等件不准照样翻印外,其余均不得享此版权之利益。又彼此言明,不论美国人所著何项书籍、地图,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凡美国人民或中国人民为书籍、报纸等件之主笔或业主、或发售之人,如各该件有碍中国治安者,不得以此款邀免,应各按律例惩办。”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下,英国等许多国家“利益均沾”,符合条件的著作都自动地在中国获得类似的保护。清政府虽然未能完全阻止美日两国将著作权保护条款写入商约,但较之美日“意在概禁译印”的初衷,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此外,在《中日通商行船续约》第5款中规定:“中国国家允定一章程,……中国国家允设立注册局、所,凡外国商牌并印书之权,请由中国国家保护者,须遵照将来中国所定之保护商牌及印书之权各章程在该局、所注册。……”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政治愿望和商约条款的规定最终促使清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关于著作权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
1904年1月,清政府新成立的商部组织人员翻译外国著作权法,正式启动著作权法的制定工作。1905年,商部拟出著作权律初稿。其后不久,学部成立,专司教育和文化事业,著作权律初稿随即移交学部进行修订。1907年民政部成立后,又接手继续办理著作权律的修订。在此期间,清政府陆续制定出与著作权法密切相关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等新闻出版法。1910年,民政部在参酌比较西方各国著作权法的基础上,终于拟具出《大清著作权律草案》55条,在咨送宪政编查馆复核后,请旨交资政院议决。经过数次决议和修改,1910年12月18日(宣统2年11月),历经7年酝酿、起草、议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正式颁布施行。由于直至清帝宣告退位,大清民律的修定仍在草案阶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民法子部门之一的《大清著作权律》,是规定私人权利正当性与合法性前所未有的破天荒创举。
二、问题的实质:权利保护与工具主义的博弈
如前所述,虽然著作权保护观念的萌生,有识之士的呼吁、出版实践的需求对《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立法起主导作用的毕竟是晚清政府。那么,晚清政府对著作权法的认识、定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客观评价《著作权律》就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著作权立法本应以保护作者对著作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为第一要义,但作为晚清政府,无论是与美、日进行保护著作权的商约谈判,还是制定《著作权律》,其最大的目的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n《清史稿·刑法志》记载“自此而议律者,乃群指意于领事裁判权。”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其《寄簃文存一·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更是对变法修律满怀期望,“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是一种政治需求,而并非完全是对著作权法律本身的认同。
(一)续议商约谈判中权利保护与工具主义的博弈
在续议商约谈判中,“最令中国谈判人员迷惑不解的是列强竟然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与热情”。o李雨峰:《近代中国版权的产生》,载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71页。谈判人员这一态度,充分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在谈判过程中,举国上下几乎一致反对著作权互保。中方谈判人员也逐渐认识到保护外国著作权对中国弊多利少,会导致因书价提高而使穷人买不起书。诚如当时所论“国际间所订条约,必以交换权利为原则,今我国既少著作物销流外国,未必得外国保护版权之益,倘加入同盟,是但有义务,毫无权利,外既违反国际间平等之原理,内又阻碍教育及工商业之生机。从此各国援利益均沾之例,将至凡为外国人之著作,概不得翻印翻译,损权利,阻教育,莫此为甚。”p上海书业商会:《请拒绝参加万国版权同盟呈》,载上海《新闻报》1920年12月8日。因此,拒绝同意著作权保护条款。但是,迫于美、日的强硬态度,作为弱势一方的晚清政府又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考虑到:平心而论,外国人“自译印其著之书,本人费许多心血,若使其书一出,即为他翻印,亦恐阻人著译。既欲广开民智,无论中外人特著一书及自译自印者,应准注册专利若干年,则新书日出,方免遏绝新机。”q吕海寰、盛宣怀:《吕盛两钦使复电》,载《政艺丛书·皇朝外交政史》第4卷,上海政艺通报社1902年版,第11~12页。转引自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即在一定条件下保护外国人的著作权可以激励外国人为中国著书,服务中国。再者,实践中已有对外国人作品保护的先例,正如吕、盛两钦使所言:“专为我中国特著之书,先已自译及自印售者,不得翻印,即我‘翻刻必究’之意,上海道厅领事衙门早有成案,势难不准。”r同注释q 。即使按照遵循先例的原则,也难以完全拒绝。因此,依当时之情势,同意对外国著作给予有限的保护。
经过近两年的谈判,中美、中日续议商约最终达成著作权互保协议,将受保护的著作权限于“专备为中国人所用的作品”。同时还特别强调,“除所指明各书籍、地图等件不得照样翻印外,其余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这样,美、日能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出乎缔约者想象的减少了。
关于外国人著作权保护的问题,1905年清政府商部拟定出的版权律草案规定:如果外国律例能够保护中国人的著作权,那么该国人的著作在中国也准遵例呈报注册,获得著作权保护。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的张元济认为该条大有流弊,如此规定等于在实质上突破了续议商约中关于版权保护的条款,扩大了外国著作权保护范围,对中国的科学、教育进步十分不利。惟有抱定“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与美国签定的商约中规定),“特为中国备用”(与日本签定的商约中规定),将著作权保护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才能避免发生大的障碍。s参见吉少甫:《中国最早的版权制度(下)》,载《出版工作》1989年第3期,第117页。民政部拟定《著作权律》时采纳了张元济的意见,回避了对外国人著作权保护的问题。从《著作权律》颁布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涉外著作权纠纷案件,比如“美国经恩公司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迈尔通史》案”和“美国米林公司控告商务印书馆译印《韦氏大学字典》案”,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最终胜诉,原因就在于这些案件的判决依据无一例外,都只适用了续议商约中关于著作权保护的条款,而没有援用清政府的《著作权律》。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近代中国虽然颁布了著作权国内立法,但该法律所保护的只是本国著作者,外国著作者不能依此法律要求保护。由于利益受损,签约后不久,美方便屡次要求重新订立商约,希望能够扩大著作权的保护范围。
中西著作权的国际保护之争,实质上是中西利益之争。从商约谈判,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各界反对著作权互保的理由主要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的考量——振兴教育。而晚清政府在内外利益的权衡中面临着两难选择的窘境:按理应保,于势又不能保,而政治诱惑和外交压力的双重作用,使得晚清政府最终同意有限制的著作权互保。在这一权衡中,晚清政府将著作权保护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和工具,意在收回领事裁判权,至于外国作者的著作权利益应否保护,却并非是重点考虑的问题。将本属于私法领域的著作权保护作为一种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来使用,这正是晚清著作权保护的悲剧所在。
(二)《著作权律》中权利保护与工具主义的博弈
“利益的分化导致法的产生”,并“决定着法及其发展。”t孙国华:《论法与利益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38页。迫于内外压力,晚清政府制定了《大清著作权律》。鉴于历史上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以资参照,因此,清政府在制定《著作权律》时,比较注意对外国著作权法的研究和选择。从《民政部为拟具著作权律草案理由事致资政院稿》中所提及的国家看,民政部在拟定著作权律时,至少参照了日本、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的著作权法。这部《著作权律》包括通则、权利期间、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5章,共55条,对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保护的对象、著作物的范围、著作权人的权利与义务、著作权的期限、著作权的注册与管理、著作权的合理限制、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法律责任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大清著作权律》虽然是比较国外著作权法的结果,但从内容上看并非照录所参考的国外著作权法,在某些方面亦有所变通,反映出立法者力求在尊重现有观念的前提下,依据社会需要和具体国情来建构本国的著作权制度,以期适应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的良好愿望。比如,《著作权律》第1条“解释著作权含义并界定著作物范围”u《大清著作权律》第1条:凡成著作物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曰著作权。称著作物者,文艺、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皆是。,民政部在拟定理由中写道:“本条为揭明著作权定义,良以今日人民法律思想尚属幼稚,义意不明,每启误解,故将著作权内容和盘托出,以资易于适用,且范围采用广大主义,不特文艺之著作物加保护,即美术物亦列于保护之中。盖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类,与文艺同为精神劳力之产物,文艺既加保护,美术固不可不加保护也。按美利坚、匈牙利等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者于著作物有重制及发行之权利,然发行权利本包含于重制之中,不重制即不能发行,无待辩也。美、匈等国既言重制,又言发行,是重复之规定矣。故本条采德意志、比利时立法主义,仅规定重制之权。”v丁进军:《清末修订著作权律史料选载·民政部为拟具著作权律草案理由事致资政院稿》,载《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第46页。从第1条及拟定理由,可以推测出清政府在制定《著作权律》时,着重强调著作权的财产权利。因为,在该律第1条仅提到著作权“专有重制之利益”,即作者通过复制而获得的财产上的利益,而未提到署名、保护作品完整等人身权。此外,努力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也是《著作权律》的特点之一。例如,关于著作权的期限,立法者经过综合比较,“采用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主义,定为著作者终身后,继续至30年。”w同注释v 。在解释著作权期限的作用时,这样写道:“良以规定著作权立法精神,固为保护著作权者利益,仍以不害社会之公益为要也。倘使不特定继续期限,认著作权为其永远之专权,则必将垄断其利益,高腾其价格,使世人不能得其著作之利,是非所以谋学术发达之道。”x同注释 v 。由此可见,晚清立法者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规定著作权期限是为了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仍以不害社会之公益为要”,即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
从总体上讲,这部著作权律吸收了当时国际通行的著作权保护原则和体例。作为国内著作权立法的开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条款上,法律工具主义的色彩依然突出。试举两例予以说明:
第一,著作权律的拟定、颁行从最初的法部移交到学部,最终转归民政部。民政部在《民政部为拟定著作权律清单请旨交议事奏折》中讲得很清楚:“臣部职司警政,首在保卫治安,而高等治安警察之中,尤以集会、结社、新闻、著作数端为最要,所有报律、结社集会律等,业经臣部奏请核定施行,则著作权之专律自当及时拟订。”y丁进军:《清末修订著作权律史料选载·民政部为拟定著作权律清单请旨交议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第47页。著作权法本属私法范畴,然而最终却由主管警政治安的民政部拟定,虽不能完全断定,但制定主体的转变隐隐彰显出清政府对著作权律的理解和定位。对立法者而言,似乎更愿意将《著作权律》界定为维护政治统治的管制之法而非私权保护之法。这种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著作权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初目的。基于同样考虑,《大清著作权律》第2条规定:“凡著作物归民政部注册给照”,第4条规定:“著作物经注册给照者受本律保护”。依此规定,著作物必须经“依法注册”方可获得著作权,并以此作为对著作权权利期间的起算点。z作为当时立法参照的国外著作权法一般采用“创作完成主义”,认为著作权的权利期间应自最初发行之日起算,登记注册只是为了进一步确立权利以对抗第三人,而非取得著作权的必要条件。同时,第30条规定:“凡已注册之著作权,遇有侵损时,准有著作权者向该管审判衙门呈诉。”这等于从诉讼的角度进一步规定了只有经过“依法注册”的著作在受到侵犯后,才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未经注册不受著作权律的保护。将受著作权法律保护的著作物范围严格限定于已经注册的范围之内,反映了晚清政府对著作进行管理、控制的强烈愿望。这样规定虽然这有利于维护公权,却从根本上背离了著作权法是私权之法的主旨。
第二,对翻译作品规定独立的著作权。《大清著作权律》第28条规定:“从外国著作译出华文者,其著作权归译者有之,惟不得禁止他人就原著作另译华文,其译文无甚异同者不在此限。”按照当时国际通行做法,如果要翻译著作物,须经原著作者同意。而依据《大清著作权律》的规定,中国人可径行翻译,不必取得原著作者的同意和授权,并且对所翻译作品享有独立于原作品的著作权。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正是《著作权律》的拟定者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希望通过赋予翻译者独立的著作权,鼓励其多译著作,以达到振兴教育,促进学术进步的目的:“各国于翻译多视为重制之一种方法括之于著作权中,如日本《著作权法》第1条即揭明此义。我国现今科学多恃取资外籍,不能不变通办理,故本条揭明著作权归译者有之。”@7同注释y。秦瑞玠对此条也持相同观点:“我国现今科学多恃取资外籍,正利用翻译之自由,且未加入万国著作权同盟,不为侵害各国著作权中所包含之翻译权,故不必得原著作者之允许,而可任意翻译,且于已译之本,为有法律所许之独立著作权也。”@8秦瑞玠:《著作权律释义》,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32页。
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晚清立法者从来没有单纯地探求著作权保护对作者所具有的原生价值,而是越出“著作权保护”自身去寻找——在他们看来——更根本、更实用的功效:收回领事裁判权,振兴教育,促进学术进步。在内外交困之中,《大清著作权律》保护作者著作权的原生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转换成“为国家强盛提供途径和答案”这样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立法者的这一理念为我们正确评价《大清著作权律》带来了“客观”上的困难。
三、问题的延伸:法律移植的价值
法律移植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9沈宗灵:《论法律移植与比较法学》,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1期,第1页。使接受移植的国家能尽快完善或替代本国有缺陷的法律,或填补某些法律空白。从理论上讲,法律移植的目的和价值在于实现被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而法的“本土化,意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与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0 肖光辉:《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现象的关联考察——兼论我国法的本土化问题》,载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研究——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1页。0由于各国的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基本国情的差别,其“法的精神”也必定有所不同,如果直接移植他国法律,极易水土不服。正如孟德斯鸠所讲:“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1#1[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2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1页。#3 杨维新:《清政府〈著作权律〉探源》,载《版权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0页。但刘春田教授提出相反观点:“这部法律,并非一纸空文,明清档案馆保存的清末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商务印书馆等大量出版物目录的历史资料说明,该法曾被认真有效地实施过。”(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4 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从晚清著作权的立法背景,我们可以看出清末著作权立法并非出于“需求诱发”,而主要是一种“外力推进”。即中国在制定著作权法时,不是因为立法条件成熟,而是因为一个较先进的法律系统对较落后的法律系统的冲击,使得中国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近代著作权立法保护模式。#2#1[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2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1页。#3 杨维新:《清政府〈著作权律〉探源》,载《版权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0页。但刘春田教授提出相反观点:“这部法律,并非一纸空文,明清档案馆保存的清末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商务印书馆等大量出版物目录的历史资料说明,该法曾被认真有效地实施过。”(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4 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由于外力的强力推进和被动接受,中国的著作权制度被很快地建构起来,但是保护著作权的观念却不能完成于朝夕之间,依然处于传统样态。即使如严复那样积极争取著作权利的作者,其主张保护著作权的理由也基本上离不开国家、社会的利益,极少从作者权利的角度论证著作权保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由于受到传统的制约,观念的进化和变迁是非常缓慢的。而在社会变革时期,观念的进化和变迁却极为快速,清末著作权立法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然而即使这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从本国需求出发,在大众现有观念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这样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例如,有学者“遍查清政府专司著作权注册事务的民政部注册局档案,并未见到一件呈报注册的文件”。#3#1[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2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1页。#3 杨维新:《清政府〈著作权律〉探源》,载《版权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0页。但刘春田教授提出相反观点:“这部法律,并非一纸空文,明清档案馆保存的清末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商务印书馆等大量出版物目录的历史资料说明,该法曾被认真有效地实施过。”(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4 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对这一事实,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但《著作权律》从颁布到为公众所知悉,进而摆脱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潜在影响,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绝非一蹴而就。可见,法律文本的近代化,并没有带来法律精神的契合:剽窃抄袭、盗版翻印依然盛行,屡禁难止,许多作者、出版者既是被侵权对象又是侵权主体。
法律移植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系统工程,只有依赖于人们长期而持续的探索和思考,经过本土化的历程,从“条文——法律理论——价值观念”都转变了,移植才是成功的。而晚清著作权立法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晚清政府变法修律的直接动因,并非改良法律,而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修律目的的异化,导致立法者急功近利,许多立法,包括《著作权律》,都没有能够成功完成域外法律移植的本土化问题。“这种不顾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片面追求移植西方法律,使得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脱离本土,脱离真实的社会生活,缺乏民族个性的弊病,即使清朝不是覆亡在即,有些新法也难免会成为具文。”#4#1[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2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1页。#3 杨维新:《清政府〈著作权律〉探源》,载《版权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0页。但刘春田教授提出相反观点:“这部法律,并非一纸空文,明清档案馆保存的清末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商务印书馆等大量出版物目录的历史资料说明,该法曾被认真有效地实施过。”(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4 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尽管商约谈判中的著作权互保从动机到观念都是著作权利保护之外的,法律工具主义贯穿其中,尽管《大清著作权律》只是晚清政府“变法修律”的举措,仅是一种法律“文本”的存在形式,但是在民间社会,一般的百姓未必真能明白和体会其中的法律意义。即使这样,法律“文本”的存在,毕竟也意味着官方业已承认著作权以“权利”为基础的价值理念。法律移植可以影响立法,立法可以改变观念。无论《大清著作权律》还有怎样的缺陷和不足,便在一定时期内舶来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将是复杂和剧烈的,它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壮举。因此,应该坚信:由于外力推进而制定的著作权制度,虽然在当时超越了国情、民情,但却启迪了人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重要的“法教”作用,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如果能够规范运作,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影响、改变大众的行为模式,改变制度与观念的脱节状态,最终促生与之相适应的法权观念。从这个角度分析,晚清著作权立法意义重大。
晚清政府十年变法修律,被迫开始,匆匆结束,法律在“仓促间”现代化了。然而世易时移,回顾清末著作权立法,包括民国时期的著作权立法,留给后人无尽思考。当今天我们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懈努力时,更深刻地体会到如何更好地吸收、借鉴域外法,在进行法律移植的同时“不废讲读中律之功”,依然是法律学人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
The copyright legisl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reciprocal clauses which concluded and signed by Qing dynasty with foreign invaders in 1903 and the 1910 Copyright Law of Qing dynasty. In fact, these two legal documents were the gambling results betwee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instrumentalism. For example, the main purpose of providing limited protection for foreign works is to withdraw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What's more, the Copyright Law of Qing dynasty can provide protection for domestic works as well as control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reinforce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plantation of law and its localization is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which need to be properly settled in the copyright legisl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mmercial negotiation; Copyright Law of Qing dynasty; interest; transplantation of law
陈凯,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