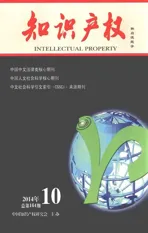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正义考量
2014-02-03向波
向 波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正义考量
向 波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在知识利益冲突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并随着知识利益冲突的变化而向前发展。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知识利益冲突各方必然会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规则设计进行讨价还价,以尽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主张反映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规则当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义考量,我们可以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和社会效果两个角度来加以评价。之所以会采取财产权制度的方式来应对知识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相关利益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社会效果,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类型的知识利益冲突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规则的社会效果展开具体的比较分析。
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 正义
关于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我们可以根据劳动财产权理论、人格理论或功利主义思想等给出一定的说明。但是,囿于上述理论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皆不能有力阐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根据。劳动财产权理论与人格理论实际上只论证了单方主体——即创造者——利益主张的合道德性,但是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协调来自于不同利益主体如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的利益主张,而非只考虑创造者一方的利益主张。这种情形显然已超出了劳动财产权理论和人格理论的说明范围,也显示出古典自然权利思想在应对当代社会日益复杂的利益格局时的局限性。a笔者曾经将知识产权正当性问题划分为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有关利益主体的利益主张是否必然要通过财产权的方式来加以保护;第二,在确定通过财产权的方式来保护有关利益主体的利益主张时,这种财产权在有关利益主体当中应如何分配;第三,在确定初步的赋权规则以后,此种财产权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及其结构是怎样的”。实际上,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传统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的阐述范围。参见向波:《关于“比较优势”的赋权理论》,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9期。随着功利主义思想的兴起,学者们便试图通过功利主义来论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根据。但由于功利主义相关结论的不可验证性,功利主义在阐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根据时同样一筹莫展。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来看,由于牵涉到多方主体的利益主张,立法者也只能尽量秉持客观中立与利益平衡的态度来构建具体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规则,我们更需要在制度的层面上来说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根据。
一、非正式制度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社会基础
关于制度,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b[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等2008年版,第3页。而奈特则认为,“社会制度是一套套的规则,这些规则以特定的方式构建社会互动。这些规则:1.提供关于预期人们在某种情形下如何行动的信息。2.能够被相关群体的成员辨认其他人在这些情况下遵守的规则。3.构成行为人产生均衡结果的策略选择。”c[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一般而言,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如法律,需要依赖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确保社会成员遵守这些规则;后者如道德、习俗等,它主要是以自我实施的方式发挥作用,没有外部权威能够保证社会成员遵守这些制度规则。
从社会制度的产生与变迁过程来看,社会制度是利益冲突的产物。d[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利益冲突各方往往基于自己的立场来理性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制度规则,以图获得相较于他方的分配优势,作为结果的社会制度就可以看成是利益冲突的产物。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非正式制度在形成社会行为人的预期方面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非正式制度还会影响正式制度的实施效果。“非正式规则是构建正式规则的基础;非正式规则可以限定正式制度构建的可行方案的数目;非正式规则不随改变正式制度的尝试而改变。最重要的是,非正式规则影响资源的分配,进而影响正式制度创建过程中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e[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就此而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在基于“知识”(如作品、技术发明、商标等)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下简称为知识利益冲突)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的,并随着知识利益冲突的变化而向前发展。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优势,知识利益冲突各方必然采取各种策略方式使得自己的利益主张能够在形成的制度中得到更多的反映,比如通过正当化话语来对自己的利益主张进行合道德性证明,以此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国家的承认,并与其他的道德观念展开公开争辩。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伊始,相关利益主体就是透过自然法思想如劳动财产权理论、人格理论等来正当化基于“知识”而提出的利益主张。比如在英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形成时期,部分英国商人试图通过财产权制度继续维持自己的利益分配地位,他们从创造者如作者、发明人的创造性劳动或者说创造行为出发来为这种财产权制度进行正当化的论证。而这种正当化论证的目的在于通过获得社会认同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奠定相应的道德基础。由于道德依靠自我实施机制来约束社会行为人,这种实施机制显然不足以维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而通过法律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知识利益冲突各方必然会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规则设计讨价还价,以尽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主张反映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规则当中。当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时,它将与通过正当化方式形成的道德基础共同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在西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其社会基础的形成、发展历史脉络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对于我国而言,由于我国是以移植的方式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我们虽然制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财产权利意识的缺乏f有学者考察了传统中国民事法,认为中国民众实际上并不缺乏“财产权利”意识,但由于“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官方法律理念与国家提供的司法服务均普遍缺乏对财产权利最基本的尊重”,便表现出传统中国民事法中“财产权利的贫困”状态。参见邓建鹏:《财产权利的贫困——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所建立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先天不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没有得到我国本土主流道德观念的支持。当然,随着财产权利意识的逐渐加强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缺乏相应社会基础这一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但是对于我国知识产权研究者而言,我们需要把握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西方诸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形成与发展历史上的这一重要差别,并在这一前提之下展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本土化研究。
二、理性选择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
制度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同时又确定了各方主体关于社会利益分配的基本模式。但是,由于利益冲突中各方实力上的诸多差别,主要反映强势主体利益主张的制度实际上就可能成为当时社会不公平现象的直接根源。而关于制度的正义思考就是源于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批判反思的结果。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义考量,我们可以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社会效果两个角度来加以评价。而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来进行正义考量,罗尔斯所构建的正义理论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罗尔斯把正义考量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试图在摒弃各种社会偶然性的基础上通过公平协商的方式来达成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g美国学者罗伯特·诺奇克认为罗尔斯正义思想是一种模式化的利益分配理论,并不符合社会现实。诺奇克认为“根本不是这种情况:某种东西已经生产出来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看谁将得到它。东西进入世界的时候已经是属于人们的,他们对这些东西拥有资格。”而且,如果“不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持续的干预,任何最终——状态原则或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都不能得到持续的实现。”参见[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5页。诺奇克在批判罗尔斯“正义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持有正义理论”。但诺奇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完全忽略了在制度形成过程中利益冲突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把权利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去论证制度的正义性,他的所谓“历史的”正义理论完全忽略了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历史过程,也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幻象。罗尔斯认为,正义的“首要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h[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尽管罗尔斯强调社会合作,他也明确意识到社会制度的产生是为了应对现实存在的利益冲突。i罗尔斯认为,“因为为了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协议”。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在批判功利主义正义观和直觉主义正义观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契约论基础上的公平的正义观。在具体分析这种正义观之前,罗尔斯首先假设了一个“原初状态”j原初状态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任意的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做决定的状态。”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页。的环境,其目的是排除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使人们在完全公平的基础上产生正义原则。根据原初状态及其各项条件,罗尔斯推论了其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并详细阐释了使正义原则演化为具体制度的“四个阶段的序列”。k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阶段召开立宪会议,制定保护个人基本自由、良心和思想自由的宪法;第三阶段为立法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发挥作用;第四阶段是“法官和行政官员把制定的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例,而公民们则普遍地遵循这些规范”。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8页。可以看出,罗尔斯的“公平协商”模式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模型构建,而现实中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仍然会受到罗尔斯所谓“偶然因素”的干扰、摆布甚至控制。
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中,知识如作品、专利、商标等在市场贸易中的价值愈加突出,这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对于知识的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则在于知识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出于对知识贸易垄断地位及高额利润的追求,部分商人开始采取各种策略方式来促使有利于自己分配地位的制度规则的形成。他们首先借助于王权的力量来促成相应的制度规则,比如特许出版权制度、特许专利制度以及商标的行会管理制度。通过这些特许权制度,部分商人获得了市场垄断地位,从而获取了高额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特许权制度却限制了其他商人的经营自由,同时也损害到了社会公众的正当利益,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这些以王权为支撑的特许权制度的瓦解。随后,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的商人开始寻求其他策略方式来稳定和维持自己的利益分配地位,而诉诸财产权的途径就成为他们的一种策略选择。从英国1710年《安妮女王法》、1623年《反垄断法》及1824年Sykes v. Sykes一案确立商标的普通法保护规则等发展历史及其内容来看,l详情分别参见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7、132~136、225~228页。这些法律在协调和平衡相关利益冲突时,尽管主要回应了强势商人一方的利益主张,但同时也兼顾了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主张。而之所以会采取财产权制度的方式来应对知识利益冲突,主要是相关利益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规则的最终形式,是相关参与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这个最终形式是以冲突中的行为人的意图和动机为基础的”,m[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其目的是为了获得针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分配优势。而由于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的存在,制度形式一经选择和确立以后就很难加以改变。
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初始并非主要为了保护创造者的利益而出现的。从作者、发明人的角度来论证著作权、专利权的正当性不过是当时商人的策略选择而已。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涉及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但由于力量上的不对等,最终产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更多体现处于强势一方主体的利益主张。罗尔斯的“正义论”给我们的提示就是:为了达至一种利益均衡的状态,在构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各方主体应通过公平协商的方式来确定具体的制度规则,还要将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利益主体的合理主张反映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当中。否则,相应的制度规则也很难得到处于不利地位利益主体的认同和遵守。比如,1603年英国书商行会之所以采取“利益均沾”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印刷专利制度的存在导致从事印刷行业的小商人经营困难,从而激起这部分小商人对原有制度规则的反对乃至以“盗版”的方式加以对抗。n参见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5页。
当代,一个国家的立法部门在法律制度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笔者看来,按照立法部门在立法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将立法模式大致分为“协商型”的立法模式与“参与型”的立法模式。前者是指立法部门并不参与制定相关法律草案的内容,而由利益相关方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确定法律草案内容,立法部门则将由各利益相关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提交的法律草案予以通过即可;o比如美国国会通过《1909年版权法》的立法情形就是非常典型的“服务型”立法模式的体现。详情参见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3页。而后者是指由立法部门来主导相关法律的制定,立法部门不仅仅要投票表决法律草案的通过与否,还要参与制定法律草案的具体内容。无论是“协商型”立法模式还是“参与型”立法模式,都应在综合和平衡利益冲突各方利益主张的基础上来制定相关法律规则。这一问题实际上与民主立法相关,“民主立法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意征集过程,更是一个利益各方在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中进行利益表达、碰撞和协调,进而实现不同利益在立法中得到合理或均衡体现的利益博弈和平衡过程”。p代水平:《我国民主立法制度建设:成就、问题与对策》,载《理论导刊》2013年第2期。从我国的立法过程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立法模式倾向于“参与型”立法模式。在“参与型”立法模式中,一方面立法部门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充分了解和掌握各利益相关方的真实利益主张,让各方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到立法活动当中,并且防止对“不在场”或“沉默”的利益主体合理利益的侵犯;另一方面还需注意防范立法活动的部门利益化倾向,立法部门应处在客观中立的地位来主导整个立法过程。
三、利益冲突类型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社会效果
从社会效果对制度进行考察具有后果主义的特点。q按照印度学者阿 玛蒂亚·森的看法,后果主义“应基于选择者对于事物 状态的评价,包括对所作选择可能带来 的所有相关后果,以及与将要发生的事情相关的全面结果加以考虑”。参见[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实际上,功利主义也具有后果主义的特点,但它仅局限在效用的计算上。而且,由于功利主义相关结论的不可验证性,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功利主义解读是不可靠的。r哈耶克认为,“规则乃是我们对于大多数特定情势所具有的这种不可避免的无知所做的一种应对或调适”,但功利主义恰恰建立在“人是全知全能”这一事实性假设之上,完全忽略了人的“无知”。参见[美]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页。与功利主义有所不同,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关注制度运行下的社会现实,主张从比较的角度选择出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而非理性地思考出“完美的社会制度”。s[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阿玛蒂亚·森并不否认罗尔斯“正义论”在学术上的历史贡献,但他认为,“罗尔斯公正制度的原则并未指明具体的制度,只是提供了用于指导实际制度选择的一些规则”。t[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而且,罗尔斯的“正义论”依然将自由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也不考虑制度运行下的社会现实。u[ 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59页。在此基础上,阿玛蒂亚·森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社会中不同主体所拥有的“整体可行能力”v阿玛蒂亚·森认为可行能力“与实质自由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个人从事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的实际能力就具有核心意义”。可行能力会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个体差异、物理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气候的变化、基于关系视角的差异等。参见[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39页。,从而评价不同主体所拥有的实质自由,由此可以对不同的社会状态进行比较。阿玛蒂亚·森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制度模式或者构建制度的基本原则,而是建议考察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在比较现实的基础上选择出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按照阿玛蒂亚·森的正义理论,制度的进步就在于逐渐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而这可以通过比较现实中存在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
考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市场环境下基于作品、发明、商标等对象而产生的利益冲突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究其实质,这些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各方主体对市场中基于作品、发明、商标等对象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争夺而已。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制度。诚如所言,“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是确认、分配知识的市场化所产生的利益,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是知识成为市场要素的结果,支撑该制度的核心利益诉求不是来自创造者,而是来自以知识为市场要素的产业”。w李琛:《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另外,所谓“公平制度”的形成并不是我们建立制度的最终目的,而是期望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达到一种可欲的社会状态。x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正义的理念》中把这种只关注制度本身而忽略其社会效果的态度称为“某种形式的制度原教旨主义”。参见[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我们需要秉持一种中立的态度来探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下的不公平现象,如此我们就可以在比较现实的基础上选择出更合理的制度规则以缓解或者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对此问题,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类型的的知识利益冲突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规则展开具体的比较分析。从知识利益冲突主体的角度,知识利益冲突可以简单划分为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创造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创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创造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四种类型。y可以看出,基于商标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仅限于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对于商标的使用基本上都是商业意义上的利用行为,而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商标符号的使用已非商标意义上的利用行为。其中,经营者一般是处于知识传播地位的社会组织,他们通过商业性利用知识而获取经济利益,而消费者则通过知识的私人消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一)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就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看,主要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和市场自由竞争的问题。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产生来看,部分经营者想通过市场垄断地位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成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的动因。就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部分经营者垄断市场的目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变革大多是由经营者来主导推动的,而创造者则相对处于辅助的地位,比如影响巨大的《TRIPS协定》的内容主要反映了美国知识产权经营者的利益主张。当然,经营者一般是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间接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但随着社会情势的发展,经营者逐渐将自己的利益主张透过各种策略方式直接反映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规则当中,比如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将职务作品、职务发明的权利直接配置给经营者。z参见《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第16条: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见《专利法》第6条第1款: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而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表面上是因为其违背知识产权设置的目的而受到规制,实际上是由于这类行为会激化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利益冲突双方的利益态势显著失衡而无法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
(二)创造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就创造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看,本质上也属于经济利益之争,而且利益冲突双方力图通过对知识控制力的强化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地位。如果考察一下劳动财产权理论与人格理论各自对于著作权法律制度构建的影响,我们会看出这两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著作权法律制度赋予利益冲突双方各自的知识控制力强弱不一。在劳动财产权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著作权法律制度,经营者可以通过其资本能力和谈判能力获得较为强大的知识控制力,从而获取相对有利的利益分配地位。而人格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其显现的利益分配格局与前者有所差别。鉴于创造者与其创造成果之间的人格联系,著作权法律制度规定了著作人格权制度加以体现。相较于劳动财产权理论,人格理论指导下出现的著作人格权制度赋予创造者更强的知识控制能力,这是由于著作人格权的专属性和不可转让性所决定的。就此而言,人格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著作权法律制度显然更有利于创造者,创造者对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变革拥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
(三)创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创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涉及到创造自由与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由于知识具有一定的传承性,新的创造成果总是在前人创造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的创造成果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到前人创造成果的内容,这就产生了新旧知识的创造者之间的创造自由与利益分配的问题。考察一下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有关内容,其中部分规则就在于协调创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关于改编作品,其权利配置往往呈现出多重权利的情形,也就是说原作品的创造者与改编者都能够参与到对改编作品进行利用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当中。相对来说,在改编作品的利益分配规则当中,原作品创造者处于一种较为优先的地位,无论是改编者改编作品,还是改编者或者他人利用改编作品的行为都受到了原作品创造者权利的制约。
(四)创造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关于创造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既涉及到知识本身作为一种利益而显现的利益冲突,同时关涉到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就作品而言,消费者希望能够尽快地、以质优价廉的方式来享用有关作品,而创造者、经营者对于作品传播的控制显然会有碍于消费者需求的充分实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免费获得和消费有关作品,但随着创造者、经营者对于作品网络传播控制的加强,消费者可以免费获得的作品的资源逐渐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对于作品的需求。当然,消费者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或者消费有关作品,但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和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创造者、经营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形通过不同的传播途径来满足相关消费者对于作品的需求,而著作权法律制度也应该促进此目标的实现。比如,就电影作品而言,消费能力较强的消费者可以支付较高的费用去电影院享受高品质的服务,而消费能力较差的消费者或者可以通过电视来享用有关电影作品,或者通过购买、租借电影光碟的方式进行消费,或者通过小额付费的方式在有关视听网站上进行消费,甚或免费获取和消费有关视听作品。
另一方面,对于创造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也会涉及到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消费者利用知识的行为称为私人利用行为,而把创造者、经营者商业利用知识的行为称为商业利用行为。知识产生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用行为,但消费者对于知识的私人利用行为会对创造者、经营者经济利益的分配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次知识传播技术的变革都会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消费者通过新的传播技术可以免费或者以低廉的价格来获取和享用有关知识资源,这种私人利用的行为无形中削弱了对知识进行商业利用的市场,使得创造者、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受到巨大的影响。
结 语
“正义有两个相反相成的侧面:一方面,作为利益交换的规则,正义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命令,正义又是无条件的”。7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所谓正义的条件性,实际上是强调一个社会中所有的行为人都必须遵守共同的正义规范,人们遵守正义规范的前提是其他人也遵守同样的规范。而正义的无条件性则意味着需要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改变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使正义规范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在现代社会,“社会独自承担维护正义的条件性的责任,并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来防止和惩罚非正义行为”;“作为交换,个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社会的正义规范”。8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8~179页。从我国当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我国还处在一个从正义的有条件性转向无条件性的阶段,一方面需要强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则需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培育人们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道德观念。
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摒弃那种仅站在某一方主体的角度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辩护的思想。随着技术的逐渐发展,知识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由此也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带来了诸多挑战。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须应时而变,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义性考量就体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所谓动态,在于社会的发展,在于观念的更迭,在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不断演进。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得出答案,还必须结合社会现实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义考量,一方面是要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根据,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结合社会现实批判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gradually formed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of knowledge, and moved forward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s of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parties of confl ict of interest will inevitably bargain for the rules of legal system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order to refl ect their claims in the rules of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much as possible. As to the consideration on justice of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can evaluate it from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reason why takes th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to cope with the confl icts of interest is mainly the rational choice of the relevant interest parties.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social effects of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can analyze the social effects of the rules of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aratively and specifi cally, combined with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onfl icts of interest of knowled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justice
向波,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学院讲师
本论文系作者主持的2013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TJFX13-003)和南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青年项目(编号:NKQ112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