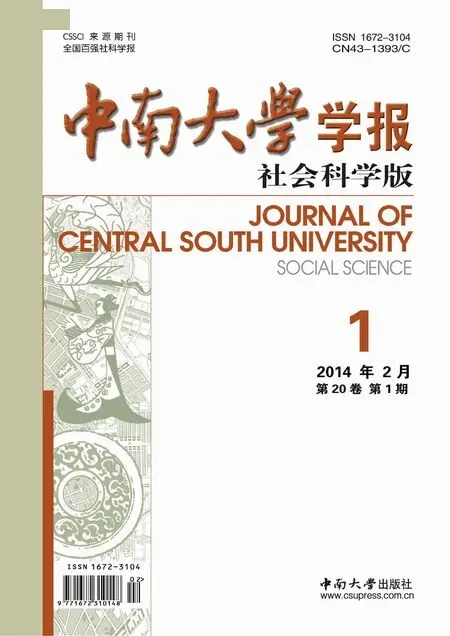文本与历史的交融
——《黑暗的心》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的再现
2014-01-23王霞
王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
——《黑暗的心》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的再现
王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认为文学可以传达历史真实,具有认知功能。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了话语建构,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这表现了康拉德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证明了对于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彰显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
康拉德;文本;历史;新历史主义;《黑暗的心》;非洲形象;殖民创伤
波兰裔英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自问世以来,国内学界从不同的批评角度对《黑暗的心》进行了解读、阐释。比如赖辉从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陌生化”三个方面,对《黑暗的心》的叙事技巧进行了分析[1];姚兰、王颖探讨了《黑暗的心》中黑与白的象征意义[2];徐平阐述了这一作品的反殖民主义主题,认为康拉德揭示了殖民者的掠夺财富和践踏人性的本质[3];吴迪龙、罗鑫则从界定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范畴入手,说明后殖民不是反殖民,《黑暗的心》不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文本[4]。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黑暗的心》的认识和理解。然而,稍感遗憾的是,很少有评论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对这一作品进行阐释。张湛和郑蓉颖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黑暗的心》的主题进行探究,认为该书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分析了康拉德的个人经历对于其创作的影响,指出主人公马洛在非洲的经历,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与康拉德有相同之处[5]。这一观点不乏精辟之处,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但没有全面探讨这一作品如何将文学文本与历史交融在一起,为何文学文本能够再现历史真实、如何再现历史真实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作品进行重新审视,探究康拉德如何通过这一作品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历史话语建构。为此,笔者将主要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基点,运用该理论中“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核心概念,考察《黑暗的心》作为文学文本如何具有历史性、反映历史真实,探讨该作品如何再现19世纪后期殖民主义严酷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
一、历史真实与文学再现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蒙特罗斯(Louis Adian Montrose )曾提出“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主张历史与文本进行互动、对话。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历史著作与文学文本并无本质区别,历史大多数是由文本构成的,历史著作与文学创作都具有虚构性,我们要通过文本才能接近与认识过去的历史,同时历史文本也不断成为更大的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文本的历史性”,是指包括文学文本、社会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和文化性。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语言虚构,类似于文学的语言虚构,同时,历史叙事不是对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照搬和机械的模仿,也不只是记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对原有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提炼的基础上,重新描写事件,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故事。怀特指出,只要历史学家“不能给历史实在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的描述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6](5),同时,史学家还要对故事进行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解释,这是一个诗性构筑的过程。由此,传统的客观的历史叙事便在怀特的理论下轰然瓦解,取而代之以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修辞性、主观性,其强烈的诗性色彩、文学底蕴,更为怀特所关注。怀特认为,历史编纂过程中渗透着史料的选择、语言修辞、情节编织、意识形态等主观建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具有文本性,类似于文学创作。为此,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乔治·伊格斯(George Iggers)将怀特的理论称为“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7]。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打破了传统学科视域下历史与文学之间森严的壁垒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了历史与文学之间互动的对话关系。
19世纪末的非洲历史,是一段黑暗的被殖民被征服的创伤历史,欧洲殖民者将黑人奴隶看作牲口一样的生命,黑人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结婚和受教育的权利。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以自诩文明与进步的立场,将殖民地看作是愚昧、野蛮、落后、未开化的等待被拯救、被开发、被教化的“他者”,启发了殖民者向海外冒险,寻求财富与领土的狂热情绪,也为其对殖民地进行杀戮、占有和剥削提供了理所当然的依据。暴力的殖民征服,往往伴随着文化霸权主义,比如在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先是以武器征服了星期五,接着对星期五进行文化征服,教他语言,用基督教思想去改造他,最终,星期五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更重要是丢弃了自己的种族文化,完全成为殖民者的忠实仆人。在殖民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殖民主义不是侵略,而是拯救,是文明的教化、财富的开拓。这样的殖民话语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身处其中的作家,如与康拉德同时代的吉卜林就承认殖民霸权的合理性,白种人优于其他人种。而康拉德在作品中却讲述了殖民征服的残酷性、破坏性与巨大创伤,反思并质疑了这种殖民行为的正当性。
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以马洛之口批判了殖民暴力的罪恶:殖民者是充满暴力的征服者,只需要拥有残暴的力量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征服比自己弱小的种族,殖民者凭借着暴力与大规模的屠杀去掠夺抢劫、搜刮财富,“他们看到有东西可捞,便把凡能到手的一切全搜刮过来。这不过是一种依靠暴力——加上大规模屠杀——的抢劫,然而人们却盲目地干下去——对那些要去对付黑暗的人来说,却也正应如此”[8](8)。在此,康拉德清晰地指出了殖民者凭借先进的武器对殖民地进行武力征服、暴力屠杀、财富的搜刮与掠夺,而这种殖民暴力并不值得骄傲,更不是一种荣耀。因为所谓对土地的征服与占有,往往只不过是把一片土地从其它种族的人们手中抢夺过来,据为已有,这种强盗式的野蛮行为并不值得赞许。正是在这种残暴的殖民活动中,殖民者获得了土地、财富,并将殖民地变成一个更加黑暗的饱受创伤的地域。
马洛讲述了一个丹麦人向黑人买两只黑母鸡后,觉得自己在交易中受骗了,于是用一根棍子不停地狠狠抽打那个村子的村长。村长的儿子听到老人痛苦的叫喊实在难以忍受,就用长矛扎了丹麦白人。从那以后,全村的村民由于“疯狂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简单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一方面,它显示了自以为文明、体面的白人对于黑人的暴力行为,两者在交易中不是彼此平等、尊重的关系,白人明显优越于黑人,正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使白人能够毫不犹豫地狠狠抽打黑人老人。另一方面,黑人在白人的暴力征服下,开始会胆怯而试探性地反抗,但最终由于对白人的巨大恐惧而逃避、退缩甚至屈从。而黑人对白人的“疯狂的恐惧”,表现了手无寸铁的弱小者对于强大的征服、杀戮者的根深蒂固的畏惧与心理创伤,也从侧面表达了白人在殖民活动中残暴的程度。这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与创伤体验,还存在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那些无辜的犹太男人、女人、小孩的眼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梅·萨塞尔指出:“一个开拓殖民地的民族,一种为殖民主义、为武力辩护的文明是一种病态的文明,一种在道德上患了病的文明。”“欧洲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条死胡同的尽头就是希特勒。”[9](145)康拉德对于殖民主义暴力造成的创伤的再现,表现了他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彰显出对于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以及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
二、文学文本的历史性与殖民创伤
新历史主义反对对文学文本进行内部的封闭研究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批评理念,主张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将文学文本置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去考察和分析。文学文本也具有历史性,能够起到反映历史真实的作用。海登·怀特指出,真实性与文学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可以传达真实,可以揭示真理,具有认知功能。怀特认为,其一,尽管许多文学作品是作家完全虚构、想象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随意虚构的,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情节编织,并非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纯粹虚构。能够传达真理或者历史真实性的,并不是仅有历史,文学常常会更加容易传达某种真理和事实[10](25)。伊格尔顿也认为,从虚构的意义上来定义文学,将文学看成是不真实的、想象性的作品的观点是行不通的。事实与虚构的区分本身就值得怀疑,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小说(novel)一词就同时蕴含着真实与虚构的事件,既不仅仅指向事实,也不仅仅指向虚构,而是两者的融合。因而,“文学不在于虚构性、想象性”[11](2)。也就是说,文学并不等于虚构,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主张客观、冷静、真实地观察和描写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原本面目去精确而真实地再现生活。其二,对于某一个特定时期和地域来说,历史与文学共享的是同一个社会或文化语境,因而历史完全可以联合文学去更好地再现这个社会、文化的意义体系和人文内涵。既然不同学科,不论历史还是文学,都共享着某一个社会或文化所特有的意义生产体系,那么,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再现这个体系,诗性的还是科学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将这个体系的意义和内涵表达清楚。同时,如果能够以通俗的文学手段将社会、文化体系的内涵表达得更生动形象、更具体完备,那么,就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文学含有虚构和想象的因素而排斥它们,而应该充分地肯定文学对传达现实生活意义的独特作用[6](43-45)。
文学的创作、流传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之下的非洲形象及其殖民创伤进行了历史话语建构,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一方面,康拉德表现了对土著黑人原始生命力的认同与赞美,认为划船的黑人与白人一样有骨头,有肌肉,有一股狂野的活力和强烈的活动能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然而真实,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另一方面,康拉德将土著黑人作为未开化的野人,“沙岸、沼泽、森林、野人,——很少有什么可以让一个文明人食用的食品”“他感到自己周围是一片蛮荒,彻头彻尾的蛮荒……在野蛮人的心中活动着的荒野的神秘生命”[8](7)。这些野人生活在地球上的黑暗的区域,需要被文明的欧洲人救赎与教化,马洛的姨母就认为马洛是一个光明使者,要对生活在黑暗地域的人进行文明教化,从而让几百万愚昧无知的人慢慢改掉当地那些可怕的习俗。
在欧洲白人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他者的黑人土著无疑是愚昧、落后的,甚至有食人的恶俗。然而,小说中提到的食人生番并未在马洛面前食人,“当着我的面,我从来也没见他们谁吃过谁”[8](48)。在白人殖民者看来,非洲野蛮部落的黑人根本不可能和欧洲的文明人一样优雅、节制,他们似乎本来就是应该食人的。因而,马洛所雇佣的土著水手没有当着他的面吃人,竟然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没有以撕裂心肝的饥饿的魔鬼的名义抓住我们——他们和我们的比例是三十个对五个——痛痛快快饱餐一顿,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简直无法理解”[8](57)。有学者指出,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否定黑人的文化认同的欲望,往往将黑人建构成丑恶、恐怖、性侵犯、肮脏、愚昧、原始等暴力原型,这剥夺了黑人存在的价值[12]。那么,在白人种族话语体系中,黑人为什么往往被界定成恐怖、粗野、罪恶等否定性的形象?
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曾指出:“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13](123-124)欧洲白人对于土著黑人的贬低、歪曲正是为了言说与彰显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并为此妖魔化黑人,认为他们肮脏、落后、食人。事实上,“进步”“自由”“平等”的欧洲白人正是打着“拯救”的旗号对它所认为的“落后”“野蛮”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实质性的侵略和殖民活动,他们以自身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异己的个人、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观念,否定文化多样性与道德多样性,并将异己文化界定为“野蛮”、“落后”,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 义。有学者认为,“跨文化的道德评价必然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必然会产生投射错误,即把自己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投射到其他种族身上”。因此,“否定普遍伦理、否定伦理原则的普遍价值,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14]。这种理论上的错误与实践上的有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种族主义者将异己的他者界定为野蛮、落后、罪恶、等待拯救的民族、文化,并进而理所当然地进行武力与文化殖民,给被殖民者留下巨大的不可愈合的创伤记忆。
非洲黑人的创伤还体现在话语权的缺失。显然,在白人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中,土著黑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处于失语状态,根本不能言说自己,无法表达与证明自己,而黑人女性更是如此。斯皮瓦克曾把妇女问题作为属下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属下能说话吗?她认为,不论是白人殖民者的表述,还是殖民地父权制捍卫者的表述,都无法听到属于妇女的声音,“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15](125)库尔茨的黑人情妇就代表了当时不能言说自己的被殖民者形象。在马洛看来,库尔茨的黑人情妇显得既野蛮又高贵,眼神既狂野又威严,步态既从容又庄重。然而,自始至终,康拉德都没有让她清晰地言说自己的情感,她最后也只能隔着河流举起手臂,以动作表达自己。与此相应,库尔茨的欧洲未婚妻则被描写成一个高雅、忠诚、和善、朴实、坚守信仰、忍受痛苦的成熟女人,最重要的是,她能用语言尽情地诉说对库尔茨的尊敬、崇拜与爱。无疑,这两个女性形象形成了一种对比。阿契贝认为,康拉德对这两位女性的态度的最大差异在于“授予了其中一位而阻止了另一位使用人类表达方式的权力”[16](453)。
在艺术形式上,《黑暗的心》运用了隐喻、象征的修辞手法,更加深刻地呈现出欧洲白人对于非洲土著黑人的殖民暴力。海登·怀特曾提出,运用文学的语言修辞手法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形象化地呈现真实,从某种程度而言,语言的修辞性不仅是一种形式,也是内容,是真实性的一部分。为此,理查德·汪曾说:“对怀特而言,语言应是历史学家的仆人,而非历史学家是语言的一个例证。”[17]也就是说,语言的形式本身就蕴涵着某些内容,传达着某种意义。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运用了象征的手法,赋予了“黑”与“白”不同的意义。野蛮的非洲土著是黑色的,“黑色的东西在有气无力地活动”“黑色的身躯蹲着,躺着……他们只不过是疾病和饥饿的黑色影子”[8](20, 22)。这些黑人生活在地球上的黑暗的地域,为白人殖民者修建铁路、做苦役,他们满身尘土、肮脏、丑陋、像蚂蚁一样来回移动。在康拉德笔下,这些拥有干瘦的胸脯、无神的眼睛的黑人经常表现出各种痛苦、认命和绝望的姿势,他们如此痛苦、备受折磨,身心满是创伤,甚至连死亡的权利都没有,只有当他们生病了,失去了工作能力,才能获得允许慢慢死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文明人是白色、干净、优雅的,他们穿着一尘不染的淡黄色的羊毛上衣、雪白的裤子,衣领是浆过的,袖口是雪白的,干净整洁,有时还洒上一点香水。从表面上看,黑色是肮脏、野蛮、落后的,白色是干净、高贵、文明的,但事实上,康拉德通过对非洲土著灵魂所蕴含的原始生命活力以及白人残酷的殖民活动、贪婪的掠夺等描写,表现了对野蛮的土著黑人的认可,而所谓文明的欧洲白人的心灵却是肮脏、堕落、黑暗的。可见,象征手法的运用本身就寓示了非洲黑人所承受的巨大创伤。
此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不仅给非洲黑人造成巨大的创伤,还给白人造成了创伤,造成了欧洲殖民者对自我、自我文明的怀疑与失落。有学者指出,文化心理殖民“不仅改变被殖民者的心理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殖民者的精神世界,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都打上心理殖民的创伤烙印”[12]。在《黑暗的心》中,马洛寻访库尔茨的航行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探索与怀疑的过程。马洛孩提时代幻想着宏伟的探险事业,然而,当他看到生活于黑暗腹地的非洲黑人被欧洲殖民者奴役、痛苦、生不如死,看到所谓文明的欧洲人对财富、象牙的贪婪,残暴、勾心斗角、诽谤、卑躬屈膝,他原本的幻想破灭了,并对欧洲的殖民行为进行反思,认为殖民者并没有任何高尚的宗旨与动机,贪婪而野蛮,他们就像半夜撬开保险柜的小偷一样从非洲的大地夺取所有的财富。“我们这些胡乱窜到这里来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能够控制住这无声的荒野吗?还是它将控制住我们?我能感觉到那个不能言语的、也许甚至完全聋哑的东西是何等巨大,巨大得令人不知所措。”[8](36)马洛看到受人尊敬的库尔茨为了弄更多的象牙而杀戮、掠夺、征服,内心装满了邪恶、贪婪的欲望,迷惑、恐吓住非洲土著,最终,这片黑暗的荒野对库尔茨所进行的荒唐的袭击作出了可怕的报复。此刻的马洛可能才真正明白,欧洲白人在对非洲进行殖民暴力与文化征服的同时,也被它所征服和控制,失去了自我,成为灵魂完全黑暗的人。
三、结语
《黑暗的心》作为文学文本,展现了19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主义活动,为我们认识殖民主义暴力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提供了文本依据,传达出历史的真实内涵,也表明,对过去的历史真实进行再现,不仅可以通过拘泥于史实的历史编纂的如实直述,还可以通过情节编织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实现历史与文学的互动、对话。在欧洲白人的殖民话语体系中,非洲土著无疑是落后、野蛮、罪恶的,非洲形象作为反面教材,正衬托了欧洲自身的文明、进步、优雅、高贵。殖民暴力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是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的双重创伤,因此欧洲应该放弃对非洲的偏见与种族主义思想,不再歪曲甚或妖魔化非洲。
[1] 赖辉. 论《黑暗之心》的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陌生化”[J].外国文学研究, 1999(2): 54-59.
[2] 姚兰, 王颖. 试论《黑暗的心》中黑与白的象征意义[J].外国文学研究, 2003(3): 38-41.
[3] 徐平. 论《黑暗的心》中的反殖民主义主题[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3(3): 33-35.
[4] 吴迪龙, 罗鑫. 后殖民, 还是反殖民?——《黑暗的心》的后殖民批评解读探讨[J]. 译林, 2007(4): 196-198.
[5] 张湛, 郑蓉颖.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康拉德——《黑暗的心》主题探究[J]. 郑州大学学报, 2008(3): 94-96.
[6]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7] 乔治·伊格斯. 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J]. 史学史研究, 2008(4): 1-8.
[8]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吉姆爷[M]. 黄雨石, 熊蕾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9] 艾梅·塞萨尔.关于殖民主义话语[A].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后殖民批评[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0] 海登·怀特. 旧事重提: 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A]. 陈恒译, 陈启能, 倪为国主编. 书写历史(第1辑) [C]. 上海: 三联书店, 2004.
[11] 特雷·伊格尔顿. 导言[A]. 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2] 陶家俊. 创伤[J]. 外国文学, 2011(4): 117-125.
[13]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4] 王晓升. 道德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批判——兼谈普遍伦理的可能性[J]. 哲学研究, 2001(2): 25-31.
[15] 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 属下能说话吗?[A].罗钢, 刘象愚主编.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6] 钦努阿·阿契贝. 非洲形象之一种: 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A].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吉姆爷[M].黄雨石, 熊蕾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17] R. T. 汪. 转向语言学: 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续) [J]. 陈新译, 哲学译丛, 1999(4): 57-63.
Interaction of text and history: the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n image and colonial trauma in Heart of Darkness
WANG Xia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New historicism claims “textuality of history” and “historicity of texts”, stre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texts and history, which holds that literature can represent historical truth. Joseph Conrad takes literary text as the medium to represent the African image and colonial trauma under the violence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This shows that Conrad’s ability of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truth and processing it into literary works, highlight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presenting historical truth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and the dialectical tension structure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Heart of Darkness achieves the interaction of text and history.
Joseph Conrad; text; history; new historicism; Heart of Darkness; African image; colonial trauma
I041
A
1672-3104(2014)01-0206-05
[编辑: 胡兴华]
2013-09-04;
2013-11-02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与当代意义”(QN2013050)
王霞(1981-),女,江苏赣榆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