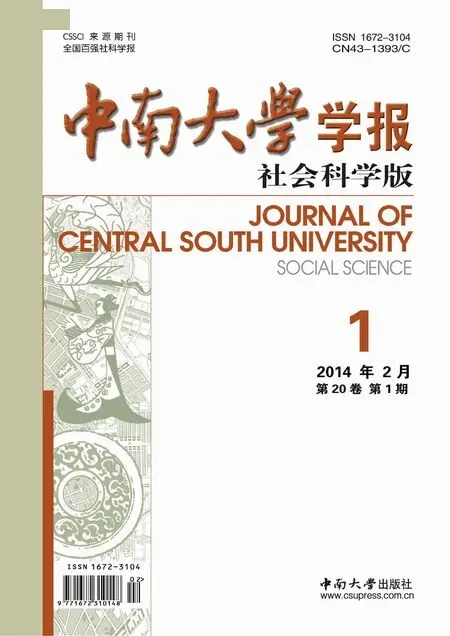虚幻的影像
——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2014-01-23肖红春肖泳冰
肖红春,肖泳冰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室,江苏扬州,225007)
虚幻的影像
——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肖红春,肖泳冰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室,江苏扬州,225007)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艾塞亚·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自由的向度;自由的限度
艾塞亚·伯林是西方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之一《两种自由的概念》也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一篇自由主义论文,一再被人征引,引起争论。其对于自由的两种存在状态的划分在自由主义阵营以及西方政治和社会理论学界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伯林的自由主义不在于构建、设计一个实现自由的社会制度或者蓝图,而是根本上批判、抛弃了前人思想中所蕴涵的哲学基础——一元论(尤其是理性一元论),伯林试图通过这种解析前人自由理论中的内在学理缺陷,来解释历史中出现的各种自由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伴随各种专制,希望通过这一工作,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哲学家们“理性的狂热”。为了全面地了解自由的各个方面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结果,伯林第一次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并将“消极自由”作为对“积极自由”的制约与解毒剂。
一、两种自由的划分
伯林对自由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在关于“自由”这一概念变幻莫测的意蕴中找到两个最重要的意义,也是最重要的两层意义。伯林将第一种自由称为“消极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免于……干涉的自由”,这一种自由的意义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作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1](189);第二种意义的自由,伯林称之为“积极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1](189)。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伯林发现在他之前的自由主义虽然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但总体上是积极自由占优势的历史,无论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或斯多葛学派还是斯宾诺莎或黑格尔、费希特,都持某种形式的积极自由观。虽然政治哲学家们大都也认同一定范围不受干扰的自由,也即“消极的自由”,但对自由之真意的理解,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到“积极自由”的思路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康德和穆勒,他们坚持把自由理解为自主性,即由具有理性的主体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范围和方式。而主体本身具有复杂的需要和属性,其中某些属性和需要不仅相差甚远甚至相互冲突,因而必须确定自主的最后根据。这一根据就是理性。而理性是超越个体性和具体性的。这种对待自由和理性的思路就有可能最终从个体性自我上升到超越性的“理性本我”,最终个体性的自我就被国家、民族、集体所取代。伯林发现,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使得自由(积极自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自由的实现变成了迫使人们自由,最终只能使追求自由的努力变成了自由的反面——强制。因为理性的内容很容易被置换,从个人的自觉、自决转向某种理论或某一群体、社会的理想。
伯林认为,积极自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吊诡,原因在于积极自由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大都继承了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传统,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是他们共同的哲学和社会心理学基础。这一基础表征为:正如在科学中那样,一切问题必定有一个真答案,而且只有一个,其余的都必然是错误;而且必定有一条朝向发现这些真理的可靠道路;一旦真答案被发现的话,必然彼此兼容,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因为一个真理不能和别的真理不相容。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按照理性原则生活,并进而获得自由,因而必须一个必要的引导和约束。这样一种信念有着古老的传统,“人们信奉的所有积极的价值,最终都是相互包容甚或是相互支撑的”,因而“在某个地方,在过去或未来,在神启或某个思想家的心中,在历史或科学的宣言中,或者在未腐化的善良的人的单纯心灵中,存在着最终解决之道”。[1](240)这些理想主义假设运用到政治自由领域,就造成了对于自由的公式化、简约化处理。人类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在这里要么被视为错误、要么被视为虚幻。一元论开始掩盖现实生活的差异性和自由的丰富性。这种简单化、平面化自由的最终结果是,当所有的目的都能够和谐一致,最终成为一个或一体,剩下来的就是如何实现之类的技术的问题,人在这种社会中就只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个人的选择也就被湮没在中技术处理中,人类的最终尊严和价值也就丧失了。
为了自由的最终实现,为了一个充分享有的自由、平等、安全、正义等善价值的社会早日实现,人们必须做一些工作、付出一些努力。在实现上述价值的过程中,我们有权控制或干涉他人,使之成为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以便实现理想的社会模型、社会秩序、社会蓝图。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可以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与途径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度,社会与政治的最后真理就在于对人性的观察、试探、分析中得到,并且这一真理和自然科学的最后真理是可以相容的。在达到这一真理之后,人类最后的自由、和谐社会就会实现。当然发现这些真理,并引导大众进行追求,只是一部分具有非常智慧、天才式的伟大人物的独特权利。这种发现被伟大人物揭示以后,剩下来的就是伟大人物带领人们去实现这一目标。即使一部分人不理解、不支持,伟人也有权利强迫他们实现,他们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分子,流血和牺牲在所难免,只是微不足道的事件,在历史的进程和人类最终的自由和幸福实现面前,一部分的愿望和追求是微不足道和不需要考虑的,甚至是必须牺牲的。只有这样,整个人类的自由和愿望、幸福才能实现。这样,一个极权也就从此诞生,即使这种极权声称是为了所有臣民的自由,依然不能淹没其极权性质及其本质上对自由的扼杀。
这就是积极自由在逻辑上的致命缺陷,在对自由即自主、自控的理解和追求过程中,积极自由最终会变成强制和压迫的一种借口甚至理由。“强迫你自由”,这一口号出现的同时,也就是自由真实意蕴蜕变的开始。当然,伯林并不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一定会导致极权和自由的丧失,而只是认为积极自由的内在逻辑中存在一种缺陷,这种缺陷会使得自由的实践倾向于极权主义的思考方式。“伯林之所以要反对积极自由,乃是由于他认为提倡积极自由在历史上、逻辑上,以及实践上很容易现落到它的反面去——强制或不自由。”[2]
二、作为解毒剂的消极自由
伯林在对积极自由的内在缺陷有了清醒认识后,提出了“消极自由”的概念,将“消极自由”作为一个对积极自由的制约限度。伯林曾经指出:“自由的基本含义就是免受束缚、免受限制、免受他人的奴役,其他的含义都只是这个含义的扩张或比喻。”对伯林而言,“消极的自由”就是对于人类基本选择能力和权利的维护。消极的自由以在两者不可得兼只能从中择其一的情势下的选择能力为先决条件。在这里,伯林已明显不同意之前自由主义者的和谐论,认为人类所重视的重要价值之间是可以和谐共处、同时实现的。伯林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发现某些基本价值之间根本不是相互包容的,而是相互冲突、对立的,是一种悲剧性的场景。此时理性置我们于不顾,无法发现一种完全妥善的解决办法,因此,这种免于受外界干涉的选择就是自由的最好表征。根据石元康的归纳,消极自由所致力要避免的外界干涉包括:“别人所加诸于我们身体上的干涉;国家或法律对我们行动的限制;社会舆论对我们构成的压力。”[3](11)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作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权,希望从他者,主要是政府的规划或强制中保持一定范围内的自我任意选择、行动的权利。但这种任意选择的消极自由并不是理性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根据自己实际或潜在的愿望进行活动而不受到别人干涉的自由概念,并不是没有限制和条件的,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任何强制,比如说法律和社会普遍规范的[4]。“伯林并没有否认自由需要通过某种强制(如法律)来保障,限制自由是为了保障自由,但是,就被限制的人而言这毕竟是自由被缩减了。”[5]
因此,在实际指涉自由时,伯林更多地是偏向于“消极自由”这一概念,并暗示消极自由应当是积极自由的一种限制。“自由观念的本质,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含义,都是阻止某事或某人——闯入我的领地或宣称对我拥有权威的他人,或者阻止妄想、恐惧、神经症、非理性力量之类的入侵与暴君。”[1](231)这实际上是以一种让人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重申消极自由的概念。伯林所暗示的自由社会是——在社会生活已开始的地方,就确保在属于个人自由的领域,即“免于……干涉”的领域不受到任何人、任何权威以任何看似合理的藉口而似是而非的侵犯。这一范围到底有多大,伯林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他认为这一领域虽然和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它们之间没有一条清晰无比的线,但伯林认为其范围取决于:
“消极自由”的程度在特定的场合是难以估计的。……我的自由的程度似乎依赖于:
(1) 有多少可能性对我开放着(虽然计算的方法从未超过凭印象的程度;行动的可能性不是一个苹果一半的实体、可以计数);
(2) 每一种可能性在实现上的难易程度;
(3) 在我的性格与环境给定的情况下,当这些可能性彼此比较时,它们在我的生活计划中有多大的重要性;
(4) 人们故意开启或关闭这些可能性的程度;
(5) 不光行动者,还有行动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观点对这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作何评价。所有这些变量都必须被考虑进来,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结论必然准确没有争论。[1](199)
正是这条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清晰无比的界限,赋予了自由以具体、现实的保障,消极自由在此意义上也成为了自由的代名词,成为了积极自由所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在这一背景下,消极自由决不能“被视为是积极自由得以实现的手段”[6]。相反,消极自由在伯林那里无疑具有某种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使得伯林的消极自由可以为积极自由设定范围,为理性主义狂热提供解毒剂。伯林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的自由社会的设计图景,这也和消极自由的理论内在意蕴有关,伯林关心的不是如何设计一个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都完全实现的完美社会,并在这一完美社会中实现自由,他关心的是哲学家和他们的理论中所隐藏的行而上学假设以及这种假设可能带来的危险性。伯林对于哲学家只顾设计理论,而完全不考虑自己理论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一行为相当不满,柏林很奇怪为什么那些追求自由哲学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活动所具有的强大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在根本上否定了自由的存在。伯林自己的努力就在于揭示这种破坏力,并对哲学家的理论予以去魅,以保证对于自由的追求不会伤害到自由本身。
消极自由相对于积极自由之所以更能够被柏林所接受,一方面是因为消极自由可以有效地作为积极自由的一种制约因素,防止积极自由的过度狂热;另一方面,是由于消极自由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状态。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都完全实现的这种完美社会的理念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总是自相矛盾的。伯林暗示现代自由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个多元化价值背景——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的、多样化的;这些多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有时在它们彼此冲突的时候,它们是不可通约的,没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对它们加以比较。没有任何理论原则可以知道我们的选择,这些价值不能转化,命题是多样的,不可通约、难以比较的,强行转化的同时意味着自由的丧失和专制的开端。就像道德生活一样,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敌对的善恶价值之间的基本选择,此时理性弃我们于危难而不顾、我们无论怎么选择都要导致一些损失,有时甚至会出现悲剧,正因为如此,所以选择作为自由的一种必然表征始终伴随着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无论是个人根据自己愿望、兴趣、欲望,还是信仰做出的选择,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在历史中做出的选择。每一种选择在消极自由的意蕴中都有其合理性,都是自由的一种体现。(法律也是对自由的一种束缚——针对传统自由主义对法律是自由本身的说法)伯林提出的那种历史主义观点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由主义当作是基于理性和基本人性的一般要求,或在历史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某种主张。
尽管伯林出于上述两重原因,非常推崇消极自由,但他对于积极自由本身并没有什么偏见,而是认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伯林的意思“并不是说自由只能是‘否定的自由’,即一个人在实际的和可能的选择活动中不受别人的干涉,也不是说只有‘否定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或只有否定的自由才是有价值的自由”[7](14)。伯林的著作中他强调“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都是正确的概念”[7](15),这两种自由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有一个自由,两种自由所指向的都是这一自由。伯林所担心和反对的是在缺乏消极自由的情况下,积极自由在理性主义传统下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一种反个体、反自由的倾向。“肯定的自由概念和否定的自由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照逻辑规范的步骤沿着背道而驰的方向进行,直到最后出现彼此间的直接冲突。”[7](15)伯林对于积极自由的作用十分清楚,“积极的自由……是公平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必要条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并不相互排斥,在说明自由问题时,人们不能只用积极自由或消极自由来说明同一件事。按照伯林的观点,消极的不自由和积极的不自由也具有相同的基础,这就是选择能力的削弱。这两个概念都体现了有效的自由概念,或者,换句话说,体现了康德所说的“任意”即基本自由的不同方面或不同维度。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两种自由的观念都得到了如此程度的发展,以至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善或不同的条件;这些价值不仅是不同的,事实上它们还经常是相互竞争的。正因为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善或不同的条件是自由的现实或理论前提,必须加以保护,否之“自由的实现”本身将是不自由的、被人设计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中一般是由于积极自由所引起的),这种保护必须由消极自由的切实存在于以提供。
柏林也并不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虽然他反对理性主义无限制的积极自由和由此带来的危险。按照伯林的观点,理性对于一个人享有自由来说不仅不是需要极力避免的,反而是自由的一个前提——个体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愿望,也不能评价这些愿望或考虑这些愿望,他必然缺乏这种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伯林的“消极自由”,也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而是本身就受到理性约束的自由。但伯林所关注的是消极自由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或政治自由,而不是那种在服从上帝意志的人们或服从绝对命令的人们中发现的自由,或者是斯多葛主义的与自然的秩序理性的秩序相一致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伯林反对理性主义和一元论的理论前提和哲学史上把积极的自由观与这种前提联系起来的观点。在伯林看来,自由,即使是积极的自由,也总是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是消极自由所极力保持的。理性之于自由,并不是代替他人自由选择的一种推理和论证,而是明白自身选择意义和价值的一种能力。
三、消极自由的限度
伯林推崇消极自由可以说是掌握了自由主义者应该持有的根本立场:如果人的行为与生活,应该是个人自行选择的结果,那么自由主义首要关怀的,当然不是人所选择的结果是否真有价值、选择的品质是否经得起质疑、检验,而是进行选择的机会是否存在、是否实际。对于柏林来说,自由更多的是行动主体面前的多种机会,而不是实际的行为。因为即使是在众多的可能性下不做任何选择的人,也可以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这个分辨,与政治态度的积极或消极,显然并没有直接关系。在价值多元情境的境遇之下,自由主义比较清楚地显露了它以“尊重人”而不以“管教人”为主旨的本色;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辨,做了重要的澄清,在这一点上,其贡献不能抹煞。可是这也是伯林的限制所在。在伯林的论述方式下,自由主义的问题,似乎简化成了对于“选择”这个概念的澄清与维护。所谓“简化”,意思是说他没有把自由看成一个需要由社会政治生活来说明和满足的概念。考虑个人的自由或者选择是怎么一回事,诚然不是无谓之举,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政治社会理论,必须进一步回答“选择为什么重要?”,“如何保证选择的进行?”等等问题。如前所说,伯林缺乏这种完整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构建蓝图,作为思想史家伯林没有完整的自由主义视野。伯林虽然声称对积极自由本身没有偏见,但他始终害怕积极自由的实施会重复历史的覆辙,因此对积极自由抱着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没有对积极自由展开积极、正面的讨论,无法在政治理论、政治生活中积极构建一个能够实现自由的社会,结果是如伯林本所意识到的那样,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根本不是两个问题,一个缺乏积极自由的社会必然无法实现消极自由。
伯林为消极自由做辩护的理由和原则本身也还存在颇多争议指出。首先,社会中确实存在一些彼此差异的基本价值,但这些基本价值之间必然在价值序列上处于同等地位,因而无法比较,最终只能相互冲突、不能协调。但事实真的只能是这样吗?多种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能过分强调,如施特劳斯提到的:我们无法通过肉眼比较两座山峰的高低,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无法衡量一座高山和一个小土丘之间的高低。有些价值之间大小和优先次序很显然是有着明显的秩序的[8](15)。因此,伯林为消极自由所辩护的价值多元主义立场是存在问题的,但这一问题决不是邓晓芒教授所指的那样——多元主义如果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信仰,那么极权主义也就会变得具有合理性了[4]。多元主义本身就预示着,诸多的价值目标和标准在终极意义上只能是个体性的,而不可能是普遍的。另外,在一个自由价值得到有效体现的社会,自由不仅仅是与其他价值相互竞争的,还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依托关系。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要有其他社会价值存在作为支撑。举一个伯林在《两种自由的概念》这本书中举出的例子,一个人不能说他缺乏自由,如果他不能按照自己意愿来行事是由于他自身身体上的某种缺陷或自身所处的实际生活处境如,经济上的贫困等引起的。一个盲人由于自己的目盲不能和正常人一样欣赏美丽的风景,他不能因此而抱怨他缺乏自由;同样一个经济收入一般的普通人不能抱怨由于他缺少足够的金钱来满足他无止境的欲望的现状是缺乏自由。伯林认同上述的说法,但他同时认为上述的例子还可以有另外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缺乏自由,即盲人的目盲是由于强权者的迫害造成的,而收入一般者不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收入不是由于自己的能力或自身的其他原因,真实原因在于某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设计。这一制度使一部分人生下来就可以享受这些,而一部分人却永远或很难达到这一地位,就像马克思描述的资本社会那样,金钱是带有血缘性的。这时,自由的实现无疑和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以及社会整体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相互影响的。这和伯林设想的这些价值之间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的悲剧性场面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事实情况也许是这些价值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的悲剧性场景和这些价值之间相互和谐、没有冲突的场景同样是一种极端情况。伯林的思考虽然对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巨大的冲击,也为自由主义带来了新的路径和生机,但其对“积极自由”限度的设定本身也引起了关于“消极自由”限度的广泛思考。反思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我们发现柏林的“消极自由”可能不过是从天平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对于什么是自由以及自由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依然有待我们后人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1] 艾塞亚·伯林. 自由论[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2] 张文喜. 自我的幻想——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批评[J].东南学术, 2002(3): 157-164.
[3] 石元康.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M].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4] 邓晓芒. 伯林自由观批判[J]. 社会科学论坛, 2005(10): 19-20.
[5] 周枫.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判[J]. 社会科学论坛, 2006(5): 5-28.
[6] 余宜斌.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J]. 兰州学刊, 2006(10): 18-20.
[7] 约翰·格雷. 伯林[M]. 北京: 昆仑出版社出版, 1999.
[8] 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6.
Illusory image——Analysis of Berlin’s freedom theory
XIAO Hongchun, XIAO Yongb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arty School of State Tax Bureau, Yangzhou 225007, China)
Isaiah Berlin’s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s a classic of modern liberalism, and his concept of freedom broke out from either empiricists or rationalists who ar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holding monism. Berlin inferred that enthusiasm and the pursuit of “positive freedom” may have been brought dangers in practice. He actively praised a“negative freedom”, which is unlike “positive freedom”, under the multi-value background. The value of Berlin’s“negative freedom”, however, doesn’t show that liberty could be achieved by what principles or systems in some way, in some social systems. The restriction of “negative freedom” to “positive freedom” itself has become an illusory image. Thus, the work of Berlin had raised issues, instead of having resolved the problem.
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 liberalism; negative freedom; positive freedom; the dimensions of freedom; the limits of freedom
D502
A
1672-3104(2014)01-0150-05
[编辑: 颜关明]
2013-06-07;
2013-12-03
肖红春(1984-),男,安徽桐城人,哲学博士,国家税务总局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应用伦理学;肖泳冰(1968-),男,江苏扬州人,国家税务总局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