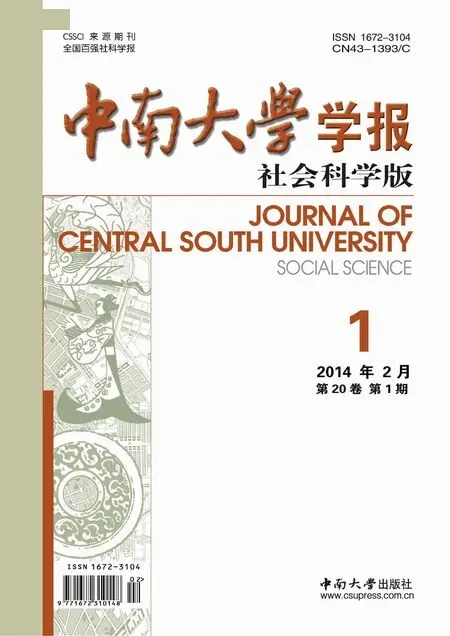文明的野蛮与野蛮的文明
——评韩少功的《日夜书》
2014-01-23唐伟
唐伟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文明的野蛮与野蛮的文明
——评韩少功的《日夜书》
唐伟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文明与野蛮的对比、翻转,构成《日夜书》历史钩沉的诗学辩证法,也是相对主义认识论与价值观的现代结晶。在《日夜书》中,韩少功着意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或一套固定的价值标准,而是以知青遭际的伦理叙事,将现实之思、未来之忧和历史之虑,将家国命运、社会变迁和个人经历,以小说的艺术样式和盘托出,作者借知青小说的物质外壳,鸣奏一曲“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时间咏叹调。
韩少功;诗学辩证法;日夜书;时间;文明;野蛮
一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的传世名言,并不因为当今现代∕后现代的语境而失效。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将小说视为解读一个民族历史密码的文化症候。但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的兴趣,显然并不止于巴尔扎克这句结论式的名言,他们关心的是,小说究竟是及时反映现实还原历史真相,还是拉开时间距离才能客观呈现公允的价值判断?小说与历史的纠缠,从上述意义上说也就成了一桩难有定论的公案。
但对作家而言,此类问题其实并不构成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障碍,因为作家们并不一味执迷于无解的学理难题,历史或现实之于他们,无非是素材和题材的区别。事实上,作家对文学研究界抛出的一个又一个话题,并不像批评家们预想的那样,表现得兴味十足——正如优秀的批评家不会对媒体炒作的文学现象、文学话题趋之若鹜,优秀的作家也会对批评界炮制出的文学潮流保持警惕。
韩少功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创作始终处于潮流之外,或是与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真要执意说他与潮流有关,那也是开创引领潮流,而非刻意迎合追赶潮流。比如,当年知青文学风生水起、方兴未艾之际,知青出身的韩少功,并未沉溺于回忆中,而是一个华丽转身,平地一声“寻根”雷,树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值花甲之年的韩少功,最新推出的《日夜书》,显然不是赶潮流的怀旧或重返,不是所谓用小说来还原历史真实——从野心勃勃的小说题目上,也能一窥这位伏枥老骥的志在千里。因此,本文对《日夜书》的讨论,并不打算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加以评说。
尽管《日夜书》的作者不是着意用小说去翻拣一堆陈年旧账,但故事讲述的那段知青岁月毕竟是基本事实——从这个角度说,将《日夜书》称之为一部迟到的知青小说也未为不可。《日夜书》的写作与八十年代知青题材小说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置身深重的“现代性后果”之中的作家,远眺那一段历史,不仅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咀嚼往事,更有机会在巨大的差距中抚今追昔,遥想感怀,因此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日夜书》不是简单的重返六、七十年代,不是简单地书写一代人的传奇,而是以此叩问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质询现代文明的幸与不幸。
正是因为有了足够长的时间距离,几十年之后,返城知青们的处境自然各不相同,他们或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或陷入生活的窘迫、跌入人生的困境,或走入婚姻的围城又突出重围。《日夜书》写到了白马湖的十一位知青,姚大甲、陶小布、安燕、马楠、马涛、郭又军、贺亦民、蔡海伦等,加上绰号酒鬼的猴子,小说中的白马湖知青群落一共是十二位成员。《日夜书》的故事讲述,既非依时间先后侃侃而谈,也非严格按人物出场顺序娓娓道来,结构看似散漫不定,并无一定的章法可循,但细读下来便会发现,作家实则遵循的是记忆的自由法则,准确地说是情感记忆法则,小说的内在逻辑,不是毫无节制地任意而为,而是理性退居次席,由情感充当穿针引线的主角,而更进一步地推敲,小说情感的触发则是由叙述者的现实境遇决定的,简言之,现实才是回忆呈现的契机——从这一意义上说,《日夜书》延续了由《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以来一以贯之的“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法则。
第一个出场的姚大甲,当年是一个十足不靠谱的“问题人物”,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初中留级生,十多年后居然远走异国他乡,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艺术家,把画展堂而皇之地开到了美国。而让“我”,即故事的叙述者陶小布,对大甲印象尤为深刻的,恐怕是跟他那次为五十张饭票而打赌吃死人骨头的事。类似惊悚的较劲,在后来的小说情节中也多次出现,马涛为证明自己游泳跳水并不弱于郭又军,居然冒生命危险夜晚去堤坝练习跳水,最后落得个头破血流也毫不在意。
小说故事的讲述,正是在这样一种生猛鲜活的氛围中开始的,知青们打赌竞赛,玩笑嬉闹,即便是表现顽劣,也是一板一眼;行为执拗,也让人肃然起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与同类知青题材小说比较,《日夜书》少有一种凄凄艾艾,不是观念的铺展,而是经过生活的一番打磨浸泡,奏响的是复杂的多声部和弦。换言之,《日夜书》的精彩好看,正在于其酸甜苦辣咸俱全的重口味。韩少功当然意不在展示地域文化风景,但小说人物所显露的湘楚文化气质历历在目,湖南人的霸蛮性格跃然纸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无论是马涛跟郭又军较劲还是陶小布和姚小甲打赌,都能捕捉到小说浓郁的湖湘风味,而吴天宝、梁队长以及后来的杨场长等白马湖农场的“主人”,他们一个个满口痞话,匪气十足,更是把民夫盲流作风演绎得荡气回肠,如果没有这种乡野生活形态的原生态展示,小说肯定会减少很多生趣。
在今天看来,姚大甲、马涛们当年的白马湖鲁莽行径,虽然比吴天宝们多了分书卷气,但无疑也是为现代的文明人所不齿,甚至称得上有几分粗俗和野蛮。同样,今天的人们也很难想象,成长于缺少关爱、常遭虐待家庭的贺亦民,后来离家出走,浪迹天涯,竟然在流浪漂泊生涯中无师自通地成为旷世电工奇才,不得不让人惊叹,如此野蛮生长能成就一位大师级人物,确实是一个奇迹。
湘人毛泽东当年喊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口号,欲用野蛮与文明来建构体魄与精神的辩证法,几十年之后,韩少功则以小说实践,将一段陈年旧事佐以油盐酱醋的饵料,烹制出一道湘式大菜,重审野蛮与文明的辩证法。我们看到,《日夜书》正是在历史/现实、往事回忆/时代精神的多重观照下,构造起一个个“文明和野蛮”的多棱视镜:依知青们当年的观点,作为从先进发达的城市去到贫穷落后农村的“落魄公子”或“落难小姐”,无论是怀抱理想充满憧憬,还是被迫无奈远走他乡,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城里的知青们是以文明的现代人身份、以外来的他者眼光打量白马湖农场的人和景,事与物,这帮有着优越感的“文明人”,对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粗野的民风民俗难免感到不适应。
有意思的是,多少年之后,时过境迁,当年的野蛮非但不再是粗俗落后的指代,还成了最文明的象征,“我万万没想到,其实没过多少年,污言秽语在特定情形下倒是奇货可居,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成了文明的前卫款和高深款——这事不大容易让人看懂了”。“这事”指的是姚大甲在美国开了一个总题为《亚利马:人民的修辞》画展,一批题为《夹卵》《咬卵》《木卵》《尿胀卵》《卵毛》的画作赫然陈列于最发达、最现代国家的艺术殿堂,成了后现代意味十足的政治波普作品。历史的翻云覆雨、阴晴难料,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
不惟如此,让郭又军、陶小布们始料不及的还有,当年下象棋、打篮球等知青们自恃比农场人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下一代眼里也早已落伍,郭又军、陶小布们与丹丹、笑月们的生活理念已迥然有别、大异其趣。“问题是,如果无力购买商家们开发出来的高价快乐,包括不断升级换代的流行美食,生活还有何意义?还算是生活么?在很多人看来,现代生活不就是一个快乐成本不断攀高的生活,因此也是快乐必然相对稀缺的生活?”[1](112)从逻辑上看,这种以消费为快乐源泉的文明论调,既无懈可击,也无可挑剔:宝马香车、酒吧KTV、大型商场超市,高级楼堂会所,不仅仅提供消费快感,也重新规定人的身份——文明的定义以前是由知识和美德塑造,而现在早已转为受资本操控。从日常的意义上说,文明不就是社会物质富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吗?
很显然,郭又军、陶小布们对养藏獒、学法语、沿长江旅游等更文明的生活已感到明显的力不从心——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经济供给能力,身处更现代的现实,他们反而怀念那前现代的知青岁月。白马湖知青返城后每年都要聚会,相互抱怨在白马湖的时候,吃不饱、睡不够,蚊子多得能抬人。但在跟晚辈们聊起白马湖时,他们又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无比的自豪,慨叹今不如昔:当年分猪油的赤诚情谊、体力劳动的火热激情、一起打蛇吃蛇肉的精彩纷呈等,“从白马湖走出来的这一群要暧昧得多。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偷偷自豪……他们的自豪与悔恨串味,被一个该死的白马湖搞得心情失调”[1](145)。文明是物质发达,是一种秩序井然,温文尔雅,人类渴望进步与文明,渴望摆脱衣不蔽体、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但无法否认的是,相比于苍白羸弱的吟诗作赋,文明唱和,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野蛮,确实又显得无比的生机勃勃,雄浑强健。
文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野蛮则是一种旺盛的生命法则,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更有甚者,“野蛮”有时比“文明”似乎更显文明,贺亦民跟马涛当年口头叫板斗勇斗狠的劲儿,不是比后来他发达后签的那些合同契约来得更认真吗?消费享受无疑是一种高级文明,但这种文明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表面看起来彬彬有礼,但实则冷血至极类乎野蛮,且野蛮得没有一丁点人情味。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除了人的生存改善、生活舒适,同样还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战争不断……这些究竟是文明还是野蛮呢?
二
在小说中,韩少功对文明与野蛮的思考,并未停留在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比较中,我们看到,小说叙事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相对主义的深渊。读书无疑是归化文明的最佳途径,但谦谦君子般的读书人,他们的表现有时又着实让人大跌眼镜,正如小说中所讨论的那样:“读书是好事吗?当然是。但读书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一不小心就在相互挑剔、相互质疑、相互教导下土崩瓦解,甚至在知识重载之下情绪翻车,翻出一堆有关智商和品德的恶语。”[1](120)品德的修养与知识的积累,并不总是呈正相关的关系,恰如民谚所说的那样,“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郎”,历史上陈世美的例子数不胜数。小说中堂堂海外知名学者、民间思想家马涛,号称“新人文主义”的首创者,竟为一件黑人球星赠送的球衫,逼得陶小布连夜折腾回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去取,又哪有半点人文关怀?而马涛的夫人肖捷则一边居高临下地贬斥腐败行径,一边又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腐败的果实”。终日操持文明事物,干出的却又是让人不齿的野蛮勾当,作家的用意或许并不在于揭示知识分子的嘴脸,而是道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相对主义真理?
至此,我们看到小说似乎陷入一种模棱两可、无可把捉的相对主义情境中去,进入到了文明与野蛮的辩证循环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少功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并非到《日夜书》才浮出水面,毋宁说是一以贯之的延续,这一如作者十年前的《暗示》所言,“我就是那样一身黑煤地急切地投入了文明,投入了都市,更大的都市,更更大的都市,更更更大的都市,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重新独坐在山谷里,听青山深处一声声布谷鸟的啼唤。我并不后悔,而且感谢这些年匆忙的生活,使我最终明白了文明是什么:它既不在古代也不在当代,既不在都市也不在乡村,只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2](274)。如果这种相对主义氛围,只是停留在往昔古今的对比中,如果只是把文明翻转为野蛮,或把野蛮重新释义为文明,那么《日夜书》又何以成为“日夜书”呢?如前所述,《日夜书》的知青回忆,难免会带有作家现实处境的思考,问题不在于作家现实思考的深度,也不在于回忆往事的真实,而是看回忆与思考的交织,指向怎样的语言事实和想象图景,从而黏合成一个有机丰饶的文学文本,因为小说毕竟是艺术实践,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自由的诗性空间,而不是描摹现实或教条说理。
相比较而言,另一位湖南作家王跃文的《亡魂鸟》较为偏重依赖故事素材,这部同样也是知青题材的小说,以主人公维娜的经历为主线,串起了几位返城知青们的故事,尽管也有现实与历史的镜照, 也有上一代与下一代的观念冲突,但诚如王跃文自己所言:“写到这些时代的文学,便怎么也无法纯粹起来。我梦想着写出抽离时代的作品……然而现实的泥太深,我的双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我想超拔现实,却没有这个功力。”可见,知青题材小说的难度,或许就在于如何去“超拔现实”,《日夜书》的成功,正是仰仗于作家的艺术想象和哲理思考。
文明与野蛮的对比、翻转不过是《日夜书》中相对主义精神最大化、最集中的一种托付,韩少功的相对主义兴趣和哲理思考,究竟要抵达怎样的一种归宿呢?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对人、对事、对物的判断对比中,大小、好坏、优劣、对错、高下、冷暖、聪明与愚蠢、漂亮与丑陋、文明与野蛮……人所形成的种种意见判断,既有以个人习性为依据的情况,也有把社会常识、道德修养当判断标准。休谟的怀疑人性论根基正在于,人无法由事实判断推导出价值判断,康德毕其一生的精力,欲破解休谟的这一难题。
相对主义的可怕后果是虚无主义,难道说,韩少功也会像休谟那样,最终也会堕入一个虚无的陷阱?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一节,整节用来描述一幅由婴儿、星空、太阳、花朵、天堂、世界等此类极富象征意味的符号构成的图景,既像是一个创世神话,又像是一个人类生存的整体寓言,通篇洋溢着一种诗意的幻灭感。《日夜书》所完成的,是否是一个以知青故事为外衣,而内里则是由相对主义导向虚无结局的暗度陈仓?
《日夜书》传达的究竟是小说艺术的高妙,还是现代价值的虚无?要回答这一问题,就有必要探讨一番相对主义与现代小说的关系。众所周知,首次在现代意义上把相对主义提高到小说艺术高度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认为,当今被命名为现代/后现代的人类处境,正处于终极悖论的时代,这种悖论的境况——体现在《日夜书》中即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律背反——是由人类理性所构设的种种价值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所致,人的理性真理本身存在先天的盲目性和荒谬性,套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现代性的合理性,既是人间天堂,又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人类文明的进程,究其实不过是人心、人性使然,人类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名义下,发明工具、使用工具,以致被工具所奴役也乐此不疲;在迈向文明的征程中,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哪怕远离自然也在所不惜。所谓现代或后现代,不过是一种用来包装人性的托词而已。
人类骄傲的理性要想走下真理的圣坛,只能存在于小说中,而现代的小说艺术,正是在承认相对主义哲学的前提下,更准确地说,是在承认相对性的个人主义基础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昆德拉对塞万提斯推崇备至,他认为“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模糊,人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为对立的真理,因而唯一具备的把握是无把握的智慧”[3](5)。
科学理性信奉的是必然法则,是独断的定在世界,而现代艺术或者说现代小说艺术则倾向取消绝对的定在,以相对性或相对主义为旨趣,指向的是一种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小说艺术才有了勘探存在的可能,“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3](156),存在并非定在之在,而正是一种可能性的所在。在昆德拉的小说中,昆德拉将他对存在和对现代小说的理解,阐发为“幽默”的艺术,幽默的艺术在昆德拉看来,不是指作家用诙谐的语言博取读者莞尔一笑,也不是那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情节所带来的喜剧效果,而是“使所有被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我们看到,理解昆德拉终究还是离不开对相对性世界法则的把握。
即使《日夜书》中题为“关于贺亦民”的那一小段出现了“米兰·昆德拉”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字眼,即使我们知道韩少功确实翻译过米兰·昆德拉,也算在纸上与那位倔强的东欧人有过神交,但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妄意揣测,韩少功一定是深得昆德拉其味,而终成一部哲理意味浓厚的《日夜书》。唯一能肯定的是,一部充满相对性智慧且不时对精神病(第25节)、对死亡(第34节)有精彩论述的小说,远超出了知青小说的命名意蕴;我们或能接受的结论是,在对存在的勘探和对世界以及对现代小说的理解深度上,韩少功与米兰·昆德拉意趣相投且难分伯仲。
韩少功的相对主义世界观,其实早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就袒露无疑,“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都是可以怀疑的……我当然不赞成动物化,不赞成‘怎样都行’,但摆脱这种最虚无同时又是最实利的生存状态,我以为出路不是重新回到神学……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重建真理和理想,不是要重返一些独断的结论。”[4](28)而在一次文学对话中,他更是直言:“小说天然地反对独断论,这也是小说的道德。”[5](8)与独断论相对的是过程论,是相对性,而无论是看重时间过程,还是注重空间相对性,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都需要以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为支撑。在《日夜书》中,韩少功的相对主义小说智慧走得更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韩少功是入世的,同时他又是脱俗的;他是充分现实的,同时他又是真正地虚无的。他的悲观主义和博爱精神有着一种奇特的混合,他会残酷的透视人性中的病态刻毒地攻讦人的时髦仿效,也会热忱而通达地原谅人的各种现代过失。……在他的冷漠底下仍流着炽热的人情,在他的超人道之下仍有着宽厚的人道,在他的虚无里仍包含着对世俗事物的执著看法,在他的静观中依旧透出他难以更改的是非好恶标 准”[6](334-335)。尽管这段描述有点罗嗦煽情,但基本上也算切中肯綮,大致将韩少功为人为文的复杂性提纲挈领地提示出来。
三
《日夜书》由现实入思考,以回忆盛情感,叙述者或悲或喜的是知青们的命运遭际,但困惑无解的同样也是这诸种斑驳现实:丹丹直呼其父郭又军之名,马涛舍下亲生女儿不管不顾,郭又军、贺亦民的兄弟之情压根经不起推敲,而无论是马涛跟肖捷,还是陶小布跟马楠,他们的爱情都并非忠贞不渝,很难经得起推敲考验。还不仅是所有的感情都千疮百孔:陶小布想坚持工作原则,却被扫地出局;贺亦民欲坚持爱国理想,却被世人讽为疯子,最朴素的原则和理想都无法保全。比起返城时没文化的大粗人梁队长说的那番话,“你们有文化,是干大事的人。不过,万一哪天你们在外面不好混,就回来吧。这里没什么好东西,但有我们的一口干,就不会让你喝稀”[1](95),很难断言锦衣玉食、披红带绿的这一切究竟是社会文明进步,还是人类的野蛮倒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题为“准精神病”一节,小说会作结到“我们差不多都是异常者,是轻度精神病人”的原因吧[1](136)。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拾级而上,人的清醒与迷顿,困惑与澄明,统统被裹挟进不确定性的漩涡之中,文明和野蛮变得模棱两可。韩少功着意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或开出一个疗效管用的药方,而是以个人命运的伦理叙事,将现实之思、未来之忧和历史之虑,将家国命运、社会变迁和个人经历,以小说的艺术样式和盘托出。韩少功的文字无意纠缠于文字语言的追逐嬉戏,也无意一味地在虚构想象的疆域奔突驰骋。作家反思的指向不惟指向远去的历史,更像是基于芜杂的现实有感而发。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中的“逝者”是指时光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做一个更宽泛的理解,“逝者”又何尝不包括时光中的事物和生命呢?从这一意义上说,《日夜书》可看成是对逝者的缅怀。事实上也确乎如此,在对郭又军、吴天宝、贺亦民等的回忆中,故事叙述者陶小布难掩心中的遥寄失落,小说的挽歌情调溢于言表。但《日夜书》显然并没有仅停留在故友追思或往事再现的层面,《日夜书》之“日夜”无疑是时间的隐喻,日夜轮回永恒,时间周而往复,《日夜书》所书的,是浩然天地间的宇宙意识,是叩问沧桑体察万物的生命哲学,一言以蔽之,是一曲有关时间主题的咏叹调。
无论天堂,还是地狱,白天抑或黑夜,人,不过是万物之一粟,除了时间,又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呢?或许,只有死亡才是最真实的归宿——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小说对死亡的讨论才不显得是横来一笔的画蛇添足,而恰是对小说形上品格的有益补充。历史打上野蛮的烙印,现实被赋予文明刻度,但线性进化论并非人类可依靠的救赎,野蛮不是一成不变,文明也并不是牢不可破。野蛮的文明或文明的野蛮,或许正是在那时间的日夜书中永不间断的翻开与闭合。
[1] 韩少功. 夜书[J]. 收获, 2013(2): 112.
[2] 韩少功. 暗示[M].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274.
[3]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孟湄, 译. 三联书店, 1992.
[4] 韩少功, 萧元. 90年代的文化追寻[J]. 书屋, 1997(3): 28.
[5] 韩少功, 崔卫平. 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J]. 作家, 2000(4): 8.
[6] 廖述务. 韩少功研究资料[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334-335.
The savage civilization and the civilized Savage——A Review of Han Shaogong’s Novel “Day Book”
TANG Wei
(Jil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angchun 130012, China)
Han Shaogong made the comparison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which constitutes a “Day Book”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poems and maximizes the modern spirit of relativism, one of the most concentrated entrusted. That is not that provides ready-made answers, or a fixed value standard, but one of personal ethical narration of fate. In a dialectical way, Han expresses his concern and worries for the future and history, social chang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his specific style. He also borrows the educated youth novels materials to expound his notion of the savage civilization and the civilized savage.
Han Shaogong; dialectics of poetry; Day Book; Time; Civilization; Savage
I247.5
A
1672-3104(2014)01-0176-05
[编辑: 胡兴华]
2013-07-09;
2013-10-23
唐伟(1983-),男,湖南东安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