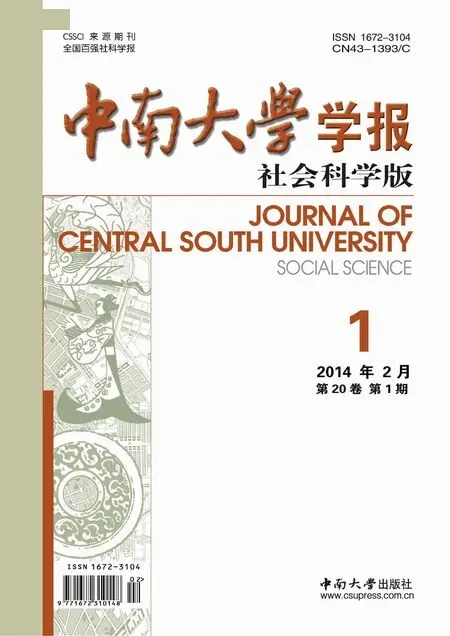伦理视域中的梁漱溟知识分子观
2014-01-23廖济忠
廖济忠
(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3)
伦理视域中的梁漱溟知识分子观
廖济忠
(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3)
知识分子观是梁漱溟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既可为师,也可为贼,这其中的确有一个严肃的道德选择问题。梁氏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讲理性,讲品格,讲实践,讲教育。追求人生意义、坚守社会立场、服务广大民众、讲求品高行修,做健全有力的“社会人”,这是梁漱溟知识分子观中有助于后人反思和提升的积极因素。
梁漱溟;知识分子;道德选择;社会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构成中,知识分子被称之为“士”。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其地位与作用可见一斑。士情结在梁漱溟的心底积淀甚厚,从近处说,这种情结来自士家庭的熏陶;从远处讲,这种情结来自士传统的承继。“有志业而无职业”“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能为”,[1](1040)这种充满自信甚至自负的夫子之道,的确是梁漱溟一生的真实写照。具体而言,便是“以近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与古人讲学的风气并作一事,而矢以终身”[2](727)。他始终站在“第三方”或“社会人”的立场,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对知识分子立场与使命的深思力行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分析他的知识分子观,必将有助于我们反思和提升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
一
“理性”是梁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最重要的概念,正如艾恺所说:“理性这一概念是梁漱溟第二次文化理论建构的基本原理”[3](132),“理性是没有进一步动机的行动的能力”[3](133)。
所谓理性,即指“是非之心表现在生命那一清明的动向上”[4](367)。梁漱溟认为,从本能超脱出来的人类生命得以豁然开朗进入无所为而为的境地,其核心在一种无私的感情。例如计算数目,数目错了,不容自昧,此不容自昧之情,即是最标准的无私的感情。再如正义感为道德之本,对于一件事情不徒计较利害,还要论是非。总之,与一般生物只有一个“生活问题”不同,人类生命更有向上一念,要求合理的生活。
理性是人类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厚爱与自信就来自于他在其中所“发现”的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到处是理性的凝聚或流露,这样的例证实在太多。
“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5](185)在中国传统社会,士人虽不事生产,但却居四民之首,其绝大功用就在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士人介于君主与众庶之间以为调节缓冲,他一面规谏君主约束自己,薄赋敛、少兴作,而偃武修文;一面教训百姓忠孝和睦,各尽其分,而永不造反。总之,理性高于一切,教化事业随以尊崇,士人的最高志向就是作“王者师”“众人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其侧重点无疑在“理”字上。这个“理”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所在:
人类有其一极强要求,时时互以责于人,有时亦内以讼诸己。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这便是所谓理。……此即人类所以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呜呼!对也,合理也,古今几多志士仁人于此死焉,于此生焉!人类生命之高强博大于此见焉!使人类历史而不见有此要求于其间,不知其为何种动物之历史也。[6](168-169)
梁漱溟的理论创造或特色之一就是将理区分为物理和情理。所谓物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不以人的情感爱憎意志向背为转移,我们因经验积累而得以认识它,行事有当于此则其事可成,无当则无成。所谓情理,著见于我们主观情感的好恶和意志的向背,如正义、公平、信实、忠诚等等,若行事有当于此则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对于物理的认识,不容稍存主观上的爱憎迎拒,但对于情理来说,离却主观上的爱好憎恶便无从认识。简言之,辨察物理靠理智,体认情理靠理性。他以理性与理智的或长或短来判定中西两方文化的或优或劣未免失之简单和武断,但他对价值理性的肯认与追求却具有深远意义,其理论目的在于以理性的方向感消除意欲的盲目性,从而把意志的巨大力量与理性的向上之心更好地结合起来。士人即为理性的集中代表,其内化于本心和外显于社会者均以理性为旨归。
二
对于何谓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梁漱溟曾给出侧重不同的定义。所谓知识阶级,“盖有机缘凭藉,得受高等教育,能挟高文典册,以享高等生活者是已;……其操业虽千百其途而不同,然其为玩弄智慧弋取大利则无不同也。”[2](795)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领导教化之责,很能超然照顾大局,不落一边。”[5](482)前一定义以文言的形式反映了知识阶级的现代色彩,后一定义则以白话的形式保留了知识分子的传统意蕴。
要较为准确地把握梁漱溟关于知识分子内涵的解读及其情感倾向,尚须明了传统之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有其特殊的职业取向和品行要求。就职业取向来说,士而出仕则为治人之官吏,农工商则为治于人者。尽管官吏数额至为有限,但士以官为业是一种明显的趋势。梁漱溟认为,传统的出仕之士于享名为常,于享权为暂,于享利最违远,这是与世人所称贵族显然不同的。就品行要求来说,士之一流既为社会所尊崇,尽管刁生劣监不乏其人,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律之者严于常人,他们的自律也不得不严,确有“为齐民矜式”的形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欧美近代文化的影响日深,传统之士与农工商之间的沟界逐渐消失,士的职业不只在政治教育领域,学为农工商者也就是士,而士为农工商之学者也就是农工商,唯有劳心一义为古今士人之通义。传统之士耻言利,而今日知识分子则竞言利,以至即士即商,即商即士。对于知识分子因时制宜的诸多变化,梁漱溟并非不能接受,他所义愤者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原有之美点既失而劣点弥彰。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未必合理,然而士农工商在其中各有位置,颇见匀称,关系巧属,无大偏倚,与今日的状况相比较为合理。欧美近代文化移植中国的后果,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均衡,而且构生出新的弊病。欧美知识分子不必皆求仕,而中国传统之士皆在求仕,于是大学毕业者、东西洋留学回国者无不求仕。欧美知识分子不耻运锤操械,而中国传统之士则以此为耻,于是学为农工之学者也不肯作此老实生活,而偷袭其为士之旧习:
凡今受高等教育得具学识者,其有能用其所学,创业致富,成其所谓玩弄智慧弋取大利,盖真其中之好者也。盖百分居一也,千分居一也。其大多数悉趋于谋差混事之一途,以苟且偷生焉而已。此则又为欧美近代之所未见也。……此即上不能为富且贵之士商,下不能为贫且贱之农工,进不能如欧西之所谓知识阶级,退不能如往昔中国之所谓士,历年由中等以上教育,暨东西留学所产生之人物之大多数,为社会病者是已。[2](797)
二是士当讲求品概行修的根本观念荡然无存。这一点尤其令梁漱溟难以释怀。中国传统之士对品行的讲求既为众人所共认,也为本人所自认。尽管士风士习的好坏时有不同难有一定,但士当讲求品行的根本观念是牢固不易的,现今知识分子所讲求者却在知识而不在品行。梁漱溟认为,要社会中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人特别讲求品行,而其他人则不必如此,这本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观念,的确应当改变:
然所以易之者,当在去品高(谓士)品低(如工商)之谬见,而一例尊重,同样讲求。非徒去士之讲求立品,而同不讲求之谓也。[2](798)
对于当时士风士习无以复加的败坏,梁漱溟深表不满:
抑何俨然为人师长者之不自爱不自重一至于此也!抑何受高等教育为大学学生者之不自爱不自重一至于此也!国会议员也,省会议员也,在此昔皆所谓士大夫也,其在议场则市井无赖不啻焉,其在私室则市侩贱人不啻焉。[2](798)
知识分子天然适合去做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但士人既有为众人之师的传统使命,又有为社会之贼的现实危险,“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于此二途,必当有所选择。”[5](482)为师或为贼的选择,在梁漱溟看来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三
尽管梁漱溟以其特有的儒家道德贵族气质对知识分子的蜕变多有不满,但基于对中国问题特殊性的认识,即中国问题是民族性的问题,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于是知识分子、教育功夫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要件。因此,他坚持认为,“一社会知识智力之士,是其社会头脑心思之所寄,社会众人离他不得。”[6](215)自中国问题构成之后所有的民族自救运动,有两种不同的发动形式:一种是由通习外面世界情势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一种是由不通外面情势的内地无知农民发动的。前者之病在虚见,后者之病在盲动。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知道问题的灼点所在,梁漱溟指出,这一灼点就在知识分子与农民。“余为数十年来中国问题之所以不能有解决,即由于此两种动力,上下不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分而为二。知识分子做外国的梦,做上层的梦;农民做自己的梦,做下层的梦。始终背道而驰,各不相谋。”[6](485)知识分子虽然在解决中国问题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它不能单独解决中国问题。知识分子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与农民联起来、为农民而说话、以农民作后盾不可。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原本是一大乡村社会,中西文化相遇所引发中国社会变化的结果就是乡村破坏。知识分子唯有在社会出路中有自己的出路,而中国社会唯一的一条生路,首先必须尽力于复兴农业生产,求全国经济的复苏;然后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经济建设。质言之,社会的生路要在乡村求,知识分子的生路也要在乡村求。从当时社会变迁的情况看,好像当初有意地将乡村子弟引出来,现在又送回去。当初若不出来,则不能与西洋文明接气而逼成乡村崩溃;现在若不回去,则不能发动乡村运动以建设新社会。在整个乡建运动的方案设计中,梁漱溟赋予知识分子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力主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去甘肃陕西等地留学,这样对知识分子和农民来说是两利双赢的事情。在构成村学乡学组织的四部分人当中,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或称乡村运动者,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他们以阖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而尤以推进社会工作为主,其地位和作用不容替代。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好像没有用处,然而他们回到乡下却至少有两大作用:一是为乡村扩增了耳目;二是为乡村增添了喉舌。梁漱溟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好比一个巨人,农民等于是他的躯干,知识分子则作他的耳目,作他的喉舌,作他的头脑。两面彼此互不能缺少。”[1](884)
抓住农村就是抓住全社会;抓住潮流、守定社会就是一大力量;唯社会有权而后国权乃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漱溟总是以“社会人”或“第三方”的身份思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于形成一个社会意志,以改变分裂的局面而建立统一的国权。他相信理性就是极大势力,能代表大多数人的要求,更是势力,他断言:
如果社会方面不能形成一大势力,隐然为主宰,则盼望政府是空的,加入政府也未必不是空的。打倒政府更是白费!翻过来说,如其代表政府的此一大势力形成了,则盼望方不是空盼望,而构成势力可以发生结果;有机会加入政府故能发挥抱负,不加入政府也能发挥抱负;政府将顺着社会的要求走,更用不着打倒它。[5](519)
与之相适应,梁漱溟将知识分子视为增加社会份量的重要砝码:
因现在所苦就是上重下轻,社会太没力量。大家都上台,则社会愈空。坐在社会一面,隐持清议,比较自己任一部长亲理行政所贡献者要大的多。并且照我们所计划的,在野不徒主持清议而已。树立起来乡村运动的联合中枢,就隐然为此一大社会的总脑筋。果有抱负,非不能施展。[5](487)
按诸梁漱溟的一生行事,他作为社会人的思考与努力的确值得称道。
四
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其志业在教育,其恒心也在教育,以教育改造社会,倚重知识分子为众人之师的主体道德选择,这是梁漱溟教育伦理的突出特点。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无疑是一个具有恒久意义的话题。“梁漱溟为知识分子在乡建中规定的这种作用不过是最后表现了他和乃父思想中那种不断发展的气质:儒家道德贵族对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感。”[3](145)梁漱溟把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力归结为人类的向上心,亦即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这一结论的局限与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强调知识分子的理性使命、社会立场和品概行修却并非无病呻吟,知识分子既可为师,也可为贼,这其中的确有一个严肃的道德选择问题。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智力活动颇为特殊,它要求其主体始终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不能把自己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他们所从事的看似个体性很强的精神生产,实际上却有着很强的公共属性。“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7](3)梁漱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指出知识分子为文化所寄托,负有培养、补充、建造文化的无可旁贷的责任,而且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相当深刻地主张知识分子要下乡与农民结合,要去甘肃陕西等地留学,充分发挥耳目、喉舌、主脑的作用,这样就为他们绽放理想之花找到了现实的深基厚壤,为他们履行神圣职责发现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台湾的纪刚先生曾尖锐地指出,传统的诚、正、修、齐、治、平的文化模式,在今日看起来似乎是发育不全,架构简缺。“一个人出了家门便入国门,忠孝双全便可成为完人,所以传统中国有优良的‘家庭人’‘国家人’,而独缺‘社会人’。”[8]梁漱溟明示并坚守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身体力行并热切期望知识分子代表理性、代表潮流、代表多数、代表社会,型塑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实践品格和精神骨架。
孔子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梁漱溟的思想期待仍然如古圣先贤那样豪迈和高亢。当今知识分子能否承继并弘扬这一优良传统,以体现自身的价值、时代的斯文和民族的希望?有人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有拍案而起的、有洁身自好的、有随波逐流的、也有为非作歹的。尽管这种划分或有粗糙、偏激之处,但屡屡暴露出来的问题已不容我们高高挂起。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的集散之地,诚然,他们在事实层面须臾不能离开社会,但在价值层面却不能一味屈从社会而须引领社会。教育的本质或基础在于道德,广大教师不只是学生的学业导师。传道、授业、解惑是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有机整体,而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事之道的传授与激发也许更为关键和难得。追求人生意义、坚守社会立场、服务广大民众、讲求品概行修,做健全有力的“社会人”,这应该是梁漱溟知识分子观中有助于我们反思和提升知识分子价值追求的积极因素。
[1]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六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2]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 艾恺.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4]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5]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6]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7] 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 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8] 纪刚. 我们原缺社会人[N].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981-07-03(241).
The research on Liang Shuming’s intellectuals thoughts in perspecrive of ethics
LIAO Jizhong
(Centre for Applied Eth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Liang Shuming’s notion of intellectuals is part and parcel of his particular education view. Intellectuals may confront the fast moral choices of either being model of world or being pest of society. It is believed by Liang that intellectuals should be well rational, noble, practical and educational, and t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pursue the essence of life, to hold steadfast their social standpoint, to serve the commoners and to cultivate personality, and that is the norm of genuine “social being” with sound and vigorous personality. That is surely the positive part of Liang’s notion of intellectuals deserving reflections and further enhancement.
Liang Shuming; intellectuals; moral choice; social being
B26
A
1672-3104(2014)01-0132-04
[编辑: 颜关明]
2013-04-11;
2013-12-05
廖济忠(1968-),男,湖南石门人,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伦理思想史,高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