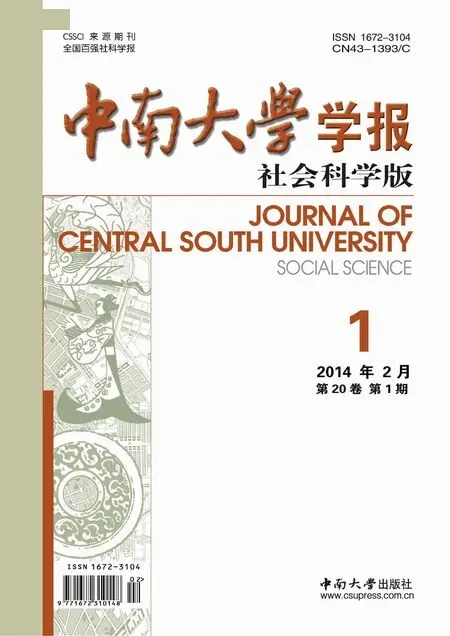合同解除效果:《合同法》第97条的解释论
2014-01-23靳羽
靳羽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1120)
合同解除效果:《合同法》第97条的解释论
靳羽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1120)
关于《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学界历来有“直接效果说”“折中说”“区分说”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司法判例亦长期不统一。在我国现行法体系内,有体物、受领劳务及金钱返还义务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在正当性基础、要件事实方面均存在差异。在标的物毁损灭失场合,因风险负担规则的介入,以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解释此时的返还义务亦不够妥当。但是,“直接效果说”与“折中说”的差异不应过分夸大,两者的区别更多地体现为逻辑自足性的优劣,从实务效果角度观察却并无根本性区别。
合同解除;溯及力;返还义务;不当得利;损害赔偿
“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这一规定历来被视为“合同严守”原则的经典阐释。然而,有“一般”就有“例外”,“合同严守”并非意味着永恒正义,为避免特定态势下的非正义结果,法律有必要在矫正正义导向下进行相应制度安排。合同解除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正在于此。但是,对于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过于原则而缺乏可操作性,实务见解颇不统一,学界亦长期争论不休,有必要寻求妥适的解释路径。
一、实务乱象与学界争议
归纳各地判例及学者见解,当前争议焦点集中于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和损害赔偿范围两个问题上。
(一) 实务乱象
1. 案例梳理
案例一:在“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解除合同的同时,判决“新宇公司赔偿上诉人冯玉梅逾期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过户手续的违约金及其他经济损失68万元”[1]。
案例二:在“桂冠电力诉泳臣房地产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是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解除合同的后果,违约方的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表现为支付违约金……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泳臣房产赔偿桂冠电力损失1 000万元。”[2]
案例三:在“仙源房产诉中大中鑫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据该违约责任条款,只要中鑫公司违约,就应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仙源公司还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至于是选择解除合同还是选择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则是仙源公司的法定权利。”[3]
2. 案例解读
前述三个案例均刊登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倾向性意见。然而,三个《公报》案例体现的倾向性却并不明确亦不清晰。案例一、案例三未言及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但是均认可合同解除后违约金条款的效力;案例二则指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进而否定合同解除后违约金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买卖解释》)第26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不影响合同中违约金条款的效力。至此,合同解除后违约金条款的效力问题得以最终明确,鉴于违约金的性质是当事人双方预先估计的损害赔偿总额[4],因此可以肯定《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应当是指对履行利益的赔偿。但是《买卖解释》仍然未言及合同解除究竟是否具有溯及力,以至于各地法院的判例很不统一,有的认为“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①,有的认为“合同解除对租赁物已使用期间无溯及力”②,有的认为“合同解除对之前已经履行的部分无溯及力”。③可见,《买卖解释》的出台并未平息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的争议。
(二) 学界争议
1. 学说梳理
(1) “直接效果说”。认为合同因解除而溯及地归于消灭,尚未履行的债务免于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发生返还请求权[5]。依照此说,原已履行之给付,现成为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或所有物返还请求权[6]。
(2) “折中说”。认为对于尚未履行的债务自解除时归于消灭(与“直接效果说”相同),对于已经履行的债务并不消灭,而是发生新的返还债务[7]。
(3) “区分说”。认为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种类、履行情况、合同目的等因素确定是否赋予解除以溯及力[8]。
2. 学说解读
“直接效果说”曾经是德国学界通说,亦为德国旧民法所采,但根据权威学者的解释,该说目前在德国已遭淘汰,学界通说已转向“折中说”[9],并为2002年新修订的德国债法所采纳[10]。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及最高司法机构均采“直接效果说”,但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立法及司法顺应潮流,改采“折中说”[11]。《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CISG)第81条第二款系关于合同解除效果的规定④,该规定并未言及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但是据日本及韩国权威学者的解释,合同解除并非使合同溯及既往归于消灭,只是使合同主义务“转换方向”,明显转向“折中说”立场[12]。采纳“区分说”的立法例以《意大利民法典》最为典型,该法第1458条明确规定,持续履行或定期履行合同的解除不具有溯及力[13]。
二、“恢复原状”与不当得利
《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恢复原状”内涵如何直接取决于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直接效果说”以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为逻辑起点,认为“恢复原状”请求权是指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折中说”以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力为逻辑起点,认为“恢复原状”请求权是一种不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债权请求权⑤。
(一) 正当性基础
依照“直接效果说”的见解,合同经解除而溯及既往的归于消灭,因此,合同解除前各方自对方所受领的给付,系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该损益关系的发生自始欠缺法律上的原因,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恢复原状”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我国现行法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规则的规定是《民法通则》第9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31条,核心意旨均指“没有合法根据”。所谓缺乏“合法根据”,在依合同给付的背景下,如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嗣后被撤销,给付人履行给付义务缺乏依据,受领人受领对方的给付亦缺乏依据,因此受领人应当将该缺乏依据的受领予以返还,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易言之,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给付依据的欠缺。再结合《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的规定,就合同无效、被撤销的效力结构进行分析,合同无效源于合同内容危害公共利益⑥或他人利益,撤销权的产生源于撤销权人意思表示不自由、错误或者权利义务分配的显失公平。这两类合同触犯了法律容忍的底限,所以法律对当事人所欲实现的法律效果实施彻底的否定性评价,将无效合同视为自始不存在、令被撤销合同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从而有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产生。
但是合同解除的情形则并不具备产生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分别是合意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的规范基础,其中合意解除系缔约双方意思自治的产物,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当依缔约双方的意愿,法律自无干涉的必要。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则源于特定事由发生后,解除权人有效行使解除权。所谓“特定事由”或者是《合同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或者是第94条以“合同目的落空”“根本违约”为核心的四种情形。前述事由一旦出现,解除权人得依《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程序,根据单方意思表示行使解除权,故解除权属形成权性质。权利人是否行使解除权以解除合同,当依其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而难谓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虑,无论约定条件的成就还是目的落空、根本违约的出现,均仅与缔约双方利益有关,而与公共利益无涉。因此,如果将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与合同无效、被撤销的法律效果等同视之,实质上是对解除权人“思想境界”的“人为拔高”。其次,如果赋予解除权行使效果以等同于合同无效、被撤销的效力,无异于赋予解除权人以可依单方意思对相对人实施否定性评判的权力,从而有悖缔约双方地位平等原则。再次,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的规定,当事人仅得向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而不能依当事人单方意思决定合同命运,从而与合同解除规则迥然不同。此种差异绝非立法者无意识为之,而是立法者实施价值判断后有意识的区别安排,亦即合同无效、撤销事关合同“生死”,因而应慎重处理,而解除则尚未达到决定合同“生死”的程度,故可根据单方意思决定。因此,如果合同解除与合同无效、撤销的法律效果一致,无异于是不当放大了合同解除事由的严重性。
(二) 要件事实
《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核心构成要件是欠缺合法给付依据。因此,论证合同解除返还义务的产生是否必须具备“给付依据欠缺”,或曰合同自始无效这一核心要件事实,就成为判断其是否属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关键环节。
1. 自始无效并非所有返还义务的发生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发生受领人承担返还义务的法律效果,但是,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被撤销与返还义务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即不能认为《合同法》上任何返还义务的产生均源于合同无效、被撤销。现行《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返还义务的条文共17条,使用“返还”术语达25处。就该17条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合同法》规定返还义务产生于以下三种法律事实:第一,合同无效、被撤销。第58条、第59条是为最典型体现。第二,有效合同履行完毕。如第十二章“借款合同”项下规定的5个关于借款人返还借款义务的条文、第十三章“租赁合同”项下第235条规定的承租人承担返还租赁物义务的条文均是有效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生的返还义务。第三,发生履行障碍。如第115条关于定金返还规则的规定、第314条关于货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承运人向托运人返还已收取的运费的规定均是因发生履行障碍而产生的返还义务。“违约”“不可抗力”与“履行障碍”是种属关系[14],前者涵盖于后者的概念外延之内。但是,第115条与第314条各自规定的“障碍”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第314条规定的“障碍”是因不可抗力致“合同目的落空”,从而有法定解除权的产生;第115条规定的“障碍”则未必达到“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落空”的程度,因而该条款所规定的返还义务可能发生于当事人根本违约或未根本违约两种情形之下,而仅有第二种情形方产生合同解除权。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返还义务的发生与合同效力如何并无必然联系,并非任何返还义务均是因为合同无效、被撤销所导致。其二,既然不可抗力致“合同目的落空”“根本违约”涵盖于“履行障碍”范畴之内,那么因合同法定解除所产生的返还义务就应当与前述“履行障碍”所发生的返还义务具有相同属性,而与合同无效、被撤销所发生的返还义务的性质相异,否则即是论证逻辑错误。
2. 自始无效并非所有免除效果的发生要件
《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学理上称这项解除合同的效果为免除效果[15](51)。《民通意见》第131条并未根据受益人善意与否而对返还范围进行区分,我国学界通说主张回归传统民法,受益人善意且其所受利益已经不存在的,免除返还义务⑦。“直接效果说”认为,不当得利受益人不能返还原物而免返还义务,既然是以合同自始无效(无法律上原因)为前提,则只有使经有效解除的合同是自始无效,才能发生这项给付义务免除的效果[15](57)。但是,《合同法》中诸多关于免除给付义务的规定并非以合同自始无效为要件。现行《合同法》共有3个条文规定给付义务免除效果,发生该效果的要件事实有两类:一是债权人的意思。第91条第(五)项、第105条均属此类;二是发生不可抗力。第314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免除了托运人的运费给付义务。显然,上述免除效果的发生均非因合同自始无效引起。由此可见,并不是非得通过合同自始无效的手段才能实现免除效果。再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德国旧民法规定,自始客观不能给付的合同无效。2002年修订后的《德国民法典》第311a条第(一)项明确规定自始客观不能的合同有效,且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同样未将合同自始无效作为免除效果发生的要件事实。
综上,既然合同解除所生之返还义务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存在本质区别,且现行法中返还义务、免除效果的发生亦并非必须借助合同自始无效的手段才能实现,故“直接效果说”主张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就不无疑问。
三、“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与不当得利
“直接效果说”主张“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属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折中说”主张“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是特定情形下的“恢复原状”,不属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崔建远教授回顾《合同法》第97条的演变历程,将“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界定为三种类型:受领劳务的恢复原状、受领金钱的恢复原状以及受领有体物灭失时的恢复原状[16]。第一种、第二种类型的恢复原状与有体物返还并无本质差异,均不应归类为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前已论及,此处不赘。该部分着重从《合同法》有关解除与风险负担交错的典型条文出发,探讨第三种恢复原状的性质。
(一)《合同法》第148条与合同解除交错
《合同法》第148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该条文明显异于第142条“交付主义”的风险负担规则,其中蕴含的法律政策理由是,质量瑕疵引起的法定解除,是以另外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为要件,故另外一方当事人理应承受解除权人无过失行为的风险[17]。第148条虽未指明风险的发生时间,但依文义,无论是解除合同之前还是解除之后发生的风险,在所不问。因此,至少就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引起的买卖合同解除,可以适用第148条,由出卖人承担风险[18](64)。由作为解除相对人的出卖人承担风险,意味着出卖人须返还买受人已经支付的价金,买受人仅需承担返还现存标的物的义务,当标的物灭失时则无须承担返还义务。尽管从解释论的角度可以推导出这一结论,但是《合同法》将所有存在瑕疵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都分配给出卖人承担却未尽合理,因为标的物瑕疵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引发合同解除,但是却并一定会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后果。在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的场合,《合同法》第148条的风险分配规则具有合理性,而在两者没有因果关系的场合,此种风险分配规则就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基础。基于此,从立法论的角度论之,对于标的物并非因其本身的质量瑕疵而毁损灭失的场合,该风险仍应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解除合同后,应当向出卖人返还标的物折价款。
(二) 《合同法》第231条与合同解除交错
《合同法》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依据该条规定,租赁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际,承租人可以选择保持合同效力同时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亦可选择解除合同,问题是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如何呢?第231条对租赁物毁损、灭失风险采“出租人主义”,因此,合同解除后,承租人仅就现存租赁物承担返还义务。至于出租人的返还租金义务则应根据第231条前后两段区分为两种情况分别处理,第一种情况是合同解除事由出现前,租赁物可以正常发挥使用价值;第二种情况是合同解除事由出现前,租赁物虽有毁损,但尚未达到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现就这两种情况分别考察:
第一种情况。依照“直接效果说”,出租人继续保有承租人已支付的合同解除前的租金系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承租人,这岂不意味着承租人在合同解除前所获取的租赁物使用价值无须支付对价?为矫正该不公平状态,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合同虽溯及既往地消灭,但承租人须按照市场价标准向出租人支付合同解除前的租金,亦即出租人仅就高出市场价的租金承担返还义务,不足部分还可以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二是根据《合同法》第174条“买卖合同准用于其他有偿合同”的规定,适用《合同法》第164~166条规定的买卖合同部分解除制度,[18](65)亦即租赁合同的解除仅向将来发生效力,而不具有溯及力。两种选择相较,第一种过于繁琐,有叠床架屋之嫌,第二种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不仅具有实定法依据,而且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源于双方意思,以此为据亦体现对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
第二种情况。第231条前段规定,租赁物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但是该条并未规定承租人减少或不支付租金的要求一旦送达出租人即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因而法律赋予承租人的此项权利并非形成权,而应当是请求权,适用2年普通诉讼时效。如果在2年内,租赁物毁损状况进一步恶化甚至灭失,达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程度,根据第231条后段的规定,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且有权根据第231条前段的规定,要求出租人返还相应租金。如果第231条前段规定事由发生2年之后才发生合同解除事由,而出租人又提出时效抗辩的,则出租人无须承担解除事由发生前的租金返还义务,法律效果与前述之第一种情况相同。
综上,虽然我国《合同法》采取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并立模式,⑧但是两者亦存在交错领域,第148条、第231条即为典型。在该两个条文规定情形下,合同解除后受领人的返还义务相当复杂,既有可能是双向返还义务,亦有可能仅是单向返还义务,甚至返还义务范围亦因具体事由的不同而有区别,将之统统归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之内明显不妥,从而证明“直接效果说”主张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不无疑问。
四、“损害赔偿”的范围与性质
对于损害赔偿的范围,持“直接效果说”的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一是信赖利益;二是履行利益;三是期待利益及其他损害[7](524)。持“折中说”的学者认为损害赔偿范围以履行利益为主,也可以包括信赖利益、固有利益的赔偿[7](528)。民法上损害赔偿大抵有三种:履行利益损害赔偿、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呢?
(一) 是否属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侵权损害赔偿与违约损害赔偿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诸多交叉地带。例如债务人加害给付造成债权人固有利益损失、债务人违反合同附随义务造成债权人其他利益损失,此类损失是否涵盖于《合同法》第97条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内?首先,加害给付的情形。对于加害给付情形下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合同法》第122条采“竞合说”,规定受害方仅能选择行使一种请求权,对此学界颇多诟病[19]。事实上,加害给付背景下,合同效力如何并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时,债务人无给付义务而实施给付,且该给付属加害性质的,则其仍然须承担侵权责任。易言之,侵权损害赔偿的发生并不取决于合同有效成立与否,而是取决于符合侵权责任规范的要件事实。据此,从立法论的角度论之,《合同法》第122条采“竞合说”明显不当,而应当采“聚合说”,受害人既可以主张违约损害赔偿,也可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基于同样理由,合同解除亦不应影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受害人有权同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因而《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并非侵权损害赔偿。其次,违反附随义务的情形。《合同法》第60条第二款仅规定附随义务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并未明确规定附随义务是否属于合同义务。但是,参考德国债法修正意见[20],应当将附随义务界定为合同义务的组成部分,从而违反附随义务亦产生违约责任。据此论之,违反附随义务亦可能引起合同解除,但是无论是因违反附随义务引起合同解除还是因违反合同约定之主给付义务引起的合同解除,作为法律后果之一的损害赔偿责任均不属于侵权损害赔偿。
(二) 是否属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
部分学者认为,作为合同解除法律效果之一的损害赔偿属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代表性理由是:“自理论言,契约既因解除而溯及订约时失其效力,以该契约之效力为依据之请求权,包括请求履行及请求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的权利,皆当因之丧失其规范基础。从而在解除契约后,原则上自当只得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亦即只得请求缔约费用、准备履行契约之费用及准备受领给付之费用等因解除契约,而落空所构成之损害的赔偿而言以将解除权人之利益状态,通过信赖利益的赔偿,回复至缔约时的水平。”[21]归纳上述理由的核心意旨,既然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作为确定违约责任依据的合同已不复存在,因而此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应当是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合同法》第42条、第58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学界历来争议不断,一部分学者认为仅限于信赖利益,一部分学者认为还包括固有利益[22]。何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包括信赖利益。但是,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效力的关系,第42条与第58条的规定存在明显差异,第58条所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合同无效、被撤销的场合,而第42条则并未做出此种限定。依文义解释,在合同有效场合亦有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余地,且此种见解早已是德国学界及实务界的普遍观点。⑨有学者指出,就我国《合同法》而论,合同有效且成立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形最少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违反情报提供义务的情形;二是可撤销合同被变更的情形;三是因撤销权的消灭而变为完全有效合同的情形[7](129)。因此,合同效力如何并不影响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只要满足信赖主体、信赖客体、信赖表征、因果关系、损害后果及归责事由等成立要件[23],就有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空间。申言之,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与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的能否成立无关,无论采纳“直接效果说”还是采纳“折中说”,在此问题上并无差异。现在的问题是:《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是否包括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依照文义,该条将“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限制于合同解除场合,处于合同履行阶段,而信赖保护义务发生于合同缔结阶段,而且《合同法》已经于第42条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因而没有必要再于第97条再重复规定,此其一。其二,第97条并未如第42条规定有信赖关系的成立要件,因而,第97条所规定之“损害赔偿”的范围就不宜解释为包括信赖利益。
(三) 是否属于履行利益损害赔偿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以及《买卖解释》均肯认《合同法》第97条所规定之“损害赔偿”是指履行利益,但是均未指出采纳该见解的理由。现分别对两种学说所提出的理由进行评析。
针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0条的规定,⑩郑玉波先生曾经有一段精辟阐释:“我‘民法’上述条文,依其所谓解除权之‘行使’‘不妨碍’损害赔偿之请求等字义观之,可认为属于两立主义中之解除契约与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之两立主义,亦与法、日民法相同是也。盖既曰行使,又曰请求,可知两者系彼此对立;既曰行使‘不妨碍’请求,可知并非因解除权之行使,而新生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是原有之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因解除权之行使而受妨碍而已。依纯理论言之,原有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过为原债权之变形与扩张,原债权既因解除契约溯及的消灭,则其损害赔偿请求权,自亦应归于消灭……然而因债务不履行所生之损害,究属一种事实,解除权之行使,仅能消灭契约之效力,不能并此事实亦消灭之,因而倘不使其两立时,实际上难免不平,故‘民法’乃有如是之明定。”[24]崔建远教授亦指出:“违约损害赔偿并非合同引起,而是合同债务被违反的法定结果。就是说,违约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事实,不是合同而是违约行为。”可见,两位学者的见解基本一致,均认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与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的成立并不矛盾,亦即,损害赔偿请求权无须借助合同关系的存在,而仅需具备违约事实即可成立。
就合同成立、生效、履行、发生履行障碍直至被解除的整个过程考察,如果说合同解除是“果”,那么履行障碍的发生就是“因”,一旦发生“根本违约”性质的履行障碍,即发生两项法律后果:一是成立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二是成立解除权。解除权的形成权性质决定,其必须经有效行使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因此,就逻辑顺序论之,损害赔偿责任必然产生于合同解除之前。损害赔偿数额固然须借助于合同加以确定,但是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无论发生于其后的合同解除是否使合同溯及既往的归于消灭,均没有理由受到影响。因此,对于《合同法》第97条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直接效果说”“折中说”并不存在实质差异。
五、结语
合同解除的“直接效果说”与“折中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就《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效果进行解释,“折中说”具有更强的逻辑自足性。但是,两种学说之间的差异不应过分夸大,就作为合同解除主要法律效果之一的返还义务的性质而言,“直接效果说”主张的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与“折中说”主张的法定返还义务之间除了具有学理意义上的差别之外,有多少实践价值呢?毕竟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均属于债权请求权,行使效力上并无多少区别。当然,有学者主张如果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力,则双向返还义务之间具有功能上的牵连性,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此种见解看似很有道理,但仍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即便采纳“直接效果说”,合同因溯及地消灭而导致双方的返还义务之间不再具有牵连性,此时,法院有什么理由判决返还义务必须有先后次序呢?况且,理性的当事人亦必然选择同时履行返还义务,而不会在对方的返还义务尚未履行的情况下率先履行自己的返还义务。至于“区分说”则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方式,具有快速解决争议的优点,但是其缺陷也不容忽视,《合同法》既未规定“继续性合同”的概念,第97条亦未对返还效果做出区分的制度安排,故“区分说”不符合立法文义。
注释:
①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柳市民一终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永中法民三终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商终字第748号民事判决书。
④ 该条款规定,已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返还其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如果双方都须返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⑤ 根据“折中说”的主张,由于解除前的合同关系仍然有效,因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权利变动显然并不当然地复归,只是依据法律的规定,可因解除而发生恢复原状的义务和请求权,日本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以“恢复原状”为目的的债权关系。该种请求权并非物权请求权,故应为债权,只是通过这种债权来实现“恢复原状”的结果,实现权利的逆变动。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33.
⑥ 《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两种情形实质上亦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参见黄忠.违法合同的效力判断路径之辨识. 法学家, 2010(5): 53.
⑦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2条规定:“不当得利之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之原因,而起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负返还或偿还价额之责任。”
⑧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草案一度采纳“一元论”模式,但在2001年付诸表决的草案中,风险负担规则被恢复,继续保持并立模式。正在进行的《法国民法典》修改草案、《日本民法典》修改草案均采“一元论”模式。参见吴春萌.论合同解除与风险转移的关系—以CISG为中心.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4): 43.
⑨ 德国学者莱昂哈德(Dr. Franz. Leonard)于1896年率先提出合同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的见解,由于当时《德国民法典》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因而未能对立法产生影响。但是,该学说自1912年被德国判例采纳以后,即成为德国学界及实务界的普遍见解。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29.
⑩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0条规定:“解除权之行使,不妨碍损害赔偿之请求。”
[1] 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新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冯玉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J].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6): 21.
[2] 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泳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J].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0(5): 25.
[3] 最高人民法院. 广州市仙源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大中鑫投资策划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J].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0(8): 31.
[4] 韩世远. 履行障碍法的体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284.
[5] 崔建远. 除效果折中说之评论[J] .法学研究, 2012(2): 53.
[6] 林诚二. 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54.
[7]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8] 王利明, 房绍坤, 王轶. 合同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44.
[9] 王泽鉴. 不当得利[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15.
[10] 杨芳贤. 德国民法有关解除契约法律效果规定之修正[C]//林诚二教授祝寿论文集(下).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 2004: 136.
[11] 陈自强. 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J]. 政大法学评论, 2007(2): 67.
[12] 成升铉.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除制度模式的比较法史研究[J]. 崔吉子, 译. 清华法学, 2011(5): 47.
[13] 陆青. 意大利法中违约解除效果实证考察[J]. 法学, 2010(5): 41.
[14] 韩世远. 中国的履行障碍法[J]. 私法研究, 2002(1): 183.
[15] 游进发. 契约解除、回复原状与损害赔偿义务[J]. 台北大学法学论丛, 2010(4): 51-57.
[16] 崔建远. 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解答(下)[J]. 政治与法律, 2005(4): 43.
[17] 卢谌, 杜景林. 论合同解除的学理及现代规制—以国际统一法和民族国家为视角[J]. 法学, 2006(4): 58.
[18] 周江洪. 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J]. 法学研究, 2010(1): 64-65.
[19] 王荣珍. 对加害给付概念与救济的再思考[J]. 政法坛, 2005(5): 31.
[20] 姚志明. 诚信原则与附随义务研究[M].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 2003: 50.
[21] 黄茂荣. 债法总论(二)[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22.
[22] 王洪亮. 缔约过失责任的历史嬗变[J]. 当代法学, 2005(5): 21.
[23] 余立力. 论信赖利益损害的民法救济[J]. 现代法学, 2006(1): 36.
[24] 郑玉波. 民法债编总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442.
The effect of contract termin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97 of the Contract Law
JIN Yu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out the legal effect of contract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Law Article 97, academics has three different ways for explanations, namely, a direct effect doctrine, compromise doctrine and the distinction doctrine. In our current law system, there are physical things, taking delivery of services and the obligation to return the money to be returned with the unjust enrichment obligations based on legitimacy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factual elements. Where damage or loss in the subject matter, because the rules of the burden of risk involved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point while the return obligations are not quite proper.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m “direct effect doctrine” and the “compromise doctrine”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which reflected in more logical merits of self-sufficiency, but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effect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retroactive; return obligation; unjust enrichment; damages
D913
A
1672-3104(2014)01-0114-07
[编辑: 苏慧]
2013-06-14;
2013-07-14
靳羽(1981-),男,河南桐柏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法学,比较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