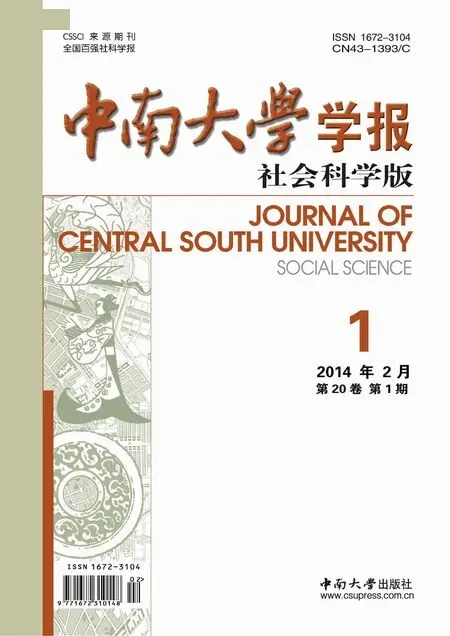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法律问题研究
2014-01-23刘长霞
刘长霞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48)
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法律问题研究
刘长霞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48)
现行国际法体系下,关于遇难船舶是否有权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国际海事组织在避难地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脱离避难准入权的单纯避难地的存在并不具有实质意义。鉴于绝对的避难准入权与国家主权原则存在直接冲突,遇难船舶避难问题更现实的解决路径是提高国际船舶标准及提倡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而非创设一种绝对的避难准入权。在国际法上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缺乏统一标准的大背景下,我国宜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进行适度干预。
避难准入;领海无害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船舶标准;船籍国责任承担
2012年7月14日,德国籍MSC Flaminia在从美国港口查尔斯顿到比利时安特卫普途中发生火灾并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地点在距离最近的陆地约有1000海里的大西洋中部。英国海岸警卫队收到事故信号后向所有航行于该区域内的船舶进行了通报。多艘过往船只对船舶及遇难船舶船员进行了救助。失事船上总共有25人,除1人失踪1人死亡3人受伤外,其余20人顺利由救生艇救出。在施救过程中,船舶不断向近岸移动,以期进入沿岸水域避难地进行货物驳运并得到维修。但直至8月13日,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允许船舶进入其沿岸水域避难,MSC Flaminia仍然在远离海岸240海里的位置等待。直至8月20日,MSC Flaminia在专家进入船舶并确认船舶完全安全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德国水域。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遇难船舶避难问题的关注。国家不允许船舶进入本国沿岸水域避难会导致船舶沉没甚至有意沉没于深水区域。2002年的Prestige就是在遭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拒绝后断裂沉入深海并引起了巨大油污污染。[1](53)
船舶遭遇海难后,如果能够进入沿海国避难地获得及时维修,则会大大降低海洋污染风险,无论对全球还是沿海国海洋环境的保护都是有益的。在早期航运时代,出于对人命救助的人道主义考虑,遇难船有权进入沿海国避难被视为理所当然。在今天可以用直升机等新的高科技单独救助人命的情况下,传统船舶避难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加之当前国际海运中,石油、化工等污染性产品运输逐渐增多,这类船舶一旦遭遇海难,往往会带来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威胁。实践中,沿海国迫于国内安全及环境保护压力,往往倾向于拒绝此类遇险船舶驶入其水域避难。
在当前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在遭遇海难后,是否有权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及解答,对我国遇难船舶能否进入他国水域避难,及我国面临这种问题时,是否有权拒绝他国船舶进入我国水域避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避难准入之法律规制
遇难船舶要进入的避难地往往设置在一国的内水及领海内。依据主权原则,国家对其领水享有绝对的主权权利,除非其承担了国际法上的义务,否则国家有权拒绝遇难船舶进入本国领水避难。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主要体现的是航运中船舶对避难地的需求与沿海国环境保护利益的冲突。因此,在避难地问题上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再明朗的情况下,要回答遇难船舶是否仍然具有进入一国避难的权利,有必要考察相关国际公约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所规定的权利以及沿海国所具有的拒绝难船进入本国水域避难的相关权利。考察我国所加入的当前有效的国际公约可知,①与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有关的国际公约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沿海国救助遇难人员的义务、船舶的领海无害通过权及沿海国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
(一)沿海国救助海上遇难人员的义务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权的分离
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已经成为一项确定的国际海商法原则。作为专门规范海上搜救的《1979 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即明确规定了公约各缔约国救助海上遇险人员义务。①除此之外,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8 条)、《1989 年国际救助公约》(第10 条)以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1条)均要求各缔约国应尽力促使其所属船舶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2004 年修正案)》则进一步规定了各国在海上遇险人员救助上的合作义务。
上述公约均规定了国家具有救助海上人员的义务,但其关注点在于人命及安全,而非发生海难时对船舶所应采取的处理措施。尽管这些公约没有明确排除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避难的权利,但这些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地为船舶规定避难准入权,也没有明确涉及沿海国建立避难地的义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人命的救助逐渐与对船舶本身的救助相分离,沿海国完全可以单独履行其人命救助义务,而拒绝接受遇难船舶。至少,这在技术层面是不存在问题的。
(二)“领海无害通过权”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法律支持
领海是一国在其沿岸行使主权的水域。在领海上的一切人和物均受该沿海国管辖。这是现代国际法所公认的。但自领海法律地位确立以来,沿海国一般都允许外国船舶在不损害其安全与良好秩序的原则下自由地通过领海,不征收通行费,不对通过中的船舶行使刑事和民事管辖权。这种优惠待遇,在国际法上称作“无害通过权”。[2](1)领海无害通过权作为对沿海国行使主权的限制,已经为相关国际公约所肯定。②那么领海无害通过权能否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的法律依据?为此,有必要从以下层次展开论证:
其一,对遇难船舶领海无害通过权的单独解读。
虽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领海无害通过权”原则,但对于遇难船舶是否可以进入一国港口或内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具有极大环境污染风险的遇难船舶通过一国领海进入其港口避难,是否属于“领海无害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8条及19条分别对“通过”和“无害”做了规定。其中,“无害”一词,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1项规定,主要是指当船舶通过领海时不会对“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造成损害。同时,该条第2项具体列举了12种有害通过的情形,其中第12项“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活动”是一项兜底性条款。
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是否属于“无害通过”,有学者认为,“除非污染遇难船处于无拖船前往救助的漂流状态, 否则,就仍属于无害通过的情形。”[3](82)该12项的列举是穷尽的、排他的,在不违反该12项规定的情况下,外国商船通过沿海国领海就应属于无害。美国和苏联1989年签署的《有关无害通过的国际法规则的统一解释》第三项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既然公约已经详尽规定了非无害通过的各种行为,那么,通过一国领海的船舶, 只要没有从事这些行为,就应视为无害通过。”[4](122)也有学者认为,荷兰行政法院在1995年的Long Lin案中表达了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为了将遇难船舶带入港口而通过领海不同于普通的航行目的,不构成无害通过”。④“通过”是一种穿越领海的临时活动,其对领海主权的限制仅在于领海可以作为船舶航行的中介而非船舶航行的目的地。⑤进入领海内的避难地显然不满足这种“临时”性要求。因此,无害通过权不能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的法律基础。[5](203)主张具有污染危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不属于无害通过权的学者,其理由主要在于遇难船舶通过领海不以“通过”为目的,而是以进入避难地为最终目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够驶往或停靠沿海国内水或领海的泊船处或港口设施以进行维修,防止海难的发生。如果这种最终的避难地位于领海内,则具有环境污染危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无害通过,但如果这种最终的避难地位于内水,则具有环境污染危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应视为无害通过,因为该停留只是以穿越领海为目的。
另外,有学者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1条的规定,沿海国可以以国内法的方式认定污染危险船舶通过领海为有害通过。从语义解释的角度上分析,公约第21条赋予了沿海国为保护本国的环境,以国内法的方式对领海无害通过权的行使方式进行限制的权利。这种限制应解释为按照沿海国所要求的方式进行通过,例如第22条的分道通航制。这一规定不应被解释为沿海国可以以国内法的方式自行确定“无害”的方式,并对“无害通过”进行自行解释。如果这样理解,则公约第19条从国际法层面关于无害通过权的规定就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当遇难船舶冒着发生污染事故或环境损害的危险航行时,如果其仅为进入内水的避难地而穿越领海,仅就其穿越行为而言,应该属于无害通过,沿海国不可以关闭外国船享有无害通过权的领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仍然是无害的,必须无歧视地给予各国船舶。
其二,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与领海无害通过权的理论碰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各缔约国采取措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同时要求缔约国在采取这种措施时,不能以转移污染的方式来保护本国的海洋环境。
准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污染的发生。然而,如果拒绝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结果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遇难船舶由于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导致公海环境污染;二是遇难船舶驶往他国水域进行避难。如果缔约国拒绝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而发生上述两种情况,则缔约国明显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要求的“不将损害或危险转移或将一种污染转变成另一种污染的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遇难船为寻求进入内水的港口避难而穿过领海固然属于无害通过,但是领海无害通过权对沿海国主权的限制仅限于领海内。如果遇难船舶即将驶往的避难地位于领海内,则领海无害通过权可以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避难的法律依据;如果避难地位于一国的内水,则遇难船舶能否进入沿海国内水避难仍受到沿海国主权的支配,单独的无害通过权不能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内水避难的法律依据。但是,基于国家所具有的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国际法义务,遇难船舶在无害通过一国领海后,沿海国不能拒绝其进入本国内水进行避难。当然,这里仅指沿海国不能以遇难船舶存在污染风险为由拒绝其避难请求。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与遇难船舶的领海无害通过权碰撞的理论分析结果是:国家具有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以防止污染转移的义务。
(三) 沿海国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及其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权的影响
国际公约在要求国家履行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时,也赋予了沿海国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即明确规定了沿海国为避免海难事故对本国海洋环境造成污染而采取措施干预海难救助的权利。⑥《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进一步赋予了沿海国在公海上的环境污染干预权,⑦并将沿海国这种在领海外的干预权限制在“有理由预计到将造成重大的有害后果”及“严重而紧迫的危险”情况下。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规定沿海国干预权时,则没有再提到这种限制。⑧相对于《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指出这种措施必须与可能发生的损害的风险及性质相称。这种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很显然,公约在这里主要是赋予国家相关权利,而不是为国家设定义务。在公海上对遇难船舶进行干预,最简单的措施是不准其进入管辖海域避难且令其驶离沿海国方向。更适当的反应通常包括拖船援助及救助服务。干预权的主要意义在于允许沿海国越过船主的意愿来提供帮助,使沿海国可以引导受损船舶离开它们的海岸。
在国际公约广泛赋予沿海国在领海外及公海上环境污染干预权的情况下,很难说国家具有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的义务。
二、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避难准入之法律困境
关于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现行国际公约均未做出明确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的探讨,只能从现行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中进行演绎推理。而通过分析,我们注意到上述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所具有的特点:① 制定和生效时间不同,缔约国不一致。② 立法主题不同,均没有直接规定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③ 前后公约之间的规定具体适用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时,存在冲突。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而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则赋予了国家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虽然这两者表面上不存在直接冲突,但具体到遇难船舶准入问题上,很难将两者做同一的解释。④ 同一公约的规定具体适用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时,存在冲突。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领海无害通过权与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相结合可以得出,遇难船舶具有进入一国管辖水域避难的权利。而根据同一公约赋予沿岸国的海洋环境污染干预权,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相关国际公约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规定的不一致,是否属于国际法上的条约冲突?条约冲突是整个国际法规则不成体系的一个具体体现,国际法学者鲍威林将这类冲突分为“固有的规则冲突”与“适用法律中的冲突”。前者是指两项规则中的一项其内在本质上与另一项相冲突,后者是指如果要同时遵循内容矛盾的两项规则或根据它们行使权利时,所产生的适用法律中的冲突。[6](315)在讨论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时所出现的国际公约规定的“冲突”,表面来看,似乎属于“适用法律中的冲突”。但仔细推敲可知,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条约冲突,所谓的冲突实质是我们在根据现有国际法规则进行推理分析时,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国际法规则没有对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以期得到答案。而国际法律体系缺乏明确的规范效力等级,这使得条约解释方法无法像国内法律体系中的解释方法那样,在规范等级明确有序的法律体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7](110)尽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第3款⑨和第4款(a)⑩确认了条约法中“后法优于先法”这一法谚,但这仅限于条约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中,而上述条约均没有直接规定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
在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的法律困境在于:一方面缺乏明确的国际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对现有国际公约相关规定的解读,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三、国际海事组织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的努力及其前瞻
遇难船舶避难问题涉及沿海国、船旗国、船主、货主、救助者、保险公司、环保主义者等多方利益主体,各利益方均强调危急情况下避难地存在的重要性。国家不希望本国船舶在需要援助时被他国拒绝避难准入,同时也不希望发生诸如Erika、Prestige这样冲击本国海岸的污染事件。在当前国际公约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规定不明确的情形下,解决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路径似乎只能是制定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法规则,这也是国际海事组织一直努力的方向。
鉴于当前国际法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规定的模糊性,意识到为遇难船舶提供避难地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IMO)在起草《1989 年国际救助公约》时,就曾提出设立避难地的想法,认为沿海国有义务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港口避难。尽管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代表的赞同,但其他代表在质疑将这种公法性质的内容加入私法中的可行性的同时,强调在类似条款中,沿海国的利益应当被充分考虑。作为一种最终的妥协结果,公约第11条规定了当事国在海上救助中的合作义务,其中包括在做出是否允许避难船进港的规定或决定时,应考虑各方合作的便宜及保证救助作业的有效实施。尽管公约在起草时考虑了避难地的问题,但从公约的最终文本表述,我们难以得出沿海国负有允许遇难船舶进港避难的义务。加之公约第9条明确规定了沿海国在“合理预期”海难事故会造成重大危害后果时,对海难救助进行干预的权利。沿海国具有判断是否属于“合理地预期”的解释权,实质上公约将是否允许遇难船进入本国避难的决定权利最终留给了沿海国。因此,《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11条并没有解决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
1999年的Erika事故促使IMO在2000年成立了海事安全委员会工作小组,并于2003年通过了两项关于遇险船舶避难地的决议案,即《关于需要援助船舶避难地指南决议(第A.949(23)号决议)》和《关于海事救援服务决议(第A.950(23)号决议)》,为各沿海国家建立船舶避难地制度提供指导性建议。指导方针认为,在船舶遇险时,阻止进一步损害和污染发生的最佳方法是过驳掉船上货油和燃油,然后修复船舶损害,这种操作最好在避难地进行。但是指导方针并没有强制沿岸国提供避难地。即使各国依照(《遇难船舶避难地指南》,简称《指南》)设置了避难地,因《指南》明确规定“沿海国不负有接受遇难船舶的义务,国家在决定是否为遇难船舶提供避难地时,需要综合各方利益,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决定。”⑪所以,在《指南》下,不涉及人命安全的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避难仍取决于沿海国对其主权行使的自愿限制。
2000年“Castor”轮事故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致力于遇险船舶避难地问题的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向国际海事组织报告。很快,法律委员会以澄清国际公约中有关避难地问题的条款为议题,向各成员国海商法协会分发了第一份问卷调查。随后,法律委员会于2002年底向成员国海商法协会分发了第二份问卷调查,以确定各成员国是否同意在接收或者拒绝遇险船舶的情况下承担特定的责任,以及船东和第三方在特定情况下应承担的责任。随后,法律委员会组织了以“避难地”为议题的多次研讨会,讨论避难地建设问题的同时,讨论了遇难船舶是否有权进入避难地的问题。然而,除了2003年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两个决议外,并未形成其他有效的国际法规定。
以主权为根本属性的国家在对待环境的方式上存在很多与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相矛盾的地方。这个矛盾可称为主权与环境保护要求的矛盾。由于主权对外是独立的,因而具有屏障外部力量对国家内政干涉的重要作用。这种屏障作用使主权也可以成为抵制国际环境保护要求的理由和妨碍国际环境保护协调意志形成的障碍。主权对于国家独立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对于人类环境的消极因素。[8](305)允许遇难船舶进入一国水域避难,可以使遇难船舶得到及时救助而避免环境污染及巨额财产损失,其对保护全球海洋环境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主权原则仍是国际法的基石,主权背后的实质是国家利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为了‘全球利益’而牺牲本国利益”。[9](155)事实是,出于复杂的政治和环境因素考虑,沿海国几乎倾向于不接受受损船舶进入本国控制的避难地避难。一个典型例证便是,在2001年1月的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Castor海难事件发生后不久,Prestige海难事件发生前几个月),西班牙代表倡议避难港行动,并提议设立避难水域。随后,在面临Prestige轮可能存在的溢油时,为避免潜在环境灾难损害本国的国家利益,西班牙政府拒绝接纳遇难的Prestige轮入港,并将Prestige轮拖至远离西班牙的公海。
国际海事组织在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并仍在进行各种努力,然而至今仍未得出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殊国际法规则。避难地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沿海国允许遇难船舶进入避难,脱离避难准入的单纯的避难地的存在,并不具有实质意义。然而,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难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强制沿海国接受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请求。以“遇难船舶是否具有避难准入权”为核心创设相关国际法规则存在极大的困难性,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避难准入权”以国家主权为直接挑战对象。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防止具有极大污染威胁的船舶在遭遇海难事故时造成巨大海洋环境污染。国际海事组织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继续着眼于提高国际船舶标准及提倡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而对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权进行保留。对一些类似Erika和Prestige这样独立的事故进行个案处理,而不是强制所有遇难船舶(无论它们所面临的具体境况是什么)进入一个事先指定的避难地,[10]从而避开与国家主权直接相冲突的“避难准入权”。提高国际船舶标准,能以“预防”的方式防止或减少具有重大污染威胁的海难事故的发生;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在督促船籍国提高本国籍船舶标准的同时,又能使沿海国在考虑是否接收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时,减少对可能产生的巨大救助费用及污染治理成本无法偿付的担忧,增加接收遇难船舶入港的可能性。
四、结语:我国对遇难船舶准入问题的应对
当前国际法体系下,很难得出国家具有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避难的义务。相关国际公约也均未对遇难船舶的避难权做出明确规定。鉴于绝对的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权”与国家主权原则存在直接的冲突,关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特殊国际法规则至今仍未确立。
在国际法相关规则不明确的大背景下,是否允许外国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避难则应主要依据我国相关法律作出判断,然而,我国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依照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的规定,外国商船在因遇难等意外没有及时获得主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可以进入我国的内水和港口,但应在进入的同时向主管机关做紧急报告,并听从主管机关的指挥。而依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1条的规定,在船舶发生海难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我国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主管部门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在公海上因发生海难事故而对我国管辖海域造成污染或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主管机关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处置。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两部法律规定看似存在一定矛盾之处。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我国似乎允许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进入我国水域避难。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又赋予了主管机关拒绝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的水域避难的干预权。面对当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应如何处理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避难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制定于1983年,那个时候因海难事故而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没有区分一般遇难船舶与污染威胁遇难船舶是有情可原的。而《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于1999年,正值国际上几个重大海难污染事故发生,并造成极大海洋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之时,其明确赋予我国主管机关的干预权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国际法上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缺乏统一标准的大背景下,我国在处理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时,应根据后法优于先法原则,首先遵循《海洋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规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进行适度干预,决定其是否可以进入我国水域避难。
其次,适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特别是对《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的规定进行修订,在避难准入上区分一般遇难船舶与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对前者的避难准入可以遵循《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所确定的现有原则加以处理,而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的准入,则应确立与《海洋环境保护法》相一致的原则,赋予主管机关一定的干预权,由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注释:
① 我国加入的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相关的国际公约有:《1954年国际防止海洋油污染公约》《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78年议定书》《1973年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定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1979 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9 年国际救助公约》及《国际船舶安全操作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国际安全管理(ISM)规则)修正案。
② 《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附件2. 1. 10.
③ 参照《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14条第1款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7条的规定。
④ Raad van State Afdeling Bestuursrechtspraak 10 April 1995, Schip & Schade 1995, 95 (Long Lin).
⑤ Welmoed van der Velde, The Position of Coastal States and Casualty Ships in International Law. CMI YEAR BOOK, 2003: 480-482. http://www.comitemaritime.org/Uploads/Yearbooks/ YBK_2003.pdf, 2012年9月25日访问。
⑥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9条。
⑦ 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第1条第1款。
⑧ 参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21条的规定。
⑨ “遇先订条约全体当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第59条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使用之。”
⑩ “遇后订条约之当事国不包括先订条约之当事国时,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适用第三项(款)之同一规则。”
⑪ 2003年“遇难船舶避难地指南”第1.7条、第3.12条。
[1] 刘占魁. 从“千岛油1号”污染事件说起[J]. 中国海事, 2005(4): 53.
[2] 黄瑶. 陈致中国际法专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3] 李天生, 韩立新. 国际法体系下我国对污染遇难船的避难准入问题[J]. 法学杂志, 2009(12): 82.
[4] 金祖光. 论新海洋法公约下的海洋航行权[M]//赵理海. 当代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7.
[5] 陈梁, 陈亚芹. 不再涉及人命安全的遇难船舶沿海国避难的法律问题[J]. 中国海商法年刊, 2008(18): 203.
[6] [比]约斯特·鲍威林. 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M]. 周忠海, 周丽瑛, 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7] 廖诗评. 条约解释方法在解决条约冲突中的运用[J]. 外交评论, 2008(105): 110.
[8] 邵沙平, 余敏友主编. 国际法问题专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9] 慕亚平.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问题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0] Christopher F. Murray. Any Port in a Storm? The Right of Entry for Reasons of Force Majeure or Distress in the Wake of the Erika and the Castor [J]. Ohio State Law Journal, 2002,(63): 1465.
Legal analysis on distressed vessels taking refuge in coastal states
LIU Changxia
(Law School,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Right of entry in places of refuge for distressed vessels is not clear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has made great efforts on this issue. But single places of refuge without right of entry could not essentially solve the problem. Consider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absolute right of entry” and“principle of state sovereignty”, the practical solution is to rais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tandards and encourage flag state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establishing absolute right of entry. China should take a case by case style to appropriately intervene the entry of vessels which could bring great pollution.
entry in places of refuge; 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 through the territorial sea;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tandards; flag state responsibility
DF961.9
A
1672-3104(2014)01-0108-06
[编辑: 苏慧]
2013-01-06;
2013-07-10
刘长霞(1982-),女,山东新泰人,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海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