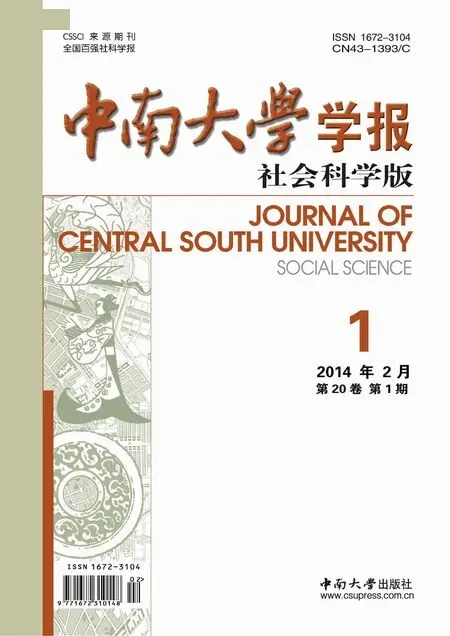自决权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审视
2014-01-23毛俊响
毛俊响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自决权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审视
毛俊响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自决权先后呈现出种族化、非殖化、集体人权三种历史形态。自决权从来就不具有一种既定的内涵与模式,它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与国际社会历史走向和现实基础密不可分。自决权也不应再局限于传统观念,而应该结合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而有所更新。维护民族关系的正义性是自决权的主要诉由,自决权本质上是一种包含内外两个面相的集体人权。行使自决权可能导致分离,但分离需要遵守一定的前提条件。
自决权;种族化;非殖化式的人民自决;集体人权式的人民自决;民族关系的正义性
人民自决经历了从政治思想到政治原则,再到国际法基本原则和集体人权的转变,并先后呈现种族化、非殖化、集体权利三种形态。①自决权发展的不同形态,对理解自决权造成了诸多困扰。特别是,有关自决权的主体、行使条件及其内容等问题,国内学者众说纷纭,国外学者也存在诸多歧见。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的争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关自决权的主体。例如,有学者认为,自决权的主体是处于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的民族及所有人民。[1]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自决权的主体范围包括所有主权国家的人民和所有其他领土上的人民的确立,包括殖民地人民、外国占领或统治下的人民、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和少数者人民这四种类型。[2]第二,有关自决权的行使条件。国内学者的传统观点是,在遭遇殖民主义奴役和压迫的情况下可以行使自决权。[3]但是,正如下文所言及的,一些国外学者对此加以了补充与发展。第三,自决权的内容。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自决权主要是针对外来殖民统治和奴役,但一些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对内自决的概念。②总之,有关自决权的概念比较混乱,这一情况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各国的不同反应上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自决权历史形态的多样化也不全是负面效应。至少,自决权发展的历史脉络也能给反思当代自决权提供历史借鉴。
一、自决权形态的历史演变
(一) 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
人民自决渊源于16~19世纪西欧出现的“民族—国家理论”。这种理论存在两种立论根据:其一,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合法性的源泉,国家的边界应该与民族的边界相一致,每个语言、文化不同的族体,都有权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4]这样的民族国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二,政治共同体是依据最高忠诚度而产生的,应承认由行使集体意志(如公民投票)来决定政治共同体命运的集体权利。[5]到了19世纪,基于民族—国家理念所引发的以反对民族压迫、反对隔断种族文化自然联系的帝国统治为内容的人民自决运动,几乎席卷整个欧洲。这一时期,被赋予自决权利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种族一词来理解的,它指的是那些具有某些共同传统和特征、共同语言或宗教和共同历史的群体。结果,19世纪欧洲的人民自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种族自决。[6]而其所形成的国家推至极致就是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谓的“部族—民族主义国家”。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在中东欧不断泛滥。民族分离主义者宣扬人民自决至上论,谋求脱离现有国家,建立以单一民族(或种族)为基础的独立国家。最为典型的、也最有争议的是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这种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运动,又回归早期欧洲的极端民族自由主义的立场,背离时代潮流并对现有国际关系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不可否认,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有其历史进步性,它最初是作为反对征服和压迫弱小民族的政治哲学而出现的。但是,在19世纪经过格宾诺、豪斯顿·钱柏林等人的发挥,以种族(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文化民族”)为单个主体的极端民族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出现,种族国家(菲利克斯·格罗斯称之为“部族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发端。[7](90-91)它强调建立国家的最基本单元是单一民族,认为为了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式,可以打破由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国内秩序。其结果必然会牺牲和平与安宁的国家秩序,使国际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并可能导致地缘政治的瓦解和种族清洗。[8]一方面,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民族疆界与国家边界合二为一的。国家之间将会因为民族的合并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划分疆界而产生无穷的边界争端。另一方面,种族主义或部族主义具有天然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性。纯粹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往往主张民族或种族的优越性,为种族主义运动提供政策合法性。种族主义过分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正当性,罔顾许多国家由多民族所组成并形成和谐国内秩序的历史和现实;过分强调单一民族组建国家的利益需求,漠视多民族国家维护统一的利益之所在。对于种族主义的危险,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阿克顿勋爵早就加以明确的批判,他说:“真正文明的生活之必要条件是将几个民族包括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就像不同成员之间的联系是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样”,“在政治疆界和民族疆界重合的地方,社会就停止进步,民族将重新回到不与他人交往的人们所处的封闭状态。”[7](94)因此,无论是从秩序,还是从正义,亦或是从多元利益保障的角度来看,种族化形态的人民自决都不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时代要求。
(二) 非殖化形态的人民自决
20世纪初,列宁和威尔逊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先后提出并积极倡行人民自决原则,并推动其演变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原则。人民自决原则真正被国家社会承认为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是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正式规定人民自决的国际条约,从而使人民自决原则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9]此后,非殖化背景下的人民(peoples)自决权被1952年《关于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的决议》、1960年《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的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所确认。联合国建立以来非殖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表明,自决权的主体已经从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文化民族或种族)转变为处于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外国奴役下的人民(一般指国族)。正是因为如此,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可谓是“国家”的自决权,或者说是反抗外来压迫、恢复独立的权利。
毫无疑问,受到外国殖民统治、占领和奴役的人民,有权行使自决权,获得民族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入其他国家或者与其他国家合并成立新国家,这是国际关系中民族独立与自由、主权国家平等价值的集中体现。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占领和外来奴役,都侵害了被殖民、被奴役人民自由选择社会发展道路以及为他们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固有权利。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应该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和平相处,基于追求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而行使自决权,本质上是恢复之前的独立自主或主权身份,也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正义化的基本要求。由此,自决权已经从形成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变为纠正殖民统治的历史非正义的方式。
当然,行使自决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现有秩序,但是它所针对的是非正义的殖民统治秩序。而且,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也须受到基于维护秩序价值(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限制。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自决权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再次重申此点认识。上述两个文件在维护秩序价值的同时又施加了基于国内民主和正义价值的限制。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该国家应保证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才可以依据领土完整原则限制自决权;《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强调,即只要这些主权和独立国家是遵从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的原则行事,并且拥有一个无任何区别地(without distinction of any kind)代表属于领土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府,才可以依据领土完整原则限制自决权。不仅如此,起源于拉丁美洲而后被非洲统一组织坚持适用于战后非殖化过程中领土争议的“维护殖民边界”(uti possidetis)原则也对自决权施加一定限制。基于有关国家是通过行使自决权而从殖民当局获得了独立或从原所属国独立出来,因此,这一原则通过维护一国的殖民边界来实现领土稳固,最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0]对自决权做出的上述限制,有利于防止自决权被滥用从而冲击一国正常领土范围内的社会或法律秩序,其目的还是为了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律体系。
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自决,它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自决。国际法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有关人民能够真正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自决和发展之间关系密切。[11](9)正是基于此种认识,1960年《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的宣言》在宣告人民政治自决权的同时,还强调所有人民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联合国大会1962年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1974年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决议又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经济自决的内涵。
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适用主体仅限于受到外来殖民统治或奴役的人民,在当前国际关系日渐民主化、殖民统治成为众矢之的的时代,其一度被认为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因此,一些学者主张一种广义上的自决权,认为自决权也适用于已经获得民族独立并已建立民族国家的人民或民族,其权利内容进一步拓展并包括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利,[12]这使得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与下文所提及的集体人权形态的自决权趋于相似。
(三) 集体人权形态的人民自决
20世纪中叶,在人民自决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与非殖化形态并行的还有集体人权形态的人民自决。195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和民族自决权是个人享有人权的基本条件。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统乐“国际人权两公约”)都在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所有人民(all peoples)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从集体人权角度重申了一切民族或所有人民的自决权。
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主要是由联合国大会决议所确认,而集体人权模式下的自决权则是由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加以明确规定。这种规范基础的变化使得自决权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既包括政治原则意义上的自决权,也包括法律意义上的集体人权。卡塞西教授就曾说,国际人权两公约使自决权突破传统内涵,从而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利,成为普遍人权的一部分。[13]它被宣示为一项集体人权,是有效地保证和尊重个体人权以及促进与加强这些权利的一个基本条件,其结果是将人权因素注入到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自决权之中,并使之成为一项具体人权。
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表述至少就集体人权形态的自决权传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自决权适用主体是作为集体概念出现的“所有人民”(all peoples),而不再局限于非殖化形态自决权的主体——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外国奴役之下的民族或人民。因此,它应该是人民自决权,而非“国家”自决权或“国族”自决权,这使国家很难再以传统自决权为由妨碍其治下的人民自由地表达政治意愿与寻求实现基本人权。第二,它泛泛地规定所有人民“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没有特地重申之前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所强调的非殖化背景。这表明,自决权不仅包含对外政治自决,还包括对内政治自决以及对内和对外经济、社会和文化自决。[11](24-27)它既包含了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又超越了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在对外方面,它关注政治、经济独立和不干涉,追求国家间主权平等和自由价值,旨在实现国际关系平等化和民主化。在对内方面,它关注民主和人权,承认一国内部人民政治上的广泛自治权和参与政治决策、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以及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体现对国内民族关系正义、民主政治、基本人权以及保障多元利益的价值追求。
二、自决权的当代审视
对自决权形态的分析表明,自决权的概念是多变的,不同的人或社会力量可以基于不同的目的对之做不同的解释。[14]在当前国际社会实践中,上述几种形态的自决权也都有一定的思想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种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多少带有早期欧洲种族化形态自决运动的魅影。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与此种思潮密不可分。不过,种族化形态的自决权在理论界没有多少赞成者,反而其危害性越来越被理性的民众所认知。非殖化形态的自决权被多份联合国决议所宣示、确认,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程度高,并演变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集体人权形态的自决权以国际人权两公约为规范基础,其内涵有待具体化。同时,它还被一些西方学者解释为包含内部自决和外部自决。对自决权的多种理解和实践,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自决权认识的混乱与多元,也削弱了自决权自身的稳定性。
在自决权形态的历史演变中,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自决权的主体不断扩大,从种族到殖民统治下的人民,再到一国内的所有人民;第二,自决权的形态不断演变,从分离权到独立权,再到集体人权。可见,自决权从来就不具有一种既定的内涵与模式,它的产生与演化与国际社会历史走向和现实基础密不可分。自决权也不应再局限于传统观念,而应结合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有所更新。
构建和谐世界有多种路径和价值层次。我们认为,它应以建立系统性国际秩序为前提,以实现综合性国际正义为关键,以保障多元化利益诉求为核心。首先,建立系统性国际秩序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前提。无秩序即不和谐,和谐世界存在于系统性国际秩序之中。系统性国际秩序强调从全局、系统的角度审视国际秩序,强调国际秩序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和动态性、自组织性,重视各种国际机制和影响要素的自身独特性及其交互作用,从国际和平与国内和平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来构建国际秩序。其次,实现国际法和谐价值的关键是实现综合性国际正义。秩序并非国际法的唯一价值,要想长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实现安宁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就必须保证处理国际关系的法律准则的正义性。实现综合性国际正义还需要切实强化以下两点: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实质性平等化和法治化。第二,要秉持自由与平等理念,维护并实现国内正义。这是因为,国内正义影响国内和平与安全,进而影响国际和平以及正义。国内正义是国际正义的基础。再次,实现国际法和谐价值的核心是保障多元化利益诉求。因此,国际法的原则、制度和规则体系,应该是尊重国家主权的国家价值(国家的自由和利益)与个人价值(个人基本人权与自由)、族群价值(少数者族群的自治要求)以及维护国际社会共同福利的全人类价值(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和谐统一。既要尊重个人的基本人权,也要保证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还要增进国际社会或整个人类的整体利益;既要关注眼前,保障当代人的物质享受,也要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以系统性国际秩序、综合性国际正义以及尊重多元利益诉求为主体内容的和谐世界观,为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自决权、消除自决权内涵模糊性与实践混乱性提供了符合历史潮流的理论视角。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当代自决权。
(一) 维护民族关系正义性是自决权的主要诉由
总体而言,产生自决权的根源主要是相关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或其一部分、民族、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者)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其折射到民族关系上面,就是民族关系失去正义性,进而产生自决权的诉求。民族关系的正义性,在价值层面上就是促进人民、民族或族群之间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基础上达致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在利益层面上就是尊重并保障国内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并使之处于一种协调有序的状态。维护民族关系正义性,包括维护国内民族关系的正义性和维护国际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正义性。
维护国内民族关系正义性,本质上就是要尊重各民族(或族群)在平等基础上自由发展、共享社会福利进而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在许多学者看来就是一种得到宪法保证并能切实实现的自治权。在政治领域,自治权是保障一国内部各民族或种族享有平等参政的权利。[15]民主和平等是自治权的重要内容,它通过在国内提供广泛的自治或给予有关人民或民族相应的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程序的权利来实现,它建立在民族关系民主的基础上。[11](25)在社会领域,自治权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权与平等权,特别是对少数者权利的平等保护,保障他们保持民族、语言、文化或宗教认同感的权利。
保障国内民族关系的正义性,能有效促进系统性国内和平秩序的构建。反过来,国内民族关系失去正义性,极有可能引发国内分离运动。当前,带有分离性质的人民自决运动的兴起并引发国内秩序的混乱,多与国内民族关系处理不当、民族政策失误相关。“即使某国的一个民族具备人民自决的主客观条件,只要该民族能在现有国家法律制度内,充分享受自治并保持其文化形态,国际社会就不愿意支持该民族的独立和该国的分裂。”[16]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及其政府越是充分保障对内的自决权,其主权的完整性就越加牢固。[12]可见,保持民族关系的正义性是消除极端分离主义运动、实现国内民族或人民和平共处与和谐共生的最好途径。
维护国际民族关系的正义性,或者说国际关系的正义性本质上是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权利,它针对的是外来殖民统治、占领或奴役。毋庸置疑,外来殖民统治、占领或奴役否定各民族自由选择发展道路、自主利用其天然资源或财富的权利,是一种违反国际关系正义原则的行为,严重违背国际法实现综合性正义和系统性秩序的价值要求。1960年《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的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所确认的自决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二) 自决权是一种具有内外两个面相的基本人权
自决权首先意味着一种集体人权,这为国际人权两公约共同第1条所明确,即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不仅如此,自决权还是个人权利的基本前提。早在1952年,联合国大会就在《关于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的决议》中强调,人民或民族自决权是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前提。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在其第12号一般性评论中认为:“自决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自决权的实现是有效保障和遵守个人人权以及促进及巩固这些权利的基本条件。”
从权利内容上来看,基本人权意义上的自决权具有内外两个面相。一方面,外部性的自决权是一种发展权,包含对外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发展权理念是从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权等概念中分流出来的,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是为非殖民化、民族解放、经济独立和发展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17]《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开宗明义地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人的发展权利意味着充分实现人民自决权,包括在两项国际人权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对他们的所有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不可剥夺的完全主权。”因此,在遭遇外来殖民统治、外国军事占领的情况下,所有人民有权行使自决权,以选择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应充分尊重相关人民行使的以独立为最终目标的自决权。这是一种“对一切”的义务,具有强行法的性质。[18]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了此种义务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在积极方面,每一国均有义务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以共同及个别行动,促进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原则之实现,并协助联合国履行宪章所赋关于实施此项原则之责任;在消极方面,每一国均有义务避免对民族采取剥夺其自决、自由及独立权利之任何强制行动。《发展权利宣言》也要求:“各国应采取坚决步骤,消除大规模公然侵犯受到下列情况影响的各国人民和个人人权的现象,这些情况是由于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和占领、侵略、外国干涉和对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战争的威胁及拒绝承认人民自决的基本权利等造成的。”
另一方面,自决权还是一种包含少数者在内的国内人民的政治参政权、经济自主权和其他基本人权,这是自决权的内部面相。这种自决权,在政治意义上主要就是尊重国内人民(主要是宗教、语言、民族方面的少数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自治权、民主权和平等权;在道德意义上主要就是被国际人权两个公约所确认的包括公民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政治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在利益层面就是充分尊重国内各阶层、各民族(族群)、个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充分尊重这种权利,有利于实现国内民族关系的正义性,实现国内社会的和平秩序,最终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完全否定这种权利,有可能导致分离运动或其他影响国内秩序的情势,最终会打破国内和平局势并危及系统性国际秩序。
(三) 尊重自决权就要承认分离的可能性
学界对于自决权是否包含分离权是存在争议的。卡塞西主张,多民族国家拒绝承认某一人民的情况下该人民有脱离国家的权利。[19]白桂梅教授认为,自决权不包括分离权。[20](58)但国际实践表明,国际法尚未肯定也未否定救济性分离权,国际法不承认单方面的分离权,但承认有关各方自由协议达成的分离安排。[21]例如,1999年东帝汶从印度尼西亚分离出来以及2011年7月苏丹南部地区通过和平方式从苏丹分离出来建立南苏丹国,都是相关各方达成自由协议的结果,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可见,自决权并不必然排斥分离,尊重人民自决权就要承认分离的可能性。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分离呢?有学者认为,应该根据政府民主程度来判定分离问题。从具有广泛性民主的国家分离出来的行为,不是一种行使自决权的合法方式;相反,从压制式的专制体制下分离出来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22]还有学者认为,如果国家大规模侵犯其统治下的人民的基本人权,有关的人民就可以行使自决权,从该国分离出来。[23]
我们认为,上述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需要做进一步补充。纵观历史上分离结果得到国际承认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分离运动的主要诱因是国内民族或族群关系失去正义性。例如,国内相关民族或族群被完全拒绝平等参政权导致最终被剥夺包括参政权在内的基本人权,或者国内相关民族或族群谋求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或利益诉求根本没有得到尊重。这些情况的持续存在意味着,统治者在行使国家主权的同时,根本没有负起主权权利所包含的保护基本人权、维护国内族群和谐关系的责任,其行为严重违背构建正义的国内社会秩序的基本宗旨。在这种情况下行使分离权,不应该受到国家主权的过分限制,否则将会纵容统治者躲在主权屏障内从事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国家主权意味着责任,即保护本国人民基本人权、自主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以及国内各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责任。这既是主权的应有之义,也是《联合国宪章》以及诸多国际人权公约所明确要求的。因此,特定情况下行使分离权既是民族或者少数者追求自由与正当性利益的充分体现,也是促进民族关系正义性的现实途径。
分离不是行使自决权的必然结果,分离行动可以因为导致分离因素的消失而停止。所以,分离是一种具有威慑性质的救济途径,可以成为推动中央政府给予寻求分离的相关人民自治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工具。分离权不能动辄使用,分离应该是最终的也是最极端的救济途径,是用尽所有国内救济途径之后为维护民族正义和基本人权所不得已采取的救济途径。实践中,一些分离分子罔顾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自治权或基本人权受到充分尊重或并没有遭到根本否定的事实而一味追求脱离母国的行为,不符合自决权的基本要求。
注释:
① 有学者认为,民族自决权经历了早期种族自决模式到非殖化自决模式,再到种族化自决模式的演变。参见茹莹:《世纪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与当代国际法的困境》,《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1期。本文作者受此启发,对该观点做进一步引申和补充,认为自决权先后经历种族化、非殖化和集体人权三种形态。
② 国外学者有关对内和对外自决权的讨论,参见白桂梅:《论内部和外部自决》,《法学研究》第19卷第3期,总第110期。
[1] 庞森. 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一些思考[J]. 国际问题研究, 1997(2): 37-44.
[2] 赵建文. 人民自决权的主体范围[J]. 法学研究, 2008(2): 133-148.
[3] 王献枢. 国际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50.
[4] 朱伦. 走出“民族——国家”古典理论的误区[J]. 西域研究, 2000(2): 107-111.
[5] Diane Orentlicher. Separation anxiety: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ethno-separatist claims [J].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8(23): 1-78.
[6] 茹莹. 世纪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与当代国际法的困境[J]. 太平洋学报, 2003(1): 19-27.
[7]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 王建娥, 魏强,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8] Jeremy Waldron. Two conceptions of self-determinatio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99.
[9] 杨泽伟. 国际法析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48.
[10] 杨泽伟. 论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J]. 法律科学, 2002(3): 39-51.
[11]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M]. 孙世彦, 毕小青,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9.
[12] 曾令良. 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J]. 中国法学, 1998(1): 109-120.
[13] 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 A legal reappraisal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3.
[14] Henry Steiner, 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Context: Law, Politics, Morals, Second Edi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48.
[15] Antonio Cassese. International Law [M].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7.
[16] 王凤波. 民族“自决”和国际社会的反应[EB/OL]. http://www. 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57-mcs-1997-issue -2/404-2011-12-29-17-45-11.html., 2013-09-22.
[17] 李蕾. 发展权与主权的互动是实现发展权的基本要求[J]. 政治与法律, 2007(4): 20-22.
[18] Louis Henkin.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M]. Minnesota: West Publishing Co., 1993: 306.
[19] 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 A Legal Reappraisal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0.
[20] 白桂梅. 自决与分离[C]//余民才. 国际法专论.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58.
[21] 赵建文. 人民自决权与国家领土完整之间的关系[J]. 法学研究, 2009(6): 174-192.
[22] Frederic Kirgis Jr. The Degreed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a Era [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4, 88: 298-321.
[23] Ved P. Nanda.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J].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2000/2001, 29: 305-336.
Evolution of forms and rethink of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MAO Junxiang
(Law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had evolved over three forms of racism, decolonization and collective rights. It never has changeless connotation and pattern, and it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depend on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onnotation of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should be renewed with the need of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world. The main appeal of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s to preserve the justice of national relation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consists of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Right to separation is part of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should be performed with some precondition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self-determination of racism; self-determination of decolonization; self-determination of collective right; justice of national relations
D990
A
1672-3104(2014)01-0076-06
[编辑: 苏慧]
2013-05-20;
2013-09-22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FX104);2011年湖南省社科规划基金(11YBA310)
毛俊响(1980-),男,湖北黄梅人,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