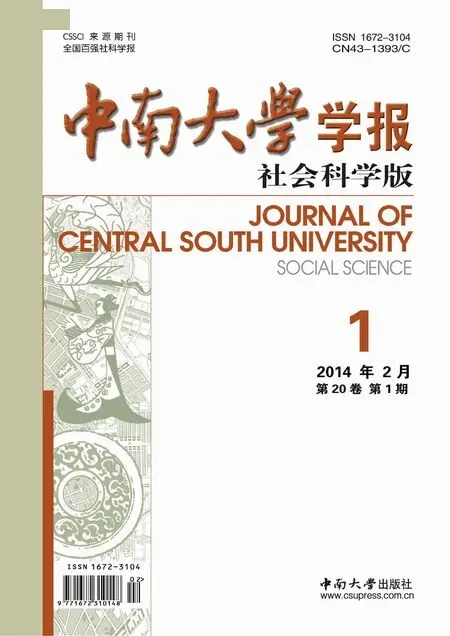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中国模式”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思与前瞻
2014-01-23陈毅
陈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中国模式”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思与前瞻
陈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表现出的显著特征,国家推动的发展战略以其“后发优势”引世界所瞩目。但是转型社会引发的复杂社会问题也在检视和挑战国家权威,国家自主性的合法性基础不仅体现在经济绩效上,而且更要体现在民众对国家的深度心理认同之上。国家自主性如何维系、如何克服自主性自身的悖论、如何吸纳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改革需求成为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必须要解决的时代难题。
中国模式;国家自主性;“国家退却”;转型社会;后发优势;国家权威
一、引言:关于“中国模式”及其国家自主性特色的争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关于“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北京大学的姚洋和潘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已成型,特色鲜明.姚洋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是指政府对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没有任何差别,这种组织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重合,也就是说,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增加它所代表或与之相结合的特定集团的利益[1];潘维认为,中国道路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他认为西方强调“分”,而中国强调“和”,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的“人民性”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总结中国模式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2](6)也有人认为在“猫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基础上的渐进改革在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原因分析也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也有很多人认为,目前总结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客观些说,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初具端倪,政党领导和国家推动的改革能走多远,还有待于执政党和国家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水平的提升。
当我们追问:是谁改变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形象,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呢?又是谁改变传统中国的面貌,走向现代化文明的现代国家呢?“救亡图存”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概念和巨大的凝聚作用,号召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的再次腾飞。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和民主的现代国家形象召唤着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开拓进取,是现代国家整合着利益冲突、引领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共识性目标而努力。
“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的鲜明之处在于:国家不是一个被遮蔽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发挥着国家的自主性。对于西方而言,尤其自近代国家出现以来,一部公民权利的增长史也是一部反抗国家权力的抗争史,国家作为一种“必要恶”的观念根深蒂固,国家总是处在被诅咒的尴尬境地,监督和限制国家成为西方基本政治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国家要么作为被反抗的对象而存在,要么以政治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而取代国家。国家自主性是被严重遏制的,国家更大程度上沦落为仅从工具性上或者从结构功能上来理解,仅仅把国家当做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博弈的一个平台,对于国家的轻视和敌视使国家成长和国家作用受阻。但是随着多元主义对国家的冲击和瓦解,整合民主冲突的共识很难达成,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福利国家阶段,过去那种对于小政府的赞美而在当今却是难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人们的需求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出现,一个集权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干预也就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趋势,这也是国家作为重要的“自变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原因,“国家主义”和“回归国家”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
而在中国,自从辛亥革命迈向现代国家以来,“为何要有国家?”“如何才有国家?”以及“国家应当何为?”[3](4)这三大根本性问题成为革命家和建设者思考的主题,国家权威和国家能力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国家的认识和国家职能国内也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方面,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和国家主义者试图赋予国家一种道德性和优先性,这给了现实的国家以超验理性的特质;另一方面,致力于限制国家权力……尝试将国家从神坛上拉下来,使其匍匐在社会之下,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结构。前者难以成为主流力量,后者难以获得主导机会,这使得国家行为的理性性质大为下降,现代国家建构的前景令人担忧。”[4](55)因此,在当下中国,国家何去何从,仍有待多方探讨。
二、要求“国家退却”的改革能走多远?
由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对于中央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也走了不少弯路。新中国成立之后,“照抄照搬”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尤其20世纪50-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中西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国家错过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让人们心中埋下猜忌、仇恨和恶斗的种子,这种阴影给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另外,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仅靠计划根本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用于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极其匮乏,什么都靠“凭票购物”的年代现在人们依然记忆犹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难有较大的改善,也纵容那些掌握有限资源分配人员的权力腐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停滞不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甚至受到打压,民营经济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由于国家核心决策层思想认识的偏差、策略选择的失当,也使得国家发展战略跑偏,走到不得不改革的境地。
的确,“分权松绑式”改革带来了市场生机和社会活力,市场繁荣、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极大改善和社会自治程度也越来越高。再加上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也使很多人认为市场化、“大社会小政府”的改革就是政府改革的目标,甚至鼓吹“国家退却”和“私有化”。然而,中国的改革并不是“甩包袱的改革”,医疗市场化和教育市场化等改革的失败教训说明“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即使我们充分看到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功效,市场有助于“把蛋糕做大”,但把“蛋糕分均”却需要国家“权威性的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减少利益集团的操纵都需要国家的干预。也可以说,只有在国家提供的法治秩序下,保持市场公平有序的竞争,才是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
对于社会自治而言,尽管传统、习俗和文化有助于社会自发秩序的传承,但是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传统的礼俗社会在世俗化的利益冲击下,千疮百孔,濒临瓦解,人们的精神家园日益失落,脑子里除了钱就没有其他什么了。而民主的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又没有形成,人们更多是向社会索取而很少对社会供给,积累的社会资本就很有限,必然从社会中获取的资源和自救就非常有限。这也是目前中央尤其重视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因所在。社会的确具有自我治理的功效,充当社会矛盾的缓冲剂和减压阀,但是,“治理社会”带来的成本与社会治理带来的绩效一样多,社会危机和社会失序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想当然的那样,形成自发秩序和自我修复。
当我们放大市场化和社会自治的功效时,我们是否又看到“市场失灵”和“社会失效”所带来的社会急剧不平等和社会失序呢。经济危机和无政府状态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又常常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境地。“经济救市”和“对社会的治理”就是人们渴望国家这方面的具体职能得以实现。20世纪80年代末那次危及国家政权的“六四事件”,使中央权威流失,“诸侯经济”的崛起也使中央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这也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的过度放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足以颠覆国家政权,也充分认识到维系政治稳定和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性。所以,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加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和完善分税制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确保社会主义道路在更加稳健的制度化渠道内有序前行,使国家职能归位到它最应该发挥作用的职能上来。
其实,无论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国家自主性建构和必要干预都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认为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彻底改革能造就西方式的发达,却没有想到在国家社会保障尚未建立之前强加自由化,在规章制度架构尚未树立前就促进私有化,在宽容信任文化和法制尚未形成前就要求民主化,结果是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衰退、社会矛盾的激化”[5](19)。“拉美现象”和“非洲危机”导致国内秩序的失序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很大程度是由于“国家构建”的失败,福山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的许多国家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家建构”,“国家构建这个议事日程……几乎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思考或者重视,结果造成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在许多国家未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确实,某些国家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框架,实行经济自由化后的状况比如果不实行更为糟糕”[6](5)。即便是“撒切尔夫人改革”和“里根改革”也是喜忧参半,到布莱尔和克林顿时代都选择“第三条道路”,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而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自摆脱殖民统治以来,选择威权统治和强化现代国家的秩序建设,以“后发优势”摆脱“发展依附陷阱”,走上国强民富之路。
三、国家自主性对超大国家社会转型的影响
对于超大国家的社会转型而言,“国家退却”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是把国家理解为实体化的国家机器,还是赋予国家绝对的伦理实体,也直接关系到国家作用的发挥。洛克给出了国家理性以限制性的规定,而在黑格尔那里“将国家作为绝对的伦理实体对待,使国家具有了控制性的力量,国家自身成为理性的象征,并提供给市民社会以德性规范和引导力量”[4](50)。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先赋予国家作为自主的伦理实体而存在,再考虑对其行为进行限制比较可行。因为人总是渴望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政教分离,“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精神家园总得找一个可靠的寄托,公共利益化身的国家最具崇高性。国家自主性就是国家可以依据“公共利益”垄断暴力性国家机器,以确保具有强有力国家行动的能力。国家自主性来源于国家的至上性、自足性和国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性,国族共识是凝聚不同族群的全国人民的心理基础,国家是一种精神象征,国家代表一种公共组织,国家也代表一套制度装置。具有的超越于个人和某一阶级的脱俗性、公共性和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这也是国家行动的依据和合法性基础。
超大国家的社会转型必然伴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又有谁能代表公共利益对其实施“整体性治理”呢?统一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统一的税制和统一的法律体系的确立又有谁能够供给呢?“改革开放成果共享机制”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权威性的分配又有谁来实施呢?……这些关系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都需求国家作为“自变量”参与政策议程的制定中来,也只有国家这一最具权威的组织能够担当此重任。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5年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有效地实现经济“软着陆”,很好地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随后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有“法治”保障的经济,在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国”建设,中国也走上了“依法治国”的制度化建设的道路。这样,通过国家自主性的政策议程的变迁,把转型社会的大国治理过渡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制度化治理的渠道中来,也使得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更加科学稳健,这些都是面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摸索出来的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
超大国家的社会转型找到了制度化治理的依托之后,也越来越显示其治国的能力和治理的绩效。诸如随着分税制改革逐见成效,国家财富积累越来越强大,也有能力通过财政杠杆来宏观调控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分配,减少东西部差距;也有能力并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逐步实现由“选择性普惠社保”向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的转变,使社会的弱势群体也能够有尊严地活着,以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革开放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国家也积极推进社会文明建设,鼓励和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帮助老百姓实现从“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以基层社区建设为依托,重塑具有多样性和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转型社会积累的社会弊病如果等到社会自我来消解又将何等漫长,而且与转型社会相伴生的贫富差距倘若越来越结构固化之后,利益集团将使减少这种差距的改革越来越艰难,也只有国家愿意和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发挥国家自主性对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才能更好地有助于打破贫富差距的结构化分化趋势。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时代发展到当今,应该转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最大政治”阶段,“把蛋糕分均”的改革要比“把蛋糕做大”的改革更艰难,但是这种基于心理的深度政治认同也要比基于利益交换的浅层政治认同更可靠、更持久。也有人指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国家的使命和政治合法性的新指向。
四、怎么样的国家自主性才能够保持国家的持久繁荣?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几点浅见。
(一) 遵循国家运行内在规律的国家自主性
民族国家是目前国际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单元,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也即是说国家是提供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好庇护所,这也是世界范围漂泊的犹太人为什么前赴后继进行“复国”战斗的原因所在;而且无论是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家的权力都不是在缩小,集权程度和扩权范围都在变大,国家自主性不论你是否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尽管驯服国家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过,但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只能尊重国家的品性,尊重国家的主体性,顺应和遵循国家行为的内在规律,张扬国家的公共性和人民性,反而可能更有利于激励国家朝着更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前行。
(二) 从接受对国家权力的外在监督走向国家自主性的反思平衡
国家的自主性往往由于其代理人的行为而使国家行为发生扭曲,诸如国家被利益集团“所俘获”,成为利益集团的帮凶,而使国家遭到非议、甚至要求“国家退却”和“反抗国家”。更准确的说,我们反抗的不是至上的国家,反抗的是无能的政府。这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一条公理:不能以任何理由去消灭现存的国家,而可以以正义的名义去推翻政府。也即是说,我们检验国家自主性很大程度上落实到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组织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上。也可能基于有限理性的认知而不主张自主扩张国家理性能力,而对国家自主性充满不信任,这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国家观。这些都要求把官僚队伍的行为和国家行为纳入到受法治约束的渠道中来,而这还仅仅是外在约束机制,这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制度设计的困境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有学者一直批评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宪法法院来行使违宪审查权,那谁来监督宪法法院法官的权力呢?也可以反问是否有了宪法法院,国家的行为就能受到很好地监督呢?其实不然。事实上根本性的内在约束机制在于国家自主性反思平衡机制的确立,因为堡垒的坍塌往往更多源于内部的瓦解。
(三) 从政党自主性阶段逐渐过渡到国家自主性阶段,更加凸显公共利益
承认国家自主性并不必然纵容国家行为的放任性,当我们追问何种国家自主性能保持国家的持久繁荣时,就是看国家意志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的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自主性的试金石,国家治理的绩效是国家自主性发挥好坏的客观标准。如果国家自主性偏离公共利益,国家治理失败就会激起人民的反抗、引发国家统治的危机。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国家自主性很多地方通过政党自主性体现出来。这也遭到不少学者简单以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来类比和批评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西方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而中国先有政党后成立国家。另外,国家权力的执掌形式也不是检验执政合法性的标准,而是主要看行使国家权力的目的是否增进公共利益的增长。一个主导性的政党对于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和建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共产党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工作重心,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建设以满足提升执政水平的需要,非常注重政党自身建设的共产党还能够很好地发挥“三个代表”的作用,很好地代表国家意志,发挥率先垂范作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有序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即是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这种“党建国家”的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权高于法权”等难题,也使少数领导干部认识出现偏差甚至错误,诸如质问你是“为党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谬论。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当通过政党领导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之后,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越来越回归到国家本身,使政党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国家为政党服务,未来改革的趋势是从“党建国家”走向“党国分离”,从“政党自主性”走向“国家自主性”,政党也只有把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实现政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才能永葆政党执政的生命力。
(四) 不断提升国家自主性的认识和判断水平,在变动的世界把握前行的方向
从“政党自主性”回归到“国家自主性”上来,使国家自主性发挥引领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作为全体人民意志代表的国家不断提升认识和判断水平。鲜明的几次调整是: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判断,国际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扭转毛时代“备战”“备荒”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思维;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领导的党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更具国际眼光,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吸纳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与世界对话和接轨的能力更加增强,全球化时代,国家自主性不仅表现在治理国内事务方面,在国际事务方面也表现其自主性,处理好融入与自主之间的关系,才不至于在国际竞争中损伤国家利益。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议程”任何一次认识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国家自主性带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不亚于任何一次科技创新带来的巨变。
(五) 在借鉴别国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保持和完善本国建设的自主性
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均有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各国先天资源禀赋的差异性,而使国家发展道路不具有模仿性,充其量只能是部分经验的借鉴而不能全盘照搬。尽管“国家引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中国经济的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对于这种模式的总结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中国的未来走向何方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何有效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吸纳到国家自主性发展的轨道中来,是确保国家稳步前行的关键。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自主性很强的差异政治,而且谁也没有能力确保国家发展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这也是政治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差异政治和不确定性政治是人类不得不面临的政治难题。选择的智慧也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地探索何种政治生活是值得向往的生活。只要国家自主性能够不断运用反思平衡能力,尽管“公意”是难以言说的,但因为是客观存在的,遵循“公意”指导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及时调整偏差、增强认识和判断能力,不断理解和趋向“公意”的行为尽管艰辛,但也是具有可行性的,胜不骄、败不馁,只有遵循这种国家自主性观念,“国家引领的政治发展”才能更好地显示其巨大魅力。
[1] 姚洋. 中性政府与中国的经济奇迹[J]. 二十一世纪, 2008(3): 15-25.
[2] 潘维. 中国模式: 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3] 许章润. 国家建构的精神索引——今天中国为何需要省思“国际理性”[C]//许章润. 国家理性.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4] 任剑涛. 国家理性: 国家禀赋的, 或是社会限定的?[C]//许章润. 国家理性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5] 林雪霏. 中国模式与弹性国家能力[J]. 宁夏党校学报, 2010(4): 17-20.
[6]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State autonomy in China’s model: introspection and prospect
CHEN Yi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China’s model of economy development of state supervision is a prominent character in the process that China becomes a modern st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tate supervision brings post-development advantage which evokes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world, but these complicated social questions that a transitional society has brought about is challenging the state authoriza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utonomy bases not only on the economy efficiency, but also on the people’s deep state recognition. How does the state autonomy maintain, how does the state autonomy overcome itself’s paradox, how does the state absorb the reformation requests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autonomy are the era questions that we must sol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hina’s model; State autonomy; state absence; transition society; post-development advantage
D602
A
1672-3104(2014)01-0052-05
[编辑: 颜关明]
2013-05-25;
2013-12-05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研究——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为例”(11BZZ044)
陈毅(1979-),男,河南信阳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统一战线基地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集体行动理论,政治学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