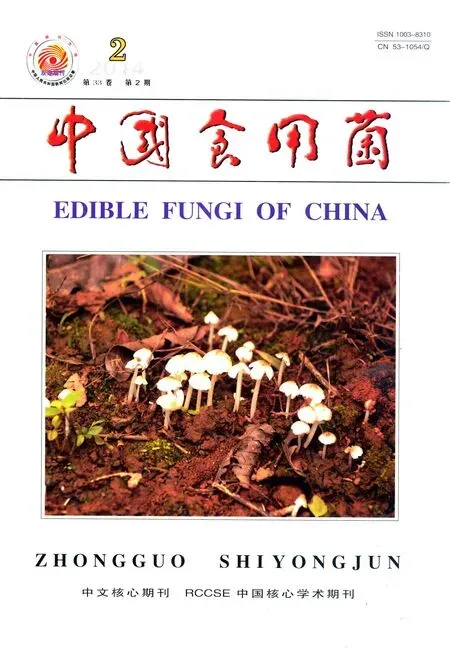我国食用菌术语标准实施现状与几个术语刍议*
2014-01-23贾身茂孔维丽袁瑞奇康源春
贾身茂,孔维丽,袁瑞奇,康源春**
(1.河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8;2.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1 标准、标准化与食用菌标准化
1.1 标准
按照“GB/T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 (ISO/IEC Guide 2:1996 MOD)定义2.3.2”的定义,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1]。”在该定义之后还有一个注:“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利益为目的[1]。”这个定义同时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的定义。
通过上述定义,可以将标准简单地理解成一种文件。然而标准不是一般的文件,它是一种规范性文件。所谓规范性文件是为各种活动或结果提供规则、导则或规定特性的文件,它是标准、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类文件的统称。
例如“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就是规范食用菌领域用以语言文字交流的国家标准,“适用于食用菌的科研、教学、生产和加工[2]。”
1.2 标准化
按照“GB/T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 (ISO/IEC Guide 2:1996 MOD)定义2.1.1”的定义,标准化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1]。”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标准化是一项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是制定条款,制定条款的目的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所制定条款的特点是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针对的对象是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再结合标准的定义可以看出:多项条款的组合构成了规范性文件,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符合了相应的程序,经过了公认机构的批准,就成为标准或特定性文件。所以,标准是标准化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
“标准化”活动是人类社会中每天都在进行的诸多活动的一种,它涉及上述文件 (主要是标准)的编写过程、征求意见过程、审查批准、发布过程、宣传贯彻过程、实施过程,以及修订过程等。实施标准是标准化活动的主要过程,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1.3 食用菌标准化
食用菌标准化目前在国内还没有给出明确、统一、规范的定义。食用菌标准化作为标准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应用,其最基本的概念包括“食用菌”、“食用菌标准”、“食用菌标准化”、“食用菌标准体系”、“食用菌标准体系表”等。
食用菌标准化的定义可简单地归结为以食用菌为对象的标准化活动。这样定义有利于全面、正确地理解、认识食用菌标准化,也有利于借鉴、吸收其他领域先进的标准化成果和经验,促进食用菌标准化的健康发展。当然,上述概念在食用菌上也可以形成以下定义,即食用菌标准化是指运用“统一、简化、协调、优化”的原则,对食用菌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通过制定标准、实施标准和实施监督,促进先进的食用菌成果和经验的迅速推广,确保食用菌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促进食用菌产品的流通,规范食用菌市场秩序,指导生产,引导消费,从而取得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最佳效益,达到提高食用菌竞争力的目的。
1.4 标准化工作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三条规定:“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标准化工作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3]。”
这条规定说明食用菌标准化的任务有三方面,即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2 我国食用菌标准化现状
2.1 重视标准制定
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历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公告、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备案公告统计,截止2013年3月31日,共发布实施食用菌国家标准37项、行业标准82项、地方标准461项,还有数量无法统计的企业标准。这些标准涵盖了食用菌全行业的基础术语、产品质量、菌种规格、技术规程、检测方法、卫生安全等诸多方面,构成了食用菌产业技术领域内系统的、全面的、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这个标准体系是食用菌行业持续稳步发展的技术支撑,是构建食用菌学科的重要基础之一。
2.2 忽视标准的宣传贯彻
1997年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了贾身茂、张金霞编著的《食用菌标准汇编 (一)》一书,该书辑录了29项食用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附录了《食用菌卫生管理办法》和《全国食用菌菌种暂行管理办法》;2006年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测测试中心、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著的《食用菌技术标准汇编》一书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辑录了54项食用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2010年由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著的《中国农业标准汇编·食用菌卷》一书又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这三部食用菌标准汇编在十多年内先后出版,说明国家有关部门对食用菌标准的宣传给予一定的重视。
虽然重视标准的制定和标准图书的出版,但有领导、有组织地对食用菌标准进行宣传贯彻,却被忽视,不论是食用菌协会、质量监督部门或食用菌主管部门,很少对发布的食用菌新标准进行过宣传贯彻,组织学习与落实。笔者曾在河南省郑州参加过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后的宣传贯彻学习班,受益颇大,但从未听说过有关食用菌标准发布时的宣传贯彻学习班,好多食用菌标准发布了多年,很多业界人士还不知道有此标准,有些食用菌标准在发布后无人问津,束之高阁。
2.3 对实施标准监督不力
食用菌标准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本文难以全面论及其实施情况,这里仅就“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国家标准实施中出现的一个典型问题为例,谈一些笔者的粗浅看法,借以反应食用菌标准实施监督工作情况。
“术语 (term)”,按 GB/T15237.1-2000《术语工作 词汇第1部分:理论与应用》的定义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4]。我国科技界习惯上也把“术语”称“名词”,这里的“名词”是英语的term,而不是noun。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术语标准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学名词是一致的。术语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传播知识、技能,进行社会文化、经济交流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是学科建设的支柱。
“食用菌”一词是我国食用菌学科和行业的领头名词,“食用菌”一词的出现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在科学发展与生产技术实践中形成的,从上世纪50年开始已被我国学术界、生产行业、政府管理部门逐步普遍接受和使用的。“GB/T12728食用菌术语”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实施,以及修订,都是由食用菌学科和行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有了这部术语标准,我国的食用菌学科、行业就有了统一交流的语言和定位的基础。1993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现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农学名词》中就有了“04.137食用菌类”[5]的位置,2011年4月9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5号公告,也把“0142食用菌种植”[6]列入《GB/T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最近有学者对国家标准中规范的“食用菌”一词提出异议,因此,本文即围绕“食用菌术语”国家标准中规范的“食用菌”一词,在出版物实施中发生的所谓“替代”的做法进行专题讨论。
2010年由罗信昌、陈士瑜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菇业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在前言中于我国出版物里第1次提出:“用‘菇菌’或‘蕈菌’(Mushroom)代替国内习用的‘食用菌’ (Edible fungi)”[7]的意见,并且付诸于实践,在书中把引用的政府批文、农业部规章、标准、单位等名称中,均把规范了的“食用菌”一词用“菇菌”、“菌类”或“菇菌类”等“术语”进行了“替代”。
本文暂不讨论“食用菌”一词该不该被替代的学术问题,而依据我国有关部门对于术语工作的有关原则规定,对《大典》这一“替代”做法进行简要的评述。因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国家的有关规定,离开这个原则与规定,对是非就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大典》中对农业部“规章”及“标准”等名称中“食用菌”术语的“替代”举例如下。
在《大典》上册第一篇、第四章[7]的第一节、第三节里有:“NY/T528-2002菌类菌种生产技术规程”。在第三节里有:“《菌类菌种暂行管理办法》”、“《菌类菌种管理办法》”等几处。很明显这是把农业部发布实施的“NY/T528-2002《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全国食用菌菌种暂行管理办法》(1996)”和“《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2006)”名称里的“食用菌”用“菌类”“替代”了。
(2)把4个农业行业标准名称及其中1个标准正文中的“食用菌”用“菇菌”“替代”
在上册第一篇、第六章[7]的第九节中有:“NY5099-2002《菇菌栽培基质安全技术要求》”、“NY5099-2002《无公害食品菇菌栽培基质安全技术要求》”、“《无公害食品菇菌生产技术规范》”、 “NY/T528《菇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无公害食品菇菌》”等,以及“《无公害食品菇菌生产技术规范》”的全文。上述4个标准名称及1个标准全文里的“食用菌”全用“菇菌” “替代”了。在“NY5099-2002《菇菌栽培基质安全技术要求》”中还拉掉了标准名称中的“主体要素”,即“无公害食品”5个字。
(3)把一个农业行业标准名称在2处“替代”为2个名称
同一个标准的名称,在《大典》的不同章节里,却用2个不同的术语代替“食用菌”,如上所述的“NY/T528《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在第四章里是“NY/T528《菌类菌种生产技术规程》”[7],而在第六章里竟然是“NY/T528《菇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7]。同一个行业标准在两章里出现2个不同的名称,这说明《大典》本身使用术语混乱,这里用“菇菌”“替代”,那里又用“菌类”“替代”。这样做违背了“标准名称中表达相同概念的术语应保持一致”的原则。
(4)在商检行业标准名称中添加“菇菌”或将“食用菌”改为“菇菌”
在《大典》下册第五篇、第三十三章、第二节[7]中引用商检或农业行业标准时,在标准名称中有些添加“菇菌”,而有些将“食用菌”用“菇菌” “代替”,有些既把标准名称中的“食用菌”用“菇菌” “替代”,后面又多“添加”了“菇菌”。实例如下:
SN/T 0626.7 1997《出口速冻蔬菜检验规程菇菌》,本文作者注:“替代”。
随着中小学教育对语文能力要求的不断提升,提高学生们阅读理解能力的重要性尤为显著,每位教师都应认真需要思考怎么做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们的阅读理解能力。一线语文老师应该都明白,课堂上关于阅读的学习仅仅是引导学生的开始,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以及能力才是小学语文阅读理解教学的本质。而对于以学生为主体的小学语文阅读理解教学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信心、责任感、持久性以及独立性,这也为增强学生课外阅读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就需要通过教师的基于学生主体的阅读教学设计以“抱”到“扶”,最后再到“放”的三部曲来达到由课堂教学到课外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目标。
SN/T 0631-1997《出口脱水蘑菇检验规程 菇菌》,本文作者注:“添加”。
SN/T 0632-1997《出口干香菇检验规程菇菌》,本文作者注:“添加”。
SN/T 0633-1997《出口盐渍菇菌检验规程 菇菌》,本文作者注:前一个为“替代”,后一个为“添加”。
NY 5099-2002《无公害菇菌栽培基质安全技术要求》,本文作者注:“替代”。
另外还有《菇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菇菌菌种品种选育技术规范》等,本文作者注:均为用“菇菌”“替代”了“食用菌”。
(5)把“中国食用菌协会”名称等中的“食用菌”用“菇菌”或“菇菌类”“替代”
《大典》对“中国食用菌协会[7]”的名称,又改作记为“中国菇菌协会”,如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中的“1987年中国菇菌协会成立后,……[7]”;有时又称作《中国菇菌类协会》,如第五篇第三十章第一节中的“据中国菇菌类协会资料显示:……。如果按Hawk worth提出的方法估算,中国蕈菌估计有1.3万种,菇菌类约为0.65万种,占全球估计数量的9%[7]。”同一个“中国食用菌协会”,在一处为“中国菇菌协会”,另一处为“中国菇菌类协会”,“替代”出了2个新的名称。
上面引用第五篇第三十章第一节中的句子后面的“中国蕈菌估计有1.3万种,菇菌类约为0.65万种”中的“蕈菌”与“菇菌类”两词紧跟的数量表述,这让读者费解。因为在《大典》前言里主编已经把“菇菌”或“蕈菌”都对应于mushroom,应是同义。这里用“菇菌”“替代”“食用菌”的结果,出现了如此矛盾的、使人糊涂的数字关系。这也是由于使用术语混乱必然带来的后果。
(6)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的名称中的“食用菌”用“菇菌”“替代”
《大典》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记录为《上海市菇菌研究所》,如“上册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中有:“他们在吸收上海市菇菌研究所香菇木屑菌丝体压块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创造了木屑袋栽香菇的新技术……”[7]。这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的名称被错误的记载成了“上海市菇菌研究所”。
(7)用“菇菌”代替娄隆后教授报告与国务院批示中的“食用菌”
1978年5月,北京农业大学娄隆后教授向国务院提交“我国食用菌事业大有可为”的报告。国务院极为重视,有关领导批示农业部、外贸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要抓食用菌发展[8]”。但是在《大典》的第一篇第一章里记载的确是:“1978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娄隆后就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我国发展菇菌产业是大有可为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指示有关部门‘要抓菇菌发展’,……[7]。”这里用“菇菌”把娄隆后教授报告题目与国务院批示中的“食用菌”“替代”了。
(8)《大典》修改地方规章名称中的“食用菌”为“菇菌类”
在第二十九章第六节有:“为此,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检验总局于2002年颁布了《进出口蔬菜检查检验管理办法》,要求出口厂商建立出口基地,并且需要备案检查。各地根据此办法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管理细则。如浙江金华地区公布了《出口菇菌类检查检验管理办法》,……[7]”。这个浙江金华地方规章名称中的“食用菌”又被“菇菌类”“替代”了。
上述《大典》里出现的对政府批文、规章、标准、单位名称、个人报告中的“食用菌”一词,用“菇菌”或“菌类”或“菇菌类”来“替代”的现象,反映出业界忽视对食用菌术语标准的贯彻执行,更反映出对实施标准监督不力。在汉语词汇中,‘典’为五帝之书,是指可作为典范的重要文献、法则和制度,本书作为中国菇业的大典是名副其实的[7]。但更说明贯彻国家食用菌术语标准重视监督实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关于科学技术术语的审定原则与使用
3.1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规定
2010年12月30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审议修订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9],其中的“科技名词定名原则”原文如下。
3.1.1 贯彻单义性的原则
一个概念仅确定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规范的中文名称。
一个概念有多个名称时,应确定一个名称为正名 (规范名),其他为异名。异名主要包括“全称”、 “简称”、 “又称”、“俗称”、“曾称”。其含义分别为:
正名——公布的规范名。
全称、简称——与正名等效使用的名词。
又称——非推荐名。特殊情况下允许定一个“又称”,只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俗称——非学术用语。
曾称——已淘汰的旧名称。
多个概念使用同一个名称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概念分别确定不同名称,以客观、准确地表达概念。
3.1.2 贯彻科学性的原则
定名应当准确表达单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定名应当注重其学术性,尽量避免借用生活用语。对不科学的,易引起概念混乱的名词应予以纠正。
3.1.3 遵从系统性、简明性、民族性、国际性和约定俗成等原则
(1)系统性
同一概念体系的名称,应体现出逻辑相关性。基本概念名称确定后,其派生概念、复合概念的名称应与之相对应。
(2)简明性
定名要易懂、易记、易读、简洁,使用方便,避免生僻字。
(3)民族性
定名时,应考虑我国文化特色和中文科技名词特性。要尽量采用具有我国特色的科技名词。外来科技名词进入汉语,意译为主,适当采用音译,尽量不造新字。
(4)国际性
定名时应与国际上通行的名词概念保持一致,以利于国际交流。
(5)约定俗成
对应用面较广,沿用已久,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名词,即使科学性牵强,也可保留,不轻易改动,以免引起新的混乱。
当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民族性、国际性、约定俗成等原则无法同时兼顾时,须仔细研究,综合考虑,合理定名。
3.1.4 坚持协调一致的原则
当同一个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名称不一致时,应根据“副科尊重主科”的原则统一定名。
若同一概念在不同学科中名称不一致,且这几个学科不易分清主、副科关系,有关学科名词分委员会应互相协调,统一定名。
如果同一个概念在不同学科中存在多个名称,确实不宜统一为一个名称,作为特殊情况允许分别定名,互为又称。
定名在原则上应同国内已公布的有关术语标准协调一致。出现不一致时,应充分协商、慎重定名。
以外国科学家人名 (包括外国地名)命名的科技名词,要按照全国科技名词委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制定的原则协调统一,基本原则是“名从主人,遵照规范,约定俗成,副科尊重主科”。
3.2 科技新词的审定、发布和使用
对科技新词的审定、发布和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9]中也有规定,其原文如下。
3.2.1 科技名词收录范围 (略)
3.2.2 科技新词定名与发布
科技新词是指国内外近年出现的代表新概念、新理论、新物质、新技术、新工艺等范畴的科技名词。
各学科分委员会在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时,都要把科技新词的收集和定名当做一项重要内容,并及时提交全国科技名词委汇总。
科技新词工作在坚持科技名词定名原则的基础上,要体现快捷的特点,并采用较为灵活的采集和发布方式。
科技新词工作分为‘发布试用’和‘审定公布’两步进行。
各学科分委员会所确定的科技新词,经全国科技名词委审查批准后,通过相关媒体向全国发布试用。
科技新词发布试用之后,相关学科分委员会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审定,然后由全国科技名词委正式公布。
3.3 关于使用科技名词 (或术语)的规定
为了我国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化与统一,对于科学“名词”的使用,国家有关部门还有一些规定。
国务院于1987年8月12日 [国函 (1987)142号]明确批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审定、公布各学科名词,是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经其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0]。”
1990年6月23日,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联合通知[11]中明确要求,为认真贯彻国务院的上述批示,现通知如下:
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并带头使用已公布的名词。
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
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4 对食用菌术语标准中几个有异议术语的讨论
4.1 Fungus的汉语对应词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名词 (或术语)是一致的。如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现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下同)公布的《微生物学名词》中, “真菌”对应于英语“Fungi”[12],而《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中“真菌”对应的英语是“Fungus”[2],前者英语为复数,后者英语为单数,两者是一致的。
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国内学者在讨论生物的界级分类时,曾出现“菌物”一词。1979年陈世骧、陈受宜的《生物的界级分类》一文中,在评介新建的由低等生物组成的第三界“原始生物界Protoctista”或“原生生物界Protista”的生物三界系统的进步、优点与缺点后,在叙述其它的三界分类系统中有新建的“菌物界”:“谷那特 (Conard,1939)把生物分为植物界Phytalia,动物界Animalia和菌物界Mycetalia,后者包括真菌和细菌[13]。”。陈世骧、陈受宜将Mycetalia译为菌物界。这是“菌物”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1991年裘维蕃先生提出:“关于Fungi一词过去都译为‘真菌’(Eumycetes或True Fungi)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个词还包含着粘菌或裸菌在内。为此我建议:今后将Fungi译成菌物而把真菌学 (Mycology或Fungology)改为菌物学。真正的真菌学似乎应该是专讲真菌门 (Eumycota)的内容[14]。”
1993年刘杏忠、刘润进、裘维蕃在《菌物之概念》一文中引用裘先生这一段话后评价说:“这是‘菌物’概念在中国的第1次提出[15]。”1991年在《对菌物学进展的前瞻》一文中裘维蕃先生又进一步解释说:“至于为什么要称菌物而不称菌类,因为菌物 (Myceteae)是一个界 (Kingdom),它的命名应该和动物及植物的物字一致[16]。”裘先生的意见在中国真菌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0年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真菌学会”于1993年改为“中国菌物学会”;1982年创刊的《真菌学报》在1997年改称“菌物系统”,之后又于2004年改为《菌物学报》;1998年,裘先生主编的《菌物学大全》出版;2003年创刊了《菌物研究》。在国内把多年来“Fungi”的汉语对应词“真菌”几乎统统改为了“菌物”,其理由是“所谓真菌学中包涵的并非全是真菌[16]”。
这一改变,首先引起了张树政院士的注意,早在1996年就在《关于“菌物”与“真菌”名词的辨析》一文中指出:“称真菌学时,大家都认识卵菌和黏菌 (1984年,de Bary称其为Mycetozoa,菌虫)不是真菌,改成‘菌物学’,把占绝大多数的真菌称为‘菌物’势必引起混乱。修改一个在国外学术界使用了260多年,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以上历史的正确名词,要被广泛接受且不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混乱,是非常困难的。在当今信息时代,统一的名词在知识传播和国际交流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17]。”
1997年裘维蕃先生曾给“Fungi”作了新的解释:“本文引用了《安·比氏菌物词典》(Ainsworth&Bisby's Dictionary of Fungi)》1995年第8版有关菌物分类的安排。字典书名的Fungi是泛指真菌和非真菌的,因此,Fungi一词在这里是广义的,应该译为‘菌物’;但在字典的分类表中,也用Fungi一词来代表‘真菌界Eumycota’,因此这里的Fungi是狭义的,应译‘真菌’[18]。”这里裘先生改变了1991年“关于Fungi一词过去都译为‘真菌’(Eumycetes或True Fungi)是不妥当的”观点,并认为“Fungi”广义可以译为“菌物”,狭义译为“真菌”。
尽管如此,2006年《中国真菌学杂志》[19]创刊;2010年贺运春主编的《真菌学》出版,而且指出:“我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韩国仍然使用‘真菌’和‘真菌学’一词,为沿袭传统和学术交流方便,本教材仍使用广义的‘真菌’和‘真菌学’一词[20]。”
2013年芦笛在《对英语词FUNGI、MUSHROOM、TOADSTOOL和MYCOLOGY的词源学阐释》一文中指出: “事实上,以上争论的焦点对‘Fungus’的复数词‘Fungi’的理解,以及汉译名中的‘真’字。通常情况下,‘Fungi’一词指真正的真菌 (true fungi;如霉菌、双胞蘑菇等);但在分类学系统中,‘fungi’首写字母大写后 (即Fungi)表示真菌界(即裘先生所谓的菌物界)。著名的真菌学分类工具书《安·比氏真菌学字典》(Ainsworth&Bisby's Dictionary of Fungi)很清楚现代真菌分类学里的黏菌、卵菌等问题,但这2种表示方法在该词典中并未造成混乱。裘先生认为黏菌、卵菌等不是真正的真菌,因此不能称之为‘真’菌。相对于悠久的使用和接受传统,这种改动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正如张树政院士所说,“‘称真菌学时,大家都认识卵菌和黏菌……不是真菌’。……裘先生的主张也带来了一些混乱,比如他既已知道第8版的《安·比氏字典》已经把黏菌归入原生动物 (Protozoa),把卵菌纲归入假菌界 (Chromista),却又随后在其主编的《菌物学大全》中,主张把真核生物分为植物界 (Plantae)、动物界 (Animalia)和菌物界 (Mycetalia),令人匪夷所思。据笔者所知,菌物界 (Mycetalia)这一说法并未在世界真菌学界产生影响[21]。”
其实,早在1993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农学名词》中,已将“菌物”一词规范为农学的分支学科“11.植物保护”的专业名词: “11.339菌物 Fungus[5]”。这明确了“菌物”不是生物的“界”级分类单位。1993年刘杏忠、刘润进、裘维蕃在《菌物之概念》一文中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菌物’不应是一个分类上的术语,而应是1个涉及3个界的 (传统称作‘真菌’的)生物总称,像动物、植物、藻类、微生物等一样的非分类学术语,相当于英文的‘Union of fungi’或者 ‘Fungi’[15]”。按魏江春院士的解释:“为了避免混乱,近年来,对于‘Fungi’的广义概念有用‘真菌学家所研究的生物’[‘Organisms studied by Mycologist’(Hawksworth 1991)]或‘真菌联合体’ (‘Union of fungi’,Barr,1992)词组以取代‘Fungi’。这一称谓,实际上是指汉语中的‘菌物’[22]。”这一解释,说明“菌物”是“真菌联合体Union of fungi”,由此可见,过去“Fungi”一词译为“真菌”、“Mycology”译为“真菌学”均不是失误。
“菌物”不是“界”级分类单位。“因为菌物 (Myceteae)是一个界 (Kingdom),它的命名应该和动物及植物的物字一致”的论点的历史意义也已经过时。通过这一时期的讨论,最终是给植物保护专业增加了1个新术语:“菌物”。术语是分专业和层次的,“菌物”是植物保护专业的专用名词。
4.2 Mushroom的汉语对应词
英语“Mushroom”很早翻译的汉语对应词为“蘑菇”、“蕈”,如1976年出版的《真菌名词及名称》[23]。1989年《微生物学名词》将英语“Mushrooms”的汉语对应词规范为“蘑菇[12]”。
而2003年陈士瑜等在其编写出版的《菇菌栽培手册》中首次又将英语“Mushroom”对应于汉语“菇菌”[24]。2010年罗信昌、陈士瑜在其主编的《中国菇业大典》中,不仅将英语“Mushroom”对应于汉语“菇菌”、“蕈菌”[7],又对应于汉语“菌类”[7]。提出“Mushroom”对应于汉语“菇菌”、“菌类”时,既未提出“Mushroom”对应于汉语“蘑菇”不合适的理由,又未对“菇菌”、 “菌类”给出定义。而“蘑菇”在《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中也已有明确的定义:“蘑菇Mushroom大型真菌的俗称,见大型真菌。按用途分为食用菌、药用菌、有毒菌和用途未知菌四大类,多数为担子菌,少数为子囊菌[2]。”
如果提出的新术语更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科学性更准确、更严密,也是好事。否则,不顾前人的成果,随意的创造使用“新词”,只能使术语更加混乱,增加了学术交流的难度。这种做法,是不利于学术交流和发展的。
4.3 食用菌
《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 “前言”中明确指出:“1)修订了标准的英文名称,由原名《Terms of edible fungus》改为 《Terms of edible mushroom》[2]”。“2 术语和定义”的“2.1基本术语”中“2.1.4”对“食用菌”下的定义是:“食用菌edible mushroom可食用的大型真菌,常包括食药兼用和药用大型真菌。多数为担子菌,如双孢蘑菇、香菇、草菇、牛肝菌等,少数为子囊菌,如羊肚菌、块菌等[2]。”
罗信昌教授是国家标准“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的第二主要完成人,但在《大典》中谈到要用“菇菌”替代“食用菌”时的理由是:“‘食用菌’这一名词词义上并不单指食用蘑菇,可食用丝状真菌、酵母菌、细菌也属于‘食用菌’,超出了大型真菌 (macrofungi)的范畴[7]。”罗先生批评的不是《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对食用菌的定义。
2013年罗先生又撰文指出: “2006年国家标准公布的‘中国国家标准-食用菌术语’中定义‘食用菌’为可食用大型真菌总称。然而,长期以来一些食用菌教科书、出版物(包括食用菌年均产量,产值报表)等都纳入灵芝、猪苓、茯苓、冬虫夏草、天麻等药用菌甚至白腐菌等内容,远远超越了可食用大型真菌的范围,与书名、杂志名不符,还有把Mushroom industry翻译成‘食用菌产业’,Mushroomology翻译成‘食用菌学’等。这种混乱情况的出现源于把‘食用菌’和‘蘑菇’两词混为同义词所致……[25]。”
《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给“食用菌”的定义是:“可食用的大型真菌,常包括食药兼用和药用大型真菌[2]。”这个定义很清楚食用菌包括“食药兼用和药用大型真菌[2]。”在这个定义下,“食用菌教科书、出版物 (包括食用菌年均产量,产值报表)等都纳入灵芝、猪苓、茯苓、冬虫夏草、天麻等药用菌甚至白腐菌等内容”是无可非议的。《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中对“蘑菇”的定义是“蘑菇Mushroom大型真菌的总称。见大型真菌。按用途分为食用菌、药用菌、有毒菌和用途未知菌四大类,多数为担子菌,少数为子囊菌[2]。”《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国标中上述对“蘑菇”与“食用菌”的定义很清楚,“蘑”是上位概念,“食用菌”是属于“蘑菇”的下位概念,怎么是同义词呢?至于有些刊物、单位名称中还用“Edible fungus”或“Edible fungi”作为“食用菌”的对应词,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说明是对《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宣传贯彻工作不力、术语使用还不规范所致,这正是需要我们食用菌界同仁共同努力要做的事情。
4.4 真菌、蘑菇和食用菌的层级关系
真菌、蘑菇和食用菌均是食用菌学科的领头术语,它们之间是层次关系。真菌与蘑菇,真菌是蘑菇的上位概念,蘑菇是真菌的下位概念。蘑菇与食用菌,蘑菇是食用菌的上位概念,食用菌是蘑菇的下位概念。在张树庭教授所著《食用蕈菌及其栽培》英译中文本的“译者的话”中曾介绍:“在翻译期间,原书著者张树庭教授和Miles PG教授就重要术语概念的准确翻译给予了指导。例如Mushroom的中文译文原来仅为‘蘑菇’,本书删除了保留这一侠义的译文外,广义上还译为‘蕈菌’[26]”。不论从汉语构词上,还是科学术语的涵义上,将“Mushroom”的汉语对应词译为“蕈菌”,是较确切的。但“约定俗成”,改变“蘑菇”这一具有传统意义的、使用多年的“Mushroom”的汉语对应词,是非常不易和不妥的。
5 结语
食用菌标准化是食用菌产业稳定持续发展的技术支撑,规范食用菌术语及其定义是标准化基础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食用菌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基础工作。让食用菌全行业的科技、生产加工、流通等部门携起手来,共同协商,加倍努力,认真实施食用菌标准,促进我国食用菌标准化的进程。本文作者学识浅薄,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
[1]GB/T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 (ISO/IEC Guide 2:1996 MOD)[S].中国标准出版社,2002.
[2]GB/T12728-2006,食用菌术语 [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S].1988年12月29日:第三条.
[4]GB/T15237.1-2000,术语工作 词汇 第1部分:理论与应用[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0.
[5]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农学名词[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6]GB/T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
[7]罗信昌,陈士瑜.中国菇业大典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8]杨新美.中国菌物学传承与开拓[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9]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S].2010.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公布天文学名词问题的批复 [国函 (1987)142号][S].1987.
[11]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使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名词的通知[90]科发出字0698号 [S].1990.
[12]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微生物学名词[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13]陈世骧,陈受宜.生物的界级分类 [J].动物分类学报,1979,4(1):1-11.
[14]裘维蕃.植物和菌物的渊源和异同/农园植病谈丛[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5]刘杏忠,刘润进,裘维蕃.菌物之概念[J].植物病理学报,1993,23(4):289-291.
[16]裘维蕃.对菌物学进展的前瞻 [J].真菌学报,1991,10(2):81-84.
[17]张树政.关于“菌物”与“真菌”名词的辨析 [J].微生物学通报,1996,23(6):376-36.
[18]裘维蕃.关于真菌和菌物译名的真实涵义 [J].植物病理学报,1997,27(1):1-2.
[19]中国真菌学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国真菌学杂志,上海市凤阳路415号.
[20]贺运春.真菌学 [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21]芦笛.对英语词 FUNGI、MUSHROOM、TOADSTOOL和 MYCOLOGY的词源学阐释[J].食用菌,2013(2):65-68.
[22]裘维蕃.菌物学大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3]真菌名词及名称 [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24]陈士瑜,陈惠.菇菌栽培手册 [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25]罗信昌.“食用菌”用语亟待规范[J].中国食用菌,2013,32(1):61-62.
[26]张树庭,Miles PG.杨国良,等.食用蕈菌及其栽培[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