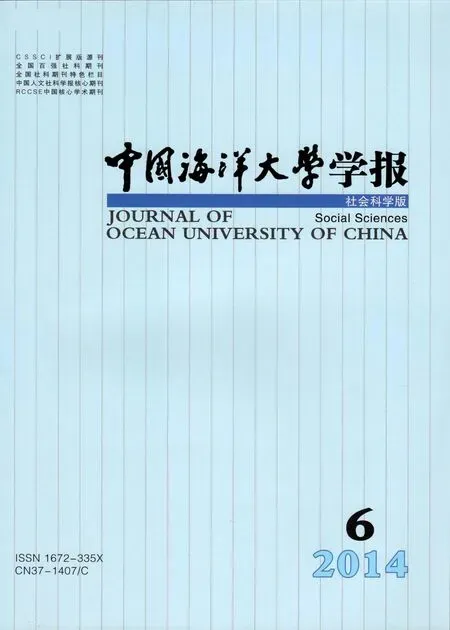鲁迅与佛陀的同与不同
——由汪卫东《<野草>与佛教》所想到的*
2014-01-22崔云伟
崔云伟
(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汪卫东教授的《<野草>与佛教》最初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现收入汪卫东著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1]之第一章第五节之第二小节第1—4部分。该文发表伊始,即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这是因为:一则其时我正对佛教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很想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二则我每年都要写作一篇关于历年来鲁迅研究述评的文章,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好的文章一网打尽。汪卫东的这篇论文恰恰投合了我这两个方面的需求。而事实也恰恰证明,这确实是一篇相当优秀和出色的论文。
汪卫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走进《野草》之前的鲁迅,正处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深渊,这时的他,与佛教的“苦谛”最为接近。读《野草》,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鲁迅的自厌与自虐。深味人生之“苦”,并产生“厌离“之心,这两者,已近于佛教之门了。鲁迅进而又由“苦”入“集”,由果而探索致苦之因。《野草》中,鲁迅把自己的困境归于缠绕自身的太多的矛盾。《野草》主体已厌弃于长期矛盾中犹疑惶惑的状态,希望做一次最终的抉择。矛盾,正是“我执”的结果。所以鲁迅由“苦”、“集”,进入“灭”、“道”,欲求得解脱,首先就要破除“我执”。然而,鲁迅在《野草》中所采取的却是一种激化矛盾的方式,这种近乎休克的疗法,在“我执”的路上愈走愈远了。上穷碧落下黄泉,鲁迅打开矛盾,苦苦追寻,却最终发现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野草》的自我追问,得出了和佛法相同的结论,那就是“无我”。证得无我,并没有达到佛教所谓了无挂碍、常乐我静*一说为: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对于《野草》,这还非最后解脱,无我之后,最终还要回到生存的人间。以佛教之另一重要解脱法门缘觉乘视之,佛教缘起在深层次上,又有“随顺因缘”之说。于是,《野草》主体由厌弃因缘,又回到因缘,回到了普遍缘起的真实世界。《野草》主体最终还是站在了现实的大地上。
由以上论述可知,汪卫东为了论证鲁迅与佛陀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主要采用了佛教中的两大解脱法门:声闻乘和缘觉乘,而以声闻乘为第一切入法门。这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佛陀当时在菩提树下悟道,即是因为明了四谛法而成为觉者的,即证得了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第二,佛成道后,初转法轮,即为阿若憍陈如等五人说四谛法,而使他们五人悟道,成就阿罗汉果位的。第三,佛陀临涅槃时,答复阿难陀四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佛陀住世时,我们依佛陀安住,佛陀涅槃后,我们依什么安住”时,说:“我涅槃后,应依四念处安住。”这四念处分别为:身念处:观身不净;受念处:观受是苦;心念处:观心无常;法念处:观法无我。而这四念处即为四谛法中“道”谛中的三十七道品中的前四个道品。佛陀在临涅槃时,于广大佛法中,只说安住于四念处,可见对于声闻乘修道法门的重视。除声闻乘外,佛教还有两大修行法门:缘觉乘与菩萨乘。汪教授在采用声闻乘的同时,还采用了缘觉乘。这两乘同属小乘佛教修道法门,菩萨乘则属于大乘修道法门。汪卫东同时采用声闻乘与缘觉乘这两大修行法门,其实已经意在告诉我们:单纯地从任何一乘法门出发,其实是很难完全发现鲁迅与佛陀的相遇与相通的。这也正是汪卫东在主要采取声闻乘之余,再补之以缘觉乘的主要原因(单就与这两块相关的论述文字而言,与声闻乘相关的文字约占80%,与缘觉乘相关的文字则约占20%)。而这则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假如单纯地从声闻乘这一法门出发,中途不再换乘别的法门,一意孤行走到底,我们是会发现鲁迅与佛陀更多的相同之处呢,还是更多的不同之处?我想,或许还会发现更多的不同之处吧。
进入论证之先,让我们再重新回味一下佛陀关于声闻乘、四圣谛的种种说法。当日佛陀在鹿野苑说四谛法,因为憍陈如等5人,由听佛说四谛法的音声而悟道的,所以另起个别名叫作“声闻”,凡属修四谛法门而悟道的,总称为“声闻乘”。“乘”是运载的意义。即是把众生从迷岸运至悟岸的工具,这工具乃指教法,故乘是譬喻而指教法——此即指四圣谛的理法,由闻四圣谛可到达(运载)悟道之彼岸。所谓四圣谛即苦、集、灭、道四法,这是圣智所亲自证验到的四种人生正确真理。所谓“苦谛”,即说明人生多苦的真理,人生有生老病死,人人免不了的痛苦。还有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都是苦的果报。所谓“集谛”,即是说明人生集起贪瞋痴等许多烦恼的“因”,去造种种的不善业,才会招受种种的苦果,故“苦”以“集”为因。所谓“灭谛”,即是指修道所证的圣果,即是烦恼灭除,获得无生(解脱生死)的真理。所谓“道谛”,道就是正道,道有多种,主要的指修习八正道,就会得到最胜智慧(般若),修善断恶,解脱生死痛苦。以上四谛,“集”为“苦”的根本,此二谛又为流传于世间的因果,知苦而断集,断集以离苦,为声闻乘厌离世间的观行;“灭”为“道”的收获,此二谛即为超出世间的因果,求证灭而修道,由修道以证灭,是为声闻乘修证涅槃的行果。*以上关于苦、集、灭、道的阐释皆出自圣严法师:《佛学入门手册》,厦门南普陀寺印赠。该书版权页署:内部资料,免费交流。欢迎随缘助印,赠送结缘,功德无量。以下正文中凡有关佛学义理处亦皆参考此书,不再一一注明。想到我写此文,亦是对于佛学义理的一次宣扬,内心甚感欣慰。
由上述佛陀关于声闻乘,尤其是四圣谛的种种说法,对之以1923年之后,鲁迅创作《野草》的实际状况便会发现,汪卫东对于鲁迅在创作《野草》过程中的“苦”与“集”的描述,是相当准确的。汪卫东指出,走进《野草》之前的鲁迅,正处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深渊,这时的他,与佛教的“苦谛”最为接近。“苦谛”具体表现于《野草》即是鲁迅的自厌与自虐。深味人生之“苦”,并产生“厌离”之心,这两者,已近于佛教之门了。鲁迅进而又由“苦”入“集”,由果而探索致苦之因。那么,“集”是什么呢?或者说,造成鲁迅自厌与自虐的烦恼的深重原因是什么呢?汪卫东认为,这即是缠绕在鲁迅自身上的太多的矛盾。而《野草》主体则早已厌弃于长期矛盾中犹疑惶惑的状态,希望做一次最终的抉择。这些论述都是相当深刻和到位的。据之,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四圣谛之“苦”与“集”中,鲁迅与佛陀确实是有其精神相通之处的。我们把这称之为鲁迅与佛陀的“同”。
接下来,按照我们的论述理路,应当是对于鲁迅《野草》中有无“灭谛”与“道谛”的考察。如前所述,此二谛为超出世间的因果,求证灭而修道,由修道以证灭,是为声闻乘修证涅槃的行果。先说“灭谛”。所谓“灭谛”,即是小乘三法印中的“涅槃寂静”(另外两个小乘法印分别是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大乘法印则是一实相印或缘起性空)。涅槃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大乘涅槃是圆满寂静(德无不圆,障无不寂),也称圆寂。狭义的二乘涅槃,是择灭义,即以圣智之抉择而断灭烦恼业生。择灭即解脱生死流转,而常住寂静,故称涅槃寂静。二乘人证我空真如,尚有所知障(法执)未断,故有所执,仅能证小乘涅槃。唯佛断我法二执,证无住大涅槃。因佛福智圆满,大悲般若常相辅翼,以般若故,不住世间,以大悲故,亦不住出世间,称为无住涅槃。由此可知小乘的涅槃,与佛果的涅槃不同。但因涅槃的境界是常寂安静的,通称为涅槃寂静。
对之以《野草》,显而易见的是,鲁迅不可能有涅槃寂静的追求。《野草》所呈现给我们的,全然是一个充满动感的世界。*鲁迅对于动感世界的追求表现在各个方面。从他的审美特质上来说,鲁迅崇尚有力之美。对于自然美,鲁迅欣赏的是“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的狮虎鹰隼,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是“蓬勃地奋飞”“如包藏火焰的大雾”的北方的雪。对于社会美,尤其是对其中的人,他欣赏的是“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的拜伦,是世俗的民间的“漂亮活动”的村女的美,而不是故作高雅,“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的化为“天女”的梅兰芳的美。对于艺术美,他欣赏的是曹氏父子的清峻通脱,阮籍的狂放,特别是嵇康的敢发议论,以及“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明末小品;欣赏对于北方人民的“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描写已经“力透纸背”的萧红的《生死场》;欣赏“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和“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复仇女吊。这一切都表明了鲁迅不可能有涅槃寂静的追求。《题辞》中的“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地火”则“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而“我”则“坦然,欣然”,既将大笑,又将歌唱。其中没有一个意象是寂静的。如果说从写作时间上说这是《野草》的最后一篇,还不能够充分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再看看《野草》的第一篇《秋夜》(汪教授把《秋夜》解读为《野草》的序,亦可)。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撞得玻璃灯罩“丁丁”响的小青虫自不必说,连小粉红花都在这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着梦,天空都是这样的“奇怪而高”,“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而故事的主角枣树,则“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睒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在这看似寂静的秋夜里,又有哪一个意象是纯然寂静的呢?不但不是寂静的,在鲁迅《野草》其他作品中,有的运动感还极其强烈,全篇如《好的故事》、《死火》,片段如《雪》中关于朔方的雪,《颓败线的颤动》中关于“老女人”的极其精彩的描写。
其实,关于鲁迅对于涅槃寂静的描写,《野草》中也并非没有。在《一觉》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极其令人神往的世界:“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一段描写与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中对于词中三种境层中的第三境层的描绘极其相似。蔡小石是这样描写的:“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这是直观感相的渲染)再读之则烟涛澒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鳞出水,又一境也。(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翛然而远也。(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江顺贻评之曰:‘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蔡小石语,此处参见: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中间括号中内容亦为宗白华先生所加。显然,如宗白华先生所言,这三种境层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审美境界和层次。它们从真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一直到了最高灵境的启示。蔡小石在这里显然充分肯定了第三境层,即最高灵境的启示。但是,这究竟只是一个古代中国文化人的见识,却并不是已经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的鲁迅的最高认识。鲁迅并没有充分肯定《一觉》中的这段描写,只是以一种不能确定的语气说这种境界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吧,然而接下来,鲁迅却说:“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对于涅槃寂静境界的追求。
由以上论述可知,鲁迅在《野草》中最终并没有通达佛陀所说的悟的彼岸,即没有冲破无明网罗,截断生死根源,证登涅槃彼岸。鲁迅仍然不能忘记人间情怀,仍然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这是鲁迅与佛陀的最大不同。在这里,鲁迅与佛陀分别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超越。如果说佛陀的超越是对于涅槃寂静念兹在兹的执意追求(其实到达最高的涅槃境界,则连这执意也要一块抛弃),我们可以称之为“向上超越”,那么,像鲁迅这种执意活在人间,既不愿意去天堂,也不愿意去地狱,更不愿意去黄金世界,就是要站在坚实的大地上,在无物之阵中一直战斗到死的超越,则可以称之为“向下超越”。*关于“向上超越”和“向下超越”的提法,其直接影响来自于伊藤虎丸和汪晖。伊藤虎丸在他的那部极富原创性的著作:《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曾经这样发问:鲁迅产生于一个与基督教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可能从一种超越的视野看待他所生存的世界,但为什么鲁迅的批判具有如此深刻的性质?最终,他找到了答案,认为在鲁迅的世界里的确存在着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但与基督教向上超越不同,鲁迅向下即向“鬼”的方向超越。2008年,汪晖则在他的文章《鲁迅与向下超越》(《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命题。他认为,“鬼”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包含着巨大潜能的存在,没有它的存在,黑暗世界之黑暗就无以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鬼”黑暗而又明亮。鲁迅的文学产生于一种自觉,即自觉到时代末日的来临。在这种自觉中产生了以一种“综合的”文学方式批判时代的愿望。就此批判方式而言,鲁迅的文学方式便有了一种宣布末日降临的“革命”意味,而“革命者”则是以“鬼”的方式现身的。由是,汪晖进一步预言:20世纪日渐远去,鲁迅的幽灵也许能帮助我们重新接近那个时代——不是从“现代”、“启蒙”、“进步”、“左翼”和“革命”等角度去接近,而是从“鬼”、“迷信”的角度去接近,即从“鬼”、“迷信”的角度去重新阐释“现代”、“启蒙”、“进步”、“左翼”和“革命”。我与以上两位论者提法的区别在于:一,在这里,我所说的“向上超越”指的是佛陀的向上超越,而非基督的向上超越。二,同样在这里,我所说的“向下超越”,指的是始终站在坚实的大地上,而非容身于“鬼”和“迷信”之中。也许有人会说,佛陀成道后,也并没有立即证登涅槃,抛离众生而去,而是也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通过不断向众生说法,从而普度众生,这岂不是和鲁迅的“向下超越”一样了?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上文所说的普度众生,指的是佛教修行法门中的大乘法门:菩萨乘。菩萨乘之不同于同属小乘法门的声闻乘和缘觉乘,即在于菩萨乘是既自利又利他的,而声闻乘和缘觉乘则仅仅谋求自利而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由于小乘人并不想发菩提心,下化众生,上求佛果,所以被大乘人斥为焦芽败种,不堪造就。但是,不论通过哪个修行法门,即无论是通过声闻乘、缘觉乘,还是菩萨乘,其最终指向都是一样的,即都指向了涅槃寂静,也就是四圣谛中的“灭谛”(小乘、大乘关于涅槃寂静的说法还有不同,参见上述)。而鲁迅则如前所言,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涅槃寂静的。故而,鲁迅与佛陀是根本不同的,他们都各自代表了一种互不相同的超越模式。
以上论述了鲁迅与佛陀在根本目标上的不同,似乎意味着鲁迅与佛陀在“道谛”上亦是不同的。然而,颇具意味的是,鲁迅与佛陀在“道谛”上却有诸多相似乃至相通之处。佛陀从四圣谛的道谛中,开示出三十七种修习基本圣道的法门,叫作三十七道品,亦称三十七菩提分法。这三十七道品主要包括:四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四正勤:已生恶令断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长;四神足:欲神足,勤神足,心神足,观神足;五根:信根,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五力:信力,进力,念力,定力,慧力;七菩提分:择法菩提分,精进菩提分,喜菩提分,轻安菩提分,念菩提分,定菩提分,行舍菩提分;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在这三十七道品中,最主要的是修习八正道。佛陀所开示的这八正道,已具有戒定慧三学的次第增进,如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戒学;正念、正定,就是定学;正见、正思惟,就是慧学;而以正精进为策励戒定慧三学的完成。八正道为圣者解脱的正轨,要求解脱,必须循着此八正道实践力行。鲁迅曾经购买并阅读过大量佛经,对于这三十七道品,尤其是其中的八正道,应该是相当熟悉的。1931年3月1日,鲁迅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2]上书:戒定慧三字。如前所述,这三字即为八正道的精华。但是,鲁迅究竟并非佛教徒,亦并未皈依佛法。鲁迅既然并不赞同佛陀之最终追求——涅槃寂静,自然不会走在实践八正道的路途之上。
那么,鲁迅在道谛之中究竟与哪些义理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与相遇呢?答案即是佛陀临近涅槃之时所千叮咛万嘱咐的“四念处”。如前所述,这四念处分别为:身念处:观身不净;受念处:观受是苦;心念处:观心无常;法念处:观法无我。其与鲁迅《野草》的精神联系试述如下:
一、身念处,即观身不净,是以修不净观之慧力,对治“缘身执净”的颠倒妄见。人到死后,尸体腐烂,遍体生蛆,穿筋啮骨,最后成为白骨一堆,这个身体的生存,实在不净,故能观身不净,则贪爱渴想,恋慕艳丽色相等烦恼,自可消除,才能把心安住于道法中。鲁迅《野草》中恰好有这样一篇散文诗《死后》。“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不是死在家里,而是死在路上,可谓死不得其所。独轮车轧轧地从“我”的头边推过,叫得人心烦,还有些牙齿齼。行人踹起黄土来,飞进“我”的鼻孔,使“我”忍不住要打喷嚏。一个蚂蚁爬在“我”的脊梁上,痒痒的。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开口便舐“我”的鼻尖,还有几个则聚在“我”的眉毛上。更可恶的是路人们的议论纷纷,连一个人的死亡也难以适合他们的公意。更可笑的还有一个向“我”兜售明板《公羊传》的小伙计,“我”都已经死了还在不断地骚扰“我”。“我”的身体如此不净,任谁都可以来欺负,来议论,来骚扰,“我”真愿意真的死去,连同“我”的运动神经和知觉。《题辞》中的“野草”带有很强的拟人性,它的隐喻意即是战士。它(或他)“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试问这样的身体又何净之有?鲁迅之“观身不净”观于此亦可见一斑。
二、受念处,即观受是苦,是以观苦之慧力,对治“缘受执乐”的颠倒妄见。人生是苦的,这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苦。苦既是由“受”而有,那么,知苦而不贪欲乐,就不为境界所转移,则“缘受执乐”的妄见便不能存在了。汪卫东对于鲁迅人生之苦的描述相当准确。正如他所指出的,走进《野草》之前的鲁迅,正处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深渊,这时的他,与佛教的“苦谛”最为接近。“苦谛”具体表现于《野草》即是鲁迅的自厌与自虐。深味人生之“苦”,并产生“厌离”之心,这两者,已近于佛教之门了。汪卫东关于鲁迅之“观受是苦”观,在《<野草>与佛教》中已有精彩描写,对此我深表赞同,此处不再赘言。
三、心念处,即观心无常,是以观心无常之慧力,对治“缘心执常”的颠倒妄见。“心”是生命的本质,同时是众生的中心,但心不是固定独存物,而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因缘和合的心物世界,即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世界,五蕴的身心世界是无常的,会坏灭的,故我们的心是无实体的,不过是心理或思惟之因缘关系的发展而已,绝无实体可捉取;而且心之现象,是念念生灭,刹那不住。怎么可以执它为常?由此观心无常之慧力,能使心念远离执常妄见的过患。《野草》关于心念无常的描写,最为精彩的莫过于《死火》。鲁迅自述:“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这种状态即是对于心念生生不息,刹那不住的出色描绘。然而,现今终于得到这样一个凝定了的“心念”——“死火”。它“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但是,就是这种本已凝结了的“心念”,一经我的“温热”助缘,马上“惊醒”过来,而且立即就要发生变化。接下来“死火”必须在“烧完”或“冻灭”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死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烧完”,“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这一切的产生、发展乃至突变,几乎都发生在一瞬间,无有丝毫短暂停留。如此这般的世界,我们又怎可执它为常,自以为会有一个真实恒定的世界存在呢?
四、法念处,即观法无我,是以观法无我之慧力,对治“缘法执我”的颠倒妄见。宇宙万法,都是因缘相互依存,我们的身体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四大(地、水、火、风)组合的躯体,一旦四大不调,五蕴离散,生命便死亡。佛说五蕴的“我”是“假我”。不可执为自性的我,统宰用的我。但众生无知,于无我法中,妄执有我,这种妄执叫作“我见”。我见有二:在有情上起执的,名“人我见”,在法上起执的,名“法我见”。也名“我执”和“法执”。有了我见,则有种种偏执烦恼,便不能接受正法。故要使心念安住于道法中,便要以“观法无我”之慧力,消除“缘法执我”的错误。关于鲁迅之首破“我执”,汪卫东已有精彩论说。他认为,《野草》首先不是回避和抛弃矛盾,而是采取了相反的路向,迎难而上,反而进入矛盾之中,把自身所有矛盾都摆出、打开,鲜血淋漓地展现出来,甚而把矛盾的双方进一步激化,推向极端,至于无可退避之境。这已经近乎一种“休克疗法”。求解脱就需破我执,但激化矛盾的方式无疑在我执的路上愈走愈远,《野草》主体为何如此执著于矛盾?绝望后仍寻找自我的努力,与佛教已知的无我背道而驰,但如果最终发现所谓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则最终与佛法殊途而同归。《野草》的追寻,到最后,并没有找到那不可分析之点——真正的自我或实在。它所最终证成的,是和佛法相同的结论,那就是“无我”。关于鲁迅之破“法执”,汪卫东在文中没有重点讲,但其实已经提到,即是他在文中所提到的“缘起性空”。*鲁迅能够深切理解大乘“缘起性空”的佛理,不但与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与北京时期的苦读佛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与他早年所接触到的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如尼采、克尔凯郭尔、叔本华、斯蒂纳、舍斯托夫等的影响密切相关。鲁迅正是集中了如此众多的思想资源才创作出他的极富个性特质的《野草》来的,这本身即是一件特别令人感到惊奇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并不是抽象地、被动地理解或接受这些资源。假如这些资源不与鲁迅自身的遭际发生密切的关联,促使鲁迅形成浓郁的存在体验,引发鲁迅对于诸如黑暗、恐惧、焦虑、绝望、希望、虚妄等的深切思考,这些资源也不过仅仅就是一些外在于人的体验的话语而已。所以,在这里最具关键意义的,恰是鲁迅的本心和自性。鲁迅正是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秉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的法则,才最终成就自己“反抗绝望”的思想特质的。而这一切均在《野草》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所谓缘起性空,系指大乘即菩萨乘修习法门。概括地说,缘起是说世间诸法众缘和合而起,同时亦因众缘分散而归于消灭。性空是说众缘合成的诸法,其性本空,没有真实的自体。所谓实相,即是无相。《野草》中最能阐释“缘起性空”这一大乘法印的是《好的故事》。但由于此“四念处”修行纯属小乘中声闻乘修习法门,故而在此只是一提。读者明了其基本意思即可。
由以上论述可知,鲁迅与佛陀在四圣谛之“道谛”中确然有诸多相似乃至相通之处。这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对于三十七道品中之“四念处”的理解。也就是说,虽则鲁迅与佛陀在最终追求目标和超越模式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其他三个圣谛,即“苦谛”、“集谛”与“道谛”上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乃至相通。经由四圣谛对于鲁迅与佛陀的精神世界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与探索,挖掘出其精神上的相同或不同之处,这绝非无聊之举。相反地,从其相同之处,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与佛陀的精神相遇,而从其不同之处,我们看到的则是鲁迅与佛陀各自的伟大。鲁迅之为鲁迅,佛陀之为佛陀,他们两者之所以有着各自的伟大,恰恰是因为他们两者有着各自的不同。
参考文献:
[1] 汪卫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鲁迅:鲁迅日记[A].鲁迅全集:第1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