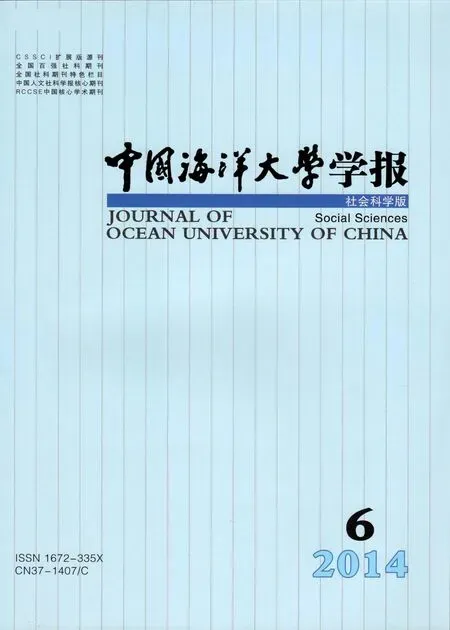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权辨析*
2014-08-18刘惠荣陈明慧
刘惠荣 陈明慧 董 跃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1959年签署的《南极条约》为南纬60度以南包括所有冰架在内的南极地区创设了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以“冻结”方式搁置各国对南极领土主张的争议,确立了向所有国家开放、和平利用南极的宗旨以及非军事化、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等国际治理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南极条约协商国签订了一系列保护南极的公约,加之历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建议、措施和决议共同构成南极条约体系。由于南极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环境,南极洲及其周围地区是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如何将人类的活动对南极这块“公地”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以保护南极的固有的荒野价值、美学价值和科研价值,一直是南极事务中各国重点关注的事项,也是历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早在《南极条约》缔结之前,美国与新西兰合作,在罗斯岛以划定“限制区”的形式保护历史遗址和科考现场,*Bob Thomso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Antarctica the Ross Sea Region. DSIR Publishing1990.287. http://agris.fao.org/aos/records/NZ910006这种做法逐渐为《南极条约》缔约各方所接受并推广应用。自1964年第3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以下简称ATCM)首次提出在南极设立“特别保护区”的概念以来,南极的各类保护区几经变化发展至今,总数已达73个,可以预测,未来将稳步上升。概括而论,南极特别保护区,即为实现区域内管理目标和保护其重大价值而被指定的包括海洋区域在内的南极的任何区域,在区域内管理国依据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审议通过的管理计划进行管理。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各国在主权冻结的南极区域建立特别保护区行使管理权的行为在确保南极环境保护的目的下是否有潜在的突破“主权冻结”的原则的意旨?各国在南极特别保护区内的管理权实践是否会给“后南极条约时代”的主权纷争埋下隐患?令人深思。
一、南极特别保护区制度的发展动态
(一)南极特别保护区制度的产生
1964年,第3届ATCM通过了《南极动植物保护议定措施》,首次提出在南极设立“特别保护区”的概念。*参见第3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最终报告,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3/fr/ATCM3_fr001_e.pdf.1966年,第4届ATCM首次设立了15个特别保护区。*参见第4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最终报告,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4/fr/ATCM4_fr001_e.pdf.1972年和1975年分别在第7届、第8届ATCM上讨论和提出建立特别科学兴趣区(Sites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SSSIs)问题,并通过了建议案VII-3(“特殊科学兴趣区”)*参见第7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最终报告,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7/fr/ATCM7_fr001_e.pdf.和建议案VIII-3(“特殊科学兴趣区”)。*参见第8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最终报告,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8/fr/ATCM8_fr001_e.pdf.1989年,第15届ATCM提出了建立包括特别保护区、特别科学兴趣区、多用途规划区和历史遗址与纪念物(HSMs)在内的保护体系。*参见第15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最终报告,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8/fr/ATCM15_fr001_e.pdf.1991年,南极条约协商国通过《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为《议定书》),将整个南极确定为“一个专用于和平与科学的自然保护区”*《议定书》序言表述为: Recalling the designation of Antarctica as a Special Conservation Area and other measures adopted under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to protect the Antarctic environment and dependent and associated ecosystems; 此处的特别保护区表述“Special Conservation Area”与本文涉及的南极特别保护区表述“Antarctic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是不同的,前者体现了协商国一致同意保护南极地区的环境的基本宗旨,而本文所关注的南极特别保护区是在南极地区因指定而单独划出来的区域,依据其管理计划而实行的区别于南极其他区域管理措施的区域。。1998年,第22届ATCM上专门设立了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CEP,以下简称环委会)。2002年,第25届ATCM依据《议定书》附件五“区域保护及管理”的规定,通过了决定1(2002)“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命名与编号系统”,将以往设立的各类保护区重新划分为南极特别保护区(Antarctic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ASPAs)与南极特别管理区(Antarctic Specially Managed Areas,ASMAs)两个类别,将历史遗址与纪念物单列并建立其目录,以往设立的特别保护区和特别科学兴趣区全部归入南极特别保护区,重新统一编号并命名。*参见第25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最终报告,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8/fr/ATCM25_fr001_e.pdf.根据《议定书》附件五第3条的规定,任何区域,包括任何海洋区域,均可被指定为南极特别保护区,其目的是保护显著的环境、科学、历史、美学和荒野形态的价值或者任何此类价值的结合,以及支持和协助正在进行的或计划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ANNEX V TO THE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 AREA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ARTICLE 3 “1. Any area, including any marine area, may be designated as an Antarctic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 to protect outstanding environmental, scientific, historic, aesthetic or wilderness values, any combination of those values, or ongoing or planned scientific research.”附件五的第4条同时规定进入南极特别保护区需要取得相关的许可证。*ANNEX V TO THE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 AREA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ARTICLE 3 “4. Entry into an Antarctic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 shall be prohibited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a permit issued under Article 7.”
(二)南极特别保护区的设立程序
关于南极特别保护区的预选、申报、审批和管理等事项,《议定书》附件五“区域保护及管理”和环委会(CEP)先后发布的“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计划编写指南”(1998年)、“南极特别保护区框架性实施准则”(2000年)以及“CEP审议南极特别保护区与南极特别管理区草案及其修改稿指南”(2003年)等一系列文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保护区的申报是由申请方在当年召开的ATCM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将英文版的“管理计划草案”提交给环委会和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SCAR),如果草案涉及南极海域的内容,还应提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CEP会参考SCAR以及CCAMLR的意见审议管理计划草案,向ATCM递交是否应通过该管理计划草案的建议报告。南极条约协商国在ATCM上依据环委会的审议建议并且按照“协商国一致同意”原则决定是否批准该管理计划草案。同时依据《议定书》附件五第六条的规定,管理计划每隔五年需重审一次,并按要求进行更新。对更新的管理计划的审批将遵循上述审批程序。一旦申请的区域被指定为南极特别保护区,依据《议定书》附件五第六条的规定,对该保护区的指定是无期限的,除非管理计划另有规定。可以说,一国南极特别保护区设立的核心就是“管理计划草案”的编写和审议。根据《议定书》附件五对管理计划的要求,提交的“管理计划草案”应该遵循一定的格式,内容包括引言、价值描述、保护目标、管理活动、保护期限、保护区区域描述、特殊地带的确认、地图、参考文献、许可证发放的条件和相关条款等内容。一份“管理计划草案”的编写并非易事,围绕申请区域所开展的各项基础性研究与长期性监测工作是特别保护区“管理计划草案”编写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一国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该国的南极科考水准,目前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数量较多的国家,也都是公认的南极科研强国。近年来新通过的“管理计划草案”一般都是经过了几届ATCM讨论、评议和修改后才获得批准,审查较为严格。
(三)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现状
南极特别保护区制度建立以来,已有不少国家单独或者与其他国家合作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尤其是澳、新、美、英等一向表现活跃的协商国更是不遗余力投入巨资。截止2014年6月底,已有15国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73个(表一)。澳、新、美、英四国设保护区的数量均超过了10个,四国的数量之和占了总数的67%。*数据来源于南极条约秘书处网站http://www.ats.aq/devPH/apa/ep_protected_search.aspx?type=0&num=&name=&prop=0&lang=e,最后访问于2014年7月22日。

表1 管理ASPA区域的国家
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现设有11个南极特别保护区,其中10个为单独设立,1个是与中国联合设立。从设立的理由和保护目的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为了保护南极动物栖息地(第101号、第102号、第103号、第160号、第164号、第167号、第169号);二是是为了保护和研究区域内苔藓和地衣群落(第135号、第136号);三是是为了保护和研究区域内有脊椎动物化石(第143号);四是为了保护区域内南极探险英雄时代遗留的莫森棚屋(第162号)。澳大利亚虽然不是保护区设立最多的国家,但却是把其南极利益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的国家,对保护区的设立管理予以充分的重视,可谓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的翘楚。
澳大利亚在其管理计划中规定的管理措施主要有:(1)在保护区边界放置标志并加以维护。可以防止未经允许误入,对放置的标志定期维护并在不再使用的时候将其移除。(2)许可证制度。进入保护区需持有经由国家主管部门核准颁发的特别许可证,且须随身携带许可证或者有效副本,在区域内开展的活动应限定为与保护内容相关的科学研究或者其他符合保护区管理目标的活动,严格执行许可证有效期限;建立活动结束向有关部门提交活动报告制度。(3)限制交通工具进入保护区。包括陆上交通工具的禁入或者对行车目的、行车路线、停泊点、与要保护的动物间距离等条件做出限制后的准入;直升机等航空器的禁入或者有条件的飞越;水上交通工具的使用规则等等。(4)对保护区内活动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区内活动范围在管理计划中也是有限制的。例如135号特别保护区的管理计划中规定在整个保护区区域内禁止野营;143号特别保护区的管理计划则规定除了指定的某部分区域之外在其他范围内禁止野营。以保护区域内南极动植物为目的设立的特别保护区会在其管理计划中对保护区内活动的时间做出规定。例如在169号特别保护区的管理计划中规定在保护区内人类活动的时间限制适用于全年任何时间段。尤其是5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孵化期,7月上旬至12月中旬的亲鸟育雏和雏鸟生长期,期间严格控制人类的进入与活动。(5)对带入保护区内物品的限制。包括严禁将活动物、植物、微生物带入保护区内;严禁家禽制品的带入;禁止将除草剂和杀虫剂带入保护区,经许可证授权为科研目的或者其他符合管理目的而带入其他化学试剂,也应在使用结束后规定的时间内移出;保护区内禁止存放燃油,因科研或其他管理活动所必备的燃油,也必须获得特别许可才可使用并在使用结束后立即移出等等。(6)对保护区内动、植物区系的保护。未经许可禁止对保护区内动、植物区系进行采样或进行任何损害动、植物区系的活动;经许可而进行样品的采集等科学研究活动,也必须严格按照SCAR的相关规定进行。(7)废弃物以及未经许可带入物品的处置。保护区内的科研或者其他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各类废弃物,以及未经许可进入保护区的物品应该及时收集并移出保护区,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活动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
澳大利亚在其管理计划中规定的管理措施详细全面,对保护区内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成效显著。有充分的研究证据表明,人类在南极的活动,包括游客的参观、车辆的驶入、飞机的低空飞行等都对南极的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干扰。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根据管理计划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对划定区域进行特殊的保护,能够有效减少上述活动对南极环境造成的干扰。
二、南极特别保护区设立国管理实践分析
毋庸置疑,设立特别保护区对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意义重大。但是在充分肯定这项制度的同时,不少人对在南极地区由有关国家而不是国际组织实施管理权存在疑虑,即它会不会冲击南极条约体系所确立的冻结主权的根本宗旨。
自18世纪南极被发现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主权纷争,直到1959年《南极条约》冻结了各国的领土主权要求,禁止各国在条约有效期内提出主权要求,也规定各缔约国不得在南极创立任何主权权利。*《南极条约》第四条。针对《南极条约》第四条冻结主权的表述,学者们发现,作为解决南极领土主权问题核心的第四条,“表述得是如此的含糊其辞,其使用措辞优势如此的微妙精炼,使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或解释其权利已在‘条约’中得以保留之法律依据。”[1]美国国会参议员格吕宁认为:它说明了它不意味着什么,但它却没有说明它意味着什么。时至今日,许多国家仍未放弃对南极地区的主权主张,各种宣示主权行为层出不穷,企图用各种事实强化其在南极的政治存在,如智利、阿根廷在南极建立邮局、机场等设施,1978年一个名叫帕尔马的阿根廷孩子在南极出生后马上被宣布为阿国公民;新西兰《公民法1977》规定,凡出生在南极罗斯属地的婴儿自然成为新西兰公民。结合这些现象我们不由得产生疑惑,各国积极在南极设立特别保护区,实施区域环境管理的行为是否存在着“后南极条约时代”跑马圈地的宣示主权的可能性?
保护区建立的基本法律依据是1991年《议定书》附件5“区域保护及管理”的规定。《议定书》包括附件是全体缔约国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为所有缔约国确立了南极活动行为指南,规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义务。可见,建立保护区并实施区域环境管理是每一个缔约国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而非权利。
各国在保护区内实施的管理权是否隐含主权权利的含义?是否违背南极条约体系“主权冻结”的原则?自让·博丹和胡果·格劳秀斯创造出主权概念以来,人们基本上认为主权包含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两个方面。印度德里大学法学院教授兴戈兰尼(Dr. Hingorani)认为,国家通过行使主权而引申出许多权利:平等权、领土管辖权、在其领土内确定国籍的权利、管理出入其领土的权利和国有化的权利,就是行使主权的一些表现。[2](P103-104)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的伯恩哈特(R. Bernhardt)教授主持编写的《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将主权定义为:“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国家之外且法律上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渗透,以及国家的排他性的管辖权和其领土于人民的政府权力的至高性”。[3]综上所述,国际法领域普遍认同一国主权具有两项特性:对内主权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人或事物拥有完全和排他的管辖权;对外有权依照国际法原则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一切事务,不受他国的干涉。由此可见,管辖权或者管理权是国家行使主权权利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主权与管辖权或管理权的关系是主权与治权的关系。
南极地区既不属于某些国家所有,也并非全人类公有。正像格吕宁所言,南极条约仅用了排除法,并未正面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可见,各国管理权的实施不意味着行使主权权利,那么它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履行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吗?如果是的话,保护南极生态环境的义务应当是对世义务,即一国对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它不会产生完全的、排他性的独占权力。我们需要对南极特别保护区内管理权的权利来源和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管理依据是管理计划。依据南极特别保护区设立程序的规定,管理计划草案由申请国编写,最终在ATCM上由南极条约协商国决定是否批准。根据ATCM的议事规则,提交的“管理计划草案”需经与会的协商国一致同意才能得到通过。修订的管理计划的审查批准也由南极条约协商国决定。由上述过程可以看出,管理计划虽然由管理国编写、修改并负责实施,但其审批权掌握在各南极条约协商国手中,其效力来源是由各南极条约协商国组成的ATCM而非管理国。换句话说,管理国制定和实施管理计划要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威——ATCM,不符合主权对外独立自主的特性。另一方面,管理国行使的管理权也非排他。《南极条约》规定,协商国有权指派观察员执行任何视察,“所指派的每一个观察员,应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时间进入南极的任何一个或一切地区”,*《南极条约》第七条第二款。并且指派的观察员只受所属的协商国管辖。*《南极条约》第八条第一款。《议定书》附件五“区域保护及其管理”第九条“信息及公开性”和第十条“信息的交流”体现了对管理国的义务要求。此外,ATCM通过每隔几年审查管理计划的方式对管理国进行监督。这种非排他性的管辖权也不符合对内至高无上的主权特性。所以,管理国在南极特别保护区内实施管理权并非行使主权权利,没有突破南极“主权冻结”原则底线。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虽然行使管理权没有突破南极“主权冻结”原则底线,但是却体现了各国际行为体在南极地区的利益博弈。早在1625年,格老秀斯就指出,国家会从国际法的遵守中获益。当代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芝加哥大学的埃瑞克·波斯纳借助理性选择作为分析工具,指出国家是出于利益而遵守国际法,而不是基于“有约必守”的信念等传统国际法对国家遵守动机的认识。*参见[美] 杰克·戈德史密斯,埃里克·波斯纳著:《国际法的局限性》,龚宇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所以,不排除这种管理权的实施对未来南极局势存在潜在的危险。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愈来愈以国家权益为标尺,南极的资源价值、环境价值、科学价值和地缘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许多国家纷纷加大国家投入来增强本国在南极的实质性存在。新建或扩建本国的南极活动基地,强化南极科学考察活动,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申报更是作为实现本国对南极有效管辖的重要途径来大力推进,并且这种管理权的实践已经得到了南极条约协商国或者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从澳大利亚特别保护区所在的位置来看,其所有独立申请的南极特别保护区均位于其提出领土主张的“澳大利亚南极领地”的范围内。*1933年,澳大利亚宣称对位于45°E 至136°E 之间,以及142°E 至160°E 之间的南极大陆与岸外岛屿享有主权,这个范围的地区被命名为澳大利亚南极领地。《南极条约》只是将各国在南极的主权要求冻结但并未废除,一旦这种冻结被解除,届时南极主权争端再起,各主权声索国在其本国南极特别保护区内有效的管理实践虽不足以构成国际法上的“先占”,但是也将会成为南极主权争夺战中的一个重要筹码,给“后南极条约时代”的主权纷争埋下隐患。即使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协商国在南极没有领土主张或者申请的特别保护区位于没有领土主张的区域,依据前文提到的《议定书》附件五第六条“除非管理计划另有规定,对该南极特别保护区的指定是无期限的”的规定,该国也可以依据南极特别保护区制度无期限地在所申请区域内继续实施管辖权。可以说,无论一国是否提出领土主张,其在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都是其参与到南极利益分享中的有力的资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南极条约》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欢迎所有国家的加入,*《南极条约》第13条。但是在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一事上却设立了很高的门槛,即后来加入的国家必须在南极建有科学站或派遣科学考察队的具体科学研究活动才可以成为协商国。*《南极条约》第9条“二、任何根据第13条而加入本条约的缔约国当其在南极进行例如建立科学站或派遣科学考察队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而对南极表示兴趣时,有权委派代表参加本条第一款中提到的会议。”目前的南极条约协商国只有28个,非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体系中影响力有限,加上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申请需要以雄厚的南极科考实力为基础,所以说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参与到南极管理事务当中来,管理权实施带来的南极权益也只能由几个在南极表现活跃的国家分享。
另外,从国际法的视角看管理权实践,就必然会联系到悬而未决的南极法律地位之争。其一是南极领土主权声索国以南极为“无主地”为由,依据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声索对南极的主权。其二是一些非协商国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张南极的法律地位应参照国际海底区域或者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应由全人类共享。“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最早因国际海底区域内矿产资源问题而提出,之后被应用于《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1979)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以下简称《公约》)之中。从上述协议和公约中相关内容的规定来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具有以下特征: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能主张主权或由国家进行管辖;对其区域的开发和探索必须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并且利益应为全人类共享;对其开发和探索应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管理权由全人类分享;区域应专为和平目的利用并且科学研究自由。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许多南极条约缔约国并不赞同。他们的反驳理由是,现在已有七国对南极地区提出过主权要求,因此不能认为南极地区不存在有效的主权要求;“人类共同继承财产”重点关注区域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益分享,而南极条约体系中的《马德里议定书》禁止在南极进行矿产开发等等。基于南极、国际海底、外层空间和天体在国际法上特殊的法律地位,其三是有学者提出“人类主权”(Human Sovereignty)或“全球主权”(Global Sovereignty)的理论。[4](P111-112)这种理论强调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外,还要从人类的全球社会角度探讨主权关系。在这种主权下,国家执行的并非其自身的价值观、利益和特征,而是代表人类社会的主权。基于“人类主权”理论,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国行使管理权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人类社会在特别保护区内行使主权,维护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调整海洋关系的并为最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公约》虽然在其文本中刻意避免使用“南极”字眼,但主流观点认为如果要排除《公约》在南极海域的适用,必须有明确的规定,而事实上并没有作出规定。1986年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也指出,《公约》是适用于所有海域的全球性公约,任何海域都不例外。[5]这样南极地区就存在着南极条约体系和《公约》两种法律制度之间的互动。依据《公约》,沿海国有权主张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一系列权利。但是由于南极的“主权冻结”,“沿海国”这一概念在南极条约体系之下无法确定。至少在目前的形势下,《公约》在南极地区的适用困难重重。南极地区法律地位的争议还在继续,并且没有哪一种主张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从特别保护区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对南极地位的定位在南极事务的发展过程中被弱化了。南极条约协商国搁置了南极法律地位之争,采用协商一致的方式一直在推进南极事务的开展。
南极问题的核心始终是南极主权的归属问题。在“主权冻结”的前提下,南极区域保护管理权实践已然实质性地享有了在南极的权益,同时也产生了模糊淡化南极真正主权归属的效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南极主权的不确定性导致南极事务管理权的诸多‘症结’,同时,主权冻结成为各国争夺南极事务管理权的前提和动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南极事务管理权的争夺加剧与南极主权之争的淡化趋势是相互促进的。”[6]许多学者依据《南极条约》签订以来五十多年的实践对未来的政治前景进行了预测,代表性的观点是存在三种发展可能:一是南极大国为争夺南极利益而退出《南极条约》,从而引发整个条约体系的解体;二是随着《南极条约》的成员国的不断增多引起南极条约组织的“泛化”,南极洲被“联合国化”并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第三种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大力维持下,南极条约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得以继续存在,主权冻结将发挥持续性作用。[7]在以上几种预测中,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在没有找到解决南极领土主权纷争的途径之前,目前最好的、也是唯一能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并且南极条约国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就是维持《南极条约》现状,继续坚持“主权冻结”原则。
四、结论
1991年第17次南极条约国协商会议上决定,将《南极条约》有效期无限期延长和50年内禁止南极的矿产资源活动。“主权冻结”原则仍继续有效。虽然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区域保护和管理并不能作为未来声索南极领土主权的主要证据,但是,当今国际社会已不再是以武力开拓疆土的时代,这种管理权实践其实是彰显国家在南极的实质性存在的良机,环境保护可以说是最好的切入点。未来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申请和管理权的竞争会愈来愈激烈。
我国是南极条约协商国。随着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南极在资源、科学和地缘战略等方面价值的日益凸显,中国在南极地区的利益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时至今日,中国在南极科考和特别保护区的设立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我国在南极单独设立了格罗夫山哈丁山特别保护区(ASPA 168),并与澳大利亚联合设立了阿曼达湾特别保护区(ASPA 169)。但与西方科考大国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在南极并没有领土主张,南极在“主权冻结”原则下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既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利益。鉴于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方面的大国责任和国家权益的考量,我国应该在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事务上投入更多的关注,积极推进我国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申报和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 颜其德,朱建纲.《南极条约》与领土主权要求[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5):79.
[2] (印度)兴戈兰尼著,陈宝林等译.国际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3] 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R. Bernhardt ed.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msterdam 1987, p.404.
[4] (日)星野昭吉著,刘小林,张胜军译.全球政治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5] 阮振宇.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冲突与协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33.
[6] 程保志.“治理与合作:2011 中国极地战略与权益研讨会”会议综述[J].国际展望,2011,(6):4-5.
[7] 郭培清,石伟华.《南极条约》50周年:挑战与未来走向[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