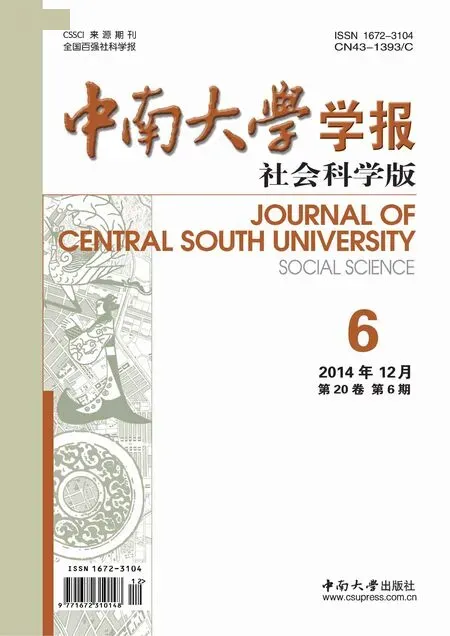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2014-01-22朱鹏王刚
朱鹏,王刚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朱鹏,王刚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国家自主性思想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国家自主性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蕴涵分立,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国家的权属、国家的作用对象和国家的利益指向性方面。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又一体相系,官僚集团的自利性说明国家自主性背离国家公共性是国家权力运使的经常情形,而基于国家自身的行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国家自主性也能偏护国家公共性。国家自主性并非必然促进国家公共性,其在合理限度内当以国家公共性为旨归。
马克思国家理论;国家自主性;国家公共性;国家的权利主体;国家的行动逻辑
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中,除了国家阶级性思想和国家公共性思想之外,国家自主性思想也是马克思自觉察知的内容:“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讨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1](79)由于国家自主性的引入,国家阶级性和国家公共性两相对分的国家性质结构也就自然地变成了阶级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三足鼎立。较之国家阶级性和国家公共性之间相对鲜明、清晰的对立统一关系,学术界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却颇有争议,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国家自主性
自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首次使用“国家相对自主性”[2]这一术语以来,按照邓利维和奥利里的说法,“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都已经被输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的观念”[3]。这种观念对国家自主性作出了两重必要的形式上的限定:国家自主性不是泛指任何社会形态中的国家的自主性,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国家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究其实质来说,国家自主性观念批评的是在解释国家问题上持有粗疏和浅薄观点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所以国家的自主性是相对于社会共同体中的经济基础和阶级集团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的语义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体系的,其意在于国家能够在部分程度上挣脱经济关系的粘滞和阶级关系的拘束,从而取得一种相对的独立地位。在国家自主性的研究视野中,“国家(相对)独立性”和“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内涵并无二致。只有独立,才能自主,“在这里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1](90)。如何界定国家的自主性,学术界的说辞不一而足。能够确定的是,国家自主性并非宽泛意义上的国家的自在性和自为性,而是指国家作为自主的仲裁者,独立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集团,追求自身行动的政治逻辑和特殊利益的性质。
在国家自主性探讨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选用的词汇是国家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以社会决定国家、政治国家基于市民社会为理论本原,国家机器被视为在生产关系的底基上浇铸的上层建筑,国家对经济关系具有天然的依附性。但与经济决定论鼓吹社会运动中经济因素的唯一性和经济关系对政治进程的单方面的决定性不同,经典作家认为经济因素和政治系统始终处于双向作用的互动之中。恩格斯晚年在批判经济唯物主义之时专门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写道:“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4](701)国家权力发挥能动性的反作用,在此国家的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独立于生产关系凝聚的经济力量。马克思所认为的国家独立性更为主要地体现在国家独立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拼合的阶级力量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5](132)早年马克思认为,由于专制主义社会中等级的余威还在、阶级的发育迟缓,政权被官吏、军官并有旧贵族和资产阶级填充其间的特殊等级所把持,国家的阶级属性还不明显,在这种社会不会出现成熟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而只能是以君主为首的官僚等级的专制统治为表现形式的独立性的国家。
马克思用以分析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经典范例是法国的波拿巴主义。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主义的行政帝国“把国家政权当作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6](119)。马克思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保持了均势,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能力直接掌握政权,国家跳出了阶级关系的管制,从而能以相对独立的形象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居中调停、纵横捭阖。对于这种阶级力量制衡的政治态势造就的国家独立性,恩格斯总结道: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4](172)。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相对于社会来说的,即国家独立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作为自主的第三方独立于社会的阶级体系,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因为国家不可能彻底摆脱赖以生成的经济基础及与阶级集团的联系;第二,国家自主性的生成需得有多方面因素的合力协作,如得力和有效的阶级统治的缺乏、阶级力量变化促成的政治平衡、强大的行政权(官僚组织)控制着国家机体等;第三,自主性国家只是国家形式的一种偶然性的“例外”,马克思谈及的德国君主专制主义国家、波拿巴主义国家等皆为历史进程中政权形态在特殊时代的非典型形式,这样的国家大都出现于阶级利益均势下的过渡时期;第四,马克思的自主性国家理论只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经验性观察,不具备规范性意义,与马克思的兼具规范性和经验性的阶级性国家理论不能同日而语。
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思想足迹,以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建构了系统的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论走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和社会阶级的分析路线。普兰查斯袭用了马克思的分析结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主性是其首先论及的内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在实际占有关系的框架中,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赋与国家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以针对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自主性”[7](310),继而又转向了资本主义国家和阶级方面的自主性分析。普兰查斯虽然认可国家自主性只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现象,但他不同意经典作家对其做出的“例外”这一特殊性设定,国家的自主性已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一般属性和普遍特征。密里本德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甚至提出:“一切阶级国家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论这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也不论它们是多么‘有代表性’或多么‘民主’”[1](91)。依托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密里本德擅长讨论国家机构和官僚集团相对于统治阶级及其内部构成的自主性,这和普兰查斯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着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分离是稍有不同的。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都对国家自主性作以相对性的阐释。因为每一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始终都是由统治阶级管控的,同构性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甚至思想关系)决定了国家难以逃脱由其编织的社会关系的缠缚,拥有绝对自主性的国家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二、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的区别
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是社会管理的机关,也是自主的仲裁者;国家集合了统治工具、公共机关、仲裁者三个角色,是阶级性、公共性、自主性三重性质的完整统一。“国家三性论”是当代学术界国家理论研究的基本议题。马克思虽以论证国家阶级性见长,但其国家公共性和国家自主性的分析都是一并在场的。列斐伏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包含了三种草图:“统治阶级的(经济上,然后是政治上的)工具”的国家,“从表面上看,是独立于各个阶级”的国家,“关心整个社会、管理市民社会的国家”[8](125-140)。事实上,多元主义、新右派、精英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新多元主义等五种国家理论的国家几乎都拥有三种形象——“傀儡者形象”“护卫者形象”和“党派形象”;对应这三种国家形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分为三种模型:“工具主义模型”“功能主义模型”和“仲裁者模型”[9]。国内学术界对国家三重性质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有学者明确指认了国家的三种层次:“阶级国家或国家的阶级性质”“公共国家或国家的公共性质”和“官僚国家”[10]。“三种草图”“三种形象”和“三种模型”,抑或是“三种层次”,实际上遵照的正是国家阶级性、国家公共性和国家自主性的划分逻辑(相应地,国家也表现为三类形态:阶级性国家或工具性国家、依附性国家、俘获型国家;社会性国家或公共国家;自主性国家或仲裁人国家、官僚国家、掠夺型国家)。国家的性质划分为三的事实说明,不仅国家公共性和国家阶级性是有分殊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也是能够加以区别的。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两者分殊的第一层内容当在国家的权属或国家权力主体方面。依照国家公共性,作为公共权力载体的国家在理念上是属于全体民众的,某一社会中的国家应被构成这一社会的全部成员所共享,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全部社会成员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在这里,国家权力主体是与公众、民众、大众等“整体”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和诸如个体、群体、团体等“部分”观念无关的。国家自主性却是一种“部分”观念:操有国家权力的是社会中的官僚阶层,国家是官僚统治的工具,官僚才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官僚,即执行政务的行政官员,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霸占着国家机器,官僚与统治阶级在身份上是重合的,政府官员通常由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员担任,统治阶级亦可借由官僚贯彻阶级意志而不必亲自出马。官僚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却不必然就是统治阶级本身。官僚和统治阶级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张力关系往往是国家自主性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的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主要是在涉及那些行政权力特别强大的制度的时候。”[1](91)在强势的自主性国家中,阶级统治可能要让位于官僚统治,行政官僚可以取代统治阶级执掌国家政权,从权力的行使者上升为权力的所有者。固然这是由于官僚势力的膨胀,其中也有统治阶级自身的原因。对于后者,密里本德和恩格斯都以资产阶级为例给出了说明。
密里本德认为资产阶级自身的不统一阻碍了它对国家权力的顺利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成分构成的,资产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只要那个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它绝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它就不可能像委托人对代理人那样行动,‘它’也就不能够简单地把国家当作‘它的’工具。”[1](73)晚年恩格斯也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并不是完全由资产阶级操控的,资产阶级已然丧失了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6](713)于是,统治阶级退出了国家政权,官僚代替统治阶级把控了国家。总之,在国家的权属或国家权力主体方面,国家公共性以国家为全体民众的国家,国家自主性则和官僚相联系,国家被官僚阶层掌控了。这是其一。其二,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的分别体现在国家的作用对象方面。依据国家公共性,国家的作用对象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及事关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由此推之,在国家自主性那里,国家的作用对象是官僚阶层的成员,即国家作用于官僚成员自身,反映、代表和维护该阶层的共同利益。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分布着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及为数众多的官僚人员。由于官僚身处政权系统之中(官僚本身就是国家系统的要素之一)实际操持着国家权力,因此极易出现官僚挟权倚势、权力自肥、退化为利益集团的情况。
官僚集团及其特殊利益的产生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官僚阶层的自利性暴露了官僚政治的市侩化本色。官僚政治形成于“活动日益增多的、分化的、自主性越来越高的行政机关”组成的政治领域,“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不同的、只顾自己的利益的承载者”,“它们主要是为了考虑自己的目的而活动”[11]。官僚阶层并不必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更不必然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官僚本身就是独立于社会各个阶级的,它在怠于服务统治阶级而精于算计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蚕食着被统治阶级。比之阶级性质的国家,官僚性质的国家对社会的攫取和剥夺同样是触目惊心的:这种国家“竖立于整个社会之上,既表现出寄生性,又表现出掠夺性,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它能掠夺整个社会的成果”[8](129)。马克思向来重视对官僚政治的揭露。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政治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本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12]。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国家称呼为“寄生机体”[5](624)和“寄生政府”[6](118)。可见,国家自主性遵从的也是“国家所有者得利”这一逻辑。依据国家公共性,国家在理念上既然属于公众所有,那么它就应该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造福社会大众;在国家自主性看来,国家既已被官僚掌控,那么它也必然会作用于官僚成员,为官僚阶层牟利。以国家活动的目的或归宿而言,国家自主性和国家阶级性一样都指向了悖于社会公益的特殊私利。于是,在国家行为的利益指向性方面,“私利”与“公益”之别也就构成了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两者分殊的第三层内容。
三、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的联系
我们说国家阶级性和国家公共性是统合为一的,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能单独显像的,探讨两者的分殊和联系必须拎出其中的原则性规定方才可行,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亦是如此。这里分析问题时都是专注了某一种性质的纯粹性,除去了与之互融、相嵌的其它两种性质的干扰。因为但凡国家必是阶级性、公共性和自主性三种性质合成的有机体,而且在这个由三种性质构筑的立体结构中,每种性质的构成亦非等量不变的;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具体展露何种面相,某一性质在这一三维坐标系中定位何处,须依自身所占的权重而定,取决于和其相关的人群主体的力量消长状况,即社会公众、统治阶级和官僚阶层的三方博弈。因此,考察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的联系须以确认两者的分别为前提,尽管两者本身是无法做出理想化的区分的。国家自主性虽和国家中立性相似,但乏有国家中立性那种公正无偏的意涵。换句话说,虽然国家获得了独立于社会的自主性,但它位居对立的社会各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以被统治阶级为主的社会大众)却无法避免倾向于各种力量体系。国家自主性追寻的是国家行动的自我逻辑,这就意味着公正不是国家唯一的或首选的行事原则;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权衡,既可能不会对统治阶级和社会大众一视同仁,也不会持久青睐于某一方;好恶与否,全凭一己之私。这说明了在静态的逻辑向度上,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的联系至少呈现为两种样态,即国家自主性背离国家公共性,以及国家自主性偏护国家公共性;官僚式国家的自利性表征的权力变质与政治腐败已然证明了前者,这里的重点是分析作为偶然情形或非常态的后者。
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公共性能否契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不厌其烦地揭批官僚政治的行为表明他对官僚国家并无好感,对于能从国家自主性中导出国家公共性表示怀疑。马克思把官僚阶层视为附随于统治阶级的寄生群体,官僚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人甚至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官僚的政治行为大体上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偏好的,官僚集团的阶层利益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熔铸一体,二者鲜有根本性的龃龉。在马克思看来,国家自主性和国家阶级性并无本质性的殊异,在背离国家公共性这一点上两者都是相同的。不过,马克思是立足于国家阶级性来审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公共性的,如若从国家自身的行动逻辑出发,以国家自主性来观察国家阶级性和国家公共性,那么问题又会有所不同。国家自主性不满意把国家简单地还原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它批评的虽是阶级还原论,却不自觉地导向了对国家公共性的眷顾,因为国家公共性和国家阶级性正好行于相反的道路上。普兰查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代表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而能保证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这种保证甚至会违背统治阶级的短期利益,“国家代表人民大众全体一般利益的这种专有的特性,并不单纯是虚构的神话”[7](207-209)。密里本德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政策并不必然就为资产阶级赞许,有时反而会与资产阶级的意志相左,例如罗斯福新政就使社会民众得益而让资产阶级的部分利益受损,“当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1](76-77)。因此,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公共性不是必然的分立,两者也有相合、一致之处;国家可以超脱阶级利益的制约而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国家自主性偏护国家公共性也是国家自身内存的现实机制。
国家自主性在偏护国家公共性这一问题上所能自主张弛的程度,既要依赖于国家自主性本身的程度,追根究底还是要被国家的阶级性所限。国家没有绝对的自主性,经济秩序奠定了政治秩序,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要服膺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臣服于统治阶级作为政权所有者的客观法则。国家自主性只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的自主性不但不会背反国家的阶级性,而且恰是国家阶级性的现实选择。“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并不减少它的阶级性质;相反,它的相对独立性使国家有可能以适当灵活的方式行使阶级的任务。如果国家果真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那么它履行其任务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1](95)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促使统治阶级和国家之间处于一种并非直接结合的微妙关系之中,从而彰显了统治阶级统治技术的经验老道。统治阶级从国家中心抽身出来、疏离于政权之外,国家充当了中间地带的缓冲力量,以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游刃于社会各阶级之间,作为貌似公正的仲裁人调解阶级冲突、平衡阶级利益、缓和社会危机、控制社会秩序,既维护了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避免了它和被统治阶级直接发生对立,又通过自身形式上的中立性做派掩护了统治的阶级性质,消解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统治阶级对国家行使的虽是间接统治,却达到了更为直接的目的。因此,国家自主性只可能偏离国家的阶级性,其在总体上附属国家阶级性的状况表明了它在关照国家公共性上不可能会大有作为。虽然一个自主性的国家能够迫使统治阶级牺牲某些利益而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让步,但这种牺牲是微不足道的,并不能构成对统治阶级权力(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实质威胁。
大致来说,在近代以前国家吞噬、挟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国家的阶级性强于国家的公共性,所以阶级性限制了自主性,但国家的自主性也是持续增长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呈现出正相关的变化关系;在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和谐交融的历史时期,则是国家的公共性限制了自主性,国家的自主性是不断减弱的,国家公共性与国家自主性呈现出反相关的变化关系。因此,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公共性并不存在必然的前后一致的关联性,自主性既可能反对公共性,也可以支持公共性。之所以如此,探其内由,还是缘于国家本身的自主逻辑。国家并非只是受制于统治阶级、为其马首是瞻的被动性的附庸工具,它同时也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积极的行动者,更是一个如同其他社会行动者那样谋求集团利益或个人福利的的利益主体。
[1] 拉尔夫·密利本德.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 范春燕.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J]. 学术论坛, 2009(9): 34-38.
[3] Patrick Dunleavy, Brendan O’ Leary.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M].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Education, 1987: 258.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 尼克斯·波朗查斯.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8] 亨利·列斐弗尔. 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M].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9] 帕特里克·邓利维, 布伦登·奥利里. 国家理论: 自由民主的政治学[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223.
[10] 孙越生. 国家必然消亡吗[J]. 社会科学战线, 1985(3): 107-111.
[11] 贾恩弗朗哥·波齐. 国家: 本质、发展与前景[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34-13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60-61.
Link and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 autonomy and its publicity
ZHU Peng, WANG Ga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The thought of state autonom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arx’s state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state autonomy is also the basic paradigm of western Marxism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ublicity of state and state autonomy have many differences with each other, such as the ownership, the target and the interest orientation. The publicity of state and state autonomy are closely connected. The selfishness of bureaucratic group can regularly deviate from the national public, but based on its own action logic of state, state autonomy can protect the publicity of state to a certain extent. Although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promote the publicity of state, state autonomy should maintain the publicity of state for the purpose in the reasonable limits.
Marx’s state theory; state autonomy; publicity of state; interest subject of state; action logic of state
D03
A
1672-3104(2014)06-0201-05
[编辑: 颜关明]
2014-01-14;
2014-10-28
朱鹏(1985-),男,江苏南京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王刚(1985-),男,安徽蒙城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