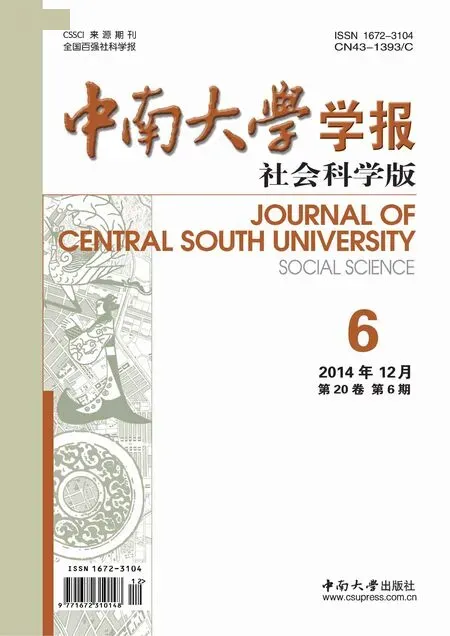城市形象视觉管理研究
2014-03-03孙湘明孙颖马玮丽
孙湘明,孙颖,马玮丽
(1.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83;2.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城市形象视觉管理研究
孙湘明1,孙颖2,马玮丽1
(1.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83;2.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城市形象以最为直接和最具普遍认同感的视觉形式进行传播,其视觉符号是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视觉载体,构成了城市视觉管理的物资媒介。以城市形象设计和城市管理理论为基点,从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出发,提出视觉文化现象是城市管理向视觉管理转型的基本动因;从精神表征化与管理可视化角度,探讨城市形象视觉管理的潜能与可行性;从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形式角度,提出意象规范的隐形管理功能和形象规范的显性管理功能构成了规范化管理形式,以及形象战略定位差异与视觉识别差异所形成的独特的差异化管理形式。
城市形象;视觉管理;价值观;视觉化
一个国家需要一种形式来体现力量,一个城市也需要一种形式来体现精神。城市形象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体现城市精神的独特视觉形式,成为一座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也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形象是人们脑海中所形成的对一个城市的综合认知印象,也是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意象。城市形象战略设立的初衷是出于营销城市的目的来打造城市品牌,并非出自于城市管理的需求,但目前无论是在战略规划阶段,还是在实施过程中,城市形象对城市的管理功能已逐步显现出来,并形成了城市形象视觉管理这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独特的管理形式。
一、城市视觉管理的动因
时代在变化,城市在变化,管理的形式也在变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丁·海德格尔就曾预言读图时代的来临,甚至极端地认为现代世界的本质正演变为图像[1]。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视觉化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并由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急速膨胀,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定式,构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视觉文化现象。
城市形象在21世纪的今天,已不仅被看作一个城市发展战略,还被看作一种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管理形式。伴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城市视觉管理的形式和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则是以视觉可触及的感知样式为呈现形态,将抽象的、非物质性的城市精神与价值观物化为可视的视觉形态,以视觉符号的形式直观地传达于受众,实现其管理职能。
(一)城市精神的表征化
城市精神是维系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哲学。正如日本学者小川和佑所言:“一座美好的城市什么都可以缺少,唯独不能缺少精神。”[2]城市精神犹如一座丰碑,唤醒公众的主体意识,强化城市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并且以此为基础构成了城市形象系统的核心动力与基本出发点。
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城市的精神内核。基于价值主体的差异性与价值自身的多样性,价值观可以划分为核心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城市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社会制度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表现为城市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城市发展的价值目标。城市的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基于城市群体对城市发展的精神理念的认同性,以及对城市主体存在的意义以及重要性的总体认同。一般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与群体的细化,是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表现为城市群体判断事物价值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准则[3]。
城市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统率和支配一般价值观,构成了城市的精神世界,贯穿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城市的法规与制度之中,具有整合社会意识、统摄发展观念、凝聚城市力量、引领城市行为等多重管理潜能。
著名美国城市学家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也就是说城市精神可以通过物化的形态表征出来,并成为文化认同与识别的视觉符号。城市标志本质上是城市精神的物化形态,也是城市核心价值观的表征符号。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被表征的城市视觉符号,较之于其他感觉器官与感受对象构成的关系更为接近事物的实体形态。这主要源于视觉形式较之于其他的感官更为着重对事物的再现性,也就是说,视觉形式所揭示的事物大多都是二元以上的结构,具有极强的可见性特征。而这种再现功能所造就的可见世界是最符合认知主体的需求,可以快速地形成认知、识别与记忆。
具体而言,非物质的城市精神,通过物化转变为具有普遍认同感的视觉符号,实现物质性价值转化。以香港区徽为例(见图1):紫金花是香港的市花,代表香港,镶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红色底面上,花中的五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星相呼应,象征香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红白双色寓意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该视觉形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政体特征。后来,为了唤醒香港的活力,重新确立香港在亚洲乃至国际社会的地位,香港又推出了以“飞龙”为首的城市标志(见图2),从城市发展宏观战略的高度对城市发展进行了定位。“飞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寓意香港与祖国同根同源的血脉相承关系。吉祥的色彩寓意香港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多元化都市。“飞龙”城市形象生动地阐释了香港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极大地推动了香港的形象建设与城市发展。

图1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

图2 香港飞龙视觉识别符号
总而言之,城市精神可以通过表征的方式,转换为被管理者可以感知的视觉形式。城市精神的表征化,打破了地域文化与语言上的限制,具有高度的识别性和非强制性管理特征。
(二)城市管理的可视化
本质上,城市群体所有的行为依据都源于自身的价值观念。伴随着可视化领域的拓展,城市可视化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意味着城市精神的可视化,价值体系的表征化,也意味着城市管理向城市视觉管理的转化。
视觉管理是将管理形式通过视觉媒介的方式呈现,通过一些具有特定指意的图形符号、色彩、文字等视觉元素以及它们的组合为载体,采用视觉控制、警示等手段快捷地传达管理信息并实现管理目标。城市视觉管理改变了传统的管理形式,属于一种间接约束型的城市管理形态,主要以非强制性手段作用于被管理群体,通过影响被管理者的心理意识从而实现管理目标。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4]城市形象视觉管理通过唤醒城市群体的主体意识,在实现城市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中,对城市群体行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引导和约束的管理作用。
追本溯源,早在20世纪初,人们就开始尝试用视觉的形式对企业进行管理。美国管理学家斯图尔特·里弗(Stewart Liff)和帕米拉·波西(Pamela APosey)在《眼见为凭》(Seeing is Believing)一书中直接引入了视觉管理的概念,并且指出视觉管理方式必将取代传统的管理模式。企业视觉管理是建立在企业形象理论基础之上的,通过视觉识别系统对企业行为进行了规范管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GE)就曾将企业形象理论应用于企业内部管理。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视觉管理功能,也为城市视觉管理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城市形象战略的提出,日本东京和韩国的一些城市在引入城市形象系统的同时,尝试通过视觉识别系统对城市进行视觉管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城市形象已经逐渐由一个单纯的管理目标转化为现代管理的重要基本形式,并且在视觉理论的影响之下,实现了城市视觉管理组织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正如我国著名心理学教授张耀翔教授所言:“视觉在人类的一切感觉中是最有势力的……视觉活动的范围不可限量。”[5]美国联邦交通部早在1974年就委托美国平面设计学院设计了《美国交通图标体系》,随后又制定了《国家公共标志设计原则与图形全集》,率先建立了视觉管理标准,对交通视觉管理要素进行规范。类似的还有美国农业部制定的视觉管理系统、联邦公路管理局制定的视觉影响指南,以及英国伦敦的地铁导向系统和日本地铁标识系统等。在这些系统的视觉设计中,视觉管理的功能与优势被逐步显现出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可,并且广泛地应用于城市管理当中。例如法国巴黎城市的视觉管理就非常普及,并形成了规范的视觉管理系统,对城市的群体与个体行为进行规范(见图3)。

图3 法国的城市视觉管理
综上所述,城市视觉管理拓展了管理的领域,增强了管理活动的客观性、规律性、互动性,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不同于一般的管理,视觉管理以显性的视觉形式,作用于城市群体的观念、情感、信仰与价值体系等,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意识,潜移默化地实现管理目标。另外,由于城市形象视觉管理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管理方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更容易被被管理者接受。
二、规范化视觉管理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R.E.帕克将城市定义为由各种礼仪、风俗与传统共同构成的整体,属于一种心理状态[6]。也就是说城市绝非单纯的人工建筑,而是以城市核心价值观为框架的人类属性的产物。对城市形象视觉管理而言,则要站在城市形象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对城市进行规范化、系统化视觉管理。规范化视觉管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城市视觉管理行为;二是指从视觉管理的整体出发,对视觉管理系统要素进行规范,形成统一的视觉形象,并通过视觉规范实现系统化管理[7]。只有进行规范化视觉管理,才能统一意志形成合力。规范化视觉管理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意象规范
“意象”一词源自心理学,用以表述人与环境间的一种组织关系,是一种由体验而认识外部现实的心智过程,意象的本质是将想法、精神、理念转化为意念形式的形象。从城市形象角度来看,意象是城市群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心物形态。“意象”表面上好像与物质属性的视觉形象没有直接的联系,实质上却与纯粹的视觉形式纠结在一起,这是由于人的大脑机制的感知模式是情景式的,那么观念意识在人的头脑中是以一种意象图式的方式存在。城市的精神凝练为非物质的意象形态,影响着人们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并以准视觉的形式被外界所感知[8]。因此,城市意象必然作用于城市群体的主体意识,影响其对城市形象的认知。
意象规范在城市视觉管理中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的规范。意象的教化作用最早可以追溯到舜帝时代,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显然,舜帝已关注到了音乐与诗的教化功能,以情感与意念作为伦理规范的一种手段,以便达到“神人以和”的境界。无独有偶,与音乐同源的视觉艺术的教化作用更为显著。据史书记载,商朝初年的宰相伊尹画九主形象,来劝戒商王成汤使之成为一代明君。孔子更是直接指出绘画对人的心理有着喻褒贬、别善恶的教化作用。
意象的群体教化功能,是通过认知、认同的方式,促进社会认同的伦理价值体系的形成。意向的个体教化就是要把真善美的价值体系根植于个体的人心之中,通过个体素养的提升和境界升华,表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的行为方式。意象教化显示出非凡的归融性和柔性管理功能,使人们的心灵情感与社会人伦秩序相互融合,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正能量的城市精神世界。 城市视觉管理正是通过意象这个中介物,将城市精神内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形象规范
如果说规范化管理的非物质层面是城市意象规范,那么物质层面就是指形象规范。城市形象是城市精神的有机肌体,是对城市精神的视觉拓展和视觉诠释。形象规范主要指的是对视觉管理的视觉要素和视觉形式进行规范。
视觉要素规范就是对视觉符号系统进行规范。《庄子·物外》有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9]也就是说,任何语言或符号,无论它的结构形式如何,其本质必然是信息的载体,其首要的价值在于它所指的意义。因此对规范化视觉管理而言,构建起规范化的视觉符号系统是规范化视觉管理的首要任务。
首先,视觉符号是管理信息的载体,是可以感知的直观形象。虽说视觉符号由于所作用的领域不同,形成了种类繁多、形态复杂的局面,但是依据符号性质,可将其分为注重功能传达的指示型符号和注重语义传达的象征性符号。
指示性视觉符号具有刚性管理的特征与法规紧密相连,直观视觉符号表面就可直接获取管理信息。如交通路标、操作指令等。通过视觉规范形成造型简洁、视觉冲击力强、直观、易记的符号系统。正如传播学者保罗·M·莱斯特所说:“图形形式使得视觉信息的产生、表达和接受都更加便捷,它将不同类型的视觉材料以及视觉形象的创造者和接受者都联结在了一起,受其视觉信息影响的人数之巨大,在大众传播领域可谓史无前例。”[10]
象征性符号与自身所指对象之间不存在必定的联系,之所以能够与所指对象产生关联是源于日积月累的视觉经验。我们的祖先就常常借助于特定的视觉符号来表达一些抽象的东西,如蝙蝠、松鹤、麒麟等来表达对于生活的美好祝愿,借助于寒梅、劲松、秋菊等视觉符号来隐喻高贵的品质。究其本质,这些视觉符号之所以能够表达诸多的含义,并非是因为其视觉符号本身与这些词语有所关联,而是在生活体验中,哲学物象逐渐被赋予了各种美好的象征,演化为约定俗成的概念。在城市形象视觉管理中,象征性视觉符号特别适合于传达城市精神和象征性旨意,成为城市文化的指代符号。但是,由于地域文化与风俗的差异,使得相同的视觉符号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解读。
其次,视觉形式作为视觉形象的基本存在方式与组织原则,在视觉管理中特指视觉识别系统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指出:关系一词是形式中特有的概念,关系也是一个模糊的语辞,在哲学上它表示思想确定的联系,或表示某种间接的、纯粹理智的甚至是逻辑的东西,其核心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城市形象视觉管理的形式规范,实际是指视觉要素按照某种规律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和谐、统一、呼应的逻辑联系[11]。正如德国艺术家希尔德·勃兰特所言,任何一个独立的元素都只有处于和其他元素的某种相关联系之中,才具有自身的意义,这也是视觉形式的本质特征。通过形式规范,实现改善系统结构、功能与组织关系,激发系统机能,实现最小耗散与最高效率的最优性组合。
以杭州城市信息系统为例,就是通过规范所有的视觉要素和空间形态,形成了同一的视觉识别形式(见图4)。规范化的视觉形式反复地出现,强化了城市形象的视觉记忆和体验,不但规范了城市行为,也规范了视觉管理语义的识别特征。

图4 规范化的杭州城市视觉识别系统
总而言之,规范化视觉管理就是将一切要素以既定的形式构成逻辑上的管理体,形成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构成一种内在的呼应、反衬、交融和渗透关系,实现城市视觉管理的整体优化。也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赋予其视觉管理的系统性和同一性。规范化视觉管理既要把握好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与结构关系,也要把握好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差异性与秩序性。
三、差异化视觉管理
从视觉识别角度上讲,可以说城市形象的本质就是差异化,那么城市视觉管理也必然体现出城市形象的差异特征。换而言之,城市形象的差异化也是城市个性的集中表现,一般可以从定位差异与识别差异两个方面来解读城市形象的差异化管理。
(一)定位差异
凯文·林奇曾说:“能够使人区别的地方与地方的差异,能够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记忆,这个地方可以是生动的、独特的、至少是有特别之处,有特点的。”[12]可见差异化是城市认知与记忆的基础。城市形象视觉管理的定位差异可具体划分为文化差异、地域差异和战略差异等方面。
首先,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历史与民族发展的集合,是城市的本源与血脉,不但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也影响着城市的管理方式[13]。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母体”,不仅是城市感知与认同的基础,更是城市之间相互区别的最重要元素。文化的差异性体现为城市文化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定位,决定着城市不同的文化导向,也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视觉管理模式。
其次,由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城市在自然条件与地貌特征上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因此,地域差异也是城市视觉管理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摩洛哥的阿尔迪加为例: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城市面朝广阔的大西洋,背依苏斯平原,南临撒哈拉大沙漠特殊的地域特征,成为了气候温和、风景秀丽、举世闻名的避寒胜地。因此,在阿尔迪加的城市视觉形象设定中,充分融入地域特征(见图5):碧蓝的线条即是水波也象征着山峦,标志中心的黄点则代表太阳,突出了阿尔迪加是一个避寒的胜地。城市名称同时用了阿拉伯文、柏尔文和英语三种语言构成,体现出阿尔迪加热情好客的个性和这所城市面向国际的姿态。

图5 差异化的阿尔迪加城市视觉管理系统
最后,城市的战略规划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战略差异也是一个城市最显性的认知差异。战略定位的差异,无疑导致了城市价值体系的差异,即形成了视觉管理重心和目标的差异,也形成了视觉形式上的差异。战略差异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既是城市的发展目标,也是城市管理目标。城市战略建构起与其相适应的城市精神与价值体系,是城市的一种思想智识活动。
差异化视觉管理,是以城市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承为基础,以城市的某一特色或者功能为主体,以鲜明的个性视觉形象张扬着城市的特色。城市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差异化视觉管理既要形象突出,又要统筹兼顾。以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城市纽约为例:纽约既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成为了纽约重要的文化特征。在核心形象设定上,以公众认同感很强的“我爱纽约”(I LOVE NY)标语性口号为视觉形象设定依据,右上角的红心在增加视觉记忆点的同时,也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凝聚力与包容性,极具感染力与视觉冲击力。城市视觉符号一经发布,如同一只强心剂,极大地唤醒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与责任感,成为了承载纽约精神文化的视觉符号,深受大家喜爱。除此之外,美国迪斯尼所在地奥兰多、树城博伊西等城市也都依据自己的文化与地域特色,在城市形象视觉管理中最大限度地体现城市的差异特征(见图6)。
(二)识别差异

图6 -1 纽约城市视觉形象系统 图6-2 奥兰多城市视觉形象系统
识别差异即是指城市精神的识别差异,也是指城市定位的识别差异,更是指视觉符号在形式与造型上的差异。识别差异与定位差异本来就密不可分,城市定位的差异必然是以视觉识别符号的差异显现出来。识别差异不仅来自于视觉图式本身,也来自于视觉元素之间的组织结构关系之上,构成了形式与造型上的差异。
首先,形式差异是指视觉符号系统在视觉式样和整体面貌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其视觉元素的形状、构成规律及结构上存在的差异。城市形象管理视觉元素之间的组织形式,构成了视觉管理的结构语义,这种结构不仅指代城市形象的物理结构,也指代城市群体在认知城市形象过程中的思维结构。
视觉符号的形式结构构成了或均衡、或疏密有序的视觉节奏与韵律,形成了极具可读性的视觉管理信息结构。这种视觉形式结构,在体现自身的形式结构美的同时,也传达出了不同的形式结构语义。例如,德国汉诺威2000年世博会主题视觉形象(见图7),虽然并不是一个以管理为主体的视觉设计,却是一个可以适应不同功能需求,调整色彩与结构形式,以动态的视觉形式体现出了管理的逻辑结构和层次。被公认为是一个满足视觉形式与技术手段的需求变化、极富动感会呼吸的视觉符号形式。
其次,造型差异是指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在视觉图式上所呈现出的差异。依据生理与心理学原理,无论视觉管理系统所处的空间与位置如何,人的视觉识别最初关注的是从对视觉元素形状的辨别与认知开始的。因此,即便是视觉符号脱离了符号所指的深层语义,其视觉符号能指本身也能承载一定的管理符号的明示义。造型差异造就了视觉符号的鲜明个性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易于引起视觉的感官刺激,能在瞬间引起注意。例如悉尼的核心形象就是以极点图的结构,构成了一个即可向外扩散,又可以向内集中的视觉图式,犹如是一种声音或意念的传播,象征了悉尼城市的凝聚力与辐射力(见图8)。

图7 汉诺威世博会视觉形象
差异化管理既要强调宏观上的整体统一,又要把握微观上的灵活机动。通过差异管理来打破城市管理的同质化,形成即统一又有区别的视觉管理系统。
视觉管理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模式,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城市核心价值观的物化形态,城市形象以最具城市凝聚力的视觉符号,对城市群体的心理与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即是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视觉管理的重要手段。城市精神通过形象物化为可视的视觉形态,构成了城市管理向视觉管理转型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城市视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形象视觉管理通过规范化管理形式,显现出意象规范的隐形管理功能和形象规范的显性管理功能,有效地改善了城市视觉管理的系统结构、功能与组织,激发系统的整体效应;通过差异化凸显城市的本体特色和独特的视觉文化特征,实现了优化管理的功效与职能的目标。

图8 悉尼城市视觉形象
[1]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6: 911.
[2] 小川和佑. 东京学[M]. 廖为智译, 台北: 乙方出版有限公司, 2002: 45-90.
[3] 冯周卓, 钟红敏. 论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公民身份建构中的作用[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2(19): 147-152
[4]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154.
[5] 张耀翔. 感觉、情绪及其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36.
[6] R E 帕克. 城市社会学[M]. 宋俊岭,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67.
[7] 弗雷德里克·泰罗. 科学管理原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157.
[8] 凯文·林奇[M]. 项秉仁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41.
[9] 庄周.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135.
[10] 保罗 M. 莱斯特. 视觉传播: 形象载动信息[M]. 霍文利, 等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3: 152.
[11] 孙湘明, 成宝平. 城市符号的视觉语义探析[J]. 中南大学学报, 2009, 12(15): 795-800.
[12] 凯文·林奇. 城市形态[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45-69.
[13] 樊海燕, 范玥. 管窥城市历史文化遗迹标识系统的创立与构建[J]. 包装工程, 2009(12): 164-165.
First research on visual management of urban image system
SUN Xiangming, SUN Yin, MA Weil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city Image can be spread widely by the visual form, which is the visual carrier of the spirit and core values of the city and the media of the Urban Vis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sign and management, starting from the city spirit and core value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visual culture phenomenon is the basic factor of city management transforming to urban visu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d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visu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ity image manage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visual management, it suggests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which includes invisible image management and dominant management, and the unique form of differentiation management consisting of the difference form of city image strategy and visual identity.
urban image system; visual management; values; visualization
J502
A
1672-3104(2014)06-0224-07
[编辑: 胡兴华]
2014-07-01;
2014-10-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GL159);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3177-72150050303)
孙湘明(1956-),男,湖南沅江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哲学,设计理论与实践;孙颖(1984-),女,河南洛阳人,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哲学;马玮丽(1987-),女,河北石家庄人,中南大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达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