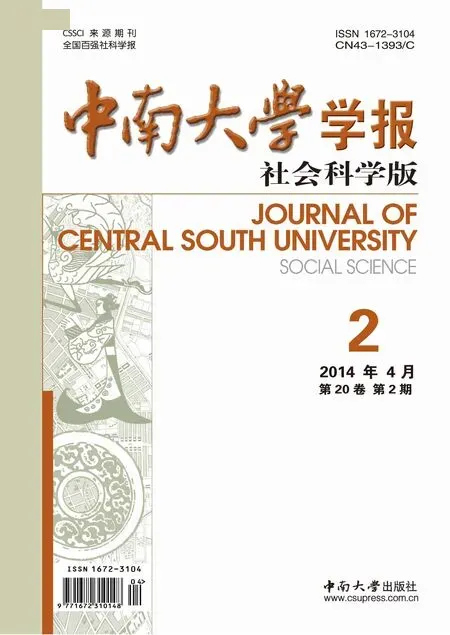论清末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之误
2014-01-21谢红星
谢红星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但又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须“从官制入手”,以“廓清积弊,明定责成”,[1](44)为立宪基础。于是在宣示立宪之后,随即启动官制改革,结果是官制久议难改,议会久议不开,宪法久议不立,迁延多时,误官制改革甚,误立宪甚,误清王朝甚。以往学界虽注意到了清政府在立宪过程中的迁延与迟缓,对其原因亦有所研究,却从未意识到立宪从官制入手这一错误战略本身即是造成清末立宪迁延迟缓的重要因子。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官制改革遇到的巨大阻力
平心而论,以官制改革为宪政改革起点,并非毫无道理。但凡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其治理国家的中坚往往是专门化的官僚群体,“宪法绝对的君主制现在只能靠常设的官僚机构的智力条件维持其本身的存在”,[2](86)帝国的兴盛实赖于官僚的精心治理,而其衰败也起于官僚群体无可避免的生命力衰竭。就清王朝而言,官僚群体治理能力的退化正是晚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内部根源,这种退化又因清代官僚体制的固有缺陷而较以往显得更为突出。与以往各朝相比,清代的君主专制最为严密,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作为实际治理主体的各级官员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制。李剑农对清代君主专制下官员的权力做过如下描述:“(1)一切权力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另一个机关;(2)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3](11)在这种“多元多轨”[4](2)的官制下,除皇帝外,任何机构都不能自行决定重要政务,一切决策都由皇帝做出,一切政令都由皇帝发布,一切政治责任都由皇帝承担。如此一来,专擅欺主的操莽之臣是没有了,各级官员施政的自主性、创造性却因皇帝专制过甚而被扼杀。久而久之,“大臣非闇陋则偏愎,小臣非鄙猥则譸张”,[5](157)多磕头,少说话,不做事,掩饰弥缝,苟且偷安,便成官场常态。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所言,“清朝统治者把控制效率(利用诱惑和恐吓)提高到了窒息官僚阶层内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地步”,结果是“行政体制的退化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灾难性外来因素侵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到19世纪末,在某种程度上用‘瘫痪’二字来形容行政机构恐怕也不算过分”。[6](187)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种腐朽退化的行政机构及官僚群体,既无力力抗外侮,亦无力推动内部改革以自强,于是外患频至,内忧加深,一切统治危机,皆由此而来。故改革官制、改造旧官僚群体,实为清政府推行其他现代化改革之前提,正如亨廷顿所言,“传统君主政体的自新重点,依照传统政体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官僚政体中,权力业已集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的官僚制度,让它去贯彻现代化改革”。[7](129)
然而,要改革旧官制并不容易,亨廷顿自己也承认,“如果传统政体已经具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职能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专门化,并按照传统的功过标准录用官员,那么改革官僚体制问题就可能是十分艰巨的”。[7](130)果如其言,官制改革上谕一发布,反对声音即汹涌而至。在发布官制改革上谕至裁定中央衙门官制这短短两个多月中,仅故宫博物院《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所载,各级官员所上反对官制改革的奏呈,就有数十件之多:《户部员外郎闵荷生建言官制不必多所更张呈》《候选道许珏陈言宜先清吏治陈》《翰林院侍读柯劭忞奏更改官制不能仓猝折》《御史蔡金台奏改革官制宜限制阁部督抚州县权限折》《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克宽奏更改官制袛各易新名实不如旧制折》《御史刘汝骥奏总理大臣不可轻设以杜大权旁落折》《御史王步瀛奏户刑两部事繁请勿轻拟裁员折》《御史杜本崇奏更改官制不宜全事更张折》《御史王步瀛奏新定官制多有未妥应饬认真釐定折》《御史张瑞荫奏军机处关系君权不可裁并折》《御史石长信奏请将政务处并入内阁其他官制勿大更张折》《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御史张世培奏改革官制不可轻弃旧章折》《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权归内阁流弊太多折》《御史叶芾棠奏官制不宜多所更张折》《御史涂国盛奏请勿遽改官制折》《内阁学士麒德奏请徐图立宪不可轻改官制折》《刑部郎中陈毅建言亟应保存礼部呈》《翰林院撰文李传元奏釐定官制不能过促折》《御史联魁等奏改革官制请从缓办理折》。
上述奏呈若只观其名,“不能仓促”“不可轻改”“不宜全事更张”“不宜多所更张”等等,似乎只是稳健持重,并非根本反对改革,然细读之下,不过以稳健之名掩守旧之实。其内容既有笼统反对改革官制者,亦有具体反对责任内阁、部院官制者,理由皆冠冕堂皇,维护君权、维护礼教、维护祖宗之制等等。实际上却是担心官制改革后自身利益受损,再也无法过“天乐看完看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除却早衙签配字,闲来只是逛胡同”[8](245)的生活。对此,江南道监察御史吴钫的一道奏折刻画得非常详尽。他说,官制改革之所以会招致众多反对,出现“大小臣僚相与议论,皇然有不安其位之虑”的现象,是因为“利害之系于身者至切也”,“今日之纡青佩紫,皆积半生之殚精竭虑而始得之。一旦改弦更张,必至顿失故步”,“士大夫以官为生者,十之七八,势至无以为生,必出全力以相抵制,卒至盈庭聚讼,是非莫定”,[1](404)可见反对者多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维护而反对改革。
虽说公开反对官制改革者官阶普遍不高,真实目的亦是维护一己私利,但其反对意见对清政府最高决策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指出了官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官制改革必将损及皇权。反对者认为,旧军机处权归君主,“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若废军机处而设责任内阁,则权属于臣,“若谓大权仍不下移,其谁信之”。旧时军机大臣同堂议事,不相统摄,今内阁设总理大臣统一政务,是“避丞相之名,而其权且十倍于丞相也”,无论何人为之,都可能“恣唯自擅,窃弄权柄,启奸人窥伺之渐”。[1](430−433)应该说,反对者上述言论虽不无危言耸听之意,但也确实极具道理。原本清政府的规划中,官制改革先中央后地方,中央官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责任内阁。然而正如反对者所言,新设责任内阁的权力必然大于原来的军机处与内阁,总理大臣权位更非旧军机大臣可比。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君权与臣权从来就是一对彼此消长的变量,臣权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君权的损减,责任内阁与内阁总理大臣必然构成对君权的限制。这在清代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却是以建立责任内阁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宣称“大权统于朝廷”,官制改革乃至宪政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君权自此受限制。
作为晚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及宪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慈禧本人“但知权利,绝无政见”。[9](83)对她来说,只要能保住既有权力,任何改革都不在话下。当初她不正是听了载泽袁世凯等人“立宪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的话才放下心来决定立宪的吗?然而经反对派官员之口,官制改革乃至宪政改革对君权的损减已确定无疑,慈禧又岂能不心生警觉,放缓甚至阻遏即将进行的官制改革。袁世凯在中央新官制拟定之后,“力求定议宣布”,慈禧却以“外廷所上条陈多有与之反对者”,宣布“此事仍须详慎斟酌,未便立即宣布”。[10](165)载泽恐改革流产,上折向慈禧解释了总理大臣权限问题,并请求召对,以释慈禧之疑,但慈禧对其已不复前之信任,未予召见。[11](58)这说明反对派官员的意见已发生作用,慈禧对官制改革的态度有微妙转变。
官制改革招致的强力反对及慈禧的动摇证明,官僚集团“对来自外部的改良措施组织起来的永恒的敌意”,是“连一个有魄力的皇帝的专制权力也很少或决不足以克服的”。[2](90)一方面,是因为“官僚集团的不变的阻力终归胜过一个人的无常的精力”。[2](90)在任何时候,体制的力量终究胜过个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旧的官僚体制本身就是传统君主专制政体的一部分。在此体制下,君主依靠官僚实行专制,官僚构成君主的统治力量,要专制君主冒削弱自己统治力量的风险去改革官僚体制,改造官僚群体,谈何容易!清代“多元多轨”的官制正是其极端专制政体的一部分,官员的苟且无为正有利于君主的独裁与控制。改革这种体制,改变这种官员,就是改君主自身。一旦慈禧认识到这一点,她对于改革的积极性自然不会太高。
然而,改革已势在必行,无可倒退。慈禧自己也知道,“因不好才改良”,[12](29)“如收回,恐有革命流血之事”。[13](162)不继续改革,清王朝必无可挽救,继续改革,自己的权力必然受损,这是个两难的困局,而慈禧恰恰不具备打破此一困局的见识与魄力。诚然,慈禧精明能干,具有驾驭群臣的高超才能,但就治国施政而言,她的才干并不突出。说到底,她只是一个传统礼教熏陶下的女性,“深居宫中,一向与外界情势不相接触”[14](101)的女主,经历有限,政治知识狭隘,对君主立宪制度下君主的权力地位缺乏认识,对削弱自身权力的改革的后果缺乏信心。她既不想放权,更不敢放权,面对此一困局,她“锐气尽消,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于及身无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12](32)最高决策者既已丧失改革之锐气,改革派又如何能克服反对者的阻力?官制改革由是在阻力中颠簸前行。
总之,官制改革牵涉到无数官员的既得利益,它招致官僚群体的强力反对是必然的;官制改革最终必然指向君权,损减君权,作为“深宫妇人”的慈禧对改革从积极支持到消极应对,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了最高统治者的稳定支持,改革者更不可能克服反对的阻力,官制改革只能在无原则的妥协中艰难前行。
二、官制改革的失败使朝廷威信再受重创
相对于地方官制改革,清末的中央官制改革稍具规模,这里仅就此加以论述。在反对的阻力下,清政府1906年启动的中央官制改革,先后出现过三个版本的改革方案。
首先是载泽等人的草案。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命载泽袁世凯等人共同编纂官制。载泽等人首先起草中央官制,经反复会商,拟定了一份草案,送总司核定大臣奕劻等人审核。该草案要点包括:限定改革内容,只改行政、司法,“凡与司法、行政无甚关系之署,一律照旧”。明确改革要旨,“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设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与旧内阁,以之为政务中枢,“首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十一部为外务部、民政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交通部、理藩部、吏部,七院为资政院、大理院、都察院、典礼院、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一府为军谘府。各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承政厅、参议厅,及参事、郎中主事、七品小京官、录事等员。妥善安置裁汰官员,“拟在京另设集贤资政各院,妥筹位置,分别量移,仍优予俸禄”。[15](17−20)
此份草案借鉴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原则,行政以责任内阁统领各部,司法则以大理院独立审判,又以资政院、都察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制衡责任内阁,在制度设计上具有相当新意。当然该草案也有其不足,它只改行政、司法机关,凡与行政、司法无关之机构,一律不改。所谓“与司法、行政无甚关系之署”,主要指直接为皇帝皇室服务、与国政无直接关系的内廷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翰林院、侍卫处、太医院、钦天监等。清代官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处理皇帝“家事”的机构多,人员多,管辖范围广,“夫以百司之设,国民仅得其四,而供奉之司,乃至十四而不止焉”,[16](351)堪称与军机处内阁六部等国政机构相对的另一政府。而其内部贪污腐化程度,更是远甚于后者。如果说因“议院遽难成立”、立法机关的设置暂不在此次官制改革内容中尚能勉强说得通的话,内务府等内廷机构不在改革名单之上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究其因由,是因为内务府等涉及慈禧及其身边太监宫女的利益,宗人府涉及宗室的利益,载泽等人为减少改革的阻力,便主动作了妥协,此一妥协不可谓不大。
虽然如此,载泽等人的草案仍充满革新意义,其最大亮点为责任内阁与司法独立。然而,虽然草案对于如何安置裁汰官员亦有措施,并承诺“优予俸禄”,利益受影响的官员们仍是群起相攻,而当他们戳穿了责任内阁限制君权这一层窗纸后,不改革内廷机构的妥协也不能让慈禧坚定支持载泽等人的方案了。内外压力接踵而至,总司核定大臣奕劻不得不对载泽等人的草案进行修改,在其基础上更定成第二份方案,进呈慈禧最终裁定。奕劻方案的要点包括:仍坚设责任内阁,但在责任内阁的组成上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各部尚书均充内阁政务大臣;一种是“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与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无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之名,以现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大学士为内阁成员。如此,“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中央行政机构定为十一部,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下设承政厅、参议厅,及左右丞、左右参议、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责任内阁及各部外,设六院一府,以大理院任审判,以资政院持公论,以都察院任纠弹,以审计院查滥费,以集贤院备咨询,以行政裁判院待控诉,以军谘府握全国军政,“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内阁”。重申不改内廷机构,“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无庸议改”。[1](462−470)
除去相关机构、职官具体称呼的不同外,奕劻方案对载泽草案的改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责任内阁不设总理大臣的方案;二是将典礼院改回礼部,仍作为内阁主要部会。前者是对反对派关于总理大臣权力太大、迹近专擅指责的回应,同时也是为了释慈禧之疑;后者则是对反对派保存礼部主张的退让。总体而言,奕劻方案虽有所退步,但仍守住了载泽草案的底线:责任内阁与司法独立。也正是因为如此,慈禧对奕劻进呈的方案仍疑虑重重,经反复权衡,最终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做出裁定,发布上谕,确定了中央官制改革的最终方案。其要点包括:不设责任内阁,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中央机构为十一部四院,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暂兼管海军部与军谘府)、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大理院、都察院、资政院、审计院。内廷及八旗机构照旧,“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1](471−472)与奕劻方案相比,慈禧最终裁定的方案除了对中央机构的设置有所变动外(取消了集贤院与行政裁判院),最大的变化是否定了责任内阁制,行政中枢一如既往,载泽及奕劻方案中最根本、最有新意之处由此被舍弃。对于载泽等人在内廷机构上主动的妥协,慈禧倒是毫不客气照单全收,然而在责任内阁的问题上,她却一步不让,连不设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也不肯接受。
当然,载泽奕劻对中央部院的调整,慈禧基本上均予以接受。虽否定了责任内阁,但又使各部尚书充参预政务大臣,加重其权限责任,似有向责任内阁过渡的意图。况且上谕最后也说,“此次斟酌损益,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如有未尽合宜之处,仍著体察情形随时修改,循序渐进,以臻至善”,[1](472)为将来深化改革、设立责任内阁留有余地。认可司法独立,以大理院专掌审判。如此看来,慈禧的改革方案也非一无是处,只是改的幅度不大,有试试看的意思,与载泽等人的初衷有相当距离,更远低于民间立宪派的预期。
总之,清政府原想从官制入手启动立宪进程,立意不可谓不高,雄心不可谓不大,“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悉无遗”。[1](385)孰知一波三折,最终弄出个“未尽合宜”的中央官制,朝野上下大失所望。立宪派由清政府宣示立宪之初的“奔走相庆,破涕为笑”[11](53)转为尖锐批评,“伪改革”之说随之而来,清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威信再受重创,宪政之建成更加遥不可及,官制改革的受挫增加了立宪的难度。
三、官制改革使廓而不清的官制积弊愈演愈烈
清政府希望通过官制改革廓清积弊,为立宪奠定基础,结果是积弊廓而不清。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不仅没能廓清积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
早在官制改革上谕发布之初,御史江春霖就上折陈事,奏请清除官制十二弊。江春霖认为,清政府的官制当时有十二大弊:“兼差之弊”“偏枯之弊”“迁调之弊”“保举之弊”“超躐之弊”“捐纳之弊”“分发之弊”“冗滥之弊”“考察之弊”“名例之弊”“仪注之弊”“习俗之弊”。江春霖认为,“官制者,犹人之形体也,诸弊则犹形体之病也。病不去,则四体五官不能效其用,弊不除,则庶司百僚无以熙其绩。去病必治其本,除弊必究其端”,官制改革必须要达到除弊的效果,否则官制虽改,积弊不除,则新官制也不能发挥应有效用,改革徒然沦为形式。[1](386−389)
官制改革后,上述积弊有无依江春霖所奏一一廓清?答案是没有。如“捐纳之弊”,清政府虽于 1901年下诏停止捐纳,结果却是“局吏倒填月日,收捐如故”。其后“各督抚筹款困绌,复以实官请。户部以诏墨未干,难于转圜,乃议典簿以上故有官职者准其加捐。既又推广其例,令举、贡、廪生皆得报捐实官,于是山东河工、广西剿匪、奉天筹边,皆奏准收捐如部库”。[17](33)官制改革完全不讲废停捐纳,捐纳之弊于是伴随清王朝直至灭亡。如“保举之弊”,清末保举之滥,“十倍于捐纳,百倍于科举”,名为不拘一格荐贤举能,实则“以贪为廉,以酷为能,以败为功,以无为有,以细为巨,颠倒是非,变乱黑白”。官制改革前清政府就曾制定章程严格保举限制,然“冒滥犹自若也”。[17](50)官制改革后,保举更成满族世家九品中正之制,“丞、参不分满汉,满员同时用十一人,皆借门望以起”,“其初俱由各部堂官指名请简,嗣经廷臣弹奏,乃先保荐后请旨,列名在前者恒得之,其弊视魏晋九品中正殆有甚焉”。[17](23)又如“习俗之弊”,清末官员私德不修,官场习俗低下。时人论当时官员,“昆冈好饮,裕德好洁,徐郙好优伶,奎俊好佛,徐琪、曾广銮好狎邪游,张百熙好搜罗浮薄名士,诸王贝勒若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胡燏芬一意媚洋,好与西人交涉。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幰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17](35)官制改革后,官场习俗低下如故。如民政部成立后,“都下赌风甚炽,自王公至负贩罔不乐从”,“载振、载搏等几无日不在赌场中”,尚书善耆一次亲率警察抓赌,发现赌徒中“王公卿相、夫人小姐、娼妓优伶,色色俱备”,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8](48)
除此之外,官制改革后,晚清官场争权之风、钻营之风、贪贿之风较以往更盛。官制改革本来是要使各机构权限分明、职责分明,然而改革之后,新旧机构争权夺利,权限不清更甚以往。礼部与学部争教育之权,农工商部与度支部争财政之权,外务部与吏部争涉教案官员任免之权,大理院与法部争司法之权,而民政部竟“自署置官僚如吏部,自创办铺捐、车捐如户部,自练警兵如兵部,自开学堂如学部,把持讼狱如刑部,大治街道辟马路如工部”, 无所不统,无所不争,以至“天下一统而辇毂之间先成乖离破碎之象”。[17](52)科举既废,士人入仕之途不明;官制又改,官员中一部分被裁之命运可预见。于是士人为谋一官半职,官员为保一己官位,无不使出浑身解数,献媚上司,取悦权贵,格调愈下,风骨早无。时人称,“向来部曹得京察者皆拜堂官为老师,外官得保举者对于督抚亦然。今则愈趋愈滥,至渺之相涉,但一奏报即拜尔门,格愈卑矣”,“盖趋利伺便之心盛,他皆不顾矣”。[8](111−112)如段芝贵原不过一巡捕,因卖力替袁世凯追拿逃仆而得候补道员,后又献歌妓杨翠喜给贝子载振,竟由候补道员直升黑龙江巡抚。改革并未使吏治好转,官员反借机图利生财,如六部中户部、工部、兵部的报销费,原来不过“内外胥吏交通关说,私以自肥,堂司染指者绝少”。自官制改革裁减书吏后,堂官便“化私为公,先后开单入告,遂视倘来为固有,行公文提取”,[17](36)无人敢置一词。而慈禧奕劻更为诸贪之首。慈禧晚年“恣为娱乐,好贡献”,奕劻于是“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供奉慈禧以固宠,[5](199)自己也是卖官卖缺,广纳贿赂,以至“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12](30)贪风日盛,政以贿成。
综上所述,晚清官场的诸多积弊并未因官制改革而得以廓清。虽然立了几个新机构,换了几个新名称,但官员贪残依旧,官风败坏依旧,官场黑暗依旧。积弊不去,改革难成,官制改革的效果极其有限。
四、结语
无论在任何时候,官制改革都是所有改革中的最难选项。因为它影响到千千万万官员的利益,而官员正是掌握实际权力的“治人者”。立宪从官制入手,等于一开始就把大部分官员逼到了改革的对立面,官制改革由此无可避免地陷于泥淖,进而延误整个立宪进程。这对内忧外患交织、改革成功机会本不大的晚清政府来说,实为不可承受之误。
官制改革是必须的,却不应是清末立宪的最先选项。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才是清政府“仿行宪政”合理可行之切入点。首先,正如康有为所言,“有知而后有行,有虚论而后有实事,有立法而后有行政,乃理之自然也。且出自众议则公而可久大,出自独断则私而难周详”。[16](350)立宪国家先立法而后行政,行政受立法监督。既然立宪,当然首先要把立法机关立起来,立法机关由议员组成,有议员们的群策群力,改革必能少走弯路。其次,议院一开,既可满足士绅阶层日益强烈的参政欲求,更可将民间立宪派士绅的力量汇集起来,增强改革的力量。如此,旧官僚群体对官制改革乃至宪政改革的阻力方有可能被克服。改革者不仅要掌握权力,而且要扩大权力。正如亨廷顿所言,“权力能够扩大和缩小,也能集中和分散”。[7](119)所谓“扩大”权力就是指通过社会动员和扩大政治参与,将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实现权力总量的扩大、强度的扩大。面对整个官僚群体的阻挡掣肘,载泽等人势单力薄,无能为力。但当时若有咨议局、资政院议员的加入,或许就是另一番局面。
立宪从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宪窒滞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官制可改,立宪可行。然而,清政府既无勇气、亦无智慧先开议院,而是选择了从官制入手这一自以为稳妥实则错误的战略,以至官制改革龙头蛇尾。立宪之路一波三折,丧失了挽救清王朝的又一次良机。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英]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瑄,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4]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M].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5][清]刘体智.异辞录[M].刘笃龄, 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8.
[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7][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 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8]汪康年.汪穰卿笔记[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9]王照.方家园杂咏记事[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0]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2]岑春煊.乐斋漫笔[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3]高树.金銮琐记[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4]吴永, 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M].李益波, 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16]王忍之, 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C].北京:三联书店, 1960.
[17][清]胡思敬.国闻备乘[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8]陈灨一.睇向斋秘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