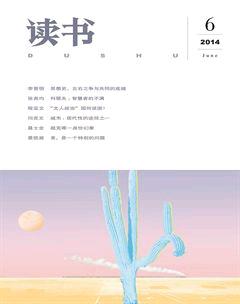夹缝里的都市文化
2014-01-09陈建华
陈建华
《留声机片》是周瘦鹃写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一九二一年五月的《礼拜六》周刊上。那时发生新旧两派的文学争论,这篇小说被茅盾点名批评,认为代表了作者以及“礼拜六派”的典型做派。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小说像在“记账”,缺乏现代“描写”技术,作者缺乏艺术良心,受了“拜金主义的毒”。但是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在今天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环境里来读这篇小说,却别具一种启示。
小说的故事颇为简单:一名叫情劫生的年轻人情场失意而离开上海,来到了太平洋上的“恨岛”。可他忘不了他的初恋情人林倩玉。林倩玉与他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然而她听从父母之命嫁了别人。八年后,情劫生弥留病榻之际,想对林倩玉有所交待。于是找来岛上的百代唱片公司为他录音,录了音后他死去。这张唱片寄到林倩玉那里,她听到了这段录音,伤心欲绝,天天播放,直至郁郁而死,躺在仍然转动着的留声机旁。
讽刺的是,尽管周氏的故事聚焦在留声机这“现代”科技上,其文字风格却向“抒情传统”频频回眸。首先对男女主角的命名隐寓着中国言情小说源远流长的谱系,林倩玉跟《红楼梦》的林黛玉几近雷同,而情劫生按照佛义解释,注定遭受情劫的轮回。这种才子佳人式的伤感含有“为情而死”的哲学意涵,跟十七世纪以降在江南城市盛放的情色文学和爱情论述的传统遥遥相应。周瘦鹃是苏州人,继承此一文士文化再自然不过。情劫生与林倩玉自由相恋,由于家长的反对而劳燕分飞,这样的故事流行于民国初期,对于当时青年男女颇具普遍性;情劫生珍藏着林倩玉的情书,以及她婚后生活不幸福而仍旧深爱着他的情节显然有着周氏自己与初恋情人紫罗兰的“影事”。
“留声机本是娱乐的东西”,小说一开场即端出有关娱乐的主题,然而悲剧的结局却让人跌破眼镜―女主人公倒毙在播放中的留声机旁。所谓:
那一支金刚钻针着在唱片上,忒楞楞地转,转出一片声调来。《捉放曹》咧,《辕门斩子》咧,《马浪荡》咧,《荡湖船》咧,使人听了都能开怀。……谁也知道这供人娱乐的留声机片,却蓦地做了一出情场悲剧中的砌末,一咽一抑的呕出一派心碎声来。任是天津桥上的鹃啼,巫峡中的猿哭,都比不上他那么凄凉悲惨,机片辘辘的转动,到底把一个女孩子的芳心也轻轻碾碎了。
尽管周瘦鹃因主张小说的“消闲”功效而引起新文化作家猛烈抨击,这一番将“娱乐”变作“情场悲剧”的说白,不啻有意挑战并颠覆了自身的语码。事实上整个故事所显示的,他在游戏于习以为常的文学套路时,却向壁虚构,为一对失恋情人营造孽海情天的异度空间,展示了本土苦痛现实与全球娱乐机制之间的吊诡张力。留声机片作为一个听觉传媒的道具、现代科技的指符,对于陷入痛苦家庭生活的林倩玉,足以充当慰藉其孤寂的良伴,却成为复制与加剧其痛苦的帮凶。作者在形式上制造起伏和转折,游走于传统和创新之间。故事的悲剧收场,使私人空间及留声机―日常城市生活常见的玩意儿―蒙上了鬼魅阴影,也给这一爱情悲剧涂上诡异的色调,遂使耳熟能详的叙事套式变得“陌生化”起来。
这短篇出现在新旧嬗变中的社会转型时期,西式的自由恋爱和婚姻在年轻人当中广为传播,实际上自由选择婚配对象的理想却被司法制度及滞后的文化观念所牵制。直至一九三零年,情投意合的情侣在经济上和法律上仍无法摆脱父母对婚姻的安排。在二十世纪初,小说诸如符霖的《禽海石》、吴趼人的《恨海》开始聚焦于父母之命与年轻一辈的进步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林倩玉和情劫生正好属于这新的世代,在社会风气开放的空气里成长,受到个体情感及自由婚姻等西方观念的熏陶。学者普遍认为周瘦鹃的爱情小说大多揭露旧式媒妁婚姻的罪恶,可是《留声机片》含有一个微妙的差别:它的重心有所转移,不单只描写家长专制所引起的悲剧,更触及都市新式“核心家庭”自身的脆弱与危机。
林倩玉出身于有产家庭,受过教育,又嫁给一个富有而体面的男子。然而她过着灵魂和肉体分裂的痛苦生活:外表上屈从命运,内心里对情劫生仍忠贞不贰。在周氏小说里的女性无论顺逆,不外乎“贤妻良母”的模型,体现其核心家庭的伦理观以及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愿景。上世纪初周氏撰文赞美“华盛顿妻子”和“华盛顿母亲”,至一九三二年创刊《新家庭》杂志,那是以欧美《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s Journal)、《家庭良友》(Women’s Home Companion)、《现代家庭》(Modern Home)等杂志为蓝本的刊物。他的娱乐取向与民国时期的国族主义和个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或相得益彰,或貌合神离,使我们不难理解周氏在《〈新家庭〉出版宣言》里强调日常生活中舒适家庭的重要性。所谓“家庭乐趣”,如维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在《家庭观念简史》(Home: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1986)这本书里所说,这一概念植根在资产阶级意识里,具有特殊的历史涵义。周氏的家庭价值观却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在林倩玉的个案中,他说:
伊的嫁与别人,并不是有意辜负他,只为被父母逼着,委曲求全,不得不这样混过去。伊原打定主意,把自己分做两部,肉体是不值钱的,便给伊礼法上的丈夫;心和灵魂却保留着,给伊的意中人。
并非偶然,几乎与《留声机片》发表的同时,周瘦鹃在《我的家庭》一文中隐约透露了他自己的不幸初恋,与小说里男女主人公的遭遇相似。作为有妇之夫,他不讳言其感情另有所属,而若隐若现地散见于他的作品里的“紫罗兰”似乎就是指那个初恋情人。周氏一向宣扬“高尚纯洁”的爱情,然而当他的罗曼哀史不断流播时,他的爱的世界变得飘摇起来,置身于感情与伦理的冲突之中,蕴含了某种中产阶级意识的两难困境。林倩玉的疯狂而香销玉殒的结局,质疑了“贤妻良母”的范式和“小家庭”的理想,也隐含了矛盾的性别政治:一方面女性的闺阁空间被资产阶级意识所编码,可另一方面这样的家庭理想却伴随着作者的终身痛楚而暗潮汹涌。
情劫生这一角色也充满矛盾。作为一个自我放逐的情人,与周氏的创作经历相对照,意味着他的爱国情怀的褪色。一九一五年,针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约,周氏义愤填膺写了有名的中篇《亡国奴之日记》,其中悲剧的主人翁自国土沦入敌国之手以后,逃遁到太平洋上的岛屿,倾诉其满腔忠诚。情劫生远离故土,同样来到太平洋孤岛上,对周氏而言更是个政治倾向的转折,可跟他对民国政治的失望联系起来。二十年代上半叶他编辑《申报·自由谈》时,几乎每日在时评专栏中指着总统、军阀及国会议员的鼻子骂,抨击他们祸国殃民的行径。
在情劫生来说,对国家的疏离尚在其次。在太平洋孤岛上他面对世界,更具讽刺的是与文明的秩序相疏离。从晚清以来有关“岛”的知识往往由报纸、期刊和文学翻译所传播,伴有异域风情的想象和本土身份的焦虑。同样的,在当时的小说如曾朴的《孽海花》之中,海的形象也牵连着中国人对全球及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想象。在运用“恨岛”来形容遗憾与悔恨时,周氏妙想天开地把整个世界变为一个“情场”―失恋者以苦为乐的乐园。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情”的本土论述被“普世化”,而“中华民国的情场失意人”被聚焦于这一微型世界的舞台中心。“恨海”即“情场”的意象让人联系到吴趼人的代表作《恨海》,但《留声机片》讲述爱的劫难如何透过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科技复制成文化产品,带着他魂归故园,加剧了当地的悲剧,使他的情人更为伤心欲绝。
在描述绝望的恋人的同时,在叙事者的犬儒口吻中,那岛屿变成一幅巨型俱乐部的讽刺画,邀请读者进入环球经济和离散的空间:
这恨岛直是一个巨大的俱乐部,先前有一二个慈善家特地带了重金,到这里来,造了好多娱乐的场所,想出种种娱乐的方法,逗引着那些失意的人,使他们快乐。虽也明知道这情场中的恨事,往往刻骨难忘,然而借着一时的快乐,缓和他们,好暂忘那刻骨的痛苦,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至于文明国中的一切公益事业,岛中也应有尽有,并不欠缺。这所在简直是一个情场失意人的新伦敦、也是一个情场失意人的新纽约。
本来这个小岛由“青天碧海,瑶草奇葩点缀成了一个世外桃源”,加上这个犹如迪斯尼乐园的“巨大的俱乐部”,不难想象,对于那些情场失意者不啻是个疗伤的天堂。然而作者似在戏弄读者的美好期待,继续告诉我们,岛中居民有十万人左右,来自美、英、法、德诸国,及欧美邻近的国家,包括少数非洲黑人和美洲红种人,“内中男女七八万人都是各国失意情场的人,其余是他们的家人咧、婢仆咧,和一般苦力。就这婢和苦力中间,也很有捱过情场苦味来的”。事实上这个幻想世界跟现实的“文明国”相差无几,像伦敦、纽约一样,被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制所主宰,那一二个好心的“慈善家”以“重金”投资建造了好多娱乐场所,并想方设法用种种方法给居民带来了快乐,实际上是通过失意者的情感消费来获得赢利。情劫生要求百代唱片的一个“分公司”为他录制唱片,即是一个细节。唱片公司的“工师”来帮他录制,当然是收费的。情劫生特地关照他还有三千块钱,除了支付唱片制作的费用之外,做他的丧葬及其他之用。这一细节有现实根据,上世纪初上海就有“法商东方百代公司”(Pathé Orient)的分公司,且推出新型“金刚钻针”留声机,更坚固耐用。周瘦鹃自己乐此不疲,说到《留声机片》的创作灵感:“近癖留声机,朝夕得暇,每以一听为快。机片转处,歌乐齐鸣,几疑身在梨园中也。日者谋草说部,思路苦涩,适闻留声机声,忻然若有得。走笔两夕,遂成一篇,题曰‘留声机片’。抒写哀情,差能尽致。于以知小说材料不患枯窘,端赖吾人之随时触机而已。”(《申报》,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这篇小说似得自神来之笔,可见他的得意情状。
想想也可怕。大多数失意人荷载着心灵的创伤,尽管岛上风景如画,享乐设施齐备,却难以遮掩他们内心愁云密布的风景。小说里反讽处处皆是。他们逃避痛苦而来到岛上,如情劫生的故事一样,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各有家庭社会的原因,不同程度受到现实的压迫,但随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婢女、仆人及苦力,在他们的小世界里,仍然维持着阶级秩序。更惨的是多数婢女、仆人及苦力也在恋爱上遭受失败,来到岛上仍然不得不服从阶级的压迫。同样在岛上有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各种肤色的民族,也有着种族之间高下的差别。情劫生因为信仰基督教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遂使他有别传统小说里“为情而死”的才子类型。他心地善良,孑然一身,与一个哑巴孩子为伴,临终时给了三百块钱,回报他的侍候。他对林倩玉也不抱怨恨,每每望洋兴叹,心念她“身体可好,可能享受夫唱妇随的真幸福”。但上帝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灵上的宁静,却一味守着他的情殇而不能摆脱。显然在岛上他不快乐,从不涉足娱乐场所,八年后郁郁以终。
当林倩玉收到唱片之后,故事进入高潮,焦点由男主角转移到女主角,错综复杂的冲突终于爆发了。最后镜头在她的闺房里,留声机正播放着,她倒在留声机旁。这里呼应了小说的开首,以留声机片来比喻林倩玉的心。当她听到情劫生的临终之言,她的心确实破碎了:那唱片仍旧漠然地在唱盘上转动着,然而好像她的心,被金刚钻针头碾碎。这不仅是个巧妙的比喻,联系故事的结构,这结局给处于公私空间夹缝里的女性身体添上了新的意义。
林倩玉对自己辜负了情劫生深感悔恨,读者不难看到她的破碎的心就如留声机片一样的脆弱,从而质疑她的家庭空间的安全性。她的心碎是精神上的,却被突如其来的外来风暴所击碎。她的婚姻不完美,但她逆来顺受,像一般的城市核心家庭,既免除了传统大家庭的麻烦,也无须在社会上谋生,她能享受她的闲暇与私密空间,保持失恋的秘密,沉醉于甜蜜的初恋的回忆中,她的丈夫经常外出,如影子般只在她疯掉的时候才出现。留声机能为她解闷,或许只是一个摆设,然而留声机片却是流动的,它由情劫生寄来,在他录制过程所涉及的外在关系,牵涉到环球资金和现代科技的力量,情殇的记忆被工业技术复制成一件文化产品,也是一件被打上了资本烙印的商品。当它经过现代交通线路而来到她那里,他的身体在空间上和文化上被卷入内外交织的权力网络。久经压抑的爱情被激活,遇到宣泄的窗口而一发不可收,同时她本来脆弱的心灵、隐秘的空间一旦与象征着现代机制与权力的外在世界遭遇,她的整个世界撕裂了,所有内在的问题曝现出来,日常的小玩意儿变成了可怖的器具,旋转的留声机片作为碾碎心灵的意象显出特别诡异的特质。
从社会寓意的角度看,《留声机片》显示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中产阶级个人处于内外、新旧的夹缝中的窘境。在发表这篇小说三个月后,周瘦鹃所主编的《申报·自由谈》继《小说特刊》之后,开辟《家庭周刊》,后继以《家庭月刊》,数年间刊登了大量以主张“模范”、“小家庭”为中心的论述,代表了旧派以维多利亚式资产阶级社会为蓝本的发展愿景。但《留声机片》却折射出周氏内心的挣扎,如林倩玉的爱情与婚姻的不幸似乎意味着某种先天不足,在本土的政治经济环境里个人自由的实现困难重重。她的留声机片一样的脆弱的心的意象,以女性的闺阁如坟墓作为悲剧的结局,揭露了她内在的不安和动荡的同时,也让我们从内而外―从她的破碎的心―来张望外在的世界。虽然情劫生逃离本土,生活在伦敦、纽约般的新世界里,但在快乐的消费主义统治底下,充斥着剥削与不平等,他得不到心灵的归宿。同样对于周瘦鹃来说,他所代表的个人的声音极其微弱,不仅其“消闲”主张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打击,《留声机片》中娱乐与死亡相伴,也不无自我揶揄的成分。事实上当周氏与他的同仁们在津津乐道都市“小家庭”之时,内乱无已,民族革命运动不断高涨,他们也不得不亦步亦趋。
小说里男女主人公看似软弱,但那种基于个体爱情、讴歌私密空间的美学表现正是现代主义的精髓。这篇小说可看作传统“为情而死”的爱情故事的现代改版。两人通过死亡而获得精神的合一,犹如《孔雀东南飞》里坟墓旁的两棵树,其枝叶在空间里连接为一体。情劫生别无选择,不得不通过商品和机械的帮助,使他的心灵回到家园和心爱者身旁,如此借以坚持纯情,面对外在的压迫保持其坚韧,也属一种抗争。
就叙事形式而言,《留声机片》糅合了写实、寓言和抒情的多样元素,是一篇结构完整、令人感动的小说,与茅盾所说的“记账式”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与其主张的自然主义也大相径庭。至于作品是否含有艺术的真诚,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它出现在新旧文学论争之际,明显留下抗拒以白话单边主义与科学写实主义为新潮标识的印痕。这篇小说是周氏形式上不断实验的产物,不受所谓客观写实的局限,而运用奇幻寓言的想象,语言上保持抒情传统,不像他的某些作品过于煽情或滥用典故,而反讽成分的加入更显得有所节制,其中交汇古今中外多种文学与文化资源,演化为一种杂体小说,一种集合着全球视野与在地政治的文学现代性,在这方面用欧美的形式和美学来衡量其优劣是完全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