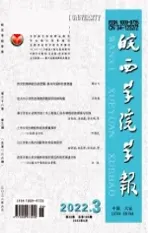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和学习动机的关系研究
2014-01-01梁端俊
李 林,梁端俊,2
(1.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239000;2.滁州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安徽 滁州239000)
《大学英语课程要求》(修订版)要求英语教师在课程设置、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注重为学生提供英语输出机会,以提高学生的有效交际能力。然而,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却发现,多数学生面对口语输出机会时要么选择沉默,采取回避的策略,要么被老师点名后,三言两语,说几句应付课堂交际的口水话。这就表明,学生自身是否愿意充分利用这些互动机会是他们进行目标语输出、提高语言能力的一个决定性内因。所以,对大学生的英语交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研究综述与目标
二语交际意愿是指“个体运用二语,在特定的时刻、与特定的人(群)主动进行话语交际的自愿性”[1](P547)。MacIntyre等认为,“二语交际意愿是一种动态的情境变量”[1](P546)。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明确哪些因素能导致二语交际意愿发生变化。
在二语交际意愿的众多先导因素中,学习动机受到了广泛关注。Hashimoto[2]针对就读于美国高校的日本留学生开展实证调查。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学习动机对二语交际意愿能产生直接的正向效应。MacIntyre等[3]进行的相关性分析也显示,不论加拿大学生是否参加沉浸式法语学习项目,学习动机和二语交际意愿都呈现显著性正相关。然而在Yashima[4]的研究中,学习动机对二语交际意愿却无法发挥预测作用,只能借助于二语交际自信这个潜变量对二语交际意愿产生中介效应。
国内外语界对交际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以交际意愿和学习动机的关系作为研究重心的实证调查更是寥寥无几。Peng和 Woodrow[5]考量中国大学生在课堂内表现出的外语交际意愿。方程模型显示,学习动机和交际意愿之间不具有直接相关性。而在谢都全、郭应可[6]的调查中,中国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却能显著预测其英语交际意愿水平。简言之,围绕二语交际意愿和二语学习动机的关系问题,学界仍未达成共识。
前人研究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对本研究产生极大的启示,但也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背景较为单一,多在国外双语或二语学习环境中展开。MacIntyre等[1]指出,只有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下开展交际意愿研究,才能更清楚地把握交际意愿和先导因素之间的关系,提高交际意愿理论的科学性。同时,研究设计多为单一式定量设计,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量化数据,缺少更具解释力的质性描述数据。此外,研究工具未能实现本土化,多直接采用国外学者针对二语学习者编写的测试量表,缺少结构效度检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针对上述不足,本研究拟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设计来探讨外语环境下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自编和改编的问卷量表,使研究工具能如实反映中国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心理特质,并借助试测,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和信度检验,以保证所得数据的可靠性。此外,将对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验证和补充定量研究获得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共120人,分别来自安徽省3所本科院校。专业的覆盖面尽可能具有代表性,性别选择上男女生大致平衡。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07份。问卷调查结束后,从有效问卷中随机选取了4名学生作为访谈对象。
(二)研究工具
1、问卷
(1)英语交际意愿量表:该量表借用了前期研究中已设计成型、且通过结构效度和信度检测的问卷[7]。量表要求受试评价自己与不同人数的交际对象、在各种交际场景中具有的交际意愿水平。记分方式为里克特五分制,1表示总是不愿意,5表示总是愿意。
(2)英语学习动机量表:本研究采用的动机量表参考了Gardner[8]编制的二语学习动机量表,删除并修改了部分题项,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实际状况。量表采用了里克特五级计分形式,以“完全不赞成”(1)到“完全赞成”(5)为反应选项。
为验证结构效度和信度,笔者对改编过的英语学习动机量表进行了试测。KMO值为0.816,Bartlett球体检验的显著水平为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于进行因子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抽取出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别将其命名为“融合型学习导向”“工具型学习导向”和“对学习环境的态度”,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为67.141%,全部项目负荷均在0.553之上,高于0.30的可接受值,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3部分的 Cronbach'sα值分别为0.760、0.755、0.702,内部一致性较高,符合统计要求。
2、访谈提纲:由4个开放式问题组成,旨在让受访者对问卷答案进行解释,从而验证和补充定量数据。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卷随堂发放,学生自愿选择是否参加。问卷回收后,笔者对4名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语言使用中文,并全程录音。
将问卷作答输入电脑后,首先运用SPSS 19.0对各量表进行描述性统计,并运用皮尔逊积矩分析来检测3种动机因子分别对英语交际意愿产生的效应;再次,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写,归纳文字信息,对重复出现的归因进行命名,为定量数据的分析提供质性参考。
三、研究结果
(一)对英语交际意愿和动机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1数据,受试在英语交际意愿量表上取得的均分为2.62,融合型学习导向为2.46,工具型学习导向为3.61,对学习环境的态度为2.45。这说明,学生不太愿意主动参与英语交流,缺乏对英语世界文化的认同感,学习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功利性需求,且对英语学习环境感到不满意。

表1 对英语交际意愿和动机因素的描述统计量
(二)动机因素对英语交际意愿的效应
皮尔逊积矩分析(表2)显示,在3种动机因素中,只有学生对学习环境的态度和交际意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366,t=0.001<0.05)。这表明学生对英语学习环境的态度越积极就越乐意使用英语交流。而融合型和工具型学习导向尽管也与英语交际意愿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但都未达到显著性(p=0.178,t=0.121>0.05;p=0.223,t=0.051>0.05)。

表2 动机因素对英语交际意愿的效应相关性(N=107)
四、讨论
(一)英语交际意愿和融合型学习导向的关系
数据显示,受试的英语学习动机缺乏融合型导向,且英语交际意愿与融合型学习导向相关度最低。访谈结果表明,这可能与受试所处的外语学习环境有关。由于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直接交往的机会甚少,所以对本族语社区的文化形态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因此不太可能产生内部认同感和外部趋同行为。例如,学生某峰在解释缺乏口语练习动机时谈到:“我又不准备出国,对西方的东西又不感兴趣,根本不需要练口语。”当然,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英语学习者能间接接触到一些异域文化。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理性引导,这种文化输入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面,难以成为启动和维持外语学习过程的原动力。正如学生林某坦言:“看好莱坞大片时都被剧情吸引了,哪还想去学英语?”
(二)英语交际意愿和工具型学习导向的关系
尽管受试者的英语学习动机呈现出清晰的工具型导向,但这种导向和英语交际意愿之间没有显著关联。通过对访谈结果的整理,笔者认为,这一结果可归因于测试的消极后效。对于绝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而言,通过四、六级考试是其学习英语的主要动力。然而,英语等级考试仍基于笔试形式,口语考试并未作为必考项目全面展开。研究表明,测试本身是否具有强制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反拨效应,比如,考生对待考试的态度,备考的积极性等[9]。因此,大部分学生将精力几乎全部用于对笔试项目的操练上,忽视了对口语能力的训练。例如,学生某浩在评价自己的英语交际意愿水平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现在,过四级才是王道!语法是我的弱项,那些时态和从句弄得我头都大了!每天,除了学专业课,就在做语法和模拟卷,根本没精力练口语。”
(三)英语交际意愿与对学习环境的态度的关系
在3种动机因素中,只有学生对学习环境的态度同英语交际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本研究中,受试者对现有的学习环境不太满意,进而缺乏主动参与英语交流的愿望,不利于其中介语的发展。定性数据显示,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学习者的情感诉求无法从学习环境中得到给养(affordance)而造成的。按照教育生态学的理念,教育是“一个由多种因子有机相连、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10](P60)。为了使该系统能够良性发展,教师需要在认知和情感2方面向学生提供给养。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囿于讲授语言知识、进行语言示范,即只注重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很少借助于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表达对学生的理解、包容和支持。尤其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往往被尊为专业权威,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这种等级制思维模式严重阻碍了向学生的情感诉求提供给养。学生自然对学习环境产生负面的认知心理,丧失主动学习的愿望。例如,当被问到是否对学习环境感到满意时,学生某宇就反问道:“老师教,学生学,天经地义。什么满意不满意,谁会在乎呢?”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和学习动机的关系,结果如下:
融合型和工具型学习导向与英语交际意愿之间均不具有显著关联。但考虑到2种学习导向均与英语交际意愿之间呈正相关,所以对这2种动机变量采取干预措施,并借此激发英语交际意愿也应具有可操作性。为此,语言教师可以通过校际交流与合作、开设西方文化课程引导学生对英语社会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增强其融合型学习导向。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对语言教材的遴选,教学活动的设计,使口语教学与学生的职业发展诉求一致,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口语学习的工具型价值,从而提高其参与英语交际的积极性。
学生对学习环境的态度同英语交际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因此,教师有必要消解自身的文化权威,满足学生的情感诉求,为学生创造一个共生互助的教育生态环境。比如让学生参与教学设计,体现教师对学生学习能力的信任;在师生互动过程中,通过适时正面评价,诸如微笑、点头、目光接触等非言语行为传递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和理解。当然,本研究虽然提出了激发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方案,但方案的实施效果还有待后续研究加以验证。
[1]MacIntyre,P.D.,et al.Conceptualiz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L2:A Situational Model of L2Confidence and Affiliation[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8(82):545-562.
[2]Hashimoto,Y.Motiv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s Predictors of Reported L2Use:The Japanese ESL Context[J].Second Language Studies,2002(20):29-70.
[3]MacIntyre,P.D.,et al.Talking in Order to Learn: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s[J].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2003(59):589-607.
[4]Yashima,T.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s and Affect o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J].Language Learning,2004(54):119-152.
[5]Peng,J.E.& Woodrow,L.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A Model in Chinese EFL Classroom Context[J].Language Learning,2010(60):834-876.
[6]谢都全,郭应可.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交际意愿结构方成建模分析[J].外国语文,2012(5):116-123.
[7]李林.对EFL环境下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实证研究[J].滁州学院学报,2014(16):99-103.
[8]Gardner,R.C.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M].London:Edward Arnold,1985.
[9]张新元.大学英语口语测试体系初探[J].外语测试与教学,2014(13):42-51.
[10]康淑敏.教育生态视域下的外语教学设计[J].外语界,2012(152):59-67,78.